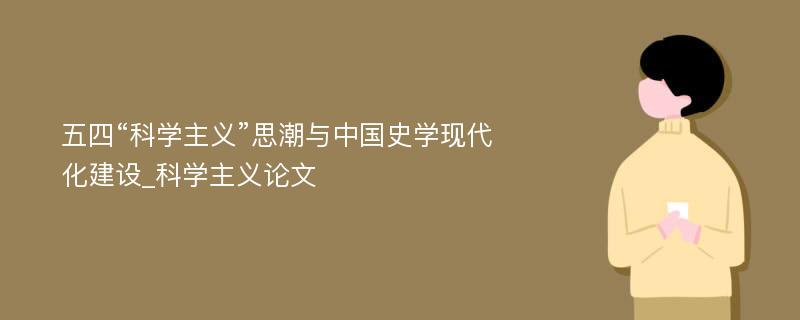
“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史学论文,思潮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开始其真正的建设性历程的。这场运动,不仅使数千年来的旧史观念受到了比二十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兴起时更为深入的批判,还为现代史学的发展直接注入了勃勃生机。而对其时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风靡一时的“科学主义”思潮。
一、科学与史学
“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主义”(有时也称“泛科学主义”),其根本宗旨,在于提倡一种新的人生观或价值体系,它渊源于十九世纪的西方。丹皮尔(Sin William C.Daupien)曾指出,十九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自然的宇宙的整个观念改变了,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类与其周围的世界,一样服从相同的物理定律与过程,不能与世界分开来考察,而观察、归纳、演绎与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但可应用于纯科学原来的题材,而且在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种不同领域里差不多都可应用。”〔1 〕即主张将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方法推广用以认识宇宙万物及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一切。这种观念,自十九世纪末便在国内渐渐传播,至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蔚为一种强大的时代学术文化思潮。
“科学主义”的深入人心,使越来越多的人确认,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2〕历史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如胡适就认为, 科学方法并非实验科学的独享之物,它对于历史学、考据学、语言学等研究也都是最有效的工具。傅斯年也主张“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3〕李大钊则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 在今日已无疑义”,它不仅要求“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4 〕从而建立起历史科学。即使是一些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巨大差异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的完备和饱满,我们仍旧可以把他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里面去。”〔5〕
依据这种认识,进步史家就推进历史学科学化的问题提出了种种看法。这些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强调学科建设及研究当有系统性。胡适就提出,“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6 〕并主张通过倡导所谓“科学的方法”来推进这一建设。李大钊且在《史学要论》中专立“历史学的系统”一节,对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内涵构成及各部分的关系作了详尽讨论,为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求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改变旧史家那种随意性和琐碎不当的习气,以科学方法重新梳理史料和总结前人治史方法,使之成为系统的知识或理论。
二是提倡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李大钊指出:“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7〕这就要求,对前人的记载或研究成果抱一种理性的批判态度, 不轻信盲从,“以批评的眼光,严密考查史料全部或一部,推翻许多向所认为可信的著作。”〔8〕而对研究者自己, 则尤应恪守实事求是的方针,使研究结果尽可能接近或符合实际。
为了增强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有人还提出了非功利主义的学术主张。1915年,任鸿隽等人便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提倡此道,说时下许多人读科学,目光均不脱物质功利一面,其实不然,因为“科学不以实用始,故亦不以实用终。夫科学之最初何尝以其有实用而致力焉,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此自然之势,无庸勉强者也。”〔9 〕“明乎科学的非物质的、功利的,则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矣。”〔10〕在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起而呼应。顾颉刚就认为:“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并声称自己治学信守的是“薄致用而重求是”之旨。〔11〕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则批评了那种以能否直接运用或现时运用的功利观念来确定学问价值的看法,说:“事物无大小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在他们看来,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功利性,易掺入主观偏见,从而干扰其求真与纪实目的的实现。
应当指出,这种非功利主义的学术观,正是“科学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如前所述,“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系由西学东渐冲积而成,而西方的科学观念本导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的流行观念中,科学乃是对于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的追求,它崇尚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即主张在研究中收敛有关实用的观念,以超越一切现实利害或道德价值的姿态,观察客观对象,使研究结果保持冷静和公正,而历史学,初因崇拜赞美英雄神灵或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教诲的实用需要而起,它所提供的只是始终处于无组织变化状态的经验事实,无法从中抽象出可确切证明的普遍判断或不变法则,故“根本上并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12〕近代以来,历史学既在西方渐被认作一门科学,受到科学精神的涵摄,则“为历史而历史”的观念自然会应运而生并得到强调。
诚然,“为历史而历史”、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完全排除主观因素而趋于纯客观的看法并不现实。因为任何人的思想行为都不可能超脱一定时代或阶级集团意识的局限,尤其是历史研究这类社会性很强的精神思维活动,更免不了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掺入主观色彩。但必须看到,这种观念在当时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否定了旧史学专以维护封建统治及其礼教纲常为务的功能观。由于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密控制,其研究的主导意识、内容乃至义例,无不以封建政治的需要为转移,以致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其本身的独立发展,故推进现代史学的建设,尤须提倡独立不羁的治学精神。王国维就指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治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与。”〔13〕显然,上述反传统观念的提出,对于克服旧史学过分依附于封建政治之弊,实为一种必要的针砭和“矫枉”,对于健全我国史学的学科独立发展机制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其次,它所倡导的纯客观研究,还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其时知识界破除迷信、追求真理的勇气。自然,求真意识并不倡自“五四”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上向以兼重“纪实”与“经世”号称于世,但对于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却始终未得到真正的厘清。“五四”时期的这种非功利主义学术观。则毫不含糊地提出应将两者的关系统一到“求真”的基点上,只要出于求真的需要,可以先抛开应用的念头。梁启超还说:“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14〕这些看法,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如进一步结合前引诸家的有关论述及其史学实践,作综合的观察,则可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本意并不在笼统地否认史学的社会功用,而在于强调:史学的功用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决不能因求应用而失去求真。
这里,还须特别注意一个事实,流行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是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在一派响遏行云的宣传、赞同声中,其实包罗着多种不同的政治和学术见解。作为一种史学思潮,也是如此。单就人们对“历史科学”内涵的理解与诠释而言,当时史学界就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亦为大部分人所信奉的“科学的历史学”,往往仅从运用新方法和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着眼,热衷于从事史料整理发掘和史实本身的求证,而忽视或根本否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寻。胡适、傅斯年、何炳松等人多持此说。其二,大体上依据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斯宾塞(Hebert Spencer,1820—19 03)、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之说去理解“历史科学”,倾向从社会学的宏观角度去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认为“历史的定律——史律——的确很没有标准,除了柏苦儿(即巴克尔——引者)一流人以外,其他的史家很少敢提及的。然而万不不能说没有,或者不会有。虽然人类活动非常复杂不定,但从‘大势’上观察出共同趋向和变迁线索,是很可能的。”〔15〕不过,持这种主张的人并未对如何寻求与解释“史律”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和深刻见解。其三,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力倡以无私无畏的科学态度和现代科学方法治史,还在确认历史学是一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的基础上,通过输入、传播和运用唯物史观,为寻求历史规律和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提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很明显,以上三种主张,尽管在倡导历史学的科学化方面有其一致的地方,但前二种至多只具有局部的科学意义(在某些方法或观念上),只有唯物史观的提出及其史学实践,才为历史科学的建立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二、现代史学的专业化建设
“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对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科学的观念大大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和创造性思维,而各种科学方法的运用又无不予史学以新的刺激与启动,由此促使史坛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空前活跃景象,一时思潮迭涌,流派繁兴,从各方面推动着史学的进步。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史学进步成就的,则是其专业化的建设。
自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二十年代末,我国现代史学在专业化建设方面进展迅速,这大致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一)、专业理论之探讨与构建。
中国古代史学,虽素号发达,然其时史家普遍之观念,唯以记载史事为重,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即使有所讨论,亦多属书法褒贬、编纂结构体例一类的经验性评论,很少构成体系,像章学诚这样在理论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并有系统发明的,实在只是凤毛麟角。“五四”时期,在科学思潮的启示下,进步史家深感,传统史学无论就观念还是内容看,有许多地方都不合现代科学的要求和社会之需。而欲改变此种落后现状,就须先变革旧史观念及其治学方法。为此,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受到了史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各杂志及出版社纷纷刊出有关史学理论的论著,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史学系或史地系,也把历史学原理、史学研究法、中国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历史哲学列为基本必修课或选修课,将其作为提高学生专业理论素质和培养现代史学人才的重要手段。
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著,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对国外主要是西方现代史学理论著作的译介。二是运用近代科学的眼光对传统史学方法的重新审视与系统总结。如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对乾嘉朴学方法的分析,何炳松《〈史通〉评论》(1925)、《章学诚史学管窥》(1925)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陈垣《校勘学释例》(1931)对传统校勘学的归纳提高等,皆其中的代表作。三是有关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及概论性的专业治学入门指导,如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1921—1927)和《历史统计学》(1922),李大钊的《史学要论》(1924),杨鸿烈的《史地新论》(1924),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1927)等。从内容上看,这些论著的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如何认识历史学本身及其社会功能。 这本是旧史家十分重视而又谈得最多的问题,但“五四”时期的探讨,则另有其特殊的时代特点,它反映了历史学的文化功能正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转换的趋势。鉴于旧史学一味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造成的种种弊端,不少人反对继续将史学充作“伦理教训”或“政治资鉴”的工具,认为其基本作用应是实事求是地弄清过去的真相及现实社会各种事物或制度的由来,以帮助人们认识并解决现实问题和推测未来。尤应改变旧史家治史仅注重政治生活的陋习,因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除政治组织之外,尚有经济、思想、自然环境……等等要素,都不可轻轻撇过。并且除非把这些要素研究清楚,我们对于政治变迁的根本原因也决不能了解。”〔16〕陈训慈的《历史之社会的价值》一文,则针对那种只看重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实用价值而轻视历史学的倾向,阐发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历史学的功用至少有四端:一、助成完全之智识;二、影响人类之心理;三、对社会进化起到引导作用;四、促进人类共同之了解。故“史断非繁重孤僻之学,而为最普遍之学识,与社会息息相关。”〔17〕这些论述的中心,都在于要求历史学从旧日专为统治集团“资鉴”的狭隘格局中解脱出来,使之真正成为一般社会大众所需之学问或知识。
(2)如何建立和完善现代史学方法论体系。 这是当时史学界讨论最多的问题。在众多的论著中,有的按照人们研究和认识历史的系统运动过程,详细地论述了从史料采集、鉴别、整理到史事分析和史著编写的方法,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等;有的致力于探讨历史学与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各种相关学科的关系,以及在治学方法上相互借鉴的可能,如陈训慈的《史学蠡测》(1924—1925)、李璜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1926)等;有的则结合治史实践,专论某种现代方法的价值和运用,如梁启超的《历史统计法》、卫聚贤的《应用统计的方法整理国学》(1929)等。这些讨论,对于现代史学方法在我国的进一步系统传播和运用,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如何看待历史哲学在认识历史中的作用。“五四”前后, 随着各种西方史学理论及哲学的传入,历史哲学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如缪凤林认为,史之目的在揭示社会演进活动之真实情况,欲达此目的,“非哲学固无由进窥其之真际也。”〔18〕李大钊更明确指出:“人生哲学或历史哲学,特有关于历史事实”,那种以为史家只能以超然虚静之智慧观察史实而“不宜豫存一先入为主的历史观”的看法,其实并不现实。因为“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治史实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19〕为了寻求一种“比较完满的历史观”,一些史家进而对古今中外各种历史哲学或史观作了认真介绍、比较、分析和批评。如陈训慈在《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中,结合中西史学的发展状况,对美术史观、宗教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综合史观等十一类历史观作了考察评介,以“求其变迁之普通趋势。”〔20〕不仅如此,朱谦之的《历史哲学》(1926)等还对创建新的历史哲学体系作了尝试。
“五四”时期重视史学理论探讨的风气,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其时丰富多彩的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显著标志。而其总的倾向,则是要求在兼取中西史学之长的基础上,构建起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史学新体系。
(二)、专业研究机构之设置。
我国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文史专业研究机构,是“五四”以后首先在高等院校出现的,其中最早当推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该机构成立于1921年底,初由沈兼士任主任,下设编辑室、考古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致力于分途搜集各项材料,并招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二十年代中后期建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1929)、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1931)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1932)等,也都属这种性质。至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始有国家行政当局系统的专门研究机构出现。与此同时, 一些地方也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 如1929年筹建的国立北平研究院,其下亦设有史学研究会,计划主要从事《北平志》、《北方革命史》、《清代通鉴长编》的编纂和地方考古工作。
这些专业研究机构的设立,为推进各项史学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通过这类按现代科学观念组建起来的研究机构,可以使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得到合理协调,变原来分散的个人研究为各学科专家的通力协作,以便对某些高难度课题展开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如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就聚集着当时国内不少第一流专业人才。其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体质、语言、风俗、文物、制度以及安阳殷墟发掘物的整理研究,也正是依靠这些专家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各方面进行研究,才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次,初步确立起我国现代历史学发展的社会规划机制。这些研究机构一般都制定了较长远的科研计划。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即由马叙伦起草了一项《整理国学计画》,提出从系统整理各类学术资料和研治传统学术两方面入手清理文化遗产的计划,并规定了搜集文献和文物古器实物材料的具体步骤方法。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在考古发掘、整理旧档文献及调查民俗资料、语言及方言变迁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划,虽然这些计划因其时政局动荡和战乱之故,在实行过程中不免时作时辍,但其积极影响和作用仍不可低估。第三,便于动员行政当局和社会其他力量,从物质上为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研究项目提供必要条件。如1924年以后,北京大学研究国学门的考古学会组织人员先后调查北京大觉寺、大宫山古迹、碧云寺古冢、圆明园文渊阁遗址、甘肃敦煌古迹。与此同时,还利用各种关系,向社会征集图书和古器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搜集了金石、甲骨、玉器、砖瓦陶等古物4.087件,金石拓本12.553 种。1929年,又与北平研究院及古物保管委员会合组考古团,发掘燕下都故址北之老姥台,获得了大量古代兵器、钱币等采集品。尤其是中央研究院,更实施过不少大型学术研究规划,如在民族学研究中,先后组织调查了广西瑶族、湘西苗族、东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浙江畲族、云南傣族,,以及贵州、四川、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风习、制度和古代羌、戎等族遗迹。至于其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些学术活动,如果没有学术上、物质上具有相当实力的专业研究机构从中主持,完全是不可能的。
(三)、专业学会和专业杂志之增多。
历史专业学会的大量出现,是近代世界各国史学走向专业化和学科独立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虽然二十世纪初这类组织就零星出现过,如成立于1908年11月的湖北史学会等,但往往随生随灭,远未形成风气。“五四”时期,随着史学专业队伍的日趋形成和扩大,史学界对于建立专业学会的呼声始高。1921年,陈训慈在《史地学报》发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专就此事作了讨论。他认为,在中国,“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新史学之声虽日见其盛,然其发展仍存在诸多不尽人意处,尤缺乏“专精之研究”。因此,应通过建立专业学会一类的学术团体,动员组织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力量,分工合作,将历史研究推向系统和深入,“诚使有史学会为之中心,于古文化为忠实之研究,以发现完全之过去,则必可畀中国文化以正当之地位。”文中,他还从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促进清史编纂及注重当代史料搜集等六个方面论述了史学会的任务,主张“参酌西制,以为规画。至其着手组织,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其后,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等文中一再发出类似的呼吁。在此前后,一些大学史地部或史学系的学生首先对此作了尝试。1920年,北京、南京和武昌三所高等师范学校的有关专业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史地研究会和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改为文史地学会),出版了会刊。1922年11月,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也成立了史学读书会,设立九条章程,规定以研究中外历史、科学史和考古学等为宗旨。此外,还有1927年成立的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和稍后的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等。上述学会中,以南京高师的史地研究会组织最为完备。该会前身为1919年成立的地学研究会,次年5 月改此名时,有会员73人,以后每年略有增减,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掞藜、束世徵、向达、 王玉璋、范希曾等皆其中骨干。研究会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絅、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讨论等各项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学会的不少会员后来成了国内史地学界的知名专家,1926年成立的中国史地学会和其后的中国史学会,也正是以这些人为骨干的。至1932年10月,北平各大学史学系师生还联合发起成立了地区性的专业学会“北平史学会”。
这些专业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会刊。除上面提到的《史地学报》外,还有北高师史地学会的《史地丛刊》、武昌师范大学文史地学会的《文史地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的《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史学杂志》,如果加上其他一些单位主办的史学杂志或以史学为主的国学杂志,数量就十分可观。这些学术专刊,把国内学报类刊物的编辑出版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使大量运用新史料、新方法、新观点的专题研究论文和其他成果得以及时贡诸于世,有的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其中的《史地学报》、《史学年报》,以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国学论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专刊和集刊等,对于史学界树立严谨扎实的治史风气,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总之,历史学会和各种专业杂志的纷纷出现和持久活动,不但使我国现代史坛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活跃,且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各项专题研究的深入,乃至整个史学专业化的建设,都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新旧史料的发掘和科学整理
在这一时期的史学实践中,受现代科学观念影响最为直接而成就最突出的,莫过于对各类新旧史料的大力开掘和整理。这是因为,各派史家对历史学科学化的理解尽管有所不同,但在运用现代方法重新厘清和认识史料,以为重建信史之基础方面,则保持着基本一致。故无论是倡导“疑古”的古史辨派还是稍后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其工作重心都不出史料学范围,而新考证派诸大家的成就,也无不与新史料的发现和运用有关。
在新史家看来,重新厘清和认识史料,首先应更新陈旧的史料观念,旧时代那种“宗经矩圣”、重正史官书轻稗官野史的做法显然已不合时宜。要使历史研究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就必须以现代科学之眼光或标准,对一切可利用的材料重加审视。其次,应从总体上拓宽史料的范围。不仅要注意一般的史部文献,而且要留意从诗文、说部、宗教典籍,乃至神话传说等其他类型的书籍中去找出反映各时代社会真相的史迹;不仅要充分运用现存的文字资料,更要重视对金石、前代遗址遗迹和现代考古发掘等实物资料的运用,开阔视野。第三,尤应在广泛搜罗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客观系统的辨别、整理和考释。如马叙伦在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拟的《整理国学计画》中便提出,我国传统学术遗产虽丰,但以西方现代科学视之,不免有“浑沌紊乱之景象”,“故今日欲阐扬吾国固有之学术,其道尤要于先整理”,当“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补助”,〔21〕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各种文献和考古实物,方能推动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进步。朱希祖也认为,应将中国古书中有关历史、哲学、文学,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建筑、制造等记载“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其法“最要者是分析、比较、综合;而尤要者在乎经验。”以历史研究而论,“先须考核事实,用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顺序排比,然后以历史、哲学,及法制、经济等科学的眼光说明之。不合于事实的空议论,一概排斥。”〔22〕
依据上述认识,史学界围绕着现代史科学的建设,从两个主要的方向上,展开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是科学考古及各种实物史料的发掘整理。“五四”以后,各研究机构和史学会都将考古发掘和实物史料的收集整理列为工作重点,认为“吾国一二出土之物(如殷墟甲骨、敦煌石室、流沙坠简等)已大有助于历史,果能从事开掘,必能多所发见。”〔23〕故当“应用考古学的方法,整理实物,以发现古代之风俗制度、文物艺术。”〔 24 〕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称考古学会),率先对河南新郑和孟津铜器出土地和西北敦煌古迹等展开了有组织的实地调查和文物搜集。1926年,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受过现代人类学专门训练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以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合作的名义,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事后写成《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有关材料后经从国外攻读考古学归国的梁思永整理研究,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中之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运用地层学原理等科学方法在国内主持的田野考古,它标志着中国的考古已完全突破了传统金石学的格局,开始真正进入了科学发掘时期。
从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我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取得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主要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相继发现,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山东历城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西北考古发现等。这些发现,不仅为我国史前史、古代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史料,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大大推进了考古学与其他相关新兴学科的建设。如通过殷墟的科学发掘,梁思永在《后冈发掘小记》和《小屯龙山与仰韶》中记录并论述了考古发掘中按土色、土质划分地层的方法及其重大发现。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则结合其参与实地发掘的收获,系统地提出了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弥补了罗振玉、王国维甲骨之学的不足,从而大大增强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甲骨文的科学性,他的《殷历谱》还大体上解决了殷周王朝的历年问题,奠定了中国上古史年代学的基础。而对西北考古发现的文书文物的整理研究,则直接促使了简牍学和敦煌学二门新学科的兴起。
其次,是对于文献史料的征集和系统整理。在致力发掘考古实物史料的同时,史学界还加强了文献史料的搜寻整理。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后人经常提到的明清内阁大库和军机处档案、流失国外的太平天国文献等新发现的史料,即使是对大量旧有的典籍和文献资料,一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高校也纷纷组织人力,展开了积极的整理工作。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伊始,便制定了访书、购书、抄书、调拨、征书等一系列搜罗文献之法和整理汇编丛书、辑逸及校刊旧籍的计划。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也提出“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的口号,主张采用现代的治学方法,为古书、古文献编纂索引。此后,何炳松也在《史地学报》发表《拟编中国旧籍索引例议》。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则专门设立古籍校订组,“以校订及整理群经以下诸典籍,辨别真伪,纠正错误,藉以发现前人著作之真面,并刊行整理贯穿便利学者之书籍为宗旨。”〔25〕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则对大量古代史料和历史记载作了考辨。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燕大中心国学研究所所长的陈垣还提出了一套较全面整理文献资料的方法和具体设想。1929年,他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发表了题为《中国史料的整理》〔26〕的讲演,主张“改良读书的方法,整理研究的材料,使以最经济的时间得最高的效能。”并分史籍、档案两类材料的整理论述了具体方法。在史籍方面,提出八条措施,除对古籍进行新式标点、分段和改进工具书的偏写与书籍装订外,还应为所有的笔记和文集编写目录、总目及索引,并编出群书篇目汇纂(即将“所有重要书籍的篇目按类编成一部总目,使人一检即知某书的内容”)、重要书籍索引(“把每一部重要书籍的内容凡是有名可治的,都编成索引,使检查者欲知某事某物系在某书之某卷某篇,皆能由索引内一索即得”,实即后来之引得)、分类专题编集(按专题内容将各书中相关材料均编集一起)等大型系列检索工具书。档案整理则可分为八个步骤,依次是分类(按种类、形式或文字等分)、分年(按年集中,顺时排列)、分部(如兵部、礼部等)、分省、分人、分事、摘由(摘出每一文件事由)、编目。并说,倘若能够依着这种方法整理下去,便能使原来浩繁零乱的中国史料变得渐有头绪,从而为史料的运用和历史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收到“一人劳而百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之效。这些提议,得到了史学界不少人的响应。其时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组织的“明清史料编刊会”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时,工作程度便系据上述“整理档案八法”制定。特别是哈佛燕京学社,1930年起在洪业和聂崇岐等人的主持下,参照上述计划,大胆实践,精心组织编写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古代典籍及有关研究文献的检索工具书《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包括群径、先秦诸子、前四史、历代艺文志和食货志、《水经注》、宋至清人物传记、道藏、佛藏、《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引得共六十一种,为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上述新旧史料的发掘和科学整理,无疑给我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骋驰战场。正如当时王国维所说的:“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日之时代,可谓发现之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27〕正是新史料与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结合,促使“五四”以后我国史学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崭新的时代面貌。
注释:
〔1〕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中译本第283页。
〔2〕陈独秀:《敬告青年》,见《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
〔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4〕〔7〕〔19 〕李大钊:《史学要论》,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1980年校印本第12、14、40页。
〔5〕何炳松:《历史研究法》,见《民铎》10卷1号。
〔6〕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见《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
〔8〕衡如:《新历史之精神》,见《东方杂志》19卷11号, 1922年6月。
〔9〕胡明复:《科学方法论》,见《科学》1915年2卷7期。
〔10〕任鸿隽:《科学精神论》,见同上2卷1期。
〔1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古史辨》第1册第25—26页。
〔1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第28页。
〔1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见《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1页。
〔15〕徐琚清:《谈谈历史》,见《燕大月刊》4卷2期, 1929年4月。
〔16〕齐思和:《论史学之价值》,见同上7卷1—2期合刊, 1930年12月。
〔17〕见《史地学报》1卷2号,1922年5月。
〔18〕缪凤林:《历史与哲学》,见同上1卷1号,1921年11月。
〔20〕见《史地学报》1卷1号。
〔21〕见《新教育》1921年3卷4期。
〔22〕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北京大学月刊》1卷3号,1919年3月。
〔23〕陈训慈:《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见《史地学报》2卷3号,1923年。
〔24〕〔25〕《国立中山大学现况》第271页, 转引自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56),1988年版第143—195页。
〔26〕文载《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
〔27〕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见《王国维遗书·静安文集续编》。
标签:科学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