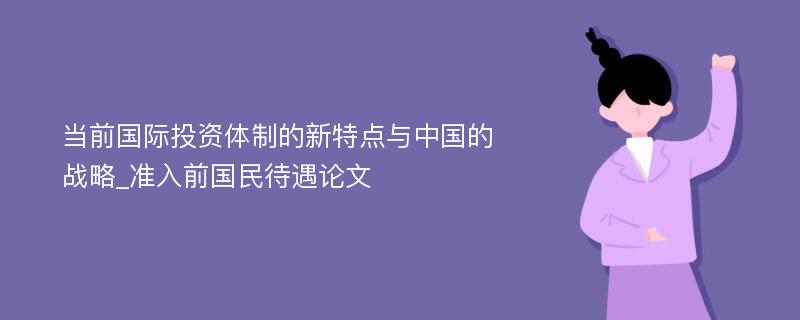
当前国际投资体制的新特点与中国的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际投资论文,体制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投资体制(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是近年来在文献中被使用得日益广泛的一个概念。纽约大学的阿尔瓦雷斯在分析国际投资体制时,表示其更倾向使用“体制”(regime)而非“体系”(system)或者“框架”(framework)的概念;而这里“体制”的概念与政治学家(包括国际关系学家)使用的“体制”概念类似。①阿尔瓦雷斯引述国际关系学大师基欧汉(Keohane)的定义说,“‘国际体制’是在国际关系的既定领域中存在的一套明确的或者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及决策程序,在此基础上各行为者的期望趋同”。②201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使用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概念。③哈佛大学的西蒙斯在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他的定义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促进及保护的一系列分散的(有时甚至是不一致的)规则”④。
无论如何定义国际投资体制,人们都不难发现它与多边贸易体系的一个很大不同:国际投资体制其实缺乏一个基本的多边框架,是一系列多边、区域和双边纪律以及单边规范的杂乱的组合。有关投资的多边纪律散见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世界银行的“华盛顿公约”和“汉城公约”等协议中。⑤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两次试图制定有关投资的诸边或多边协议的计划都以失败告终,但与此同时,制定多边投资纪律的呼声持续高涨。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谈判方兴未艾。双边投资协定目前每年新达成的数量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所减少,但一些重要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在进行或者计划之中,例如中美、中欧、美印的投资协定谈判都在进行之中或者即将展开。欧盟从2009年底《里斯本协定》生效之后,将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权力收归欧盟。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投资体制目前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时期。世界各国以及各个利益集团也都在争相提出自己关于国际投资体制走向的主张。尽管中国目前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但在国际投资体制的建设中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缺乏明确的主张和清晰的声音。为此,厘清当代国际投资体制发展的最新特点,有助于明确中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战略。
当前国际投资体制的新特点
从最近几年国际投资体制发展的情况看,有几个新的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投资保护谈判与投资自由化谈判互相融合,且后者的发展势头强劲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传统上是国际投资体制的主要形式,但是无论在英文文献还是在中文文献中,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保护”一词都在被淡化,更多被使用的是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s)的概念。究其原因,目前国际上的双边投资协定有许多实际上也起到了投资自由化协定的作用,而非单纯的准入后投资保护协定。对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影响巨大的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从1982年制定以来,于1994年、2004年和2012年三次修订,其宽泛的投资定义、全面的国民待遇要求(包括准入前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要求)以及以否定清单规定例外措施的方式,三者结合,实质上规定了一个“自上而下”(Up-down)的高标准投资开放义务。正因为这样,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不仅被美国用来进行投资保护谈判,也被视作投资自由化谈判的基础。该范本最后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第11章投资自由化规定的基础,也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多边投资协定》(MAI)的文本基础,最近又被美国用来指导其“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的投资自由化谈判。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标准进行投资保护谈判,实际上投资自由化谈判自然就被纳入其中了,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
以传统的双边投资协定为基础的国际投资体制正在发生变化,许多投资谈判发生在区域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REIOs)有许多都突破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区(FTAs)的谈判内容,纳入了投资议题。这些投资议题不仅包括投资保护的内容,也常常有投资自由化的内容。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不少经济伙伴进行了自贸区谈判,但是除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的非约束性承诺,中国在对外进行投资自由化谈判中实际上裹足不前,投资议题往往止步于投资保护方面,这大大束缚了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步伐。到2010年为止,世界上的对外投资存量大约有2/3处于某种国际投资协定(IIAs)的管辖之下,其中只有一半是仅仅处于双边投资协定管辖之下的,另外一半处于自贸区协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管辖下或者同时处于两类协定的管辖下,至少有630个双边投资协定同时也处于投资自由化协议的覆盖之下。⑥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进行投资谈判的时候,投资自由化议题成为了他们所期望的基本议题,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不断面临外方提出“准入前国民待遇”(Pre-establishment National Treatment,或者Pre-entry National Treatment)谈判压力的原因之一。
(二)美国式高水平投资保护与开放标准被接受的范围正在扩大
在投资自由化方面,美国投资协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基于否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即原则上在所有领域的外资享有不低于东道国内资的投资自由,特殊领域可以明确列出作为例外。这样的规定在20世纪连许多发达国家也无法接受,这也是1998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多边投资协定谈判流产的原因之一。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这类条款,并大量使用在自己的对外投资协议中。截至2009年,仅在亚太地区已经至少有26个自贸区协定中的投资条款包含了准入前国民待遇,涉及的国家既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发展中国家。印度虽然至今拒绝与美国达成这类协定,但却在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协定中纳入了这类条款。日韩在2002年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首次包含了以否定清单为基础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此后两国在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多次使用这类条款。⑦不仅如此,日韩在与中国的投资谈判中也强烈要求中国接受基于否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⑧
(三)卡尔沃主义有所回归但投资自由化进程仍在稳步发展
在国际投资法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倡导“卡尔沃主义”(Calvo Doctrine),主张国内法对外资排他的管辖权。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自主开放投资市场并且争相吸引外资的形势发展,卡尔沃主义逐渐退出政策舞台。根据“华盛顿公约”建立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ICSID)允许投资者私人主体就投资东道国的政策发起国际仲裁请求,这是国际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卡尔沃主义的背离。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发展中国家被大量的投资仲裁案困扰,开始重新诉诸卡尔沃主义。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声音,要求限制外资向东道国发起国际仲裁请求的权利。⑨
然而,卡尔沃主义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回归是有限度的。尽管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强烈要求美国在修订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时考虑限制投资领域国际仲裁对国内法的可能干预,同时对投资自由化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美国经过三年的反复酝酿,在2012年推出的新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基本没有推出这类限制条款。而与此同时,亚太地区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速,美国主导的TPP更是明确提出了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要求。
(四)各种类型投资协定并存交错,使得多边协调的必要性上升
尽管世界上有1/3的外资存量不受任何投资协定的管辖,但有不少投资关系同时被不同的投资协定覆盖。例如,前文提到的有630个双边投资协定同时被区域投资自由化条款所覆盖;另外有至少570个双边投资协定与其他投资协定在准入后保护问题上重叠。⑩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于2012年达成以后,三方相互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仍然生效。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与东盟签订的投资协定上。欧盟对外签订统一的投资协定后,其各成员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仍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效。这种投资协定重叠交错的现象必然隐含着大量的法律冲突,这使得人们需要考虑在投资领域多边协调的必要性。
(五)国际投资仲裁空前活跃,有关投资协定的实际作用日益显现
在1997年以前,国际上投资人与东道国的争端很少,ICSID在1997年以前的争端案例每年一般是1~3个,有时甚至没有争端案。1997年以后,ICSID的争端案每年都是两位数,到2011年已经高达37个。(11)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国家与国家间的仲裁机制,许多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也有自己的仲裁机制,这些机制下也都有不少案件。争端案件的大量出现显示出各种投资协定正在发挥实际作用。传统上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愿意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作为政策稳定的一个信号,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际发生的争端很少,因此法律风险有限。但近十多年来,投资争端案的大量出现使得有些发展中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例如,到本文成稿为止,阿根廷在ICSID被诉案件达到49起,阿根廷政府为了应对这些案件而投入的资源巨大,而且一旦败诉还需负担沉重的赔偿。(12)2011年,中国首次在ICSID成为被申诉方,马来西亚某公司因海南省政府收回其租赁的土地而将中国政府告上了ICSID仲裁庭。(13)该案虽然目前双方已经同意中止仲裁程序,但这说明对外签订投资协定产生的法律风险是现实存在的。
中国积极参与当前国际投资体制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上面总结的当前国际投资体制发展的一些新特点可以看出,一方面,投资自由化进程正在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以卡尔沃主义的复苏为表现,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约束投资人权利的呼声。但是,从根本上看,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仍是主流,无论是主张东道国公权的卡尔沃主义,还是某些国家出现的投资保护主义,都是在投资自由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出现的自然反应。发达国家以“公私冲突”面目出现的新“卡尔沃主义”,其本质是其资本外移后出现蓝领就业机会减少而导致的劳资矛盾。这些问题是全球化曲折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由于面临全球化进程伴随着的一些国家就业岗位流失、环境问题压力增大等矛盾,近年来各国采取的单边投资监管或限制措施有所上升,但与此同时,单边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仍然远远超过监管和限制措施,而且这些监管和限制措施有些恰恰是为了配合自由化措施而采取的辅助管理手段。(14)因此,在当前国际投资领域,投资自由化的主流趋势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以传统双边投资协定为主要形式的旧的国际投资体制面临着挑战。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的,当前的国际投资体制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约6100个互相重叠交错的投资协定已经如此复杂使得各国政府和投资人难以驾驭;另一方面如果要全面覆盖世界投资,至少还需要14000个双边协定。(15)正因为这样,双边投资协定正在被区域及国家集团层面的投资协定所替代。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计划”(TPP)一旦按计划达成投资协定,则可以取代现存的47个投资协定。欧盟实施统一对外签订投资协定后,大量现存的双边投资协定也会逐渐淡出。与此同时,在多边层次建立投资保护与自由化框架的呼声一直高涨。尽管这一进程已经几度受挫,但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目前已经日益显现了。
中国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方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中国目前已与大约130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在6个区域协定中包括了投资部分。1998年,中国在与巴巴多斯缔结的双边投资条约第9条中首次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将所有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在目前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大约1/5规定了准入后的国民待遇。这说明,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在签订投资协定时已经越来越自信。然而,这种进展仍然落后于当前国际投资体制发展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中国目前在投资自由化方面,一直仅仅依赖单边措施,在签订有约束性的投资自由化协定方面几乎没有作为,甚至在这方面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政策态度。
在目前国际投资体制的关键转型期,中国在国际投资自由化方面采取具有可操作性的立场,明确自身在国际投资体制建设中的角色,已经变得日益重要。首先,在国际投资自由化方面裹足不前必将阻碍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在目前周边国家纷纷加入或签订具有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的投资协定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仅仅包括贸易内容或者在投资方面只涉及准入后保护,都将降低这类协定的价值,从而出现贸易转移以及投资转移等不利影响。其次,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继续对多边投资纪律特别是国际仲裁机制和竞争政策进行研究和讨论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一直缺乏自己对多边投资框架的系统主张,必然使得自己在今后的多边投资纪律的制定中降低话语权。最后,在当前国际投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已经形成某种竞争态势的背景下,长期仅靠单边自主开放来吸引外资的作用有限,在签订投资自由化协定方面裹足不前很可能延缓中国对外资的吸引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投资体制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强,正面临一个战略机遇期。首先,中国目前不仅是吸引外资的大国,而且成为资本输出的重要国家。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关注投资者利益与投资东道国利益的平衡,因此中国的立场更容易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其次,中国目前在多边贸易领域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谈判经验日益丰富,更容易借助该方面的影响力影响国际投资体制。再次,目前在发达国家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中,要求反思传统上美国式投资保护和自由化标准的主张相当普遍。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在投资问题上的立场是可能逐渐接近的。最后,当前国际投资体制仍然处于转型变动时期,相比成熟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国更有可能施加自己的影响。
中国在国际投资体制建设中的战略
中国近年来对外进行投资协定谈判时,常常面临的一个压力就是外方要求中国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而且是基于否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中国正处于一个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关键期,国内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这种原则上全面对外资开放的承诺,带来的政策、法律和经济风险难以评估。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经济合作协定中,都没有包括这类条款。这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相比,在投资自由化承诺方面显得相对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言权。因此,在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上的沉默是目前中国影响国际投资体制的最大障碍。
谨慎对待投资自由化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但这不等于在投资自由化承诺方面应该无所作为。在暂时不接受基于否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同时,中国应该主动出击,明确主张基于肯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此为基础与其他国家展开投资谈判,并争取将这种谈判方式重新纳入多边领域。应该强调的是,之所以说“重新”纳入多边领域,是因为这种基于肯定清单的投资自由化谈判模式一度是世界贸易组织准备进行投资谈判的模式。下面简单回顾一下历史。
从1995年开始,有“富人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曾经在其成员中组织了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并打算对非成员开放。这次谈判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担心。(16)出于对发达国家率先推出全球资本流动纪律的担心,有些国家支持将这一谈判纳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在1996年的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会议上,各方同意就投资问题、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的透明性和贸易便利化等四个议题成立工作组,研究谈判的可能性。这四个议题被称为“新加坡议题”,实际上代表了世贸组织可能扩展的谈判领域。2001年多哈部长会议将这四个议题纳入了多哈部长宣言,明确各方在取得明确共识的前提下就这些议题展开谈判。在当时情况下,经合组织的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于1998年已经流产,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愿世贸组织将管辖范围扩展到投资等领域。2004年坎昆部长会议后,支持新加坡议题最为坚定的欧盟最终放弃,世贸组织于2004年8月1日决定将四个新加坡议题中除了贸易便利化之外的三项议题剔除出多哈回合多边谈判的议程。
尽管投资议题最终没有纳入多边贸易体系谈判,然而多哈部长宣言中就投资谈判方式的阐述值得注意。宣言的第22段明确主张,投资谈判应该采取基于肯定清单的投资自由化模式;同时指出,这种模式类似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自由化模式。事实上,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初期,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也就谈判是采用肯定清单还是否定清单产生过争议,为了争取发展中国家同意将服务纳入谈判议题,发达国家最终同意了使用肯定清单谈判方式的折中方案。
现在看来,采用肯定清单谈判方式渐进地推动投资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在2001—2004年间,投资自由化议题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都是新议题,像日、韩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是到2002年才在其投资协定中首次采用基于否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基于肯定清单的投资自由化都不太容易被接受。尽管有中国学者对基于肯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持支持态度,然而中国当时面临履行入世协议的压力,对世贸组织议题的扩展持谨慎态度,此后对基于肯定清单的投资自由化方式也没有明确和坚定地表示支持。(17)
国际投资体制在2004年世贸组织剔除投资议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模板的修改中向维护东道国权利的方向进行了一些微调。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纳入了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为投资自由化发展的主要形式。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进TPP谈判,同时宣布将于2013年6月与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谈判。在国际投资体制暂时缺乏多边纪律的情况下,美国正将其标准通过区域和双边层面不断推广。在此背景下,中国对投资自由化谈判继续持消极态度的结果就是坐等美国标准成为国际规范。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中国的投资体制已经进行了一些调整,2004年外资从审批制转为核准制,之后实行了两税并轨,推出了《反垄断法》,从而使外资管理体制由原来的税收优惠加准入审批为特征的管理体制向以竞争政策和技术标准为核心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转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对外投资谈判中做出渐进的投资自由化承诺已经条件成熟。推出以肯定清单为基础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谈判方式,从技术上来说对中国已经困难不大。关键的是,明确主张这种谈判方式可以在对外投资谈判中转被动为主动,改变在投资自由化承诺方面裹足不前的局面。
以肯定清单为基础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谈判在谈判阶段也许工作量比基于否定清单的谈判要大,但是在之后的执行阶段风险更小,更加稳妥,加上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实际上通过服务贸易谈判都积累了这种谈判方式的经验,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比美国式的条款更有吸引力。中国可以先与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方式达成投资协定,然后逐渐推广。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一般的肯定清单承诺可以推广,将准入前国民待遇给予其他与中国签订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家。与此同时,在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可以制定一个更高标准的肯定清单,然后援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例外,不按最惠国待遇要求给予其他国家(18),从而便于中国灵活地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随着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和对外投资规模的迅速增长,维护和促进投资自由化,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投资体制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是有利的。鉴于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渐进式的开放模式对中国最为有利。在此情况下,力推基于肯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是中国的最佳选择。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建立平衡发展的国际投资体制。同时,通过基于肯定清单的投资自由化谈判,中国也可以更好地梳理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和产业政策,再次发挥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促进国内投资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使之成为新一轮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当前国际投资体制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期。一方面,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的投资自由化进程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在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权利的平衡方面出现了有利于维护东道国权利的声音,同时各种投资协定的重叠交错使得形成多边投资纪律的必要性进一步提高。中国目前正处于可以影响国际投资体制的战略机遇期。在此背景下,明确对国际投资体制的主张至关重要。中国应积极突破目前以单边开放为主的形式,提出以肯定清单为基础的投资自由化模式,接受并主张以肯定清单为基础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以此为基础开展双边投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并适时将该谈判方式向多边领域推广。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国际投资自由化进程中掌握主动,也可能为国内的改革带来新的推动力。
①参见Alvarez,J.E.,The Once and Future Foreign Investment Regime,In Arsanjani(Ed),Looking to the Future: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r of W.Michael Reisman,2010,The Netherland,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607-648。该作者另一相关著作为Alvarez,J.E.,K.P.Sauvant,et al.,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Expectations,Realities,Options,2011,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Alvarez,J.E.,The Once and Future Foreign Investment Regime,In Arsanjani(Ed),Looking to the Future: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r of W.Michael Reisman,2010,The Nether-land,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P.608 note 8。这里体制(regime)一词的译法在中文文献中并不一致,本文采用任东来等人的译法,参见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
③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100页,见http://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1-Full-en.pdf。不过,在《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这个概念并没有再次出现。
④见 Simmons,B.,"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since the 1980s:A Transnational 'Hands Tying' Regime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Working Paper,2011,Harvard University。
⑤“华盛顿公约”即《关于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汉城公约”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⑥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102页,见http://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1-Full-en.pdf。
⑦参见赵玉敏:“国际投资体系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从日韩投资国民待遇看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国际贸易》,2012年第3期。
⑧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中,中方受到日本和韩国的谈判压力,但在2012年达成的中日韩投资协定中,中国仍然没有做出同意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承诺。今后中日韩的自贸区谈判中,投资自由化议题必然重新提上谈判桌。
⑨就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可见单文华:“从‘南北矛盾’到‘公私冲突’:卡尔沃主义的复苏与国际投资法的新视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2008年第4期。
⑩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102页,见http://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1-Full-en.pdf。
(11)(12)根据ICSID公布的案件整理。
(13)Ekran Berhad.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ARB/11/15).
(14)《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的201 1年各国单边投资自由化与促进措施为52项,单边监管与限制措施为15项。参见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2-Full-en.pdf,第76页。
(15)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93页,见http://www.unctad-docs.org/UNCTAD-WIR2011-Full-en.pdf。
(16)当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曾经派员前来北京召开与中国官员和学者的对话会,笔者参加了这次对话会。会上中国官员与学者以及来自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代表对经合组织的这一谈判出现了一边倒的反对声。
(17)对基于肯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持赞成态度的代表性观点可见余劲松:“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外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问题”,《法学家》,2004年第6期。
(18)近年来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大多规定有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外。但是,早期有许多协定没有这样的例外条款。这一问题可以按照中国和罗马尼亚的经验解决。中罗两国于1994年曾经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其中没有规定最惠国待遇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外。罗马尼亚加入欧盟后,两国于2007年签订了一个补充议定书,增补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例外条款。
标签:准入前国民待遇论文; 国民待遇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会议议题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