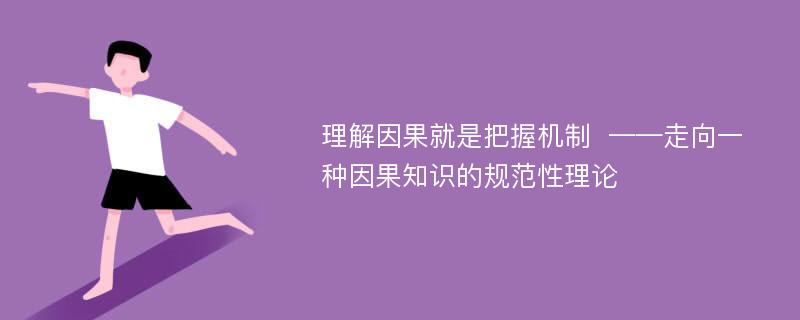
摘要: 对因果关系的知识如何产生科学理解?这一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争论,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因果判断的语义分析。与两者都不同的是,塞拉斯主张因果知识仍然是先天综合的知识,这建立在他的“以语用为中介的语义”分析上,提出因果判断表达的是因果推理的话语实践之内的实质规则,因而是一种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这一理论将重新评价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理论特质,重新阐发“理解因果就是把握机制”的概念直觉,提供了与主流因果理论不同的但又另辟蹊径的理论选项。
关键词: 因果关系; 理解; 机制; 塞拉斯
对因果关系的知识历来是认识论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因果知识之所以重要,乃是由于它并不仅仅给出陈述某个事实的命题,更是能为认知者提供对所陈述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而理解乃是比一般知识更有价值的认知状态[1]203。即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仅仅“知道”某个因果关系的存在、能够复述某个陈述因果关系的命题,却仍然欠缺“理解”的例子。而一旦涉及日常经验与科学知识的差异,这样的情况就更屡见不鲜了。譬如,你可能也知道微观粒子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相关性,甚至知道有关的数学表述,但却未必对此有真实的理解。
在科学哲学中,科学理解(scientific understanding)向来与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的讨论联系在一起。任何一项科学的理论,只有当它能够用来解释经验现象时,我们才谈得上对理论所陈述的因果关系有真切的理解[2]337。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科学解释能够提供对因果关系的“理解”?科学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对立。休谟主义者主张这应该是基于规律性经验概括的解释,而反休谟主义则强调只有诉诸真实存在的自然倾向或机制才能真正理解因果关系。两方的观点是在因果关系的语义分析上形成对立:如果陈述因果关系的命题内容必须具有某种模态涵义(modal sense),那么如何从语义关系上——亦即仅仅考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来刻画因果必然性?休谟主义者认为这种模态性仅仅来源于对经验规律的人为选择,而在反休谟主义者看来,必须从语义上将这种必然性解释为实在世界的固有特征*关于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在因果理论上的争论,可参看本文作者(徐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的《因果知识的德性转向:重审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之争》,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第48-57页。。
然而,在既有的概念版图之外,还存在着新的理论选项。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思想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而塞拉斯早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工作中,就提出了对因果知识的“先天综合论证”,既不同于休谟主义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反休谟主义观点,而是在当代分析哲学语境中复兴了康德的因果理论,是一种“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因果知识乃是关于推理的实质规则(material principle of inference)的知识。根据实质规则的推理不同于纯形式的逻辑推理,它是综合的;但同时它仍是对推理规则的认识,又是先天的。塞拉斯的规范性理论也是对因果关系的一种语义分析,但与休谟主义或反休谟主义都不同的是,这种语义分析不是直接呈现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以语用为中介的语义关系”[3]101,即从语言使用者的视角构建因果判断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对塞拉斯这一思路的重新阐发,为反思、评价当代因果理论论争、特别是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与“机制”等概念的关系,提供了综观性的理论透镜。
这种理论综观最终要论证的结论是,“理解因果就是把握机制”,当然这里的“理解”与对机制的“把握”都要在塞拉斯的规范性理论视域中得到阐发。对塞拉斯的理论细节,笔者已有专文讨论,这里不再展开[注]对塞拉斯的因果知识理论的讨论,参见本文作者的《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塞拉斯论先天综合》,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9-15页。。但这里的确会用到其中的主要论点,所以为了叙述方便起见,这里把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简要概括为以下几条论题:
(S1)因果知识的“所与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注]“所与的神话”最初是针对知觉知识提出来的:“有(确切地讲,必定有)一个关于具体事实的结构,(a)每一个事实不但能被非推论地认识到是这样,而且不预设关于其他具体事实的知识或关于一般真理的知识;(b)这个结构中关于事实的非推论知识构成所有关于世界的(具体的和一般的)事实断言申诉的最终法庭。”(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第56页)之所以说这种想法是一个神话,是因为任何处于话语实践与理由空间(space of reasons)之外的自然事实,尽管看似不作任何预设因而能成为知识断言的终极评判,但恰恰也因此无法与非推论的知识断言建立理由证成的关系。而任何能够用来辩护知识断言的东西,必定处于话语实践之中,因而就不会是纯粹自然的事实。塞拉斯进一步认为,“所与的神话”在因果知识的讨论中也存在,譬如实在论者也会把因果必然性当做某个独立于话语实践而存在的自然事实。批判,因果判断不能是对实在世界中的必然联系的言外(extra-linguistic)把握;
(S2)因果判断的断言(assertion)意义,因果判断是从语义上断言相应的反事实条件句为真,可以刻画为与现实相近的可能世界的情况;
按照《总体规划》和《南水北调工程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南水北调主体工程贷款本息的45%由水费收入偿还,其余55%在工程建设期满后筹集南水北调工程基金偿还。
(S3)因果判断的传达(convey)意义,因果判断表达了基于概念把握的推理的实质规则,在语义上传达了判断者遵从规则的心理状态;
(S4)因果知识的先天性:作为推理的实质规则而非言外把握,因果判断相对于具体语言框架是先天的,但同时也存在着替代性语言框架;
“由于健康需求的迫切性和多样化,我国特殊食品市场潜力巨大。”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说,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增强,人们的观念正在从吃得饱、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向均衡营养摄入、利于身体健康的方向转变;从有病治病向无病预防、提高健康质量转变,这些都将促进特殊食品产业迅猛发展。
我们首先基于这一理论对以往的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因果理论作出评价,从比较中将会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深入考察因果知识所提供的“理解”,而这将体现出与传统的因果理论论争不一样的新面向。
一、休谟与休谟主义
首先来看休谟本人以及此后的休谟主义者发展的因果理论。从S3来说,因果推理不仅是真正遵从规则的推理,而且所得出的因果判断本身就表达了推理的实质规则。塞拉斯谈到,“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主张即认为因果推理不是真正的推理,而是伪装成推理的习惯性期望,在这里就完全不合理了,特别是当它宣称要包含实质上的反事实条件时,就与事实完全相反”[4]。在他看来,休谟正确地指出,要论证一项因果推理的正当性,既不能仅仅根据纯粹形式的逻辑规则,也不能靠诉诸对直接经验的归纳:因为因果推理本身也属于归纳,所以用归纳方法来证明因果推理就相当于是循环论证。由此,休谟就否定了因果推理能够从理据上获得证成,而只能作为一种自然的习惯倾向存在。
但是,塞拉斯认为,休谟的否定毕竟还是过于匆忙了,因为他没有考虑根据实质规则展开推理的可能性。例如,在“假如某甲不发生,则某乙也不发生”的推论中,的确有鲜明的必然性涵义存在:这并不仅仅是面向有某甲和某乙的环境而作出的关联性回应——在这个维度上因果推理的确是自然的心理倾向;同时,它更是根据对某甲和某乙的概念把握而作出的受规则调整的符号行为——并且,正是在它受某甲和某乙的概念关联制约的意义上,这一从符号到符号的推导行为才是因果知识的体现。所以,塞拉斯评论说,“休谟曾经找到了正确的轨道,但由于他不能区分受规则调整的心理活动与观念的联结(这在今天表现为不能区分受规则调整的与关联环境的符号行为),他的理论就势必不够充分”[5]。
传统休谟主义的,亦即实证主义的因果理论否定了S1和S4,主要是反对因果知识具有先天性,这在塞拉斯看来是陷入了“所与的神话”。对实证主义者而言,例如亨普尔(C. G. Hempel),因果判断只不过是得到观察经验辩护的规律判断,其真值来源于语言之外的经验事实,所以也并非先天综合的知识。但塞拉斯的主要批评在于,实证主义在这里混淆了两个维度:一是说某类知识“不是先天的”,意味着它的使真者(truth-maker)是语言之外的事实;二是说某类知识“不是先天的”,却是意指它的语言框架是可替代的。在塞拉斯看来,因果知识的语言框架当然是可替代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它不是先天知识的结论,因为即便如此,使因果判断为真的东西仍然不是语言之外的事实。
近二十年来,国际科学哲学的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实践转向”,即从传统的“理论优位”(theory-dominated)的视角转向关注介入性的科学实践(scientific practice)[注]关于科学实践哲学及其对理论优位的批评,可参看吴彤:《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科学实践——兼评劳斯等人的科学实践观》,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85-91页。。在像神经科学与社会科学等具体科学的实践中,谈论“机制事实”不能不依赖于“机制模型”的表征。换句话说,所谓的在本体论上的机制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实际使用的机制模型所表征的东西。反休谟主义者对科学理解的辩护,应该是着重于其本体论的意义而未止步于表征模型;但塞拉斯的规范性理论似乎更容易从对科学实践的关注中获得支持。因为我们不可能脱离表征性的科学实践来谈论真实存在的“机制事实”,“机制”在这里就已经不是处于话语实践之外的自然事实,而毋宁说就是人们在因果推理时遵从的那些实质规则的集中体现,本身就是话语实践中的规则性事实。脱离机制模型而谈论作为言外事实的“机制”,并不是科学理解真正需要的事实性涵义。
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在物理学革命的时代背景中否定了康德意义上的“先天综合知识”,它主要依据的应该是后者而非前者。具体说来,实证主义认为,牛顿力学被相对论力学所取代,最好地证明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先天综合知识,所有经验科学的命题最终都不可能有先天的辩护。然而,在塞拉斯看来,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力学的转变乃是语言框架的转换,因而也就是“推理的实质规则”的整体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还可以被解释为“先天知识的辩护根据的类型多样性”,譬如像彭伽勒的约定主义解释所主张的那样。而不管是在什么实质规则的约定下,使因果判断为真的东西都仍然是话语实践之中的存在,而不会是语言之外的某种所与或自然事实。
根据试验结果对试验结果做极差分析如表3~表5所示,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空穴率的影响不是很明显的。其中,3个因素对空穴率的影响程度,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是最大,输送带的速度次之,吸孔的直径影响最小。吸孔的直径与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和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与输送带的速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单粒率的影响稍微明显一些,其中3个因素对空穴率的影响程度: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是最大,吸孔的直径次之,输送带的速度影响最小。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与输送带的速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重播率影响稍微明显一些,其中3个因素对重播率的影响程度,吸孔的直径是最大,种箱相对于滚筒的角度次之,输送带的速度影响最小。
刘易斯(David Lewis)的因果理论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因果依赖关系必须定义为反事实条件的依赖关系,而“反事实条件依赖”(counterfactual dependence)的语义规定又进一步取决于“可能世界的相似性”的评价,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自然律——与现实世界相近的可能世界总是要保持自然律的有效性。而在自然律与全称量化的经验规律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分。实际上,这仅仅来源于认知者的选择:科学家会从规律判断中“筛选”出其中的一些组成尽可能简单且推理能力足够强的演绎系统,能够进入这个系统的就是自然律,否则就只是偶然的规律判断[6]73。所以,因果模态的涵义归根到底仍然取决于我们选择哪些规律判断具有自然律的地位,因而因果判断的真值最终也来源于言外的事实,也就仍然认同“所与神话”而反对先天综合的知识地位。
从休谟到传统休谟主义再到新休谟主义,共同的特点是以变量间相关性来界定因果关系,反对有任何非推论的(non-inferential)单称因果(singular causation)判断。这里共同的理论动机是追求因果知识的辩护。与能力知识相比,作为命题知识的因果判断当然需要得到认识论上的辩护。既然休谟主义否定S1和S4,主张因果判断等同于某一类规律判断,那么对于像“某甲是某乙的原因”这样的单称因果判断,认知者就只能从全称量化的规律判断做推论才能得到,所以单称因果判断也就只能是推论性知识,而不会是非推论的。因为在休谟主义者看来,因果判断仍然是命题知识,而不是对某一类规则的能力知识。
在因果判断的传达意义上,反休谟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把先天知识所要求的必然性,特别是因果关系的模态意义,看做是世界本身实际具有的某种联系,或者至少是关于客观存在的可能世界方面的特征。塞拉斯认为,“我们在因果的和逻辑的语境中使用‘必然’一词,应回溯到语言规则上。休谟指责理性论者(以及此前的常识)把对受迫的主观感受投射到环境之中,而我们所要指责理性论者的是,把他的语言规则投射到语言之外的世界之中[5]。”塞拉斯在这里所批评的“理性论者”主要就是反休谟主义的因果实在论者。在他看来,尽管休谟的因果理论也没有支持S3,但反休谟主义距离规范性理论更远。在反对因果模态的形而上学地位方面,塞拉斯与休谟的立场是更接近的,都认为那种主张因果模态形而上学根源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恰当的“投射”。
制定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工作方案,确保按期实现农村低保和扶贫“两线合一”。对全市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衔接工作进行专题研究、专门部署,明确工作重点,提出任务要求。出台《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衔接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职责分工、实施步骤、行动措施,为开展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恰好就与S5相冲突。规范性理论的核心就是把因果知识看做掌握因果推理的实质规则,就是知道如何(knowing-how)遵从规则作推理的能力知识,而非只是语言表述的命题。能力知识并不在意所要掌握的规则本身如何表述,重要的是具备能够在复杂情境下遵从规则行事的能力。如果因果知识意味着遵从实质规则作推理的能力,那么基于命题形式的辩护便不再是首要的评价角度,而单称因果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有可能以非推论的方式获得。
二、反休谟主义
一方面,对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解需要协调事实性(factivity)与虚构性(fictionality)的关系。“理解”的事实性也像知识那样要求信念大部分为真,但科学理解的形成往往需要借助模型表征,而任何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成分。那么,一个虚构的模型为什么能提供符合事实的理解呢?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的事实性乃是相对于“机制事实”(mechanical facts)而言的,而符合机制事实的同时也就是相对于个别具体事实的虚构性[注]关于事实性与虚构性关系的详细讨论,可以参看本文作者的《科学理解的事实性与虚构性》,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8-13页。。毋庸讳言,谈论“机制事实”的确带有非常鲜明的反休谟主义色彩:因果判断所断定的“机制”并不是休谟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相关性”,而是在时空中真实存在的生成过程。但反休谟主义也正是因此陷入了“所与的神话”,因为这个实在世界的生成机制确实是独立于话语实践的事实。
表5显示了不同育肥条件下母羊小肠及胰腺的胰蛋白酶活性。表5结果可见,TMR组母羊十二指肠和胰腺胰蛋白酶活性显著高于NG组母羊(P=0.003、P=0.02);回肠胰蛋白酶活性有高于NG组母羊的趋势(P=0.08);空肠胰蛋白酶活性略高于NG组母羊,但差异不显著(P=0.46)。
具体说来,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这种分歧在自然律(laws of nature)理论上表现为确认问题(problem of identification)与推论问题(problem of inference)的两难困境[8]:因为休谟主义认为自然律本身也是经验规律判断,所以它就能很容易解决推论问题,但它不容易说清楚,为什么定律必然性与规律判断的非模态涵义之间仍然有着根本差异。如果必然性仅仅来自于认知者主观的“筛选”,而非客观世界的话,那么应该不存在这样的差异。相反地,在S2方面,反休谟主义者认为语义学的特征必须由形而上学的事实来保证。这样虽然能够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确认问题,但却付出了推论问题上的代价,即我们不容易看到,基于经验规律判断上的推理如何能够得出形而上学上可靠的结论[注]关于自然律理论在确认问题与推论问题上的两难困境,参见本文作者的《论自然律与因果知识的知觉经验基础》,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84-92页。。
每隔一周便举行一次半社交性的会议。有时开会地点是在社会服务部主管的家中,有时在一个中国餐馆里,有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礼堂的社会厅。社会服务部的社工们发表有关北平城中各式各样社会机构的研究报告,也经常有北平市声誉卓著的社会工作者和著名的海外人物受邀做演讲。
不难发现,塞拉斯对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批评,与康德同时拒斥经验论的与理性主义的两种独断论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康德而言,经验论的独断论没有看到,人类认识在知觉的被动接受性之外还有主动综合的一面,而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则把世界本身看做纯粹理性的现成对象,忽视了先天的感性与知性因素的对象建构作用;同样地,在塞拉斯看来,休谟正确地判断出因果模态涵义并非来自世界本身,但他只是将其看做面向环境刺激的关联行为,忽视了它作为受规则调整的符号行为的可能性;而反休谟主义则直接在遵从规则的语言实践之外寻求因果模态涵义的基础,同样错失了语言实践对因果知识内容的建构作用。
在因果知识的先天性方面,反休谟主义与塞拉斯理论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首先,即便是像阿姆斯特朗这样的概念实在论者,也会认为他所说的属性共相之间的关系不是先天的,而是以后验的方式确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塞拉斯的“先天性”也不具有传统先验哲学意义上的不可错性或不变性,另一方面S4的先天性主张本身就是相对于语言框架而言的,在同一语言框架之中实质规则的不可替代性与语言框架本身的可替代性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可以调节的张力。但两者之间根本的分歧在于,规范性理论所主张的是语言规则意义上的先天性,而对反休谟主义者来说,因果判断的必然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话语实践之内。
财务会计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对于企业的发展也能提供更多的活力源泉,在一定程度而言,财务会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所以发挥财务会计的作用是在经济管理中对经济命脉的深层次认识和了解,其对于保证企业发展评估的正确性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S5)实质规则的能知(knowing-how),获得因果知识就是掌握推理的实质规则,这是知道如何遵从规则作推理的能力知识,而非只是语言表述的命题。
S5应该是反休谟主义非常不同于休谟主义的地方。反休谟主义者赞同有非推论性的单称因果判断,其背后的理论动机是寻求由因果知识提供的“理解”。在某些哲学家那里,这就意味着要超越因果判断表面上的命题结构。像扎克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等认识论学者就主张,理解的对象不会是单个的命题,而是非命题结构的实在整体[9]。
从这个意义上看,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或许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反休谟主义者会主张单称因果判断可以是非推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非推论地作出单称因果判断是在熟练掌握规则前提下的实践表现。在反休谟主义的理论中,因果判断本身还不是对推理规则的判断。而从塞拉斯的立场看,掌握因果判断本身就是获得相应的能力知识。正是因为因果判断本身就是对某一类规则的表达,所以掌握这类规则的能力就使人们有可能非推论地判断“某甲是某乙的原因”。所以,S5的内涵恰恰支持了这样的常识直觉:“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知识,是知道如何做某事的能力。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具体地说,这就是“把握相关机制”的能力。
最后,传统休谟主义也无法把握S2即因果判断的断言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否认模态词项的意义独立性,认为它们最终应该以全称量化的方式还原为仅仅包含描述性词项的规律判断。与之相对比的是以因果性的反事实条件理论为代表的新休谟主义,支持S2但仍否定S1和S4。新休谟主义比传统休谟主义进步的地方在于,承认因果判断的必然性应该以一种区别于描述性词项的方式来刻画模态涵义。这里的区别主要是因果判断必须支持反事实条件句,而仅包含描述性词项的命题则完全不需要。但同时在新休谟主义者看来,模态涵义仍然是某种人为地添加到描述性词项上去的东西,而因果判断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依赖于言外事实的规律判断。
三、理解与机制
寻求因果知识产生的“理解”,这是反休谟主义区别于休谟主义的理论动机。在塞拉斯的规范性理论中,这意味着要从S5来界定因果知识。对作为实质规则的因果判断的认识,最终是“知道如何遵从规则”的能力知识;而要获得能力知识,就不能拘泥于对规则的命题表述,最好的办法是向已经掌握能力知识的榜样范例学习,使自己也具备善于习得实质规则的理智品质,从而能够以比命题知识更有价值的方式“理解”因果关系。
然而,反休谟主义毕竟不同于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如前所述,一个根本的分歧是,对反休谟主义者来说,理解因果关系意味着把握某个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自然机制;而我们已经看到,塞拉斯的理论所呈现的是,所有因果判断都首先是一个语言之内的规则性事实。所以,如果我们还试图在塞拉斯的立场上继续坚守“理解因果就是把握机制”这一概念直觉,那么似乎就不得不重新诠释反休谟主义的“机制”概念。这其实就需要非常丰富细致的理论工作。限于篇幅,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肯定是挂一漏万,不可能涵盖所有的面向;但或可以管中窥豹,约略展示出它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独特价值。
反休谟主义的因果理论倾向于从生成的概念上刻画因果关系,并主张可以有非推论的单称因果判断。与休谟主义相比,反休谟主义通常也是把因果模态意义归之于实在世界的必然联系。譬如,按照这一派的代表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的观点,因果关系最终立足于属性共相之间的“必然导致”(necessitate)的关系[7]95。这虽然不同于传统休谟主义所主张的感觉材料,但同样是陷入“所与的神话”,因为属性共相之间的“必然导致”仍然是话语实践之外的形而上学事实。这也证明了并不是说只有经验论立场才会陷入“所与的神话”,理性主义也同样有此危险,只不过他们所利用的不是“经验所与”,而是理性意识上的被给予性、概念上的直接性[注]实际上,塞拉斯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一文的开头就声明了,他所要批判的是“所与的神话”本身,而不论其来自于经验论的还是理性主义的传统。。从断言意义上说,因果判断意味着相应的反事实条件句为真,在S2方面反休谟主义与新休谟主义并无根本分歧,它们的分歧在于如何解释这种语义学特征的来源:究竟是由什么保证了这些反事实条件句为真?休谟主义者认为是人为地赋予规律判断以模态意义,而反休谟主义者批评说,不能把使真者归于认知主体,这样会造成相对主义的后果,而应该归为世界存在着的必然联系。
进入暖箱的新生儿需要全程监护,医护人员会定时查体、喂奶、换尿布、观察宝宝的皮肤颜色、原始反射和生命体征等,及时调节暖箱的温度和湿度,避免暖箱温度失控,影响宝宝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真正从科学上理解因果关系,还意味着能够适当地规避认知运气(epistemic luck)。对现象产生原因的科学理解不能是碰运气的结果——用刘易斯的反事实条件语义分析来说,这要求现象的因果解释在相邻的可能世界中也能成立,即具备“解释评价的可靠性”[10]。而评价这种可靠性又依赖于确定机制与其周围环境的边界:既要厘清哪些要素属于该机制之中,哪些又只属于周围的环境;也要确定机制的通常运行模式——在世界中实际上是怎样运行的,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又会怎样变化,等等。具体说来,如果现象的因果解释是基于对机制与环境的关系把握作出的,那么它就会是可靠的[注]关于科学理解与认知运气的关系讨论,可参看笔者《科学理解及其机制论概念:从认知运气的视角看》,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5期,第20-27页。。
从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出发对认知运气的考察会有一点复杂,最好是具体考察一个受认知运气的影响而不能真正理解因果关系的例子。例如,费欧娜案例:
假设费欧娜……从Nero的房屋烧过的余烬中收集所有的证据,在这方面她做得相当不错。基于这些证据,她相信起火的原因是开关箱的故障,而这也是一个真信念。但实际上,在开关箱故障导致起火的同时,接地线也发生了短路。这两个事件在因果上是独立的,所以接地线短路并不是实际造成起火的原因。然而,倘若是接地线短路而非开关箱故障导致了起火,费欧娜也还是会发现相同的证据,并进而以开关箱故障来解释Nero的房屋起火的原因[11]。
换言之,因果知识上的认知运气,意味着不同的、彼此可替代的因果链条可能导致同一个现象。这其实对S4主张的因果知识的先天性提出了挑战:仅仅知道“开关箱故障导致起火”,与把“开关箱故障”与“接地线短路”同时纳入起火原因的考量,背后所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机制模型,也就是因果判断所依赖的语言框架不同。尽管因果判断作为推理的实质规则是先天知识,但它所依赖的参考系——语言框架本身却又是可替代的。
因此,认知运气的可能性正意味着因果知识先天性的局限:以其他方式组织推理的实质规则的框架总是可能的。例如,在费欧娜案例中,尽管实际上存在着不同因果链条可以导致同一个现象,但对认知者而言,并不一定把两个因果链条都纳入同一个有待于考察的“机制模型”,即并无必要把相互独立的因果链条都看做是机制系统内的要素作用,而也有可能将其划为环境因素的偶发作用。这就取决于她如何界定机制与环境的关系,如何判断相关机制的正常运行模式。当然这种表征模型又是可以变动的,变动就意味着是更换不同的语言框架。但这仍不能推翻S4的主张,即在已确立的语言框架中,理解因果关系意味着把握推理的实质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把握机制的因果理解仍然是“先天的”而非运气性的。
四、结语
塞拉斯的规范性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张因果知识仍然是先天综合的知识,因为它表达的是人们在因果推理的话语实践中基于概念间关联的“实质规则”。具体说来,判断“某甲是某乙的原因”,并非陈述某个语言之外的事实,而是表达这样一条实质规则:“鉴于某甲的概念与某乙的概念之间存在如此这般的联系,在因果推理中我们可以由前者推论出后者。”当然,概念间联系可以变化,存在着可替代的语言框架,但这并不是因果知识“非先天性”的证明,而只是表明因果知识具有可错的、多元不唯一的“先天性”。
王昌龄诗作于太子丹和荆轲的精神人格并无识见,亦不察小说笔墨灌注之处的用意。但是,认识到秦国瓦解之因在于“无道”,与小说所揭示之秦王无道相一致。
如果我们假设因果知识的规范性理论是对的,那么回顾休谟主义与反休谟主义的理论论争,就会得出很有意思的结论。从塞拉斯的立场看,对立的双方都陷入了“所与的神话”,但理由又各不相同。休谟主义相信因果判断的模态涵义最终可以消解在进入话语实践之前的经验事实中,反休谟主义则诉诸某些话语实践之外的形而上学事实来为因果必然性奠基。归根到底,两者都试图用言外事实来作为因果判断的理由根据,而没有看到任何话语实践之外的存在都无法担当理由提供者的使命,除非它原本就在理由空间之中,即本身就是话语实践之内的存在。因此,“理解因果就是把握机制”,但所把握的机制并不是言外的形而上学事实,而是科学实践之中的表征对象;表征所用的语言框架是可替代的,因而任何机制所代表的相关实质规则是可能失效的,但在任何既定的框架中,对因果推理规则的把握都的确是知识先天性的体现。
然而,说因果判断竟然是一种“先天知识”,这毕竟还是太反直观了,这源于塞拉斯对因果判断的分析追求一种“以语用为中介的语义”,也就是从认知者的话语实践中建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当代哲学的主流却是纯粹的语义分析,也就是像刘易斯那样,直接谈论语言关联到世界的语义模型。但是,我们从主流的分析进路中得到了什么呢?毋庸讳言,我们在一般科学哲学上面临着诸多困境。尽管因果理论有很多细节上的完善,但一般性的哲学洞见却越来越贫乏,或许这恰恰是由于太执著于主流做法,而忘记了它也是有限历史的产物。这样,重新发现塞拉斯,挖掘因果知识的多重面相,或有别开生面之效,正当其时。
不同的学生在身体素质以及运动能力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性。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提高花样跳绳的创新程度。体育教师可以将年级作为划分跳绳活动的主要依据,选择合适的跳绳活动内容。在形式多样的花样跳绳活动中,能使学生对这项运动的参与兴趣有所提高,更能使学生得到与之身心相适应的体育锻炼,从而达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J. Kvanvig.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e Pursuit of Understand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C.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3]R. Brandom.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Towards an Analytic Pragma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W. Sellars.“Inference and Meaning”, Pure Pragmatics and Possible Worlds: the early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J. F. Sicha (eds.). Atascadero, CA: Ridgeview Publishing, 2005, pp. 218-237.
[5]W. Sellars.“Language, Rules, and Behavior”, Pure Pragmatics and Possible Worlds: the early essays of Wilfrid Sellars, J. F. Sicha (eds.). Atascadero, CA: Ridgeview Publishing, 2005, pp. 117-134.
[6]D. Lewis. Counterfactuals,Oxford: Blackwell, 1973.
[7]D. Armstrong. What is a Law of N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B. van Fraassen.“Précis of Laws and Symmetr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3, 53(2): 411-412.
[9]L. Zagzebski.“Recovering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Truth, and Du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35-251.
[10]K. Khalifa.“Understanding, Grasping, and Luck”,Episteme, 2013, 10(1): 1-17.
[11]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Understanding Causation is Grasping Mechanism:Towards a Normative Account of Knowledge of Causation
XU Zhu,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of causation an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Humeanists and Anti-Humeanists argue against each other, the main difference of which lies on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assertions on causation. However, Wilfrid Sellars, who disagrees with both positions, has put forward a distinc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argue that knowledge of causation is still a priori. What Sellars characterizes is the “pragmatically mediated semantic relation”, which suggests assertions of causation as material principles of causal inference. And it is thus a normative account of knowledge of causation. In terms of Sellarsian normative account, Humeanist and Anti-Humeanist theories could be reevaluated, and the particular kind of understanding on causation could be also re-elaborated as grasping mechanism.
Key words: causation; understanding; mechanism; Sellars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9)02-0015-07
DOI: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2.03
作者简介: 徐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因果理论前沿研究”(12CZX01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1-10
责任编辑 吴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