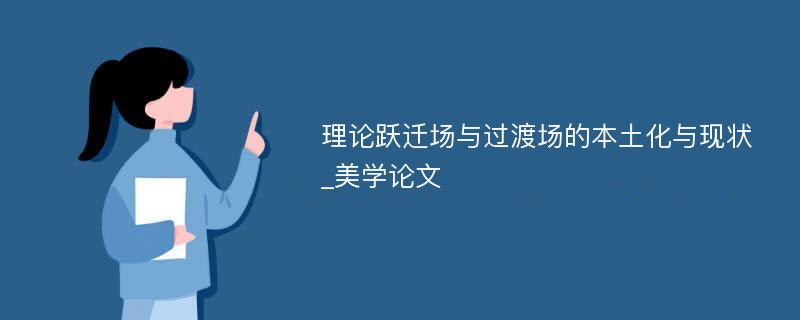
理论转场与转场的本土化、当下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场论文,本土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美学用非美学理论话语扫荡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造成当代美学疏离中国审美现场,对活生生的文艺生活失聪、哑语,美学已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普遍性、最富时代性、最有能指性的思想理论交往的公共话语,矮化为少数专家学者的“理论”独白。一句话,当代美学话语正在慢慢失去其社会实践性。当代美学失聪、哑语症状的主要病因,既源于多年来美学撤离中国火热的文艺现实生活,严重气血乏匮;又根于当代美学与中国本土美学传统自断血脉,美学的民族精神先天不足;还与误读西方理论,食洋不化所造成的后天不良直接相关。要言之,在于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未能真正进入当代现实的审美文化与文艺实践的场中,关键话语与主要表达功能没有实现真正的理论转场,而是处于当代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的场外。同时,西方美学话语没有中国化、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没有现代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主流文艺理论没有当下化。可以说,当代美学理论的主要话语和关键表达功能并没有现实地转进中国本土当代审美经验中,尚在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场外踯躅。因此,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理论话语体系,最重要的路径就是自觉地对古今中外的场外理论进行理论转场,并在理论转场过程中使之本土化、当下化,使之成为面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置身当代中国审美生活、言说与表达当代中国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并具有广泛话语影响力与巨大社会参与度的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一、场外理论转场是构建美学话语体系的合理性路径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审美活动通常是一种感性的愉乐活动,个体化与感觉化是其基本特性。而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文艺实践活动是一种典型的情感观照活动,感性形象性和情感体验性是文艺活动的根本规定性。美学作为关于社会生活中审美经验和文艺活动的逻辑建构与理性表达,其理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对感性的审美共同经验和文艺实践活动的普遍性归纳和概念性总结。感性的现象不能自主转换为理性的本质,普遍性归纳和概念性总结的手段、方法、观念,通常从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场外的其他场域理论中借用或沿用。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主要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大多源于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可以说,各种场外理论为美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理论观念和方法手段,这既是美学构造其话语体系的不争事实,又是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场外的理论必须能够面向审美活动,能够走进文艺实践,能够有效地言说文艺文本和审美行为,能够合理地昭示审美与文艺的本质与普遍真理,这就需要理论转场,即各种场外理论从他场转进审美经验与文艺实践的在场,成为关于言说审美经验和文艺实践的美学理论。理论转场是理论成为美学理论的合理性所在。凡不能走进审美世界言说文艺文本与活动,揭示关于审美活动、文艺实践本质与普遍真理的理论,也许是关于其他场域的理论和学说,但绝不是真正的美学理论。如其自诩为美学理论,那只能是张江教授所说的“场外征用”,是对审美活动与文艺实践的“强制阐释”①。 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资本的生产与消费、把握世界的方式、历史的发展动力与评价标准等核心观念、关键范畴,源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些来自审美活动、文艺实践场外的关于世界、历史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观念,面向审美活动,深入文艺实践,以欧洲具体文艺文本和共同审美经验为阐释对象,揭示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与消费的特殊规律性,昭明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异化与复归的必然性,披露了西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审美文化和文艺生活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解放的现实性,解释了古希腊艺术高峰不可企及和不可重复的社会发展客观根据,阐发了悲剧与喜剧戏剧冲突的历史客观性,描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文学,评价了英法现实主义作家通过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来透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肯定了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超越,通过这种理论的转场,来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场外理论成为真正场内的美学理论话语。 中国古代美学博大精深,绵延不断。在中国古代美学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伦理学思想、哲学思想始终为其提供着理论观念和思想方法的支持。在中国古代思学行一体化的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理传统中,中国古代伦理学、哲学思想观念浸润在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直接理性表达。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念,同时也是关于审美本质的美学关键词。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本体论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审美理想的最高定位。自秦、汉以降,儒家“仁爱”、“中庸”的伦理学范畴成为诠释文艺文本,评价文艺活动的基本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主导风貌。先秦孔子的“诗无邪”、“尽善尽美”、“兴、观、群、怨”,孟子的“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事”;两汉司马迁的“发愤以抒情”,《乐记》的“声音之道与政通”,《毛诗序》的“诗言志”;魏晋曹丕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南北朝陆机的“诗缘情”,刘勰的“文之为德也大矣”、“风骨”;唐陈子昂的“兴寄”,韩愈的“气盛言宜”、“不平则鸣”,白居易的“为事”,杜甫的“不薄今人爱古人”,皎然的“诗教”;宋代欧阳修的“兴于怨刺”,王安石的“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明代叶燮的“理事情”、“才胆识力”,谢榛的“体志气韵”,李贽的“童心”,袁宏道的“性灵”;清代王士禛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袁枚的“性灵”等种种中国古代美学概念范畴,皆蕴涵着深远的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但又是对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最地道的经验言说和理性概括,是真正的古代中国本土美学话语。 西方美学的理论话语主要源自西方哲学对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转场。罗素认为,当古希腊人对古希腊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时,哲学就产生了”②,同时,美学也就产生了。古希腊人对普遍性问题发问的直接背景是宇宙起源诗。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许多片断以诗的方式叙述着客观世界的故事,表达着古希腊人以一种万物恒变又不变的观念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阐释发挥得愈自由、愈富于个性,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中与时间相关联的具体因素便丧失得愈多,由此出现了关于超越时间变化的万物始基是什么、万物始基如何变成特殊事物、特殊事物又何以成为万物始基等哲学本体论的普遍性问题。可以说,西方哲学发端于对古希腊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的解释,在对具体文本进行普遍性提问与回答过程中,转进于哲学场中,生产了最早的哲学话语。古希腊哲学话语出现后,又再次转场进入古希腊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悲剧的审美、文艺场中,古希腊人用哲学的概念、方法、话语,对神话传说、诗歌、戏剧文本进行理解和阐释,这就产生了苏格拉底“美即有用说”、柏拉图“双重摹仿说”、亚里士多德《诗学》等著名的美学理论。古希腊罗马之后,西方美学成为西方哲学的有机部分。如普洛丁“分享论”之于“太一哲学”,奥古斯丁“适合论”之于“教父哲学”,阿奎那“美愉论”之于“经院哲学”,培根的“虚构论”、霍布斯的“观念联想论”、洛克的“反思论”、夏夫兹别里的“内在感官论”、哈奇生的“趣味论”、休谟的“同情论”之于“经验主义哲学”,笛卡尔的“身心对应论”、莱布尼兹的“预定和谐论”、伍尔夫的“完善论”、鲍姆伽顿的“感性论”、莱辛的“动作论”之于“理性主义哲学”,伏尔泰的“规则论”、卢梭的“自然论”、狄德罗的“关系论”之于“人性论哲学”等等。 可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中国古代美学,抑或是西方美学,其生成、发展、流变的基本规定性都是场外理论向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转场。用场外理论的观念、方法,去发现、诠释审美的共同经验,总结、提升文艺的特殊本质,建造、言说关于审美和文艺的话语,是构建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同时,美学的发展史也证明了一种场外理论越深入到审美活动的内部、越准确地阐释具体的文艺活动,就越能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美学。一种场外理论越有效地发现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内在情状,它对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阐释与表达越能得到人们共同经验的确认和社会普遍诉求的肯定,它的转场就越成功,就越是能在学科的意义上成为美学。因而,更多的场外理论转入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成为在场的美学,是审美活动、文艺实践和美学自身不断发展的需要。场外理论转场为美学理论,是构建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具有理论构建的合理性。 二、理论转场的本土化是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路径 如果说场外理论走进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成为关于审美与文艺场内的美学,是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合理性路径的话,那么,理论转场的本土化则是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的必由之路。 美学作为对特定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一种思想话语和理论的表达,本土性、民族性是其拥有普遍性的内因。只有本土的、民族的美学才可能是全球的、世界的美学。西方美学的关键词大多来自于西方本土话语。如古希腊美学中的悲剧概念来自于古希腊古老的戏剧形式——“山羊剧”,苏格拉底美学的辩证概念来自于古希腊社会交往中的“诡辩”一词,亚里士多德的摹仿一词来自于生活中“发现后的学习”。康德美学核心概念审美判断来自于中世纪北方方言中的“味道”,17世纪的法国沙龙话语将其改造为“品味”这一文化用语,而18世纪英国美学家哈奇生又将“品味”转化为美学概念“趣味”,最后再转场为康德的“审美判断”。席勒美学中重要关键词显现就来自于德语方言“发光”、“发热”等等。在这方面,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转场是本土化的典范。 德国古典美学的基本观念、核心概念、主导方法,皆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场而来,其研究对象、问题导向、话题设计、立场观点、逻辑思路、思维方式、言语风格和理论结论,都具有启蒙运动以来德意志社会生活的独特性,鲜明地表现出德意志本土情境和民族情致。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对启蒙时代德意志本土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中不断生长的审美现代性,有着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理解,他亲身参与德意志本土和西欧大陆文化界关于新旧审美趣味优劣、古今文艺水平高低的大争论。他批判守旧的文艺观,倡导新兴审美理想,力求通过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消解启蒙时代西欧、特别是德意志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现象与本体、自然与人性、认识与实践、必然与自由的现代性分裂。康德认为,人的主体性中有一种被称为反思判断力的能力能够弥合这种现代性分裂。反思判断力在主体与世界发生对象性关系时,“只将客体的表象与主体联系在一起,不让我们注意到对象的性质,而只让我们注意到那决定与对象有关的表象能力的合目的形式”③,以此来调节现象与本体、认知与理念、感性与理性的背反。这种被称为反思判断力的感性能力就是人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是感性的,它源于自然生命,符合自然天性,且能沟通知性、顺从信仰,天然的感性承载着理性认同,个体的能力获得社会的确证。正因如此,审美是感性的却涵纳着理性,是自然的却拥抱着自由,是个体的却又顺随着社会,无功利却又暗合于最普遍的利益,无目的却又指向人类最高的目的。 在康德阐述审美判断理论时,他为审美判断设置了两个极富德意志本土文化特质的规定性:(1)审美判断是感性的,它拒绝理性一统天下,反对工具化。这个规定性本源于德意志民族的浪漫主义传统文化。(2)审美判断是自律的,不受外在概念、功利、目的规范,只受自身内部规定和要求约束。这个规定性又来自德意志本土新教文化因信称义的民族传统。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则从德意志力求主客体统一的哲学传统出发,认为“自我的本质既不是主观东西,也不是客观东西,而是一种同一性”④,具体表现为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自我设定自我就是自我创造自我,自我即存在。自我设定非我意味着人不仅是普遍的存在,而且也是具体的存在,只有非我才能证实自我的对象性活动。如此,在费希特那里,审美活动便是感性对理性的直观,是精神中普遍性的个体化,也是生活中个体性的普遍化。 而富有诗人情怀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则秉承德意志民族思与诗同一的文化观念,在物质与精神统一的高度上界定审美本质。在谢林看来,物质与精神本来就是绝对同一的两方面,物质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物质,感性是感觉到的理性,理性是思维中的感性。因此,谢林对自然山水与自然人性充满着诗意化的尊敬。其实,尊敬感性的自然是德意志文化不同于英法文化的传统所在,格劳秀斯、莱布尼兹、莱辛、歌德、康德、赫尔德这些德国启蒙大师无不对自然充满敬意。谢林一再强调,自然与诗一样,既是创造者,又是创造物,自然成为无意识的诗,诗成为有意识的自然。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面对德意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而人们却更深切地感受到社会冲突、生活不幸、精神分裂的本土状况,将消解德意志的社会冲突、和解文化对立确立为其哲学主题。黑格尔要“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⑤,如此就须把握美与艺术的本质与根源。黑格尔将美与艺术的本质界定为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绝对理念则是一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最初原因,而将美与艺术的根源描述为绝对理念在精神发展时期的感性阶段。绝对理念在思维中通过逻辑的否定之否定外化为感性的自然世界。感性的自然世界历经机械的、物理的、有机的否定之否定又发展为以精神为存在方式的人类社会。而在以精神为存在方式的人类社会中,主观精神被客观精神否定后,就进到绝对精神阶段。在绝对精神阶段,绝对理念以感性直观的形式认识绝对精神便产生了美、艺术,以知性表象形式认识绝对理念就生成了宗教,以理性思想形式认识绝对理念则造就了哲学。所以黑格尔说,美、艺术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在关于绝对理念层层递进的逻辑动态结构中,黑格尔为美与艺术设计构造了一个极具德意志文化特性的本质,赋予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客观历史力量,以此来消解德意志现代社会中主体性的内在冲突,和解德意志现实生活内部中的种种矛盾。由此可见,德国古典美学立足于德国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土现实,凭借着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哲学理路与方法,造就了德国美学的高峰。正是这种德意志的本土性、民族性,成就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全球性、世界性。 德国古典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迄今所公认的史上最有思想深度和理论力度的美学,它们的理论生命力和思想引领力,肯定了理论转场为美学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场外的理论,在转场进入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必须置身特定文化生存场中,成为特定审美活动的本土话语、具体文学实践的民族表达。理论转场只有实现了本土化,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才真正具有了合法性。 三、理论转场的当下性是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现实性路径 美学的生命在于其理论的社会实践现实性,以及对现实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进行直接言谈与指引的当下性。 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古代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中就具有很强的当下性,如先秦两汉的儒家理论以德言诗、以礼说乐,使先秦两汉的美学获得强大的现实性。魏晋南北朝以来,以道家理论诠释诗歌和书画,以性情论诗词、以心性话书画,使中国古代美学对历代诗词书画的创作与欣赏赢得当下的文化话语权。 当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转场进入审美活动与文艺实践之时,马克思面对的是欧洲工人阶级刚刚走上历史舞台的现实。马克思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⑥,就是他们的实践活动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⑦。应该“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⑧,在马克思看来,感性物质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他断言要解决人的内在矛盾、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的对立、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冲突、人类历史与人类现实的断裂等危机,只能依靠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改造现实社会,并通过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解放自己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展开在人与自然的社会关系中,造就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全面对象化和人对一切属人的对象的全面占有,这也就是人的彻底解放,最终的标志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⑨。 马克思将审美活动理解为人类生存、发展、解放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审美活动成为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对社会的革新、对精神的变更的社会力量,是“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⑩的客观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一旦将感性的审美活动理解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人类将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超越单一肉体欲望需求的审美活动使人意识到与自然界的不同,自觉地将自然作为主体实践的对象,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关系,“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12)。在这样一个感性的、实践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按照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来改造世界、塑造自己,即“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3)。由此可见,马克思将审美活动确认为物质与精神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当下现实的社会实践。马克思相信只有在客观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才能真正揭示审美的感性本质,他明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 从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审美活动,马克思将审美置于整个人类社会有序多层的现实社会结构关系中。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5)。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物质系统,这个系统是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现实地推动着社会前进,而且以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多形态、多方式地决定着其他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为其他社会构成的发生、发展规定了基本轨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物质存在结构上生长着源于社会物质存在结构却又具有特殊社会功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系统。上层建筑是社会法律、政治等制度体系和管理机构,而意识形态则是一切社会存在的文化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共同组建了人类社会的总体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同时,三者相互依存、相对独立,各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并互相渗透、作用、转化。 审美作为现代生活的文化意识活动属于意识形态这个大结构中的一部分,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7)。审美活动以其感性的特有方式把握着真实人生与现实世界的丰富性、真理性,在文化意识中建构自然,塑造主体,创生世界,“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18)。所以马克思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19)在审美活动中,自然通过文学艺术活动成为显现人的本质、表达人的情感的载体,凝聚着创作主体作为社会存在方式的特殊历史性和现实性。而人对文学艺术的鉴赏也成为对自我本质的直观与占有,表现为把握了对象与自身之后的喜悦和在喜悦中对自我与对象的再创造。换句话说,作为特殊的实践活动,马克思将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映生活、把握现实、直观自我,从而实现将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对象化确立为审美活动的社会文化规定性,使得文学艺术这种形象的意识形态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力量。 马克思还进一步从社会生产与消费方面探究文艺自律的实践性内因。在马克思看来,艺术是一种感性的社会精神生产活动,不过这种感性的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生产主体、生产过程、生产结果和对结果的消费,确实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也不同于其他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生产活动的生产主体是富有感性的想象力的艺术家,生产过程限定在审美领域,生产的产品是以感性形象为形态、以审美为特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文本,而对艺术产品的消费,则是对艺术文本中人类本质力量的感知、确证和占有,鉴赏的本质正在于此,“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20)。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审美活动与文艺实践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生产过程与产品、产品与消费对立、断裂的现象。正因如此,艺术“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1),且直接塑造了人的主体能力,“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22),艺术生产使非人的感觉成为属人的审美感觉,非人的情感成为属人的审美情感,非人的被动的占有变成了属人的创造性享受。艺术生产的这种自律性又生成了艺术消费的自律性,“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对象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它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23)。具体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具体主体的审美能力,而人的审美能力的每一次形成与增长都是人的自由本质的一次获得,是人的真正解放的一次实现。 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自律性还使艺术发展具有了特殊性。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24)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自律性也解释了古希腊文学艺术为何在当今仍具有巨大魅力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人类发展中的正常儿童,充满了令人愉快的天真,饱含着人类实践的历史真实性,展现着人类生活的某种完美性。对它的欣赏是现代人对人类自然天性的观照,也是现代人对人类自由本质的一种复归与创新,古希腊伟大文艺作品的永久魅力正在于此。基于对艺术生产与消费活动自律性的坚信,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背离审美本质、否定艺术自律的社会根源进行了彻底批判。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极端的私有化和剩余价值剥削,异化劳动也发展到顶点:劳动者同自己生产的产品分离,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强大,劳动者就越渺小;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分离,劳动过程成为奴役劳动者的活动;劳动者与自己的自由本质相分离,劳动成为对人的本质的否定。严重的异化劳动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对抗,这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严重异化的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蜕变为物与物的关系,一切生产与消费都成为金钱的生产与交换,文学艺术也不能幸免。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26)。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地揭露与批判的同时,马克思又赋予文学艺术以伟大的使命。一方面,他希望文学艺术不断确立着人的自由本质,使真善美“不仅作为工人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成为工人阶级“作为人所应有的各种需要”(27),成为工人阶级作为获得人的存在与权利的有力动因。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文学艺术成为强大的社会批判武器,在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中揭露与否定丑恶现实和人性异化。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英法批判现实主义极为推崇:“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莱、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28)。马克思认为英法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对黑暗的揭露、对异化的批判以及对美好的希望都对认识与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起着积极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可见,马克思通过对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本质与规律的揭示,使马克思主义美学迄今具有强大的现实活力,成为理论转场具有当下性的光辉典范。 在美学的发展历史中,也有美学理论因未能面对社会审美经验的转型与文艺实践的发展而即时转场,使其理论话语失去理论的思想表达有效性和文本阐释的当下性而最终解构的教训。20世纪60年代,以蔡仪、以群等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借鉴苏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汲取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经验,总结“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新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以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这两个核心概念为轴心,在文学本质论、发生发展论、作家论、创作论、作品论、鉴赏论、批评论等方面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对中外现实主义文学实践,尤其对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名家名作和新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实践做出了当下极有说服力的阐释,在那个时代具有巨大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当代最系统、最权威的教科书式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审美活动中先后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文学、网络文学等一系列全新的文学实践,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理论却没有实现理论转场的当下化,没有即时调整、改进、提升自己的话语意涵和方式,当它走进当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实践活动中,参与新时期的文学实践、解释新时期的文学文本、指引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就失去了理论的当下有效性,理论话语逐渐哑化。这一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曾经最富中国化、最具时代性的主流文学理论的社会实践功能逐渐边缘化了。历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生动地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理论转场的当下性是构建当代美学话语体系的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理论转场是构建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其内在要求在于场外理论必须身处当下审美文艺场中,面向现实审美活动,以其话语的本土化、当下化为其话语的合法性、现实性,才能真正建构能够总结中国审美经验、阐发中国文艺实践、具有强大信服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当代美学理论话语体系。 ①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②罗素:《西方的智慧》(上),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③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in Paul Guyer et al.(eds.),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Immanuel Ka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 p.70. ④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梁志学、李理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7页。 ⑤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页。 (2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9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6页。标签: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古希腊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德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