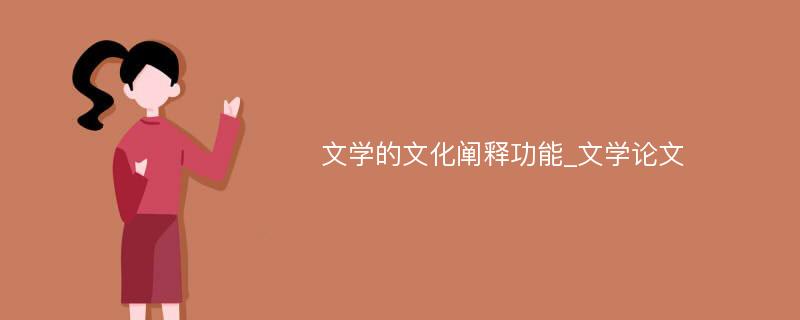
文学的文化阐释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文化涵盖了人类创造活动的一切,文化价值涵盖了整个文学的价值属性。文学的价值就是文化价值,文学价值的形态,即通常人们说的文学的功能,就是文化阐释的功能。
这里不是从普泛的大文化角度,而是特定的具体的某种文化角度,即从民俗学、宗教学、哲学价值的角度,来谈谈文学的文化阐释功能。在这样一些方面,文化的特征往往特别鲜明,文化的内涵往往厚重而彰著,又比较地难以为其他文学价值功能的论述所完全容纳。在我国,它们甚至一度曾经被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价值所掩盖,受到轻慢和忽视。实际上,民俗学、宗教学、哲学价值在文学的价值属性中,当是最古老而又最普泛的属性。而其表现形态,又追随历史的前进和文学的发展,时时绽放新花,展露新容,因而又极富现代价值内涵和现代审美意味。对于文学中的民俗学、宗教学、哲学价值问题的探讨,应该成为一个受关注和重视的话题。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最优秀的诗歌作品是所谓十五“国风”,即今天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一带的民歌。这些民歌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地方民风、民俗的表现特色。当时的统治阶级在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采集和整理,其思想动因就是借此了解天下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反映,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和对策,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可见,民风、民俗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项内容,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是文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因为其具有地域特征,也就赋予了文学以地方色彩,且成为考察文学价值效应的一个视点。自古至今的收集民歌的活动即采风的活动,其着眼点也在民风、民俗。
但是,文学从来不是为表现民俗而去描写民俗,描写民俗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反映社会生活,以人为主体的、一定地域的、具体的、表现为特定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社会生活。因此,注重于民风、民俗的描写的文学创作,必须通过民俗的描写展现出生活的整体的面貌,展示生活的全部的丰富和复杂,发展和变化,必须写出人物,写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茅盾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正确:“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关于乡土文学》,1936年2月1日《文学》第6卷第2号)20年代中期兴起的乡土文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股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乡土文学作品具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价值。其所描绘的各地农村社会风俗图画,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组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中国社会极有特色的生动画卷。乡土文学作为现代新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的重大贡献,其价值既在于民风、民俗的生动描写,更在于透过民风、民俗描写,对于中国宗法制农村社会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现实主义表现,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地域环境和人物性格,外在的民风习俗和内在的心理气质,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既历史悠久又幅员广大。各个地方由于自然条件,例如山川、气候、物产的不同,和文化传统、历史开发迟早的差异,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习惯爱好、心理气质,各具特色,不可互换。文学的民俗学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不但要描绘出该地区的自然风貌和生活习俗的生动图画,而且要开掘出那为一方水土所养育和陶冶的人的灵魂和精神风采。因此,文学作品的民俗学价值的文化阐释、需要从民风、民俗的表层、深入到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处,才不致流于表面和肤浅。在这方面,80年代的寻根文学似乎更具有自觉的意识。
寻根文学热衷于表现现代社会中仍处于原始自然状态下的古风遗习,这种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偏远角落的古旧习俗的描写和表现,却以现代精神为参照,伴随着痛苦的思索和深沉的理性剖析。民族历史风情风俗的描写,其意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和民族心理结构的探寻。寻根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是某种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体。有的形象,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于一身,例如韩少功笔下的丙崽一类形象。有的形象,更多地表现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强烈追求,表现出某种民族文化的理想境界和复杂状态。例如阿城、郑万隆笔下的形象,王一生们,《异乡异闻》中的垦荒、开边者硬汉们。作家们希望自己的创作“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并“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韩少功:《关于文学“寻根”的对话》,1986年4月26日《文艺报》)。
需要指出来的是,寻根文学虽然对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和民族心理结构的探寻,更具自觉意识,并因此使创作具有思想的和民俗文化价值的曾所未有的深度,但在艺术表现上却留下了较多的有意为之的斧凿痕迹,民俗的描写和形象的刻绘,以及作品情调、氛围的整体营造,不及20和30年代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那样自然天成。这与寻根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努力追求艺术表现上的陌生化的题旨有关,但也是这种借鉴和学习尚未能得心应手、融会贯通的证明。
宗教和文学的结缘,起始于人类社会的早期。远古时期的人类童年阶段,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贫乏,人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自然,只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解释周围世界。宗教依靠想象力与意象构造神的世界,维系信仰体系。文学依靠想象力与意象创造形象和意境,借以抒发内心的情感。这种内在的一致与和谐,使得文学艺术和宗教自始就处于一种同胎孕育,共生共长的混同融合状态。人们在产生宗教意识、宗教观念、宗教情感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原始的未被文字记载的诗歌、神话、故事、传说等文学。文学艺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其关系密切不可分割。文学艺术最初是作为宗教礼仪的表现形式和工具而出现的。进入中古时期的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和文学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宗教借助文学的力量,运用生动形象的神话、故事阐述教义,运用有韵律、有节奏的诗歌祭祀、祈祷和赞颂神灵。宗教利用文学为自己服务,促进了宗教文化自身的发展;宗教赋予文学以宗教文化阐释的功能,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正因为文学与宗教之间这种互为影响,互相促进的紧密联系,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学价值。古希腊神话显示着多神教的价值,《一千零一夜》显示着伊斯兰教的价值,《神曲》显示着基督教的价值,中国古代许多诗歌、小说、戏曲作品显示着道教和佛教禅学的价值。更有一种十分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应当引起人们更深刻的关注。世界上最著名的宗教的经典,佛教的《百喻经》等,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同时又是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但源源不断地为文学创作提供和输送题材、故事、情节和人物,而且在思想上、精神上、意境上和趣味上,滋润和培育文学创作。它们不但是文学创作的材料库,而且是作家灵感产生的源泉。同时,这些成书年代甚早的宗教经典,其自身在艺术表现和文字修辞上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和文学的密切联系,对文学的影响,范围逐步缩小,力度逐步下降。但是却又仍然不容漠视。文学不再是宗教的直接的载体,宗教和文学大多不再呈现出重叠的、交叉的混融结合状态,但是,宗教的意识、精神、情绪仍然渗透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于文学的潜在的深刻的影响。基督教和西方文学之间,伊斯兰教和一些亚非地区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文学之间的深刻的精神联系,这里暂且不论。即以中国的现代文学为例,宗教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就是相当地鲜明可见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深处,中国现代文学的血脉里,流淌着和涌动着一股深深的不可割舍的宗教文化的情绪和情结。
任何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通读者都无法回避和不能不正视这样一种文学创作实际和文学史事实的存在。新文学初期即出现了冰心、王统照、叶圣陶、庐隐等人热情宣扬的“爱的哲学”的创作群体。冰心等人的那些“爱的哲学”的诗歌、小说和散文,正是以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为其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的。新文学作家中也出现了以文学创作阐释宗教文化要义和真谛的代表性人物,这就是许地山。许地山的整个文学创作深受基督教、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佛教的生本不乐思想,道教的顺应自然的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共同构成他作品的独特的人生境界。此外,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曹禺创作中的宿命论、原罪倾向,巴金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激情,老舍小说中的平民观念,郭沫若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都和基督教文化有着内在的渊源关系。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的创作,又弥漫着佛教禅宗的宁静、淡泊、达观的文化氛围和情调,林语堂、沈从文的作品中,则有着道教传统文化自然、率真、飘逸的影子和印痕。
夸大宗教对于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无疑是不正确的,但是,忽视甚至漠视即使在科学倡明发达的现代文明时代,宗教对于文学仍然具有某种影响力和渗透力,无疑同样不正确。宗教和文学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学追求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宗教同样追求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解释,和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关注。文学和宗教在精神上有着相通和一致的地方。不论社会如何进步,科学如何发达,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生活中间,无论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们自身的种种复杂关系之间,仍然有着许多令人难以索解的谜团,存在着令人惶惑的大自然之谜,人类生存之谜。人类仍然面临着一个广大的未知的世界。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疑难,特别是人们精神上的、心灵的和感情的种种疑难。为求得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平衡和感情的解脱,人往往求助于宗教。精神信仰的需要,形成宗教存在的心理基础。从更宏大、广阔、深远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宗教和文学之间互为影响,互相促进乃是事物发展的符合规律的现象。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人为的因素,宗教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时断时续的,但是却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一般地说,社会发展平稳安定,思想开放自由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和理解趋向多义和多元,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就大一些。例如“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初始时期和发展时期就是这样。政治动荡、斗争频仍,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封闭的情况之下,人们对文化的选择和理解趋向单一和固定,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就会小一些。三十年代后的中国社会便是如此。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和禁锢封闭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80年代的文化热,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力开始活跃起来。作家们在为文学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在提升和完善自身的精神建构的努力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宗教,开始从宗教文化中吸取营养和借镜。贾平凹的作品表现出对佛教精神积极思考的心态,企图以佛老的从容淡泊超越现实的纷乱,对抗物欲横流的世俗世界,平衡内在心灵世界失重的苦闷;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将佛教和藏民族的精神心理联系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借此考察现代化进程中藏民族神秘的精神信仰的复杂形态,写出时代赋予藏民族精神心理的震动;阿城以道家的思想作自己的精神信仰,又在自己的创作中力图对道家思想作出适应时代变化和实际人生体验的现代阐释,借以寻找和确立自身的精神定位;史铁生的小说注重基督教文化价值的开掘与弘扬,赋予基督教的博爱情怀以精神拯救的意义;张承志的小说把政治热情和宗教热情结合在一起,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皈依中,寻找捍卫理想的力量等等。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涌动着一股显在的、清晰可辨的宗教意识和宗教精神。宗教文化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深度,促进了当代文学主题开拓和美学风格的多义性和多样化、多元化,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话语。
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最为重要和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哲学价值。文学不只是再现生活,还要表现生活;文学家不只是描述生活事实和生活现象,还要表达对于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文学是人学。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展示,对于人的性格、命运的描写,对于人的精神、灵魂的追问,是文学表现的中心和重点。在文学的人学命题的内涵中,包含了对于人的本质、人性人情问题的理解和阐释。因此,作为特殊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意象、直觉的,也是概念、推理的。感性的、意象的直接审美表现中,隐蔽着理性的、观念形态的对于生活、对于人的理解和认识,即隐蔽着关于自然、关于社会人生的哲理性认识。理论形态的哲学和审美形态的文学之间,表面上似乎横亘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哲学指导和滋润着文学创作,给文学以思想,以力量和深度,赋予文学以超越具体对象的整体性的、形而上的深刻文化蕴含。文学和哲学始终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轨道上发展和前进。
哲学价值既是文学自身的文化选择,也是作家自觉的文化选择。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以对生活表象的琐碎事实的描述为满足,而希望自己所描写的个别的、具体的、有限的生活内容,获得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本质属性,使之通向无限的生活的海洋和辽阔的生活的天空。即是说,使创作获得高于具体生活的特定涵义的某种对于整个历史、现实、人生的抽象的艺术概括和深刻的理念蕴含。契诃夫说过,真正的艺术应当在真实的生活画面中像渗透汁水样地渗透着目标感。这目标感正是基于对生活的整体的深刻认识的思想哲理。而高尔基1923年写信给罗曼·罗兰诉说自己创作中的苦恼,这苦恼就是他有时在对生活的描写中不能具有一种对具体生活的超越,而只是在纯粹地说着故事,他因为无法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整体性的上升为哲理的认识而苦恼。南斯拉夫当代作家斯韦塔·卢基奇则正是在具有“鲜明的哲学和理性的色彩”的意义上,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小说艺术,认为是“一种更高级的现实主义”。
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相比较,现代主义的文学对哲学价值的文化阐释表现了更高的热情和更强烈的愿望。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期暴露得更加彻底和充分,两次世界大战更使人们受到强烈的震撼,昔日的理性、传统观念和信仰被血淋淋的现实砸得粉碎,一种无力把握命运的怀疑悲观情绪笼罩着社会,一种重新探求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哲理思索成为时尚。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哲学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结。萨特在谈到哲学与文学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是自己“写作的基础和依据”,并且说“我在作品中陈述了个人的哲学见解”;加谬声称“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引自《存在小说经典小说选·“存在”小说导论》,作者张容)。从创作实践上看,萨特和加谬等人的作品,也是以阐释其存在主义哲学体系中有关“存在”的思想为主的文学。包括存在主义哲学在内的西方近现代哲学,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直觉哲学等等,对我国的当代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一些锐意求新、力图突破创作固有模式的作家尤其是年青一代的作家,争先恐后地和不约而同地从西方近现代哲学借鉴和吸取思想的和精神的养料。这样一种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创作原有的精神风貌,而新造了和重铸了新时期文学崭新的精神风貌。
文学作品的哲学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和宗教价值交织在一起。因为在实质上宗教也是哲学,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哲学。凡是富有宗教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一般也富有哲学价值蕴含。这是最为一目了然的事实,在前面论述文学的宗教价值问题时实际上也已涉及到这种宗教和哲学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冰心等人文学创作中的“爱的哲学”,实质上也就是基督教的“爱的宗教”。这一方面的问题似乎无须多加说明和论证。
文学寻求哲理,文学阐释哲学。当然文学并不等同于哲学,文学仍然是文学。文学家不应当在作品中大写哲学讲义,在任何感性形象、文艺形式里也不可能容纳得下一种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全部思想观点。文学艺术审美的特点和自身固有的规律不允许这样做,即使是对非常热衷于表现哲理的作家而言,也是如此。但是,文学艺术寻求诗情和哲学的更深刻结合的变革趋势,又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改变了作家接受和体验生活、形象的方式,也引起了文学艺术对于自己内在结构关系的某种新的调整和改造,以便在文学的艺术表现上寻找一种具体性和抽象性的新的平衡,以使文学创作在既不放弃艺术的形象美的同时又尽可能求得扩大主题、思想、寓意的哲理的容涵。
文学与哲学进一步联姻和结合的文学发展现状对文学评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文学批评应该在文学构造的相互辉映的现实的与形而上的两个世界中,仔细谛听和深刻感受创作主体发自内心深处的关于世界、关于人生的哲学叹喟,并进而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去与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对话与交流,去解读和阐发作品的哲学价值。这就要求作为接受主体的批评家不但是一位审美情感的体验者,而且是一位能够从哲学的理论高度来阐释人生的文化哲学家。现代西方许多批评家都是这样的文化哲学家。他们从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中,发现了人的异化的哲学问题,从屠格涅夫的作品中,解读出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从莎士比亚和其他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的作品中,发掘出人文主义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当代中国的许多批评家也正在努力成为这样的文化哲学家。当文学批评站在世纪末用总结性的眼光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道路时,突破了单纯社会学和政治家的思想的藩篱,多了一份哲理的沉思和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探寻,许多被误解甚至被曲解的作家及其创作因此获得重新评价,被重新确定了历史地位。近年来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阿Q的研究,散文诗《野草》的研究,在思想的艺术的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新的突破,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作品和阿Q性格中的哲理意蕴、哲学意义得到了更深刻的发掘和更科学的认识。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文学批评同样注重从其和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的联系上,去开掘和阐发作品深层的人生内涵和人性内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哲学价值解读和阐释的重视,说明了文学在发展在前进,文学批评也在发展和前进。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