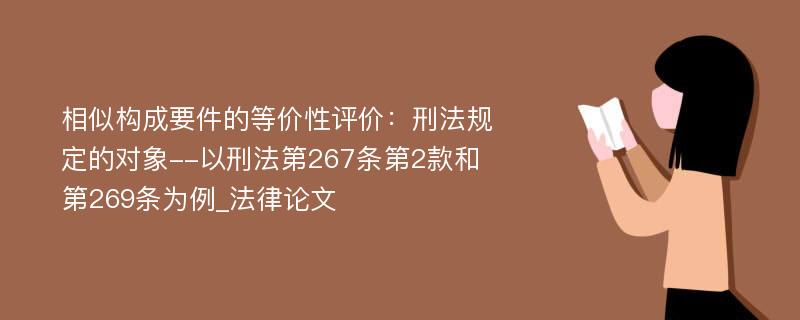
相似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刑法中拟制的对象——以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为例论文,对象论文,评价论文,构成要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28(2013)04-0110-14
一、理论、司法解释及案例分歧之争点
法定拟制是指立法者“有意地将明知为不同者,等同视之”。[1](P142)与被参照的法条相比,“法定拟制可谓是一种特别规定。其特别之处在于即使某种行为不符合刑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刑法明文规定的特殊条件下也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论处”。[2](P632)作为立法技术的拟制是法律观点的表现方式之一,即通过隐藏的方式指示法律适用者适用相关的规定,无论一般情况还是特别情况,适用与否只能根据拟制规定的应有内涵以及规范目的作出解释。然而,在我国理论与实践中由于没有准确地揭示拟制规定的逻辑内涵,对其是否适用以及在什么范围内适用并未达成共识。例如,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能否成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抢劫罪的主体,刑法理论、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判决都存在极大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观点:肯定的观点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的刑事责任主体。[3](P167-169)[4]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2003年4月18日《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有关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指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204号指导案例中,被告人姜某(15岁)在对被害人孙某实施抢夺行为之后,为了抗拒抓捕,将协助孙某抓捕的出租车司机打伤(轻伤)。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认定姜某的行为成立转化型抢劫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5](P86)否定的观点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人不是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的刑事责任主体。[6](P66)[7](P207)[8]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月11日《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0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777号指导案例中,被告人王某(14岁)潜入被害人戴某家中盗窃,在准备离开之际被戴某发现,为了抗拒抓捕,将戴某的头部、手部咬伤(轻伤)后逃跑。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二审法院认定王某由于对盗窃不承担刑事责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成立抢劫罪,不承担刑事责任。[9](P35)
相对于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典型的抢劫行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是拟制的抢劫行为。正如法谚“法律拟制背后经常隐藏着衡平(in fictione juris semper aequitas existit)”所指出的,拟制以违背真实性的方式,造成合理的、符合是非感的结果。[10]拟制虽然整体上不符合形式逻辑,但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法定拟制常常表明,它除了“单纯的参考”、“不真实”或“形式的”之外,它同样是真实的。[11](P26)然而,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对拟制规定的适用存在诸多误解。从上述理论、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案例争论中,本文认为若要正确适用拟制规定,必须澄清以下三个问题:(1)拟制的对象是什么(构成要件抑或法律效果)?(2)拟制规定的逻辑内涵如何表现?(3)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应当如何限制?拟制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法谚“无法律,无拟制(numquam fiction sine lege)”[12]表明拟制只能由立法者以法律规定,司法机关不得创设法律拟制。本文讨论的拟制是立法上的拟制,即法定拟制,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表现方式之一,与司法机关作出的类推解释存在本质的区别。本文首先从拟制对象存在的分歧展开,其次论证拟制规定的逻辑内涵,最后说明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的限制。
二、拟制的对象:构成要件抑或法律效果
在现代意义上,法定拟制逻辑结构表现在三方面,即拟制的基础、拟制的对象和拟制的效果。[13]拟制的基础是拟制规范得以成立的正当性基础和前提,①拟制的对象是拟制规定得以成立的核心和关键,拟制的效果是拟制基础和拟制对象共同作用下的逻辑结果。[13]拟制规定的正当性基础是在法律规范之外讨论的,在拟制规范内部讨论的主要是如何理解拟制的对象与拟制的效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准确理解拟制规定的关键。在拟制规定的具体适用中,法律适用者经常混淆了拟制的对象和拟制的效果之间的关系,致使拟制规定在适用中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如第204号案例与第777号案例的判决)。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需要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存在各种争论,本文将其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拟制说、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和区分说三种观点。
(一)构成要件拟制说
构成要件拟制说认为法定拟制是比较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在整体上确立二者的相似性,通过类比推理的方法使二者在规范上等同评价,进而赋以二者相同的法律效果,即“依照第×××条定罪处罚”②。例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法定拟制的目标通常在于:将针对一构成要件(T1)所做的规定,适用于另一构成要件(T2)。……为达到此目标,他(立法者)指示法律适用者:应将T2‘视为’T1的一个事例”。[1](P142)换言之,“拟制之作用并不在于将不同的法律事实,事实上予以同一化,而只是要求在规范上给予系争事实以相同评价。”[14](P204)其结构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构成要件→(规范上)等同评价→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
就具体的拟制抢劫而言,立法者通过对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构成要件的拟制,使其与第263条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能够等同评价,并依照刑法第263条定罪处罚。例如,张明楷教授指出:“该条(指刑法第269条——笔者注)规定的行为(T2)与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T1)原本存在重大区别,或者说该行为(T2)原本并不符合刑法第263条的规定(相关规定)的构成要件(T1),但第269条对该行为(T2)赋予抢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2](P632)同理,在第267条第2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又如,最高检的《答复》指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了刑法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抢劫罪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答复》没有明确是对构成要件的拟制,但实质上与构成要件拟制说的观点一致。在日本、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中也有类似于我国刑法第269条拟制抢劫罪的规定,也是从构成要件能够等同评价的视角解释拟制抢劫罪的。例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指出:“对于盗窃犯在盗得财物之后,为确保已盗得的财物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情况,如做实质性评价,则可视为通过实施暴力、胁迫行为而获取财物,因而应与强盗罪作同样处断”。[15](P139)又如,在德国的司法判决中认为:“抢劫性盗窃与抢劫同等看待是以两种行为方式在犯罪心理学上的可比较性和等价性为基础的:为了保护赃物使用暴力或威胁,同样是为了达到取得财物的目的”。[16](Rn3)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的大法官解释(释字第630号)中也指出:“经该规定(第329条规定的准强盗罪——笔者注)拟制为强盗罪之强暴、胁迫构成要件行为,乃指达于使人难以抗拒之程度而言,是与强盗罪同其法定刑,尚未违背罪刑相当原则,与‘宪法’第二十三条比例原则之意旨并无不符”。[17](PA-627)从上述的观点中可以发现,构成要件拟制说关注的是,通过对构成要件拟制,把形式上不同的两个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相同的法律效果是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逻辑结果,或者说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是赋以相同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
(二)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
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认为拟制的对象是法律效果而非构成要件,或者说拟制规定是直接“准用”基本规定的法律效果。该说主张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是不同的,由法律直接规定对拟制法条赋以(或准用)基本法条的法律效果,使不能等同评价两个刑法规范获得相同的法律效果。其基本的结构为:(事实上)两个不同的构成要件→赋以(准用)相同的法律效果。我国的刑法理论习惯把拟制规定称为“准犯”,于是普遍认为“准犯”就是“准用(比照)规定”。“准用(比照)规定”是指基本法条所规定的案型与引用的法条所规定的案型在事实上不同,但是存在类似之处,基于平等原则,对二者作同一处理的情形。[14](P174)例如,陈兴良教授认为:“一般准犯是指对某种类似于某种犯罪的行为通过法律推定,规定以该罪论处的情形”。[18]又如,曲新久教授认为:“转化型犯罪属于各种具体犯罪的‘准’犯罪类型,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携带凶器抢夺的危害性低于抢劫犯罪,更显然低于携带凶器抢劫”。[19]再如,张小虎教授认为,刑法第269条规定(准型转化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其虽不完全符合该条所规定的转化犯罪(抢劫罪)构成要件的标准形态,但是却依照抢劫罪论处。[20]按照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的观点,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但立法者直接对拟制规定的法律效果进行拟制,或者法律规定直接“准用”基本规定的法律效果,使其与基本规定的法律效果相同。例如,最高院的《解释》第10条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该规定的言下之意在于第269条规定的行为不能与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行为等同视之,即不是抢劫行为,只是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或者准用抢劫罪的法律效果而已。因而,既然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的不是抢劫行为,也就不能按照抢劫罪论处,只能根据情况成立其他的犯罪或者无罪。又如,曲新久教授认为,刑法第17条第2款是对具体行为的规定,不是具体罪名,具体罪名的有无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罪状的规定,进而认为只有第263条规定的才是抢劫行为,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的规定虽然按照抢劫罪论处,但是其规定的不是抢劫行为。[19]也就是说,拟制法条与基本法条规定的罪状(构成要件)是不同的,相同的法律效果不是从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把不同的罪状(构成要件)与相同的法律效果直接对应,相同的法律效果是直接拟制或者“准用”的结果,或者说拟制的对象是法律效果。事实上,虽然拟制规定和“准用(比照)规定”都表现为引用相同的法律效果,但是“准用(比照)规定”与拟制规定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主要表现为:(1)对于形式描述的构成要件的看法不同。拟制是将形式不同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并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但“准用(比照)规定”将两个形式上不同的构成要件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2)具体适用上存在差别。拟制规定由法律明确规定了构成要件,且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严格对应,故可以直接适用。而“准用(比照)规定”所指的构成要件与准用的法条之间只存在大概的对应,不能直接适用,适用与否由法官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以及具体情况裁量。[21]本文认为,拟制规定与“准用(比照)规定”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对应“类推”与“比附”的关系。[22]拟制规定和类推的重心在于构成要件或案件事实的相同评价,而“准用(比照)规定”与“比附”侧重直接援引的法律效果或刑罚,以适用相应的法律效果或刑罚为目的。因此,“准用(比照)规定”关注构成要件在形式描述上的不同。
(三)区分说
区分说认为拟制法条能否适用,需要“具体考察拟制情形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给予与引用法条相同的法律评价。对拟制情形在多大范围内可适用拟制引用的法条,必须考虑立法意旨,针对具体情形,斟酌在何种程度上拟制情形可以适用引用法条”。[23]区分说认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携带凶器抢夺与抢劫行为在法益侵害程度上有相当的差别,无论基于何种立法政策考虑,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携带凶器抢夺行为都无法与抢劫罪等同评价。但是刑法第269条的情形不同于第267条第2款,事后抢劫在法益侵害程度上与抢劫罪基本相当,即具有取财行为与暴力行为,区别仅在于暴力行为的时间点不同。因而,第267条第2款的拟制抢劫不适用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第269条的拟制抢劫则可适用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23]区分说在承认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都是法定拟制的前提下,对第269条是按照拟制规定的本质进行理解的,可以与典型的抢劫行为等同视之。但是在第267条第2款的解释中又放弃拟制的前提,认为不可以将其作为抢劫行为来看待,因此对于能否适用法定拟制需要视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四)学说的评析及反思——基于方法论的立场
拟制是立法者作出的不可反驳的决断,其适用是由拟制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能否成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的刑事责任主体,需要结合法定拟制的本质以及拟制的对象的形式描述与规范评价之间的相互关系综合认定。
1.构成要件拟制说的方法论意义
构成要件拟制说把拟制法条与基本法条的构成要件相类比,如果二者可以作相同的评价,则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反之亦然。在方法论上,拟制是现存构成要件的最终对比,把不应当同等对待的事物相同看待。[13]虽然在事实层面,刑法第263条与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的构成要件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没有拟制规定,那么只能根据其他规定认定犯罪。但法定拟制是对“不同构成要件的相同对待的一种法律命令的表达方式”[11](P26)。法定拟制整体上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其中包含了政治和权力的因素。[24](P138)在规范层面,法律有意识地将两个不同的事实构成等同,以期待取得预期的法律效果。[25](P64)具体而言,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与第263条规定的构成事实不同,立法者明知存在这种不同时,由于二者具有相同的意义内涵和规范目的,将二者在规范上等同评价,并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构成要件拟制说既看到了构成要件在事实上的不同,又看到了构成要件在规范评价上的相同。此外,构成要件拟制说把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作明确的区分,虽然二者总是相互伴随出现,但是真正的核心是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拟制规定是刑法规定的一部分,而不是立法解释,故不能认为拟制本身违反罪刑法定原则。[2](P634)因此,构成要件拟制说正确地看到了拟制的本质特征以及拟制对象的形式描述和规范评价之间的关系,把拟制的抢劫行为与基本的抢劫行为在规范上等同评价,进而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同样可以成为拟制的抢劫行为的主体。构成要件拟制说对理解拟制规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第一,构成要件拟制说通过“类型比较方法”将拟制的抢劫行为与典型的抢劫行为等同评价,赋予二者相同的法律效果。“类型比较方法”对新出现的类型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为不同类型的抢劫罪的确立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第二,构成要件拟制说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实现了两个不同的构成要件之间的等同评价。例如,在典型的抢劫行为和拟制抢劫行为中都包含有取财行为和暴力或胁迫行为,虽然二者之间存在一些差别,但是立法者选取关键的共同点,通过类比推理的方法使两个已经类型化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获得相同的意义内涵。第三,构成要件拟制说遵循了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即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之所以能够赋以相同的法律效果,是因为二者的构成要件在规范意义上可等同评价的缘故。第四,构成要件拟制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关注定罪标准的协调统一。例如,第204号案例的裁判理由中明确说明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当成为拟制抢劫罪的刑事责任主体,是定罪标准协调统一和该类型犯罪的本质特点的要求。[5](P88)在拟制规定中,类型化思维与类比推理方法也要求构成要件之间在整体意义上具有一致性。第五,构成要件拟制说是基于同一规范目的思考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之间关系的。例如,在拟制抢劫行为中包含诸如盗窃、抢夺、诈骗以及伤害、杀人等多种行为,不是单独考虑各个行为的规范目的,而是在抢劫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之下展开的。第六,构成要件拟制说能够明确区分立法与司法。立法论上的思考是关于法律的思考,司法论上的思考是根据法律的思考。[26]构成要件拟制说不关注那些法学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而是从客观的角度分析拟制规定应有的真实内涵,回到拟制规范本身去思考它的内在逻辑。
2.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的方法论批判
就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而言,值得肯定的是,这种观点看到了拟制抢劫与典型抢劫在事实层面上的不同。因为,“如果没有第269条的规定,对上述行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笔者注)就不能以抢劫罪论处,而只能对前一阶段分别认定为盗窃、诈骗、抢夺罪,对后一阶段的行为视性质与情节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者仅视为一种量刑情节;如果没有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拟制,对于单纯携带凶器抢夺的,只能认定为抢夺罪,不能认定为抢劫罪”。[27](P589)但是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却忽视了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与第263条的构成要件在规范评价上的等同性,完全从形式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例如,曲新久教授认为:“依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应当对抢劫行为负责,但是并不对所有的抢劫罪负责”。[19]而事实上,法定拟制常常通过一种例外突破正式维持的法律规范。[28]根据曲新久教授的看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能够成立抢劫罪,但不是抢劫行为。换言之,非抢劫行为可以成立抢劫罪。这种观点也与我国古代的“比附”③制度具有了某种家族的类似性。本文认为,这种观点错误地把法律效果当作拟制的对象,把法律效果视为拟制对象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的问题。第一,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混淆了拟制规定和“准用(比照)规定”。拟制规定与“准用(比照)规定”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例如,“准用(比照)规定”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不需要严格对应,其重点不在于两个构成要件是否可以等同评价,而是是否给予刑罚处罚,因此套用“准用(比照)规定”的思维理解拟制规定必然误解拟制规定的本质。第二,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或者把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构成要件视为抢劫罪的概念而非抢劫罪的类型,或者将抢劫罪的概念与抢劫罪的类型混为一谈。事实上第263条的构成要件只是一种类型化的规定。正如考夫曼指出的,“类型无法被定义,只能被描述”[29](P117)。“立法之目的:完全将类型概念化,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在具体的法律发现中必须一再地回溯到制定法所意涵的类型,回溯到作为制定法基础的模范观念”。[29](P119)单纯地采用概念的方式去界定抢劫行为,必然会造成处罚上的漏洞。第三,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对拟制规定采用了反向推理的方法,试图说明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不同。但是无论类比推理还是反向推理,选取的都是对整个案件性质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而不是那些在定性上可以忽略的因素。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仅仅因为拟制抢劫和基本抢劫存在不重要差异就作出的反向推理是站不住脚的,也不符合反向推理的要求。更何况,拟制规定是不可以通过举证的方式推翻的。第四,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之所以会认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按照抢劫罪论处,但不是抢劫行为,是因为没有揭示其内部的逻辑关系。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忽视了在拟制的内部同样存在的逻辑推理(设证、归纳和类比)的要求,忽视了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虽然拟制在整体上并非完全是一种逻辑推理的结果,但也并非是一种恣意的行为。立法上对两个形式上不同的构成要件赋以相同的法律效果是因为两者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可以等同评价。第五,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对拟制规定采取的是一种个别化和分离式的思维,即前行为和后行为都不能成立犯罪,那么前行为和后行为相加也不能成立犯罪。例如在第777号案例中,法院认为,由于行为人王某不对盗窃罪承担刑事责任,那么王某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拟制抢劫行为的主体,也就不能要求其承担拟制抢劫罪的刑事责任。[9](P36)这种个别化或分离式的思维模式不能从整体意义上考虑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可等同评价,因而不符合拟制规定类比推理的方法和构成要件类型化的要求。第六,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只看到形式上的不同,忽视了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是受同一刑法规范目的的指引的要求。正如考夫曼所言:“拟制本质上是一种类推,在一个已证明为重要观点之下,对不同事物相同处理,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以某种关系为标准的相同性中(关系相同性、关系统一性),对不同事物相同处理。”[29](P59)简言之,能够拟制的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必定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规则或目的追求,以限定构成要件存在的范围。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抢劫罪的规范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不管是拟制的抢劫还是典型的抢劫都必须服从抢劫罪的规范目的。第七,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否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拟制抢劫的主体,相当于把拟制规定视为类推解释而通过解释的方式否定其适用范围。事实上拟制不同于类推解释,它是立法者所作出的不可反驳的立法决断,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法律适用者不能随意地否定拟制的适用范围。因此,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其实混淆了立法与司法的区隔。
3.区分说的方法论批判
区分说认为,在刑法第269条的场合,其构成要件可以从规范上评价为抢劫行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需要对第269条的抢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为二者对法益侵害的程度具有相当性。但是在第267条第2款的场合,无论基于何种立法政策考虑,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携带凶器抢夺行为都无法与抢劫罪等同评价。[23]所以,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对第267条2款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区分说在行为主体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时,否定第267条第2款是对构成要件的拟制,在论证思路以及结论上滑向了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区分说对于拟制规定是否适用需要视情况而定也是“准用(比照)规定”的思维方式。但在刑法中,司法拟制无非是一种类推解释,适用中严格限制是无可厚非的。而法定拟制的适用与否并不取决于适用者的个人意志。区分说认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是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行为的刑事责任主体是一种实质的解释,其实这种所谓的实质解释仅为基于“法感”作出的直觉判断。第一,区分说的目的是为了限制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成立抢劫罪的范围,但却在拟制的本质问题上摇摆不定。德国学者拉伦茨指出:“当立法者本身怀疑,T2是否确为T1的一个事例时,亦可应用拟制的方式。”[1](P142)更何况,从本质上看,把第267条第2款的构成要件与第263条的构成要件作相同的评价不存在理论和现实上的障碍。立法者“之所以设立该规定,是因为在抢夺案件中,被害人能够当场发现被抢夺的事实,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会要求行为人返还自己的财物;而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客观上为自己抗拒抓捕、窝藏赃物创造了便利条件,再加上主观上具有使用凶器的意识,使用凶器的可能性非常大,从而导致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与抢劫罪没有实质的区别。”[28](P589)。第二,区分说认为在携带凶器抢夺的场合,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承担抢劫罪的刑事责任会损害第267条第2款本欲追求的实质正义。本文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从立法层面按照抢劫罪论处,不意味着法律适用者丧失了自由裁量空间,实质的正义完全可以由法律适用者在量刑时通过减轻刑罚的方式予以实现,并且正义的实现不在于否定犯罪的成立,而在于正确理解相应的法律规范(关于减轻刑罚的具体看法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阐述)。
综上,本文认为,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错误地把拟制规定等同于“准用规定”,采用“比照”的思维模式直接把不同的构成要件与相同的法律效果作简单的对应,不符合刑法规范的应有逻辑。区分说一方面肯定有的拟制法条与基本法条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可以等同评价,另一方面从直觉出发否定某些拟制法条的拟制规定性,在拟制问题上犹豫不定,犯了简单的折中主义的错误。而构成要件拟制说正确地把握了法定拟制的本质特征、思维模式,表明了拟制的对象是构成要件。
三、拟制对象的实质:相似的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
作为一项重要立法技术的拟制,除遵循一般法律规范的逻辑外,必须在拟制规定和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之间进行类比,使二者实现等同评价。在确立拟制的对象是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构成要件在形式描述与规范评价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的关系
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具备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大要素,构成要件是具体生活事实抽象化和类型化的结果。在体系意义上,构成要件包含了“与犯罪的产生有关的全部典型特征”。[30](P181)因而,在构成要件确定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所要求的法律效果。正如恩吉斯所言:“法律结果概无‘对象的事实,既不在物理世界,也不位于心理世界中’。法律结果不外乎存在于‘基于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的逻辑关系中,存在于事实构成的规范关联性中’。”[31](P37)换言之,法律效果只有在由构成要件所确立的犯罪类型中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在立法和理论上,构成要件在刑法规范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例如,德国刑法第16条第1项规定:“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没有认识属于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情况的,不是故意地行动”。这反映出构成要件在刑法规范构造中的重要地位。如果行为人对法律效果认识错误,不会对犯罪的成立与否造成任何影响。因此,法律效果是以构成要件的存在为前提,离开构成要件的法律效果如同无源之水。拟制规定虽然需要参照基本规定,但它仍是完整的法律规范,同样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部分组成,也应当遵循法律规范的基本结构。与一般刑法规范的相比,其差别在于:需要在两个类型化的构成要件之间进行比较和权衡以及需要借助基本法条的法律效果,但不影响其成为完整的刑法规范。甚至在法定拟制的场合,构成要件的作用会显得更为重要,除了考虑拟制规定的构成要件外,还必须把拟制法条与基本法条的构成要件进行比较。因此,构成要件是架设在拟制规定和基本规定之间,使二者等同评价并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的一座桥梁。简言之,“法律后果的相同性只有在事实构成的评价同等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证立”。[32](P60)
(二)构成要件的类比推理与类型化
从本质上来看,拟制的实现就是一个类比或等值(恩吉斯)或评价性归类(拉伦茨)过程的实现,那么这一过程的实现就必须存在相似的构成要件。正如齐佩利乌斯所言:“同等对待的问题实质上是对事实要件的比较。这些事实要件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其相似之处,也就是说,仅在重要方面相同,而在另一方面则有所不同。”[33](P308)然而,从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出发,两个不同的构成要件所指向的法律效果是完全相同的,此时相同的法律效果已经丧失了比较的前提和基础。构成要件拟制说采取了“类型比较的方法”,既看到拟制法条和基本法条在形式描述上的不同,又看到了它们在规范评价方面的等同。不管是一般刑法规范还是拟制的刑法规范,其构成要件都是类型化的结果。在立法领域,“立法者应当持续地审查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是否在其一般化的程度上已经合乎所调整的事实情境的需要以及具有多数公认力的正义观念的需要”。[33](P312)第263条规定的抢劫行为是基于一般常见的生活事实类型化的构成要件,但其很难涵盖诸如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行为,立法者必须基于特别的生活事实再次类型化,使两种类型化的构成要件能等同评价。通过类型的思维和类比的方法使得刑法的构成要件能够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因此,通过类型化的方式确立的构成要件是符合事物本质的要求的,使得事实与规范相互不断接近,相互调和。[34](P120)人们也可以在不法类型的轮廓下找寻基本规定和拟制规定之间的相似性和可类比性。拟制抢劫和典型抢劫的构成要件都是类型化的结果,只是这两种类型化的构成要件存在典型与不典型的差别。立法者还可以通过再次类型化的方式确立一个上位类型的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使其包含典型和非典型的构成要件。把典型的抢劫行为等同于抢劫行为必然遗漏了非典型的抢劫行为,这样既不符合类型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刑事立法发展的基本目标。认为只有第263条的规定的行为才是抢劫行为不是类型化思考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化的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概念式的思维是一种分离式思维,足以瓦解并败坏生活现象的整体性”。[35]况且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多变,各有各的特点,试图通过绝对定义的方式必将使刑法过于僵化。[36](P4)拟制规定和基本规定的等同评价是通过构成要件的对比来实现的,这种对比并不要求在每一个特征上都是一致的,而只是从它们各自的特征中选取能决定案件性质的共同特征进行比较,以达到对规范等同评价的目的。然而通过定义的方式来确定抢劫罪就必须不能遗漏其中任何一个特征,最终带来的危险就是拟制的抢劫和典型的抢劫行为都不符合抢劫罪的要求。因此,法定拟制的类比特性决定了不能采用概念的方式理解拟制法条和基本法条之间的关系,只能从事物的本质出发采用类型化思维解释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性。类型化的思维和类比推理的方法决定了要使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得到等同评价,就必须采用整体思维的方法,而不是单纯地地考虑拟制规定内部各个孤立的要素。例如,在事后抢劫中,不能单纯分别考虑先前行为(盗窃、诈骗、抢夺)和后续行为,然后做简单相加,确立是否成立事后抢劫罪。这种个别化或分离式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案件的认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的只是各个分离的行为要素,忽视了拟制抢劫与典型抢劫之间在整体意义上的等同性。在第777号案例中,这种个别化和分离式的思维贯穿整个裁判理由,法院将刑法第269条前后两种不同的行为(取财行为和暴力行为)完全分离开来,而非将其视为一个犯罪类型的两种行为要素或特征,把构成一个犯罪所需的两个特征完全孤立地判断,用个别的思维代替整体的思维,违背拟制需要整体判断的要求。
(三)一体化立法与分离式立法的相同内涵
抢劫行为与抢劫罪一样都是人们用来概括这种犯罪类型的称谓,它不仅可以指典型意义上的抢劫行为,也可以指非典型意义上的抢劫行为。在法条的构造上,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属于不完全法条,其完整的法条意义只有借助第263条才能得到体现,但不会导致对它们与刑法第263条作不同的评价。在我国刑法中拟制抢劫包括指转化型的抢劫和携带凶器抢夺的抢劫,在德国指抢劫性盗窃和抢劫性勒索,在日本刑法中指事后抢劫和昏醉抢劫,[37](P248)在我国台湾地区是指事后抢劫罪。[38](P270)在形式上,这些拟制的抢劫与典型的抢劫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仅是一种典型和非典型的关系,在规范意义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假如立法者没有把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单独规定,而是将其置于第263条当中,与典型抢劫行为并列规定,或许认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不是抢劫行为的疑虑可以自然消解。其实这种一体化的立法模式亦属常见。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8条第1款规定:“为使自己或者其他人获得不正当利益,采用对人身的暴力或威胁,使他人的动产脱离持有人的控制,将其据为己有的,处3年至10年有期徒刑和516至2065欧元的罚金。”第2款规定:“为确保自己或其他人占有被窃取的物品,或者为使自己或其他人不受处罚,在窃取物品后立即使用暴力或威胁的,处以同样的刑罚”。又如,《希腊刑法典》第380条第1款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针对人身的身体暴力或者即刻地危害身体完整性或者生命之威胁为手段,全部或者部分地劫取他人动产或者强迫他人交付动产的,处惩役。”第3款规定:“正在实施盗窃行为而被抓捕之人,为了维护所盗窃物品而使用针对人身的身体暴力或者即刻地危害身体完整性或者生命之威胁的,处与第1款和第2款相同的刑罚”。立法模式的选择并不会导致法律规范基本性质的变化。例如,在日本刑法中单独规定的昏醉抢劫与我国典型的抢劫罪中以其他方法实施的抢劫并无实质差异,在我国没有人否定以其他方法实施的抢劫是抢劫行为。同样,日本刑法中规定的昏醉抢劫,理论和实务上也没有否定其是抢劫行为,只是存在解释的差异而已。④因此,无论采取何种立法模式,抢劫罪都可以包含典型的抢劫和拟制的抢劫,也就是说,抢劫罪之下可以涵盖不同类型的抢劫行为。将典型的抢劫和拟制的抢劫置于同一法条的立法例中,无论实施的是典型的抢劫行为还是拟制的抢劫行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都应当承担抢劫罪的刑事责任应该不会存在争议。在我国,虽然没有采用一体化的立法模式而采取了分离式的立法模式只是一种立法习惯和立法技术的考量,并不能说明我国刑法将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也作分离式考察。因此,拟制行为与基本行为之间虽然在立法体例上是分离的,但在规范评价意义上是相同的。认为只有刑法第263条规定的行为才是抢劫行为,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行为不是抢劫行为的看法比较狭隘地理解了抢劫行为存在范围,既不符合立法的要求,也违背了法定拟制的本质特征以及构成要件的形式描述与规范评价之间的意义关联性。
(四)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逻辑内涵
构成要件的相似是拟制规定和基本规定获得等同评价的前提。二者是否相似需要看是否存在着决定案件性质共同特征。例如,典型的抢劫罪具有两个决定性的特征,即暴力或胁迫行为和取财行为。在拟制抢劫罪中,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⑤以此为基础类型化的拟制抢劫和典型抢劫的构成要件是相似的,立法者在同一规则之下通过等置或类比的方法将二者在规范上等同评价。如果立法者认为不同点是更重要的,当然可以通过反向推理的方法否定二者之间具有相同的意义内涵,也就不会在立法上做出拟制抢劫的规定。但是法律适用者对立法上已经确定的拟制抢劫是不能用反向推理予以推翻的。立法者设定的拟制规范并不是漫无边际的,除了受构成要件相似性限制之外,拟制与其他立法一样都会隐藏一些立法目的和政策性因素。正如康德所言:“一种假设之所以可以被接受,要么是为了说明某种现象;要么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39](P190)因此,两个相似的构成要件能够等同评价必须是基于一个共同的规则或者规范目的。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在抢劫罪中,保护的法益是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那么不管是拟制抢劫还是典型抢劫都必须在抢劫罪的规范目的下展开,都必须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这一规范的目的也决定了抢劫罪的类型范围,因为“类型”正是以“意义的一致性”而被确定其适用范围的。[40](P96)正因为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具有同一意义的规范目的,因而拟制规定不仅在一般情况下“依照基本规定论处”,在特别的情况下也必须“依照基本规定论处”。例如,在拟制抢劫罪中出现加重结果的场合,司法实务上都会对其适用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如果否定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规定的行为是抢劫行为,仅仅是立法上赋以了抢劫罪的法律效果。那么即便出现了加重结果,也不能适用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加重法定刑,因为对于不是抢劫行为所引起的加重结果当然不能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法定刑。德、日以及我国刑法都不否认,拟制抢劫行为引起加重的结果时,仍然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法定刑。日本学者大谷实指出:“法条中规定‘以抢劫论’,就是在刑罚以及其他法条的使用上,都按照抢劫罪处理的意思。因此,在法定刑上,除了准用刑法第236条(日本刑法对抢劫罪的规定——笔者注)之外,在抢劫致人死伤罪、抢劫强奸以及抢劫强奸致死罪等条款的使用上,也作为抢劫罪处理。”[41](P219)在德国,对于抢劫性盗窃中出现加重结果时,同样需要加重处罚。[42](Rn220)之所以在出现加重结果时也以抢劫罪论,是因为其实质是已将典型抢劫和拟制抢劫等同看待了,即,既然在一般情况下,拟制规定和基本规定能等同评价并赋以相同的法律效果,那么出现加重结果时等同评价并赋以相同的法律效果也就成为其题中之意。同样,在行为人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时,不仅必须对典型的抢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也必须对拟制的抢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能因为主体的特殊或者某些刑事政策的理由就歪曲拟制规定的应有内涵。认为拟制的抢劫行为不是抢劫行为的观点,完全是为了追求论证结果而忽视拟制的特性,只在形式上看到了构成要件的不同和法律效果的相同,没有看到法律效果的相同是构成要件在规范上能够等同评价的结果。
总之,拟制的构成要件与典型的构成要件确实存在差异,但拟制本身存在隐藏的指示,即意义的同一性,通过类型化和类比的方法使二者在规范上得到等同的评价,相同的法律效果是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逻辑结果。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重新审视最高院的《解释》以及第777号指导案例的合理性,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对拟制的抢劫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应当回归到法定拟制的本质特征中去思考。
四、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限制与修正
在拟制的场合,对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所适用的范围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应当如何限制并未深入展开。本文认为目前对拟制规定的适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将拟制规定的定罪和量刑都与基本规定作同一考量。陈兴良教授指出:“定罪是以类型性的构成要件为根据的,但量刑则要考虑非类型性的因素。因此,定罪是类型性思考,量刑是个别性思考。”[43]同样,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仅仅解决定罪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量刑问题,换句话说,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与定罪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并没有与量刑形成直接对应关系。⑥在拟制的场合,需要在定罪和量刑方面作两个面向的思考,在定罪方面需要考虑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在构成要件上的等同评价,在量刑方面需要回归到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在事实上的不同,对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在量刑上作出限制和修正,使定罪与量刑相互协调,实现拟制规定的正义诉求。简言之,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并不等于在处罚上也需要等同,二者应当相互分离,分别考虑。
(一)法定拟制下定罪的不可选择性
在法定拟制的场合,拟制的对象是构成要件,立法者通过类型化方式和类比推理的方法使形式上不同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指示法律适用者必须按照基本规定定罪。如上文所述,拟制规定是立法上作出的不可反驳且具有可接受性的立法决断,适用与否,法律适用者并没有自由决断的空间。换句话说,在逻辑三段论中,拟制规定是立法上已经确立的大前提,法律适用者只能对案件事实(小前提)作出判断,看其是否能涵摄到大前提之下,而不能推翻大前提。但在司法实务中,法律适用者经常直接否定拟制规定的适用。例如,第777号案例中,二审法院直接否定适用刑法第269条,认定王某不成立犯罪。从拟制的本质出发,第777号案例完全违背了拟制规定的应有内涵,法官用自己的判断取代立法上的决断,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由于本文前面三个部分其实就是在说明法律适用者对拟制规定的定罪并没有自由适用的空间,必须严格按照基本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定罪的不可选择性毋庸赘述。
(二)法定拟制下的量刑选择
拟制规定是立法者把相似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但规范上的等同评价不等于事实上是同一的,或者说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大同中隐藏着小异,而这些小异在法律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法律适用者在量刑时要充分考虑这些小异,使其在量刑上对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作出必要的限制与修正,从司法上保证判决的正义性。目前对拟制规定的量刑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
1.等同处罚的观点
在我国,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在量刑上等同对待的观点可谓通说。有学者从字面上解释“依照第×××条定罪处罚”,是指“依照第×××条定罪量刑”[18]。也就是说在拟制规定下,不仅按照基本规定定罪,还要按照基本规定量刑。但本文认为,“依照第×××条定罪处罚”与“依照第×××条定罪量刑”之间并不等同,因为按照基本规定定罪处罚最终只能认定犯罪和确定法定刑,在此基础上,法院在量刑中的起点刑选择、基准刑的确定以及最后的宣告刑都必须回到案件事实本身,而不是回到基本规定所确立的案件事实,因此,具体的量刑活动根本没有办法按照基本规定进行。也有学者从构成要件上解释拟制规定应当等同处罚。有观点认为,如果对两个不同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等同评价,那么在量刑上也应当等量齐观。[44]就具体的拟制抢劫而言,例如有学者认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转化型抢劫行为时……对被害人人身和财产双重法益的侵害性质与程度、客观方面的行为、主观方面的罪过,均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实施第263条的普通抢劫罪在性质和内容上一致,二者具有等质的可罚性”。[45](P178)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之所以承担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抢劫罪的刑事责任,是因为其与普通抢劫罪在主、客观构成要件方面都是一致的,所以它们是等质可罚的,或者说把构成要件的可等同评价与等质的可罚完全等同了。
本文认为,法定拟制是将两个形式不同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并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止于定罪和法定刑,并不延伸到量刑的领域。而等质的可罚性观点已经将等同评价性延伸至量刑领域,是过度实质化的表现,忽视了刑法第269条与第263条的构成要件在事实上存在的差异,把定罪和量刑所需考虑的因素完全一体化了。事实上,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之间也只是在重要方面上相同,而非在每个方面都相同,如果它们之间每个方面都相同,那么拟制规定也就丧失了存在的空间,或者其本身就是一个注意规定。从事实层面看,在相同情况下,拟制抢劫行为与普通抢劫行为相比,其不法和罪责的内容都相对较小,所以等同处罚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2.加重处罚的观点
少数学者持加重处罚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在聚众犯罪的转化犯中,只是规定了转化犯定罪量刑的依据,并没有强调是否在处罚时要从重处罚。并认为,应将聚众犯罪的转化犯从重处罚作为一个原则。其理由如下:第一,转化前的基本犯罪部分没有被评价;第二,认为应当把转化犯理解为吸收犯;第三,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对聚众犯罪转化犯从重的司法文件规定。[46]加重处罚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拟制规定的本质特征。首先,认为转化前的基本犯罪没有被评价,是将拟制规定中的各个因素孤立考虑的结果,无论是转化前的部分还是转化后的部分,都是拟制之罪(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的部分,在犯罪认定中已经充分考虑,在拟制的情况下甚至被过度考虑,如果在量刑中再将其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无疑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其次,把拟制规定的犯罪理解为吸收犯是不正确的,在转化犯或拟制规定中,前行为只是整个拟制犯罪成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独立于后来成立的重罪(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将完整的犯罪构成分割成几个独立部分的做法,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拟制规定的整体性特征,并且拟制规定的构成要件是通过前罪(行为)和后罪(行为)重新整合,形成另一种类型的构成要件,并不存在吸收关系。再次,司法实践中存在聚众犯罪转化犯从重的司法文件规定并不能说明其正确理解了转化犯或拟制规定。最后,加重处罚说与等同处罚的观点一样,完全忽视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在事实层面的不同,不仅是对拟制规定的误解,而且在逻辑上也存在悖论。
3.减轻处罚的观点
减轻处罚的观点认为,虽然两个不同的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可以等同评价,但在量刑上可以减轻处罚。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1条第1款规定:“因身份或者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许玉秀教授认为,在但书中规定的减轻其刑没有实益,应采必减规定。因为在没有拟制的场合,没有身份的人成立共犯都需依正犯减轻其刑,在拟制的场合,也应当减轻其刑,所以单独规定的减其刑,是不平等的。[47]又如,德国刑法第13条规定第1项规定:“行为人不防止属于刑法的构成要件的结果,只有当他在法律上必须保证该结果不发生,并且当该不作为与通过作为实施的构成要件相当时,根据本法才是可罚的。”第2项规定:“其刑罚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的规定予以轻处”。从拟制的角度来看,德国的不纯正不作为犯也是一种立法上的拟制。在具有作为义务的情况下,不纯正不作为犯虽然在构成要件上与作为犯等同评价,但是在量刑上可以减轻刑罚,正是因为“不作为所具有的不法与罪责的内容在相同的情况下,也是少于实行行为的”。[48](P528)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办案指南》也指出:“对于转化型抢劫,与一般抢劫相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在确定量刑起点时应有所区别”。[49](P143)
本文认为,减轻处罚的观点正确处理了拟制规定的定罪和量刑的问题。因为在刑法中,与构成要件相对应的是定罪和法定刑,在拟制规定中也一样。因此,在量刑中,法律适用者必须回溯到构成要件等同评价之前的基础事实部分,使得在构成要件上没有评价和评价过剩的部分在量刑中得以考虑。定罪与量刑的分离以及对拟制规定的犯罪减轻处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相同情况下,在量刑时对拟制规定的行为减轻处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例如,在刑法第269条的事后抢劫中,暴力或胁迫与取财的时间先后在构成要件等同评价时没有被考虑,虽然它不会对犯罪的性质产生影响,但它是量刑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因为在典型的抢劫中,暴力、胁迫行为是为了获得财物的占有,而在事后抢劫中,暴力、胁迫是为了保护已经取得的占有,因此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反映出事后抢劫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同样,在携带凶器抢夺时,虽然以抢劫论,但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主观恶性要远远低于典型的抢劫行为。这些主观责任要素的差异性在构成要件等同评价时是被忽略的,但法律适用者在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这些被忽略的情形,以实现罪刑均衡。第二,量刑时予以减轻处罚并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是对案件事实的充分评价。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在选取决定案件性质的共同特征后进行类比推理的,不影响案件性质的特征几乎被忽略不计了,所以在量刑时重新考虑这些特征并不存在重复评价问题,反而是对案件事实的充分评价。第三,在量刑时对拟制规定的犯罪减轻处罚与其他的从重、减轻和从轻处罚情节并不冲突,它们之间可以并存,法律适用者在量刑时对这些情形都应当充分考虑。例如,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实施拟制的抢劫行为时,年龄的因素与拟制规定中未评价因素和评价过剩的因素都可以对量刑形成多重的限缩,以达到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目的。第四,虽然法律适用者在犯罪的认定上不能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拟制规定,但是可以在量刑中充分考虑案件事实每一个部分,从司法层面保证案件的正义性,充分发挥司法对立法的调和作用,而不是直接否定立法上的拟制规定。
总之,在拟制规定中,将定罪与量刑分别考虑,既有助于反映出案件的性质,也有助于反映出案件事实的全貌。在案件中既不重复的评价某些因素,也不遗漏某些未评价或过度评价的因素,保证拟制规定的定性与定量的协调统一,在量刑中实现对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限制与修正。
尽管刑法第267条第2款、第269条与第263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所确立的行为都是抢劫行为,第263条确立的是典型的抢劫行为,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所确立的是拟制或非典型的抢劫行为。不同类型的抢劫行为的规范目的和法益侵害是一致的,其构成要件在规范上能够等同评价,相同的法律效果是对它们等同评价的逻辑结果。在解释和适用拟制规定时不能随意地脱离拟制的本质特征以及规范的目的,拟制的抢劫行为与典型的抢劫行为在规范评价上并无不同。但是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仅仅解决了拟制规定的定罪问题。在量刑时,法律适用者必须回归案件事实本身,应当充分考虑到拟制规定中未评价和过度评价的部分,在相同情况下,应当对符合拟制规定的行为减轻刑罚。因此,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典型抢劫罪的刑事责任主体,当然也是拟制抢劫罪的刑事责任主体,在量刑时除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年龄因素外,也应当考虑到拟制规定中行为相对较轻的不法和罪责部分,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案件的公平公正。
注释:
①由于拟制规定是通过立法方式确立的,与其他规定一样,在立法上是否正当属于哲学的范畴。目前学界对拟制规定是否正当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限制:一是,拟制规定与基本规定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相似性。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并且对相似性的判断并非是由外部观察到其有某种物理程度的相似性,而是由内涵上认知到其有意义的相同性。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二是,拟制规定和基本规定具有相同的价值。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②“依照第×××条定罪处罚”是刑法中参照性法条的标志。在法定拟制和注意规定的场合,如果不参照其他的法条,就丧失了法律规范的基本功能。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162页。参照性法条的出现是为了避免立法上的重复和法条的复杂化。在拟制规定和注意规定中,都是参照的法条和被参照的法条共同起作用。因此,在判定案件时,必须同时适用参照法条和被参照法条,以说明规范的完整性。在注意规定的场合,参照法条与被参照法条的构成要件在事实上是同一的;在法定拟制的场合,参照法条与被参照法条在形式上不同,但在规范评价上是同一的。关于注意规定与法定拟制的区分,可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2页。
③关于“比附”制度的性质,参见陈新宇:《比附与类推之辨——从“比引律条”出发》,《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④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在昏醉抢劫中,使用睡眠药、麻醉剂等使人泥醉、施以催眠术的行为,“在广义上是行使有形力的一种,可以包含在暴行的概念之中,但是现行刑法没有关于暴行概念的定义,在解释论上有将这些情形除外之虞,因此,特别设立了本规定。”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注释1。按照大塚仁的理解,昏醉抢劫是注意规定,而非拟制规定
⑤目前国内有观点质疑把携带凶器抢夺拟制为抢劫的正当性,其主要是因为携带凶器抢夺中的“携带凶器”与典型的抢劫中的“暴力或胁迫”存在差异。单纯从形式上比较,确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质疑的观点忽视了“比较点的决定,主要不是以理性的认识为基础,而往往是根据决断,亦即根据权力运作”。参见[德]阿列克西:《考夫曼的法律获得理论》,载[德]Neumann、Hassemer、Schroth主编:《自我负责人格之法律——Arthur Kaufmann的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同时考夫曼也强调,“比较点的获得,既非根据赤裸裸的权力,亦非根据纯粹的认识,而是两个因素合一作用。”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⑥德国刑法学家贝林非常形象地指出:“从类型出发一条直线笔直通向特定的法定刑。而量刑中的罪刑相适应,虽然关键仍是有责不法的‘类型性’行为,但它并不能直线通达法定刑,而必须首先越过这个或那个量刑的因素以及该因素所包含的不同类型,才能确定适当的刑罚。”[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