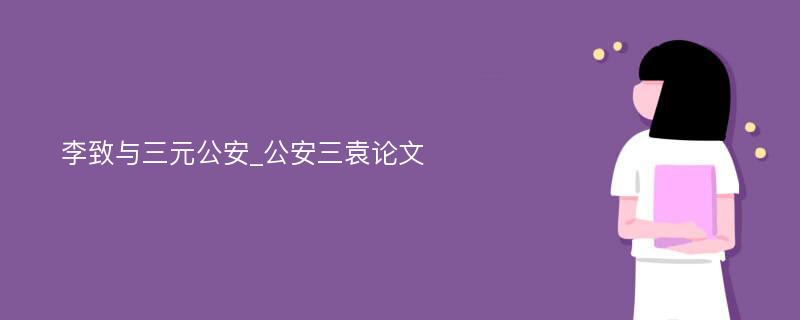
李贽与公安三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安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3-0032-07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市民阶级壮大,市民阶层的观念与习俗日益影响社会,加之郑和下西洋,利玛窦传教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这一切都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革新运动,和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潮,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启蒙作了铺垫。在这种启蒙思潮中,文学表现得更为突出。文学观念上重情求真尚俗与宗经宗圣宗道的对立,文学创作上小说、戏曲新文学样式的发展,与“高文大册”传统散文迥不相同的新鲜活泼、清新自然的小品文、书信文的大量创作,都表现出文学由传统向近代演进的轨迹,显示出一种新变的特征。而李贽与公安三袁在这一新变中占有着重要地位,研究李贽与公安三袁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认识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与创作的价值,而且对探讨中国文学由传统到近代的新变和启蒙思潮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
公安三袁与李贽的初识极富传奇色彩。袁中道《柞林纪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
柞林叟,不知何许人,遍游天下,至于郢中,常提一篮,醉游市上,语多颠狂。庚寅(公元1590)春,止于村落野庙。伯修时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访之。扣之,大奇人,再访之,遂不知所在。[1]
“柞林叟”是袁氏兄弟对李贽的称呼,“郢中”即公安(今湖北公安)、江陵一带,李贽在这里“醉游市上,语多颠狂”、“止于村落野庙”的异端行为,引起了袁氏兄弟的注意,因此,他们一起前往访问,和李贽这个“大奇人”开始了友谊的来往。(注:明人萧士玮《春浮园别录》认为《柞林纪谭》为伪作。但袁中道在《游居柿录》卷十中曾说:“昨夜,偶梦与李龙湖先生共话一堂。是日,有人持伯修、中郎与予共龙湖论学书一册,名为《柞林纪谭》,乃予兄弟三人壬辰岁往晤龙湖,予潦草记之,已散佚不复存,不知是何人收得,率尔流布。夜来之梦,岂非此耶?”可证《柞林纪谭》确为袁中道所作,只是原稿“散佚不复存”。同时,袁中道对“率尔流布”之稿并没有持否定态度,因此,不能轻易否定《柞林纪谭》的真实性。不过,袁中道说此稿为“壬辰岁(公元1592)”会晤李贽论学之书却是误记,实为癸已岁(公元1593)袁氏三兄弟访李贽后的成果。因为壬辰岁并没有袁氏三兄弟共同访问李贽的记录。)其实,这一传奇色彩的描绘,不过是袁中道以文学之笔加重与李贽初识的奇幻色彩罢了。实际上,公安三袁与李贽之间,在此前虽未晤面,却早已互为倾慕,这在他们后来的诗文酬唱和书信来往中都有着鲜明体现。
第二年即万历十九年辛卯(公元1591),正当李贽与道学家耿定向围绕着《焚书》的出版而展开激烈论辩之时,袁宏道又亲到李贽寓居的湖北麻城进行了拜访。而且,一住就是三个多月,甚为契合。袁中道对此次相会,在《妙高山法寺碑》中有如下的记载:
时闻龙湖李子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李子大相契合,赠以诗,中有云:
“诵君玉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盖龙湖以老年无朋,作书曰《老苦》故也。仍为之序以传。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2]
在武昌,李贽与袁宏道先游了黄鹄矶,后又同住到离武昌二十里外的洪山寺。袁宏道《哭刘尚书晋川》说:“记相识,相识黄鹤楼。当时稚齿青衿子,平揖方伯古诸侯。……尔时山翁(李贽)问余言,乘兴遂作洪山游。中间离合苦不下,长别已经十春秋。”[3]此诗写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长别已经十春秋”,正是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考取进士,故诗中自称青衿子”。“刘晋川尚书”,即刘东星,字子明,号晋川,山西沁水人,历官右佥都御史、工部左侍郎,曾总理河漕。当时黄河决口,刘东星因治河有功,升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李贽与袁宏道到武昌时,刘东星正以湖广左布政使在这里任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贽在游黄鹤楼时,遭到道学家的围攻,他们指责李贽是“左道惑众”,对李贽进行人身攻击与迫害。(注:李贽《与周友山书》:“不尚株守黄、麻一十二年矣,近日方得一览黄鹤之胜,尚未眺晴川,游九峰也,即蒙忧世者有‘左道惑众’之逐。”《焚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页。)也正是这时,原来只慕李贽之名而并不相识的刘东星主动到洪山寺拜访了李贽,并把他邀到自己的公署,加以保护。(注:袁中道《李温陵传》:“于时左辖刘公东星迎公(李贽)武昌,舍盖公之堂。”见《珂雪斋文集》卷八。)袁宏道与刘东星之相识即在此时,可见他们与李贽的交往,都是建立在识见一致、意气相投的基础之上。
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识见一致、意气相投的友谊基础,公安三袁与李贽不但交往频繁,而且思想感情愈来愈密切。袁中道有《大别山怀李龙湖兼呈王子》诗曰:“去年六月访李生,抱病僵卧武昌城。今年三月复东游,访李再过古亭州(指麻城)。龙潭十月同笑傲,虎溪千古失风流。”[4]“去年六月”,指万历二十年壬辰(公元1592),袁中道曾到武昌访李贽,不幸病倒,后雇舟回公安。袁中道走后,李贽也患痢甚重。(注:李贽《寄京友书》:“弟今秋苦痢,一疾几疾几废矣。”《焚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0页。)第二年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三月和十月,袁中道又两次访李贽,并极为惬意。特别是“东游”时的“再过”麻城,同行的有其兄长袁宗道、袁宏道和王以明、龚散木。袁宏道曾作《将发黄,时同舟为王以明先生、龚散木、家伯修、小修,俱同访龙湖者》一诗。[5]这次三袁的访学李贽,不但相互留下了多篇诗文酬唱,而且广泛的进行了学理研讨,诸如圣凡之同异,学道的根器,学问、功业的关系,《六经》、《庄子》、《水浒传》的意义,以及对荆轲、田克、管仲、晏子、留侯、韩信、太史公、杜甫、何心隐、王心斋、耿焚倥、赵大洲、邓豁渠、王龙溪、罗近溪等历史及当时人物的评析,内容丰富,语言犀利诙谐。后来,袁中道把这次问学的内容整理成《柞林纪谭》一文,成为研究李贽以及李贽与公安三袁关系的重要文献。
以上是就公安三袁与李贽交往中的主要行迹的论述,从中可以见出他们交往的密切。正是在这种密切的交往中,公安三袁与李贽之间得到了思想情感的交流,促进了相互间学识见解的。特别是李贽对公安三袁的影响极为深刻,这在三袁的有关诗文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袁宗道称赞李贽“龙湖老子手如铁”,“胆气精神不可当”,“莫道世无赏音人,袁也宝之胜琼玖。”[6]并说他读李贽的著作“目力倦而神不肯休”,“读他人文字觉懑懑,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7]袁宏道不但把李贽直称为师:“自笑两家为弟子,空于湖海望仙舟。”[8]而且赞李贽的《焚书》是“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的佳作。[9]袁宏道还把当时的天地比作一个大罗网,把李贽的出现,比作是要用“无羽镞”,“扇海作洪炉,燎山煮精玉”,从而要解除这个大罗网的“大妄人”。[10]袁中道不仅在诗文中多次赞誉李贽,而且,在李贽被迫害致死后,特意撰写了《李温陵传》,满腔热情赞颂李贽的斗争精神,并称颂李贽的著作是“剔肤见骨,迥绝理路。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狮子迸乳,季象绝流,发咏孤高,少有酬其机者。”[11]公安三袁还曾多次把李贽比为三教大圣人之一的老子,可见其对李贽是如何的尊崇。在这种尊崇中,也足见其在思想上受到的深刻影响。
二
作为文学家,公安三袁受李贽的影响,当然要表现在文学主张与文学创作上。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是很重视文学为其统治服务的。到明代,这一思想更加自觉和强化。明代统治者曾多次明令,杂剧戏文只许演“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违令者“一律拿送法司究治。”[12]诗文创作更是以宗经、宗圣、宗道为准则。就是哲学思想上颇具启蒙色彩的王阳明,也主张应该把不符合孔孟之道的“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13]高则诚在《琵琶记》中明白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原则,而这种“风化体”,则是“只看子孝共妻贤”,可见这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文学思想如何深入作家之心。
针对这样的文艺思想与创作现实,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14]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而“童心”就是“真心”,是人们“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当然是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李贽提出文艺要表现“童心”,其矛头正是指向封建统治者要文艺成为孔孟之道的传声筒的理论。李贽说得很明白,如果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得来的“闻见道理”充斥内心,那么人就变成了“假人”,写出的文章也只能是“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的“假文”。而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文以载道”,正是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的假文学,这种文艺只会“障其童心”使人们成为“假人”一类奴隶。李贽反对文学受“闻见道理”的注入,在当时就是反对以孔孟之道的统治思想影响文学;李贽主张文学要表现“童心”,就是要求文学要表现不受孔孟之道毒害的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且,这些作品都是作者“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之,势不能遇”,“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便借着某种原因以发其端,终于“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15],喷口而出,发泄心中的感慨,总之,文学作品都是发自作家的心内,来自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感受,而不是什么充满“闻见道理”宗经、宗圣、宗道之作。很明显,“童心说”的真谛,就是提倡绝假纯真的表现情感和表现生活,要求文学打上创作者的个人印迹,而具个性美,这实际上是李贽在人生哲学上张扬个性的思想在文学主张上的表现,是与泯灭个性的封建统治与传统思想相对立。由此出发,李贽还对当时被正统文人视为俗文学的戏曲、小说以极大重视。李贽认为,只要“童心常存”,则“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只要表殃了不受“闻见道理”污染的“童心”,即人的真情实感,什么样形式的作品都是“至文”,都是好文章。这种文学思想,在当时的创新意义也是极为明显的。总之,李贽的重情、求真、尚俗的文学思想,无疑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的疏离与对立,具有着强烈的启蒙精神。
正是在李贽这种思想影响下,公安三袁提出了“性灵说””。这一理论在袁宏道的《叙小修诗》一文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体现。袁宏道赞美其弟袁中道的诗是:“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所以,其作品是“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在此文中,袁宏道还特别称赞“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而且“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16]袁宏道强调的“独抒性灵”、“愁极则吟”、“若哭若骂”、“任性而发”,无疑都是要表现真情实感,而特别提出《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的民间文学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但表现出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显示出反对“闻见道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袁中道也曾说过,诗文之作要“抒自性灵”,“性情之发,无所不吐”。[17]他称赞其兄袁宏道的作品是“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玄旨,嘻语谑词,口能如心,笔又如口”。[18]称赞在袁宏道影响下,“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19]显然,这与李贽的“童心说”都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公安三袁在承受了李贽文艺思想的熏陶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李贽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而是包含着他们自己的创作体验。公安三袁在倡导“性灵说”时,特别强调“趣”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即是一例。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自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踰于此时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薄,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16]
在这里,袁宏道赞童子的虽不知趣而趣的无处不在,赞山林之人虽不求趣而无拘无缚、自在度日的无上乐趣,赞愚不肖率心而行、无所忌惮的独乐之趣,以及对高官显宦由于“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而“去趣愈远”的揭示,其核心都在强调趣是“得之自然者深,得自学问者浅”。接下去袁宏道又指出,陈正甫的《会心集》,由于作者是“深于趣者”,故所述人物也是“趣居其多,不然,虽介若伯夷、高若严光,不录也。”袁中道在《夏道甫诗序》中指出,夏道甫挟数千金经商,却不得其道,但“神情静嘿”则沉醉于诗,却取得了优异成绩。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士之有趣致者,其于世也,相远莫如贾,相近莫如诗。”[20]袁宏道对“趣”的称赞,对陈正甫作品中所体现的求趣精神的肯定,袁中道对夏道甫趣与诗近的赞赏,和李贽“童心说”中强调文学要表现“绝假纯真”的童心,其精神完全一致。同时,他们所强调的“趣”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又是对李贽“童心说”的一种拓展。他们把作家个性的解脱与作品创作的尽情抒写情趣进行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这其中既包含着自身创作的深切体验,也是对当时宗经宗圣宗道以及传统文学观念的一种背离。
公安三袁对李贽文艺思想的继承,还表现在对明代复古文艺思潮的批判上。明代的文艺复古思潮极为严重,起始于明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原本是对明初以“台阁体”为代表的那种歌功颂德、萎弱不振之风的反抗,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片面强调形式上摹拟古人,并认为一切文学越古越好,以致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21],甚至公然声称文学创作要像“慕临古帖”一样去模拟古人的作品。(注:李梦阳《再与何氏书》:“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李空同全集》卷六一。明浙江思山堂本。)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更加推进这一错误主张,致使文坛弥漫着复古、摹拟以至剽窃的风气,对文学的创作与发展造成极坏影响。
对于这种复古文艺思潮,李贽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李贽从“童心说”的理论出发,提出只要是出于“童心”,即来自人们内心的真情实感,则“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李贽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艺也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所以,从秦汉以来,“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针对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标示,李贽针锋相对地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很明显,李贽认为,文学作品不管产生在什么时代,不管任何体裁的创造,只要表现了人们的真情实感,都是好文章,好作品。正因为如此,李贽对宋元以来生气勃勃的小说、戏剧作品,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对于具有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倾向的作品,如《水浒传》、《西厢记》,更是推崇备至。如若说李贽倡导文学要表现“童心”是对文学个性美的张扬,那么,李贽反复古文艺思潮的主张,则是对文学发展观和对文学时代性的鼓吹。这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到公安三袁。
公安三袁对当时的复古文艺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里略举几例:
如袁宗道在《论文·上》中说: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亦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22]
袁宏道《叙小修诗》曾言: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16]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论道: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唯识时之士,为能隄其聩而通其所必变。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23]
前后七子在鼓吹夏古的时候,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语言上的拟古。他们认为语言辞汇以及名物称号,只有古代的才雅驯,因此,为文就要“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24]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诘屈聱牙的古代字句,甚至用古代的名物称号写当代的文物制度,从古诗文中撦一些字句重新组合成诗文。《明史·李攀龙传》称:“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已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上引袁宗道之论,即是针对前后七子这样理论与创作而言的。袁宗道认为,文学作品都是内心情感的表现,今人读古人的作品觉得奇奥而不通晓,那是由于时代与语言的变化所致,其实古代著作也都是运用当时明白易晓的通俗语言,故能真切地表情达意。这是对复古派一意从古人作品中句比字拟的剽窃、模拟理论的有力批判。袁宏道从通变的角度对复古派的批判更为深刻。文学的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新变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创作也必然要发生变化,而且只有在这种变化中,才能创造出不同于前人的独具特色的新文学。秦、汉的作家如若只是一味模拟“六经”,哪里还有秦、汉的文学?唐代的作家如若只是一味模拟汉、魏,哪里还有唐代的诗文?如若一味拟古不化,那不就像在严寒的冬天而穿着盛夏的衣服,不仅可笑,而且不适时宜吗?“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文之不能古而今也,时使之也”,是对文学发展的科学阐释,也是对复古派倒退文学思潮的深刻批判。这和李贽提出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只要表现了“童心”都是好文章,文学要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
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状》中曾这样描写李贽在文学上对袁宏道的影响:“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 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其未有涯也。”[22]这段文字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袁宏道“性灵说”与文学发展观以及在文学创作上受到李贽的深刻影响。正是在李贽的影响下,袁宏道摆了当时统治文坛的复古思潮的束缚,把文学导向表情达意的正确方向,使文学创作走向一个无限广阔的坦途。袁中道在这里说的是李贽对袁宏道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对公安三袁以及整个晚明文学的影响。从李贽的“童心说”,到公安派的“性灵说”,以及后来汤显祖的“至情说”,冯梦龙的“情教观”,直至张岱的理论与创作显示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相背离的一股强大文艺启蒙思潮,为近代人文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
李贽深刻地影响了公安三袁,公安三袁直接承继着李贽的思想。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对他与李贽的不同有着极为生动的论述。他说:
或问袁中道曰:“公之于温陵也学之否?”予曰:“虽好之,不学之也。其人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公为士居官,清节凛凛,而吾辈随来辄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学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而吾辈不断情欲,未绝嬖宠,二不能学也。公深入至道,见其大者,而吾辈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学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读书,而吾辈汩没尘缘,不亲韦编,四不能学也。公直气劲节,不为人屈,而吾辈胆力怯弱,随人俯仰,五不能学也。若好刚使气,快意恩仇,意所不可,动笔之书,不愿学者一矣。既已离仕而隐,即宜遁迹山林,而乃徘徊人世,祸逐名起,不愿学者二矣。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不愿学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学者,将终身不能学;而其所不愿学者,断断乎其不学之矣。故曰虽好之,不学之也。[11]
在这里,袁中道(实际上包括公安三袁)把他与李贽的不同说得极为明白。有些论者以此认为这是公安三袁与李贽思想的实质区别,是从李贽进步思想的倒退,这并不确切。有论者认为这只是为了尊重与突出李贽而故为的夸饰之词,同样不符合历史实际。李贽与公安三袁在人生态度和文学思想上有着一致的一面,也有着鲜明的差异。大致说来,李贽更为激进,对封建压迫与传统思想有着强烈的反抗。他反对封建束缚,公开批封建统治者的“德礼政刑”对人民的统治,要求“各从所好,各聘所长”[25],自由地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他反对封建等级制,提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26]、“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27]的平等思想。他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指责封建统治者“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28],并对儒家“经典”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学家及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独特的与传统思想相对立的大无畏精神。正因为如此,他鼓吹“童心说”的文学主张时,特别强调愤怒之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愤怒也是一种发自本心的自然之情,所以“不愤则不作”,好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都是“发愤之所作也”。[29]而且,这种愤怒之情,“喷玉唾珠”,形成文字,不但作者自己是“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而且能使见者闻者产生“切齿咬牙,欲杀欲割”的愤激之情。[15]李贽把愤怒之情纳入到他的“童心说”理论之中,就是主张文学要有强烈的爱憎,就是要用文艺这一武器揭露压迫者,道学家的丑恶面目,用文艺去冲击传统思想对人们的禁锢。由此可以说,李贽的“童心说”,既重文学的个性美,又重文学的社会性,是个性美与社会性的统一。李贽自己创作的大量匕首投枪似的作品,就是他这种文艺主张的实践。
与李贽相对照,公安三袁则有所不同。前引袁中道在《李温陵传》所说,他们对李贽“不能学者有五,不愿学者有三”,归结为一点,就是李贽在追求自我解脱、个性自由的同时,对那种束缚自我、束缚个性的社会及传统思想进行了猛激的抨击,并企图以此解除由社会与传统思想造成的束缚自我、束缚个性的樊篱。公安三袁则不然,他们追求自我的解脱,追求个性的自由,但却想在耽于山水和物欲中去实现。袁中道曾作《感怀诗》五十八首,其十曰:“山村松树里,欲建三层楼。上层以静息,焚香学薰修。中层贮书籍,松风鸣飕飕。右手持《净名》,左手持《庄周》。下层贮妓乐,置酒启冶游。四角散名香,中央发情讴。闻歌心已醉,欲去辖先投。”[30]在幽雅的山林之中建楼棲息,读诗书,谈佛道,听歌狎妓,醉酒冶游,身心俱爽,在这种自适愉悦之中,精神为之彻底解脱。从这种人生态度中,我们也可以窥视到为什么公安三袁那么热衷于山水游乐,创作了那么多的山水游记。这和李贽那种愤世疾俗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态度确实是有距离的。但也不像有的论者所说,公安三袁沉湎于山光水色之间,只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其实公安三袁借山水以自遣,以自适,以解脱,这都是存在的,但更主要的则是借助山水的自然真趣来表达对社会现实虚伪黑暗的对抗。周作人曾说:“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31]公安三袁正是这样。公安三袁在耽于山水和物欲中去反抗社会,这是他们人生与创作的特点。同时,公安三袁也有对社会黑暗的愤激,袁宏道就有不少作品直接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表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混乱。正如鲁迅所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32]当然,与李贽相比照,公安三袁也确有其隐遁、消极的一面。李贽直面社会人生,痛斥道学家的丑恶与虚伪,批判封建统治及传统思想对人们个性的戕害,以及他所提出的文化思想命题,在当时的形势下,都具有着振聋发聩、惊世骇欲的启蒙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称李贽为近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代表与旗帜,是不为过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安三袁当然不及李贽。但公安三袁在李贽影响下,提出的“性灵说”等文学命题,和以寄情山水的自适与社会的对抗,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严密的封建统治与传统思想也是相对立的。从这一方面看,公安三袁也为近代人文主义的启蒙作出了贡献。
〔收稿日期〕2000-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