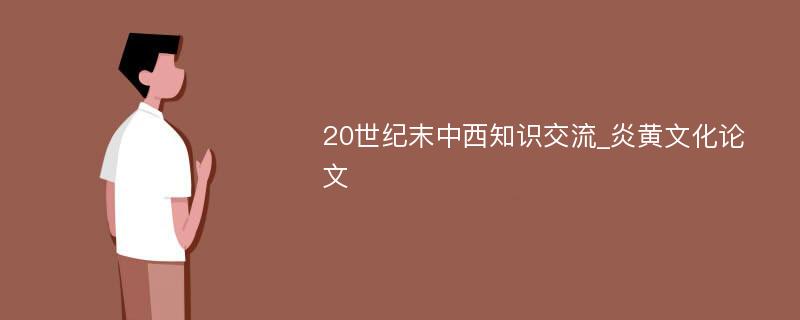
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期论文,中西论文,世纪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理雅格的生平和事业(注: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8日在英国阿伯丁大学召开的纪念理雅格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大会演讲稿。)。像傅兰雅一样,理雅格的职业生涯也是以在中国当传教士、教师和翻译为开端的,后来他在西方又成为中国问题的教授,成为他一生中的第二项事业。傅兰雅和理雅格的生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作为传教士他们日常的专注不是宣传基督教教义而是付诸行动,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媒介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文化媒介时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地合作者的帮助。不过,在一个基本方面,两人则不甚相同。而中西知识关系在总体上的最为明显、极为重要的不对称性正深藏于这一差异之中。
我所指出的这种不对称性直到19世纪末一直是中西知识分子关系的特征,在某种重要的程度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一点与中西之间知识流动的基本模式有关。有人曾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模式的含义:长期以来,西方的主要兴趣在于了解中国,而中国则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就这一模式中的中西双方来讲,当然会有很多例外。但作为一个总原则,它还是很能站得住的。如果我们只考察一方,即西方人对中国的立场,那么从总体上看,在过去150年内到中国的西方人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文明能存在下去,而到中国去寻找我们所需要的中国文明所拥有的某种东西。相反,我们到那里或者是出于某种理由要使自己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或者是把什么东西带给中国,即按我们的理解,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福祉所需要的东西。由此,又推动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当然,过去两个世纪中世界上权力关系及其变迁的基本格局,是形成了解(某种文化)和学习(某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根源所在。由于过去200年间西方在军事、技术和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西方人就不用像其他伟大文明的代表那样,不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有目的地把我们自己文化的基本部分进行拆解和重新构建。正如傅兰雅用自己的翻译工作一样,我们曾经帮助其他民族向我们学习,但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义务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对其他民族产生兴趣,力图更多地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时是纯粹出于好奇,有的是为了确证我们自己的优越感,有时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像理雅格一样,是为了提高自己从而更有效地推动他们的精神转变(注:理雅格承担了把“所有儒学经典”译成英语的艰巨任务,“为的是……必须以足够的智慧在这些人民中从事传教工作,以获得永恒的成果”。Lindsay Ride,"Biograp-hical Note",in James Legge,The ChineseClassics,SVol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0),1:1)。
我刚才提到了解和学习之间的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部分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人自己的优越感,部分程度上是非西方人民对这种情况(至少在财富和力量的范畴上)的认可。直到20世纪末叶,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知识和文化的流动中这种差异仍然非常明显。不过,这个看法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今晚演讲的一部分将要探讨另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这个概念至少需要部分地修正。
从广义上来讲,19世纪末西方的优越感在本质上是包罗万象的,不仅是在诸如财富和力量等物质范畴方面,而且包括了文化、宗教、道德、风俗及其他的精神领域。非西方人有时接受了这种全盘估价。例如,我们会想到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期开篇文章中大胆的宣言。陈在1915年9月写道:“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注:《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不过,更常见的则是非西方人拒绝这种极端的西方优越的观点,只承认西方在物质上的优胜。同时,必须指出,在20世纪末,这种情况已经变得更为复杂,部分原因是许多西方人自己对西方在文化、道德领域上的优越提出了质疑,另外则是由于把“西方”和“中国”作为两个各自独立、划分明确的实体的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后一种现象极为有趣,它体现在最近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之中。其中之一就是1980年以来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大陆基督教令人惊讶的发展。这一发展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就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言,现在是新教教徒的人数第一次超过天主教徒。第二,在过去十几年内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在完全没有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下取得的。事实上,许多发展似乎是由一些自立的基督教团体完成的,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曾经一直是有激烈的反外倾向,反对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注:Daniel H.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1900~1937:A Pentecostal Case Study",in Steven Kaplan,ed,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5,138;P.Viii.)。第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上述发展中这一点最直接地向把中国和西方截然划分开来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基督教社团在中国的发展是其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发展的一个部分,这一发展已经使得非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徒的数目超过了西方基督教徒。请允许我引一段裴士丹教授的话:“事实上,从基督教的世界构成来看,它的非西方成分现在要多于西方成分。”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学者们越来越认为“‘与其把基督教作为独特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宗教不如把它作为一种世界宗教来探讨’更为有益”(注:Daniel H.Bays."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1900~1937:A Pentecostal Case Study",in St-even Kaplan,ed,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P.135,138;P.Viii.)。
如果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动摇了众所熟知的“中国”和“西方”这两个范畴的话,那么,相应地,在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先前的旧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这一点也越来越明显了。西方人在中国皈依基督教可能将永远是一种并不常见的现象。但相反的,中国人通过西方人来了解中国则已成为一种确定的模式。当然,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完全对称的。
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一些中国人通过学习西方人的东西来了解中国的零星例子——例如,高本汉(Bernardkarlgren)关于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但是,直到70年代晚期,这个过程是真正的开始了。这一过程之所以在这一时机开始有两个直接的原因。第一,战后西方的中国研究有爆炸性的增长。在美国,中国研究取得了戏剧性的发展,以联邦政府和福特基金为主,数以几千万计的美元被投入这一领域。在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学习中国语言的人,从1951年不到150人增加到1970年超过6000人。亚洲研究学会的中国分会的人数,战后初年才有几十人,1957年达到205人,1973年则超过了1500人。50~60年代和70年代出版的数以几千计关于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反映了中国研究引人注目的发展。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70年代末编辑出版了1949~1977年间中国及海外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目。目录中列出中国出版了193种著作,日本337种,苏联431种,英语国家出版了986种,其中大部分是美国出版的(注:本段所引资料是从不同的来源收集的。有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迅速发展的极其有用的资料取自:John M.H.Lindbeck,Understanding China: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New York:Praeger,1971).)。
这一目录编辑中隐含的自我鞭策精神——请记住这一目录是在“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后不久出版的——表明了中国人通过向西方人学习来了解中国的这种倾向正在发展,这也就成为这一过程开端于此时的第二个原因。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中国大陆严肃的学术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60年代中期稍前一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严肃研究也有相当的限制。不过,到70年代后期,这种情形有了显著的改变,特别是在比较古老的、被确认的历史领域更是如此。国家放松对社会的限制已经成为这些年的一个特点,作为这种情形的一个部分,中国历史学家们开始经历深刻的思想解放,其早期的显著征象之一就是对欧美学者如何论述中国历史产生了新的兴趣(在此我必须指出,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中国大陆能见到的非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大部分限于苏联和东欧的著作,西欧和美国学者的研究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而遭唾弃。因此,在邓小平时代之初,中国历史学家们几乎没有或者很少能接触到30多年来美国和西欧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而确切地说,正是在这几十年内,欧美学者的中国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日趋成熟)。
我最初注意到中国学者对西方中国历史研究发生兴趣,是在1979~1980年之交的冬天对中国大陆的一次访问,当时,我是美国中国学各学科访华团的成员之一。在访问中,我了解到,薛君度(Hsueh Chun-tu)关于黄兴的著作,韦斯特(Philip West)关于燕京大学的著作和凯普(Robert Kapp)关于四川军阀的著作都已经全书或部分被译成中文。中国历史学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的编辑们告诉代表团说,他们正在考虑发表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稿件,他们计划不久将刊登关于外国著作的书评。而且,中国刊物上征引西方学术成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注:Paul A.Cohen and Merle Goldman,"Modem History",in Anne F.Thur-ston and Jason H.Parker,eds.,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Recent History and Future Prospects(New York: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1980)pp.38—60,esp.p.45.)。
尽管以90年代末的眼光来看,这些发展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当时这标志着中国历史研究方向的重要转变。从80年代初期以来,数以几百计的西方中国学研究者的论文被中国刊物发表,许多反映欧美中国学最新成果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为题的系列专门出版已在欧美刊行的学术著作,自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着手此事以来,已经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包括魏菲德(Wakeman)的《洪业》、李文森(Lev-enson)的《儒教中国与它的现代命运》、史华慈(Schwartz)的《古代中国思想的世界》、葛瑞汉(Graham)的《论“道”者》、许里和(Zurche-r)的《佛教征服中国》、谢和耐(Gernet)的《蒙元人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肖公权关于康有为和艾凯(Alitto)关于梁漱溟的著作、周锡瑞(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桑格瑞(Sangren)的《一个中国村社的历史与魔力》。印在每一册书前的《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明白地道出了体现于这项出版事业中的开放精神,在此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些令人吃惊的话:
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特别兴趣,不仅反映在外国的中国研究著作的译本日渐增多,一批中国大学纷纷建立了研究海外中国学的专门机构也说明了这一点。最近建立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就是这样的机构之一。按中心创办人的估计,今天在中国之外地区至少有1000个机构(除了学术机构外,还包括军事、政治和商业机构)和10000名以上的非中国人专家从事对中国的研究。他们还说,从16世纪到目前,在中国之外已经出版了不下20万种关于中国的著作(注:Interview in Huadong Shifan Daxue,May 10,1996,p.3.)。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数量如此巨大的外国研究中国的著作,使得中国人必须熟悉这些东西。当然,在部分程度上,是为了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中国的,同时,也显然正如在丛书序言中提到的,是为了拓宽和深化关于中国自身的知识。
关于“中国”和“西方”之间界限模糊性的现象,在一些与“文化中国”概念有关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注:My discussion of cultrual China is drawn from Paul A.Cohen."Cultural China:Some Definitional Lssue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43.3(July 1993):557~563.)。“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有实质性的和战略性的双重含义。从实质上来讲,它指的是价值观、行为模式、思想及传统等,即在某种客观意义上人们公认的可以界定为“中国的”的那一整套东西;更主观一点的说法,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觉得有归属感的那种东西。从战略意义来讲,文化中国的概念为那些散居世界各地、而不是居住地理或者政治空间意义上中国的华人提供了一种方式,使之可以讨论、说明、甚至界定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含义。几年前,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曾在《代达罗斯》(Daedalus)有关中国文化认同问题专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有力地指出“过去的40多年中,国际上关于文化中国概念的讨论”不是在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社会和世界各地华人社区的综合影响下,而是在学者、教师、记者和商人等人群中展开,“他们是为了在思想上认识中国”,然后向同语种的人解释中国(注:Tu Wei-ming."Cultural China:The Periphery as Center",Daedalu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120.2(Spring 1991):12~13.)。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杜至少是含蓄地指出了作为一个概念的内在不明确性,他认为内在的和外在的区别,正如中国和西方的区别一样,并不像我们倾向于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和不言自明。
让我来解释一下。林同奇在1992年提交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了支配着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探讨的三种力量。其中的两种,即反传统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显然是源自于西方,即使这第三种力量,林称之为转变主义,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可能也是受到了非中国思想的间接影响(注:转变主义者声称尽管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基于选择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基础之上,但这些被选择的方面必须经过“创造性的改造”以符合现代化的需要。Lin,"A Triadix Tension:A Glimpse into the New Intellectual Discourse in the China Mainland(1978—89)",paper Presented at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meeting,Washi-ngton.D.C,April 5,1992.)。因此,这种探讨的实质性内容在某种重要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之外的思想的影响。不过,就80年代中国大陆争论的内容而言,其中心是文化特质问题,很难设想还会有更“中国式”的争论了。换言之,当被用来解答那些在本质上纯粹是内在的思想和感情问题时,外来的思想被内在化了。
这种现象的其他例子经常见于中国的历史学杂志。我记得在几年前读到1980年的《历史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时,颇受触动。此文作者是已故罗荣渠教授,北京大学一位对中美关系史有特别兴趣的历史学家。在谈到19世纪时,罗写道:“中日两国是具有相似背景的东方国家,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大致相似的冲击,但两国对待西方冲击的态度和对策却大不相同,其结果也就迥然不同。这一对比说明了资本主义侵略下各国发生的变化是通过各国内部的种种因素而实现的。”(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第9页。)我对罗的观点感兴趣的是它对法兰西斯·莫尔德(Frances Moulder)多年前称之为“传统社会”的立场——许多西方中国学家在1980年已经摒弃——的那种方法的反应程度(注:see her Japan,China,and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ca.1600 to ca.1918(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不过,从罗写作时中国的内部情况看,采用冲击——反应的分析模式,并将日本成功的反应与中国不成功的反应相比较,强调各自社会的内部因素,不再那么强调帝国主义的作用,这反映了对当时历史编撰学的一次重要挑战。林同奇在1992年论文中提到,80年代中国的西化论者更多地把批评指向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近传统”而不是(像“五四”时期的西化论者那样)批评中国文化的“远传统”。罗荣渠采用美国中国历史学的主要方法,这似乎是批判“近传统”的一个较早例子。
在我所引证的几个例子(以及我们可以记起来的无数其他论著)中,起源于外国的、认识中国的思想,在被用于中国内部的辩论时被内部化了。我记得我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有一些大致相似的看法,我认为以中国中心观来观察中国的过去,就是对那些即使是由于与外部因素有关而产生的变化,也更倾向于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来考察。伦纳德(Jane Leonard)在中外关系的层面上对魏源的研究就是这么做的;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的《内部的鸦片战争》在考察了当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状况后,对鸦片战争提出了新的看法;兰金(Mary Rankin)以浙江为重点,研究了晚清社会精英的动员和政治化的进程,尽量体现了我归纳在中国中心论的框架中所有特点,她严谨地探讨了外国帝国主义对晚清内部政治演进的影响(注:Jane Kate Leonard,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Jame M.Polachek,The Inner Opium War(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2);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这些著作在方法论上都属于中国中心观范畴,但是,这不仅不表明这种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对外来因素的重要性采取忽视的态度,而实际上是使他们能以特殊的方式来阐明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我使用中国中心这个术语,带来了另一些与内在性直接有关的、并且不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在我的书的结束部分明确的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局外人——在此是指美国人——真的能形成一种从(中国)内部观察问题的认识。美国人以中国中心观看问题的观念是否就是一种词语矛盾?在该书中,我事实上答复了这一问题:我认为所有历史学家,无论美国人或中国人,对中国的过去(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过去)都是局外人,历史学家们越是注意到他们研究的假想深藏于他们对过去提出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受到这些假想的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在实质上很不相同的办法,已经由杜维明含蓄地提出来了。在前面提到的《代达罗斯》的文章中,杜从三个符号体系之间的不停的互动关系出发仔细考察了文化中国的概念,他认为,第三个符号体系,包括了(正如我们看到的)“一些个人……他们试图从思想上认识中国,并把他们对中国的观念传达给他们同一语种的社团”,它对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对文化中国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然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构成了这个第三符号体系的一部分,那么不言而喻的是:在文化中国的探讨中我们就不是局外人,即使我们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不是中国人,由于我们的专业素养和义务,我们能成为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参与者。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和中国历史学家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在中国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并看到我们的著作越来越多地被翻译过去并为中国同行所熟悉,局外人和局内人显而易见的区别也越来越难以确立。逐渐地,正如刚刚提到的,我们所遇到的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会遇到的局外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内在性与外在性界限泯灭的过程远未结束。如果说,中国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把西方人当作研究中国的一批认真参与者,甚至表示了他们准备从我们这里了解关于中国的知识,那么,相反一方的情况则远非如此。在西方,我们有许多研究机构,它们把对中国进行认真的研究作为其任务之一。但我至少没有看到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请原谅我对自然科学方面情况的无知——西方人向中国人那里寻求关于西方的新资料、新解释和新分析的任何迹象。
当然,我们有时会偶尔注意到涉及西方某些方面的中国著作,因其观点的新颖而引起我们的兴趣。对历史学家来说,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严复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约翰·密尔的《自由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西方社会政治思想著作的解释性翻译。正如史华慈在其卓有影响的严复研究中所表明的,我们不仅能从这位思想家那里了解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与同时代的西方的进程是多么不同——而且能知道从原著所依据的前提中可以逻辑地导出不同的结论(有时这些结论十分令人惊讶)(注: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
但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说明的。我所想到的是中国关于西方的学术研究,即那种西方人感到为了解自己领域中最新进展所必须知道的成果的普遍匮乏。有中国关于梅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托马斯·麦恩(Thomas Mann)和布朗蒂(Charlotte Bronte)研究,因为它们的解释新颖或包含了新的资料而被译成英文,被研究梅尔维尔、麦恩及布朗蒂的西方学生所阅读吗?或者有关于美国内战、法国革命,甚至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均是直接参战国)的中国著作为西方历史学家所熟知,并且由于这些著作公认的重要性,经常地指定学生去阅读吗?或者有中国关于一般的社会学理论的论著被西方社会学家像对桑巴特(Sombart)、德克海姆(Durkheim)及韦伯(Weber)的书那样去阅读吗?
对每一问题的答案,就我所知都是“没有”。我并不确知情况为何如此,但我想非常初步地提出几点解释。第一,中国仍是一个欠发达国,因此没有资金在国内建立第一流的西方图书的收藏,也不能使它的学者长时间呆在国外利用欧美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从事西方问题的研究。第二,我怀疑,即使在这个或那个西方问题领域,或者在某些一般性理论的领域中已经有一些杰出的中国著作,但这个“翻译的环节”是缺失的,即西方的美国文学的学生或法国历史学家可能都不懂中文,因此不能期望他们能注意到已经有了这样的学术成果,他们更缺少把这种成果译成英语、法语或德语的能力(当然,随着数量日增的真正懂双语的华裔西方专家居留在西方,成为西方学术团体的成员,并越来越在中西之间发挥媒介作用,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第三,可能与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而不是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有关,这种半殖民地经历的后果之一就是,在中国永远也不会像在印度、越南或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那样,你能遇见有着很强的双语能力、浸淫于西方国家文学与历史之中的土著精英;更不可能有中国人像印度人那样撰述英国历史被英国人所阅读,或者像越南人那样撰述法国文学被法国人阅读。因为印度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越南则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对中国的情况而言,真正的类比应该是印度学者研究德国文学而被德国人阅读,或者是越南学者研究英国的历史而被英国人阅读。尽管我不能确知是否有这两种情况存在,但这两者我都认为是极不可能的。
至于西方对中国已有的关于西方或者一般性理论问题的学术成果的生疏感,另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是西方顽固地坚持西方优越的态度,甚至在20世纪末还是如此。根据我与美国同行非正式的讨论,我的感觉是,我们不仅对中国关于西方的学术成果少有兴趣,就是对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国家,拥有一批在西方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学有专长的学者,而且,与中国不同,日本有财力派遣学者到国外做研究,出席学术会议等等,但就我所知,它对西方国家的研究对西方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面对另一个可能性,即问题毕竟不是残存的西方优越感,而是非西方学者的西方研究或者一般理论研究的学术成就,或者是由于不够精深、或者是不面对西方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或者在另一方面不够理想,水平较差。我记得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1961年的一段话。他写道:“目前,西方之外的整个知识界,即使那些最有创造力的国家,都处于一种地方性的状态。它们专注于西方的成就,它们着迷于西方的知识成果并被它所吸引。甚至在不同的方面有着自己极具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的日本、苏联和中国也关注着西方,而这关注并不仅仅出于国家的、或者军事和战略的原因。它们被西方耀眼的光芒所眩惑了。它们缺乏知识上的自信和自尊。”(注:The Intellectua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The Indian Si-tuation(The Hague:Mouton,1961),p.13.)
在把西方描述为世界的知识中心,其他则是中心之外的地区时,希尔斯是完全正确的。但另一方面,他没有能认识到正是西方自身也存在着“地区性的状态”,因为在现代世界的所有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没有过在其之外有一个文化中心的经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方是被“眩惑”了。无论如何,我们马上要面对的问题是:希尔斯的估价在35年之后仍然有效吗?我们正广泛讨论的问题是正如希尔斯所说的,西方之外的民族缺乏知识的自信心吗?或者是西方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可能性:即西方之外的民族是能对我们关于自身的知识及关于世界的一般知识作出有用和重要的贡献吗?我不能肯定我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必有一个答案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不过,不管答案如何,我们仍然碰到我在谈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知识流动的不对称性:在20世纪末,西方最主要的兴趣还是了解中国,而中国则是向西方学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在西方与中国在知识上的关系仍然处于理雅格去世时的状态呢?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的;在某些方面,完全不是这样。为了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西方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完全沉浸于我们称之为西方研究的学者,另一类就是我们这些在这个圈外的人,或者是成为对非西方社会例如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学者,或者是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如基督教徒皈依的经历、或资本主义放在全球范围来研究,这种方法自觉地抵制把西方的变体认定为规范。第一类学者,尽管包括了许多无可争议的视野开阔的有识之士,在总体上并不认真看待非西方人对西方研究或者一般理论的学术贡献(在美国学术界这种问题尤其严重,他们甚至狭隘到忽视欧洲学者在自己同一领域中的学术成果,只要这种成果不是以英语撰写的)。西方学者不关心非西方学者成果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这些成果确实不够好;或者虽然很不错,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或者,我们确实知道这些东西,而且按照公认的标准,质量很高,但由于残存的优越感,我们不愿意接受它们。
第二类非常不同。当然,我们正如在19世纪晚期,非常关心的是了解中国——或者更广泛的是了解非西方的“他者”。我们已经致力于从中国学习的东西,如太极拳、针灸、佛教、《易经》算命及武术等等,仍然是处在大多数西方人文化视野的边缘。但是,尽管我们强调的仍然是了解中国,主观思想的走向——即引导我们研究的假设——已经明显地改变了。
有两个方面可见这一点确实无疑并且特别重要。第一,我们中许多人在20世纪晚期接触了中国研究,我们这么做是认为这个研究本身是有好处的,是值得做的,姑且不论这种知识能带来的实际利益或战略优势。也许,这对研究20世纪以前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更是千真万确。但是,尽管有例外(最显然的或许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及军事科学等领域),对我们主要学术兴趣在于探讨中国近几十年问题的许多人来说,也是如此。
第二,我们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术语为我们的中国研究和其他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来辩护。那就是,我们对自己和学生都强调研究其他文化的重要性,它是一种有利途径,使我们能认真探讨在过去的世纪中我们自身文化选择的非理性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摒弃了所有价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们并不只是因为某种事物是我们的,而给其较高的评价,相反,我们坚持用更客观的、不是自我肯定的范畴来评价文化的特点。
我们致力于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这种认识处境的转变,同样也可以应用到更深刻地理解全球范围的历史和文化现象。与理雅格时代逐步形成的“宗教比较学”的新学科不同,20世纪末对世界宗教现象,如宗教皈依的经验、降神附体、魔法、仪式等的研究,不再采取明显的或不明显的自视优越或美化西方宗教经验和实践的态度。不管我们个人信奉什么,我们要约束自己,避免使自己的信仰影响到我们的专业研究。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这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地区的研究方法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在知识与真理、事实和体现事实的方式之间从来没有简单的一对一的对应;任何描述,在一定程度上都存有歪曲的因素,反映了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性别、所属的阶级、种族及所处时代的影响。不过,歪曲的程度则有很大的不同,实质性的进步是完全可能的。目前投入于西方中国研究的人力、财力和技术等资源是一个世纪以前不可比拟的,理雅格所开创的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专业化久已形成规范,并为大家确认和遵守。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的100年中我们致力于增进和深化西方对中国的理解所走过的路程时,有许多值得庆贺之处。此刻,我们聚集在阿伯丁大学向这位西方中国学无可争议的巨人致敬,正是他为这个世纪的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庆贺中国学的进步。
(译者注:本文在翻译过程中曾参考过何冀婷的译稿。此译文曾经作者作了个别概念的修正。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