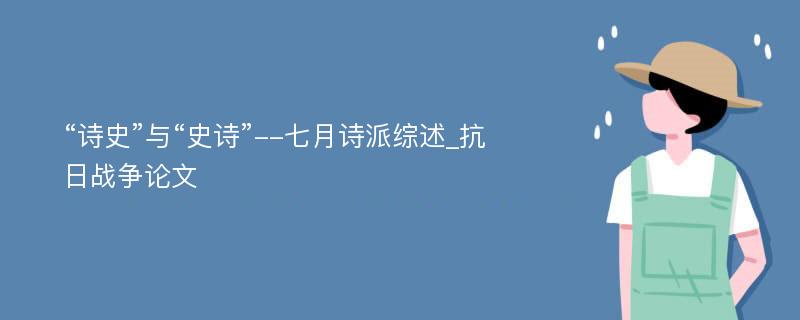
“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诗派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历史行程像战争本身一样艰苦卓绝,它所构造的艺术天地,又像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厚重。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在诗坛上坚守的时日之久,它的诗人队伍之壮大,它的艺术实践、理论探索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之密切,以及它的美学追求之开阔与坚定,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全部艺术活动,构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诗的史”与“史的诗”。
这个流派就是“七月”诗派。
上篇:解放之声与进步之声
“七月”诗派诞生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解放之声一直是“七月”诗人奉献给时代的战歌的主旋律。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与持久,以及人们无法想象的艰苦卓绝,抗战初期为高涨的民族解放情绪所掩蔽的,现实生活中的腐朽、没落的一面,便日益暴露了出来。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方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和干扰。是以“解放”掩盖其他矛盾,还是坚持进步,揭露黑暗,促进解放,成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文化人共同面临的抉择。作为一个清醒的、坚韧的艺术流派,“七月”诗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由他们的理论代言人胡风作了这样的概括:“战争不但是为祖国底解放的斗争,同时也是为祖国底进步的斗争,不,应该说,正因为战争是不经过艰苦的长期的过程就不能达到的为祖国底解放的斗争。那么,这一个对外抗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发展过程”(注: 胡风:《民族战争与我们》,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1945年重庆希望社版。)。这种坚持解放与进步相统一的、辩证的、深刻的、继承与深化了“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的认识,在“七月”诗派抗战中期之后的作品中,常常得到鲜明的艺术体现,凝结为“七月”战歌的另一个主旋律:进步之声。
曾以极为高亢的音调,写过《祝中原大捷》的庄涌,又以无比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解剖着战时的“陪都”:
重庆,你长江身上的一块疮,/现在又来了一大批下江化装师,/用脂粉掩饰你的内伤,不见红肿!/血腥的黑夜,/再捆一道矛盾的绳/我不懂你怎样再忍耐生命的惨痛?!(注:庄涌:《朗诵给重庆听》,《突围令》,1947年上海海燕书店版。)
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之初,诗人敏锐地看到大后方腐败的“内伤”——“贫穷,破乱,凄惨,黑暗”,“鸦片,麻将,盗贼,娼妓……”。诗人愤怒地发问:拖着这样的“病体”,怎么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里对于文过饰非的“下江化装师”的痛斥,也正是对于一场严正的、刮骨疗毒的、坚持进步清除腐败的“内部发展”的企盼。
如果说,庄涌的这类揭露黑暗、痛陈时弊的诗篇,还带着较多的抗战初期的痛快淋漓,因而略嫌刻露、浮躁的话,那么,抗战后期出现的这类作品,就显得含蓄、深沉得多了。绿原写于1944年岁尾的长诗《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竭力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条分缕析地披露了大后方“阳光下的罪恶”。这首诗的第3节, 写的是“例如,每次空袭解除了,庆祝常常比哀悼来得更热烈……”。尽管街道扭曲了,房屋“飞升”了,电线杆上挂着横飞的血肉——
不过,大体说来,这光荣的城不容易屈服!/几分钟后它又美丽地抬起了头:/男人照样同女人吊膀子……/电影院照样放映香艳巨片……/理发厅照样替顾客挖耳粪……/花柳专科医师照样附设土耳其浴室,奉送按摩……/绅粮们照样欢迎民众们大量献金……/保甲长照样用左脚跪在县长面前,用右脚踢打百姓:如此类推,而成衙门……/译员们照样用洋泾浜英语对驻华白侨解释国情……/公务员照样缮写呈文和布告……/报纸照样发表胜利消息,缉拿和悬赏,更正和驳斥……/可怜的学生照样练习他们的体操:立正、敬礼、鞠躬、下跪……
一切都“照样”。前方将士的殊死战斗,后方同胞的濒临绝境,对这个腐朽的社会似乎都毫无触动。诗人好像写得很平静,但这平静的冰山下面奔涌着巨大的愤怒。正是这平静的愤怒调度着、梳理着蜂拥而至的诗的意象,把诗人自己的,也是亿万普通中国人民的“平凡的感受”、“平凡的悲愤”,组织成“痛切的控诉。”“一样地是反抗现实,但有的人只是用抽象的理想来保护自己,以能够在那里安居的幸运来藐视现实的红尘,有的人却非得踩着现实生活里的荆棘开拓道路不可。”(注:胡风:《〈希望〉编后记》,《希望》第1集第3期,1946年3月。) “七月”诗人们显然属于后者。无论是艺术思考还是美学呈现,他们都充分显示出拓荒者的姿态,从“现实生活里的荆棘”丛中抽象出一些曲隐的、耐人寻味的吟咏,开发出一种深幽的、悲凉的诗美。
请看他们笔下一段中国现代史上“密云期”的“冬天”:
肺结核菌/成团的飞滚着/人们闭紧嘴/不敢呼吸
有人按着胸口,低声的咳嗽/有人窒息得脸发青,像煤块/喘着气,成群的倒下
(朱健:《低云季·沉默》)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低云季”,启齿获罪,动辄得咎。谵妄与荒诞,成为统治者认定的行为逻辑:
我不举起我的拳头来/你说我是植物/到一举起拳头来/又说是太阳系的破坏者/——总之,一张口就看清楚了你的牙齿。
(方信:《给诅咒者》)
于是,人们唯有沉默,在沉默中消耗自己,蹂躏自己,甚至像汪文宣那样,吐着血痰,窒息而死。而滋养着幸存者的期待、憧憬,又常常会在一夜之间为失望的愤懑所取代:
昨夜,/听伐木的声音/响在山上,/欣喜/山下将有火;
今天,/扒着窗口/去迎接——/呵,是/一道又一道/白楂儿栅栏,/并且落了锁!
(牧青:《火的想望》)
在期待中可以保存火种、燃起烈焰的林木,却被制成了囚禁火,囚禁向往火红、火热、火爆的人们的栅栏!于是,留给大地的,仍然只有阴暗、潮湿和寒冷。期待中的火变成了牢狱,期待中的民主变成了独裁,期待中的自由变成了奴役,期待中的繁荣变成了凋弊——“七月”诗人笔下这个阴冷的“冬天”,也就是鲁迅笔下的“现代史”:“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的“变戏法”式的社会现状(注:参见鲁讯《伪自由书·现代史》。)。不消灭空气中的结核病菌,不驱散压抑人民、窒息人们的“低云季”,不把栅栏改造成火炬,那么,即便赢得了这场驱逐异族侵略者的战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仍然只是一句空话。“如果虚伪的叫喊不一定必然得到战斗的感应,那么,真诚的叹息也未始不能引起对残酷现实的憎恨和对于光明来日的追求。”(注:胡风:《曹白著〈呼吸〉小引》,《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七月”诗人们“真诚的叹息”是让人铭心刻骨的。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最艰难的历史时期。“九死一生”、“赴汤蹈火”、“度日如年”等成语用于这一时期,似乎都没有多少夸张的意味。而“七月”诗派却正生于斯时,长于斯时。多难兴邦,多难亦兴诗。民族的深重苦难铸炼了诗人的感觉,磨砺了诗人的笔锋,深化了诗人的思考,使得诗人们“从燃烧自己开始来燃烧世界”(注:亦门(阿垅):《论形式·引论》,写于1941年9月,《诗与现实》,1951年五十年代出版社版。)。在“七月”诗人们以自己的心血烧灼的现实生活中升华出来的诗篇里,我们不但能够清晰地听到那个时代的呐喊与诅咒,而且能够感应到整个中国历史沉重的脚步。惟其如此,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才会被征服,才会感到一种很少经受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强烈震撼。五十年或六十年以前的,我们并不十分熟悉的社会生活,经过诗人们苦心孤诣的浓缩、抽象、概括与变形,已经变成一页历史,一页诗的历史,一页与我们血肉相连的历史,一页启示我们、感奋我们、滋养我们的审美化的历史。
“七月”诗派在抗日战争中逐步成熟了。1944年7月, 时值抗战爆发了7周年之际,诗人冀汸用一首简短的小诗, 极精练地勾勒出了“七月”诗派从激愤走向沉炼,从单纯走向丰富,从热烈走向凝重的前行轨迹,同时也是对七年来中国社会“众生相”的高度概括——
从激动的流泪到痛苦的流泪/从哑巴要说话到说话的变成哑巴/从老人像孩子底天真到孩子装成老人/从歌唱到悲愤地叹息/从火把到没有灯光……
(《七月底轨迹》)
岩浆冷却了。但凝聚了地层深处低沉的轰鸣。这是休眠状态的愤火,一旦复燃就将烧毁整个腐朽的世界。脚踏实地的韧性的坚定,使得“七月”诗人的艺术洞察力更加敏锐也更加深刻。八年抗战终于“惨胜”之后,胡风在一篇题为《空洞的话》(注:胡风:《空洞的话》,1946年1月2日《新华日报》。)的短文中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对于“胜利”并不感到多么欣慰,“实际上正有深沉的悲哀在”。因为“抗战当中,应该是一往向前的罢,但实际上几乎每年都被抗战到底呢还是中途重新掉进奴隶命运里面去的恐惧所侵袭”。“现在,不管怎样,抗战是胜利了,然而出乎意外地,我们又临到了一个是否重做奴隶呢的关头前面。如果内战打下去,政治专制下去,那我们不是奴隶又是什么呢?中华民国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又是什么呢?”胡风的这段话,也许可以看作“七月”诗人共同的“胜利”观。胜利没有给他们带来狂喜,他们也就没有“沉醉不知归路”的困惑。他们一如既往,为民族的解放与进步坚持着韧性的战斗。与《空洞的话》差不多同时,诗人冀汸曾这样吟咏噩梦醒来之后的《生命》:
生命呵,生命呵/在今天,在中国/没有更多的期求——/能够唱歌最好/能够大声哭泣也好/能够骄傲地活着最好/能够不屈地死去好
为了不重做奴隶,为了永远结束专制政治,诗人们期待着放声歌唱,期待着“骄傲也活着”——战斗下去;但也随时准备着“大声哭泣”以至“不屈地死去”。据冀汸的诗友阿垅说,这首诗的初稿中,原来有这样两行诗:“我们都是徒手/而且垂着手”,后面一行诗以后删掉了,因为它“和这诗底风格完全不相称”,“他底手只有举了起来;他是始终举着他底诗的怒拳的。难道他能够垂着战斗的手,就此听命于政治么?”(注:亦门:《冀汸片论》,写于1947年4月8日,《诗与现实》。)
“七月”诗人们都是举着“诗的怒拳”的。怒拳所向,是异民族的侵略者,也包括本民族的腐朽势力——一切阻碍解放与进步的腐朽势力。
下篇:美学的敏感与政治的敏感
经过抗日战争艰难时日过滤和冷凝的诗思,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在中华民族又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口,得到了进一步的淬砺。国统区的萧条经济,萎顿文化,以及政治上日甚一日的专制与高压,使得诗人们“向内”的开掘更加深入也更加刻苦。一批几近炉火纯青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政治抒情诗,政治讽刺诗,脱颖而出。储蓄的尖锐,冰结的热情,平淡掩盖的深挚,寓于回味之中的辛辣,成为这些诗作的主要审美特征——带着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社会地壳运动特有“擦痕”的审美特征。
我们看到,在这些诗作中,美学的敏感与政治的敏感是那样地密不可分,真正达到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境地。鲁藜是这样写遍地皆是的《草》的:
我是绿草。/我的装束很朴素,/也没有美丽的花朵……/可是,我是春天的信号,/人们看见我而高兴;/盛夏,劳动的人们/喜欢躺在我的怀里憩息,/到秋天,我就枯萎,/我准备火种给严寒的世界。
绿色的欢乐——生之欢乐,生之情趣,生之美, 被诗人爱的诗笔点染得异常轻盈、流丽、素朴。可是,当我们读到那决绝的、凛然的“我就枯萎”的时候,却不能不为之屏息敛容,不能不肃然起敬,从轻盈、流丽中体味出深沉、凝重来。我们方才悟出:这平凡的绿草,不管是快乐地活着还是勇敢地枯萎,都是为了炙热那“严寒的世界”。这样的诗,在和平时期的花前月下,大约是写不出来的。
朴素的绿草是可爱的,然而,诗人也并非“不是不管花/不是不被花感动”,诗人也愿意“工作完了,走在林荫路上”,“只是还没有一条平坦的路”,“我们这世界依然寒冷而荒凉/理想的花朵还没有完全开放!”(牧青:《爱花》)草为“寒冷的世界”枯萎,花也为“寒冷的世界”凋零。然而这肃杀大地冰封的土层,却禁锢不了花草根本强韧的生命力。这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花草杂咏,如同阿垅所说,“那是被战斗底旷达的心胸所怀抱的。一种鼓舞的声音。……握拳固然必须击敌,舒指也一样可以摘花的。”(注: 亦门:《〈醒来的时候〉片论》,写于1947年9月,《诗与现实》。)握拳为了护花,舒指也为了击敌。战斗也是审美,审美也是战斗——在这里,诗的辩证法既丰富又单纯。
与诗人们艺术思考的日益深入,以及整个诗派艺术积累的日益丰厚相适应的,是其后一批较长的政治抒情诗的集中出现。从1946年6 月至1949年初,徐放写出了《在动乱的城记》(注:写于1946年9月, 见《白色花》,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郑思写了《秋序》(注:载《希望》第2集第4期,1946年10月18日。),阿垅写了《去国》(注:写于1947年5月2日,见《白色花》。),牛汉写了《锤炼》(注:写于1947年, 《彩色的生活》,1951年上海泥土社版。),罗洛写了《旅途》(注:载《奔星》小集,1948年第1期。),化铁写了《解放》(注:写于1949年2月,《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1951年上海泥土社版。)。而绿原在1946年和1947年,接连写了《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悲愤的人们》,《咦,美国》,《复仇的哲学》、《伽利略在真理面前》《轭》和《你是谁?》。稍后,胡风将这7首长诗结集为《又是一个起点》, 作为《七月文丛》的一种,于1948年付梓印行。这部诗集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曾被一位论者许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成功的政治抒情诗集”(注:参见骆寒超《中国现代诗歌论》,198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胡风曾把这一时期出现的短小的诗称作为“突击性的速写”,“而诗,却总是不断地要求情绪世界底深厚和深长的”(注:胡风:《〈给战斗者〉后记》,《在混乱里面》,1946年上海作家书屋版。)。这些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的集中出现,标示了诗歌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日益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诗人们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敏感与成熟,艺术上的赅博与开阔。他们已经能够十分从容地以诗歌形式,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较全面、较深入的历史评价与美学评价了。在这些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指陈时弊,抨击暴政的。徐放的《在动乱的城记》,就是一首十分激愤的、火药味很浓的长诗。这首300 余行的诗作,以抗战胜利之后的重庆这座“动乱的城”为背景,以对一位友人的怀念为中心线索,痛快淋漓地抨击了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为加紧内战准备,掠夺人民,愚弄人民,残害人民的罪行。人民“生活在恐怖的血海里”,谋杀,盗窃,卖淫,充斥着这座“动乱的城”,充斥着整个国统区。一场殊死的民族解放战争,丝毫没有改变这个腐朽凶残的社会制度。由于篇幅较长,诗人就有可能在激愤的抒写中,从容地穿插一些事件的描述,甚至一些事件的细节——当然是诗的细节,是极其简洁的,浓缩的,凸现了抒情意象的诗化的细节。例如诗中关于谋杀,关于友人聚散,关于“我”以及和“我”一样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窘迫困境的描述等等,使得作者的激愤之情似乎有所“依托”。此外,由于诗人充分利用了诗篇相对开阔的物质空间,所抒发的感情容量和层次也都更加丰富:有大的愤懑,有小的哀愁,有凄楚的兴奋,有低抑的渴望,有穿透了浓密恐怖的炽烈向往……诗篇更全面,更确切也更真切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情绪与心态,从而更内在、更本质地表现了这个民族的历史——这历史“到底不过是一部血债”(注:亦门:《〈我是初来的〉片论》,写于1947年12月,《诗与现实》。)。诗人愤怒地写道:
在这暴君国度;/人/是没有自由的;/人/生活着;/反抗不反抗都一样要流血。……
但是,不反抗的流血,/那是懦弱的血,/那是被宰杀的血;/我要反抗/把自己的血/和敌人的血流在一起。……
“我要反抗”——不仅是这首诗,同时也是“七月”诗人“解放与进步”歌吟的共同主旋律。它像三十年前鲁讯的“救救孩子”,像十五年前巴金的“我控诉”一样震撼人心。将坚持了八年的反抗继续坚持下去——这万千灵府之声在诗篇中或隐或显,或高昂或低迴,但都同样深切而坚毅。
比较起来,绿原似乎更善于驾驭长篇巨制。他的作品更集中,更凝练,更有条不紊,常给人一种感情异常浓烈,但又经过了沉淀的清澄透彻的感觉。不时有沉甸甸、亮闪闪的,哲人的警句从饱和的诗的溶液中溢出:
我们连一滴唾沫/都没有了,/然而,/这种生活/就是教育。
饥饿!寒冷!漂泊!/透明的三棱镜/把我们/集合在/一个焦点上,/使我们发出/愤怒的/轰然的光辉
(《复仇的哲学》)
痛苦是一种危险的营养:/要是长久地咀嚼/这份伤心的茶点,/不错,我们会增加精神的钙质;/但是——/它更会使我们的骨头/变成海绵呀!
(《你是谁?》)
天堂的地板就是/地狱的天花板,/它撕着我们的头发做窠……
为了打死它/我们要学习它的残酷!/专门对它,和/对它的种族!
(《你是谁?》)
在这几首作品之前,写于抗战胜利当月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更是珠玑满篇。一连串深思熟虑的警言、箴言、预言式的诗句,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不得不更加全神贯注,仔细辨析每一缕奇幻的智慧之光。在庆祝抗战胜利,山呼万岁,举国狂欢的时刻,诗人当然比任何人都更激动。但这激动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情绪,同时还是一种力量。诗人是弄潮儿,他能推波助澜,随波逐流,但也能驾驭感情的狂潮,乘风破浪。这一切,取决于他所意识到了的、整个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势与美学走向。因此,诗人一方面兴奋地感觉到,“中国的/体温/升腾着;/脉搏/弹跃着,”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九死一生的/胜利,与失败几乎没有距离的胜利呀”。胜利来之不易,胜利又岌岌可危。为了巩固胜利,只有把这个“终点”当作“又一个起点”,时代要求“中国人民/再前进!”诗人以极精粹的意象,传达了深刻的诗的感悟:对于未来的岁月,胜利并不是一片霞彩,而只是一点微弱的火星:
“胜利/来了:/啊,火种/出现在/冰河时代!”
在其后三四年中诗人所写下的,以及其他“七月”诗人们所写下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星“火种”是如何点燃亿万人民的愤懑、狂怒、反抗,终于燃成燎原烈火,结束了中国历史的“冰河时代”,走向了真正的民族解放,如同诗人化铁所忘情讴歌的《解放》。诗人满怀解放的喜悦,以极其宏朗的音调,歌颂阳光,歌颂树木,歌颂丰收的禾稻与宽大的谷仓,歌颂红旗,歌颂坦克的装甲和油漆。但当我们读到:“奔放的小涧可以用它底愤怒告诉你,幽怨的河流可以用它底深沉告诉你”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与《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与《在动乱的城记》,与《秩序》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歌颂是从痛苦思索所长期浸泡的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热烈中又带着特有的苦涩与深沉。这首诗结束于“中国,中国哟!/永远不息地前进吧!”成为四年前绿原的“中国人民/再前进”的继续与发展。没有民族的不断进步就没有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史所提供的,也是“七月”诗人反复吟咏的一个“永恒主题”。
诗人聂绀弩的长诗《日出》(《山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歌》之第一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里对于冉冉旭日的忘情歌颂,有着十分明显的寓意。十多年来,诗人们执着地追求,热切地期待的那个诗的理想国度终于迫近了,而他们用坚韧的诗笔所抨击、所诅咒的阴冷的长夜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诗人写道:“多少年辰以前/先知就告诉我们:/将有一个日出。/饥饿么,日出就好了,/寒冷么,日出就好了,/痛苦么,日出就好了,/恐惧么,日出就好了!”隐约闪现在“七月”诗人的那些厚重的篇什中的“先知”的预言实现了。“七月”诗派作为一个以讴歌民族解放与进步为己任的现代文学流派,集结在国破家亡的战火硝烟中,艰难地又是顽强地穿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漫漫长夜,走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灿烂阳光下,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虽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又经历了一次或多次“日出后的恶梦”,但对于自己年轻时艰难的历史行程,他们是无怨无悔的。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敏感与美学敏感,忠实地录存了中国历史中十分厚重的一页。
1943年,已经写过十多年白话新诗又研究过十多年古典诗歌的前辈诗人闻一多,在给自己早年的学生臧克家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注:闻一多:《书信·致臧克家》,《闻一多全集》第3卷,194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诗的史”与“史的诗”的精到概括,标示了那个时代富有历史责任感的诗人和学人们比较普通的美学追求。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七月”诗人们奉献给中国新诗史的,正是这样一部不断向历史深处和社会现实深处掘发的“诗的史”与“史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