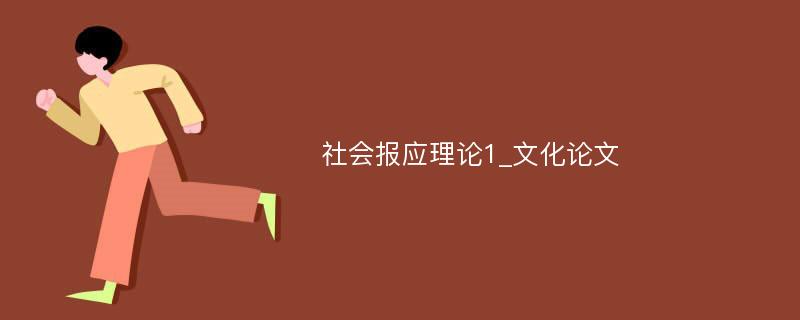
社会报应论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应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因果报应在理论界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落后的、反科学的观念,到底其中有没有积极、合理的成分,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否具有这种职能,这种职能是否应该加以倡导和发展以及如何使之发展等等是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又未曾被认真地加以系统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就这一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因果报应是人类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想
因果报应的思想被看做与宗教宣传、迷信相联系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观念,是对问题未做深入研究的结果。流行的因果报应思想的确是与宗教的教义和宣传相联系着的,也发挥着一种欺骗、麻痹劳动群众的作用。但如果透过现象的表面,从其产生、流行的心理学原因上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存在。这种合理的因素就在于它是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想。从其最抽象、最朴素的意义上看,因果报应的思想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人的行为有善有恶,其有利于社会生活和他人者为善,反之即是恶;第二,有善行为者得善报,有恶行者得恶报,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存续和发展;第三,这一社会生活的原则适用于社会的所有成员。通过因果报应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和限制以利于社会的存续和发展,这无疑是一种合理的要求。对绝大多数真心信奉的广大劳动群众,是一种善良的、合理的愿望或理想。
这种理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极大的普遍性。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目前世界上信奉者最多的三大宗教的教义中都有有关因果报应的内容。佛教是宣扬因果报应说最多最系统的宗教,从印度的原始佛教起,发展、流变以至今日,其关于因缘、报应的说法有很大的变化,但始终是其教义的主要组成成分〔1〕。 因果报应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虽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但《古兰经》所规定的六大基本信仰中也依然有“信后世”、“信前定”的内容。要求信徒们信“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在今世走“正道”,行“善功”,争取死后经过审判复活进入天堂〔2〕。基督教虽不明白地讲因果报应,但要求人们“爱人如己”, 有“牺牲精神”,“为兄弟舍命”,通过这种活动,达到“出死入生”,获得未来天国的幸福〔3〕。 这里也都蕴涵着一种比较广义的因果报应的思想。可以说,三大宗教的信奉者们都是秉信因果报应的理想的。
在我国,因果报应的被信奉是由来已久的,在传统文化思想中有很大的影响。随着科学昌明与无神论宣传的深入人心,为宗教迷信所宣传的那种因果报应说的信奉者是大为减少了。但就是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在激情状态下来评骘善恶的人和事时,往往运用因果报应说的语言(如当多行恶事而长期未受到惩罚的人最终受到严惩时,快意地称之为“难逃的报应”)。甚至坚决反对宗教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如陈毅同志痛斥林彪集团反革命罪行时所说出的一番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恶不报,时间未到”,不能认为只是出于义愤而沿用了社会上的习惯语言,而应该认为表现出了讲话人的情感与愿望,这些情感和愿望又是和认为人的善行恶行都应该受到相应的报应这种社会生活的理想相联系的。可见,因果报应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合理的、普遍的理想,是与人们是否相信宗教的荒谬宣传无关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的实质,弄清人类的这一社会理想的发展,以及它如何成为宗教的迷信思想,又如何从宗教观念的迷雾中走出来走向必然的独立与现实化并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的曲折道路,我们必须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因果报应的观念做一番考察。
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及其对人的启示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因果报应的思想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巨大的影响。从其被人信奉的情况而言,在全国解放之前,是十分广泛盛行的。解放后,随着无神论思想的宣传和深入,信奉者大为减少。而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宗教迷信思想的复活,这种观念又开始盛行。
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说,是一种在宗教迷信中产生认为一切都是由冥冥之中的神明管理和执行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在我国已有的儒家、道教和后来的佛教的结合中形成的,但三者的作用又各有不同。儒家学说中本来就有“积善有余庆,积恶有余殃”的说法,但却又认为“天道远,人事迩”,极少深入去议论这一问题。在佛教大肆传入中国之前,道教已多言鬼神,且谓上天可以察知人之善恶而予以报偿,并提倡天国与地狱之说〔4〕,其说较儒家为多而具体。 而佛教关于因果报应之说则最为系统和完整。当佛教传入我国后,即与我国道教原有的鬼神之说相结合,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理论。因此,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之说,主要是出自佛教和道教的教义,而儒家则不过加以认可和利用而已。
根据对我国民间传说与一些笔记类小说的分析、整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理论,有下列几个基本的特点:一是报应的必然性。认为行为之善者必有善报,恶者必有恶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人之行为善恶,冥冥之中,神鬼明察,甚至有专门的录载、注销、实施之司。对人之行为,其报应或速至眼前、今生,或迟至来世、子孙后代,但不能淹没不报。对大奸、大恶者,有时对其小恶虽报不及时,则是有待成其大而后更加严报之。二是报应的适宜性。指善者得福,恶者得祸,而且所得之福、祸之大小、性质,是与其所行善、恶之大小与性质相当的。三是重视行为者的动机。认为善恶之行均由善恶之念所引起,所以特别重视人的善恶之念的发生,有所谓“一念之生,鬼神已察之”。有以一善念之生,而可以免致狐鬼之加害者。四是对位高权重、明于事理者给予更严格的要求。位高权重者,操人之生杀予夺。一政善,千百万人受其福,一政失,千百万人受其祸,故其行之善恶,受报不可不严〔5〕;对明于事理者,理应为善,明知其恶而为之, 据“诛心”之义,其受谴亦应加重〔6〕。
然而,这种虚构的理论是不可能不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相矛盾的。因此,在大量述及因果报应的书籍,如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上述精神的条件下,而对之加以相反方向的修改。修改之一是在宣扬报应不爽的同时,又承认天意之难测。“死生转毂,因果循环,如恒河之沙,积数不可以测算;如太空之云,变态不可以思议”。“天道乘除,不能尽测”〔7〕。 修改之二是在儒家传统的“天道远,人事迩”,“《六经》所论皆人事,《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的宗旨指引下,要求人们不能“舍人事而言天道”,从而把注意的中心转向人事的考虑上〔8〕。 如提出鬼神所司的报应是假诸人甚至物的作用实现的。这一点在后人曾国藩的家书中说得也更明白:“人满则天概之,……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9〕; 又如强调势的作用:“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贫,势也”〔10〕。所谓势也就是指的社会生活中的(有时也指自然的)必然法则;书中又提出了许多提高人的自我修养,以求得福避祸的原则和方法,如“天道忌太甚,过俭过奢,皆足致不祥”;“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母太快口,则永保终吉”,“不为已甚”等都完全是根据人情之势理而提出的。 对于这种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纪昀的思想可以代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他认为这种理论是与“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其事殊,其意同”的社会用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另一种主要手段〔11〕。其作用“亦足警戒下愚,使回心向上,于世不为无补”〔12〕。但就其与讲人生之道的儒家思想相比,则应以“明人道者为主,明神道者则辅之”。“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而“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盛,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人。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13〕。与政治道德相较,只具有次要的、辅助的、补充的作用。另外,与道德之为自觉为善者而设不同,因果报应之说与刑赏则是为占人口中之数的中人以下者所设,而具有一种强制、强迫的性质。因此,对一些传闻是否出自虚构,不欲深究。“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14〕,“不必曲为之词,亦不必力攻其说”〔15〕,持一种灵活而宽容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些,才使鲁迅得出纪昀“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投教”〔16〕的结论。
我们认为,上述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一、人类有着普遍的对人的行为的善恶进行报应的愿望,而现实的社会生活确实也在一定范围内具有这种职能。二、这种社会职能由于受各种现实的原因的影响,如对立的社会阶级的存在、人类对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不甚了解等等,因而显得太有限和微不足道,根本不能满足上述愿望。三、这一矛盾情况的存在就驱使人们从普遍的善良愿望出发,以社会所具有的虽属有限但仍存在的现实的报应职能为依托,构想出一套由冥冥中的神灵所司的因果报应的理论,藉以宽慰人们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规范人的行为,稳定社会的秩序。四、这一套理论也具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但它却只是人们幻想中的东西,虽然也能给受害者以慰藉,对强暴者施以儆戒,但并不能真正起到抑恶扬善的作用。因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其虚空无凭的性质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现实的人的关系和行为上。
上述诸点对我们的启发就在于:既然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社会的报应职能的有限性,驱使人们构想出一套虚假的宗教的因果报应理论,那么,在科学更加昌明、人对社会的自然的认识更加深入、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都能够为人类自觉掌握的今天,可否使思维走一条相反的道路,把宗教的因果报应的理论,移置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一种社会的现实的因果报应理论,用以提高和扩大社会本身的因果报应职能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呢?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戴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17〕我们的任务是在打碎套在身上的锁链时也抛弃掉宗教的因果报应这种虚幻的花朵,但同时却去摘取改造后的回到现实的基础上的社会的因果报应这种真实的花朵。
现实的、社会的因果报应的理论就是在上述的背景和根据之上提出来的。
三、现实与社会报应的实质及社会作用
这样,我们就把因果报应由幻虚返回现实,变成了受制约于现实规律的东西,成了可以解释,可以预测,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可以谋求和避免的东西。把现实的报应与社会的报应在相同的意义上加以运用,是由于人的一切活动的作用及其所受到来自他人的或外物的报应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和实现的。但仔细地分析起来,二者在其具体涵义上还是有区别的。
人在自己的生活活动中,要与两个方面的实体或对象发生相互关系。一是具体的人(亲友、同学、同事、买卖双方),或由人所组成的人类群体(如阶级、集体、家庭、企业),另一方面是其所作用的各种具体的客观的对象(如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的物理条件等)。对于这两者,人类的活动都对之发生作用。同时,由于作用的不同而受到来自它们的不同的反作用,即报应。前者是有意识的人,其对人的行为的报应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受社会法则的支配(例如,当人的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时,就会受到他人的报复)。后者则是物,是自然的物体或人改造而成的物体,其所给人施予的报应是无意识的,受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的客观法则的支配(例如,在人之使用工具或改变自然物时由于方法错误而导致损失和灾祸)。所谓社会的报应,从其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是人以自己的行为所得到的来自他人或人类群体的报应。
这样的划分是有意义的。因为二者在其起作用的方式与效果上都是不同的。对人的社会行为的报应主要是前一种报应,但却不应该忽略它们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在一般情况下,自然的物的报应总是受制于社会的人的报应的。人总是在社会报应所赋予的地位与条件下来接受自然的物的报应的。然而,由于社会总还是在自然之中存在,它本身也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特别限定的部分,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越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影响。因此,在自然物对人的报应在其强度和范围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人以自己的行为造成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重大破坏时),人对社会他人的行为和其所得到的报应不仅可能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改变,甚至还会使社会生活的存在及其方式发生很大的改变,使其正常运行发生困难。另外,在二者之间还经常不断地进行着转化。人的社会的报应可以转化为自然的物的报应,而自然的物的报应亦可以向社会的人的报应转化。因此,明于此理的人就可以努力使之向有利方面而避免其向不利方面的转化。
粗略地看来,社会的报应相当于前边所说的社会劝善途径中的“刑赏”(法律)与“褒贬”两个方面的总和,但仔细地加以分析,其中还有一些为上述二者所不能尽括的内容。就其所施报应的原由来说,不只包括一个人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动机是否善良,而且包括一个人的知识能力道德修养以及为这些条件所决定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实际效果;其给人的思想行为所给予的报应的内容,不只有依据法律所给予的刑罚与奖赏,根据社会道德标准所给予的表扬与谴责,而且还包含根据社会生活所依据的一切实际准则而得到的一切社会生活地位、条件等的相应的改变。因此,社会报应实际上是涉及到整个人的社会生活的一条根本法则。
社会报应的客体是每个在社会生活中活动着的人。任何具有行为能力与责任的人都不应逃脱社会对其行为所施予的报应。社会报应的施予者包括代表社会利益的各种人群组织和每个人。社会群体有着不可推卸的对行为人施加报应的权利和义务,其作用固属强大。但群体乃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素质的个人无疑会影响群体作用的发挥;另外,群体的作用也必然受到所有社会成员的影响,由他们的支持、反对、冷遇等而影响到它的效果。因此,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其素质、责任感、勇气、毅力等都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报应的实现及社会生活的提高和完善。
人总是生活于人的相互关系中,整个社会就是由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受到来自他人(或社会群体、组织)的报应。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生活就是一个人的因果报应的整体,人们都处在这复杂的报应的链条之上,而社会也是在这一链条的作用中不断进行着。但是,由于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狭隘的个人利益和见解来作出报应的,社会的这种报应作用的实现又是不尽相同的。无论就报应之有无,还是报应是否及时、公允上看,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得好就会使社会广大成员感到公平、快慰、欣幸并逐渐导致社会风气的好转而使人们一心向上。而如果实现得不好,就会使人们感到不公平、内心压抑、不满,对当前的社会秩序持否定的态度,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和秩序紊乱(极端的情况下还会导致社会生活发生动乱)〔18〕。因此,社会的健全和发展要求它的社会报应职能的完善和改进。
四、加强和改善社会报应的途径
社会的报应从其心理学实质上看,乃是由整个社会所施行的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的正面的和负面强化作用的体系。作为一种对人的思想行为的社会的强化,有一些独具的特点:一是强化手段的多样性,不只有身体的、物质的强化,还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的、社会的强化;二是被强化的不只是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还有识见能力、品质等,而且强化不必等待行为及其后果之发生而具有一种前行性;三是强化的作用,即对个别人的强化可通过作用于他人来实现,具有一种间接的可替代的性质。
由于社会生活及其报应活动的复杂性,常常会使报应与其受报应的思想行为之间发生某种“脱节”,受报者常常不明白所由得报的原因,从而降低了社会报应的效果。因此,个体(不限于受报者)对报应的归因活动乃是实现社会报应并获得其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前提。归因的对象既有自身的,也有他人的;既有个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所由发生的归因,也有行为所得到的强化及行为本身特点间关系的归因。社会除了确定强化的对象及强化方式、手段之外,还应该创造条件,使这种归因活动达到最有效的地步。
加强和改善社会的报应系统,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里仅就几个重要问题略加阐述。一是如何确定被报应或强化的行为的标准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应该考虑到如下几点:首先是该种行为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于社会和他人,以及这种有益或有害的性质和程度;其二,在确定行为之有益或有害时,要注意到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既考虑到行为的后果,也考虑到行为者的动机和用心;其三,在考虑到行为者的主观因素时,不仅应考虑其基本出发点,即所谓善恶、为己还是为人的问题,还应该考虑到他是否有足够的思想修养而善于把这一善念在实际中加以实现的问题,如吕坤曾对“恕”字的运用做如下的具体化:“恕人有六:或彼识见有不到处,或彼听闻有未真处,或彼力量有不及处,或彼心事有所苦处,或彼精神有所忽处,或彼微意有所在处。先此六恕而后命之不从,教之不改,然后可罪也已”〔19〕。要求从政者能从这些方面去体谅他人的苦衷,这也是对人的道德修养的要求。此外,人的能力、知识经验,也应予考虑。其四,在考虑行为的效果时,不仅要考虑其直接的切近的效果,还要考虑到它的长远的间接效果。如对于统计工作中的虚报现象,就应该看到它对宏观规划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危害。不仅要考虑到其社会影响,还要考虑到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如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其五,对权位高和明事理者作更高的要求。对这一点,吕坤曾做过明白的解释和有力的强调:“世道有三责,责贵、责贤、责坏乱纲纪之最者,……贵者握风俗教化之权,而首坏以为庶人倡,则庶人莫不象之。贤者明风俗教化之道,而自坏以为不肖者倡,则不肖者莫不象之。责此二人,此谓治本。”他还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对贵者、贤者“以体面宽假之”,以免“苛刻以伤士大夫之体”〔20〕的作法。这一点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二是对不同的行为施行什么报应和如何施行报应的问题。对此应该特别强调如下特点:第一是行为的善恶必有其报。不能无报,更不能相反,使善得恶报或恶得善报,而且这种报应应当尽可能地及时,不能过久施延;尽可能公平,使善恶之大小与所受报应的大小轻重相当。前一段时期内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混乱,实与这一原则没有被有效贯彻有关。以后加大了打击坏人坏事的力度,从各方面奖励好人善行,“不使英雄人物吃亏”,这才使社会风气、秩序有所改善。第二是报应必须是多方面的,包括身体的、物质的与精神的,而且应该将这些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对于一切受善恶之报者,都必须特别注意精神上的奖惩。这样才能加强、扩大报应的力量和社会效果;最后是在施报上要注意到人的主观修养水平上的差异,既要适应这种差异,又要通过这种报应的施予对之加以提高。如关于什么是最高的善报,就有不同的看法。吕坤就曾提出“名”是高于禄、位、寿、康、宁、顺、适、子孙贤达的天“所最靳而不轻以与人的”福报〔21〕。我们或可以认为最大的善报是在各种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为社会做了应有的贡献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但这样的观点恐怕只适合于有较高文化和道德修养的人,而对那些只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人则是不能接受的。死,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对一般人来说,可以算是最大的罚或恶报了,然而对于那些一味追求享受、刺激而毫无道德良心的人却可能认为既不能再照样享乐则生不如死。显然,对前一种人的奖励如果过分强调物质方面的东西,就会被认为对其品德的亵渎。报载浙江某企业提出重金奖励好干部之所以引起非议,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对后一种人即使判处极型也不一定能触动其灵魂深处。所以在判刑与执行的过程中,还必须加强对其精神上的鞭挞与谴责。以不仅能触动其本人,且更多地影响后来者,从而改变其对祸福的观点。如果通过这样的活动能使我们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接受前一种祸福观,我们社会的面貌就有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
三是如何加强进行报应的动力以推动人们去进行报应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加强社会对报应必要性的宣传教育。要树立社会风气的改善与社会的合理发展有赖于社会报应的有效进行,而这又有赖于全社会的自觉的观点。要使全社会明白:社会报应人人有责,如有可能为而不为,就是失职、犯罪,有愧于作为社会的合格成员。对一般的社会成员与专负报应之责的专门机构应作不同的要求。对一般的社会成员,除了特殊的情况如知人之犯罪而不报者等之外,一般只做精神上的或舆论上的谴责。而对那些专司报应之责的机构(不只是一般司法机关,一切主管人事升迁、福利待遇、奖励评骘的机构均属之),则由于职能所在,有所失就是渎职犯罪,而应该科以应有的处罚。纪昀在其《笔记》中所记的关于某刑名吏由于但“知刻酷之积怨,不知忠厚亦能积怨”,“但见生者之可悯,不见死者之可悲”,曲意为罪犯纵容开脱而获冥谴的故事〔22〕是很有深意的。纪昀所说的还只是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所引起的渎职,对那些由于私利所引起的该报不报或报应不当的行为,则应该得到更加严厉的报应。
五、提出社会报应理论的意义
应该指出,这一理论虽然把整个社会生活都涵盖进去了,但并没有提出为实现这种报应的新的领域和途径,因为这些生活领域都是早已存在了的。它的意义在于提出和强调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对社会生活和每一个个体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
首先,从对社会生活总体来说,这一理论对社会生活做总体的考察,认为社会生活是一连续不断的人们之间的因果报应的总体,任何人都是这一链条上的个别环节,个人不能离开这一总体,个人的行为也必然最终影响着这一总体。对于社会生活的存续和发展,个人就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社会的发展,要求改进、完善自身的组织、机能、发挥个人的作用和主动性。而个人如果想使社会有所改进的话,也只有以自己的行为来加以促进。
如果只就个人来看,则可能获得以下的益处:一是使个人明确自身的思想、行为,必然要带来一定的社会后果;二是个人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三是在个人的思想、行为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上,个人总是有其进行选择和决定的主动性和余地的。因之,个人的命运和前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来争取的。
此外,这种理论的提出对破除宗教迷信也有好处。人们曾想从神灵所司的因果报应之中寻找公平和慰藉,但那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或欺骗。而把因果报应完全放置在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理解和运用的基础之上,它就不再是虚无缥渺而是用人的力量来求得和改变的东西了。当人们着眼于现实的努力时,宗教迷信的吸引力就会日趋减弱和缩小。
在谈到社会报应理论的意义时,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吕坤所提出过的。他说:“若执福善祸淫之说,而使之不爽,则为善之心衰矣”。如果报应彻底地得到公平的实现,一切善行得善报,一切恶行都得到恶报,人们就会只是为了避免恶报才不去作恶,为了善报才去为善。这样的问题的提出似乎有道理,但是,这样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首先,提倡最大限度地实现报应的公平,这只是提出一个努力争取实现的原则,力求避免社会报应中的不公正现象,改变吕坤所说的“祸福是气运”而“气运只是偶然”〔23〕的情况,实际上真正的“不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组织与人的工作不可能绝对完善,疏漏总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类对社会、自然认识的不可能一下就达到完善,究竟何者为善为恶,给予何等报应才能促使社会的完善发展的认识亦永远不能达于完善。其次,即使报应达到极大公平的程度,社会还会要提倡和褒扬人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不会号召人们为了得福才去做善行。在大多数人得到公平报偿的情况下,少数人的“委屈”也就可以在人们的自我肯定中得到补偿。
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报应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可以认为,二者是同时存在并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各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推移等无疑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社会报应则是在其中起作用的更为内部的、发动的力量。在各种社会形态的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都内涵有社会报应的内容并受制约。同时,二者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社会报应的具体内容和作用的方式与程度,受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制约;同时,社会报应进行的完善与否又影响着社会人心的平衡与满足的程度,社会秩序的稳定或动荡,以及重大变动、变革的是否发生等。
①收稿日期:1996—02—06
注释:
〔1〕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25、128页。
〔2〕曹琦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 91年版,第226页。
〔3〕罗国杰等:《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324页。
〔4〕《道教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9—310页。
〔5〕〔6〕〔7〕〔8〕〔10〕〔11〕〔12〕〔13〕〔14〕〔15〕〔18〕〔2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3、158、268、173、199、340、80、152、125、235、178页。
〔9〕《曾国藩家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 第184、302页。
〔1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9〕〔20〕〔21〕〔23〕吕坤:《呻吟语》,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308、262、193、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