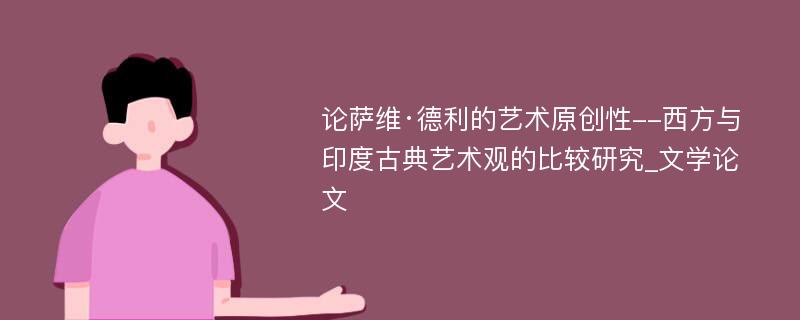
试论莎维德丽的艺术独创性——兼及西、印典型观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创性论文,试论论文,典型论文,维德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莎维德丽作为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成功最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很难使人相信她却不是《莎维德丽》〔1〕着意刻划的重心, 而其形象的塑造却又是那样出奇的无容置疑的成功。这是《莎维德丽》最令人惊异的地方,也是其在艺术上最令人值得赞叹的地方。莎维德丽形象艺术上的独创性也正表现在这里。
金克木先生在论及《那罗传》时说,“《那罗传》〔2〕在现代人的解说中往往只是作为一个歌颂个人爱情的浪漫故事,但在大史诗里它却是一个鼓励流放中的国王不要灰心的有政治意义的作品。”〔3〕这一评论同样也适合《莎维德丽》。因为这“两篇都是仙人讲给流放在森林中的坚战王听的,用意很明显是给失势的王者以安慰和希望。”〔4〕也正是这些明显的政治意图,致使莎维德丽形象的塑造居于次要地位,并使刻意叙述故事成了作品执意强调的重点。因为要达到为般度王排忧解愁的目的,大仙人玛尔根德耶就必须审慎地安排故事,把叙述的重点放在莎维德丽怎样以其异乎寻常的德行的魅力和高超的说服手段,说服阎摩神,满足她的五大心愿上。〔5〕也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说服业已失去王国的坚战相信:德行高尚的德罗波蒂(黑公主)将象莎维德丽那样给般度五子带来同样的福分和好运,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恢复王国。作者在临近尾声的第七章第14、15两颂诗中说:
就这样莎维德丽
把自己的父母和公婆,
和丈夫家世与门第
救出了灾殃脱网罗。
同样这贤德的德罗波蒂
也是家世品行件件强,
她将如名门之女莎维德丽
救你们诸位脱出灾殃。〔6〕
更是再清楚不过地道出了玛尔根德耶刻意叙述的动机和明显的政治功利目的。因此,讲好莎维德丽的故事或者怎样把莎维德丽的故事讲好才是他最关心的。与其说他着意的是人物形象,勿宁说他更着意作品的叙事结构。
这是由一般民间口头文学与史诗讲唱文学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还同古印度叙事文学口语化较强的总体风格不无干系。《莎维德丽》是如此,整个《摩诃婆罗多》的主干故事和大大小小的插话无不如此。只是无意着墨刻划人物的《莎维德丽》却在人物塑造方面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并达到了一般民间口头文学和史诗讲唱文学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大史诗众多人物的塑造固然不乏精采之笔,但无论如何都难以比得上莎维德丽“无迹可求”的浑然天成。她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似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就象智慧女神雅典娜不曾经历过正常的分娩渠道,一下子就从其父宙斯的脑袋中跳出来一样。这种类似于中国“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艺术超常现象,从平凡中见不凡,恰恰显示了作者非凡的艺术功力。就印度古典梵语诗学传统而言,同样也把“无意”带来的艺术上的成功视为梵语文学的极境。譬如印度11世纪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安主在他重要的诗学著作《诗人的颈饰》中就曾把诗歌的艺术魅力分为“无意、有意、部分、整体、词音、词义、词义和词义、修辞、味和著名故事”〔7〕等10种,并把“无意”列为艺术魅力的第一位。凡是作者有意谋求的艺术效果,无论其多么成功,都将等而次之。由此可见印度人对这一艺术境界的推崇程度。
二
那么《莎维德丽》是怎样步入这一崇高的艺术境界的呢?作者又是怎样在“无意之中”成功地完成了莎维德丽形象的塑造,使“无意”同“奇迹”这对难以克服的矛盾在作品中,或者说在玛尔根德耶精彩的叙述中获得完美统一的呢?
在我们看来,这种奇特的成功,首先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作品叙事结构的完整性,得力于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叙述艺术。同时又与古印度独特的“人物叙述论”的典型观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印度古代叙事文学很发达,可他们的典型论却很不景气。远不象西方把其作为诗学理论探讨的中心,他们更着重文学的形式因素的探索。“庄严”、“风格”、“韵”、“味”、“诗德”、“味病”等美学范畴才是他们探讨的重心。一句话,怎样表达,怎样叙述才是他们致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公元前后婆罗多牟尼的《舞论》出于戏剧表演的需要,例是曾专门在第34章论述过戏剧的角色,还依人性和品格把男女主角分为上、中、下三等,并在理论上对男女主角、配角乃至丑角及其他们各自所应具备的性格特征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和具体规定,从而开辟了印度独特的典型观。可惜后来脱胎于《舞论》的古典梵语诗学在人物塑造方面并没有很好地继承它的衣钵,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反而更多地转向了修辞、味、韵本身。从七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檀丁的《诗镜》,直到十四世纪毗首那特的《文镜》,这中间产生的众多的梵语诗学著作大都把人物同味、情、味病、情节之关系等放在一起探讨,或者在论及情味等美学范畴时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譬如十一世纪著名的诗学家曼摩吒在《诗光》里谈人物时就是把其作为第九种味病“违背人物性格”的补证材料来谈的。尽管这里不乏称呼要符合人物身份和服饰,行为要符合时间、地点、年龄和种姓等类型化规定,明显也是为准确的叙述服务的。只有雪月的《诗教》和维底亚那特的《婆罗多波楼陀罗名誉装饰》对人物没有专章论述。及至十五世纪般努达多专论男女主角的《味花簇》也没能象《韵光》、《诗光》那样蔚成大观。一千多年来还形成了“庄严论”、“风格论”、“韵论”和“味论”四大梵语诗学体系。金克木先生在他的《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译本序》中把这四个都未能深入到内容的梵语诗学体系,统统归结为形式主义美学范畴〔8〕,是很有见地的。因为无论“庄严论”、“风格论”, 还是“韵论”、“味论”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解决如何表达、如何叙述的问题。他们所创造的“连串插入式”的框架叙事结构,差不多传遍了整个世界,便充分地显示了印度人叙述方面的特殊才能。
叙事文学都很发达的古代印度和西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却沿着两条不同的价值取向朝前发展。西方人在着重发展“典型展示论”的同时,印度人则着重发展了“形象叙述论”或“人物叙述论”。西方的“典型展示论”重展示,强调形象的展示性,主张故事叙述为人物塑造服务,造就的是“展示性人物”,即后来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的美学目的是求真。而印度形式主义的“人物叙述论”重叙述,强调形象的叙述性,主张人物形象为叙述故事服务,造就的是“叙述性人物”,换句话说就是“叙述环境中的叙述性格”〔9〕,其美学目的是重想象,重诗意,求美。 前者必然是典型化的,后者必然是类型化的。印度的“人物叙述论”为了叙述故事,求得某种圆满的伦理意义,可以部分地牺牲人物,改变人物性格。因此,古印度的叙事文学中,只要故事叙述是成功的、完满的,那么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必然是成功的。故事叙述如果是失败的,他的人物必然也要失败。而西方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人物是成功的,其故事叙述却未必成功、完满;人物是失败的,其情节叙述却未必失败。由于前者遵循的是重在表意达情、诗以载法的印度文学传统,后者遵循的是重在展示思想、文以张人的西方文学传统。另外,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所造就的两种典型观,还决定了西方人在塑造人物时,必然是刻意的,有意追求的。而印度人则必然是无为的,顺其自然的,无意中水到渠成的。这样,西方人在塑造一个人物形象时要费劲得多,印度人在塑造人物时要轻松得多。前者由于“刻意”而费劲,后者由于“无意”而轻松。西方叙事文学中成功的人物典型之所以比印度多,还由于西方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貌似费劲却容易成功,古印度作家在塑造人物时貌似轻松却极其艰难。原因是前者靠展示,后者靠叙述。所谓“展示”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自我展现完成其形象塑造,与其有关的价值判断往往需由读者自己做出,带有较强的客观性。所谓“叙述”主要是通过作者对人物的直述和转述完成其形象塑造,与其有关的价值判断往往由作者事先做出,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前者在侧重人物的自我展现时,作者的叙述较为隐蔽,往往是潜在的。后者在侧重作者对人物的展示和讲述时,作者的叙述较为直露,是显在的,人物的自我展现则往往是潜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展示”又是作者的潜在叙述,所谓“叙述”又是人物的潜在展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为人物直现,后者为作者代现。
正因为此,莎维德丽这一形象的成功在古印度叙事文学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同时,也正因为古代印度叙事文学这一形象塑造的总体特征,无论莎维德丽这一形象怎样的无与伦比,她既然处在古代印度叙事文学的具体情境之中,就只能靠作者叙述的优美完整来造就。
事实上,作品中玛尔根德耶着意叙述的主人公的三次说服活动,不仅很好地显示了作品完整的叙述结构,同时也充分地展现了莎维德丽优美的内在性格结构。因为莎维德丽形象的成功塑造基本上也正是在玛尔根德耶讲述的这三次说服活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完成的。莎维德丽的第一次说服活动,是她以传统的近乎迂腐的婚姻正法观念为幌子,说服父王同意她同一个已经失去王国的盲国王的儿子——只有一年寿限的品貌双全的青年王子萨谛梵缔结婚姻,有效地维护了她爱的抉择和崇高的婚姻理想。莎维德丽的第二次说服活动是她以出嫁一年来不曾出过家门,采野果为的是供奉双亲和祖先系正法规定,不该阻拦为由,说服公婆同意她同萨谛梵一起去林中,真正的意图却是要保护寿限就要到期的丈夫。这样,她的所说和当时的心中所想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高尚的不一致”。然而我们决不能据此指责她对长辈不恭。因为恰恰在这种“高尚的不一致”里,表现了她无与伦比的德行和天大的孝心。莎维德丽的第三次说服活动是她对阎摩神的说服。其说服中心是说服阎摩神放回萨谛梵的灵魂,不要拆散她与萨谛梵美满的婚姻。围绕着这个说服中心,莎维德丽同阎摩神之间展开了五个紧张的说服回合。五个说服回合中阎摩神在莎维德丽顽强的说服意志的强劲攻势之下,节节败北。阎摩神让她挑选心愿时,她的前三个心愿都是为别人着想,只是在挑选第四个心愿时才想到自己。最后在第五个说服回合里,由于阎摩神逻辑上的悖论和谬误,还是被迫极不情愿地放回了萨谛梵的灵魂,由一个铁面无私的执法神蜕变为一个颇值得人称颂的令人尊敬的善者。这时莎维德丽对萨谛梵的爱已上升到一种“爱即生命”的高度,她高超的说服艺术和说服智慧也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境地。由于夫君的失而复得,莎维德丽克服暂时的人格分裂,实现心理复元,其形象的塑造也随之告一段落。可以说莎维德丽高尚的道德品格、卓越的说服智慧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三大性格特征,贯穿于三次说服活动的始终。由于它们共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各自又都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内涵层面:就其说服智慧而言,包含着对父王、对公婆、对阎摩神的说服三个层面;就其爱的忠贞不渝而言,也包含着“爱的执着”、“对爱的职责的超凡履行”、“把爱情上升到自己生命的高度”三个层面;就其高尚的品格而言,第一个层面主要表现为“择偶的高尚”,关心的是自己,第二个层面主要表现为“去林中目的的高尚”,关心的是丈夫,在第三个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如果说莎维德丽制服对手的两大说服手段——非凡的说服智慧和高尚的道德品格是其形象运作不可或缺的两条重要的发展轨道,那么她对萨谛梵忠贞不渝的爱情便是其形象发展的生命原动力。一旦它们在最终结合点上重合,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就算基本完成了。
然而,倘若没有三次说服活动之后说服效果的情节延伸,对其主要性格特征加以丰富补充,整个形象就会显得干瘪、苍白,缺乏血肉。因为《莎维德丽》叙述结构的完整性正是由这三次说服活动及其说服效果的情节延伸部分来充分体现的。她的第一次说服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二章,其情节延伸部分主要体现在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前17颂。在这些章节里,父王转化为她爱的支持者,帮助她缔结了同萨谛梵的婚姻。然后通过叙述她婚后吃苦耐劳、孝敬公婆,对丈夫温存体贴,勤修苦行为夫消灾等一系列称职的贤妇之德,就使她当初所追求的美好的爱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补充。同时通过“只有莎维德丽一人/坐卧不安怀隐忧;/那罗陀仙人的言语/不分昼夜常在心头。 ”这颂诗向我们揭示了她欢乐生活背后的隐忧和焦虑。 她的第二次说服活动主要体现在第四章第18 —28颂,其情节延伸部分主要体现在第四章的第29—33 颂和第五章的前6颂。这次说服活动所表现出的“高尚的不一致”,通过去林中采野果的途中美好的自然风光、丈夫频频的妙语温存与她痛苦的心态形成的强烈反衬,被赋予了丰富的心理内涵。“她脸上仿佛带着笑容,/ 心中却怀着忧愁”便是这一品格很好的具象化和外象化。第三次说服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五章的第60—108颂和第六、七两章, 详细交代了五大心愿奇迹般的兑现情况。通过渲染萨谛梵死而复活后在林中怕父母晚上见不着自己,“忧急心焦痛苦深”哭天抢地的种种情态,和业已重见光明的父王与母后在森林湖沼到处寻找尚未归来的儿媳时“双足走僵已开裂,/ 伤痛处处血斑斑”的具体情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爱意的温馨世界,同时也印证了莎维德丽说服活动的道德价值。至于对主人公性格的补充主要突出了她的女人味和对夫君的柔情蜜意。
总之,离开成功的叙述,离开完整的叙事结构,不仅莎维德丽形象的成功将无从谈起,甚至古印度叙事文学中一切艺术形象的成功都将无从谈起。正因为古印度叙事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成功总是靠成功的叙述来体现的,这种成功就往往显得无意而非凡。所谓“形象的叙述性”指的也就是这种人物塑造对故事叙述过程不自觉的艺术伴随性或无意伴随性。莎维德丽形象成功的貌似神秘之处大抵不过如此。
三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不难发现,玛尔根德耶讲述的三次说服活动和它们各自说服效果的情节延伸并不与作品的运作结构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往往是相互包容,相互穿插,相互叠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是一次说服效果的情节延伸部分蔓延到了另一次说服活动集中所在的章节,有时是一次完整的说服活动及该次说服活动的情节延身部分共处同一章中,且又无明确的界限。这样三次说服活动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天衣无缝的内在结构形式。这种篇章结构上的艺术共体和联体现象,固然体现了作品艺术结构的严谨完整,更重要的是还体现了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原则。莎维德丽形象的成功及其“无意”与“奇迹”在叙述过程中的完美统一,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这种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因此我们说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也是莎维德丽形象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荣格把这种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归因于“自主情结”。在他看来,所谓“自主情结”指的是“一种维持在意识阈下,直到其能量负荷足够运载它越过并进入意识门槛的心理形式。它同意识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被意识觉察。它并不隶属于意识的控制之下,因而既不能被禁止,也不能自愿地再生产。这一情结的自主性表现为:它独立于自觉意志之外,按照本身固有的倾向显现或消逝”〔10〕。而“创作情结同别的自主情结一样,也具有这一特征”〔11〕。倘若剔除其形成“自主情结”来源的唯心主义成份,把其建立在先天因素(集体无意识)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坚实的基础之上,该理论对揭示文学创作的这一普遍规律,还是很能触及其实质的。按照荣格“自主情结”的创作理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旦开始在作家心目中孕育,它就有了一种自主的运动方式和方向,并有了它独特的内在运作逻辑,作家只有顺应其逻辑发展,听从自主情结的召唤,才能使其创作活动充满一种创造的活力。对自主情结的妥切干预虽然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但任何使其偏离自身运行轨道,违背其内在运作逻辑的粗暴干涉,势必造成创作活动的最大失败。根据荣格的说法,如果说孕育在艺术家心灵中的作品就是一种自主情结的话〔12〕,那么人物形象的自驱运动便是这“自主情结”的核心。由此看来,《莎维德丽》中体现的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就在于作者充分尊重了该形象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而他自己却根本没有意识到。三次说服活动之间在篇章结构上的艺术联体现象无疑也正是主人公自身运行逻辑独立运作的结果。而莎维德丽形象的成功自然也离不开作者对其自身运行逻辑的充分尊重。
这种充分尊重在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故事讲述人的创作意志同主人公意志不自觉的重合和混为一体。这时作者的意志暂由人物自身的运行意志统辖,不由自主地受主人公意志的引导,象影子一样紧紧地伴随,而他还自以为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讲自己的话。实际上他不过是在替人物代言。他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人物的话,是人物按照自身独特的运作逻辑必然要说的话。因此,人物直接对话颂数的多少和“玛尔根德耶说”这一非逻辑插入语出现频率的大小,便成为衡量莎维德丽形象塑造过程中作者的非自觉性程度和人物性格自我运行的自主因素所起作用大小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如果据此两点,把作品中出现的由“玛尔根德耶说”这一插入语所限定的有关部分排列组合,分为“人物直接对话为主”和“作者直接叙述为主”两大类进行探讨,我们就不难发现:凡是主人公的自主性原则和作者创作的非自觉性体现得较为充分的地方,均系作品的主干故事部分,同时也是人物对话较为集中的部分,也正是主人公主要性格特征得以充分体现的部分。凡是作者创作的自觉性原则和主人公的非自主性原则体现得较为充分的地方,均系作品情节的铺垫部分和三次说服活动的情节延伸部分,同时也是几乎没有人物对话或人物对话较少的部分,大多都是对其主要性格特征进行补充的部分。另外就篇幅而言, “以人物直接对话为主”类共有对话诗139颂,“以作者直接叙述为主”类共有叙述性的诗节79颂,其比例差不多为2∶1。就整个作品而言,共有对话诗175颂,“叙述性的诗节110颂,其比例为3∶2强一些。 据此我们说莎维德丽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得力于这种文学创作的非自觉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创作的非自觉性恰又体现了莎维德丽形象塑造的艺术独创性。因为它从根本上大大突破了古印度叙事文学传统的显在叙述原则,更多地依靠了人物直观。美国著名学者M.H.艾布拉姆斯说:“叙述体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大致分为‘展示’(showing)和‘讲述’(telling),两类不同的手法。在展示手法里又称‘戏剧性手法’, 作者只是客观地表现人物的言语、行为,而让读者去分析推论这些言行背后的动机和气质。在用讲述手法塑造人物时,作者搀杂了个人意志,经常对人物的动机和气质给以评价。”〔13〕如果依此作为我们的理论支持和评判标准,我们不难看出莎维德丽形象的艺术独创性就在于,叙述者在用古印度传统的讲述手法塑造人物时,却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展示性手法”或“戏剧性手法”(the dramatic method)的美学原则。 除前面提到的人物直观更多地代替了作者代现之外,还表现在:叙述者对人物内在的自我运作逻辑的充分尊重更多地代替了传统的讲述手法对人物自身内在发展逻辑的无端干涉。
四
莎维德丽形象塑造前后高度的一致性和美的完整性,是其成功的又一重要所在。这一点同样是由古印度“人物叙述论”的典型观所决定的。西方的“展示性人物”重在展示人物性格,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历程,必须完整、逼真,但不一定完美。而印度的“叙述性人物”带有很强的叙述性,一开始就把人物整个地介绍给读者或听众,先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人物不一定真实,非要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或相关,它不追求效果的逼真,但必须完美。《莎维德丽》第一章开头部分,当坚战王问及仙人玛尔根德耶,“见过或听说”还有没有象德罗波蒂这样一位“忠于丈夫,有德,有福”的女郎存在时,他便这样回答说:
坚战王啊!你且请听,
贤德妇人的品行福分,
如何这一切都归了
莎维德丽她一人。
同样也是先给人以完整的印象。然后随着三次说服活动的展开,主人公由远及近向我们款款而来。由于她高尚的道德品格、超凡的说服智慧、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三大叙述特征,在每次说服活动中都显示出一种整体运作方式,使人物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阶段性的完整。第一次说服活动已经基本上勾勒出莎维德丽的形象。但如果没有后两次说服活动尤其是第三次说服活动对第一次说服活动的整体延伸,没有主人公的心理复元,就无以实现其形象的完美。因而美的完整性一直是玛尔根德耶讲故事时刻意追求的美学目标。《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众多妇女形象的塑造,也都是以此为目的的。幸运的是莎维德丽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对其她妇女的形象塑造却部分地失败了。当悉多、黑公主、沙恭达罗、乔萨里雅、达摩衍蒂当初在作品中出现的时候,她们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完美无缺,艳天丽地。然而随着情节叙述的进一步展开,这样那样的道德缺陷和修养缺陷便接踵而至,一个微不足道的品行的斑点往往就把她们艺术上的完美性破坏殆尽。究其原因,我们尽可把造成人物形象前后矛盾的过错归罪于印度史诗讲唱文学口语叙述的随意性和对人物性格自身运作逻辑的不尊重或不够充分尊重。当悉多在林中无端疑忌并羞辱克尽职守的王子罗什曼那的时候;当黑公主挟私报仇,疯子般一再在般度五子中鼓动血腥战争的时候;当沙恭达罗对豆扇陀好言劝服不成,花容骤变,由于气急败坏而斯文扫地的时候;当乔萨厘雅一味忍气吞声,在十车王面前连起码的正当权益都不敢声张的时候;当达摩衍蒂在林中把那个对她充满情欲的救命恩人——一个倒霉的猎人诅咒而死的时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遗憾和美的幻灭。对此我们能否这样说,较之莎维德丽的形象,悉多失于疑忌,黑公主失于偏狭,沙恭达罗失于过分泼辣,乔萨里雅失于驯顺,达摩衍蒂失于冷酷武断。莎维德丽形象美的完整性不在于她形象结构运作过程中没有心理矛盾和感情挫折,而在于她成功地克服了这些心理局限,维护了形象的完整、统一及其前后的高度一致。具体而言就是她成功地经历并完成了由“一个正常的人”(天真无邪的少女时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以爱上萨谛梵到成为人妇后为夫君的命运怀隐忧时期),再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通过说服阎摩神放其夫重返人间,消除精神分裂症状,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平衡)的形象蜕变。金克木先生说,《摩诃婆罗多》中的理想妇女形象中,“能配上罗摩妻子悉多”(神之妻)而在现代还得到歌颂的只有莎维德丽(救夫)和达摩衍蒂(认夫)”〔14〕,可见莎维德丽形象之超凡魅力。不过这是就艺术形象的道德效果而言,如就其艺术的完美性而言,莎维德丽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有的论者会说莎维德丽也不完美,因为她因循守旧,宣扬了陈腐的道德观念,是一位旧思想的维护者。实际上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持类似的看法。〔15〕最容易引起人们分歧的恐怕莫过于第二章第25、26、27三颂诗了。当时大仙人那罗陀介绍完萨谛梵各种天神般的美德却只有一年寿限的情况之后,父王认为这一缺陷已超过他的所有美德,并要莎维德丽重做选择时,她却坚持了自己的抉择。为了充分表达她不可动摇的决心,她说:
“生命只有一次死亡,
嫁女儿也只有一次,
只能说出一次‘我给’,
这是只有一次的三件事。[25]
“不论他是长寿还是短命,
不论他是有德还是无能,
我只挑选一次夫君,
我决不再挑第二人。[26]
这里的第25颂与《摩奴法典》第九章第47颂相同,带有较强的原始
性。而第26颂却带有一种浓郁的封建主义说教色彩,似为后者所加。这与大史诗形成过程中较大的历史跨度具有密切的关系。就以现有的这两颂诗而论,是否就真象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她宣扬了陈腐的道德观念,是一个旧的正法思想的维护者呢?这里有一个前提不容忽视。那就是莎维德丽是在亲自聆听了连天神都敬重的大仙人那罗陀对青年王子萨谛梵各种美德的极力赞美之后,才坚持自己的选择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颂扬前提存在,莎维德丽依然信誓旦旦时,我们真相信她就是这样一个陈腐的婚姻观念的宣道者。假如萨谛梵不具备这些美好的品格,是个恶棍,寿限也只有一年,很难想象莎维德丽还会坚持自己的选择。她之所以要这样做,那是因为她从那罗陀的颂扬声中印证了自己的选择正确,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这里明显有一种少女的窃喜和得意。同时那罗陀对萨谛梵无与伦比的才貌德酣畅淋漓的无尽颂扬,也很难不令一个庆幸自己命运的少女动心。什么“光彩好似日神毗婆薮,/ 智慧仿佛神师祈祷主,/英勇如神中首长因陀罗,/度量如大地持财富”,其貌“象耶耶提王一样豪华,/象明月苏摩一样的丰姿,/象天上双马童一样的仪表,……”,其德诚实无欺,“胸怀无恶意”,“谦逊虚心”,温和又刚毅,“他的为人永远是正直,/他的德性永远是坚定”,不一而足。 象她这样美得没人敢要的青春少女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理想的夫君,自然舍不得轻易放弃。能同萨谛梵这样一位富于天神品格的美男子相爱一场也真正值得。为了捍卫自己爱的珍贵果实和爱的权利,不免要信誓旦旦。因此与其把信誓旦旦的这两颂诗看作是她对婚姻正法观念循规蹈矩的尊崇和礼赞,不如说是她为自己理想的爱情寻找到的恰切的社会观念庇护,而且还明显带有一种对这种陈腐的婚姻法则的温柔的戏弄。无怪乎其父要她丢弃理想的爱人重做选择时,莎维德丽便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个公共正法婚姻道德的武器,对自己业已证实的理想的爱进行果敢的捍卫。因为只有以公认的正法婚姻道德规范掩盖自己爱的果实,才能真正博得大仙人那罗陀的赞赏和认可,并从根本上说服父王。谁能说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自我保护呢?这里充分地表现了一个青春少女近乎狡猾的一种可爱的机智和调皮的智慧。如果以上论述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听听莎维德丽自己是怎么说的:
“先在心中有了决定,
再在口中用言语说明,
然后做事依此而行——
我的心就是这话的凭证。”[27]
可见她的爱情抉择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审慎的选择,决不是瞬间的心血来潮。是有意把正统而又带点迂腐气息的婚姻正法观念推向极端,作为其向周围包括父王在内企图扼杀自己美好爱情的人们施放的一团道德迷雾,决不是这种观念的真正信奉者和维护者。如果说第25、26两颂表现了她近乎狡猾的可爱的机智的话,那么第27颂戏剧式的独白就是她战略步骤最好的自我暴露。很显然,不能把这三颂诗作为她本人婚姻观念滞后,德行不完备的立论依据。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人物包括男女主人公在内很少有现实生活依据,大都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人物,并作为理想化的处世典范来称颂树立的,更注重的是主人公的社会伦理效果。一个艺术形象德行完备的程度往往是评判其成功与否的重要价值尺度。十三、十四世纪时印度有一位叫做维底亚那特的理论家在他的《婆罗多波楼陀罗名誉装饰》中还这样主张“作品的价值在于他所描绘的主人公的美德”〔16〕,足见该传统在古印度之根深蒂固。我们一再强调莎维德丽形象美的完整性即在于斯。我们说“莎维德丽印度妇女美德的化身”,正是这一形象的艺术独创性所显示出来的独特质地。
小结
总而言之,印度的“叙述性人物”本质上是类型化的,集中体现的是人物类本质的真实,具有一种很强的超时代性。西方的“展示性人物”本质上是典型化的,集中体现的是人物个体本质的真实,往往带有一种浓郁的时代色彩。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典型观是不能相互代替的。我们之所以讲,“形象的叙述性”、“创作的非自觉性”和“美的完整性”不仅是莎维德丽形象成功的奥妙所在,也是这一形象的艺术独创性所在,那是因为除“创作的非自觉性”所带来的更多的人物直现对传统的显在叙述手法的重要突破之外,还在于这一成功的艺术形象遵从“形象的叙述性”、“美的完整性”这一印度“叙述性人物”在艺术上的独特要求,在古印度众多理想妇女形象的塑造中达到了某种高不可及的范本的高度。
注释:
〔1〕《摩诃婆罗多》著名文学插话之一, 莎维德丽系该作品之主人公。
〔2〕同为《摩诃婆罗多》著名的文学插话。 又一译名为《那罗与达摩衍蒂》。
〔3〕〔4〕见季羡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金克木撰“摩诃婆罗多”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93、91页。
〔5〕摩神答应莎维德丽:a.复明其公公盲国王耀军的双眼。b.恢复耀军的王国。c.同意其父王生一百子。d.她个人亲生一百子。e.放回萨谛梵的灵魂。
〔6〕见金克木译:《莎维德丽》, 载金克木编选:《〈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北京,1005 —1006页。以下凡作品引文,均据此书,不再注出。
〔7〕〔16〕转引自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43、249页。
〔8〕见金克木:《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译本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北京,19页。
〔9〕所谓“叙述环境中的叙述性格”, 主要就古印度人物塑造离现实生活较远,且较强的想象性和理想化特征而言。所谓“叙述环境”指的就是富于想象性的理想化环境,所谓“叙述性格”指的就是富于想象性的理想化性格。如把其概括为“理想环境中的理想性格”也许更妥切些。
〔10〕〔11〕〔12〕见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117—118,118,117页。
〔13〕见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37页。
〔14〕金克木:《旧学新知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64页。
〔15〕同〔3〕,93页。这里金克木先生认为, 《莎维德丽》宣扬了陈腐的道德观念。就作品而言,除第二章第25、26、27三颂诗之外,找不出别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