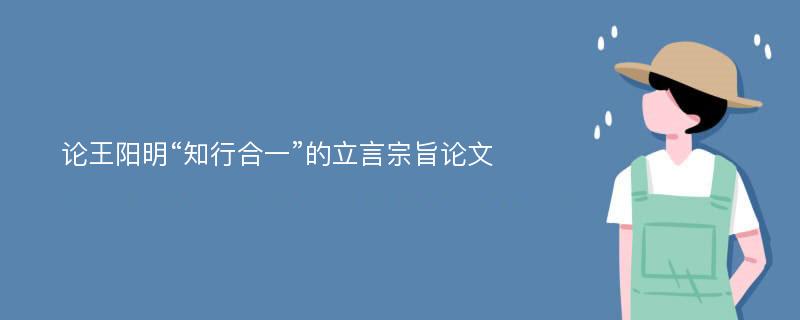
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
周海春, 韩晓龙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430062)
[摘 要] 王阳明虽然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他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本体-遮蔽-去蔽。“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都是用这一思维模式来表达。在整合不同概念的基础上,这些不同的表达集中为“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具有同构性,其理论的聚焦点都在于解决良知良能由体达用的障碍问题。从“致良知”来把握“知行合一”既是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本来面貌的需要,也是顺着王阳明的理论思路补充完善“知行合一”学说的需要。就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而言,“致良知”的“致”突出了克倒不善的念头的重要性,更明确了“知行合一”的宗旨。就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实质而言,只有一个知行合一,即良知的知行合一,舍弃良知就无法洞见“知行合一”的实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一个发展过程,“致良知”使“知行合一”更为完备,“知行合一”的多种论述都是良知圆成自身成为至善的逻辑环节。
[关键词] 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至善
一、引言
“知行合一”在王阳明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知行合一之说,是先生论学最要紧处”[1]233。但“知行合一”自提出,就一直是一个争执很大的命题。本文认为,需要结合王阳明思想的宏观框架来把握“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哲学虽然有变化,但自龙场顿悟以后其思维模式是一贯的。王阳明的哲学概念框架主要来自《大学》和《孟子》,王阳明同时把“天理”、“穷理”等概念置入对《大学》和《孟子》的理解之中。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也来源于《孟子》和《大学》的整合,他是把《大学》的“致知”、“格物”概念嫁接到《孟子》上去了① 耿宁重视王阳明良知概念对孟子良知概念的继承(参见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林月惠则认为耿宁讨论阳明的良知概念,重《孟子》而轻《大学》,脱离了阳明良知说的问题意识。“换言之,从《传习录》卷上到卷下,‘良知’(致良知)概念的讨论,是与《大学》古本、朱子改本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的理解相关,而‘知行合一’的议题也有所涉及。因此,探究阳明的良知概念,不能忽视他与朱子《大学》‘格物致知’的思想搏斗与对话。也许我们可以如此说,阳明的‘良知’概念虽于《孟子》有所本,但从《大学》‘致知’来立说,‘致知’即是‘致良知’。从某个意义上说,阳明是以《大学》‘致知’之‘知’来诠释《孟子》的‘良知’。因此论及良知概念的含义,显然不能忽略《大学》之讨论脉络”(参见林月惠《阳明与阳明后学的“良知”概念——从耿宁〈论王阳明“良知”概念的演变及其双义性〉谈起》,《哲学分析》2014 年第4 期)。 。
王阳明如何整合了《大学》和《孟子》呢?最为关键的是三点:第一,赋予致知之“知”以良知的含义。在《徐爱录》中,王阳明把孟子的良知表述成“见父自然知孝”一类的表达,并强调这个良知是会受到“私意”障碍的,所以才需要格物、致知之功,当去掉障碍后就是“致其知”,就是“意诚”。
第二,王阳明在把孟子的良知概念输入到《大学》中的同时,也输入了一个思想的话题,即回答了为什么要“正心”,为什么要“修道”和“率性”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私意障碍。这个问题在孟子那里是放其良心的问题,是从“小体”的问题。耿宁认为:“在关于‘本原知识’由于自私欲望而受到阻碍以及通过‘对行为的纠正’来消除这个阻碍的思想中,王阳明已经超出了孟子。”[2]189的确如此,因为王阳明在向《大学》中输入“良知”概念的同时已经把理论关注焦点定位是在什么阻碍了明德以及如何明明德这一问题上了。在《中庸》中,“自诚明”和“自明诚”中的“明”是一个明,一个“明”分为天道和人道。人道使用的“明”是被障碍和遮蔽后透出的“明”,这个“明”和“明”的本体是一个,但也不是一个。这个问题的聚焦使得王阳明的学说有着强烈的功夫论和工夫论的取向① 王阳明既用“功夫”,也用“工夫”,前者有本体自身做功的意味,后者凸显的是人做工夫,本文同时使用两种说法。 。
第三,对至善的遮蔽问题的聚焦使得王阳明有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模式:本体因为障碍所以不能很好地体现在功用上,去掉障碍,本体就显现为功用。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本体-遮蔽-去蔽。只不过王阳明是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这一思维模式的。用“心即理”来说就是心没有私欲之蔽,即是天理。用“知行合一”来说就是没有私欲隔断,即是知行本体。用《大学》的概念来说,去心的不正就是格物,没有了私意障碍,心的良知就流行了,自然就是“致知”,意也就诚了,也就复了天理。
文化内部的主要要素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道德文化价值的基本构成主要反映在道德与文化内部上述诸要素的关系上。
从王阳明的理论诉求来看,“真知行”既包括何谓真知、何谓真行的问题,也包括知行关系的问题。致良知本身就是真知行。王阳明对“真知行”的回答不是一次完成的,与“知”相关的说法有“知寒”、“知饥”、“闻恶臭”、“知得父当孝”、“知天的知”、“良知”、“明觉精察”、“口耳谈说”、“知识”、“知觉”、“自知”、“自私用智”等;与“行”相关的有“行孝行弟”、“冥行”、“真切笃实”、“好好色”、“自饥”、“着实去做这件事”、“致”、“循”等。其中的关键是区分出何谓真。“良知”比“知”完善,就在于“良”字更能表示出“好”的意思。“致”比“行”更不容易引起误解,就在于“致”更有利于表达克服障碍的意思。恶念也是知行合一的,所以才有克服的必要。就善恶的区分而言,“致良知”优于“知行合一”。王阳明已经从“致良知”的角度对“知行合一”进行了一定的新的阐释,但并没有足够的机缘对先前“知行合一”论述中的欲发而未发之意一一进行说明。从“致良知”来把握“知行合一”的相关论述既是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本来面貌的需要,也是顺着王阳明的理论思路补充完善“知行合一”学说的需要。
王阳明的“良知”来源于《孟子》,但并不是直接取自《孟子》。耿宁认为,在1520 年前,王阳明使用的良知概念本质上并未超出孟子,还是从孩童知道爱亲和敬兄来说的[2]188。但王阳明更强调见父知孝,见兄知悌。后来王阳明强调了良知对善念和恶念发动的“知”,进而发展为强调知是知非。耿宁把区分善恶的良知概念说成第三个良知概念,并认为这个概念超出了孟子。在《孟子》中,智和智之端是和是非之心关联在一起的,不放弃良心被看成是“智”。对于王阳明的哲学来说,“知行合一”带有理论的预设性。天理、明德如无阻碍就会实现出来,这本身预设知行合一。当天理等概念被换成了良知概念以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间就获得高度的理论一贯性。
王阳明的天理、性、心、知、意、物的概念系统从“心”到“意”再到“物”,有比较明显的内外、主客的分别,而通过把身、心、意、物看成是一件消融了内外的分别。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指出,如果领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1]46~47,那么对知行并进之说就没有疑问了。有内外是认良知未真,当认良知为真的时候就会内外两忘、心事合一。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王阳明强调了理、性和学都是无内外的。王阳明延续了二程的看法,把“有内”说成是与有我、自私有关,把“有外”说成是与“用智”有关。抛开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具体论述不谈,仅就理论路向来说,要保证无内外,就必须赋予理、性、心、知、意、物之间具有一种“行”的关系。而最恰当地突显提出“知行合一”必要性的地方在于这种“行”遇到障碍的地方。找到这个“行”的障碍的关节点,就是提出“知行合一”最恰当的逻辑节点。显然,这个关节点就是“意”。在这里有了私意的发生,“意”“逐物”让“心”失去主宰,从而使得“行”有了不同的方向。“知行合一”的提出,一方面可以显示知行本体,另一个方面也为补偏救弊。
从“本体”和“功夫”范畴来看,“知”、“行”两个字主要是说功夫的。王阳明在指点“四句教”的时候,区分了两种功夫:利根的人一悟本体就是功夫,本体有蔽的人要在意念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本体功夫对应的是本体自身的知行合一,意念上为善去恶的功夫对应的是本体受蔽时如何去促成本体的知行合一。基于以上,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就聚焦在指点“真知行”上面来了。建立在自私、用智基础上的知行学说显然就不是“真知行”① 蒋国保《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思辨逻辑》(《江淮论坛》1998 年第3 期)一文即从“真知行”入手来讨论知行合一。《徐爱录》中记载王阳明说:“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第4 页。) 。
王阳明虽然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基本思维模式一致,这就产生了整合的必要性。在《徐爱录》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整合的趋势,王阳明把《大学》的“明德”说成是“天理”,把“明明德”说成是“穷理”,把宋以来理学家的“天理”、“穷理”概念和《大学》连接起来。明明德到精一处就是至善,就是心的本体。这样就把“天理”和“明德”说成是心的本体,并直接讲“心即理”。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看成是明明德之功。王阳明完成概念整合的关键理论环节是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引发出来的。在《答顾东桥书》中能够看到进一步的这种概念整合,王阳明把“知天”理解为是自己分上的事,与天为一,如果结合《徐爱录》中对“知行合一”的论述来看,“知”范畴已经开始向明德、天理的逻辑地位靠拢。在王阳明哲学中,性是就理的凝聚处而言的,心是就身的主宰或理凝聚之主宰而言的,意是就心之所发或主宰之发动而言的,知是就发动之明觉或意之灵明处而言的,身是就心的充塞处而言的,物是就意之所在而言的。在这一概念结构中,“知”或“良知”可以等同于天理、明德,也可以从意动时的明觉这一逻辑地位上来理解。因为“知”或“良知”本来就是理的灵处,这个灵不被遮隔,自然就完全是本体了,天理本身就可以表述为良知。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明确把“天理”说成是“良知”,这样致知就成了把天理落实到事物上,致知也就是格物。良知在就意之动的明觉来说的时候,就要先讲意,再讲“良知”;从意的本体来说的时候,可以先讲“良知”,后讲意。“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1]53,这里就是用心的虚灵明觉的良知感应而动来说意的。《答顾东桥书》中把天理、格物、致知、诚意等概念整合进“良知”和“致”以后,“致良知”就可以兼容早期的思想表达,而成为一个相对完善的表达方式。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一种整体逻辑设定,如果没有“知行合一”的逻辑设定,心就无法是理,良知就不是良能,也就无法贯彻无内外的理论原则。不应把“知行合一”和“心即理”、“致良知”平列起来看,而应从整体的逻辑原则的角度来看“知行合一”。“本体-遮蔽-去蔽”模式中的“本体”是“明德”、“天理”和“良知”,当遮蔽去掉以后,至善就完成了自身,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一个至善圆成自身的过程。只有把“知行合一”中的“知”领会为“良知”,“知行合一”的道德意义才能有效地彰显。
为了拓展活动空间,我们对幼儿园的环境、班级楼层设置进行了反复的调整,例如:加盖二楼和三楼露台的风雨棚、拆除大操场的舞台、移动大型玩具的位置、构建共享区等等,都是为了让孩子有较大的活动场地。同时我们注重每一个小角落的利用,在绿色长廊下面和操场、教室的四周、楼梯间,都有为方便孩子活动而投放的器材,即使在槐苑的树下都埋有梅花桩。
二、“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阳明学说的核心讲法。相比于“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致良知”在理论和实践上最为完善,“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1]119,“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1]106“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具有同构性,共享同一个逻辑结构,即由“知”(心)到“事事物物”。“‘致吾心之良知’,‘致’是由主体所自主发出的行为,是主体本然实在之良知(‘知’)经由其‘致’的自主行为(‘行’)而获得充分显扬的过程,是为‘知’的表达;‘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致’(‘行’)所实现出来的现实结果,是为‘知’的实现或完成;‘皆得其理’的事事物物,同时也是‘知行合一’所实现出来的事物现存状态,它显然是充分体现了‘知’、‘行’之共相统一的”[3]。这一论述已经把“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放在一个思想结构中来考察。良知就是从天理的“灵明”和“明觉”处来说的,认良知真了,良知就是天理。心是就理的主宰处来说的,心的主宰性体现出来了,理就在心上,心就是理。心的主宰是对应意念之动来说的,心有意念的发动,主宰性才显现出来,但是心的主宰性不表示心本身能纠正意念偏离方向。纠正意念偏离方向的是良知明觉,良知明觉保证人可以按照善念去行动,从而所作所为都符合天理,对具体事物的理的把握也没有在心之外,也可以说心即是理。没有“知行合一”,“心即理”就无法变成现实,也就不能称之为“致良知”。“知行合一”对于“致良知”和“心即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理论环节。
此类试题,适合作为选择题的命题形式,通过解决复杂或有难度的问题,内容上综合考查核心概念,要求学生理解科学的本质;方法上要求学生熟练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将知识迁移后解题;品质上主要考查学生思维品质的深刻性,综合体现考试选拔各水平人才的性质。
回去的路上,楚墨伤心不已。现在,那个县城里跑得最快的小伙子,只能够长年累月地坐在轮椅上,靠玩魔方赢得一点所谓的尊严。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之体”、“知行体段”到底指称什么呢?在王阳明的语境中,“知行合一之体”是从致知的角度来说的,其中包括意念发动时候的知行合一(不分善念、恶念),克服不善之念,善念得以实现。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说:“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1]56致知之知行合一既是本体又是功夫,总体来说是功夫,但有深浅难易的差别。生知安行的,良知精精明明的,自然会依照良知落实下去;学知利行的,需要时时省觉,努力落实良知;困知勉行的,良知禁锢较深,私欲阻止了良知落实,需要更大的努力。
针对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由氰化物泄漏所引起的地表水及可能的地下水污染问题,某一小组在2016年下半学期实验研究了水中氰化物的快速高效降解技术。学生们采用不同的氧化技术,并与生物处理技术相结合,测定进、出水中氰化物的浓度,比较各工艺技术的处理效果,推荐最佳技术。
从“知行合一”提出的时间点来看,“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形成于同一时期。《年谱》记载,在1508年,也就是正德三年春,王阳明悟格物致知,即龙场悟道① 董平认为,“心即理”是“龙场悟道”的实质内容(参见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 。王阳明还用“五经”来证明自己的体悟。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书院的时候不回答朱陆异同问题,而是讲“知行合一”,并用“五经”指点知行本体。根据《年谱》的描述,王阳明使用的应该是摘抄本的“五经”。显然,“知行合一”应该是王阳明在学习默记“五经”的时候已经孕育了② 默记“五经”和《五经臆说》作于何时,尚需详细考证。根据《年谱》的描述,用默记“五经”来证明顿悟发生在1508 年,《五经臆说》的创作也在1508 年;王阳明自述时也曾提及龙场顿悟后“在更寒暑”用“五经”来证明了自己的体会。 。在《徐爱录》中,先讲“亲民”,然后讲“心即理”,接着讲“知行合一”③ 徐爱所录谈话的时间点在1512 年到1513 年,这些语录记载了王阳明在龙场的思想发现。 。结合《答顾东桥书》来看,王阳明说“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应该是有来由的。王阳明在龙场顿悟的时候,曾经用“五经”来证明自己的悟解,并且因此还写了《五经臆说》。《五经臆说》是否直接表达过“知行合一”不得而知,不过从现存十三条中还是能够窥见一点端倪。王阳明说:“日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大明。有时而不明者,入于地则不明矣。心之体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有时而不明者,蔽于私也。去其私,无不明矣。”[1]1079这应该是王阳明思想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认识。明德也就是天理、良知,恶念就像云,去恶念,日光就照出来了。“去其私”就能“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了。“致”和“知行合一”既能指点出“照心”,也能指点出“妄心”。从不曾被遮蔽处说,良知像太阳一样无照无不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本体;从被遮蔽处来说,遮蔽之“妄心”也有“照心”在,妄念、私意也是知行合一的,这是“知行合一”的本来体段;从去蔽来说,去蔽本身是良知之行,可以说成是“知行合一”之体本来如此。应该说,王阳明在龙场顿悟时已经奠定了自己基本的思维模式④ 确定体悟到“良知”和“良知”提出的时间点对本文也有一定的影响,目前有正德三年(1508)、正德十四年(1519)、正德十六年(1521)等不同说法。本文认为“大悟‘良知’之旨”和“始揭‘致良知’之教”不能混淆,从体悟良知,到使用良知概念,再到提出较为系统的良知学说是一个过程,不能因为使用良知概念出现得晚,就认为体会到良知境界也一定是晚的。 。
要比较好地回答“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论关系,需要明确三点:其一,不能把王阳明的良知预设为静态的知识,而应理解为不动不静、从不止息的;其二,善念的发动和恶念的发动都是行,背后都有本体,这样才能讲清楚“知行合一”;其三,宗旨是要重视恶念的发动并克服恶念。为了说明这三点,需要对王阳明“良知”与孟子“良知”的关系略作说明② 关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理论来源,尚需更为详细的专文论证。“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从这段话来看,“智之实”已经包含了仁义实现出来的含义在内。耿宁把王阳明直接继承孟子的良知概念翻译成“本原能力”,这个翻译突出了良知本身的“行”的色彩(参见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 年版,第187 页)。把良知看成是静态的知识并用来把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会遇到较多的逻辑矛盾。 。在《孟子·尽心上》中,“良知”和“良能”是分开讲的,王阳明讲的“良知”已经包含了“良能”的意思在内。“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1]124欧阳德对此有过说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和功夫要了解“举良知,则良能固在其中”,“举良能,则良知亦在其中”[4]153。
从理论上说,如何处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一个难题⑤ 陈来先生认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侧重点不同,王阳明晚年的思想中区分了“良知”和“致良知”,也就是区别了“知”和“行”,知行之间不再有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意义,而“知行合一”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即是行、行即是知。陈来先生的这一分析把“知”对应“良知”,“致良知”对应“行”来进行讨论(参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103 页)。董平先生认为“致良知”所强调的仍然是“知行合一”,在这一意思上,“致良知”也可以被认为是“知行合一”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知识”发展为“良知”,“行”发展为“致”后更为侧重于由内在本心而向外推展的实践过程(参见董平《“知行合一”的思想巨擘》,《浙江日报》2016 年12 月26 日第011 版)。 。本文认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姚江学案》中把王阳明的“致”解释成“行”,以及《明儒学案》所记载的刘宗周把“良知”说成“知”,把“致良知”说成“行”是一种简化的说法。“致良知”不等同于“行”,而是包括“良知”和“致”,也就是“知”和“行”两个方面。“良知”本身就是“知至”,“致知”不过是去掉妨碍“知至”的恶意之动,也就是“至之”。“致”本身就是良知的一个逻辑环节。只有这样,“致”才能成为一种本体功夫。王阳明在解释“知之非艰”时,从字面上看,“良知”对应“知易”,“致良知”对应“行难”,实际上王阳明不过是强调应对良知被障碍需要有一个“致”的功夫。人人都有良知,不能说无知,良知本身就是“知至”的,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容易的。说良知容易不是说良知是静态的,良知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没有私欲间断的心是不息的,不息就是说“行”。“知及之”已经是行了。难题是不能常行,所以才有一个“致”[1]137。
“致良知”的“致”字要结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来看。“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1]109~110这里提到“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提到“分作两件”,提到“将这不善的念克倒”,这三个观念中哪个更能体现“立言宗旨”?本文认为是“将这不善的念克倒”,“致良知”的“致”就强调这个克倒的重要性① 陈来先生反对把“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看成是宗旨,认为对于朱学知先行后说的批判意义是宗旨。他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只适用于“去恶”,不适用于“为善”(参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98—99 页)。 。
诺贝丰产品技术总监宋涛在分享中表示,依托于以色列先进技术,诺贝丰现已推出水溶肥、液体肥、叶面肥等“深海能”系列水溶性肥料产品,其中含有的海藻提取物具有良好的抗逆和生长调节能力功效,在全面补充营养的同时有效提升了作物和农产品品质。通过现场试验,“深海能”系列产品的营养均衡、中和酸碱等功效得到了与会果农的一致认可。
王阳明曾经在自述其学术思想的时候指出,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良知”的意思,只是没有明确点出这两个字。钱德洪说王阳明1508 年到1509 年就没有离开“良知”两个字的意义,从而浪费了很多辞说,良知两个字能够洞见全体。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说:“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1]1559 甲戌年为1514 年。1524 年到1526 年间,是王阳明论述“知行合一”学说比较集中的时间。嘉靖三年(1524),《书朱守谐卷》中把“知行合一”直接和“致知”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同年,王阳明给妻侄诸阳伯的教诲中也论及“知行合一”。在《书诸阳伯卷》中,王阳明依次论述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答顾东桥书》集中论述了“知行合一”,时间点为嘉靖四年(1525)九月。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曾写过一篇《答友人问》,强调心体是知行合一的,“知行合一”是知行体段本来如此。由此可以看出,1524年到1526 年间,“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三个命题之间在一个新的理论层次上得到了某种一致性的论述。1524 到1526 年间王阳明论述“知行合一”的本体就是良知,这使得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论述最终形态为“致良知”语境下的“知行合一”。
《孟子》思想中的“思”、“求”、“忘”、“助”既涉及到内外,也涉及“四端”如何“达之于天下”的问题。《中庸》讲“自明诚”是人之道。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人积极心灵状态“放失”的根源在哪里?人克服消极心灵方向的能力来自于哪里?孟子归结为自身,或自暴自弃,或“求则得之”。如果本体是有息的,恶念也就没有生起的缘由;如果本体是有息的,善念更无从得以成立。这是本体功夫论的难题。关键就在于哪个更能得着本体,显然王阳明认为是后者。功夫里面都是有本体的,但有直接来自于本体的,有间接得着本体的,用本体做功夫就有很多的细节。这一点也是常常令弟子困惑的问题。“致良知”不是谋力所不及,不是强知所不能,乃是本体自身的功夫。良知即是良能,但是有“不肯知”,有“信不及”,有“不能”,有私欲。确定“行”和“致”在王阳明思想中的逻辑地位至关重要,“行”和“致”的使用是和知行被隔断联系在一起的。私欲隔断了知行合一,“自私”和“用智”使人陷入内外之别的境遇中,但良知本身的动能不会因此消失,依然有行的动能,这种动能表现为一念发动时的良知明觉,这是本体自身的功夫,人依着本体的功夫去做功夫,知行就合一了③ “知行合一”有不同层次论要求,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知道自己有良知,信得良知的真是真非,这样就去掉了“知行合一”的一道障碍。 。
“行”和“致”包含不同层次的问题,包括良知本身预设的良能,善念和恶念的“行”,包括为善去恶的“行”,包括落实到行为中的“行”,总体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面貌。
三、“知行合一”:本体和功夫的区分
把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即知行合一的不同层面的问题,如知觉、感知、知识、良知等层面的知行合一。但是就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神实质而言,只有一个知行合一,即良知的知行合一,舍弃良知就无法洞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质。知觉、感知、知识都必须成为良知的发用的时候,才能达到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功夫,但是这个功夫离不开良知良能的本体。在《答陆原静书(二)》中,王阳明就直接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1]78“知行本体”是讲知行背后的本体,即良知良能。知行合一其实就是良知自己知、自己行,可以不用讲知行合一,如“本来体用”;也可以讲成是知行合一,如“生知安行”,即良知本体的知行合一。“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1]66。这一意义上的“知行本体”并不是指知与行的本然关系① 丁为祥反对把“知行本体”理解为与功夫相对的本体(参见丁为祥《王阳明“知行合一”三指》,《人文杂志》1993 年第3 期)。从“本体”和“功夫”把握“知行合一”不会割裂二者的关系,“知行合一”具有从功夫上指点出良知本体的功效。 。王阳明曾经“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1]1355。这里提到的“知行本体”应该已经包含“心之体本无不明”的意思,已经开始直面知行本体了,不过那个时候“知”虽然有“良知”的意思,但是“良知”两个字还没有被直接点出来,在“良知”两个字被指点出来以后,讲知行合一就是直接以良知为本体的。
“知行合一”是有条件的,前提是“真知”。“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1]211。良知有着落对于“知行合一”非常关键。“致良知”的实功,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见良知见得真;一个是“致”。在《与陈惟濬》中,王阳明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近时同志亦已无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能于此实用功者绝少,皆缘见得良知未真,又将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处。”[1]247知行合一的前提是见得良知真,然后是良知决而行之,“致其知为善之知”于事事物物。不能把“良知”和“致”简单地归结为“知”和“行”。良知不是静态的,本身已经包含了良能。“致”是良能实现的环节,大略包含三个理论层面:本体的良能;一念发动处有不善,把不善的念头克掉;正念得以行,从而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只有良知有着落,本体才能不受限制地发挥功用,从而做本体功夫,“致”字也就有着落了。“知至”,良知即良能,为知行的本体;“致知”的知行合一是功夫的知行合一。“知”字是本体,“致”字是功夫,本体不离功夫,功夫不离本体,知行合一就是本体功夫。
良知像水之就下,本身可以讲成是知行合一,但其实不必讲,只要在“致知”的角度讲知行合一就可以了,这个层面讲知行合一就是功夫论的知行合一。在《答友人问》中,王阳明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1]233这里说的“工夫”是什么功夫呢?就是彻上彻下的功夫,本体功夫。为什么要两个字说一个功夫呢?就是因为良知本身即良能,这个能处就是功夫;“能”的显现恰好在“不能”处,所以必须讲个“行”和“致”才行。在《答友人问》中,王阳明紧接着指出,如果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即便把知行分作两个说,做得还是一个功夫,始终都能融会。如果头脑处见得不分明,看作两个了,即便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也只是生硬的结合,如果再分作两截去做,那么从头到尾就都没有下落处了。“原是一个头脑”是什么头脑呢?显然就是良知本身。见得良知为真,做功夫就是做一个功夫,但在理论上可以分成知和行两个来说。相反,如果把良知仅仅看成是知,或者把良知分成知行两截去做,那么知行功夫就不能落实了。
埋藏深度1152.90~1597.50 m,厚度444.60 m。该地层据测井解释成果反映,共有47层砂岩,砂岩总厚度为101.60 m,砂厚比为22.84%。砂岩孔隙度22.96%~47.38%,渗透率18.02~1444.70 md;热储层顶板井温为58.11℃,底板温度为66.06℃。
“知行合一”是本体功夫的要求。“知犹水也,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此吾所谓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1]308。决而行之就像水之就下,良知恒照,无有不照,然毕竟有妄心,需要去妄存真。“决而行之者”应该从“勿忘”、“勿助长”的意义上来理解。良知就像水之无不就下,决而行之就像“致知”,合起来就是知行合一。“道一而已”,说明“心外无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其实都是一贯之道。
现有成果已经肯定了“知行合一”是“心即理”的理论展开② 董平认为,“心即理”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知行合一”为“心即理”在理论上的一种展开形式,是“心即理”作为一种“知”在行动上的实现方式(参见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 。关于“知行合一”和“心即理”的关系,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已经从两个方向作了较为充分的说明。一个方向是说明求本心不会遗物理。如果心“遗”了物理,那么这个遗物理的心一定不是本心,换句话说,心和物理如果成了对立的两面,这个心就不是本心。由此自然要说明另外一个方向,即心背后的本体,这个本体体现出来的心才是本心,心的本体就是“性”和“理”。“知行合一”就成了“心即理”得以成立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要件。从《答顾东桥书》中的论述来看,“知行合一”回答了“心即理”何以成立、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回应了专门求心会忽略物理的疑问。在进行了上述论证之后,王阳明直接说:“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1]48从这个论述来看,“心即理”被看成是“知行合一”思想传统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致知会遇到各种具体的情况,因而可以有很多层面的知行合一,就不同大用层面的知行合一来说,虽然各有层次的不同,但是都是良知发用和致良知的本体功夫的表现,因而可以说是“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凡古人说知行,皆是就一个工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1]232。“知行体段”是着眼于本体功夫来说的。在《答陆原静书(二)》中,王阳明指出佛教常存本来面目,“体段功夫大略相似”[1]75。“体段功夫”就是认得良知明白,随物而格,致知之功。随物而格的体段功夫要求通过知行合一的补偏救弊说逐步揭示了本体的知行合一。
四、“知行合一”的诸种功夫与至善的圆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多种论述,这些论述可以看成是“致良知”的理论环节。不同的理论环节从整体上构成了至善的图景。
第一,行为中包含着知行合一。“知至”才是良知,“至”的终点是善的行为,至善的行为是良知的自我完成。至善的行为不同于“冥行”,“冥行”中也有知行合一的体段,不过其中的“知”是“妄心”、“私意”,良知是被遮蔽的。应当性的道德知识使良知到此止步,而“不行”。“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1]4道德行为中的“知”是已经“致良知”的知。“空然知之为如何温凊奉养”是“知”,不是“致知”。“必实致其温凊之功”,“知始至”,这个才是“致知”[1]309。王阳明并不否定“当如何为”的知识,但这一知识需要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上,这样才具有行动的动力。“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1]55。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当如何为”的知识是真诚的,这保证了足够的行动力。“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1]55。诚意意味着良知的明觉,必“为之”“无一毫之不尽”,这样才称得上是“无自欺”。
对2018年8月某日某大型公立医院能耗监控系统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可在能耗监控系统中查询到医院实时电、水等能源当天的用能情况,用能趋势、同比和环比情况。当天,电耗为主要能耗,其中空调用电占34.2%,照明与插座用电占31.4%,动力用电占25.1%,特殊用电(重点医疗设备)占8.2%,其他用电占1%。根据医院建筑面积、床位数,得到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为0.02千克标准煤/m2,单位床位能耗为1.3千克标准煤/床。医院实时能耗和能耗分类统计如图1和图2所示。可查看按楼宇划分的能耗排名和按科室划分的能耗排名情况,如图3所示。
至善的行为表现在外的样子就是“著实去做这件事”。把事做实需要精神的专注,需要学问思辨如何做这件事。不管是道德知识,还是学问思辨,抑或是明觉精察,离开了良知的发用,都是良知的遮蔽,知行合一是很难脱离良知而孤立存在的。作为良知完成自身的行为,其至善的属性来自于良知这一前提。然后是良知发用的正念以及对恶念的明觉,这一环节保证了“意”是“诚”的,保证了“心”是“正”的。在良知、正心、诚意的基础上,良知发用的感觉和知觉更为敏锐,良知发用的思考是精思,良知发用的道德知识不会停留在“应当”的阶段,一定会变成行为。在行为的时候才有真知,在王阳明这里并不是说,知识来源于行为,而是说行的时候,良知明觉观照行,从而获得相应的知识,“知”和“行”是同时在场的,是知行合一的。
第二,知性能力和欲求能力合一,认识性的知觉和道德知觉合一。王阳明在回答徐爱关于“知行合一”的疑问的时候,讲了一段话:“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1]4这里的“见”、“闻”属于感性认识,在康德那里属于知性能力;“好好色”、“恶恶臭”涉及善恶问题,在康德那里属于欲求能力。“见”不是静态的,而是有“好”行的势能在其中。“见”本身就“好”,“见”的善恶分别就很重要了。“见”和“好”都属于意念之动,王阳明在这里只是指点出意念发动本身是知行合一的,结合“致良知”来看,还要克服不善之念的发动。意念之动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欲求活动,一个是知性活动,二者统一于意念之中。“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1]80。“见”和“好”互相规定,从良知而来的“好”是高级欲求,从良知而来的“见”更能发现善,从而成为善行的动因。好善和见善相得益彰,从而成为良知实现自身的环节。
流道式污水换热器具有如下特点:流道式换热器污水侧通道呈宽大的矩形结构,流道式换热器污水侧通道表面平整,无任何凸起物或支撑点,原生污水工况下无须前置防堵、过滤设备,污水中常见的污杂物能顺畅地通过,不会造成钩挂与缠绕。
第三,生理活动和知觉活动的合一,身心合一。王阳明指点徐爱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1]4自饥是行,知饥是知,知行是合一的。知寒、知冷都是感觉和知觉的范畴,自饥是身体的功能。在王阳明那里,身心合一是有理论基础的。“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1]103。心是主于身的,但是没有身,心也不能有感觉和知觉。身体产生的感觉,为心灵所捕捉,变成意之动,从而有视、听、言、动等感觉或者行为,同时发生的是良知明觉观照身体和意之动,从而保证了身心合一。良知的灵明之知对身心合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良知的明觉同时观照身体及其感觉使得身心保持同步,这也是良知的功夫。低级欲求涉及身体的需要,“知觉”依凭于身体而发生,道德知觉的发生也依赖身体知觉的敏锐性。良知发用的知觉是敏锐的,能够对他人的感觉感同身受,道德的发展也表现为知觉的敏锐性和随之而来的道德判断、道德行为。良知的本体功夫保证了二者的有机合一。
第四,明觉精察和真切笃实的合一。“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1]232。“良知”的关键在“明觉”,“致”的关键在“实”。良知良能一体,二者表现出来就是“明觉精察”和“真切笃实”的合一。在具体的知觉或知识活动中,心如果做到了“真切笃实”,“明觉精察”就在其中了;在行为过程中,心如果做到了“明觉精察”,“真切笃实”就在其中了。“若知时,其心不能真切笃实,则其知便不能明觉精察;不是知之时只要明觉精察,更不要真切笃实也。行之时,其心不能明觉精察,则其行便不能真切笃实;不是行之时只要真切笃实,更不要明觉精察也。知天地化育,心体原来如此”[1]234。王阳明在这里讲的“知时”和“行之时”是就用上来说的。用上的知行即知觉和行为,知觉中要良知先行了,所以要求心灵的真切笃实;“行”中则要求有良知明觉指引。可以从“本来体段”来理解“真切笃实”是行,“明觉精察”是知。“真切笃实”和“明觉精察”合一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体现良知本体的活动。
从这一“过程—事件”的分析可知,和以往政府“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的“硬策略”不同,“大调解”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工作人员或相关关系人共同参与化解矛盾的一种“软策略”,是一种集合“心理感悟”和“情感投入”更加人性化的应对方式,亦是一种“半正式”的治理策略。
《中庸》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说。在王阳明的时代,学者接受的看法是学问思辨是学,笃行是行。在《答友人问》中,王阳明心目中行的含义是真切笃实,实在地去做这件事。王阳明对行的含义的这种说明,更多是取“笃行”的“笃”的含义,而淡化了行为的含义。“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1]232。王阳明依据这一“行”的含义,论证了知行合一。不过这里的知行合一是理性知识方面的知行合一。学是知行合一的,因为实在地做学问思辨的功夫,那么学问思辨就是行了。行也是知行合一的,行也是学问思辨。因为行的时候需要学问思辨做这件事。行的时候的学问思辨属于理性知识层面,进一步说就是明觉精察之知。学问思辨和明觉精察二者之间有细微的差别,这里讲的学问思辨是就着知行二分意义上的学问思辨来说的,就是指的学习、思考外物的知识性的活动。行为、“著实去做这件事”和“真切笃实”也有细微的差别,“真切笃实”可以兼容“著实去做这件事”,同时可以有良知本体运作的含义。行和学问思辨合一,行就是学问思辨,是说学问思辨做这件事,并不是说行的时候去做学问思辨的事情,但是行的时候可以有明觉精察,明觉精察和行是合一的。“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1]232。行的时候的学问思辨如果达不到明觉精察,是对良知的遮蔽,所以是冥行。“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1]232。那种先学问思辨某件事,然后去行的学问思辨是悬空的。王阳明提出明觉精察、真切笃实本质是要保持良知警醒,同时要求良知在知识性的活动中和行为中都保持高度的在场和当下性。在知识性活动中,如果能够明觉精察,意味着良知发用为知识,如果能够真切笃实,意味着良知的力量得以观照求知的活动。其中包含着多个层面的知行合一:良知发用为知识和行为,是本体的知行合一,即在求知活动中得以致良知;求知本身变成一个真切笃实的事情,知识就是行为了,这也是一个知行合一;学问思辨做这件事,行便是学问思辨了,这是知行合一;明觉精察、真切笃实二者之间高度合一,这也是知行合一。致良知在知行上,则是本体的知行合一,明觉精察、真切笃实二者之间高度合一是本体合一在大用中的本体显现;而学问和行为本身在知识和行为层面上的合一是大用。二者的区别是知行体段和补偏救弊的差别。
知行合一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学习、思考、知识、意念、知觉或感觉是良知的发用。学思问辨落到实处,意味着明觉精察贯穿到学思问辨中。思可以是良知的发用,也可以是私意的安排。“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扰劳忧,良知亦自会分别得”[1]81。知行本体最怕被私意隔断。逆、臆想、求先觉都会自蔽其良知。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则直接指出,“学孝”一定是服劳奉养才能叫做学。这样的学意味着良知的警醒,在学的开始已经是行了,天下的“学”没有不行就可以叫做“学”的。问、思、辨、笃行都是即学即行的。道德性的“应当”被王阳明理解成是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或者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都不是知行合一所要求的“知”。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还举了舜不告而娶,周武王不葬而兴师的例子来说明知行合一。如果要查阅典章,咨询他人,悬空讨论这些不合常规的事情,然后作为做事的标准,事情是做不好的。舜和武王是在心感应的时候精察义理才有了这些行为。
第五,通过“至之”的功夫,达成“知至”,良知圆成自身为“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嘉靖三年(1524)王阳明在《书朱守谐卷》中说:“如知其为善也,致其知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如知其为不善也,致其知为不善之知而必不为之,则知至矣。”[1]308这段表述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致”,是非都依着良知,“致”则是不为“不善”,而去“为善”。这种“必为”和“必不为”是一体的两面,即良知本体之“行”。王阳明也指出,在长者之后徐行不是人所不能的,而是所不为的。良知之行是人所能做到的。这个“行”由体达用,从而实现体用一源。“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1]58。
由良知到行为,要保证良知发用成思考和知识,因而包含着诸多的逻辑环节。其中的关键就是意之动。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说:“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1]47只要认良知认得真,对不善之念有足够的明觉,善念发动无滞,任何情境都可以做本体功夫。
从意之动到行为,良知完成了自身。“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1]52。行为是良知的完成,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1]5。这是知行的本来面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抓住了“道问学”的根本。天命之性统率生命,生命就是一个被天命之性规定的生命,生命就走在道上面。因为生命会偏离道,因而就存在“修道”的问题。这一问题或者被表述为正心、诚意的问题,或者被表述为养心的问题,学术表述不同,要解决的都是保证道如何从内在规定人的生命过程的问题。王阳明认为“命”就是“性”,“性”就是的“道”,“道”就是“教”,进而把良知说成是道,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去做就都是道。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功夫,因而可以有多种“知行合一”的讲法,但多种“知行合一”功夫成立的前提是知行本体的良知良能。也就是说,多种功夫只有在成为良知良能展开为自身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的时候,才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一个良知的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对于“道问学”的意义就在于“知行合一”是“道”成立的内在逻辑要求。如无“知行合一”,“道”就不能展开自身为道路,良知也就不能实现自身为至善。多种“知行合一”样态存在的根据是良知本身就是良能,当去蔽的过程完成以后,良知就实现了自身,至善得以圆成。“致良知”就是一个至善圆成的过程,从而凸显了“知行合一”的至善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上册[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 董平.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4] 欧阳德.欧阳德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 汪学群.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思想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3-0109-09
[收稿日期] 2018-10-15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16Y015
[作者简介] 周海春(1970-),男,内蒙古扎兰屯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研究;韩晓龙(1981-),男,陕西宝鸡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7 级博士研究生,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标签:王阳明论文; 知行合一论文; 致良知论文; 至善论文;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