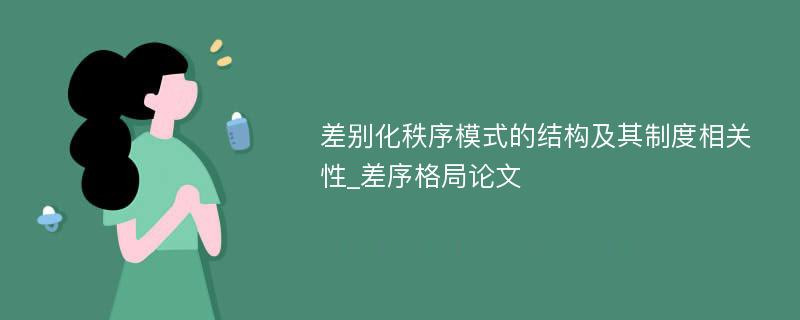
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格局论文,结构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03-0042-07
一、问题的由来
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阐述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社会结构,作为其参照对象,则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费老是在比较了与西方社会的不同之后得出“差序格局”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由于中西社会发展的位差关系①,这一比较具有两个可能的维度:从时间层面来看,可以分为传统和现代;从空间层面来看可以分为中国和西方。因此按照这一逻辑,要想理解“差序格局”的内涵,必须先要厘清这一概念所基于的比较维度。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的关注点集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把“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比较简化为帕森斯的模式变量,如特殊主义/普遍主义。这一简化使“差序格局”的概念失去了中国乡土味,而上升为传统社会的一般性比较变量,这与费老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从费老的本意来看,他对“差序格局”的概括建立在乡土中国的基础之上,他说:“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费孝通,2002:4)。因而化约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空间层面的比较意义。这一化约主义的误区大致缘于费老散文式的行文风格,因为费老在原文中只是指出:“我在这个分析中只想从主要的格局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在西洋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费孝通,2002:37)。问题由此而生:费老所说的“西洋社会”究竟是指西洋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显然,这里的所指和能指之间是不一致的,能指的范围要大于费老实际的所指。按照前面的比较维度来看,如果费老所指的是西洋现代社会,则所谓本土化概念的“差序格局”就有可能在逻辑上发生动摇:由于发展位差的原因,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于传统—现代之间的普遍性行为模式或社会结构的变迁,因为西方传统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模式、社会结构可能也是这种类似的“差序格局”或社会圈子,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这样一种格局迅速被新的组织和结构取代,那么对化约主义的批评有可能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对于上述推论的社会基础方面也作了类似的论述:
社会的基础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有所变化。随人类起源而有的社会基础是社会组织的一种雏形,可将其定义为“原始”社会组织。社会的微观结构是以人们与生俱来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亲属关系。社区是各种亲属关系相结合的产物;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均来自上述原始关系发展而来。
变化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使生产走出家庭作坊。此种持续不断地演进,导致家庭与社区组织为一方,经济与政治组织为一方,相互联系日渐减少……原始组织衰亡是许多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们正在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詹姆斯·科尔曼,2008:1)
在科尔曼看来,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以血缘为关系的家庭,而现代社会结构的基础则转化为法人团体,这一分析与费老关于“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区分又存在某些暗合:因为差序格局也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团体格局则是建立在社会团体(次级群体)基础上。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推进,“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中国本色”将会自然褪去,而只是帕森斯模式变量的本土话语表达而已,也即“差序格局”的界定仅仅是“位差”状况下的一种错觉,本质上和西方传统社会基本结构和行为模式是一致的;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差序格局将会自动的解体,而进入一种团体格局的状况。
众多学者在分析和使用“差序格局”概念时所存在的实践意识也强化着上述逻辑的悖论:一方面强调“差序格局”是为数不多的基于本土社会资源而产生的概念,另一方面在分析当代社会情况时又很自然地把它化约到帕森斯的模式变量,认为差序格局在中国已处于半解体或解体的局面。如美国汉学家傅高义(Bzra F.Vogel)试图用“朋友关系”和“同志关系”来解释这种关系的变迁(Vogel,1965),而这种解释的假设就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孙立平在分析中国社会关系模式时,以利益为基础,在再分配体制的视角下,认为“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人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构成的,而不是由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构成的”,这种关系就形成了“由纵向的庇护主义和横向的工具性关系模式构成的社会结构”(孙立平,1996)。这一解释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魏昂德、奥伊、李沛良等人的研究成果,而这一研究的前提也在于对社会关系阐述的两分法: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表达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这样一种化约的方式产生了问题:“差序格局”与这种新的行为模式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在两分法的前提下差序格局没有自动地演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团体格局?还有学者在分析差序格局的现代内涵时,认为传统的差序格局的基础在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家长制、等级制度、礼治和人伦”(卜长莉,2003),而这些基础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中心点发生变化、利益成为“差序”影响因素、人际关系范围扩大、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固定和流动两重性。这一研究虽然没有简单地认为差序格局已经解体,而且认为这一概念对于分析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还有重要意义,但仅仅是以“社会变迁”来解释“差序格局”的现代内涵。同时这一解释也暗含着一前提假设:差序格局的基础在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家长制、等级制度、礼治和人伦”,这些要素基本上可归纳到模式变项的范围内,因而还是在使用简单的两分法的思维来分析差序格局及其变迁。
这种使用两分法方式来解释“差序格局”概念固然能说明某些问题,但往往容易造成这一概念“事实上的西化”,而模糊了中、西方空间意义上的差异。按照这一认识,对于“差序格局”的社会转向的实际情况也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为什么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这一格局并没有自动解体,甚至出现了“传统的回归”?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于如何来理解“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由于费老是以类似散文的形式提出概念的,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论述,只有一些表象层面的描述,因此很多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并没有进行学理方面的思考。同时,由于现代化的推进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同现象,往往使人们忘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性。因而,要澄清化约主义的误区,必须从以时间为重点的分析转向以空间为重点的分析,即对“差序格局”的结构进行分析,而这一结构的形成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差序格局的结构
费老并没有对“差序格局”作严密的定义,而是用非常形象的说法来阐述这么一种现象:
“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2002:26)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相对随意的表达方式导致了人们对其理解产生了歧义,“当代的学术话语逐渐地将差序格局概念从社会结构的层次位置换到人际关系的层次。但是,人际关系的结构仅仅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而已。在人际关系结构的层次上,与中国的关系相对应的是西欧北美社会中的个人网络或社会网络,而不是费孝通所概述的团体格局。显而易见,在这种错位的话语中,‘差序格局’的丰富内涵的某些部分便失去了”(阎云翔,2006)。通读费老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14篇短文,虽然也有涉及“社会关系”概念,但一般用于差序格局框架内,如“在差序格局内,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费孝通,2002:30),更多的时候在使用差序格局时,是指“社会结构的格局”,因而,在理解这一概念时,社会结构的视角才是把握差序格局结构的途径。
另外,从费老的学习和师承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结构的,这从费老后来在《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一文中可以印证,在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之间学术争论的影响下,“带进了这在本文开始时所述对社会的两种看法的迷阵”(费孝通,2002:332),后来进一步在涂尔干的影响下,基本倒向了社会实在论的阵营,把社会与文化脱离。而布朗、涂尔干“常常强调把社会看成是社会本身,因而认为可以用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结构对团结和整合的需求来解释文化要素”(特纳,2001:14)。站在费老当时的情境下,其对社会结构的理解基本上是宏观结构主义的传统,所谓社会结构,一般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地位)的分布状态,常用人口规模、分化、社会地位间的异质性及不平等性、各地位群体之间的关联程度、群体内与群体间的交往、社会整合等来对其进行分析研究。那么按照这一对社会结构的界定,对“差序格局”的理解可以从社会基本单位、社会组成及社会运作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一)社会基本单位
正如科尔曼所言,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现代社会则是法人团体。费老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研究也是从社会的基本单位出发的,他也找到了与科尔曼相同的单位:家庭。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西方,家庭“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而在中国,对于家庭的概念是相当含糊的,“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很难分清楚家庭所包括的成员:
“家里人”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费孝通,2002:25-26)
在费老看来,这样的家庭实际上是家族、氏族,其依血缘关系而延伸,与西方基于生育功能的家庭所不同,家族还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功能,因而它就不再是一个暂时性的组织,而产生了稳定性,成了一种事业组织。这种组织可大可小,但其基本特点都是一贯的:单系、差序延伸。
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关系上的。在儒家文化设计中,以亲属的伦常去组合家庭的规模。虽然我们一般形容这样一种家庭为扩大家庭,但从中国历史统计资料来看,我国的家庭规模几千年来一直在四至六人之间浮动,也即人们常说的“五口之家”的规模(李银河,2001)。因而,所谓的扩大家庭,是“变形的扩大家庭”,实则是在家庭基础上松散的亲属关系,由此而形成了费老定义的“小家族”。这种形式虽然基础在小家庭,但其重点却在维护超越小家庭的亲属关系网络。
费老对于差序格局的内涵虽然没有明确解释,但从其叙述来看,应该包括横向的“差”和纵向的“序”。对于这样一种形式的家来说,“差序”的特征尤其明显。“差”主要以小家族的规模大小来体现;“序”主要以伦常的等级体系来表现。在这样的小家族内,虽然依靠各种血缘关系形成一张关系网络,但其规模到底有多大,是很难具体来算清楚的,按照费老的说法,“自家人”的范围可以因时因地伸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候和地方,家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存在着大小的差别。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家族内,还存在着按照伦常体系来建构的等级序列。费老说:“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差等……伦是有差等的次序”(费孝通,2002:28)。一般从亲子轴出发,按照儒家文化中的伦常设计,分为若干等级,按照辈分大小,家庭中的每个人按照这一设计对号入座。在这样的序列中,每个人都有其角色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但这种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如父为子纲,即不管父亲说的、做得对错与否,作为儿子都必须绝对服从和遵守,由此而形成了家长制。
(二)社会组成
在传统社会中,有一条社会的中轴线,即费老所说的“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费孝通,2002:28)。整个社会就是按照这样一种结构形成的,而在儒家的文化设计中,这样一种体系的维持有着其自身的原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一原则中所包含的“孝悌忠信”都是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费孝通,2002:35)。从己到家可以用“孝”来维持,那么,如何来处理家与国的关系?因而,在儒家文化设计中,缺少处理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关系的道德要素和原则。为了克服这一障碍,儒家文化采用了倒推的手法,在这一设计中有一前提假设:所谓的社会、团体只不过是个人的组合,并不是一种实在,认识社会的基础在于认识个人。因而,家、国、天下只有人数多少的区别,并没有其内在的区别于个体的特征,这样就形成了从天下到国,到家,直至个人的认知格局。这样的设计主要用来型塑个人与家庭、个人与陌生人群体、个人与社会(团体、国家等)的关系——后两者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人与家庭关系的再造——其终极目标是形成个人的等级制度。
1.个人与家庭。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而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即在于家庭的结构。儒家文化中虽然有着“从己到家”的说法,在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其最大的问题也正好在于“不被发现的自我”。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是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煞”(梁漱溟,2003)。个人在家庭中的行为受到严格的家庭伦理的制约,“孝”成为这一家庭伦理的核心标准,一切行为都必须以此来衡量。这种“孝”在制度化儒学中不再是价值观或道德层面的意义,而是一种制度设计,从经济(资源分配)、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具体体现“孝”的存在。个人价值并不是体现在能力大小上,而是在“孝”的语境下来评判。费老虽然说个人在差序格局下是“自我主义”的,但这种“自我主义”和杨朱不拔一毛的绝对主义不一样,它是有相对性和伸缩性的。这里的相对性和伸缩性的底线即在家庭。到了家的层面,“自我主义”就退无可退了,必须把自我意识压抑起来,牺牲自我利益,走向集体主义道路。
2.个人与陌生人群体。在儒家文化设计中,只有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这五伦,在实际交往中,总有很多时候会越出这五伦的界限:如,如何与陌生人交往?这在五伦当中是没有明确的原则的。为了处理类似的情况,儒家采用的是“类推”的方式,以拟血缘的关系把这类情况纳入五伦当中,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来再造个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一些学者阐述“差序格局”时认为这一概念是用来表达人际关系行为模式或社会关系,其基础正在于讨论个人与陌生人群体的处理方式上。
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实体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主要是指家庭以外的群体。在五伦中虽然有“君臣有义”来调适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显然还是侧重在君、臣相互之间的私人关系层面。在此之外,普通人如何处理国家、团体的关系?五伦中没有规定。按照儒家倒推的原则,国家、团体的结构与家的结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范围、人数多少而已,普通人与国家、团体的关系就演化为个人与家庭的关系,而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又可以依照具体规定个人之间关系的人伦制度来处理,“移孝作忠”是这一演化的儒家制度规定。在这样的规定下,公与私、群与己的界限就被模糊了,仅仅是一种个人关系的外扩而已。
由己出发,到家、国、天下,其关键在于“己”。因而儒家说要修身,要克己复礼,目的即在于去自我中心化,以人伦关系来塑造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并把这一关系固定化推广到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层面。所以费老说:“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费孝通,2002:36)。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整个社会。社会结构的基础在于家庭,而家庭的基础在于个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从己到家、国、天下只是个人关系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和再造,其整个模式即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因而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费老也正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由于人伦设计中包含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也只能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
(三)社会运作机制
在这样的社会中,其运作的基本机制是“推”、“恕”。由于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上,通过拟血缘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把这种伦常扩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处理社会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人际关系上,有学者把它称为关系本位社会。这种关系是不固定,具有相当强的弹性。因而,面对同一个人(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行为路径,这种路径是由人际关系网络所形成的,从自我出发,选取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五伦的范围内。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推”的问题:
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费孝通,2002:27)
“推”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维,国家、社会的结构形成是建立在“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推”的基础上,处理日常事务还是建立在“推”的基础上,这种“推”的思维其根源在于社会被简化为人与人的组合及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所有的制度化建设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主体进行的,而缺乏具体处理事情的刚性标准和规则。由于制度安排与权力运作机制都建立在以“推”为中心的基础上,因而处理事情就出现了过程多元化和结果多元化,在这样的情景下也很难有公平、公开的机制和制度建立。
从上述对社会结构的这种“差序”属性分析来看,虽然其暗合着特殊主义的情结,但还是包含着自身的独特之处: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群己、公私界限的相对性;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机制等,这些也正是差序格局的“乡土”特征之所在,而这样的一种特性离不开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土壤,差序格局的形成也是政治—经济制度性安排在社会结构层面的体现。
三、差序格局的制度关联性问题
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特性的形成有其最初的初始条件和要素安排,费老虽然没有详细解释,但也有涉及:
(团体结构)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的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费孝通,2002:31)
当然这样的论述还需要史学家去考据,这也不是本文的重点。笔者考察的重点在于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是如何与其他结构共生的,相互间有何种亲和力。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嵌入性”概念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他们对“嵌入性”的理解在于强调“制度的关联性特征”。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就把问题进行了转化:从结构形成的要素和条件转到结构的特点,通过制度特征的关联性可以进一步去研究制度的变迁与发展。因此,在这里我们主要探索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与其他制度的亲和力。
从制度的关联性角度出发,社会结构与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社会结构的这种差序格局属性与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和观念是分不开的,它通过一体化的政治文化为其设计了制度的合法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实践的可能性。
(一)政治文化一体化与差序格局
金耀基认为,儒家在文化设计中尝试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外设计第三条道路:伦理典范(金耀基,2004),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制度化的儒学中,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就是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结构下,文化设计的目标在于确立封建专制权力的合法性,儒家从社会基本单位家庭入手,主要采用伦理规范形成了事实上的人格的不平等,权利和义务在不平等的人格中也就失去了平衡,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必须压抑自身的自我意识,通过修身克己来服从伦理秩序。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这样一套秩序可以自动复制到国家中,国家只是皇帝的家,君主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而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因此,儒家文化的这种设计逻辑其资源来自下层,但出发点是自上而下的,通过封建专制权力,儒家文化把这种不合理的差序格局普遍化和制度化了。
(二)政治经济一体化与差序格局
孙立平指出,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孙立平,1996)。在家庭中,资源掌握在家长手中,资源的分配按照血缘关系进行,这也是大多数人愿意服从伦理规范的物质动力。在社会层面,不同的社会圈子只是家庭的外扩而已,社会资源也掌握在这些名义上的家长手中,他们可以无偿占有这些资源,同时也使成员依附于不同规模的社会圈子,这个圈子的尽头就是国、天下。因此,这种资源的高度共有性导致人们对其产生依附感。换句话说,这种差序格局之所以能在社会中自动复制,是有其重复实践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稀缺资源的分配模式。通过这种分配制度,使资源高度集中,从而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但这种结构的稳定又具有一定的弹性,个人通过自己的能力,进行不同路径的“推”,可以获得不同的利益。因此,这种高度集中的资源分配体制是与差序格局共存的,它通过资源的共有制度与弹性的分配可能性,进一步强化了差序格局实践的效果。
在这种强制性权力的作用下,通过文化设计和经济引导,差序格局已经成为一种体制,虽然其初始模式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但通过体制化建构,差序格局已经可以脱离这些基础而具有了文化根基和经济动力,它可以自动运转。因此,差序格局变迁的关键点应在于体制的实质性重构,而不仅仅是血缘、地缘关系的消失或衰弱。
注释:
①所谓“位差”,在此主要用来指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形成的自然落差,这种落差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体系综合评价的结果。
标签:差序格局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费孝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人际关系理论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