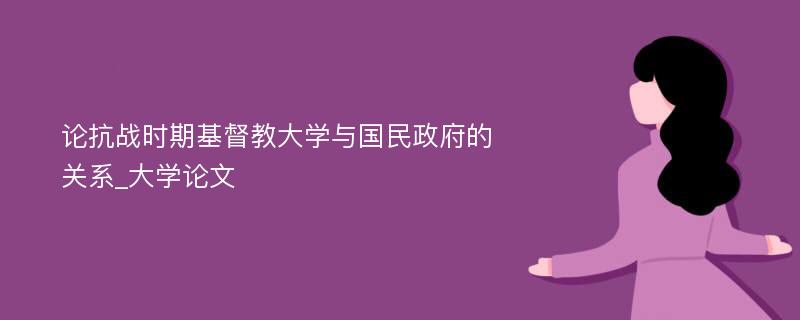
论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基督教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关系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3-0077-08
中国基督教学校在经历了1922-1927年间“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不得不适应民族主义的潮流,加快本土化步伐,任命中国人做校长,并向中国政府立案。抗战前,13所基督教(新教)大学中,除圣约翰大学外,均已在南京国民政府以私立大学名义立案。正如金陵大学老校长包文博士(Arthur J.Bowen)评价那样,基督教大学与中央及地方政府有着真诚而密切的合作,它们不再是“外来”机构,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员。(注:Bowen,"China in l937",Letter to the Friend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October 5,1938),见亚联董藏中国基督教大学档案,原件藏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全宗编号G11-238-3933(以下注释同)。作者使用的是亚联董赠送给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缩微胶卷,特此致谢。)抗战军兴,基督教大学和整个国家一样,面临生存危机,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基督教大学的国家认同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且为适应国家战时需要,双方合作更加紧密。但战时国民政府对全国高等教育的控制也逐步加大,使基督教大学面临失却原有特色和办学自由的危险,导致了基督教大学与政府教育政策之间的一系列紧张。基督教大学为了谋求发展,不得不再思基督教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理念的差别,并努力与政府沟通,寻求理解和支持。
一 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
九·一八事变时,基督教大学师生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得毫不逊色于国立大学,一二·九运动时,燕京大学更发挥了先锋作用。抗战一开始,政府号召大学生以从事军训、宣传、救济、服务等活动来表达爱国之心。基督教大学积极响应政府这一号召,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把所有学生都投入到附近农村做民众动员。福建省政府要求全省所有初中以上学校都要以华南为模范,在1938年头3个月参加社会服务和宣传活动。(注:President's Report for the Year 1937-38.RG11-176-3191.)福建协和大学的师生也深入内地进行民众动员,宣传“抗战建国”的意义,从1938年1月开始,大学负责8个县的民众教育,宣传普通卫生知识等。(注: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37-38.RG11-108-2393.)
随着战事逐步深入,基督教大学和公立学校一样纷纷内迁。齐鲁、金陵、金陵女子迁到成都,落户于华西协合,东吴和之江先后搬进上海公共租界,与圣约翰、沪江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燕京则坚持原地办学,直到珍珠港事件后才迁至成都。华中先迁至桂林,后又于云南大理喜洲小镇定居。福建协和去了闽西邵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去了南平,岭南先迁香港,后又到曲江。整个抗战时期,13所基督教大学中除华西协合不用搬迁外,其余12所大学都作了迁移,距离从十几千米到几千千米不等。基督教大学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继续生存,同时也是基于为国家保存教育命脉,在政府看来,是一种国家认同及忠诚的体现,也是协助政府实施“抗战建国”方略。
暂时留在沦陷区的基督教大学,象燕京和在上海的联合大学都是靠着美国国旗和治外法权的保护才得以生存的,难免要受到国人甚至校友的误解。司徒雷登1938年2月去上海会见一些校友时,发现他们用“某种严厉甚至不赞许的态度”看待他,怀疑燕京所以能平静地办理下去是因为在国家忠诚的基本原则方面妥协了。(注:J.L.Stuart to B.A.Garside(Feb.17,1938),p.2,RG11-359-5531.)当时正在英国读书的费孝通也给司徒雷登写信,对燕大继续办学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建议在西北地区另开分校。(注:Fei Hsiao Tung to J.L.Stuart(April 28,1938),p.2,RG11-359-5631.)这些大学以后的表现在在说明它们并没有背叛国家利益,它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仍保持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没有一家和日本或傀儡政权有任何正式的官方联系。(注:珍珠港事件后,上海惟有圣约翰继续照常公开上课,有人认为圣约翰行政当局过分迁就了汪伪政府和日本人的要求。校长沈嗣良曾出席日伪在上海和南京召开的教育及其他会议,并在公开场合发表反美亲日言论,也曾在日伪政府和社会组织担任职务。战后,沈嗣良被捕入狱,并被判处一年半徒刑。圣约翰校董会和差会当局都对沈做了辩护,认为沈和伪政府的来往是为了减轻学校所受的压力,沈本人也认为自己是不顾政治形势的险恶,通过提供教育机会为中国服务。详见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161-165页。)司徒雷登面对抗战爆发后的复杂局势,提出办学的三原则:保持大学创办者、支持者的忠诚;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忠诚;用适当的办法同日本当局保持友好关系。(注:J.L.Stuart to B.A Garside,June 6,1938.RG11-359-5532.)1939年4月,12所基督教大学的校长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基督教大学面对国家危机应采取的对策,他们发表了一致声明,认为应当维护基督徒的品格、学术自由和对国家的忠诚,为保护这些权利作出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注:Galen Fisher,ed.The Effects of Stno-Japanese Conflicts on American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ic Enterprises in China:General(American Council,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39),p.37.)
沪江校长刘湛恩的例子更可以说明基督教大学师生的爱国之心。刘在抗战爆发后曾担任上海文化救亡协会会长,积极参与救亡运动。1937年9月30日他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控诉日寇暴行,呼吁美国民众支持中国抗战。他的抗日立场引起日方嫉恨。在几起日方策划的暗杀行动失败后,周围朋友都劝他去香港或汉口躲避,但他拒绝去任何地方。1938年4月7日,刘湛恩被杀害。国民政府对刘按照国葬规格下葬,以表彰他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注:Chinese Educator Slain in Shanghai,New York Times,April 7,1938;Shanghai Educator Heard of Death Plot,A Copy of Newspaper Report;An Open Letter to Friends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April 25,1938.RG11-240-3954.)
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不仅表现在对敌态度上,更体现在它们在战时对中国所做的杰出服务。金陵和金陵女子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校园保护和救济了数万平民百姓,这些教职员被南京20多万难民亲切称为“活菩萨”。(注:参阅章开沅教授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之江、岭南在日军侵占杭州、广州时,也都曾以自己的校园作为成千上万市民的庇护所。华中在接到教育部要求接受华北和沿海逃难学生的指令时,积极准备房舍,接受了多名华北难民学生。华中师生还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在救护伤兵方面贡献很大。(注:President's Report for the Year 1937-38,华中大学档案,第226卷,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金陵在华西从事一百多个社会服务项目,努力满足当时各方面的需要。(注:Oliver J.Caldwell,"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War",School and Society(Feb.28,1942,Vol.55,NO.1418),p.233.)华西协合在发展实用科学方面成绩也很显著,尤其在制革、印染、药材和畜牧业改良方面。福建协和等在后方从事的乡村建设事业对战时人民福利也有重大贡献。1939年华西协合和齐鲁的医牙科学生作为军医直接参军,1941年金陵等一批工科学生参军从事公路及兵工制造等工程。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发动了“学生从军运动”。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志愿服役,远远超过政府预料和接受能力,结果只有一小部分被录取。燕京学生参军热情甚高,共有79人被录取,有66人参加陆军或后勤部队,3名男生参加了远征军,9人参加了空军,1人进了海军。入伍空军的9人相当自豪,因为9所大学的数百名报名者只录取了30名。(注:Ch'en Fang-chih to Colleagues and Friends,Fortnightly Letter(Nov.30,1944).RG11-377-5731.)还有相当多的基督教大学学生成了美军翻译,有3名福建协和学生在史迪威的缅甸作战军里担任翻译;相当一部分金陵女子和燕京的女生在成都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担任打字员、电报员或会计等地勤工作。
国民政府对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和战时服务作出了正面回应。1938年4月6日,宋美龄在武汉一次传教士集会上发表演讲,盛赞传教士和基督教大学对战时中国的贡献:
你们对我们国家最有影响、最具价值的贡献不是这些工作本身,而是你们工作时表现出来的精神……我非常高兴告诉你们,那些很多年前批评基督教的人正是现在赞扬你们的人。你们通过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语言不足以表达我对传教团体的感激之情,他们不畏日军要把他们赶跑的恐吓,坚守岗位,把许许多多中国妇女和孩子从濒临死亡中拯救出来。
宋在演讲中还提到,她和蒋介石都觉得有必要修改教育部禁止宗教教育的条款,如果教会要求,把宗教教育作为必修课是可行的。(注:Christian Educationists Takes Note,May 23,1938.RG11-4-73.)此番言论通过《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广为传播,让关心中国基督教教育的美国教会人士大为振奋。1939年,一条新的关于宗教教育的条例建议案出台并被通过:在私立学校,如果开设宗教课程,学生可自由选修;宗教活动如果在课下举行,学生可以自由参加。虽然只是一个建议案,但它对在中国从事基督教教育的人士来讲是极大的鼓励。他们认为这至少表明政府领导人对基督教价值的赞赏,对宗教教育某种程度的认可。(注:Chester S.Miao,"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1938-1939.p.219.)
基督教大学在纽约的联合办事机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为战时基督教大学持续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合会非常重视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每年年会都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和其他著名人士参加,中国政府也借此机会表彰基督教大学。宋美龄曾出席1937年年会并发表演讲。1938年邀请驻美大使王正廷出席年会。(注:Garside to C.T.Wang,April 18,1938.RG11-27-687.)次年邀请驻美大使胡适参加年会,胡因故不能出席,特在5月31日写信给组织者罗炳生(Edwin C.Lobenstine)表示歉意,并赞扬基督教大学是“现代中国的开拓者”:
几十年来,基督教大学把新的生活观念、新的道德价值标准、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他们是现代中国的开拓者。最近几年,他们集中财力和人力发展少数几个中心,其中一些已能够和国立大学在学术上一比高低……由于日军侵华,基督教大学师生不得不离开他们美丽的校园,迁入内地,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工作,这种伟大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中国人纪念。(注:Hu Shih to E.C.Lobenstine,May 31,1939.RG11-12-287.)
1939年6月30日,基督教高等教育干事葛德基(E.H.Cressy)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国政府能对多年以来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几位美国人士给予特别表彰。(注:E.H.Cressy To Hu Shih,June 30,1939.RG11-12-287.)11月30日胡适回信说,中国政府已经在双十节庆典上授予Paul D.Cravath等四人蓝白玫瑰翡翠。(注:Hu Shih to E.H.Cressy,Nov.30,1939.RG11-12-287.)1942年联合会又邀请胡适出席年会,胡适回函表示他非常忙,加上离开中国太久,对国内情况不是很熟悉,不适合做“前进中的中国教育”演讲。但他对基督教大学的评论让基督教教育者们颇感欣慰:
你发现在所谓的非国立的外国教育即基督教教育中心,在战争来临时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民族主义的训练中心。个别学校试图比国立学校还要民族主义。……他们的学生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国家生活。跋涉数千里,和国家脉搏一起跳动。政府十分赞赏这些学校,积极帮助他们闯过难关,并把他们极力展示给外面的世界,表明我们是欢迎而且需要这些学校的。(注:The 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A Program for Service:The China Colleges and the Crisis,A Memorandum to United China Relief,1941,p.8.)
蒋介石和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曾在不同场合发表声明,称赞并感激基督教大学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国民政府也从实际方面资助基督教大学在战时的发展。在战争初期,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办理战区学生登记,不分公立私立,一律帮助安排迁移转学,发给贷金,很多基督教大学学生因此得以安全转移并复学。尽管战争使得军费猛增,但战前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资助仍继续保留,只是数目减少,大都只付70-75%。对基督教大学中比较实用的系科,尤其是与战争和国家建设相关的项目,如机械制造、农业改良、化工等方面,政府资助的力度还是很大。
总的说来,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基督教大学对国家的忠诚、为国家所做的服务以及在美国进行的关于中国抗战的宣传,得到了国民政府前所未有的肯定和表彰,政府对宗教教育管制的放松,也是对基督教大学的正面回应。但必须看到,国民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赞赏,与战时国民政府渴慕与美国修好、争取美援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也密切相关。而基督教大学在这宽松友好的氛围中得到了较战前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宗教教育领域,很多传道人可以借用大学的礼堂开布道会,甚至用教室作主日礼拜。(注:赵君影:《漫谈五十年来中国的教会与政治》,中华归主协会,1981年版,第16-18页。)战时基督教大学(也包括国立大学)的宗教生活与战前相比活跃很多。但基督教教育与国家教育之间并非总是那么和谐,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紧张,甚至是根本性的冲突,尤其是在教育理念和具体的教育政策与行政方面。
二 基督教大学与政府教育政策之间的冲突
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因条件艰苦而一蹶不振,相反,在政府支持下,至少从规模上得到了发展。到1942年,大学数目由战前的108所上升到115所;学生增长7.5%,达到45000人;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人数也由战前占大学生总人数的15.3%上升到20%。(注:Oliver J.Caldwell,"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War",School and Society(Feb.28,1942),Vol.55,No.1418,p.233.)在陈立夫的主持下,教育部在推进专业和课程标准化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且以此加强了对公私立高等教育标准的控制。
大学课程向由各校自订,各校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过于高深,有的程度不够,因此早在战前两年政府就着手调查各大学所设科目,加以比较,然后整理研究,经各大学系主任和教授发表意见后,于1938年9-11月间公布大学科目表,详细规定了文、理、法、农、工和商学院的共同必修科目,1939年8月又公布了各系必修和选修科目。(注:杜元载主编:《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五十八辑,第150-151页。)由政府统一专业与课程标准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保证了毕业生具有一定的程度,弊的方面是束缚了高校个体的灵活性。此外,这次专业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当时急需的实用课程比战前大增,人文和社会学科则明显减少。教育部认为国家由于战争已无力负担研究生教育,因此要求提高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教育部还禁止高校随意开设选修课,并要求主修课一般要达到80个学分小时。其他必修课还包括每周两学时的军训、体育和卫生课,一门三民主义课,基础课就有60个学分小时。1940年后,每周还有几个小时的劳动服务。这些政策造成学生选课机会减少,即使可以选课,也只能在经过政府批准的课程中选择。(注: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362-363页。)对师资培养也作出新的规定,私立学校不得开设师范专业,师资培养只能由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承担。留学教育政策也作了很大变动,不论公费、私费,一律纳入国家计划,所学专业要配合国防建设需要,以理工医农为主。(注:杜元载主编:《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五十八辑,第104页。)
这些新政策的出台无论对国立大学还是对基督教大学影响都很大,对基督教大学来说,在专业设置上,几乎无法保持自己原有的特色。学生和老师都抱怨说,在教学计划中自己毫无选择余地。教育部还规定只有医学院才能开设医预科,这就置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困难的境地,因该院化学专业学生实际是为医预科准备的。对师范教育的严格限定使得沪江也很难堪难,因为它的师范专业一直很强,而且很受欢迎。(注: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no date,probably in 1939),RG11-240-3948.)
基督教大学由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或称博雅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向的趋势由来已久,而此时政府对专业与课程的整理使这一趋势更加严重。战争时期选修人数最多的专业集中在经济、化学、工程、教育和医科等领域,哲学失宠,文学院难以保持以往的注册人数。(注:E.H.Cressy,"Effect of the War on Christian Educ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January 1941),p.6.)福建协和的徐光荣(Roderick Scott)说,没有学生再有可能选修一门哲学课,不得不停开,他只能在英文课里加进一点哲学知识。这种转变当然很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建设需要人才,尤其是在战争年代,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国家需要是所有大学的倾向。(注:Pei-sung Tang,Chinese University on the March,p.1.RG11-158-2998.)但这对一贯强调通识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很多基督教教育工作者提出要警惕职业教育走向极端的危险。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现代的各种应用科学,但也需要纯粹科学和更深厚的文化教育来丰富生活和未来领导人的视野;基督教高等教育不能跟在国立大学的后面亦步亦趋。(注:Chester S.Miao,"New Trends in Christian Educ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Feburary 1941),p.63.)葛德基认为,基督教大学向职业教育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基督教大学为满足国家需要而做的努力,但他也批评这是“机会主义”,远离了基督教大学创办者的初衷。(注:E.H.Cressy,"Effect of the War on Christian Educ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January 1941),p.6.)为应对这一局面,许多基督教大学增加了关于仁爱和理论科目的奖学金,以吸引学生选修。
军训对基督教大学来说并不是新鲜事,因为国民政府在1928年就开始要求中等学校及大学必须接受相当之军事训练,每周要3小时。随着日本侵略日益逼近,到1936年夏天,政府决定把军训时间延长为3个月,但大多数学校并没有严格执行。多数基督教大学变更军训的形式,如华西协合得到中央政府批准,军训只保留了夏令营的形式,省略了训练的军事成分。但抗战开始后,四川省政府不仅要求大一的学生参加军训,大二大三的学生也要参加,并要求学生在双十节持抢游行,还要练习打靶。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向当局解释,华西从来不参加军训,只是在冬夏假期进行身体素质训练,要求在校园里军训,但政府拒绝了。双方关系有些紧张,因为有报社记者评论华西“不爱国”,尤其是在有学生曾主动要求参加全部军训课程时,校方不予支持。后来双方采取折衷的方式,军训在学校进行,枪支存放他处。医科和牙科学生减免军训课,因为他们主要从事战时医疗服务。其实当地政府限于条件也无法实施新生的集中训练,最后还是各学校自己组织,政府派员协助。1939年教育部又指令各校每周军训时间为6小时,3小时是军事课,3小时是与战争有关的时事课。(注:Cabinet Bulletin of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Oct.25,1937,NO.8).RG11-277-4384.)学生们认为时间耽误太多,教育家们也一致反对,军训制度在1940年后徒具空名,既没有实际效用,又丧失军训尊严。
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基督教大学和政府政策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1939年教育部命令对专科以上学校行政组织进行改组,规定校长是行政首长,下面设三名负责官员: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学、课程和学术研究,总务长负责学校的财产、财务和经营,训导长负责学生的纪律和福利工作,实行官员负责制。基督教大学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多是部门委员会负责制,关系全校重大问题的政策一般由董事会或教员大会决定,而不仅是校长一人负责。但教育部要求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一律按此制度重组,这让很多基督教大学颇费踌躇。不过,他们还是表示要尽力去做。(注:Lincoln Dsang to Friends(April 22,1940).RG11-297-4625.)
国民政府的训育制度规定训导长必须是任大学教授两年以上的国民党党员,然后配以导师制。导师制名义上是仿效英国剑桥和牛津,但实际上却毫无共同之处,不仅未得其精髓,反而引起很多误解和争论。实行导师制的本意是为了改善过分注重知识传授,以言传身教来恢复道德教育的传统,规定导师应对学生言行负责,如果学生毕业后误入歧途,导师将受到谴责,这样导师制就沦为政府监督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手段,很多导师,特别是一些外籍教授对此极为反感,他们觉得在做这种有关学生的各种报告时,“感到就象做间谍”。(注:E.H.Cressy,Confidential Report on Conferenc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March 10,1941).RG11-005-108.)但有趣的是,战时燕京大学虽然处在沦陷区,但从1938年就开始积极试行国民政府要求的导师制,特由英国聘来两名导师襄助办理。(注:《基督教大学校闻》,《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第20页。)实际上,这套训育制度即使在大后方从来也没有学校认真实行过,教育部也承认是“无可讳言之失败”。(注:杜元载主编:《抗战时期教育》,《革命文献》第五十八辑,第214页。)究其原因,训导长大都难以负责,其学术声望和道德品行未必能引起学生的信仰,导师也不愿沦为“教育特务”,最终不了了之。
基督教大学传统的训育制度是靠校牧、师生团契来完成的,注重用耶稣基督的信仰和教授人格来感化学生。道德训练、人格培养一直是基督教大学在教育理念上的特别追求,也是其最擅长的领域。一位经常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美国人说:“我认为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诚实、道德和伦理标准。除了在基督教大学我没看到其他学校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一位在方威廉(William P.Fenn,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驻中国代表)看来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真正有社会关怀的商界领袖认为,通识教育比单纯的职业教育更重要。很多大学只注重职业教育,他以为基督教大学的人格养成是最好的,因此,他在招聘雇员时首先选基督教大学的教徒学生。(注:William P.Fenn,Two Comments on Christian Education,pp.1-2.RG11-8-186.)显然,基督教大学更愿从信仰的根基上培养学生人格,而不喜欢用秘密报告的方式。
战时基督教大学并非不能理解政府的教育政策,但他们普遍感到,这些政策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办学自由。对一向注重学术自由的基督教大学来说,这些限制不可避免引起它们的怨言,但正如华西协合校长张凌高所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所有限制都可以宽容。(注:William P.Fenn,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Chengdu,Szechwan,May 6-12,1943),p.2.RG11-8-187)基督教大学并非消极坐等,而是主动与政府对话,寻求解决之道。
三 与政府对话:追寻基督教教育的理想
基督教大学为谋求战后的发展,不得不再思基督教大学与一般大学在教育目标上的区别,并努力与政府对话,取得理解和支持。方威廉认为基督教教育和一般教育不同,也理应不同,“这些基督教大学如果满足于跟随其他学校的潮流,他们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注:William P.Fenn,The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d Face a New Year(Dec.30,1942).p.5.RG11-8-185)东吴校长杨永清认为,基督教大学应当为社会重建做贡献,究竟以何种形式服务社会应由基督教大学自己来决定,但现在的趋势是基督教大学什么样的任务都接,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中国的未来领导人。(注:William P.Fenn to Charles H.Corbett(May 27,1943),p.3.RG11-008-187.)
方威廉怀疑政府有把基督教大学纳入国立教育的计划,因为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其他人的讲话都体现出这种思想,他认为德威廉提出“基督教大学依靠政府是危险的”论点值得重视,尤其是面临战时经济困难,基督教大学急于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资助,而政府有时也特别大方这一形势,更应该注意这一点。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基督教大学在外汇汇率方面损失很大,国家特别给予基督教大学汇率比官方高一倍的优待,虽然并没有附带条件,但他们认为学校的发展一旦离开这些资助就会陷入困难,这意味着学校将受制于各种压力。为从经济上解决问题,方威廉提出,基督教大学的资金来源中,属于基督教会的部分应不低于51%。其实,他也很清楚,即使有51%也不足够,因为这不同于股份公司里的股票,一个失去49%收入的基督教大学如何能抵挡各种压力?因此他又认为非基督教的收入最多只能占20%。当然这些数字是粗略的,其意是原则上不要用政府太多补贴。(注:William P.Fenn to Charles H.Corbett(May 27,1943),p.4.RG11-008-187.)
关于和公立学校的竞争问题,方威廉认为在校产和人员上无法和它们竞争,即使联合起来也不济,应努力在一些擅长的领域内超过它们。基督教大学的国际性使它们在这方面很有竞争力。因此,方威廉以为基督教大学应当在课程设置上多一些实验,虽在政府的控制和标准化要求下并不容易,但加强某些学科是完全可能的。基督教大学将来的重点应放在人文学科,因为基督教大学总是愿意承担人们不愿意干的事情。他说:
当哲学很流行时我们开启了科学的教育,现在科学淡出了,我们再来做人文学科的开拓者,而且这也是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的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注:William P.Fenn to Charles H.Corbett(May 27,1943),p.4-5.RG11-008-187.)
基督教大学为谋求战后发展的方向,曾以各种渠道主动寻求与政府间的沟通,摸清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真实意图,也希望政府能理解他们在教育理念上的特别追求。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干事葛德基曾三次拜见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就教育政策对基督教大学的影响进行沟通。葛德基提到基督教中学对师资需求很大,问基督教大学能否在一个特别系科为想做教师的学生开设包括6-12个学分的教育背景和教学方法的专业,顾回答说已让高等教育司进行研究;葛德基认为课程规定普遍僵化,但顾认为有一些标准是必要的,差标准总比没有强;葛德基提出,对大型国立大学很合适的规章制度对基督教大学就有些困难,基督教大学规模都比较小,目的是为了人际交往和人格塑造,顾认为这很有道理,允许基督教大学建设某些很强的专业;关于导师制,葛德基问导师制的目的是否激起教员参与更多的学生活动,还是仅为教育部获取报告,顾认为导师制是想帮助学校让学生表现得更好一些,以便于学校控制;关于宗教选修课程,葛德基指出,由于其他功课的压力很大,以前曾选修宗教课程的学生现在也无法选修,而这关系到宗教自由和基督教大学的基督教特征,顾回答说如果他是大学的校长,他不会强调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课程,而是多进行直接的警告和教导,周一的纪念仪式可用于基督教的教导,还有月会,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全体学生都参加,而选修课程总是很少一部分人。实际上基督教大学校长们认为并不能在这些会上自由讲基督教的教义。(注:E.H.Cressy,Confidential Report on Can ference with the Ministry of Edncation(March 10,1941).RG11-005-108.)
葛德基和方卫廉、陈文渊主教在1943年9月11日曾再次与顾毓琇讨论基督教大学的未来发展问题。顾说教育部对基督教大学(尤其是在战后)的政策跟过去一样,否认教育部有把教育全盘国有化的想法,认为教育部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接管所有学校。当他们问及教育部对基督教大学的期望和要求时,他说教育部希望每个基督教大学发展一个或多个比较强的系科。(注:William P.Fenn to Charles H.Corbett(Sep.12,1943).RG11-8-189.)
齐鲁校长汤吉和在1943年春面见教育部长陈立夫,问及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政策时,陈回答相当含糊,但对具体问题回答很详细。陈希望基督教大学继续存在并发展,尤其是在技术培训领域,因为它们以往为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称赞了基督教大学在培养学生人格方面要比国立学校做得好,也批评了基督教大学学生多来自富裕家庭,不习惯艰苦的工作;他认为基督教的人格训练和三民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反对牧师偶尔在周一的总理纪念仪式上讲两句,导师也可以在课堂讲《圣经》;最后他说政府不会打扰基督教大学的工作,而是希望它们作得更好。汤认为这些谈话听起来像是给予很多自由,但政府仍有可能在战后限制基督教大学的工作。(注:William P.Fenn,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Chengdu,Szechwan,May 6-12,1943),p.1.RG11-8-187.)
方威廉认为这些对话非常有价值,他们对教育部的政策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为以后基督教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顾毓琇曾留学美国,是虔诚的基督徒,虽然顾是代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来讲话,但很显然,顾比陈对基督教教育有更多的了解和同情,这也难免让基督教教育工作者们认为顾是一个头脑清晰的思想家,而陈身上则更多一些政客的味道。(注:William P.Fenn to Charles H.Corbett(Sep.12,1943).RG11-8-189.)
为了确定基督教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于1943年5月6-12日在成都开会。汤吉和与陈立夫的谈话在大会上被充分讨论,最后确立了基督教大学应向政府争取的的五大自由:选择教员的自由、决定学生入学标准和人数的自由、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宪法规定的学术自由和在实验基础上修改政府课程的自由。大会通过了7项具体决议:
1.应当通过限制入学人数、恢复到战前规模的办法来维持教育的高效率;
2.军训官应具备讲师以上的资格,如果不具备,纪律和军事训练应分开进行;导师制应当和强,要有预算,减轻工作负荷并配备办公室;
3.基督教大学在制定课程方面应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学术自由;
4.基督教大学应重申其培养基督教运动领导人的宗旨;
5.在男女合校的基督教大学里应强调女子教育;
6.基督教大学中外教职员应待遇一致;
7.为中学培养教员应是基督教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注:Excerpts from Dr.Fenn's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at Chengdu,Szechwan(May 6-12,1943).pp.1-2.RG11-8-187)
这次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应如何与政府协商。华中韦卓民校长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知道政府想让我们做什么,或者告诉他们我们想做什么。齐鲁汤吉和认为第二个办法比较好,因为教育部并不清楚它需要什么。方威廉认为应向政府要求给予更多实验的自由,葛德基认为教育部应允许基督教大学选择一些特殊的任务,最后决定由在重庆的校长们去教育部协商。(注:William P.Fenn,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n Higher Education(Chengdu,Szechwan,May 6-12,1943),p.8.RG11-8-187.)
在战争最后几年,尽管基督教大学极力寻求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希望校正抗战以来发展方向上的偏差。然而,由于战争拖延、经济困难、士气低落以及学生对时局的反抗,政府几乎无暇回应基督教大学的要求,基督教大学的所有改革理想都难以付诸实践,只好寄希望于战后。但战后局势更加动荡不宁,早已制定好的战后计划也最终仅停留在纸上。
四 结语
概括而言,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在整个抗战时期的关系,较以往更为密切,合作更为广泛。这一方面反映了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中国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其表现出的国家忠诚和杰出服务赢得了政府的赞赏,政府也把基督教大学看做是中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关系也来源于国民政府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考虑。的确,在抗战时期,基督教大学在联结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但基督教大学与国民政府教育政策之间仍存在着一系列的紧张与矛盾,实质上是两者之间教育理念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教育自由的认识不同;一个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关于教育自由,这在当时基督教教育家的眼里是很敏感的话题,尽管战时基督教大学受到教育部统一课程标准的种种限制,他们也很清楚认识到,在当时中国不可能有美国式的那种教育自由,更何况,在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思想中,统一课程不仅关涉到教育,也是民族主义的体现,用他的话讲,所谓统一课程标准,就是要收回“文化租界”。(注: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转引自陶飞亚:〈文化民族主义中文化因素与非文化因素:国民党与‘反对文化侵略’初论〉,未刊论文稿,第10页。)战时基督教大学领导人对教育自由只能非常谨慎地同政府对话,但战后一部分外籍人士开始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只是“为了加强法西斯专政,不顾学术自由”,甚至认为由美国国务院以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改革教育建议是“合适的”,基督教学校应该有勇气向美国国务院和中国政府抗议,来影响这项基本的教育改革。(注:J.K.Choy,Proposed Educational Policy for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Confidential Memorandom,Oct.3,1945).p.2.RG11-240-3955.)通识教育和人格教育一向为基督教大学所倡导,但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大学面临着社会急需和政府统一课程的强大压力,她所秉持的这些教育理念受到专业教育的极大挑战。基督教大学的主持者仍坚信基督教大学教育与一般大学教育在目标上应有所不同,否则,基督教大学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正如沪江的葛德石(George B.Cressey)所说,中国一般其他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学生,但不一定强调要有卓越的品质,因此基督教大学必须在知识整合和培养学生的品格方面做到高标准。(注:George B.Cressey,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hina,p.6,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Professors,Vol.31,No.1,1945.)这正是基督教教育家们所希望追求的目标,也是很不容易达到的目标。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并非水火不容,但要求得两者之间发展平衡并非易事,事实上到今天,这个问题也仍在讨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