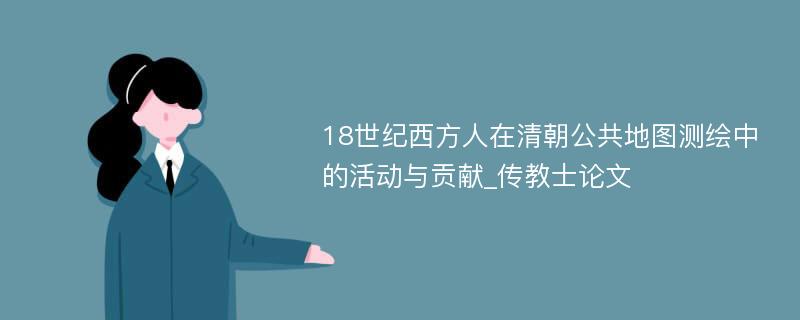
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舆图论文,清朝论文,贡献论文,世纪论文,西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地图中的活动
1.大一统清王朝的建立与清帝对舆图的重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虽政权更替,历有分合,但中华统一的国家却越来越巩固。到了清代,我国的疆土得到了最后的奠定。今天我国现有的领土和海域,基本上是继承清代的版图,这可以说是清朝的一大历史功绩。
清朝统治者对版图的管理十分重视。所谓“版”,就是记载人民户籍的档案。“图”是地图,是国家土地、山水的图记,所以历来版图被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要凭证。所谓“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1]清统治者深深认识到图籍的重要性,所以在入关之前就成立了文馆,重用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广为收罗明朝的图籍档案。
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后,经四十多年的统一战争,始建立起大一统的清王朝。清初虽在戎马倥偬之际,统治者仍不忘记收集明朝的图籍。顺治五年九月曾以纂修明史的名义,谕令京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提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有关明朝的档案“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2]。康熙四年十一月再次谕令礼部:“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查送。……其官民之家,如有开载明季时事之书,亦著送来,虽有忌讳之语,亦不治罪。尔部即行作速传谕行。”[3]根据皇帝的谕令,各地陆续收集到许多明朝的档案图籍,送交清廷,存于内阁大库。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千多件明朝内阁、兵部、礼部等国家机关的档案和图籍,基本上都是清初为修明史而搜集来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批明档中,有一批珍贵的明代地图,如《大明混一图》为万历年间绘制,纵347厘米、横453厘米,为当时最详细的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其幅页之大,绘制之精,居我国古地图之冠。清廷收存后,为体现其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将汉文地名统一用浮签换成满文地名,汉文“大明混一图”改为满文的"Dai Ming Gurun i Uherilehe Nirugan"。再如明万历年间刻制的《广舆图》、《论九州山镇川泽全图》以及明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进呈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也极为珍贵。
2.康雍乾三朝任用西洋人测绘舆图的活动
康熙帝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亲政后,先后平定了“三藩”和统一了台湾,接着又领导了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他三次亲征,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阴谋,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他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任用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任钦天监官员修订历法,又聘请学有专长的传教士入宫任职,或在内阁充当翻译;或在内府任职医生、画师;或为皇帝、皇子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康熙帝亲自学习,孜孜不倦,他演算的几何算草,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康熙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地图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在使用地图中也发现不少问题,如有的地图模糊不清;有的测绘不精,内容有错,等等。他深感“疆域错纷,幅员辽阔,方舆地理,又今昔互异”。今后要想治理全国,没有详细而准确的地舆图志,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结束平定三藩和台湾的战争后不久,于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便下令纂修《大清一统志》:“务求采搜闳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成地图。万几之暇,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慎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4]
康熙帝在战争和外出巡视活动中,还非常注意地理的调研和测绘。如康熙三十五年他在亲征噶尔丹行军途中,所记的测量独石口至喀伦的情况:“自独石口至喀伦,以绳量之有八百里,较向日行人所量之数日见短少。自京师至独石口为路甚近,约计不过四百二十三里。皇太子可试使人量之。喀伦地方用仪器测验北极高度,比京师高五度。以此度之,里数乃一千二百五十里……。”[5]又如,康熙三十六年间三月他在回军途中,记录了在宁夏测量的情况:“朕至此以仪器测量北极,较京师低一度二十分,东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今安多以法推算,言日食九分四十六秒,日食之日晴明测验之,食九分三十几秒,并未至昏暗见星。自宁夏视京师在正东而微北……”。[6]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康熙帝命进有关地图呈览。当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张诚乘机把早已绘好的亚洲地图送上,并指图说明中国的东北部分地区,因地理知识缺乏无法绘制,请求皇帝进行一次全国大地测量。康熙帝认为很有必要。
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来华传教,沿途细察各省地图,发现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地不符甚多,他将此事上奏康熙皇帝,再次建议重新测绘全国各省地图,这就更加坚定了康熙皇帝测绘全国省级新图的决心。于是命白晋返回法国,又挑选十几位精通天文、地理和数学的教士来华,参加皇朝地图的测绘工作。由于这次绘图准备使用西方经纬度制图法绘制,为了慎重从事,康熙皇帝于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命白晋等传教士先在北京附近进行小块试验性的测量,以与旧图相比较。经半年的努力,地图绘制完工,上呈康熙帝。“帝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7]。这样才开始测绘各省地图。这次测绘,康熙帝除聘用外国传教士外,还命中国有关官员、精通算法人员和钦天监等有关机构人员,共同到各地进行测量。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708年6月4日)命法国传教士白晋(Bouvet)、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和日耳曼神甫费隐(fridelli),从长城测起,至次年一月返回北京,绘成一图。该图上绘有长城三百个门口、堡垒以及附近城寨、河谷、水流、山岗等。至于北直隶(今河北省)的测绘,因先在北京附近试测,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便开始,到四十七年(1708年)六月完成。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五月十八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诸人开始测量东北地区。先从辽东入手,东南到朝鲜边境,东北到黑龙江口。测绘了《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热河图》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七月康熙帝命再前进到黑龙江地区,对新建边镇墨尔根(今嫩江县)和齐齐哈尔(今龙江县)二镇进行重点测量,于当年十二月完成了东北地图的测绘工作。图送至北京后,因“鸭绿、图门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公元1711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8]
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命增加测绘人员,分成两队,一队往山东,主要有雷孝思、麦大成(Cordoso,葡萄牙人)等。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绘成山东省图。一队出长城测定喀尔喀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人员有杜德美、费隐及潘如(Boujour,法兰西人)等,该队在蒙古测量后,途经陕西、山西,于康熙五十一年回到北京,但图未能完成。又命麦大成、汤尚贤(de Tartre法兰西人)同往山西、陕西(当时陕西包括今甘肃省)协助测绘工作。图成以后,康熙帝甚喜。以后雷孝思又同冯秉正(De Mailla)及肯特雷(Kenderer),同往河南、江南(江苏和安徽)、浙江及福建(包括台湾)测绘。汤尚贤、麦大成合测了江西、广东及广西。费隐及潘如、雷孝思又测绘了四川、云南、贵州和湖广的地图。由于康熙帝亲自主持这次测绘工作,并随时发布谕旨,命各地方督抚很好组织本地的测绘活动,并招待、保护好西洋测绘人员等,所以测绘工作进展很顺利。如江南、河南地图于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测绘完毕,遵旨随时报上。据江宁巡抚张伯行奏:“康熙五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准兵部咨,奉旨往河南、江南画舆图去的宫拜唐阿、西洋人不必回来,就从彼处往浙江舟山等处、福建台湾等处画去。但走海时,着你等谨慎。看好天色时节行走,不必急了,须要仔细。再,下旨与他们,伊等著画完一省将舆图就交与该抚,着家人好生送来,钦此。臣查江南、河南舆图已经钦差护军参领臣陶蕃齐等经临各府、州、县丈量绘画,起程北上。……于闰五月初八日抵苏,准护军参领臣陶蕃齐等将所画江南、河南舆图于初九日交臣恭进。现催江南驿道换给勘牌,前往浙、闽二省绘画舆图。……臣谨遵旨将所画江南、河南舆图,差家人谨慎赍捧赴京进呈”。[9]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浙江巡抚王度昭奏报,浙江省地图绘完送上。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江西巡抚佟国勷奏报,李秉忠及西洋人麦大成、汤尚贤等所绘江西统省舆图告成送上。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报,武英殿监督布尔赛、西洋人费隐等“于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由四川北界保宁府属之广元县画起,于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十日至东川府画完川省全图。即将全图交与臣家人魏之辉收存。布尔赛等随由东川入滇画图去讫。”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十七时,江西巡抚佟国勷奏报,江西省图绘完送上。
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云南巡抚甘国璧奏报,西洋人费隐、雷孝思及武英殿监督常保等绘画的云南舆图画完,遵旨差家人送京呈览。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贵州巡抚刘荫枢奏报:“钦差绘画舆图大人、西洋历法雷孝思、西洋历法费隐、向导护军参领英珠……于十月三十日将贵州舆图画毕,赍送到臣。臣谨遴选家人兼程赍送来京进呈御览。”[10]至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一月除新疆及西藏部分外,测量工作全部完竣。各路测绘人员回京后,在杜德美的领导下,编绘完毕关内十五省及关外蒙古各地地图,取名《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进呈皇帝。帝重加嘉奖,并命内阁学士蒋廷锡示谕群臣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以此与九卿详阅,如有不合处,九卿有知者,举出奏明”。[11]稍后九卿回奏:“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此图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钜观。”
《皇舆全览图》从康熙四十七年正式开测,到康熙五十七年完工,历时十年。所反映的疆域为东北至萨哈连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在十八世纪初叶,进行如此全国范围大面积的实地测绘图工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亚洲也可谓是一个创举。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于1722年去世。继位的是雍正皇帝。雍正帝对传教士采取严厉的态度,也没有继续聘用西洋人进行绘图工作。不过他为了指挥对西北用兵作战和管理改土归流后的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命怡亲王允祥等组织皇朝有关绘图人员,绘制了皇舆十排图(后称《雍正皇舆十排全图》)。雍正十排图采用以北京为经、纬线中心的方格绘法,这不如康熙图实地测量投影绘法科学。但在舆地的幅员广袤方面,雍正图却大大超过了康熙图。该图北起北冰洋,南到中国南海,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
乾隆帝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虽然继续执行乃父的禁教政策,但他却仿效乃祖的做法,大胆使用西洋各类专门人才,为皇朝服务。他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先后聘用西洋人高慎思、宋君荣、蒋友仁等人,会同中国官员和测绘人员,完成了康熙时期没有完成的对新疆和西藏地图的测绘工作。康熙时期清朝的统治势力犹未控制全新疆,到了乾隆时代,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和回疆,才有可能测绘新疆的地图。乾隆帝先后派西洋人高慎思、傅作霖、宋君荣及何国宗等专门人员,到新疆随同军队进行测绘工作。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上谕刘统勋会同何国宗前往,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谘询者记,得自身所经历汇为一集。”[12]乾隆帝对有功的中外测绘人员,随时给予晋级加俸,如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同左都御史何国宗前往伊犁等处测量之监副傅作霖,著赏给三品职衔。西洋人高慎思,著赏给四品职衔。俱准照衔食俸,其马匹廪给亦即照衔支给。钦此。”[13]
将近一年的测量绘图工作完竣后,乾隆帝命何国宗及西洋人回京。“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命何国宗等赴伊犁测量并绘舆图。今大段形势皆已图画,其余处所可以从容再往,是此等已属完竣。何国宗及西洋人等现已回到肃州闲住无事,可即令其乘驿来京,著传谕遵行。钦此。”[14]
关于这次绘图的情况,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允禄、傅恒的奏折讲得很清楚:“臣允禄、臣傅恒等谨奏。钦惟我皇上德威遐播,武功大成。五年之间,辟地二万余里。准噶尔、哈萨克、布鲁特及诸回部尽归。特命何国宗、明安图暨西洋人傅作霖等前往测量绘图。复命臣允禄会同查办,入时宪书,永光钜典。臣等伏查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命臣允禄,监制地球,维时准噶尔回部尚在版图之外。今皇上疆圉式廓,臣允禄、臣傅恒等公同商酌,请将地球添画新辟土宇,以成昭代典章。再查内庭尚有铜板、木板地图,其间或有阙略,参差未能画一,并请敕令各该处查出。臣等率同何国宗、明安图、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等细心查办,稍有纤疑,再与亲在军前诸臣,细加斟酌,务期允协。办成恭呈御览,伏候钦定。为此谨奏请旨。”[15]
刘统勋、何国宗、高慎思等人绘的《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六月绘成,奉旨交军机处方略馆,这是以后一切新疆地图的根据。以后乾隆帝又专派一批总裁、提调、纂修等官去纂修,经二十年之久,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才完成《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朝在平息了颇罗鼐子朱尔墨特妄图割据西藏的叛乱后,命测绘人员对西藏地图重新实测,绘制了新的西藏地图。这样在康熙图的基础上,加上实地测绘的西藏、新疆地图,使得全国实地测绘的新图——《乾隆十三排地图》得以完成。《乾隆十三排图》又叫《乾隆内府地图》。全图共一百零四块,图幅范围基本上和雍正图相似,北尽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不仅为我国最完整的实测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为了宣扬这一成就,使其留传后世,“皇上又令在朝修士,将大清一统地舆,及沿革之疆域,加工绘成图册,令蒋友仁镌为铜板。友仁遵旨刊刻,刊成铜板一百零四片,每片刷印百张。”[16]这一百零四块铜板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乾隆帝在看到成图后,曾题诗二首,以表达他喜悦的心情:“括地多年仰圣猷,核真今复逮渠搜。闳誇讵类参军注,厄塞应同主吏收。益切觐光周诰凛,匪关凿空汉臣求,宇安岁美吾恒愿,望蜀宁当意更留。乾隆丙子夏六月御题。”“敢云扩宇蒇前猷,偃伯从兹罢剿搜。厄鲁马牛无一牧,筠冲屯堡并全收。本朝文轨期同奉,昧谷寒喧重细求,无外皇清王道坦,披图奕叶慎贻留。庚辰秋八月叠前韵再题。”[17]
为纪念乾隆帝在平定准噶尔与回部叛乱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乾隆三十年(1765年)由西洋人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和安德义等人合作特绘一份“得胜图”共十六幅,献给清廷。乾隆帝令郎世宁等将其带往欧洲,镌刻于铜板上。后在法国镌版印制,再运回北京。
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乾隆九年(1744年)来华,1745年到京,为清廷效力三十余年,主要为皇帝装饰宫廷,曾在圆明园设计大水法等。特别是乾隆帝五十岁寿辰时,他进献了一幅《坤舆全图》。据舆图房存乾隆二十九年福隆安续办归类舆图档中记载:“舆图房陆续收存图三十七件。蒋友仁进坤舆全图一张。”《坤舆全图》是蒋友仁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南怀仁《坤舆全图》为基础,又增补了“新辟西域诸图”而成的。该图为东西两半球图,左边是西半球图,上绘亚墨利加州。右为东半球图,上绘亚细亚洲、利末亚洲、欧逻巴洲。在图的上方有文字说明,它详细介绍了四大洲的疆域,如“亚细亚州,天下第一大州。乃人类肇生之地,圣贤迭出之乡。其界东至大东洋;南至赤道南约第十度;西至红海、地中海、黑河、同河、白海;北至冰海。所容国土不啻百余,其大者首推中国,声名文物礼乐政教远近所宗……”。[18]图中的中国疆域部分,明确绘出了乾隆二十四年清廷粉碎大小和卓的叛乱、平定回疆后的西域名称,如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塔什干、阿克苏等等。除两半球图外,蒋友仁还在图的四周绘制了天文地理学内容的插图和文字说明。在这些图、文中,明确阐述了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介绍了正确的刻卜勒三定律和一些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如说“歌白尼置太阳于宇宙中心”、“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地球为椭圆形,围绕太阳转”[19]等等。蒋友仁为第一次向中国全面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人。
这幅图进呈乾隆帝后,帝仔细审阅,并于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命“庄亲王会同何国宗认为如有不对之处,即传问蒋友仁。”经过仔细察看研究,庄亲王允禄等复奏皇帝道:“臣等看得蒋友仁坤舆全图一卷与内庭地球天主堂内坤舆全图形势大概相同,其绘画亦甚详细。惟俄罗斯往东较旧图展开四十余度。北亚墨里加往西亦展开五十余度,皆系旧图所无。询据蒋友仁云,旧图系康熙年间西洋人南怀仁所作,彼时无人测量未入舆图。乾隆六年有西洋人李勒等测量至其地,是以新图添入等语。询据刘松龄等皆与蒋友仁所说同。惟伊犁回部等处山水形势较之明安图、傅作霖等所画新图微有不合。询据蒋友仁云,此图系按伊犁旧图山水形势绘画,今应改正等语。臣等将伊犁回部等处另绘小图签入,其应改之处用红色绘画,恭呈御览。伏候命下,臣等遵即改正。其图说一卷,皆系西洋旧说。西洋人戴进贤等重修考成后编,亦用其法。但文义间有未能明顺雅驯之处,请一并交发。臣等率同武英殿修书翰林等,量加修饰妥协,再行恭呈御览。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帝阅折后,批答道:“是。着另画一张,派好中书缮写。”[20]乾隆三十六年《坤舆全图》修改增绘完毕,献给乾隆帝,帝大悦,特意嘉奖参与中外有关人士。这两幅《坤舆全图》都存于内务府的舆图房,备皇帝随时阅览。后一幅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一份世界地图。
二、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地图中的贡献
十八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当时大批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一方面,他们来华是为了传播和发展天主教。另一方面,他们也把欧洲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药、生理解剖学、机械学以及各种技艺带到中国。尤其是西方传教士传播了先进天文地理观念,并运用先进的测绘制图方法,帮助清政府实地测绘了皇舆全图,这是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最大贡献之一。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是我国首次经实地测绘而成的全国地图。在十八世纪初叶,进行如此全国范围大面积实地测绘地图的工作,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而且在亚洲也是一个创举。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他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这些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美。”这表明“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
当时的中国在制图学方面所以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这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和新的绘图方法是分不开的。
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学说在华传播,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中国历来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居天地之中,四周都是藩属蛮夷。在中国,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自称授命于天,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故又称天子。天子统驭华夏,抚绥万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和南怀仁、蒋友仁的《坤舆全图》,逐步在中国传播后,中国的开明绅士开始改变天圆地方的观念,认识到地球为椭圆形,感到画图必须实地测量经纬度。康熙帝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君主。他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地理观念,决定用西洋人测量经纬度绘制皇朝舆图。及至乾隆时期,蒋友仁借着向皇帝献《坤舆全图》机会,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这些新的天文地理学说,无疑对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是一次巨大的推动,也是清政府采用新方法绘制皇朝舆图的一个前提。
西方传教士带来了三角测量绘图的新方法。所谓三角测量法,是在地面上按一定条件选定一系列点,构成许多相互联接的三角形,然后在已知点观察各方向间的水平角,并精确地测定其始边长,以此边长为基准线,推算其它各点的经纬度座标。法国传教士杜赫德说:“从教士根据他(指康熙帝)的旨意绘成的北京地区地图中,皇上发觉欧洲的测绘方法精度很高,乃决议以同样方法测全国各省包括所属之全部鞑靼地区”。[21]
采用三角测量方法,必须在天文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所以第一步先用天文观察方法测出一部分点的经度。如雷孝思、杜德美观察测定凉州为西经13°43′56″。巴多明观察测定热河为东经1°30′,纬度为41°6′。哥波尔观察测定广州为西经4°00′11″,纬度为23°8′,等等。第二步是以天文观测的点为基本点,然后采用三角测量法推算其它点的经纬度。西方传教士在绘皇朝舆图时,还采用了桑逊投影法,以及边疆与内地的地名采用满、汉文分别记注的方法。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制图方法。
在这次测绘舆图时,还统一了丈量尺度。由于我国历史上尺度的长短不太一致,从而造成地图制作的差误较大。康熙帝根据西洋传教士实际测量的结果,规定以当时工部营造尺为标准,合一千八百尺即一百八十丈为一里,也就是每尺合经线百分之一秒。测量长度单位的统一,是中国测绘史上一个进步。另外,把长度单位与地球经线每度的弧长联系起来,这在当时世界上是一个创举。
康乾盛世时期所以能绘出当时世界一流的中外地图,除了西洋传教士带来的先进测绘方法和绘图技术以外,这和传教士们的奉献精神及他们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据清宫档案记载当时参加这一测绘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先后廿多人。在康熙时有张诚(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法国耶稣会士)、杜德美(法国耶稣会士)、麦大成(葡萄牙人)、汤尚贤(法兰西人)、潘如(法兰西人)、费隐(日尔曼传教士)、马侠、肯特雷等等。各省舆图测绘之后,最后由杜德美汇集成册。在乾隆时,有高慎思、宋君荣(法国耶稣会士)、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蒋友仁(法国耶稣会士),等等。
在西藏、新疆地图测绘完成之后,由蒋友仁等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基础上,汇编成《乾隆十三排地图》,并将中国测绘地图的新成果,绘入《坤舆全图》,进献给乾隆皇帝。
在中国如此广阔的国土上,进行史无前例如此大规模的测绘活动,其困难是可以想像的。正如始终如一参加这一测绘活动的雷孝思神甫所说:“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警惕之处多得不胜枚举。皇上把对他的帝国至关紧要的任务委派给我们,为了不辜负这位贤明君主的信任,同时也希望求得皇上的庇护,这对要在他的帝国里弘大基督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信念驱使我们跨越了在从事如此浩繁的工作中所不可避免的种种艰难险阻。我们出于至诚,甘之若饴,自愿继续在帝国的东西边境和相隔适当距离的若干地点,反复进行日食观测,测定经度,以校正绘好的地图。”[22]
传教士在测绘活动中,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正如雷孝思以全体传教士的名义,在给巴黎杜赫德神甫的报告中说:“我向你们保证,为使地图尽可能完善,我们已使尽一切手段。我们亲自走遍各省各地,包括那些很次要的地点,查阅了各地官府所藏的舆图和史书,询问了所经各地的官吏和耆老缙绅。”[23]为了使地图精益求精,神父们对于已绘好的地图,还要反复测量校正。
在艰苦的测绘活动中,由于水土不服和劳累的关系,有的神甫病倒了;有的神甫带病坚持工作;有的神甫甚至牺牲了生命。如康熙四十七年,在测绘刚开始两个月,白晋神甫由于劳累病倒了。病稍愈后他又继续工作。康熙五十四年,费隐神甫在测绘云南地图时累病了,但继续坚持工作,一直到测绘完云南地图为止。张诚神甫到张家口附近测量时,到白河某支流源头,突然累倒了,不停地恶心和呕吐,生命处于危急之中。他以为很快就要死去,写了遗书。后幸被出使蒙古的一位官员抢救了他的生命。
特别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他于乾隆十年(1745)五月来华到京,于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病故,在华三十多年。他不仅设计修造了圆明园大水法,而且为乾隆时皇舆地图和战图的编绘及刊刻印刷,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他参加汇编了《乾隆十三排图》,图成之后他又将图稿运往法国,刊刻成铜板印刷。乾隆三十年西洋人郎世宁等所绘平定准噶尔、回部等处《得胜图》完成后,遵照皇帝的谕指,“蒋友仁将图寄至法国刊板。法国皇上类思第十五位,自颁库银,令本国巧匠名高山者,刻成铜板,赍回中朝。蒋友仁刷印二百张。复将印稿连板寄回法国以便改良。乾隆三十七年,洋历十二月,由法国先寄回改板七片。皇上即命蒋友仁试印。友仁刷印若干张,忽患呕血,十分危急。仅得预备善终之暇,虔领终礼而卒。时乾隆三十九年,降生后1774年,洋历10月13日也。皇上赐帑银百两助葬。”[24]
蒋友仁为了在中国传教,为了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来华三十多年来,可以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最后累死在刊印清朝的舆图工作中,他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三。
[2]《顺治实录》卷四十。
[3]《康熙实录》卷六十。
[4]《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四。
[5]《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九。
[6]《康熙御制文集》二集、卷二十四。
[7]《清史稿·何国宗传》。
[8]《清史稿·何国宗传》。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
[10]以上均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
[11]《清史稿·何国宗传》。
[12]《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
[13]《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
[14]《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
[16]《燕京开教略》中篇。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十三排图》。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蒋友仁绘呈《坤舆全图》。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蒋友仁绘呈《坤舆全图》。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档案。
[21]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
[22]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
[23]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记事》。
[24]《燕京开教略》中篇。
标签:传教士论文; 清朝论文; 我在大清当皇帝论文; 测绘仪器论文; 西洋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测绘论文; 康熙帝论文; 蒋友仁论文; 雷孝思论文; 乾隆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