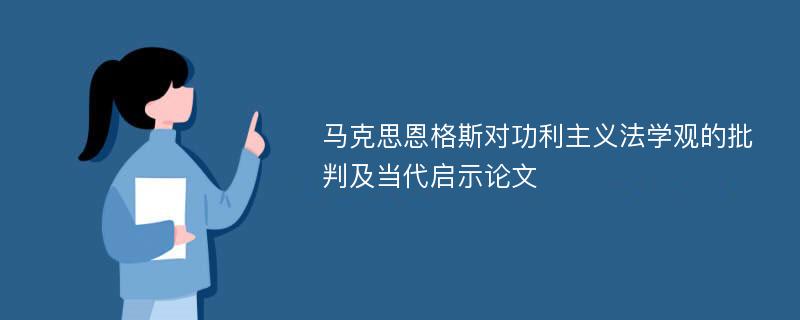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徐 晓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 要: 功利主义的目的是实现人的最大幸福,避免痛苦,与经验主义的方法有紧密的关系。它重视研究和识别人的行为,坚信人们可以认识行为的趋向。功利主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法律观,为人们认识法律现象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功利主义对法律现象产生的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历史意义,同时从本质、方法、价值三个角度揭示了它的历史局限,指出功利主义法学观依然未能超越时代赋予它们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的三重批判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重视经验,但要警惕对经验的过度迷恋。对法律现象的认识,既要充分重视经验,又要注重抽象力,辩证地分析中国的法治建设,积极构建我国的法治话语体系。
关键词: 功利主义;经验论;道德哲学;法学观
自19世纪以来,功利主义一度成为占据西方哲学顶端的思想流派,深刻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政治观、道德观与法律观,直接导致了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催生出奥斯丁、边沁等一批法学家,且一直主导着西方的立法与司法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被重视且容易被误解的领域。尽管学界重视功利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的重要影响,甚至一些学者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本质上来说可以归于功利主义这一学派,但鲜有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讨论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功利主义对法学的影响是深刻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功利主义法学观,也深受其影响,在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功绩的基础上,极为深刻地揭示了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本质,并对其进行多层次的批判。这无疑对我们认识法的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界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一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归于功利主义,认为他们提出的生产力发展的标准实质上就是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总福利,因此他们在本质上也是属于功利主义流派的[1]。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学术名称体系,但实质上与功利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2]。虽然这一观点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因而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就引起了第二个影响较大的观点,即“超越论”。它认为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有着较强的功利主义倾向,然而随着他们思想的发展,逐渐认识到功利主义哲学的本质,超越功利主义也逐渐成为必然[3]。然而,这种超越是怎样的,是如何完成的,学界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利益说”,它把功利主义等同于利益,不过此利益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阶级利益[4]。它不仅比较成功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还指出所谓的超越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去认识、评价功利主义的本质,进而提出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就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概言之,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关系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且呈现出层层递进、逐渐精细化的态势。不仅如此,这些研究实际上也隐含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法学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法学观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未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首先,它关系到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哲学前提和方法基础——经验主义的问题,或者说通过法学的视角,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论述经验主义在认识法的现象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限度的。喻中教授曾以恩格斯的《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为研究文本,详细阐述了“恩格斯采用了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恩格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现实中的宪法图景”[5],并指出这种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次,功利主义与法学之间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边沁、密尔等人的著作中得到证明。总之,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在深化对功利主义的认识上,还是在发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当代启示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进一步关注。
一、功利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法律理论的影响
宣告功利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6]。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这场由蒸汽机开启的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近代工厂制度的诞生,使资产阶级在英国确立统治地位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同时也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使各个领域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功利主义的兴起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一以ODIS-E工程师软件为例,详细介绍对“44-动力转向”进行手动编码的具体步骤。使用ODIS诊断系统同理,操作基本一致。
(一)功利主义的两个基本内容
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功利主义虽然有“利”,但不是关于利益的哲学,不是一门如何获取最大化利益的科学,而是一门道德哲学[7]。这就把功利主义纳入了“善”“正义”等传统的哲学谱系之中,只不过更强调可识别的人的行为,认为人可以把对“善”“正义”等的认识限制在可见的范围内,摒弃模糊不清的上帝法、自然法等。功利主义不仅通过这种理论尝试把自己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脉络,而且还启发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基本命题。功利主义主要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从目的上来看,它是为了实现人的最大幸福,避免痛苦,把其他的一切都看作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从方法上来看,功利主义与经验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它重视研究和识别人的行为,坚信人们可以认识行为的趋向,即人类能够分辨出什么是有害的行为、什么是有益的行为,并且认为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感觉把行为规则化。
功利主义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其具体内容不限于以上两个方面。但是追求最大幸福的目的与坚持以经验论为基础性研究方法是功利主义的两个最典型、最基本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在功利主义出现之前,“道德哲学对幸福或效用的判断是基于上帝的意志或者所谓灵魂的状态”[12],功利主义改变了这一状况,指出人类的幸福不能建立在这样虚无缥缈的基础上,应该另寻一个坚实的基础——功利主义原则。此后,功利主义据此开始赢得声誉,并且在思想史上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功利主义之后的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等亦遵循经验研究的范式,但在道德哲学的观点上与功利主义大相径庭。
功利主义与经验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功利主义深受经验论的影响。边沁看过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人性论》后,“顿时感到眼睛被擦亮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第一次学会了把人类的事业叫做善德的事业”[9]149。并就此开启了告别“原始契约”论并探索功利原则之路。不仅如此,边沁还致力于探求一种清晰的、准确的数学方法,以求把功利原则发展为一种具有无可争辩性质的科学[11]。边沁之后,密尔、奥斯丁、哈特等人虽然修改、完善了边沁的某些观点,但总的来说依然坚持从经验出发的基本观点,遵循经验研究的基本方法。
具体而言,功利主义在目的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功利主义致力于促进人类的幸福,“功利逻辑在于在一切判断过程中都坚定地从痛苦和快乐的计算或比较出发,以及不允许任何其他观念的干扰”[8]58。功利主义的开创者边沁在不断的研究中,逐渐发现了“功利”一词不能完全表达出功利主义的根本目的,转而用“最大幸福原则”的表达替代了“功利”一词。这可以充分证明功利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幸福观。利益虽然与功利有紧密的联系,但并不能代表促进人类幸福的全部内容,它只是其中之一。其次功利主义在对人类幸福的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至少它给人提供了一个可以依赖的、相对确定的切入点。就像边沁所说的那样,“人类不可毁灭的特权不需要建立在幻想的不稳固的基础上”[9]149。尽管后世的批评者总会指责这一点,认为我们的行为并不是理解、实践幸福的最佳方式,因为它会使人走向极端的邪恶。最后功利主义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发现,它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与古希腊时期的幸福观、善论是一脉相承的。功利主义的优势就在于利用一个比较清晰、可靠的标准来衡量与促进人类的幸福。有学者将边沁称为客观功利主义的开创者[10],这些都与功利主义的方法论密切相关。
(二)功利主义对法律理论的影响
作为一种道德哲学的功利主义,它不仅用新思维、新方法诠释了幸福与善等命题,而且还逐渐转向依靠规则增进人类幸福的研究进路。功利主义在兴起之时,就已经对当时的法律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极大地启迪了葛德文、密尔、奥斯丁、哈特等人的研究,使法学研究出现了富勒所说的“英语世界中的法律哲学基本上是被奥斯丁等人的传统主宰着”的局面[13]。
我们岭北人是有感情的,这一天知道驮子要离开我们村,很多人都来帮忙搬东西装车拉绳子,然后目送他们离去。大家都说,你们要回来噢要回来噢,我们要想你们的。
首先,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法律理论开始逐渐明确自身的研究范围,为摆脱神学、哲学、伦理学等母胚奠定了基础。在功利主义出现之前,法学虽有发展,但依然难逃“婢女”的地位。把法理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尝试肇始于奥斯丁,他希望能够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的科学的范围,企图改变法学中“语词的割据”,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14]。奥斯丁不仅提出了这一任务,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奥斯丁由此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他在《法理学的范围》中曾花费了大量的篇幅阐释功利主义,回应一些理论家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对边沁试图把法学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的做法深表赞同,并继续拓宽这一思路。边沁同样表现出了对法律的浓厚兴趣,在实践中受阻后,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研究中,完成了多项法学著述的创作,坚持把功利主义原理作为批判现存法律制度及支持社会改革的准则[8]3。
其次,功利主义重视研究人的行为,认为人可以通过常识判断出行为的趋向,并且判断哪些行为是促进幸福的、哪些行为是导致痛苦的,指出人总会趋向幸福,远离痛苦。它要求人们要通过道德直觉和生活常识,自觉遵守道德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幸福。尽管不同的功利主义者有不同的偏向,如边沁更重视人的行为,而奥斯丁与哈特可能对规则更感兴趣,但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把人的行为作为基础。这一点恰好使对法的考察有了某种“客观性”,也使人们对法的认识具有了相对确定的依据。边沁以后的追随者及受其启发者对此非常重视。
然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英国人听从经验、反对人类超越自己理解力的范围去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也逐渐影响到了经济、道德、国家与法。在恩格斯看来:“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15]105”而边沁与葛德文同时在英国提出了功利主义,把公共福利作为最高的原则与法,“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15]105。而这些实质上就是经验论在伦理道德以及法哲学领域内的具体表现和必然展开。马克思恩格斯深受影响,并且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完整的社会史。不仅如此,在他们之后的研究中,也十分重视经验,运用其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一文中,就充分利用了纯粹经验研究的方法揭露、批判英国的法治状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强调“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15]111。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十分重视经验材料的搜集,重视经验的作用。功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内容,一个是在目的上以重新解释、塑造道德哲学(包括法哲学)为使命,另一个是在方法上坚持经验主义。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二、马克思恩格斯与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历史际遇
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位于静安区的一条热闹的街道。与街道的烟火气相得益彰,上海印协走出了一条特色独具的“亲民”路线。
与其他法学流派相似,功利主义法学派在发现某些原则之后也非常兴奋,庆幸自己得到了解释某些问题的密钥。他们对目前的状况也极为不满,希望运用自己的原则和方法,改善当前的社会状况,比如边沁就曾致力于立法的改革,曾尝试发现“一套从形式(亦即方法和术语)方面考虑在所有分支领域完整无缺的法律体系梗概……其阐述囊括了所有可以恰当地说属于普遍法学这一总题的内容”[8]53。所以,“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7]20。可是他们所进行的改革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最后法律被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法律,法律的“永恒正义”“确定基础”“普遍法学”等也终究不能超越时代给予他们的限制。
最后,功利主义的方法同样对法律理论产生了影响。边沁曾花费大量的精力,试图把法律变成一门像物理学那样确定、明晰的科学,他醉心于“对有效原因或手段的快乐和痛苦本身及其分类、影响因素、计算方法等做了详尽的分析”[11],希望能获得一种精确的计算术。这一做法虽然遭到了很多批评,但它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至少它为确定法律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法律开始逐渐摆脱模糊不清的状态。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形成的初期,希望通过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揭示真理、改变现实。当时,康德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无政府主义、历史法学派、费尔巴哈派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等多种学派交织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对每个学派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虽然也曾先后认同和追随过一些思想流派,但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问题,尤其随着林木盗窃问题、普鲁士书报审查制度等社会现实的刺激,他们的思考更加深入了。此时正值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转变。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接触到功利主义法学观并受其影响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在充分肯定它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它的反思与批判。与边沁的追随者们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继承与发展边沁思想中的法律规则论,而这些追随者们逐渐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相融合,形成实证分析法学派,逐渐淡化了道德哲学的色彩,更多地关注法律技术与思维层面的知识。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法律与人的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法律与物质利益的关系,但他们终究将法律的认识置于更为宏观的社会发展中。他们把现实个人的活动作为全部哲学的根基,并据此构建了唯物史观。具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批判有如下的呈现。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本质的批判
功利主义者试图把自己纳入道德哲学的谱系中,且将“善”“正义”等问题的研究与人类的经验紧密联系起来,使人们对道德哲学的理解有了新的思路。这确实是功利主义的理论价值。功利主义法学观把功利原则作为立法的重要根基,并构想出一个比较系统的立法技术体系。边沁尤为重视功利主义原则在法律中的运用,并极大地启示了后世的追随者。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意识到了功利主义法学观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了它的本质。
功利主义法学观把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作为最根本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书写了一部真正的英国社会史,而且造就了一个被称赞为“英国理性的最完善的产物”——英国宪法,因为英国人认为它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因而它的基础是稳固的,是三千多年的法律实践的经验凝结。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评价经验的研究方法,指出这也是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的原因之一。
猪丹毒病发生后可根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病理变化等作出初步诊断。注意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的鉴别诊断,有条件的最好进行细菌检查和血清学反应等加以确诊。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研究方法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本质是利益的统治。他们在考察英国工业革命史的基础上,逐步勾勒出一幅现代工厂制度取代传统手工业的画面,进而指出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典型的国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最明显、斗争最激烈的国家。他们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最明显、最具意义的结果是利益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原子式绝对对立的状态。为了避免社会在巨大的冲突中遭受损失,国家与法律才成为必要。在利益成为统治者的地方和时代,一切都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包括婚姻、亲情等。财产成了国家与法律的本质。恩格斯在详细考察英国总体状态的基础上,指出既不是英国国王,也不是贵族和下议院统治着英国,真正统治英国的是财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功利主义原则产生于英国也是必然的。恩格斯指出,尽管功利主义者(主要是指葛德文与边沁)认为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律原则,一切的立法都要以此为依据,但他们没有真正解决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争端。当陷入二者的对立中时,他们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是把单个利益作为最高的立法原则,“最初他说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就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15]106。因此,功利主义法学观实质上就是依据财产的规律进行立法,用物的方式和原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这并没有解决矛盾,而且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经验的研究方法始终与具体的语境密不可分,他们在肯定经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对它存在的问题高度关注。当时身处英国的青年恩格斯,一直在通过亲身观察或者搜集各种官方报告详细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真实状况,了解英国真实的法律实施状况,尽管恩格斯也称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为纯粹经验的研究方法,但恩格斯在《英国宪法》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就先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好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他对纯粹经验的方法所持有的警惕。“先用”是恩格斯批判纯粹经验的方法的第一步,不仅说明了他要用经验主义者的“矛”去攻击它的“盾”,还为今后进一步展开的批判埋下了伏笔。恩格斯揭示了被欧洲所羡慕的、让英国人自己都非常自豪的法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尽管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宪法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是三千年政治与法律实践经验的重要体现,但与实际上的实施状况相比,却依然矛盾重重。英国宪法的“实践和理论处于极端的矛盾中。双方彼此相异,已经毫无相似之处了”[16]568。换言之,恩格斯的论述中蕴含了英国宪法既是经验的凝结,在当时的实施状况也是经验的体现,两者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偏差的内容。这种矛盾是经验主义者始终不能解决的。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在文本中明确批判功利主义法学观的研究方法,不过通过对两种经验的矛盾的揭示,我们不难判断出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研究方法所秉持的批判态度。马克思也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5]8。如果说显微镜和化学试剂是经验研究方法的代称,那么马克思实际上就指出了对经济形式、物质形式(包括法律形式)的研究要依靠抽象力。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价值的批判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的专制制度非常不满,痛恨当时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的学派。当时普鲁士政府实行各种专制政策,施行扼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是一个“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的政府。与同时期的英国与法国相比,德国还在经历着它们已经抛弃的历史。“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15]8德国政府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世界,而且还对自己的制度充满着盲目的自信。一些学派还极力维护这个专制制度。历史法学派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当前行为的合法性,还有的学派从德国的原始森林中为专制制度寻找依据。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德国这种过度迷恋宗教、神学、国家、法学的哲学倾向十分不满,转而非常赞同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力肯定它对近代历史发展做出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把目光开始投向英国,开始研究英国,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唤醒德国人,改变德国的现状。与德国不同,英国更注重经验,更注重现实的社会生活,也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领先世界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例3 已知常温下在溶液中可发生如下两种离子反应:Ce4++Fe2+==Fe3++Ce3+,Sn2++2Fe3+==2Fe2++Sn4+,由此可以确定Fe2+、Ce3+、Sn2+三种离子的还原性由强到弱的顺序是( )。
因而,功利主义法学观所坚持的普遍法学这一论题同样没有逃离时代的限制,坚持这些观点的人们总是受到“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等的制约,即便在某一历史阶段他们曾推动了法学的发展、拓展了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但依然难以揭开笼罩在法律上的神秘“面纱”,不能窥探法律的本质。他们总是无条件地相信那些“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意志概念本身”等,他们所做的不是把法学置于真正的社会现实上,而是要让现实服从于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功利主义试图用立法原理改造法律以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愿望是空洞的、无力的,夸大规则的作用、过度迷恋法律等往往会有南辕北辙的结果。恰恰是决定着人们行为的利益,以及伴随着利益出现的生产活动、交往方式等,才是规则产生的深刻动因。因此,并不是规则决定着人的行为,而是人的行为创造了规则。而公平、正义、平等的概念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样,为了使商品的交换得以实现,作为商品的监护人,“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所以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15]103。同样,功利主义法学观提出的普遍性法学问题也只有在对经济形式和人们交往形式上的分析中才有意义,否则这些法学概念依然难逃空洞之嫌。
式中:τ、τ0分别为浆液的剪应力和屈服剪切力;μp(t)为浆液黏度随时间的变化函数;-du/dz为剪切速率;u为浆液的流速;z为铅直方向的距离。
四、当代启示
19世纪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法律等多方面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8]36。“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8]36资产阶级也有十分杰出的思想家,如休谟、洛克、边沁、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黑格尔等,他们为这一历史进程贡献了许多新知识、新思维,在思想上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直接参与了政治制度与法律的设计、包括之后进行的改革。功利主义对法律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实证分析法学的重要思想渊源,界定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促进了法律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力,关注到了它对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政治、法律、道德等的影响。功利主义一定程度上促使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经验、重视人的行为(活动)以及它们对法律的影响。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以及所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始终保持着警惕,并对其进行批判。这一批判对于当下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这些启示集中体现在如何理解法学研究中的经验主义方法。
(一)法学研究需要经验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利益成为世界的统治者,才为功利主义法学观的诞生创造了深层次的条件。尽管功利主义不是关于利益的哲学,但利益归根结底是影响人们行为的主要因素。要看到功利主义法学观的真正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经历了神学世界观到法学世界观的过程,法学世界观是神学世界观的世俗化,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法学要从神学的庇护中走出来,就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以替代万能的神学。功利主义恰好可以为法学提供这样一个比较可靠的视角,事实证明它也非常胜任这一角色。要积极利用功利主义法学观的合理因素,服务于有利于无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与建设。在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更需要正视西方法律思想中的精华,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既能从中汲取养分,又能深刻地把握其历史局限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来源。比如,大数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且日渐常态化,已经成为影响法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学界与实务界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多项专题案件的司法大数据报告,其中的离婚纠纷司法大数据报告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一审离婚案件原告的性别分布、年龄差分布、婚姻存续时间分布等多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公众对离婚案件的认识。其中的功利主义色彩是相当浓厚的,与边沁的精心计算在目的与方法上相似,亦可以指导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当前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需要分析大数据,也需要基于此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二)如果过于迷恋经验、过于夸大经验的方法对于法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
当前法学研究中盛行实证主义研究、经验主义研究,学界对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重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左卫民教授所说的,“尝试并推进法律实证研究应当是永不满足的中国法律人的使命,就让时间来见证未来究竟会如何吧”[19]。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思考。其一,什么才是真正的法治经验。如果我们按照那种“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17]25的方法,直接移植到对法律现实的认识中,就不能获得真正的经验,得到的只是片面的、孤立的、狭隘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用辩证思维和方法考察事物之间的联系,把握社会的总体状况,把对法律的认识与社会总体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对于那些不去总体上把握情况、只从个人的需要、幻想让社会的状况符合自己臆想的做法深恶痛绝,指出这样的方法和思路不能正确发现事物之间真正的联系,这样的方法和思路同样不能正确认识法的现象。其二,如果所得到的对有关法律的经验认识之间发生冲突,应当如何取舍?马克思恩格斯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几点建议,比如上述提到的用撇开宏大的总联系的方法得到的经验、“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等都不是真正的经验,建筑在这样经验基础上的法律认知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因而也是片面的知识。真正的经验一定是与规律一致的,是与那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相一致的。所以,获取有关法律认识的经验也必须符合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曾精辟地总结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是指获取经验,而正确就是指获得的经验要符合规律。其三,单纯依靠经验能够得到对法律的正确认识吗?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我们知道在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定要遵循唯物辩证的分析方法。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会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科学地认识法律。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不是片段式,不是主观式,而是客观、准确、全面地占有材料。然后运用辩证的分析,加以运用,才能得出那个类似于“先验结构”的结论。此时,通过辩证分析得出的那些基本的要素,如商品、价值、资本、地租、劳动力等,就不再是那个纯粹的先验的概念了,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具有普遍联系,而且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简单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对包括法律现象在内的人类社会各种复杂的乱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融资平台的发展,关键在人,建立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体制,激励好每一位员工,人尽其才。制定系统完备的预算管理制度,实现零基预算管理,更高效率的管理好每一分钱;加强往来资金管理,尤其是短期资金拆借的追还,安排专人负责往来资金催缴和管理。
(三)重视经验与抽象力,辩证分析中国法治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对功利主义法学观的批判最重要的启示还在于对法律的认识和对法学的研究,既要充分重视经验,又要注重抽象力,辩证地分析中国的法治建设。一方面,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要认真对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验。首先要注重搜集和整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新进展相关资料,了解法治发展的总体状况,把法治深深植根于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中,不能脱离现实探讨抽象的法治,要认识到社会现实与法治建设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要重点关注法的运行与实施状况,关注现实中的法,不能只关注法律文本与条文,要用更加宽广的视野与思路研究法律。再次要认真对待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典型案例。它们是推动法治发展的关键点,是鲜活的法律。另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建设也不能盲从经验,要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审查和批判,进而把具体的经验上升为高度凝练的理论,才能形成科学的研究结论,才能得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0],积极构建中国的法治话语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华夏.道德哲学与经济系统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89-90.
[2]Derek.P.H.Allen,The Utilitarianism of Makx and Engels[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Vol.10,No.3,Jul.1973:189.
[3]杨松,韦庭学.马克思主义伦理观是功利主义吗?——德里克·艾伦与布伦克特的争论评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107-114.
[4]丁成际.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功利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6):71-75+86.
[5]喻中.恩格斯“英国宪法”对宪政研究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4):47-52.
[6]白春雨.马克思与功利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62-68.
[7]姚大志.当代功利主义哲学[J].世界哲学,2012(2):50-61+161.
[8]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边沁.政府片论[M].沈淑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0]张伟.浅谈密尔个性自由主义功利思想[J].重庆社会科学,2005(2):59-62.
[11]徐同远.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与分析法学思想[J].比较法研究,2008(6):119-130.
[12]乔洪武,师远志.正义的不平等与不正义的不平等——功利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思想评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6):93-100+160.
[13]富勒.法律的道德性[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
[14]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M],5th ed.Rec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don:John Murray.1885,vol.I,p:85-86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9]左卫民.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解读中国法律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7(3):45-61.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02).
Marx and Engels' Criticism of Utilitarian Legal View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Xuxiao
(School of Law,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utilitarianism is to achiev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and avoid suffering,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empiricism.I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and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behavior,and firmly believes that people can recognize the trend of behavior.Utilitarianism profoundly influences people's moral and legal concepts,and provides new ideas and perspective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legal phenomena.Marx and Engels realize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utilitarianism on legal phenomena,affirm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utilitarianism legal concept,and at the same time revealed its historical limitat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essence,method and value,pointing out that some viewpoints adhered to by utilitarianism legal concept still failed to surpa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Marx and Engels'triple criticism of the utilitarian legal concep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Our country's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need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xperience,but we should be alert to excessive infatuation with experience.To understand legal phenomena,we should not onl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xperience,but also to abstraction.We should dialectically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in China 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rule of law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Utilitarianism;Empiricism;Moral philosophy;Jurisprudence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基础理论研究”(2016BFX015)。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3-0031-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3.003
作者简介: 徐晓(1987—),男,汉族,河南长垣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律思想史、法律方法。
标签:功利主义论文; 经验论论文; 道德哲学论文; 法学观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