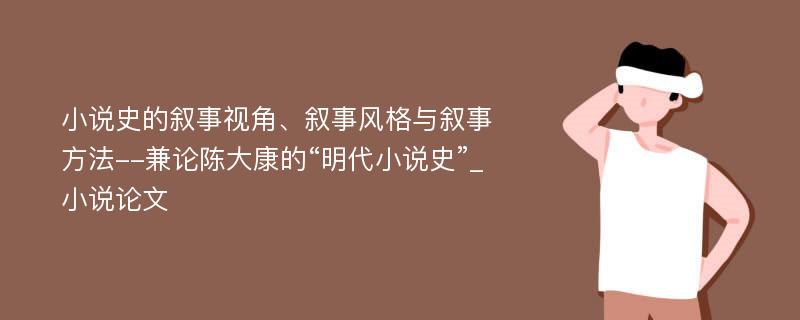
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兼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例论文,小说论文,明代论文,视角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已经充耳有年,“重写小说史”的实践也已经果实累累。仅就我近 五年书架所插,耳目所及,仅中国古代小说史新著就有17种之多。《中国小说史丛书》(杭 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包括断代史六种: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侯忠义《隋 唐五代小说史》、萧相恺《宋元小说史》,齐裕焜《明代小说史》、张俊《清代小说史》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体裁史三种:苗壮《笔记小说史》、薛洪勣《传奇小说史》、 陈美林等《章回小说史》;流派史三种:林辰《神怪小说史》、向楷《世情小说史》、曹亦 冰《侠义公案小说史》。此外还有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 6),将松源、谭邦和《明清小说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胡益民、李汉秋《 清代小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王增斌《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史稿》(北京: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陈节《中国人情小说通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等。 我们在1998年曾经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小说史”的热潮作过一个基本的估价:“这 一 时期的古代小说研究给人总的印象是在一个平面上的扩张,小说史作为‘书’的规模不断扩 大,但却并没有给人带来量变引起质变的现实或期盼。甚至连有些所谓‘填补空白’的研究 也并没有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充其量只是‘跑马占地’。学术研究多元化的格局,仍有待 于从学术与非学术错位的混乱局面中凸现出来。如何在研究规模的无限膨胀中寻找新的突破 口,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郭英德、刘勇强、竺青《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 ——关于20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第11页)
当我们还在认真思考小说史撰著的新的突破口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深入反思小说史研究的 成败得失的时候,当我们还在热忱期盼黄钟大吕式的小说史著作出现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陈大康教授《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一书以其独特的历史审视 角度、学术研究模型和历史叙事风格,异军突起,格外令人瞩目。
《明代小说史》一书内涵甚丰,值得提出讨论的话题也很多。本文无意于全面评说《明代 小说史》的优劣长短,只想以此书为例证,兼及近年来的小说史著述,集中就小说史的叙述 视 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三个方面谈些看法,抛砖献芹,与学界同仁讨论。
一、小说史的叙述视角
小说史的叙述视角,指的是小说史家选择、审视和叙述小说史现象的独特角度。历史上的 小说现象如恒河沙数,而小说史家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总 是根据自身对小说历史构成的独特认识和态度,选择、审视和叙述不同的小说现象。于 是,由不同的叙述视角所折射出的小说史,便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或繁复,或单纯,或 深邃 ,或浅显,或斑斓多彩,或线条明快。
我认为,《明代小说史》最为突出、也最富创意的叙述特色,是从历史现象之间复杂而密 切的有机联系这一独特的角度,去选择、审视和叙述小说史现象。陈大康明确地表述说:“ 宏观研究却必须遵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即古代小说的整体并不等于历史上所有作家 作品的简单叠加,它还应该包含构成整体的各 部分之间的种种有机联系。”(5页)仅就小说史而言,我认为,这些有机联系至少应该包括 四个方面:(一)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二)作家创作与作品传播之间的联系;(三)作品的文 学艺术价值与作品在历史发展上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四)历史发展的结局与过程之间的联系 。
首先是作家作品之间的联系。陈大康说:“当涉及某一具体的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 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显示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 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横’,则是指把握它与 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联系。”(2页)简单地说,研究历史上的作家作品, 必须上挂下连,左顾右盼。新近出版的大多数小说史著作往往只着眼于具体的作家作品,当 谈到一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或艺术特点的时候,习惯于“悬空”地、孤立地分析或评价作家作 品的所谓“特色”。要知道,有比较才有鉴别,作家作品的特色只能以同时代和其他时代的 作家作品作为参照系,才能真正地得以凸现,并得以确定价值坐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经典评论,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几乎成为不刊之论,就是因为鲁迅善于 通览全局,抉发特色。当然,这一点说来容易,但是如果没有对上下左右的小说史现象的通 观和沉潜,恐怕很难做到。而《明代小说史》却自觉地将它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并努力地付 诸实践。
其次,新近出版的大多数小说史著作往往将作家创作与作品传播分割为两个不相关联的部 分,要么仅仅注目于作家创作而忽视作品传播,要么仅仅将作品传播方式或接受程度作为作 家创作的背景或影响单独地加以论述。这种叙述视角,把互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割裂成各不相 干的碎片,无疑不利于对历史的整体把握。有鉴于此,《明代小说史》明确地提出“将研究 范围由作家创作延展至作品传播”(14页)的研究思路,认为“创作与传播实为不可分割的完 整过程,所谓小说发展史其实就是众多作品该过程交融性的组合”(348页)。这一思路建立 在两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第一,“在小说发展史的研究中,‘出版’意义的重要性更甚于 ‘问世’。”(15页)第二,“从整体上看,还是得承认小说在明清时的既是精神产品,同时 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17页)基于这两个基本认识,该书不仅延续陈大康的博士论文 《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的路数,对于小说作品的出版、发 行、传播、接受等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该书始终关注作家创作与作品传播 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互动关系,由此构筑崭新的小说作品阐释模式。小而言之如对嘉靖元年司 礼 监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意义的探讨(254页),大而言之如对“熊大木模式”及其意义 的论述(262-281页),对嘉靖、隆庆间文言小说刊刻与创作的互动的发微(287-314页),对 明代中篇传奇小说的兴亡的探究(348-357页),对明末文人推动与书坊扩大销路的努力的描 述(563-578页)等,这些举重若轻的叙述,使我们深深感到,叙述视角一变,果然境界全新 。
正因为关注作品创作与作品传播的有机联系,《明代小说史》对作品的文学艺术价值与作 品在历史发展上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往往独具慧识。陈大康指出:“至少在某些历史阶段,平 庸之作迭出是小说创作演进的主要表现方式”(11页)。因此,该书着眼于“广大读者的迫切 需求”与“书稿的严重匮缺”这一对尖锐的矛盾,重新审视嘉靖年间以熊大木为代表的书坊 主编创小说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意义,论定其“有着扩大通俗小说影响,减少其传播障碍的 作用”(280页)。尤其是该书第十章《明代的中篇传奇小说》,从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多运用 羼入诗文的创作手法切入,分析了当时小说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变迁,指出中篇传奇在整个明 代小说史乃至整个小说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它体现了小说创作羼入诗文由多到少的变化,是 小说体裁从糅杂趋于纯粹的重要的中介过渡;它从多模仿前作到逐渐增添独创成分的创作方 式,构成明代小说编创手法演进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它努力融合唐宋传奇与宋元话本的创作 传统,提供了介于两者之间的小说创作模式;它应急式地填补了通俗读物阅读市场的空白, 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崛起与繁荣。由此得出结论:“在小说史上,某些创作流派无甚佳作,可 是那些平庸之作构成的整体却具有承接以往启迪后来的意义,甚至某些转折过渡也由它们完 成”(357页)。
如果说,《明代小说史》对书坊主小说和中篇传奇的研究还是就“有”立说,从史实出发 ,重新论定这批小说作品的价值与意义;那么,该书更为精到之处,还在于就“无”立论, 透视小说历史发展的结局与过程之间的联系。陈大康说:“对于‘小说’决不可只狭隘地理 解为作品,它的确切含义是指小说创作,即使某阶段作家作品甚少乃至全无,它同样也是小 说创作的一种态势。”(1页)的确,小说创作的停滞,并不等于小说史的停滞。某个时期小 说新作可以甚少乃至全无,但是历史之流却不会因此中断或干涸。在小说新作一片空白的局 面中,我们只要仔细谛视,仍然能够辨认出历史蹒跚迈进的脚印。《明代小说史》的第二编 用了整整四章的篇幅,专门讨论宣德至正德七朝(1426-1521)近一百年小说创作的萧条与复 苏,认为封建统治者的高压控制、印刷业的落后与抑商政策的伤害是造成近一百年通俗小说 创作空白的三大阻碍因素,并对这三大阻碍因素的形成及其消解作了精细的分析。能够在小 说创作空白中写作如此精彩的小说史篇章,这完全得力于作者与众不同的叙述视角。
二、小说史的叙述体例
叙述视角的变化,使《明代小说史》关注的现象和问题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小说史体例 已显得过于掣肘拘牵了,于是该书便不得不独创一种新的叙述体例。
该书实际上包括两部史著,即《明代小说编年史》和《明代小说史》,分别采用了编年体 和纪事本末体两种不同的叙述体例。《明代小说编年史》以时间为主,将有明一代的小说史 现象,包括作家编创、作品抄刻传播、评论家序跋评点、书商刊刻采购销售、艺人说书以及 政府有关小说法规等,逐年著录,尽可能地征引原始资料,并略作考辨,它基本上是小说史 现象的梳理和缕述。而《明代小说史》则以小说创作作为核心的叙述要素,将明代小说创作 分为五个阶段,分别展开对各阶段小说的创作环境、创作内容、创作方式、创作旨趣、创作 格局、创作流派等“事件”的叙述,从而构成纪事本末式的历史叙事。二者相辉相映,相辅 相成,为读者展示了两幅气势宏大的明代小说历史长卷。
陈大康对该书的写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明代小说史》的任务并不是用具体创作事例 证实已知的古代小说发展通则不妄,而是应对有明一代小说行进轨迹作更为准确的勾勒,对 其独特的发展态势、规律与特点作更为精细的论述”,“考察重点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说 创作在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与约束下行进的历程,发展变化的动因、方式与它的各种表 现形态及其过渡转换。”(2页)因为,任何一种历史景观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发展状貌, 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不是普遍的文学规律的演绎或印证,而是由个别的历 史景观自身的叙述对象和叙述内容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明代小说史》采取了“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五个因素”的叙述体例。
所谓“一个中心”,指的是《明代小说史》认定“小说”的“确切含意是指小说创作”(1 页)。因此,小说史实际上就是小说创作史,小说编创方式的变迁便成为该书历史叙事的聚 焦点,小说作品的结构设置、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刻画等各方面都聚集于小说作品的编创方 式。这一点在明代通俗小说的演变中格外引人注目,“宏观考察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时,就 必须去梳理与分析它的编创方式的变化,即它从改编转向独创的具体形态与途径,并探讨导 致这一过程发生与变化的动因。”(24页)改编与独创是两个端点,“在联系改编与独创这两 个端点的中介过渡阶段中,各部作品都可有一个相应的位置,它们形成了一个序列”(26 页)。从总体上看,明代“通俗小说编创的发展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作品中改编的成分慢慢 地减弱,而独创的成分却在逐渐增强”(26页)。持此以衡,《明代小说史》对“熊大木模式 ”的历史意义(272-281页)、中篇传奇小说的历史作用(345-358页)、《金瓶梅》小说的编创 特点(448-449页)、万历年间文言小说集的编撰(489-505页)、拟话本小说的过渡型编创方式 (603-615页)等,都作了精彩纷呈的论述。这种从具体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来的文学发展规 律,既有着很强的历史针对性,又有着很高的理论价值。
所谓“两个基本点”,指的是在叙述对象上,《明代小说史》采取了通俗小说与文言小说 的二分法。与文言小说相对称的一般是白话小说,该书却宁取“通俗小说”一词,并对这一 选择作了雄辩有力的说明(104-109页)。迄今为止的小说史著作,除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略》以外,无论是小说史通史、小说断代史、小说流派史还是小说艺术史,绝大多数都是通 俗小说独霸天下、叱咤风云的疆场,文言小说顶多只能“叨陪末座”,充当“跑龙套”的角 色。这实际上是一种“瘸腿的”小说史。在中国小说历史发展中,文言小说与通俗小说犹如 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这是历史的事实,怎能不加以正视,予以重视呢?《明代 小说史》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留给了文言小说的叙述,在中国小说史编纂史上,不仅第一 次全面地考察了有明一代文言小说发展变迁的生动状貌,而且也是第一次精细地勾勒出文言 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相因相成的密切联系。例如羼入诗文的写作手法(111-119页),“教化 为先”的传统(119-128页),逐渐贴近现实的创作路数(304-314页),才子佳人故事的写作(3 28-344页),文言小说选编本与拟话本写作(519-530页)等等,这些擘肌入理、新意叠出 的篇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明代小说史》独特的叙述 视角 的叙事功能。
在叙述内容上,《明代小说史》认为推动或制约小说发展有五大因素,即作者、书坊主、 小说评论者、读者和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这“实际上是构造了一个明清小说在作者、书坊 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这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研究模型”(23页)。对 明代小说史上的诸种现象,该书都尽可能地运用这一研究模型进行论述,运用得相当娴熟, 相当精巧。例如,谈到明末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时,该书从明末小说创作的舆论环境切入, 首先说明当时官方对通俗小说的容忍甚至是倡导的文化政策,其次分析小说理论逐渐成熟的 情况,再次说明围绕通俗小说创作与评论的若干松散的文学团体的形成与作用,最后描述退 出小说创作领域的书坊主是如何努力扩大销路、吸引读者的。这几个方面的合力,便形成明 末小说创作的良好环境,使小说创作趋于空前的繁荣。这一研究模式的成功运作,大大拓展 了《明代小说史》的历史叙事空间。
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有自身的叙述体例。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历史著作的 撰述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叙事,而历史著作的叙述体例就是一套历史叙事的“规矩”。概括地 说,历史著作的叙述体例有着三个主要的构成因素:一是叙述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以时间为主的是编年体,以地点为主的是国别体,以人物为主的是纪传体,以事件 为主的是纪事本末体;二是叙述线索,包括历史著作以何种规律审察历史和以何种方式连接 历史,于是有因果链接式、螺旋曲线式、历史进化式等叙述线索;三是叙述板块,即历史著 作中叙述对象、叙述时间、叙述内容等的设置与结构方式。历史家对这三个构成因素不同的 选择与处理,使历史著作体现出不同的叙述体例。
综观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著作的叙述体例,无不笼罩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耀眼 光芒之下。《中国小说史略》的叙述体例可作如下归纳:综合时间、体裁、类型(或流派)、 作家作品几种叙述要素,以历史进化为基本叙述线索,采取以时代为框架,兼顾体裁、类型 (或流派)、作家作品的叙述板块,展开小说史的叙述。鲁迅犹如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奠定了 中 国小说史叙述体例典范的“规矩”,竟使后人唯有附骥之作,少有突破之举。虽然在近年来 小说通史演变为小说断代史、小说体裁史、小说流派史、小说艺术史等等,但是稍作抽 绎,略为归纳,不难看出,这些林林总总的小说史著作,绝大多数在叙述体例上与《中国小 说史略》亦步亦趋。
如果说,“因体为文”是一切文字书写的常规惯例,那么,“变体为文”或“创体为文” 则应是一切书写者的努力追求。变则立,创则生,文字书写正是在“变”与“创”的推动下 生生不息的。《明代小说史》便向世人展示了“变”和“创”的气魄和胆略。陈大康在分析 明代通俗小说结构时,曾经指出,并联型结构和串联型结构是通俗小说的两大结构模式 ,前者注重空间上的展开性,后者注重时间上的延伸性;而从《金瓶梅》发端,出现了“将 这两种结构基本单元交织为初步网络型的结构”(458-461页)。《明代小说史》正是成功地 将小说发展的空间展开性和时间延伸性交织在一起,构成相当精致、相当成熟的网络型结构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历史叙事范式。
三、小说史的叙述方法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著作至少有三种叙述方法:一种是罗列式的,一种是描述式的,一种 是评价式的。罗列式的历史著作,即人们常说的“长编体”,是将历史资料按照一定的纲目 加以排列,历史家略作说明,按而不断。描述式的历史著作,即历史家采用叙述的语言,比 较客观地描述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历史现象的基本状况。而评价式 的历史著作,历史家往往采用某一种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居高临下地评判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
自从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进行反思,认为中 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有着过多的史料堆积和史料辨证,而缺乏史观、史识,缺乏对历史规律的 深刻认识,更缺乏对历史的理性批判。于是评价式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以科学方法的面貌出现 ,在历史界影响广泛。再加上大学教育的普及,几乎非评价就无以成历史了。与此同步 ,在小说史研究中,研究者致力于用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取代传统的评 点式的小说批评形式,表现出浓厚的理论色彩和明晰的思辨特征,但却同时滋生出先验的理 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参见郭英德、刘勇强、竺青《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轨迹——关于2 0世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研究的谈话》,《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第8页)。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强调“以论带史”的撰史原则,评价式的历史叙述方法几乎成为 中 国大陆地区历史著作编撰的唯一方法。尤其是当人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历史批评方法应用于古代小说史研究时,评价式的历史叙述方法更走上了简单化的歧途 。在这一时期,大多数的古代小说史著作严格恪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 批评原则,用来衡量和评判古代小说作品,注重对古代小说作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世界观的分 析,并以此为准则评定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更有甚者,人们还将“以论带史”作为一种科学 的历史研究方法,借以贬低所谓“以史代论”。于是,主观武断地抽绎出某种“历史规律” ,不负责任地用曲解的小说史事实去印证所谓“历史规律”,就成为小说史著述的普遍现象 。
对这种“规律先行”的撰史方法,《明代小说史》有着清醒的认识。该书列举了明代小说 史的事实,对一些人云亦云的规律进行了清醒的反思。这些规律包括:“凡能揭示时代本质 、反映人们意愿的作品,一般都能在问世后迅速传播”;“优秀作品的问世往往会刺激 创作的繁荣”;“新流派的产生一般都得力于功底深厚且有创见的文人”;“文学发展规律 ”至少在明清小说领域里“似乎常要走样变形”(12-14页)。如果我们拿这些“文学发展规 律”去衡度明清小说史的事实,或拿明清小说史的事实去印证这些“文学发展规律”,这不 是削足适履,就是胶柱鼓瑟。
正是有见于此,近年来学术界倡导用描述史学去取代评价史学。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 总绪论》中说:“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靠描述,要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 换成描述式的语言。评价式的语言重在定性,描述式的语言重在说明情况、现象、倾向、风 格、流派、特点,并予以解释,说明创作的得失及其原因,说明文学发展的前因后果。描述 和评价不仅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习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描述并不排斥评价,在描 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寻绎‘史’的规律,而不满足于事实 的罗列。但规律存在于文学史事实的联系之中,是自然而然的结论,而不是从外面贴上去的 标签。”(《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5页)
的确,寓史识于描述之中,这是历史著作的最佳叙述方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之所 以彪炳史坛,在某种意义上正得力于这种叙述方法。该书清晰地描述了每一种小说类型、小 说流派的产生、演进与变异、合流过程,辨析了每一种小说类型、小说流派的构成特征,并 有针对性地透视小说变迁背后的历史原因,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同时,对小说作家 、小说作品、小说现象进行精微独到的评论,往往一语中的,发人深思。
在这一点上,《明代小说史》与《中国小说史略》一脉相承。该书对描述式语言的运用不 仅相当自觉,而且相当娴熟。前述该书对明代通俗小说从改编转向独创的规律的认识,就是 明显的例证。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该书经常运用“提问—解答”的叙述策略,先就历史上的 小说现象提出问题,然后仔细地爬梳史实,抉发关节,勾勒脉络,最终圆满地解答问题。例 如在“拟话本的形式特征及其蜕变”一节中,首先就鲁迅的归纳,提出话本的三个“必要条 件”:“1.须讲近世事;2.什九须有‘得胜头回’;3.须引证诗词。”(鲁迅《坟·宋民间 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138页)然 后依次就这三个“必要条件”,以明末拟话本作品为实例,一一列表分析,雄辩地说明:“ 演述近事并不是拟话本的特征”(596页);“含有入话与头回是拟话本的重要特征,但由于 它们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在拟话本的发展过程中或是被省略,或是走了样,以致 最终在后期的一些拟话本中,这一特征已依稀难辨”(600页);拟话本征引诗词和两句韵文 运用的数量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的变化过程(601-602页)。通过细致地考察与分析,该书最 后得出对拟话本的“概括性描述”(603页)。这种“提问—解答”的叙述策略,在《明代小 说史》的许多章节中都运用自如,构成该书一以贯之的叙述语言风格。
由于坚持描述式的历史叙述话语,即使对一些自古至今都被打入另册的小说史现象,《明 代小说史》也能秉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进行鞭辟入里的历史分析。研究明代小说, 谁也无法回避万历朝前后风靡一时的色情小说。对此,《明代小说史》同样采取了描述式的 历史叙述话语,因此得以超越道德评价,对色情小说在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做出相 当细致的分析和较为准确的定位:在明代通俗小说“从以改编旧作的方式描述历史或神魔故 事出发,逐渐走上以独立创作反映现实人生的道路”的转折之际,色情小说的出现具有不可 抹煞的历史意义,“这现象表明了小说发展进程的曲折与复杂,以及文学规律的显现不可避 免地要受到时代风尚的摄动”(476页)。这不正是寓史识于描述之中,从现象描述中得出历 史规律吗?
我们常说,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事求是”。在历史研究中,“实事求是”应该是在选择 、认知、考察、描述、分析具体历史现象的过程中,去求得历史规律之“是”,而不应该拿 着先验的所谓“历史规律”之“是”,去选择、认知、考察、描述、分析历史现象。前者是 追根溯源,后者是舍本求末。在历史叙事中,描述远比评价更为困难,但是也更有价值,其 原因正在于此。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旨在褒扬《明代小说史》达到了历史叙事的尽善尽美的境界, 也 不愿附和时尚流行的书评,在文末不关痛痒地评说一番该书的“不足之处”或“瑕不掩 瑜”,做出“劝百讽一”姿态,虽然该书的确有些可议之处。本文旨在以《明代小说史》为 例证,揭橥一种理想的小说史的叙述视角、叙述体例和叙述方法,与陈大康共勉,也与学界 同仁“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哲人有言:科学植根于对话之中。与学界同仁输诚对话 ,这正是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