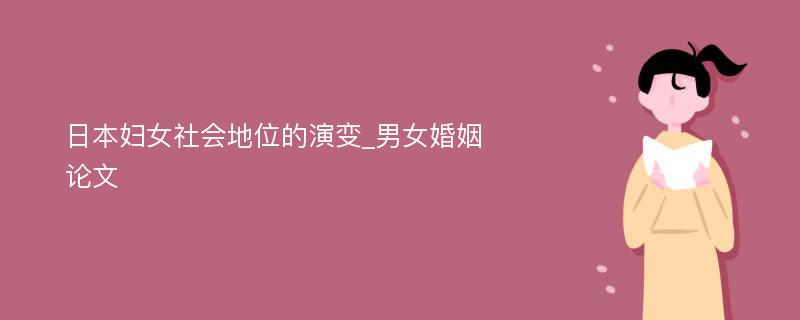
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社会地位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到现代文明社会之前,被压迫、被奴役可以说是妇女的共同命运。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因其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所表现出的对妇女的压迫和奴役的程度与方式各不相同。在日本历史上,直到武家社会形成之前,女性曾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此之后,随着婚姻形态的变化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才逐渐丧失了她们昔日的辉煌。明治维新后,近代教育的普及虽然造就了大批有知识的妇女,而人们注重和社会提倡的女性形象只是“贤妻良母”,女性仍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这种不平等的状况直到战后才得到根本改观。
一、招婿婚下日本妇女的历史辉煌
日本有一句歌颂女性的名言:“原始社会,女性是太阳”。在日本古代,日本的女性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两度历史的辉煌。第一次是“女帝的世纪”。从公元6世纪末至8世纪初,先后有六位、八代女帝秉政,她们是推古、皇极(重祚齐明)、持统、元明、元正、孝谦(重祚称德)。不仅第一位女帝即位的时间早于中国的“大周皇帝”武则天和新罗的善德女王,而且女帝人数之多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这几位女帝掌权的时间正值大化改新前后,她们在位期间在内政、外交和文化方面颇有建树,在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方面功绩卓著。“女帝的世纪”是日本女性在政治上表现最为杰出的时代。第二次是平安时代贵族女子对日本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从小接受文化教育的传统造就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女性。她们几乎横扫当时的文学领域,从《蜻岭日记》、《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日记》、《更级日记》,到作为日本古典文学代表作的《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几乎全部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假名这一日本独特的文字也是由女性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上述女性对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的杰出贡献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古代日本女性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必然反映。关于女性的社会地位,除了上述事例之外,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说明:
古代日本人对亲属的称谓反映出人们对母权的尊重及男女之间的平等。在日本古语中,称父母为“母父”(おもちち),以母在前;称夫妻为“妻夫”(ぬおと),以妻在前;称兄妹为“妹兄”(いもせ),以妹在前,这些都是女先男后。日语中“御祖”(おや)一词,其本意并非父亲、祖父,而是对母亲的尊称。至今,日本人对父系亲属和母系亲属也保持同一的称谓或许就根源于此。
女性拥有较为稳定的财产权,男女在经济上平等。如女性可通过劳动创造财产,通过垦荒获得土地私有权;在财产继承方面,女儿也有与男子同样的分割继承财产的权利;女性在娘家得到的财产,婚后并不归丈夫管辖,其所有权、处分权仍在女性本人,甚至到了镰仓时代初期,女子能继承的份额仍相当于次子的一半;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一定份额的遗产。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妇女的权益,使女性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女性是家政的掌管者。据考证,直到10世纪之前,日本的女性多以“刀自”、“刀自卖”相称,“刀自”、“刀自卖”意为“家政的掌管者”。
古代日本女性之所以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除了女性一直是生产活动中的主力这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日本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然长期保留着母系制的残余。其突出表现就是长期流行招婿婚。所谓招婿婚,就是以女方为婚姻的主体、招婿上门的一种婚姻形态,与男娶女嫁正相反。最为典型的是招婿婚的早期形态、即存在于大和时代并延续到平安时代的访妻婚。“访妻”在日语中称“妻问”(つまとい)。问有访、访问之意,“妻问”即指男女双方在结婚后并不同居一处,而是各居母家,过婚姻生活则由男到女家造访来实现,或短期居住,或暮合朝离。在这种婚姻形态下,子女由母亲抚养,家政由妻子掌管,妻子是家庭的中心。这就必然造就了日本古代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化改新之后,日本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较过去发生了巨大变化,模仿中国的制度建立的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取代了过去的氏族组织。家庭在夫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婚姻形态也由过去的夫妻生活不固定的“访妻”发展为“招婿”,实现了男到女家落户的固定的从妇居,除了贵族社会的男子为了畅行无阻地享受一夫多妻的自由而仍对访妻婚乐此不疲之外,一般农民家庭都以招婿婚代替了松散易离的访妻婚。在访妻婚发展到招婿婚的过程中,虽然父权制也在日益成长,但是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这一“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在日本则出现较迟。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儒家的“三从”、“七出”的思想虽早已传入日本,却没有立即得到全面贯彻。至平安时代,女性仍然受到社会的尊重。即使是到了武士称雄的幕府时代初期,贱视妇女的观念已经产生,但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并未发展到极致,妇女的地位也没有一落千丈。在人们心目中,“夫妇乃人伦之大纲,父子兄弟由此所生”,在镰仓幕府法律《贞永式目》中,尚在亲权的概念上将父母并称,即父母均为亲权人。这些事实说明人们还能较为正确地认识妇女和夫妇关系。
二、婚姻形态的变化与妇女地位的衰落
自从武家社会形成之后,曾经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招婿婚这种婚姻形态逐渐走向没落,并逐渐被嫁娶婚所取代。据史籍记载,12世纪末期,关白九条兼实的儿子与武将一条能保的女儿结婚。一条能保主张举行嫁娶式的婚礼,而九条兼实则坚决要求实行旧式的招婿婚,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还是“武家”服从了“公家”,举办了招婿婚的婚礼。可见。此时在武家社会已经变成了嫁娶婚,而在其他阶层仍然实行招婿婚。嫁娶婚取代招婿婚有诸多原因,最根本的是随着平安时代开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私有财产不断增加,男子在生产和创造财富方面逐渐发挥主要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越来越明显。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谋求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因此,首先发生了对招婿婚的否定,使女性婚姻关系中由主导变为从属。嫁娶婚之所以首先发生在武家社会,是因为武家社会已经成为讲求弓马之道的地地道道的男人社会,婚姻与家庭必须要与这种情况相适应。除此之外,通婚圈发生了变化也是重要原因。在招婿婚时代,人们基本上是实行村内联姻,至多不过是在相邻的村内寻求配偶。而在武家社会产生的同时,封建的等级身份制也随之产生,且日益严格。武士家族的婚姻是家族间的契约行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若与同等地位的家族通婚,不得不实行远方联姻,因为在同村或邻村这样的小范围内,可以选择的对象毕竟很少。村外婚与远方通婚,是婚姻关系中阶级性的最明显的表现。嫁娶婚首先在武家社会形成后,逐渐向庶民阶层普及。到室町时代,史籍中已常常可以看到“嫁取(娶)”、“嫁人”的字样。从招婿婚到嫁娶婚,不仅仅是民俗习惯的变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嫁娶的形成,是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彻底否定,是日本封建的“家”制度形成的前提与基础,也彻底改变了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
室町、战国时代,以家业为核心、以家督继承制为基础、实行家长制统治的“家”制度逐渐形成,到了江户时代,“家”制度成为幕藩统治的支柱之一。到了此时,中国儒家的伦理纲常日益深入日本社会,加上女子逐渐从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的地位退居到以家务为主的社会分工的变化,女性的地位彻底沦落,昔日的辉煌消失得无影无踪。
女性地位由盛而衰的表现首先是女性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的道德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贱视妇女的观念在《女大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女大学》是江户时代中期的武家女训书,堪称幕府时代以来众多女训书之集大成者,因影响大、流传广而成为日本儒教女训的代名词。《女大学》强调妇女要以夫为天,“女人别无主君,以夫为主君,敬慎事之,不可轻侮,妇人之道,一切贵在从夫”。《女大学》还毫不隐晦地阐述贱视女性的观点,“大凡女性在心性上的毛病是不柔顺、怒怨、长舌、贪心和智浅。她们十之七八有这五种毛病,这是女人不及男人的地方”,“女人属阴性,和夜晚一样黑暗,所以女人比男人愚笨”,这些无非是要说明男尊女卑的正当性。《女大学》在当时是女子必读的“圣典”,按照其要求,妻从夫与仆从主、子孝亲一样,是武家社会乃至全社会妇女必须遵守的行动准则。为人妻者,要遵守“为妻之道”,就是要“对夫之词色应殷勤而恭顺,不可怠慢与不从,不可奢侈而无理,此女子之第一要务。夫有教训,不可违背。疑难之事问诸夫,听其指示。夫有所问,宜正答之,返答有疏者,无礼也。夫若发怒,畏而顺之,不可争吵,以逆其心。女子以夫为天,若逆夫而行,将受天罚”。〔1〕可见,一个女性一旦结婚为人妻, 丈夫的家就成了她的世界,她就成了这个家的奴仆。她的职责就是小心翼翼侍奉丈夫、公婆,操持家务,为夫家生儿育女。
在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念中,人的再生产即生育的职能是“家”的第一位的基本职能。男女婚配、构成家庭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取得子嗣,延续家族的世系。“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延续家业,祭祀祖先,生儿育女便成为婚姻的最高目的,尤其是妇女的首要任务。她们结婚后,被作为繁衍后代的工具,女人被称作“惜腹之物”,成了一架生殖机器。于是,丈夫休弃不能生子的妻子,为生子而纳妾,一夫多妻都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封建家族制度达到顶峰的德川时代,上至幕府将军,下至庶民百姓,蓄妾之风盛行,将军德川家康的妾仅仅知名的就不下15人。他还在遗训中要求人们遵守“天子十二妃,诸候八嫔,大夫五嫱,士二妾,以下是匹夫”的礼教。一些文人学者公开维护一夫多妻制,如攘夷论学者会泽正志斋鼓吹“男女之道亦如亿兆臣民事一君。一家一夫而有妻妾,众女共事一男,天地之道也”,“娶妻之事乃重祖先之后、子孙不绝之义也。随天寺之道,蓄妻妾,广继嗣,圣贤之教也”。〔2〕被作为领主楷模的“名君”上杉鹰杉在自己的孙女结婚时, 将“男子娶妻是为了传宗接代,所以,丈夫无论纳多少妾都不能嫉妒”,“如有比自己好的女人就推荐给丈夫”当作“作妻子的道理”告诫孙女遵守。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着“女人和席子,都是新的好”,“女人和衣服一样,可以随便换”这样的说法。丈夫可以随意纳妾,寻花问柳,而妻子必须保持贞节,这就是封建家族制度下人们奉行的双重道德标准,而且被社会所承认。连幕末倒幕维新志士中,也有不少人崇尚“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权”。正因如此,一夫多妻制在明治维新后仍维持了很长时间,迟至1882年才在社会舆论、尤其是启蒙思想家的强烈指责下被废除,而且实行得很不彻底。所以,不仅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及皇室成员在婚姻生活中依然故我,实行一夫多妻制,而且许多标榜文明开化、在欧化洋风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们也对婚外之情津津乐道,很不符合他们极力倡导的近代文明国家的形象。
女性地位的沦落还表现在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力。在离婚问题上,男子独断专行,拥有对妻子的“七去”权。“七去”本是中国封建婚姻制度下男子单方面休弃妻子的理由,日本人几乎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每一条都反映出男女不平等”,《妇大学》将“七去”作为“圣人之教”,这实际是给丈夫以无限的权利,可以用任何借口休弃妻子。在江户时代,男子休妻极为简单,只要写上一纸休书,就算结束了夫妻关系。如果作丈夫的不会写字,便只须在纸上划三行半的直道道,妻子——这个对于妇女来说生命攸关的地位就轻而易举地被抹掉了,因此“三行半”便成了休书的代名词。对于女性而言,不论在婆家境遇如何,都必须履行与丈夫同居的义务,对于离婚是连想也不能想的。当妻子因种种原因离家不归时,丈夫有权对妇方娘家提起诉讼,娘家必须将女儿送回夫家,还要被科以罚款。唯一能使妇女得到解脱的是逃到寺庙寻求保护,经确认实属不堪丈夫虐待而要求离婚的,便被寺庙收留下来,由寺方出面召集丈夫及妻子的父母、媒人进行谈判。如果丈夫同意离婚并写休书,女子即可随父母回家。如果丈夫执意不写休书,妻子则必须在寺内当三年尼姑,才算自然结束夫妻关系。妇女为达到离婚的目的,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明治维新后,日本女性未能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那样享受到与男子同样的权益,明治民法虽然承认了妇女拥有离婚的权利,但同时又在离婚理由上作出极不利于妇女的规定: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便可以提出离婚,而丈夫在犯奸淫罪、并被判刑的情况下,妻子才能提出离婚。这一不平等的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实在是日本妇女的悲哀。
综上所述,自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形成起,妇女便被置于家庭和社会的最底层。日本家族制度本身决定了妇女一生“三界无家”的命运。所谓“三界无家”,即女人降生人世后,由父母抚养,其家是父母的;长大成人出嫁后,其家是丈夫的;丈夫死后,家是儿子的。所以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她们一生必须遵守的准则,女人一生的宗旨只有两个字:服从。
三、近代贤妻良母的女性观
近代以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明开化”运动带来了家庭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纺织工业的优先发展,使得大批士族和农家女儿走进近代产业工人的行列。尤其是近代教育的普及使人们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封建社会完全无视女性人格的传统道德已经远远落后于新的社会现实,女性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明治维新后,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儒家女子道德,把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的女性作为理想的母亲的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识的母亲是社会的重要任务。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指出“子女的精神心术大体与其母亲相似,连后来的嗜好庇习也多似母亲。人民改变情态风俗进入开明之域必须造就善良的母亲,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中村还提出,为了实现“造就善良母亲”的目标,要男女受到一样的教育,实现共同的进步。〔3〕1887年, 文部大臣森有礼在视察歧阜县的教育情况并发表演说,更明确指出“国家富强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培养足以成为人之良妻、人之良母、料理一家的气质与才能的女性。”〔4 〕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亲说”和森有礼的女子教育观是近代新的女性观即“贤妻良母论”的起源。因此,在明治初期大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所谓欧化时代,学校教育实行男女共学,教科、教材也完全相同。
然而,从明治时代中期起,随着天皇专制主义的确立,强调维护日本固有传统的国家主义思潮和家族国家观开始滋长,并日益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居主流地位。经过民法论争后公布的明治民法肯定了封建家族制度,再次把妇女置于无权地位。在教育领域也通过“教育敕语”的颁布,对明治以来的欧化教育政策进行了总清算,确立了以儒教理论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在这种形势下,贤妻良母的女性观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一些人提出要塑造“日本独特的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不是能讲流利的外语、精于算术理科之学,却拙于家事,尤其是盲目于现今社会风俗的欧化妇女,也不是长于咏歌弹琴却迂于育儿的职业妇女,而是适应此过渡时代的国情,足以培育下一代国民的妇女。”〔5 〕明治启蒙期的开明的、近代的贤妻良母观遂转变为日本式的儒教型的贤妻良母观。这种贤妻良母的标准包括:1、胸怀国家观念;2、通晓日本妇道;3、 具有作为母亲的自觉;4、具备科学的素质;5、富有健全的情趣;6、 身体健康。一言以蔽之,贤妻良母即“排除个人主义思想,具备日本妇人固有之从顺、温和、贞淑、忍耐、奉公等美德”的女性。〔6〕
培养造就贤妻良母是近代教育的重要使命。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一般都在十六、七岁结婚,所以,高等女校(女子高中)便成了女子的最终教育机关。因此,女子高中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目标就是培养贤妻良母的素养,涵养优美高尚的风气和温良贞淑的资性。正如菊池大麓(文部次官、后任文部大臣)所说:“女子结婚后要为人妻,为人母,男女互相帮助是各自的本分。家乃一国之本。一家之主妇成为贤妻良母是女子的天赋。故高等女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相应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的必要的机关。”根据1899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在当时的女子高中的教学内容当中,除了加强女子修养教育之外,家务、裁缝、手工艺授课内容增加,而外语、数学、理科的内容大大减少。在女子实业学校(如家政科、裁缝科等),则以培养“不辞劳苦,具有勤勉素质的普通家庭主妇”为主要任务。教学内容全部为家务和修身教育,其他课程的教育仅仅保持在复习的水平。应当承认,贤妻良母的思想反映出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即女子由毫无权利变为男主外,女主内,由完全从属的关系发展表面上的对等的关系,这与封建时代相比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尤其是妇女的教养水平提高以后,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日本妇女有“教育妈妈”的美称。但是贤妻良母思想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从传统的家族道德出发,把妇女限制在家庭内,实际上不过是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观的翻版。对外侵略战争中,军国主义政权重弹“家绝不是以夫妇关系为中心,而是以亲子关系为根本”的老调,婚姻的概念也“不仅仅是妻子与丈夫结婚,而是妻子嫁给了这个家”。因此,作为女性,“不仅要成为对丈夫敬爱随顺的妻子,还要生养祖先的后继者,培育将来奉仕国家的国民”。〔7 〕这种女性观不仅贯穿了封建社会的“家”的思想和儒家女性道德,也染上了浓重的国家主义色彩。在战争中,“军国之妻”、“军国之母”成为新形势下理想的女性和母亲形象。因此,有人说贤妻良母思想不过是的“家族国家观的女子教育版”。
四、战后日本妇女地位的提高
战败后的日本,经过民主改革,最终完成了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而被大大延误了的社会改革任务。经过战后民主改革,处于家族最底层的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妇女获得了参政权。在战前旧的家族制度下,妇女是丈夫的奴仆,是为了实现家的延续目的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尽管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的教育与教养水平不断提高,在产业革命及其以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她们却不能与男子一样拥有参政权,被无理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点使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大打折扣。战后,占领当局对妇女参政权问题极为关注。在1945年10月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发出的要求改革的“五大指令”中,第一条就是要赋予妇女参政权。在占领当局的推动下,日本妇女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积极行动起来。1945年9 月11日,成立了战后对策妇女委员会,提出改善妇女地位的具体要求,如要求妇女的公民权、选举与被选举权、妇女的政治结社权、就任公职权等等。妇女参政运动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政府也构成一定压力,因而不得不采取顺应时代潮流的措施。1946年4月10日, 是日本历史上妇女获得参政权后首次行使投票权的日子。人们曾预想妇女投票率不会超过半数,而实际上66.97%的有选举权的妇女参加了投票。 在这次选举中,在79名女性候选人中选出39人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代妇女众议院议员,妇女当选率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现象。这次选举促进了日本妇女的政治觉醒,象征着妇女解放的历史开端。
其次,战后日本妇女地位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法律地位的变化。在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顾预下,1946年11月,公布了《日本国宪法》。新宪法针对旧家族制度之弊,在第24条中专门规定了这样的原则:①、婚姻基于男女双方之合意即得成立,且须以夫妻享有同等权利为基础,以相互协力而维持之;②、关于配偶的选择、财产权、继承、居住之选定、离婚以及其他有关婚姻及家庭之事项,法律应以个人之尊严及两性平等为依据而判定之。这一规定,将新宪法“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和“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两种基本思想应用到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根据新宪法的精神,新民法也于1948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民法通过以下规定改变了千百年来妇女被压迫的状况,实现了男女平等。
1、改革婚姻制度。旧民法的婚姻制度, 无视个人尊严与男女平等。新民法对此予以全面修改。在结婚制度方面所作的更改是:①保护成年男女婚姻自主的权利。旧民法规定,婚姻不仅要得到户主的同意,而且凡年未满30岁的男子或未满25岁的女子的婚姻,还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新民法则把这些规定删去,改为“未成年子女结婚,应经其父母同意。父母一方不同意时,有他方同意即可”〔8〕。②旧民法规定, 结婚后,妻称夫之姓,由改变姓氏来表示进入另外一家。新民法则规定姓氏由夫妻协议定之(第750条)。确定姓氏的目的,完全在于方便称呼, 而不存隶属关系。③同居义务的变更。旧民法只规定“妻负与夫同居之义务,夫应使妻与之同居”。这种男女不平等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新宪法第24条的精神,故新民法规定:“夫妇应同居, 相互协力, 相互扶助(第752条)”,从此夫妻互负同居的义务。
2、保障妇女的权益。 在明文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宪法面前,妻子的无能力制度被废除了。新民法亦在各方面保障妻子享有与丈夫完全平等的权利。它主要表现在:①新民法实现了离婚原因的合理化。在旧家族制度下,丈夫的不忠不能成为妻子要求离婚的理由,妻子只能为此而哭泣。新民法剔除了这种不平等,改为配偶者不贞行为时,即可提起离婚诉讼(第770条),不因其为夫或妻而不同。 ②规定家庭财产系由夫妇协力而得,故不管是协议离婚,还是裁判离婚,当事人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要求分割财产(第768条), 这是一项保障男女平等的实质性规定。③提高被继承人配偶(妻子)的继承地位。过去,妻子在继承上地位很低。在家督继承方面,不能作为法定家督继承人;在财产继承方面,继承顺位在直系卑属之后,即在被继承人无子女或子女死亡及其他丧失继承权、而又无代位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继承丈夫的财产。新民法规定:被继承人的配偶有权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在与子女为共同继承人时,配偶的应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一;在与被继承人的直系尊属为共同继承人时,配偶的应继承份额为二分之一;在与兄弟姐妹为共同继承人时,配偶的应继承份额为三分之二(第900条)。 此规定使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真正得到提高,对于妇女来说“长而又长的黑暗历史总算结束了,妻子长达几个世纪的隐忍服从的世界里脱身出来,好容易才得以成为财权的主体”。〔9〕。④母亲成为亲权人。 在旧民法时代,子女的亲权人是父亲。母亲生养子女,为孩子一生操劳,法律却不赋予母亲以任何权利。尤其在不得不离婚的情况下,因为孩子的亲权是父亲,孩子就是丈夫的,母亲因此无权要求孩子与自己一起生活。新民法结束了这种不平等的状态,在第818条中规定“未成年的子女, 服从父母的亲权”。据此,父母在婚姻过程中,共同行使亲权,父母离婚时,为了孩子的利益,确定母亲为亲权者的居多,母亲对孩子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根据新民法的上述规定,妻子获得了独立、平等的人格。
3、继承制度的改革提高了女子的经济地位。 在家长制家族制度下,实行由长子单独继承,女儿取得继承权是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如果婚生的孩子都是女孩,而非婚生子是男孩,那么,户主的权利、义务、财产、地位便要由非婚生的男孩继承。因而女儿和只生女儿的母亲的地位是不安定的。根据新民法,家庭子女不分男女,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已婚的女儿,也可以与其他子女一样,平等地继承娘家父母的财产。由于实现了继承方面的男女平等,女儿成为财产权主体的机会多了,这对于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经过战后民主改革,日本妇女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然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是长期的任务,既需要有法律上的规定,更需要道德上的认同。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不可能迅速销声匿迹,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日本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大男子主义”国家。1982年总理府进行的“妇女的生活与意识国际比较调查”的结果表明,有66%的家庭由丈夫掌管家庭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而由妻子或夫妻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的加在一起也不足30%。〔10〕“男主外,女主内”已经成了日本社会分工和家庭义务的定式。人们依然认为家庭主妇就是妇女的终身职业,操持家务、照料孩子是妇女的本分,无微不至地伺候丈夫是妇女必须具备的美德。即使是双职工家庭,也必须由妇女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家务。〔11〕日本的妇女似乎是温顺的代名词,最能容忍。由于“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存在,妇子就业的人数虽然逐渐增多,但总的趋势是呈M型, 即从学校毕业后就业——结婚或生育后退职——孩子长大后再就业。使妇女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家庭,从而难于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注释:
〔1〕《女大学》见《日本思想大系·34·贝原益轩·室鸠巢》,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203~204页。
〔2〕会泽正志斋:《新论·迪彝篇》,岩波书店1969年版, 第275页。
〔3〕《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5卷·家族制度》, 家庭出版1976年版,第348~349页。
〔4〕福岛正夫:《家族·政策与法》第7卷《近代日本的家族观》,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第253页。
〔5〕1989年《教育时论》转引自:《妇女解放的思想与行动》, 时事通讯社1975年版,第132页。
〔6〕《关于战时家庭教育指导的文件》, 见《日本教育制度史料·第7卷》,金子书房1957年版,第54页。
〔7〕文部省教育局:《臣民之道》, 见《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5卷·家族制度》,第475页。
〔8〕本文所引日本战后民法之内容,均引自曹为、 王书江等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9〕佐佐木静子:《妇女法律入门》,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 第108页。
〔10〕人口问题审议会等编:《日本的人口、日本的家庭》, 第102页。
〔11〕据1982年的调查,赞成“男主外,女主内”的达70%,同上,第1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