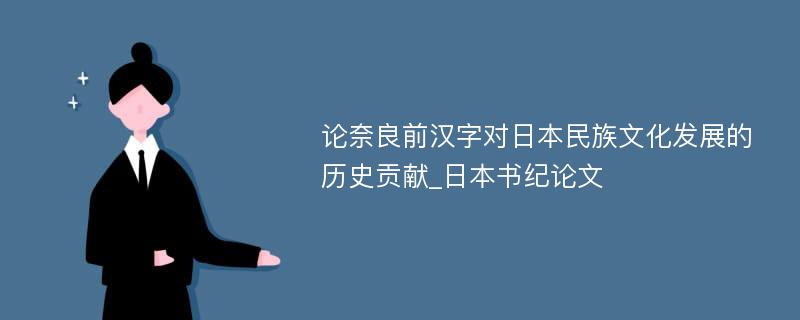
试述汉字对奈良时代以前的日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奈良论文,汉字论文,日本论文,文化发展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汉字传入日本,对日本民族理性思维的拓展,对日本文化内容的丰富和格调的提升,乃至对日语的形成,均发挥过巨大作用。历史上中国典章制度和儒释等思想文化对日本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我国学界有较多探讨,而实际上汉字在促进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方面,亦贡献颇丰。本文之所以着重阐述奈良时代以前汉字对日本民族文化的贡献,是因为这个时期汉字不仅传入了日本,而且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撰写纯汉文和变体汉文的文章;同时开始以汉字为万叶假名表记一般性日语词汇。这些文化行为为8世纪以后日本文化的兴盛以及日本民族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一、日本人与汉字的接触 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其中《海内东经》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钜燕在东北陬。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如果这里所说的“倭”指的是日本的古名,则这是中国现存古籍中有关日本的最早记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攻灭以现在的平壤为王都的卫氏朝鲜国,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了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汉武帝死后不久,真番和临屯二郡相继废止,玄菟郡也被移至辽东地区,但是乐浪郡吸收了改废后的真番、临屯、玄菟三郡的一部分属县而管辖范围扩大,成立了大乐浪郡,成为汉朝统治东方民族的最前沿机构。《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这十九字是中国正史对日本的最早记载,倭人定期朝贡的地点应是乐浪郡首府所在地。 乐浪郡存在420年之久,两汉时期最为鼎盛。西汉时期乐浪郡人口约406000余人,东汉时期约250000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官吏、商人、农民、工匠、富豪和知识分子。[2]据《后汉书·王景传》记载:“王景八世祖仲,本琅邪(山东)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为避吕氏之乱,移居海东乐浪山中。及至其父闳,成为乐浪郡三老(乡职)。”[3]山东移民王景因帮助王遵平定原住民叛乱而封为列侯。像王景及其祖先那样移居朝鲜半岛,死后埋在那里的中国人墓葬,仅在今平壤市乐浪区土城南面就多达两千座。如此众多的中国人移居朝鲜,在乐浪郡存在的四百余年间朝鲜半岛形成了浓厚的汉文化氛围。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还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这个时期日本与中国交往,主要是北九州地区的“百余国”定期至汉朝在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机构乐浪郡朝贡,乐浪郡成为向日本输送中国文化的前沿地带。 古代日本和中原王朝的直接接触应是在东汉以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光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4]倭奴国“奉贡朝贺”和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的地方应该是东汉王朝首都洛阳。根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至三国时期,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往来增多,关系趋于密切。[5] 《文献通考》记载: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6]当时日本朝贡东汉和曹魏王朝是经由辽东地区来到洛阳。这条线路不仅是政治上的朝贡路线,也是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列岛的传播通道。汉魏时期或通过乐浪郡及带方郡①或直接从洛阳,中国文化传入了日本列岛。1899年,从位于福冈平原中央的春日丘陵须玖冈本遗迹D地点发掘的众多瓮棺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西汉镜;[7]博多湾沿海地区日本弥生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制造的铜剑、铜鉾;福冈县西北部(古代筑前国)筑紫郡春日村大字须玖以及丝岛郡怡土村大字三云等地的弥生时代瓮棺内也发现了很多中国古镜、璧、玉之类的文物。在丝岛郡小富士村的海边遗址中还发现了中国王莽时代的铜钱“货泉”等物;[8]在长崎壱岐原之过、福冈县系岛郡小富士村松原、京都府熊野郡函石浜、大阪府中河内郡瓜破、广岛县福山市津之乡等地出土了王莽“新”王朝(9-20)所铸铜币“货泉”。[9]这些都在说明两汉时期中国和日本已有了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 据目前所取得的考古成果,能够认定在日本发现的最早的汉字是王莽“新”王朝所铸铜币上刻写的“货泉”二字。②如果该钱币传入日本的时间也是在1世纪,那么汉字传入日本则是在弥生时代中期。东汉光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向东汉遣使朝贡时,“光武帝赐以印绶”。一般认为这个“印绶”就是1784年在福冈县糟屋郡志贺岛(今福冈市东区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也能证实至迟在1世纪中叶日本人就已经接触到了汉字。另外,三重县大城遗迹出土的2世纪刻书陶器上书有“奉”或“年”字;福冈县三云遗迹群出土的3世纪陶器(甕)上书有“竟”字;三重县贝藏遗迹出土的3世纪陶器上书有“田”字;三重县片部遗迹出土的4世纪陶器也书有“田”或“虫”字。[10] 迄今为止,在日本发现了许多汉魏时期带有铭文的刀剑和铜镜,现举其要者于下: 1.奈良县东大寺山古坟出土汉灵帝中平(184-189)铭大刀。 铭文:中平□□ 五月丙午 造作支刀 百練清剛 上応星宿 □□□□ 2.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三国吴国赤乌元年(238)铭神兽镜。 铭文:赤鳥元年五月廿五日丙午□□□□百湅□□□□君侯□□□□万年 3.大阪府黄金塚古坟出土三国曹魏景初三年(239)铭三角缘神兽镜。 铭文:景初三年陳是作铭(镜?)铭之保子宜孙 4.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出土三国曹魏景初三年铸三角缘神兽镜。 铭文:景初三年陳是作竟(镜)自有経…… 5.群马县芝崎古坟出土三国曹魏正始元年(240)铭三角缘神兽镜。 6.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赤乌七年(244)铭画文带神兽镜。[11] 由上举文物,能够进一步肯定汉魏时期汉字已传入了日本。 文字的使用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对于处于较低文化发展阶段的人们而言,外来文字只是一种图案或纹饰而已。汉字刚传入日本列岛时,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也只是不解其意的图案或具有一种咒术功能的符号,而没有成为记写事物的工具。例如,佐贺县东松浦郡谷口出土的三神三兽镜,可能是仿制汉镜,其铭文如下: 吾作明竟甚独保子宜缘富无訾奇 其中,最后的“奇”字,应该出现在“独”字后面,说明对铭文没有理解,结果仿制时把文字顺序搞错。铭文的正确字序应是: 吾作明竟甚独奇,保子宜缘富无訾。 奈良县北葛城郡新山出土的仿制王莽镜的方格四神镜,也把表示十二地支的汉字顺序排错,或同一字重复出现。上述三神三兽镜和方格四神镜的铸造年代推测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此时距汉字传入日本已过了数百年,但当时的日本人对汉字的功能尚不熟悉,依然把汉字当作一种装饰符号。 据《古事记》记载,百济照古王(肖古王)通过阿知吉师向日本国王奉“横刀”和“大镜”,[12]《日本书纪》记载肖古王献“七枝刀”和“七子镜”。[13]学界认定“横刀”和“七枝刀”,“大镜”和“七子镜”属于同一物,且认定“横刀”或“七枝刀”就是今天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所藏“七支刀”,献刀的时间为369年。“七支刀”刀身两侧各有三个分叉,故称“七支刀”。刀身全长74.9厘米,上刻有61字铭文(正面刻34字,背面刻27字)。因此能够断定4世纪末日本人已接触到了较长的汉语文章。据《日本书纪》记载,到了履中天皇四年(5世纪中叶?)“始之于诸国置国史、记言事,达四方志”。[14]有研究者认为这一记载是模仿了《春秋左氏传》杜预注,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时期应有很多来自朝鲜半岛的通晓汉字汉文的“渡来人”(4至7世纪从朝鲜半岛和中国来到日本列岛的移民)生活在日本,他们率先在日本使用汉字记写事物,并承担了大和朝廷的文书工作。 二、日本最早的汉文体文章 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记载,曹魏景初二年(238)难升米来洛阳“朝献”时,魏明帝“诏书报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正始元年(240),曹魏“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倭王也“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如果上述记载正确的话,倭王答谢曹魏皇帝恩德的诏书也应该是用汉文写成。首先是与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关系,决定了日本使用汉字的历史命运。诚如有学者所说的亚洲汉字或汉文化圈的形成是以中国皇帝对周边诸民族首领授予官爵为形式而建立起来的册封体制为背景的。[15] 《宋书·倭国传》收录了南朝刘宋升明二年(478)倭国雄略大王致宋顺帝的一则上表文,行文流畅,文辞得体,现抄录于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15] 如果此上表文确为原文或即便由《宋书》编撰者沈约润色,也说明5世纪末日本与中国交往时使用了汉文国书,表明至5世纪后半叶,汉字对日本的渗透和影响加剧。而古代日本社会的文明层次得以提高,与4世纪末以后有很多通晓汉文的朝鲜半岛居民移居日本列岛的情形密切相关。可以推认,6世纪末7世纪初之前,充当中日之间文化传播中介的是这些识文断字的渡来人,他们对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据《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十四年(283)秦氏祖先弓月君“自百济来归”;应神十六年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应神二十年九月,“倭汉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十七县而来归”。学界认定应神朝时期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③[17]《日本书纪》钦明纪元年八月条又记载:“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18]秦人总户数为七千五十三户,按每户四口人计算,其人数近3万人。弓月君、王仁、阿知使主以后分别成为秦氏、西文氏、东汉氏的祖先,他们当时承担着征收赋税、财务出纳、制作文书、文字记录以及外交事务等工作。大和朝廷把他们当中从事文字工作的移民以世袭制组织起来,称他们为“史”。具有“史”姓的诸氏均居住在大和河内地区。大和政权的“史”部的主体是应神朝时渡来的阿知使主子孙东汉氏一族东文氏,河内“史”部的主体同样是应神朝时渡来的王仁的子孙西文氏。正是这些“史”部的成员及其子孙开始撰写日本最早的汉语文章。其代表作有: 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 正面:辛亥年七月中記。乎獲居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児多加利足尼。其児名弖已加利獲居。其児名多加彼次覆居。其児名多沙鬼獲居。其児名半弖比。 背面:其児名加差彼余。其児名乎獲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獲加多支鹵大王。寺在斯鬼宫時。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練利刀。記吾奉事根原也。 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铁刀铭 治天下獲□□□卤大王世、奉□典□人名无□弖、八月中、用大鐺釜并四尺廷刀、八 十練捃三寸上好□刀。服此刀者長寿、子孙注々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書者張安也。[19] 上示铭文中,琦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铭文由115字组成。铭文中的“辛亥年”应为471年(亦有研究者认为是531年)。文中的“獲加多支卤”一般指雄略天皇。通过解读这一铭文,能够了解到熊本县江田川山古坟出土的铁道铭文中出现的“獲□□□卤”也应是雄略天皇。该大刀铭文末尾有“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字样,推断铭文书写者应是“史”部成员。上述刀剑5世纪在日本铸造,但这个时期日本人还没有作为文字书写者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情况进入6世纪后依然如故。1165年编纂的《元兴寺缘起》所载《元兴寺露盘铭》(596年铸造),其书写者明确记载署名为“书人百加博士、阳古博士”,也应该是“渡来人”。[20]如果将汉字传入日本列岛的时间由1世纪算起,到6世纪时已有五百余年的时间,但日本人中恐怕还没有人能够使用汉字写文章,其原因是他们尚未熟练掌握汉字,文字工作完全由“渡来人”承担。 三、日本人撰写汉文体文章 (一)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 汉语对东亚地区民族语言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还是以中国文化的渗透为基底或先导,语言的影响是在文化渗透中实现的。历史上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也以中国儒释文化传入日本为重要前提。 5世纪移民潮中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主要是须惠器(陶器)烧制、铁器加工、织锦等技术。日本社会虽已开始使用汉字写刀剑铭文,但还没有受到儒学、佛教、阴阳道等中国思想文化的系统影响。 由于汉字是表意文字,5世纪以前汉字无论以怎样的途径传入日本,日本人因此已有可能接触到了儒学内容。但是即便认定这个时期儒学随汉字传入了日本,恐怕也是片言只语,而且儒学的社会功用尚未被日本人认识。儒学作为政治和学术思想系统地传入日本是在6世纪以后。 根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应神天皇时期百济王派遣阿直岐向天皇奉献良马二匹。阿直歧擅长读儒学经典,所以天皇令他教授太子菟道稚郎子。当天皇问阿直歧是否有超越他的儒学博士时,阿直歧向天皇推荐了王仁,于是天皇派人从百济请来了王仁。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太子菟道稚郎子随王仁学习了诸经典。《千字文》是中国南朝梁朝(502-549)人周兴嗣编写的儿童识字课本,成书于6世纪上半叶,所以应神天皇统治时期的4世纪末5世纪初不可能传入日本。上述记载显、然是《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饰词,不足为凭。[21]但应神朝时期随着通晓汉字文化的朝鲜半岛移民大量移居日本,儒学在此时传入日本的可能性很大。进入6世纪后有确凿证据表明儒学已传入了日本。据《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六月条记载,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同十年九月条又记载百济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取代先前的段杨尔。[22]此后百济又向日本又派去了儒学博士,如钦明天皇十五年(521年)二月条记载王柳贵来日本替代了马丁安。[23](p.336) 这些儒学博士来到日本之后,当然有可能系统地向日本人传授儒学,扩大儒学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推古朝时期(592-628)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和“官位十二阶”中明显体现着儒学思想。如《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三条规定:“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覆天,则致坏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慎,不谨自败。”[24]“官位十二阶”是以儒学德、仁、礼、信、义、智等德目为名称。 7世纪以后,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增大。在《日本书纪》天武天皇四年(675)正月条中出现有关“大学寮”的记载。[25]持统三年(689)正月条中也出现大学寮献杖八十枚的记载。[26]说明至晚在7世纪末,大和朝廷就已经在中央设立了国立大学“大学寮”。大学寮所使用的教材为儒家经典。在7世纪的日本,儒学得到很大发展,这通过从日本各地出土的木筒和漆纸文书等得到证实。儒学的政治价值被日本人发现,这对汉字在日本社会广泛使用以及植根于日本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东渐日本,对古代日本社会文明进程的飞跃发展,影响巨大,犹如日本佛教学者村上专精所言:“佛教初传到本土,东海灵岛之民深深领悟佛陀大悲的圆音,佛法真如冲破无明长夜的黑暗,呈现明月般的光辉。”[27] 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据《日本书纪》记载,552年百济圣明王派遣使者“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23](p.331)但很多研究者根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圣德太子传记)及《元兴寺伽蓝缘起》(记载元兴寺形成、变迁过程的书籍)的记载内容,认为佛教传入日本的时间为538年。 佛教在日本普及很快。据《日本书纪》记载,594年“诸臣、连等各位君亲之恩,竞造佛舍”;624年当时有寺46所,僧尼1385人;[24](p.373,339)645年8月孝德天皇下诏:“天皇至于伴造,所造之寺,不能营,朕皆助作。”[28]说明7世纪以后,佛教开始在日本兴盛。 由于古代日本人更多看重的是佛教中的巫术成分,因此为佛教在日本弘传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也为汉字在古代日本社会大显身手创造了优越条件。为了诵读佛经,日本人须加强对汉字的学习和使用。《隋书·倭国传》记载: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29]佛教传入之前,日本已使用汉字,但是此段记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佛教对日本使用汉字发挥了推进作用。另外,佛教的传入也使日本出现了通晓汉字的僧侣阶层。 总之,汉字的传入,扩大了古代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渠道,而佛教、儒学等中国思想文化受到日本社会的青睐,反过来又拓展了汉字在日本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 (二)日本人撰写纯汉文体文章 如上所述,汉字传入日本后,首先是用来撰写纯汉语文章,而且这一工作是由“渡来人”承担的。前引《宋书·倭国传》中的雄略大王“上表文”和出土的刀剑铭文,都应出自“渡来人”之手。以后,这些“渡来人”向日本人教授汉字汉语。儒学和佛教的传入,向古代日本人首次提供了系统学习中国文化的契机。如上所述,为了理解和研究儒学和佛教理论,有必要掌握汉字和汉语。其结果是,到了推古朝时期,日本人中出现了圣德太子等具有很高汉文水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推古朝以后的整个7世纪是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100年间,日本人向中国派遣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很多留学僧和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加之百济、高句丽灭亡后,大量的通晓汉字汉语的“渡来人”移居日本列岛,这些都大幅度促进了7世纪日本人使用汉字能力的提高。除了圣德太子撰写《三经义疏》之外,7世纪时日本人还撰写了其他书籍。《日本书纪》推古纪中记录了《天皇记》、《国记》、《臣连伴造百八十部公民等本纪》等书籍,但这些书籍在大化革新的政变中被焚毁。《日本书纪》中还出现了《日本旧记》、《日本世记》、《帝记·上古诸事》、《帝王本纪》、《谱第》、《神别记》、《国造记》等书名,这些书都应该是在7世纪或7世纪以前撰成。7世纪时还出现了《天武天皇律令》、《近江令》等法律书籍。8世纪编纂的《万叶集》中还出现了先前的《类聚歌林》、《柿本人麻吕集》、《笠金村歌集》、《高桥虫麻吕歌集》、《田边福麻吕歌集》、《古歌集》等歌集名称,由此可以推知这个百年中日本人已经能够以汉字为字母(万叶假名)表记和歌了,这些和歌于8世纪中叶成为编纂《万叶集》的重要来源。总之,正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书写经验,进入8世纪以后日本人才能编撰出纯汉文或变体汉文书籍。也是在这个百年中日本人进一步掌握了汉字,为奈良时代以后训读汉文以及汉字和训的固定运用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日本人撰写变体汉文体文章 古代日本社会学习、使用汉字汉语,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需求,与中国的交往中需用汉文撰写国书或表达政治意图。而文化发展上的巨大落差,④也促使日本人积极学习汉字汉语。但是从地理条件看,日本列岛孤悬太平洋西北部,环以汪洋,水天浩渺,波涌天际,在古代社会,是一个舟楫不易的遐方殊域,因此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受制于自然条件;另一方面,历史上日本基本上游离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之外,这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全方位地影响日本,加之日本民族具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使古代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同时,将其本土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学习汉文方面亦是如此,从而出现了使汉文日语化的“变体汉文”。 所谓的变体汉文就是貌似汉文,但实际内容是用汉字表记的日语文章。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日本的变体汉文萌芽于推古朝时期。圣德太子撰写的《三经义疏》之一《法华经义疏》带有“和臭”、“和习”,即夹杂着日语语法。如“長行无所”、“汝悉知応”、“共議来欲”等句,其中“无所”、“応”、“欲”等词的使用方式,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则,而带有日语特征。⑤汉语和日语属于不同系统的语言,语法上差别很大,当时的日本人若要写出纯正的汉语文章,实属不易;因此,其所汉语文章中便自然出现有日语语法特征。 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菩萨半跏像铭》全文如下: 歲次丙寅年正月生十八日记高屋大夫為分韓婦夫人名阿麻古願南无頂礼作奏也[30] 此铭记录了高屋大夫为已故妻子阿麻古制作佛像的事宜。“丙寅年”一般被认为是606年(也有666年之说)。句子末尾“作奏”中的“奏”字,应该是“作ゐ”这个日语动词的补助动词,表示谦让。因为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と奏す”这样的日语表达形式,所以试图以“作奏”表达“観世音菩薩像をお作り申し上げゐ”(制造观世音菩萨像)这一意思。这种补助动词性用法,显然是受日语语法影响所致。如果“丙寅年”能够确定为606年,则以上一段文字应是目前所知的日本最早的变体汉文体文章。 据传日本奈良县法隆寺是由圣德太子于607年所建。该寺院的金堂药师如来像铭也是用变体汉文写成的,现抄录于下: 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像光背铭 池辺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労賜時、歲次丙午年、召於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願賜、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将造寺薬師像作仕奉詔。然、当時崩賜、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東宫聖王、大命受賜而、歲次丁卯年奉。 上面一段文字中,像“薬师像作”、“大命受賜”、“造不堪”等词组的语序和“大御身”、“御病”的敬语接头词以及所使用的“労賜”、“願賜”、“崩賜”、“仕奉”等敬语补助动词等,都表明这段文字不是纯汉文,而是夹杂着日语语法的变体汉文,在此将其转写假名文于下: 池の辺の大宮に天の下治しめす天皇、大御身労れ賜ひし時に、歲丙午に次りし年に、大王の天皇と太子とを召して、誓願し賜ひしく、我が大御病太平かにあらむと欲し坐すが故に、寺を作り薬師の像を作りて仕え奉らむと詔りたまひき。然はあれど当時に崩り賜ひて、造ゐに堪へねげ、小治田の大宮に天の下治しめす大王の天皇と東宮の聖王と大命を受け賜ひて、歲丁卯に次ゐ年に仕へ奉りつ。[31] (四)万叶假名的产生 如上所述,在古代日本社会,汉字首先是用于撰写纯汉语文章,而这一行为是通过渡来人实现的。在汉字传入日本列岛之后的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汉字的应用价值逐渐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开始积极主动地学习、使用汉字。起初是利用汉字撰写纯汉文体和变体汉文体文章,继而还把汉字当做表音字母表记日语,从而开启了汉字日本化的进程,“万叶假名”的诞生就是汉字日本化的重要步骤和成果。 所谓的万叶假名就是借用汉字字音表记日语字母,其主要应用在奈良时代。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集中使用了这一表记手法,所以称之为万叶假名,亦称“真假名”、“真名仮名”等。其不考虑汉字字义,以一个汉字字音记写日语一个音节,是万叶假名的基本特征。利用汉字字音表记外来语的事例,在古代中国早已有之。如早在秦汉时期表记北方游牧民族的名称为“匈奴”,匈奴首领名称记写为“单于”;3世纪时的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名字记写为“卑弥呼”等。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使用汉字记写了很多佛教概念和用语,如将那些信奉佛陀教义、修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的梵文名称“Samgha”音记为“僧伽”,等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日本社会使用汉字记写日本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从5世纪开始。如前所述《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中,被推定为日本第二十一代天皇的雄略天皇的名字记写为“獲加多支鹵”,其皇宫记写为“斯鬼宮”,铁剑的制造者及其子孙记写为“乎獲居”;《江田船山古坟出土大刀铭》文中也出现了“獲加多支鹵”、“无利弖”等日本人名。目前,一般认为日本人借用汉字字音记写固有名词以外的普通日语的资料,是在大阪市中央区难波宫遗址发掘出土的652年以前的木简上所写的“皮留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这11个文字。⑥将其转写成平假名就是“はゐくさのはじめのとし”,这应是一首和歌的开头部分。故7世纪时日本人使用万叶假名表记一般性日语,其意义重大,日本的民族文字之一平假名就是由这样的万叶假名发展而来的。 根据1991-1999年间的调查,从奈良县飞鸟池遗迹出土了8000多件属于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的木简(目前所知最早的木简为飞鸟坂田寺遗或难波京遗址出土的木简,其不晚于7世纪中叶)。[32]除了给我们提供“天皇”这一称号始于天武朝(672-686)等重要的历史信息之外,这些木简还帮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日本人在通常的社会生活中均书写变体汉文。根据这些木简内容,能够总结出当时的变体汉文至少有万叶假名主体、训字—万叶假名并用体,以及训字主体这三种文体。[13]因篇幅所限,加之万叶假名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对于奈良时期日本人使用万叶假名表记日语的情况,拟另撰专文阐述。 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这种影响产生于日本民族的幼年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日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两种要素就像生物DNA双螺旋桨结构一样,紧密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古代日本的民族文化。汉字传入日本列岛后,得到多方使用,助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是其重要体现。古代中日文化交流涉及许多层面,汉字文化对日本民族文化影响应是其主流之一,对于汉字在日本列岛历史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应是中日学界予以重视的课题。 ①带方郡是中国东汉末年至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郡级行政区划之一,属于幽州,为东汉末年的辽东太守公孙康分乐浪郡所置,治所带方县(今属朝鲜黄海北道)。带方郡后来被百济短期占领,于475年被高句丽吞并。 ②据标点本二十五史《汉书》卷24下《食货志》记载:“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③关于应神天皇的年代,在永原庆二监修、石上英一等编撰的《岩波日本史辞典》中,其释文为:“5世纪前半叶的天皇。”(日本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143页) ④池田温的如下阐述有助于了解古代中日文化发展落差:“中国和古代日本的发展阶段差距显著。秦统一帝国诞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因此,日本的国土统一即使从雄略朝算起,也约有700年的差距。而且,秦汉帝国已经克服官僚的氏族世袭制,确立以推荐人才为基础的选举和官吏考课制;与此相对,八九世纪的日本的统治组织依然根深蒂固地留存着氏姓传统。在经济方面,当前汉已用五铢钱征收人头税,五铢钱流通全国时,与此相对,八世纪的日本的货币流通经济,不过是在首都开始使用货币而已。中国和日本的规模上的差距不必待言,在质的方面对比社会发展程度,在大陆,与八世纪日本相近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而能与唐朝相比的,则是安土桃山以后的日本近世社会。德川封建时代也很难看出唐代科举和辟召所演示出来的阶层流动性。”参见池田温编:《唐与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第8页。 ⑤这三组词句分别对应于日语“長行には无き所”、“汝悉く知ゐ応(べ)し”、“共議に来らんと欲す”。 ⑥2006年10月12日,日本大阪教育委员会和同市文化财协会宣布在大阪市难波宫遗址发现了“皮留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这11个文字。标签:日本书纪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日本佛教论文; 万叶假名论文; 日语汉字论文; 日语学习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汉字废止论文; 朝鲜汉字论文; 日文字论文; 万叶集论文; 古事记论文; 片假名论文; 日本人论文; 日语论文; 百济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