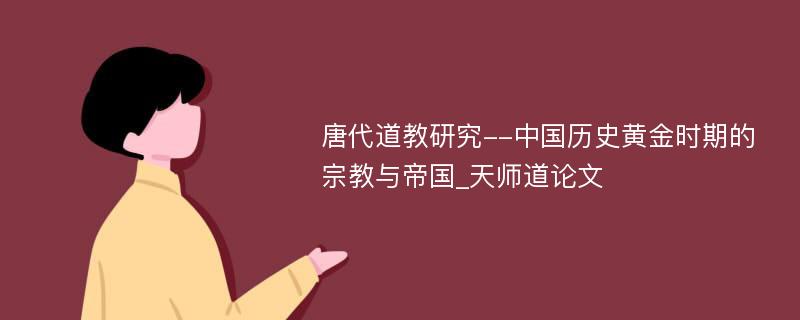
唐朝道教研究——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帝国论文,唐朝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章 历史背景以及初唐道教
在研究唐朝道教之前,首先得坦率承认我们目前对道教史的很多方面还很无知。这倒不是因为缺少研究资料,而是道教一直没有编史的传统。对道教史的研究起于二十世纪,兴于二十世纪末期。虽然道教的主要发展阶段已基本厘清,至少对唐以前的道教史的梗概有所了解,但仍然有许多研究需要我们深入进行下去①。
一、唐以前道教概况
当今大多数道教学者都认为道教观念以及修炼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却只把道教的组织起源追溯到动荡不安的二世纪。在汉末以及紧接着的混乱时期,宗教组织蓬勃兴起。其中的一支通过发展壮大,足以向权势提出挑战,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组织名叫“五斗米道”或者“天师道”,由张道陵于二世纪中期在四川所创立。张道陵的孙子张鲁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在公元215年与取代汉朝的魏国统治者达成协议,允许天师道在四川以及魏国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继续传教。于是,在发源地四川起着领导作用的天师道神职人员“祭酒”得到魏晋王朝皇室的支持。
西晋朝廷在四世纪二十年代被逐出中国北方,其社会精英在逃难时将天师道带到了西晋早年从东吴手中夺取的长江以南地区。这个地区保存有不少的宗教传统,包括大量很可能源于汉朝的方士传统。起初,当地士族欣然接受这些从北方与难民同来的祭酒,但是到四世纪七十年代,南方的世家大族发现他们的政治地位被北方人篡夺,因此准备改奉一种新兴的教派,虽然这个新教派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天师道的影响。
正如张道陵的天师道声称自己比其他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的各种教派高明一样,这种新教派也声称自己高于天师道,但是它却没有明确抵制天师道信徒所信奉的旧教规,而是降低天师道祭酒所推崇的神灵的地位,使其位居“上清派”神灵之下,这样就能很好地适应新教派信徒的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上清派的道经源于杨羲(330-?)的扶乩,他作为一个神媒取代了天师道的祭酒,迎合了南方贵族许谧(303-373)及其家族的需要。杨羲扶乩的书法被呈献给许谧,许谧发现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南方久远的方士传统和北方新传入的宗教理论融合发展为一种全新的宗教实践和教义,这对于一个身处高位,又缺少知己的朝廷要员来说非常适合,他急需与彼岸世界的密切联系。
这些新造的上清经书在南方社会非常流行,其内容主要与许氏家族在东晋都城附近的茅山归隐生活有关。杨羲手书的上清经书受到热烈追捧,还出现了很多摹本。道经造作风行一时,这极大地激励了葛巢甫(他的妻子来自许家)和四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其他人。他们造作了大量的灵宝派道经,既延续了以往宗教信仰,同时呈现出新的特点,即吸收一些佛教的教理教义使道经看起来更加新颖。我们知道五世纪南方出现的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都出身于当地的古老世家,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给不同道派的经书划分等级,最基础的是《三皇文》,它代表西晋末年北方流民到来之前南方的古老宗教,其上就是灵宝派和上清派经书。
虽然茅山道士最终享有了最高地位,但上清和灵宝两派孰优孰劣,很明显是由上述高官的支持程度所决定。不管怎么说,在这段历史时期,不同的道教信仰流派似乎形成了一种更高级别的宗教——本土宗教,其各个派别都一致反对佛教所提倡的各种教义。在这个过程中天师道对其地位颇感困惑,一方面祭酒们要负责满足高门士族的精神需求,然而他们同时却和乡野鄙俗的民间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祭酒们不时地和地方民间宗教作斗争,不仅损毁了其作为高级宗教的最初倡导者的地位,而且似乎天师道本身也蕴涵着放纵的因素,这些都深深地扰乱了士族们的神经。
于是我们发现在北魏统治时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个改良的道教,它力图清整在此地传播的天师道。其创始人寇谦之出身高门士族,他分别于公元415年以及423年在嵩山得到神授。这个教派的主要支持者崔浩(381-450)也是士族出身,在少数民族的朝廷中担任司徒一职。在中国北方苛刻的政治体制下,神权如果不直接依附皇权就几乎是无所作为,于是这些没有靠山的道士很快就把神授的宗教介绍给北魏统治者太武帝(424-452在位),其教旨很受崔浩以及北魏皇帝欢迎。天道神授是神化老子的依据,自汉末以来,老子以不同的儒家圣人形象现世,如化身李弘,并以其名号发动了多次救世起义。但是这一次圣人却对作为道教管理者的拓跋氏皇帝表达出了一种强烈的建立良好秩序的愿望。让皇帝接受这种汉族圣人发起的宗教生活革新,更加符合崔浩力图汉化北魏政权的企图。
自从公元425年以来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直到崔浩认为必须要对作为天师道一直以来的斗争目标的异端邪教以及非本土的佛教作一次清洗为止。灭佛事件发生在公元446年,但它并没有将改革后的新道教确立为北方无与争锋的宗教。不到10年,三位参与这次灭佛运动的主要人物都相继离开人世。由于失去了朝廷支持,寇谦之发起的这次改革运动难以继续下去。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迄至五世纪末,中国南北道教虽发端各异,却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去取代佛教。
当历史的年轮又跨越到下个世纪,随着茅山派以及其他富有哲理的南方道派传入北方,新一轮的宗教融合又开始进行。南方道派的北传大概是由于公元六世纪上半叶南方萧梁王朝对道教严格限制所引发。大量的事实证明,当北周武帝(560-578在位)即位时,道教早已依附于政治,这个时候的道教无论从组织上还是从教义上都能与它的竞争者一决高下。
的确,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了大量的佛经,其内容既有虔诚信仰的传教内容,还包含精妙的佛教哲学。同时,佛教还带来了一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制度化力量:禁欲的僧侣放弃所有的世俗生活,把毕身奉献给他们的宗教;同时,提倡供养宗教的价值,这种观念使得寺院很快获得了大量的捐赠财富,这为僧侣们的清修生活创造了条件。虽然从财富上比较,道教从未超过佛教,但是道教还是从佛教提倡的慈善、宗教生活等概念中获益颇丰,这些概念与中国本土宗教的价值观相去甚远,因此道教也吸纳了这种全职的,有些甚至是禁欲的僧侣制度模式。
与佛教相比,道教的存在要容易得多。道教可以不需要道观就能很好发展(现在也如此),而佛教却总是因其拥有大量的财富而遭朝廷嫉羡。全职的和自养的道士之间以及禁欲的和能结婚的道士之间都没有清晰的划分。和尚们被要求要与世隔绝,而道士们却并不一定如此。因此,虽然我们用“道教(Taoist church)”这个词来指道士及其信徒,但这仅仅是用一种简洁方便的权宜称呼来概括这种十分松散的群体,该群体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与基督教教会甚至中国的佛教团体都大相径庭。虽然给道士下一个清晰的定义毫无疑问符合朝廷的利益,也许甚至还可以赋予道士一种类似于僧人的精神生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定义只可能是某种模糊的概念。
因为道士传教的内容不关注人类的状况,而最擅长与神灵进行交流,所以道士能够靠传经等类似活动所获得的费用独自生活或者与家人住在一起。例如,天师道的祭酒就似乎是作为教区中的一员生活在教民之中,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并不是因为脱离了红尘俗世,而只不过是道法高深。他们的宗教领袖地位一直是世袭,尽管张道陵家族的世袭从未间断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值得怀疑。
与世俗社会联系密切,这为个别的道教首领利用道教的救世传统来发动群众起义对抗朝廷提供了可能性。虽然佛教的信奉者指责其对手有煽动造反的不好倾向,但却显然忽略了六世纪末佛教的救世信仰也同样导致了人民起义。由于社会各要素对统治者的忠诚具有不确定性,而统治者对宗教的支持则可换来对社会的有力控制,因此朝廷有充足的理由对佛、道两教都提供施舍。
很明显,道教在与朝廷打交道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是本土宗教。一方面佛教尽管已经尽量适应了中国的各种环境,但它仍然保留了明显的世界宗教的特质,另一方面,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始至终都是采用本土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提倡个人为其所作所为负责,这与道经中所表达的逝去的祖先会赐福保佑整个家族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印度人关于时空、关于宇宙循环以及大千世界的宏伟思想体系在道教的发展过程中都被吸纳,不过这也仅仅是作为中国人对物质世界,尤其是神州大地以及其上的神山圣河的基础认识的一种拓展。
与此同时,道教远远超越了儒家神圣经典中的天、地、人概念。特别是它让帝王,又称“天子”,在道教中扮演沟通天人的中介,这与汉朝儒家所构想的理想帝制相比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道教用这种方法来稳固统治者的地位,这在六到七世纪中国北方王朝并立,帝王们的地位经常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颇具诱惑力。因此北周武帝崇道废佛的决定也许正是基于政治角度的慎重考虑而非出于宗教偏见,这也仅仅是他为了创建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最后一统天下所采用的措施之一。
北周武帝的宗教政策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感到非常困惑,他们有时把他描绘成一个对所有宗教都非常敌视的人,然而他又会对那些能给他带来直接好处的宗教提供支持②。周武帝登基之初,天师道涉足佛道之间的辩论,却因为煽动起义以及道德败坏被佛教屡屡指责,然而在皇家发起编撰的道教类书《无上秘要》中,我们却发现道士以及道教科仪并没有被佛教所诟谇。这部道教类书由南方贵族道派编撰,而其中的科仪部分则由皇帝自缵或者敕纂而成。然而,很明显此书中的科仪部分吸纳了大量的天师道以及佛教的传统。换句话说,皇帝似乎计划把当时所有的宗教都吸纳到他能牢牢控制的道教中来。
但是这个大胆且富于想像的政策在周武帝578年驾崩之后没有继续下去。当隋朝最终实现了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之后,它更关注的是利用现存的宗教来整合这个新兴的帝国,而不是只发展单一的宗教模式。众所周知,即使算上道教,隋朝的宗教格局还是由佛教所支撑。因为佛教正是在长时期的分裂中发展起来的,它事实上跨越了不同文化和社会的鸿沟。相反,道教思想的潜能作用在当时却影响甚微。
隋朝的宗教政策虽然有效但却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而且这些有效的政策并没有被传递给随后的王朝。隋帝国的轰然倒塌引起了一种混乱,精心建立起的宗教政策显得毫无用处。这并不是否定隋朝宗教政策的成效,而是因为唐王朝从始至终都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讨论道教与唐王室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本论著的篇幅有所增加。除非我们对整个道教史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否则唐朝道教的研究必定是围绕宗教与政治的关系③。因为无论唐以前道教的地位如何,唐朝必须被确立为道教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高潮时期。甚至就连唐朝的得名也蕴涵有道教色彩④。
二、初唐的道教与政治
道教之所以能在唐朝宫廷中地位显赫,最常见的解释是:唐皇室姓李,而老子也据说姓李。因为自称是圣人的后代,所以唐朝皇帝从家族的缘由出发都支持道教。这个解释乍一看似乎苍白无力,然而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说,家族发端却并非小事。事实上,唐朝皇室的祖先是没有纯粹汉族血缘的贵族,在中国北方汉族社会中地位相对低下。因此,通过对道教的支持,高调声称自己是远古汉族圣人的后代,这对于提高皇室家族的声望是一条非常必要之路。
非常奇怪,在公元七世纪初,李姓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上流社会而言。正如前面谈到的,老子和相关的人物李弘都被认为是潜在的救世主,他们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出现在历史当中。关于“李氏救世”的谶语应该被认为是唐朝成功建立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或许还记得周期性出现的谶语都具有明确的意图,“李氏代隋”的确是一位姓李的皇位觊觎者提出来的⑤。如果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那反倒有些令人惊讶,唐朝是由贵族首领所建立的,而非农民起义,因此与传播到北方的富有玄理的南方道派惺惺相惜。在南方道教中,“李氏救世”谶说的革命政治意义已大为降低。
更有可能的是,唐朝的创立者利用了这些成熟道派信徒不满隋朝偏爱佛教的情绪。分析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十分小心,虽然部分唐朝的开国功臣的确是道士出身,但是另一些政权的竞争者,虽然并不都姓李,却也成功地获得了道教的帮助⑥。因此,用神迹来衬托唐朝的建立毫无疑问反映了道教出于自身的考虑而提供支持的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道教与帝国之间的明显联系,只有在其成为政治现实后才被记录下来,所以在最早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
与其从建立帝国的背景中直接探寻唐朝支持道教的原因,还不如考虑北魏和北周支持道教的早期历史背景,这涉及了一个更深的缘由。不仅仅是姓氏上的巧合,唐朝支持道教也许可以看作一个兴起于北方的皇朝在面对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矛盾时采取的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控制着中国大地上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长达几个世纪。
关于唐朝建立者李渊奉道的最早记录尽管有些随意,但很好地阐明了道教在凝聚北方各民族,使其热心尊奉汉族的崇拜的潜在作用。在公元617年,甚至在李渊起兵反隋以前,他就已开与东突厥人对话之先河。据说在完成马匹买卖后,突厥首领进入了一座老子庙,而未来的皇帝却紧跟其后。这件事之所以被记载了下来,是因为在李渊的随从中有一个道士,他对进入庙门的先后顺序非常不满⑦。
在唐高祖李渊以及其后的唐太宗统治时期,宗教的外交价值得到了重视,朝廷对道教的支持可见一斑。在公元624年以及643年前后,应朝鲜高句丽王朝的邀请,唐朝两次派出使团前往朝鲜传播道教。据说使团由道士组成,他们带去了道教神灵的图像,并且讲授《道德经》。高句丽的学生还被允许到中国来学习道教,正如他们的同胞以及各国人民来中国学习佛法一样⑧。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647年,唐太宗要求佛教的朝圣者玄奘法师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以便其在印度传播就不奇怪了。零星材料显示,在八世纪早期,唐朝廷还提出了在土蕃传播道教的类似计划,大约与此同时,在公元735年,日本人也提出了和高句丽人一样的请求⑨。在中国版图边缘,有一个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佛教传播中心——敦煌,事实上在敦煌手卷中就包含很多道经,再往西边,远至哈剌和卓城还出土了一些道符,甚至还有道观的遗迹。这些都表明,唐朝皇帝的确希望道教能传出汉地,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太多实质上的外交收益⑩。
另一方面,在初唐的两位帝王时期,道教并没有在国内政策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初唐的宗教政策总的来说似乎与先前的王朝有很明显的不同。虽然隋朝对佛教的支持力度要大很多,但北周和隋朝都在都城建有道教机构作为官办的道教学习中心(11)。这些机构都不是由初唐的统治者所建立,除了在短暂的过渡时期,有个别德高望重的佛教高僧被赋予某种地位。与前朝不同,初唐政府更愿意直接与宗教组织打交道,而不愿通过全国或地方性的宗教监管机构。这段时期朝廷管理道教的具体措施现在已难觅踪迹,但是在公元648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体现出当时使用的管理方法。
据佛教类书《法苑珠林》记载,就在这一年,吉州(今天的吉安市)地方长官发现一位囚犯之妻持有《三皇经》,此经称“妇人有此文者,必为皇后”。经审讯后她招供此经得自于一位道士。这部违逆的道经被火速送往京城,在那里两位来自于清都观和西华观的道士被询问相关的违逆内容。道士回答,此经乃先前道士所抄,并非正统抄本,也不是他们所作。即便如此,此经还是被禁止。一位田令官指出此经对道教来说与佛教一样,是他们获得荫田的资格保证,如果此经被废,道士将不合受田的要求。在京道士于是请求用《道德经》代替《三皇经》。在得到同意后,所有的《三皇经》都被集中起来毁掉(12)。
这次禁毁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阻止此经流通的效果,后来此经又重新出现,并被冠以《三皇文》这个更加常见的名字。然而这次事件常常被用来证明唐朝的早期法令中的确有授荫田与宗教神职人员的事实,还有学者提出这种法令或许早在公元624年就已经在产生效力(13)。这次事件同样还表明《三皇文》被用来确定道士的资格。因为早在此事件发生以前两百多年,道经就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代表三个不同道派,与《三皇文》相关的道经被认为是最为通俗。到公元七世纪时,已经出现了更多精细的分类方法,其中包括与《道德经》相关的大量经书。照此看来,不太可能只有《法苑珠林》中所记载的经书才与道士身份相符。
对此事件更好的解释是对道教教义传播的具体实践,只有通过相关的传授仪式,经文才能传给信徒,这包括与佛教传戒相似的发愿等宗教仪式。这类仪式对《道德经》的束缚作用早在六世纪中叶就有很多外人进行过评论,八世纪以来与此仪式相关的文献都被保存在敦煌手卷中(14)。虽然我们目前这方面的知识还不足以断定七世纪中叶的道士把道经分为几种不同类别,虽然所有的这些分类大概都或多或少的有好辩之嫌,(例如在将道经分为三类时,《三皇文》被给予了一个很低的地位),但是七世纪末一次比较重要的分类中,不仅将《道德经》列于《三皇文》之前,而且按照传播的广泛度,在《道德经》之前还罗列了大量的道经(其中之一清楚地记载有方士的称谓)(15)。因此在公元648年以后,道教传授的经书很可能改由道教内部自己决定,而政府不再过问此事。
对此问题深究下去就涉及到西华观道士。敦煌道经中有几部的确是抄于都城的道观,这些道经表明这种机构起着把道教文献传播到全国各地的作用,这或许正是朝廷询问道长的原因。那些非法抄写的道经往往具有违逆的特点,这暗示了朝廷将鼓励集中抄写道经以便管理。在这个事件中,涉及到一个为道经作注的杰出道士成玄英,他也参与了前面提到的将《道德经》译成梵文的事情。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他的《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庄子疏》,以及为道教灵宝派的主要经典《度人经》所作的注。从他的这些著作以及别人对他作品的研究,可以将其归为一种诠释学派,其在注解道经时借鉴了大量佛教的概念(16)。
这种诠释的倾向实际上在唐以前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部分原因无疑是儒、道、释三教在历代帝王宫廷中正式论辩的结果。虽然这类辩论在唐朝后期退化为仅仅是论辩技巧的较量,但在公元七世纪它们却是各种思想冲突的一个论坛。因为印度宗教的哲学术语体系很明显更加精炼,因此道教经常光明正大地窃用对手的思想,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7)。尽管在公元624年举行的唐朝第一次三教辩论中,熟悉佛、道术语的大儒陆德明令三教折服,然而次年,高宗却将道教排位于前,先于儒家,而佛教因其外来,排在最末(18)。
太宗637年时,道佛排位,道在佛前的顺序定了下来,道教显然与唐皇室颇有关系。虽然在625年时还没有正式讨论此事,但在次年的一块刻碑上明确阐明了这种联系,并且除了记载道教曾经帮助过唐军的事情之外还包括很多内容。这块石碑刻于长安南面终南山中的楼观台,自五世纪起,这里就成为了中国北方道教的首要中心,并且与在此地区掌握政权的势力联系紧密(19)。隋朝灭亡时的观主岐晖显然早在公元617年就把决定自己命运的神签抛给了李唐,而且还以粮草资助唐军,随着唐朝统治的建立,他还被认为已名列仙班。对大唐的支持换来的是公元619年赏赐的土地,以及620年更进一步的慷慨捐助,并改所修道观名为宗圣观,这一行为表明唐朝的统治者已经尊老子为其家族先祖。公元626年的石刻铭文证明了这个意图,其对道观历史的回顾描述了公元446年以灭佛为代价来实现宗教的本土化的运动,这无意间展示了道教所负载的文化价值(20)。
关于初唐王朝与茅山南方道教之间的关系,现有的著述不多。当时道教活动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要数德高望重的王远知,他以在公元635年仙逝时活了125岁而著名。尽管隋朝对他极其推崇,但据说他却推测唐军会夺取政权。虽然写于公元642年的他的早年自传表明,直到唐太宗时期他才与唐朝廷密切联系(21)。如同七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事件一样,这时建立的联系只有在下一位帝王高宗时才会充分表现出影响,唐帝国的宗教政策开始缓慢变化,逐渐从前两位皇帝时期的少量参与宗教事务发展成全方位的神权政治。
注释:
①关于1980年以前道教研究的历史,参见马伯乐(H.Maspero)著,科曼(Frank A.Kierman,Jr.)翻译的《道教与中国宗教》第vii—xxiii页,艾摩斯特,1981年。接下来的概览基于文献回顾,特别是第一、二次国际道教大会,以及近期的一些重要著作:司马虚(M.Strickmann)的《茅山道教研究》,巴黎,1981年。但是我并不把灵宝经书都归源于葛巢甫,而更认同小林正美的研究结果,参见《刘宋时期灵宝经的形成》,《东洋文化》62期,第99—138页,1982年3月;以及《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思想和形成》,《东方宗教》60期,第23—47页,1982年10月。
②对北周道教的阐释参考劳格文(J.Lagerwey)的《无上秘要:六世纪的道教大全》,巴黎,1981年。漥德忠对这段历史的观点却颇有不同,参见他的《中国宗教的受容、变容、行容》第26—68页,东京,1979年。砂山稔却认同劳格文的观点,《关于宇文邕的道教序言》,《佛教史学研究》21:1,第46—75页,1978年6月。
③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两部力作:方永辉的《唐代皇室与道教关系之研究》,1966年香港大学硕士论文。此著作上半部分五次发表于《景风》第18期,1968年9月,第28—42页;第19期,1968年12月,第66—78页;第21期,1969年6月,第67—89页;第22期,1969年9月,第80—89页;第23期,1969年12月,第81—100页。另一部是孙克宽的《唐代道教与政治》,收于《寒原道论》,台北,1977年。贝恩(Charles David Benn)在其《玄宗时期的道教信仰研究》(1977年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中,除了对所涉及的时期有深入的研究之外,还有一章概述了唐初100年的历史。此外,中国和日本学者还有相当多篇幅不长的相关研究。
④参见吉冈义丰的《关于自白和见闻》注41,《古代佛教思想研究》第609—627页,东京,1972年。参照司马虚的观点,第214、273页,注39。
⑤参见《剑桥中国史》第3卷,第154页。
⑥关于道教与唐朝的建立,参见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176—187页,京都,1964年。关于道教支持政权竞争对手的例子,见《资治通鉴》卷187,第5850页。
⑦参见宫川尚志的《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179页。关于突厥人接受道教,见毗伽可汗于公元716年建议修建一座汉族式的都城,其中包含有佛道两教的寺院道观。《旧唐书》卷194上,第5174页。
⑧漥德忠,第189—192页。
⑨关于印度和《道德经》,参见伯希和(P.Pelliot)的《围绕〈道德经〉译成梵语的问题》,载于《通报》第13期,第350—430页,1912年。关于日本人学习道教,见《册府元龟》卷999,18b。关于土蕃与道教的关系,参见戴密微(P.Demiéville)的论文,收于苏远鸣(M.Soymié)编的《敦煌论文选萃》第6页,日内瓦—巴黎,1979年。
⑩见小笠原宣秀的《再论西域出土的寺院文书》,载于《印度学佛教学研究》8:1,第105—109页,1960年1月。
(11)山崎宏:《隋唐佛教史研究》第65—84页,京都,1967年。
(12)《法苑珠林》卷55,第708页a—b,参见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第77—78页,北京,1963年。
(13)参见滋野井恬的《唐代佛教史论》第131—136页,京都,1973年。
(14)参见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第469页。陈祚龙的《敦煌道经后记汇录》,收于《大陆杂志》25:10,第10—11页,1962年12月。劳格文的《无上秘要:六世纪的道教大全》第125—129页。
(15)《奉道科戒》中的这次排位后面将讨论,见吉冈义丰译文的第197—201页,《道教与佛教第三》,第161—219页,东京,1976年;吉冈义丰关于这些文本起源的观点在第77—159页。
(16)关于成玄英和他的学派,参见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的《七世纪以前对〈道德经〉的评注》第97—203页,第228—260页,巴黎,1977年。最近还有砂山稔的《道教重玄派表征——隋至初唐的道派》,载于《集刊东洋学》第43号,第31—44页,1980年5月;《成玄英的思想研究》,《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2集,第125—139页,1980年。
(17)关于唐朝发生的此类事情的研究,参见罗香林的《唐代三教讲论考》,收于《唐代文化史》第159—176页,台北,1955年。关于这种窃用源于辩论的明示例证,见镰田茂雄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第100—111页,东京,1969年。
(18)《旧唐书》卷189,第4945页。《集古今佛道论衡》卷2,第318页。
(19)关于这个中心的简史,参阅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第261—264页。
(20)《金石萃编》第41卷2b—3b,上海,扫叶山房,1919年。孙克宽在注③的引文中也推测过岐晖的角色。
(21)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第47—50页,收集了王远知的所有早期资料。
标签:天师道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历史论文; 道教起源论文; 道教论文; 日本道教论文; 宗教论文; 道教传播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道藏源流考论文; 道德经论文; 道士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