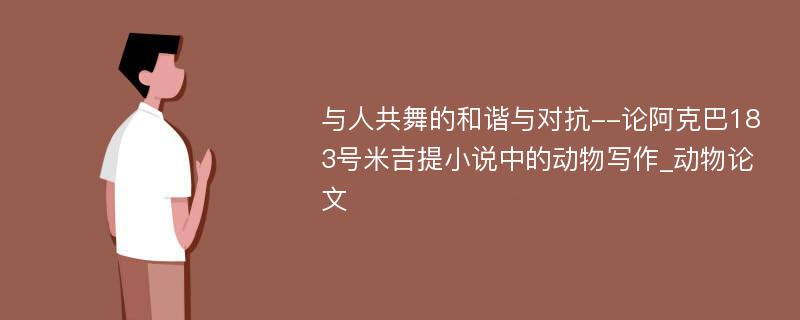
与人共舞中的和谐与对峙——试论艾克拜尔#183;米吉提小说中的动物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共舞论文,试论论文,艾克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14)04-0062-05 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以来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其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曾一度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又有一大批优秀作品相继问世,诸如短篇小说《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瘸腿野马》《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单》《蓝鸽、蓝鸽……》等等,作品的价值得到了研究界的一致好评。特定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哈萨克族人与动物的特殊情感关联,身为草原之子,艾克拜尔的小说中随处可见牛、羊、马等动物的身影,不仅透出清新的草原气息,也显示了他对于动物的真实情感,对动物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的希冀与守望,以及这些情感背后,对现代社会人类价值转变后的定位与反思。 一、基于生态的和谐相伴 伊犁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对大自然天然存在特殊而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小说中,关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俯拾即是:草原、跑马滩、天山、伊犁河,这些具有新疆特色的环境意象,在艾克拜尔的很多小说中既是故事人物活动的背景,同时也是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线索,其短篇小说《蓝鸽、蓝鸽……》《金色的秋叶》和《绿茵茵的草坪》等都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关注与热爱。这些小说中既有天山的巍峨,草原的辽阔,伊犁河的优美,也有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读完这些小说之后,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艾克拜尔小说创作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人们仿佛走进了哈萨克族牧民生活的世界,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人畜相伴的幸福与美好。哈萨克民族从古至今都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无论是旅途的迁徙、生活的陪伴,还是日常饮食的需要,都离不开动物的贡献,可以说动物在哈萨克族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小说《红牛犊》中描写了祖母对红牛犊的依恋之情,“祖母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便开始成日絮絮叨叨……你们爷儿俩哪怕就是奔到天边也得把它给我找回来呀。”[1](P191)对红牛犊浓浓的思念和牵挂溢于言表,业已成为这位哈萨克祖母心中热切的期待与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叔与“我”寻牛路上的执着也表现出草原人对动物的爱护与关怀。在这里,红牛犊不只是作为草原人食物的动物,它的身上自然承载着哈萨克族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存法则,他们将动物作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中的一分子,在生活的彼此接触与相处中慢慢融入感情,终究无法割舍。 动物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动物与人之间超种群的情感牵绊也是草原上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努尔曼老汉与猎狗巴力斯之间的情感称得上是艾克拜尔小说中塑造的最为自然的发生在草原上动物与人亲密相处的故事,动物与人之间的和谐联系在猎狗巴力斯与努尔曼老汉的情感上得到了有力的体现。猎狗巴力斯被刘书记带走后的“一个清晨,努尔曼照例起得很早,想从草滩上把那匹乘用马牵回来。一出家门,巴力斯卧在门口。一见主人出来,巴力斯‘哼哼’着,双耳朝后一贴,摇着尾巴,亲昵地嗅着主人身上的特殊气味,又跳起来将两条前爪搭在主人肩上。”“巴力斯回到了主人家里的消息,在阿吾勒里传开了,乡亲们都感到这是一件传闻——一条狗,居然能从遥远的城市跑回主人家里……”[1](P223)哈萨克草原世界里充满了温情,这温情源自动物身上的本能及其与人之间日久天长的相处。猎狗被刘书记凭借权力从努尔曼老汉身边带走之后,巴力斯挣脱束缚千里迢迢回到努尔曼老汉安身的阿吾勒,一种精神与情感在猎狗巴力斯身上涌动,这是动物们内心世界里存在的那些人的权力无法支配的情感激流。这“一别一聚”的背后,完满地表达了猎狗巴力斯对努尔曼老汉的那种超越物种、忘却族群的情感依恋。古罗马城徽上的“母狼育婴”图案蕴含着一种自然的胸怀,一只母狼面部狰狞,警惕地环视四周,表现出狼性的残忍与机警;然而它却又同时在呵护着两个人类的婴儿,它正在给两个男婴哺乳,这看似不可思议的情景表现了动物对人类本能存在一种特殊情感,而这种动物与人相互依存的美好在艾氏小说中更有体现。 狼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动物之一,然而在草原人眼里,它们的身影更多伴随的是野性与残杀。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中描述了一只夜袭羊圈的母狼,在被猎狗巴力撕扯住咽喉的情况下,仍旧撕咬着肥羊,“不住地用尾巴抽打着羊身,企图牵着肥羊溜掉”,欲将活着的肥羊“偷”回窝中。然而,这是一只单独的母狼,它如此不计后果的冒险,只是“想牵回只羊,让崽子们学会下口吃羊的本事”,可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独有偶,姜戎在长篇《狼图腾》中也描述过一则母狼护崽的故事,“为了教狼崽捕猎,母狼经常冒险活抓羔羊;为了守护洞中的狼崽,不惜与猎人拼命;为了狼崽的安全,常常一夜一夜地叼着狼崽转移洞穴;为了喂饱小狼,常常把自己吃得几乎撑破肚子,再把肚中的食物全部吐给小狼;为了狼群家族的共同利益,那些失去整窝小崽的母狼,会用自己的奶去喂养它姐妹或表姐妹的孩子。”[2](P257)母狼凶残的本性背后却隐藏了对狼崽们的温情与对狼族的无比忠诚,而这与人类身上存有的贪婪、冷漠形成鲜明对比。艾克拜尔笔下母狼的死亡源于对狼崽们的自然天性,作家以此反观现代社会里人类自身为了利益早已忘却自然天性所在,在这里也呈现出兽性对人性的一种诘问与痛斥,人类对非人类自然界的疯狂进攻令人触目惊心,而自身的精神衰微与病态却更让人扼腕叹息。 小说《蓝鸽、蓝鸽……》讲述的是与青春有关的话题,一群天上飞的蓝鸽见证了一群地上跑的孩子们的成长历程,美丽的蓝鸽是这群青年人青春、激情与美好的见证者。蓝鸽在小说中首次亮相的场景十分沉醉,“一群蓝色的野鸽,从下游河岸土崖群那高高的崖壁上的一个洞口里飞出,低徊着朝河面飞来。”“鸽群贴着水面溯流而上,它们忽悠的双翅看看就要蘸在起伏的浪端上了。”“鸽群在飞过他们的草滩近旁的刹那,忽然整体拉出一个漂亮的菱形轮廓,直向那湛蓝湛蓝的天穹深处飞去。”“鸽群的队形在不断地变幻着。那不同于碧空色彩的蓝色的群体倩影,十分洒脱地辉映在蔚蓝色的天幕上空。”[1](P16)蓝鸽群华丽地扑面而来,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与这些精灵们不期而遇,它们的轻盈、洒脱、纯洁如此这般猝不及防地闯入孩子们的心房,人类每一次心跳的律动都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也是自然生物种群极为重要的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处原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同贾兰斯所想的那样,“倘使此刻还在游泳……只要从河水里猛然挥出手来,一定可以让一只蓝鸽栖息在你大拇哥上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类自身能否以一颗善良博爱之心平等地去关照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是解决人类当前困境的最佳选择;可以说,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无间并非痴心妄想。一群跃动于天空的蓝鸽是青春舞动的旋律,它们载着青春的梦飞向远方的天际。这群蓝鸽是伴随这群少年成长的天使,同样这群少年也是蓝鸽之美的分享者。当少年们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发生巨大蜕变后重新返回他们儿时的领地——绿草滩,迎接他们的依然是那抹夕阳,那条永不停息的、流淌着的伊犁河,那群纯洁美丽的蓝鸽,“忽然,从那快要被他忘却的土崖壁上,飞出了一群蓝鸽。”那股喜悦的激流瞬间涌上中年贾兰斯的心头,令他的心紧缩了一下,时光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他不禁热泪盈眶,嘴中喃喃道,“你好!蓝鸽;你好!土崖……蓝鸽一如既往(它们一定是当年那群蓝鸽的后代,他想),在伊犁河上空——在蓝天和大地之间自由自在地翻飞、盘桓。”[1](P31)小说以一种恬淡的絮语式的口吻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生态和谐的图景,此刻人的心境与自然之境的切合度令人振奋。人类通过自然动物映照自我、反省自我,它们是人类自身成长成熟的旁观者与见证者。立足生态批评的视角,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界存在着丰富而多面的表意体系,可以说人类的存在与福祉与自然界其他种群是紧密相连的。在艾氏的小说中,人们看到了动物与人之间发生的超越工具理性的道德关怀和突破食物链式的情感牵绊,动物成了人的依恋,人也成了动物的一种寄托。 二、源于生计的欲望对峙 “意味”的悠长是艾氏短篇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点,这里的“意味”呈现的是文学创作中一种耐人寻味和意蕴的含蓄表达,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表达效果[3]。在艾克拜尔的诸多作品中猎人是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通常被人们赋予某种英雄行为与英雄主义的符号意义,这些猎人们的存在彰显并体现哈萨克民族的勇敢、机智,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草原人的一种生活状况。用生态的眼光再来回顾艾氏小说的全部,又能从中获得与之前不同的感悟,而这又再次提醒人们关于生态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功能:重申与重释经典。小说《披着羚羊皮的人》是一个充满了象征与隐喻的故事,其中暗含了多种多样的生态迹象。原先居住的村庄被战后的瘟疫“吞噬”,兄妹俩因此失去了亲人,不得已他们俩流浪到现在这片荒漠的草原上。为了维持生计,哥哥每天要伪装成羚羊的模样去诱惑羚羊,从而获取食物,可最终却因披着羚羊皮而被猎人误杀。小说中哥哥为了兄妹俩的生计,不得不披着羚羊皮去捕杀羚羊;而猎人也是为了家庭的生计把披着羚羊皮的哥哥误杀了,这些生命悲剧的发生,不论是捕杀羚羊还是误杀哥哥,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因个体的生存而造成的残杀。 当代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在散文《永生羊》中说,“羊生不为罪过,人生不为饥饿。”为了不被饥饿蚕食,人们不得不为获取食物而作出各种努力,有时甚至牺牲自我或是当前的自然环境。在这里,关注生命悲剧目的不在于反思食物链这一自然法则是否合理,而在于自然食物链背后所掩盖的人类基本价值观念[4](P43)。猎人凭借对羚羊生命习性的了解与把握,利用羚羊对同类的亲近感和轻防心理,通过“披羚羊皮”这般伪装与欺诈让羚羊成了猎人的囊中之物,动物对于人类的无可奈何,导致羚羊数量锐减,而这从某个层面上看会造成自然界生物种群失衡的可能。毋庸置疑,羚羊种群数量的减少也使人类不得不扩大捕杀范围,这为人类自身彼此枪口相向的遭遇埋下了伏笔。精心伪装下的人们,不仅欺骗了羚羊也欺骗了自己,无法区分自己的同类,形式上的误杀就成了自然上的必杀,人类的死亡也成了必然。可以说,人性的贪婪,使得人类自己的眼中只剩下占有与杀戮。然而,人类是否还应记起一句古语:“始作俑者,宁无后乎?”猎人在倒向大地的瞬间,“痉挛着扔掉手中的劲弓,拼命伸开了双臂,似乎即刻就要振臂飞上蓝天,去追回那支离弦的箭。”生命的最后时刻,猎人选择了“扔掉劲弓”,这从某种层面上暗示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追悔与反思,同时也体现了艾氏对发生在人类与其他种群之间的杀戮行为的质疑与批驳。 小说《瘸腿野马》[1](P314)讲述的是一件历史轶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人类自大与贪婪行径的批判。在无垠的草原上,一群野马在一块云影下静静地吃草,偶尔还打一阵得意的响鼻,骑士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与和谐,他拈弓搭箭射中了其中的一匹。伤了一条前腿的野马奋不顾身地想要逃脱。“高傲的骑士”却对它穷追不舍,最终“瘸腿野马”却把骑士引向了死亡,“那一匹企图摆脱死神的野马,穿过密林,挣扎着涉过河水,却跌倒在河对岸的苇荡里了。不一会儿,有一只不知来自何方的秃鹰,凄厉地鸣叫着,在苇荡上空盘旋……”小说中“高傲的骑士”带有一种象征意味,影射了人类的贪婪与欲望,对“瘸腿野马”的穷追不舍正如人类对千疮百孔的地球家园无休止地索取与占有。小说结尾处凄鸣的秃鹰是不是也在控诉人类这一路的血迹与杀戮?很多时候,人类还未来得及反思、修补自身的过错,生命的挽歌早已被非人类生命奏响。小说《天鹅》叙述的是哈萨克民族远古时代的一种印记,带有一定精神指向性的图腾信仰及民族传统文化是这篇小说的重要内容。高洁的白天鹅可以喻示、象征世界上那些美好事物,在它们身上寄托了哈萨克族人对世界、对未来、对命运的一种希冀与期待。“就在这一刹那,一幅奇异的图景映现在她眼前——在蓝幽幽的天幕上,有小小的两朵白云越过她头顶,飞向赛里木湖。不,那不是白云,分明是两只比白云还要洁白的天鹅!啊,天鹅呦天鹅,你果然就像奶奶的故事里所讲述的那般洁白。”[1](P392-393)“两只天鹅悠闲自得地拍着洁白的翅膀,向那蔚蓝色的赛里木湖面上飞去。渐渐,在湖面上低回盘旋,最后终于落在了水面上。”[1](P393)哈丽曼茜对白天鹅的执著追寻具有很浓的象征意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是一种对自然生态美好的有意选择,作家借助白天鹅这一纯净的生命意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遥远的过去,由此去追寻哈萨克族先民们的某些印记。人们经常借助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愿望,寄托一种理想,这种有意为之的行为体现了人的潜意识中的生态表达。对动物世界抱有一种可掬的情怀,诗意地歌颂动物的美好心灵,呈现出人类关于生态美学的审美姿态。 小说《增长的极限》言说的是,“世界不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未来,而是一个选择。”[5](P257)立足一种生态的视角,选择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再现。面对非人类自然界,需要人类倡导一种审美的态度和“够了就行”的价值选择。生态美学主张将生态审美的原则推行到现实生活中去,使人们掌握这些原则,并以审美的态度去对待自然。描写的隐喻性与象征性,可以把人们想象的触角指向人类的过去与现在——这可能是一种历史现象。《麻雀》可以说是艾克拜尔“微型小说”的代表篇目之一,“城市在年复一年地漫延,麻雀也在年复一年地繁衍。”“城市在成熟,简直要熟透。可它依旧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城市的上空,雀跃在属于城市的土地上。”人类在用钢筋水泥铸造城市的“铜墙铁壁”的同时,也无情地剥夺了自然界鸟类生存的家园。然而,鸟类顽强的生命力却给人们以新的希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阻挡不了自然生命的无限活力,在钢筋混凝土的隙缝间求生存的壮举令我们人类肃然起敬。艾氏以此立意,在批判现代社会的庞杂、无序给人们带来的紧张感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弱小动物顽强的生命力。一种动物生存的智慧,一种坚韧、乐观的生活姿态令人欣慰。生存空间被无情挤占,但它们依旧能找到可以栖身之地——那是一座中心邮电局的立柱,“那立柱上装饰着一片片的荷叶塑瓣,它就在某一片叶心里筑起了窝。它和它爱的结晶——第一窝鸟雏,就是在这叶心里破壳而出的。”[1](P169)这种先人一步的“破壳而出”的勇气令人钦佩,尽管生存艰难,但麻雀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生的权利。一只小小的麻雀,让人们感受到了自然生命的顽强与坚毅;在这里,艾氏试图传达一种强大的、不屈的生命力量,不论人还是动物,只要有这股力量做支撑,就不会迷失方向。而这种不屈的精神让人们读懂了人类与动物的内在统一性。 就自然整体而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动物,动物的繁衍生息同样离不开人类的态度,二者应该是和谐共处,相互依存,共享一片蓝天;然而,人类的贪婪与冷漠,不仅威胁到动物的生存,使人与动物的关系日益恶化,同时在人类身上也发生着一个个悲剧,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悲剧的发生便是贪婪与欲望背后的两败俱伤。正如俄罗斯诗人舍夫涅尔在《箭》中所说,那支射向猎物的箭“它环绕着地球飞,为的是扎进我的脊背”[6](P254)。从这种“生物环链”之中的相对“生态平衡”出发,“生态整体”原则主张“普遍共生”与“仁爱”的原则。任何事物,只要它趋向保持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应该像生态理论家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轻轻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平衡。”[7](P227) 三、回归理性的伦理延伸 人类通过与动物的朝夕相处,逐渐发现了动物身上有利于自身的价值与功用;与此同时,动物在与人类的相处中对人类产生了一定的依赖,从而形成了艾克拜尔笔下游牧民族与动物之间和谐的、美好的相伴关系。然而,人类在了解到动物价值的过程中变得愈加贪婪,而动物也在人类不断膨胀的欲望中为了生存而不断地改变自我。艾克拜尔以“局内人”的姿态经历与体验了哈萨克族的现实生活,凭着对草原民族自有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挚爱,积极探索哈萨克民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在《王蒙师剪影》[8](P30)一文中,作家在北京看到被开发作为经济手段(为游人收费照相)的马和骆驼时,不由得感叹,“瞧,那匹可怜的马。”“我这是生平头一回看到马也会有这样一种商品价值,不免有点猝不及防,只是怔怔地望着它。”在作家眼中本应该自由自在奔驰在辽阔草原上的小马驹,是与之为伴的邻居,是为他提供食物、打发消闲时光的生命;因此,作为报答,他有责任保全其免受过度残忍的伤害,以此向它们施加恩赐与回报,哪怕只是一句由衷的感叹和一个怜悯的眼神。短暂的停留中,艾克拜尔看到了“那马瘦骨嶙峋,浑身的汗毛尚没有褪尽,迷瞪着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勉强支撑在那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让马儿离开了草原,让骆驼走出了沙漠,商品社会对动物本性、功用的异化与过度开发,让艾克拜尔这样的草原儿女不免有些不知所措。动物们在生存空间的城乡迁徙中表现的“水土不服”,喻示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作家对家园意识的某些隐忧。少数民族的狩猎文化让他们所有的思考、信仰及行为都与自然界的动物们融合在一起,将动物看成是与人一样平等的存在,视他们为人类的朋友,艾氏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游牧民族狩猎文化观念中“物种平等”和生命伦理延伸的渴望。 狼是草原生态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员,也是许多当代作家比较钟情的描写对象,在艾氏的作品中写到狼的就有好几篇,从《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中狼为了偷肥羊而与人的勇敢对峙,到《初次遇狼》中狼的智慧逃生,不难窥见生态环境的变化对狼的影响与改变。在现代科技帮助下,坐在车上近距离地与狼同行让作家对自然界中的狼这一族群有了清晰的认知。与狼同奔的草原之行,给艾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展现了与传统言说不同的人狼相处的理想模式。狼在逃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机智、灵敏是狼对于这个日益社会化的自然被动适应与接受的结果,人类不断侵占它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变得像“狼”一样富有攻击性,而狼面对人的侵占与攻击却在不断地妥协,在这“一进一退”中间,人类的自大昭然若揭。在作家对狼生存智慧的赞美、惊叹的背后,也流露出他对生态伦理的呼唤和对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一种渴望。“生态主义是一种道德理论”[9](P23),在生态系统彼此关联的基础上,人类应将道德关怀延伸到非人类自然界,彻底摒弃“人类价值标准”,关注非人类的“内在价值”。不可否认,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来看,狼是伪善贪婪、狡猾凶残、血腥的代名词;然而,如果从维护草原的生态平衡来看,狼又是生态环境链条的重要一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保护狼就是保护草原,就是保护身边的自然环境。因此,在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关系时,要将触角延伸到人与动物的情感当中,一方面揭示出人与动物的完满、美妙的生存状态,使动物成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寄托和依靠,另一方面也启示人对于现实状态的反思和对于人与动物的和谐回归之情的追求。对非人类存在物给予尊重的人类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比起那些只有纯粹工具性态度的人类群体能够更好地繁衍生息。 四、结语 艾克拜尔·米吉提是一位十分值得研究的重要的当代作家。身为哈萨克族作家,他能够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中寻求精妙的切合点并融会贯通,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去审视、思考当下的现实生活。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读,可以看出作家在创作选题方面的一种独特的追求。在艾氏笔下,无论是似敌非友的狼还是朝夕相处的牛羊、猎狗,哈萨克族人都会用一种真诚善良的心来面对,用仁慈与爱护守望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用崇拜与敬畏守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心怀仁慈、知恩图报,面对生活的“助手”时,悉心照料、相知相依。他们保护生态、感恩自然,对于自然的变迁感同身受、忧心忡忡。他们的包容与尊重展现的是自然与心灵的靓丽风景,探索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永恒话题。事实上,立足生态主义这一角度来看,人类应该形成一个关心和关怀的“生物共同体”,既作为关心者,又作为被关心者,并把她作为人类谋求福祉所需要的自然基础。生态道德与生态责任的延伸更要超越这个共同体的一般主张,超越我们熟悉的家庭成员、邻居、民族组成的共同体的观念,将这种关怀和守望延伸至非人类生命,这些共同体成员对共同体之外的生命富有超越这些共同体的更为广泛的责任。在持续的交流与对话中不断反思和检验自身,达到人与非人类自然界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