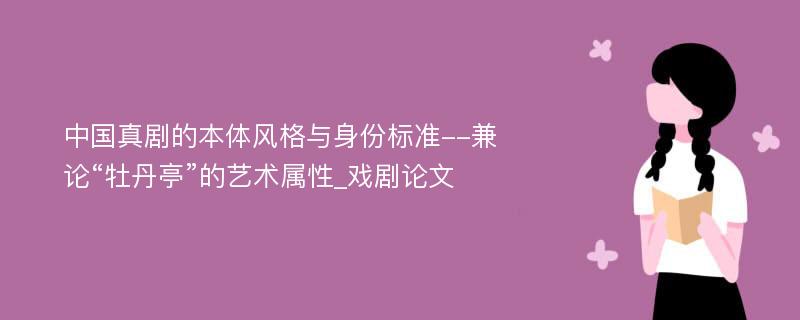
中国正剧的本体风格和鉴别标准——兼论《牡丹亭》的艺术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文,正剧论文,中国论文,属性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三大戏剧体裁中,正剧研究较之悲剧和喜剧研究薄弱得多。因此,面对林林总总的戏曲作品,人们常感到:由于“正剧具有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双重情感色彩。这一点,与我国悲中有喜的悲剧、喜中有悲的喜剧相类,这就使得正剧与悲剧、喜剧很难区分。”[①]实际上,“正剧在中国戏曲剧目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字远远超过悲剧和喜剧。”[②]因此,从理论上加强正剧研究,意义不仅是对戏剧理论自身的拓展,更重要是有益于为数众多的戏曲剧目及其艺术规律研究的深化,甚至还可以使一些因“很难区分”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得以解决。本文试图以三大戏剧体裁审美特征相比较的思维方法,结合《牡丹亭》艺术属性的讨论,对正剧的本体风格和鉴别标准进行考察。
一
戏剧文学的最终价值,体现在观众参与创作的过程中。戏剧文本的美学风格,在观众的审美效应中得到最实在的显现。悲剧冠之以“悲”,喜剧冠之以“喜”,正剧常被称为“悲喜剧”,都清楚表明,三大戏剧体裁命名的思维视点,首先是瞄准观众的审美情绪。说得确切些,观众审美心境和审美情绪的个性效应,是衡量和评判某一文学样式艺术风格和鉴别标准的重要依据。
正剧的情感结构与悲剧、喜剧一样,存在着“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双重色彩”,这是比较容易把握的艺术共性。然而,由于作家创作意图和文本内在基因的特殊规定,在不同体裁的戏剧作品中,两种情感的组合方式及其观众心理效应各各不同。
悲剧所以为“悲”剧,原因无疑在于它所激发的是“悲”的情感主流。中国悲剧虽然常常交错着“喜”的因素,但它大多是“悲”的一种烘托和反衬,“以乐写哀,倍增其哀”是中国悲剧情感组合的常见现象和最高原则。正如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言:“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③]然而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往往是“无边笑哈哈,不觉泪纷纷。”[④]
对中国悲剧这一民族风格,学术界常以“悲喜交融,苦乐相间”去概述。其实,两种情感的交融渗透不止限于悲剧,同样存在于喜剧和正剧。不同的是:悲剧坚持“以悲为主,以喜烘悲”的原则。因此,在谈中国悲剧这一民族特色时,不要把两种情感组合的艺术共性,即“悲喜交错,苦乐相间”的一般性视为中国悲剧的特殊性。即使中国戏曲评论中所言的“于歌笑中见哭泣”、“寓哭于笑”、“苦乐相间”、“忽而乐,忽而哀,忽而喜,忽而悲,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等,也不要轻易看成是对中国悲剧风格的指谓。只有像李渔那样,在强调“说悲苦哀怨之情”的主调下,提出“抑圣为狂,寓哭于笑”,这才真正切入中国悲剧“以悲为主,悲喜交融”的艺术风格。
喜剧情感的组合方式虽然同样具有“悲喜交融,苦乐相间”的特色,但由于作家创作态度和剧中人物、事件、冲突等方面的表现方式不同,故两种情感交融结合的结构与正剧和悲剧的情感结构大有区别。从大量戏曲文学的创作实践看,“以哀写乐,倍增其乐”,或者“以喜为主,喜中见悲”是中国喜剧的一贯追求,也是中国喜剧有别于西方喜剧的主要风格。
正剧所以为“正”,同样不在于“具有悲喜交集、苦乐相错的双重情感色彩”,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因素经过作家的艺术整合,生成一种既不是以“悲”为主,也不是以“喜”为主,而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之间,性质处于“中正平和”状态的“情感结构”。对这种“情感结构”的特殊色彩,以往人们常用“悲喜混杂”或“悲喜结合”去说明,其实这也没切中正剧效应的真正个性。对此,西方第一次给这一戏剧体裁起名为“正剧”的黑格尔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正剧是“处在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第三个主要剧种”,它的审美原则是“把悲剧的掌握方式和喜剧的掌握方式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并不是使这两对立面并列地或轮流地出现,而是使它们互相冲淡而平衡起来。主体性不是按喜剧里那种乖戾方式行事,而是充满着重大关系和坚实性格的严肃性,而同时悲剧中的坚定意志和深刻冲突也削弱和刨平到一个程度,使得不同的旨趣可能和解,不同的目的和人物可能和谐一致。……正剧就是由这种构思方式产生出来的。”[⑤]可见,黑格尔的“正剧观”与那种正剧即“悲喜混杂剧”的观点明显有别。他反对“悲喜并列”或“轮流出现”的主张,他认为“正剧”是两种情感“互相冲淡而平衡起来”的“新的艺术整体”。在这里,黑格尔虽然没有正面论述正剧的情感效应,但从他对“主体性”(剧中代表人物,笔者注)的行为特征分析可知,“充满着重大关系和坚实性格的严肃性”可视为正剧审美风格的内核。因为一个剧本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品格,主要体现在剧中代表人物的行为表现中。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正剧”之称,但有“正声”之说。《荀子·乐论》曰:“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这里的“正声”指的是“中正平和之音”。荀子认为“正声”感触人心时,其审美效应是“顺气应之”(“顺气”即适应正常生理节奏的“平和”之气)。当“顺气”产生并形成一种可以感触的东西——“象”时,便能起到“治生”的功效,用荀子的话说即“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的功效。荀子的“正声顺气说”,与我国辞书中的“正者,矜庄也。”(《辞海》)“正者,正中平直,与偏斜相对。”(《辞源》)的释义同于一辙,都是源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中和”精神,这与黑格尔的“和解严肃说”有不谋而合之处。可见,正剧所以为“正”,从审美效应看,首先给人以“中正平和,矜庄严肃”的审美感受,这既是正剧风格的主要特征,也是正剧鉴别标准的重要方面。
为什么正剧给人以“中正平和,矜庄严肃”的美感效应?原因可谓多方面,但就戏剧本体构成的主要因由看,冲突展开的特殊风格与人物行动的特殊表现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是中外戏剧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公认的准则。然而,不同的戏剧类型有不同的冲突走向。悲剧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⑥]也可以说是美丑相抗,美被丑扼杀的冲突,观众目睹美的毁灭沉浸在悲哀和怜悯的强烈共鸣中。与此相反,喜剧冲突是美的力量压倒丑,战胜丑的冲突,观众的审美心境处于喜悦超脱的主调上。正剧冲突与悲剧、喜剧的冲突同中有异。
与喜剧比较,两者所表现的都是“美胜丑”或“正敌邪”的冲突情结,两者都让观众带着“喜”心态走出剧场。不同在于:喜剧的“战胜过程”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逆变性”的过程。所谓“偶然性”,即剧情展开由一个个出人意料的事件或情境构成;所谓“逆变性”,即人物的行动发展往往出现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突然悖反变化的情状。康德的“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⑦];赫斯列特的“荒谬可笑或喜剧之事则是……我们一系列的思想突然颠倒次序,使精神失去戒备,忽然进入趣味盎然的快感”[⑧];弗洛伊德的“我们身上经常存在抑制的作用,而当我们听到天真的言辞,抑制的作用就会骤然解除,从而产生笑”[⑨];都是着眼于“偶然突变”这一契机揭示喜剧的笑因。
为什么喜剧节奏充满着一系列的“偶然”与“逆变”?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一个人对某种现象发生注意的时候,他的各种心理活动就集中指向那个对象,他的感觉、知觉、思维等都高度活跃起来。……如果某人的内容与形式相一致,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期待,就按照常理和逻辑发展,对这人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一步一步地顺利前进,结果,我们的想象、期待与客观事物完全一致,这就不会有什么惊讶、出乎意外之感,也就不会发生喜剧性的笑。当一个内容与形式相矛盾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的注意力及想象、期待起初老是往一个方面发展,到最后,事实却完全相反,想象及期待完全落空,这就引起我们发笑。”[⑩]这里所言的“出乎意料”和“完全相反”,同样是对喜剧冲突的“偶然性”和“逆变性”的把握。
正剧的“战胜过程”虽然不排除“偶然性”和“逆变性”事件,但从冲突发展的总体态势看,它是一个充满“必然性”和“顺变性”的自然情结。原因在于:正剧是“融悲喜于一炉的写实艺术”,[(11)]或者说是较之于悲剧和喜剧更接近人生现实的艺术。它不仅“用真实而自然的手段来打动我们”,而且“除了享受其他戏剧形式所共有的便利之外”,“它只能有一个风格——自然的风格。”[(12)]说得具体些,正剧冲突的展开,既不像悲剧冲突那样在强烈的爱憎中表现与现实人生有一定距离的“崇高美”,也不像喜剧冲突那样在强烈的阴差阳错中表现不易多见的幽默或滑稽,而是以平实、自然、真实的笔调,把冲突的视角对准人们熟悉的题材,对准平凡人身上时有发生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中外正剧所以较悲剧和喜剧为数更多,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忠实图画”,而且有人们进行娱乐和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此外,喜剧冲突的完美结局,必然体现鲜明的“喜剧性”,即在“突然逆变”的矛盾冲突中引发观众的乐感或笑声。正剧的最终结局由于受情节本身的“必然性”内因影响,虽然“美胜丑”的结局同样可以令观者喜悦,但由于这种喜悦大多是顺势而来,即在观众先前的审美心境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可胜”的必然定势,因此难以产生喜剧结局那种“突然逆变”效果,也难构成真正的喜剧性。如被视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的《西厢记》,在张生高中返回与崔莺莺成就“眷属”之前,作者让郑恒突然出现,并让他编造谎言说张生被卫尚书招赘。这时老夫人喜出望外,连崔莺莺也不得不信以为真。就在老夫人备好筵席让郑恒前来娶亲的关键时刻,张生突然归来,有情人几经磨难终得团圆。这种充满“突然性”和“逆变性”的结局,是喜剧性结局的典范模式。而像《单刀会》、《白兔记》、《浣纱记》、《牡丹亭》这类正剧作品,它们的结局尽管有“团圆”之“喜”,但由于作者没有使用“突然逆变”的手法,而是在循序渐进的态势中收煞,故虽然见“喜”,但不构成“喜剧性”。
正剧与悲剧相比较,相同的在于:两者的情节发展和冲突走向都是以“渐变性”为基调;不同的在于:悲剧的“渐变”是丑逐渐扼杀美,正剧的“渐变”是美逐渐战胜丑。
如果正剧与悲剧冲突发展的“渐变过程”真是如此泾渭分明,要鉴别判断当然不难。但由于中国正剧的冲突线索往往不那么单纯,大多数作品都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即悲剧性事件和喜剧性事件)交错其中,故鉴别起来确实有不同一般的繁难。《牡丹亭》一剧的艺术属性,目前有悲剧、喜剧、正剧三种不同的看法,原因就在于剧中既有杜丽娘“为情而死”的悲哀,又有杜丽娘“为情而生”的喜悦,且两者在剧中的比重都不轻。再加上评论者的视角不同,标准不一,出现分歧意见就成必然。不过,如果在掌握前一鉴别标准(中正平和、矜庄严肃)的基础上,又能把握正剧呈显“以正压邪,自然顺变”的冲突走向这一标准,问题的解决就容易了些(见第四部分)。
三
冲突虽然是戏剧的生命,然一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说到底是由剧中代表人物的行动历史去体现。正剧的审美效果和冲突走向所以以“矜庄严肃”和“自然顺变”为特征,其艺术根基决定于剧中人物的行为表现和行动历史。从中国古典正剧人物刻画的普遍现象看,成为显著特征的是:代表人物的行为表现和行动发展,大都显出“和谐统一,昂扬坚实”的风格。是这,使正剧人物与喜剧性人物划清界限。对此,应深入比较。
追溯中国喜剧的演变历史,从原始神话的“半人半兽”刻画开始,华夏喜剧(美学范畴)的艺术思维与西方喜剧一样,都十分注重通过“不谐调”的艺术情状显示作品的喜剧精神和引发观者的乐感心态。如原始时代真人假扮兽物的“百兽率舞”,先秦时期“言非若是,说是若非”的俳优风范,汉代“头戴牛角以相抵”的角抵戏表演,唐代“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的傀儡戏创作,宋金两代“全以故事,务在滑稽”的杂剧艺术,无不以“真假反差”或“正反逆比”的“不谐调”手法,显示中国喜剧形态的审美品格。难怪刘勰《文心雕龙》中以“辞倾义正”为“谐隐”的注脚,司马贞《史记索引》中以“能乱同异”为“滑稽”的功能。中国喜剧成熟以后,虽然较之西方更富有歌颂的传统,然而,不管是肯定性喜剧人物,还是否定性喜剧人物,他们无不体现“寓庄于谐”的特点,这是喜剧人物的显著特征,也是喜剧人物与正剧人物的最大区别。正如黑格尔所言:在正剧那里,“主体性不是按喜剧里那种乖戾方式行事,而是充满着重大关系和坚实性格的严肃性。”这里所言的“坚实性格”,就是指正剧人物在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或动机与效果的“和谐统一”中显示自身的严肃性。如关汉卿《单刀会》中的关羽,他明知江东鲁肃所设的“不是待客的筵席”,而是“杀人的战场”,但为了卫护汉家气节,他一身忠诚赤胆,单刀赴会。筵席上,他大刀在握,直言不讳地把鲁肃的“三计”挫败。其中,丝毫不见关羽“乖戾”的表现,全然一种昂扬奋进,势不可挡的英雄气派。关羽这一正剧典型与关汉卿笔下的喜剧典型赵盼儿和悲剧典型窦娥判然有别。
不过,矜庄严肃,和谐统一不止限于正剧人物,悲剧世界也是一个“严肃的世界”,“悲剧的实质,一方面在于善恶两种社会阶级的理想、意志和由此而产生的行动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两种阶级力量,两种对立的实际的力量对比的特定性质。一方面是理想、意志、立场的善恶的限界,一方面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际力量对比,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而又不能不加以区别的。前者决定悲剧的倾向性,后者决定悲剧的严肃性。”[(13)]可见,把握正剧人物行为表现的特殊性,关键在于区别正剧人物与悲剧人物的不同。
在悲剧和正剧这两个“严肃世界”中,悲剧人物以其震撼人心的“悲壮感”和“崇高美”显示自身的“严肃性”,正剧人物不存在这种“悲壮感”和“崇高美”,他们往往是以“坚实昂扬”精神,即对自己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充满信心和坚定不移的进取精神体现自身的“严肃性”。例如《清忠谱》中的周顺昌,面对穷凶极恶的魏忠贤及其爪牙的酷刑拷打,即使胫骨折,舌头断,丝毫不动摇他与强大的奸诈势力斗争到底的正义之心,因而屈死在狱中。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行为是悲壮的行为,“崇高之美”便从作家对这“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对悲剧人物的“人格力量”的颂扬中得到显示。正剧人物在实现自己理想和目标过程中虽然也会有困境之时,但经过主人公坚韧不拔的努力,结果总是战胜阻力,冲出困境,走向如愿的彼岸。如《单刀会》中的关羽,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一出场就坚信自己是“一人拚命,万夫难挡”的“大丈夫”,并以坚定昂扬的乐观精神独闯“千丈虎狼穴”。在这前前后后,他既不过悲,也不过喜,全然一副“大江东去浪千叠”的豪迈庄严气派,结果却实现了他“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英雄大愿。可见,悲剧和正剧虽然都是再现“严肃的世界”,但悲剧的“严肃”是厄运的严肃,正剧的“严肃”是幸运的严肃,这是悲剧人物与正剧人物的又一不同。总之,通过“和谐统一”的人物行动和“坚实昂扬”的主体精神去展现人物自身的“幸运历史”,是正剧艺术风格和鉴别标准的根本所在。
四
通过以上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正剧是一种以“矜庄严肃”为美感特征,以“美战胜丑”的自然顺变为冲突走向,以“和谐坚实”的人物行动为创作重心的戏剧样式。三者共同构成正剧的本体风格,并成为有别于其它戏剧类型的主要评判标准。对此,不妨以《牡丹亭》的艺术属性加以验证。
关于《牡丹亭》的艺术属性,有人认为是“一部离奇的喜剧”;[(14)]有人认为“全剧笼罩着一股悲剧的气氛”,[(15)]或明确指出“《牡丹亭》是悲剧”;[(16)]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悲剧和喜剧糅和在一起”的“悲喜剧”。[(17)]我赞同后一种看法。不过,由于过去对正剧的本体风格和评判标准缺乏深入研究和具体把握,故对其中的“为什么”仍未深入作解。
首先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该剧的情节结构看。《牡丹亭》全称《牡丹亭还魂记》,其意很明确,就是以记“还魂”之事为主,即以杜丽娘死后如何“为情而生”为创作重心。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明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对这段人们不知引用多少次的剧作宣言,我们应特别注意汤显祖的艺术思维。为刻画一个天下女子中少有的“情之至”者,汤显祖的创作逻辑是:先写杜丽娘“情不知所起”(情在不知不觉中自觉萌发),再写她“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控制),继而写她“生可以死”(为情而死),最后写她“死可以生”(为情而生)。《牡丹亭》的情节结构完全体现这一构想。
全剧一共55出,第20出《闹殇》之前,主要写杜丽娘“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之事,后35出主要写杜丽娘“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并终得“圆驾”之事。可见,全剧的主要情节并非写美的“毁灭”,而是写美的“新生”,即杜丽娘死后如何追求和实现她在阳间无法实现的爱情,这与“还魂记”的命名完全一致。
再从冲突设计的实际情形看,作为杜丽娘行动的对立面,无疑是随时钳制她和扼杀她青春个性的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至情”与“酷理”的矛盾是贯穿全剧始终的冲突线索。由于杜丽娘生活的环境是悲剧的环境,其行动染上哀伤色调这是必然。但是,作者在展开情节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戏剧作品那样,以矛盾双方代表人物面对面交锋较量的方式,在舞台上正面表现美与恶的冲突,而是重在写杜丽娘面对冷酷无情,令人窒息的悲剧现实,自觉萌生强烈的青春欲望,勇敢超越“酷理”的束缚,为实现爱情理想进行出生入死的抗争。总之,作者没有把“美恶相争”和“美的毁灭”作为冲突发展的起点和终点(这是悲剧的写法),只是把残酷的现实作为杜丽娘面对的一把“屠刀”,着重表现杜丽娘在现实人无法逾越的“屠刀”面前,以自觉的“求生”意识,“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然后以“精灵飞越”的自由方式,上天入地孜孜寻找梦中的情人,最后在“至情”力量的作用和感召下得以“回生”。一位西方理论家认为,“喜剧的情感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它向智慧和意志提出挑战,而且加入了机运的伟大游戏,它真正的对手就是世界。”[(18)]《牡丹亭》表现的就是这种以残酷的现实世界为对手,并向自己原有的智慧和意志提出挑战的“强烈的生命感”。挑战的结果,不是杜丽娘的彻底毁灭,相反,是“至情”战胜“酷理”——杜丽娘不仅找到梦中情人,且在父母面前,在禁欲森严的衙门里堂堂正正地与柳梦梅“圆驾”。这实在是“美战胜恶”的一场“游戏”,或者说是杜丽娘生死追求而赢得的“大幸”。学术界有人视之为“喜剧”,主要依据就在这。
不过,我们不能因该剧表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就轻易断其为“喜剧”。因为喜剧除了“美胜丑”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人物行动“不谐调”和冲突走向“突然逆变”这两条标准。从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她怀抱的一直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坚定执着的爱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爱情理想的过程中,她用不着像《西厢记》崔莺莺那样诸多作假,做出许多想爱又不敢公开爱的表现。而是以想死就死,想生就生,想爱就大胆推门进去爱的超脱行为,显示自身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的“和谐统一”。此外,从杜丽娘爱情追求的始末过程看,游园——惊梦——寻梦——写真——闹殇——魂游——幽媾——冥誓——回生……这其中没有跳跃突变的情状,尽是循序渐进,孜孜求生的执着与严肃。如果说正剧是悲剧的表达方式和喜剧的表达方式和解交融,并在矜庄严肃的氛围中表现“人生的幸运”,那么《牡丹亭》是中国戏剧史上悲喜交融得最为鲜明,悲剧性与喜剧性和解渗透得最为得当的正剧典型之一。它的成功并非限于剧中既有“为情而死”的悲哀,又有“为情而生”的喜悦,而是两者互为因果,互融互渗于人物行动、事件选择、场面设计、冲突展开的各个方面。因此,杜丽娘的“死”既不同于现实人的夭折,也不同于悲剧中的死亡,而是“死里含生,哀中见喜”——具有鲜明的喜剧色调;同样,杜丽娘的“生”也不同于现实人的生和喜剧人物的生命情感,而是“死中求生,喜从哀生”——染上鲜明的哀伤色调。对这种悲喜交融的情感结构,《牡丹亭》的第一位评点者王思任指出:“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19)]就是从不同观众的不同视角,揭示该剧情感功能的多样性和复合性。以往有人以相传中的冯小青、娄江女子俞二娘、金凤钿、女伶商小玲在《牡丹亭》的影响下为情而死作为“悲剧属性”的证据,[(20)]显然是只看到正剧“复合情感”可以因人而异的某一功能,而忽视“其款置数人”所产生的“可喜、可哀、可恨”的多种功能。从中国古代哀乐相融、正反相济的“中和”观看,悲剧论者的这一“证据”,强调的只是正剧情感系统的某一方面,而忽视正剧情感系统中对立因素相融相济所构成的整体。
总之,不管从人物行动的“和谐坚实”,冲突展开的“自然顺变”,抑或从审美感受的“矜庄严肃”去判断,《牡丹亭》完全体现中国正剧的本体风格和鉴别标准。因此,《牡丹亭》是正剧,不是喜剧,更不是悲剧。
注释:
① ② 张庚 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③ 李渔:《闲情偶寄》。
④ 孔尚任:《桃花扇》“加二十一出”老赞礼语。
⑤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5页。
⑥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6页。
⑦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0页。
⑧ 赫斯列特:《英国的喜剧作家》,见《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0页。
⑨ 转引自段宝林:《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⑩ 陆一帆:《文艺心理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11) 阎广林 赵康太 周安华:《戏剧的奥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12) 博马舍:《论严肃戏剧》,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403、405页。
(13) 秋文:《论悲剧的美学意义》,《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
(14)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1页。
(15)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16) 赵景深:《〈牡丹亭〉是悲剧》,见《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页。
(17) 叶长海:《〈牡丹亭〉的悲喜剧因素》,见《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18)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19) 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20) 赵景深:“倘若《牡丹亭》不是悲剧,怎么有这么多的妇女,如冯小青、娄江女子俞二娘、金凤钿、女伶商小玲……都在《牡丹亭》的影响下为情而死呢?”见《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