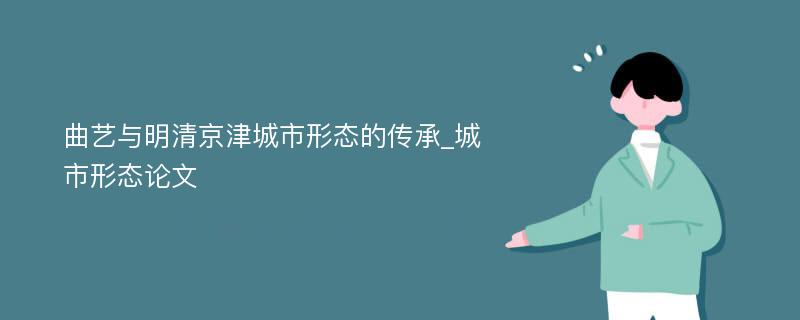
曲艺艺术与明清京、津城市形态的推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艺论文,明清论文,形态论文,艺术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8-0035-05
一、何为“以个性实现为目的”的城市
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城市发展史》中写道:“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设想一个城市,不是主要作为经营商业或设置政府机构的地方,而是作为表现和实现新的人的个性——‘一个大同世界的人’的个性——的重要机构。……现在城市必须体现的,不是一个神化了的统治者的意旨,而是它市民的个人和全体的意志,目的在于能自知自觉,自治自制,自我实现。他们活动的中心将不是工业,而是教育;每一种作用和功能将按照它促进人类发展的程度来加以评价和批准,而城市本身将为日常生活中自发的冲突、挑战和拥抱提供一个生活的舞台。”[1](P584)这是芒福德在这部近百万字巨著结尾处所勾画出的人类城市的理想形式。芒福德所期望的城市是一个以人的个性和意志自由实现为中心的城市,城市的目的在于人,而不是相反。
与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的目的在于“实现新的人的个性”构成相反命题的是“城市成为人的目的”。首先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城市成为人的目的”。芒福德指出: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中,存在着在城市语境中的被神圣化了的城市“统治者”,这种“统治者”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是原始宗教,然后是封建君主,再后是以巨大的经济利润而自我神化的资产阶级,与此相对应的城市类型是宗教城市、军事城市和政治城市以及经济城市。芒福德进一步向我们指出,使人放弃个性发展的城市之吊诡正在于:它对于人的奴役却是以表面上对于人的目的满足来实现的。芒福德说:城市是一个具有巨大吸纳力量的“容器”(urban container),“城市便是促成这种聚合过程的巨大容器,这种容器通过自身那种封闭形式将各种力量聚拢到一起,强化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1](P37)城市的“容器”性首先是来自于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因单个个体力量不足而产生求群的社会要求。人多力量大,城市容器聚拢起了单个的力量,开山填海,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可说是充分实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目的。但关键在于,当人类以群体的形式聚拢起来实现征服自然之目的的时候,却无意而又必然地呼唤出了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集体的“统治者”,因为群体性的社会要保持其稳定性必须要有一个超越众人之上的“领导者”,而群体性的社会在呼唤出这一“领导者”之后却并无力量能够约束这一“领导者”权力的膨胀——于是,最终由大众群体选出的“领导者”成为大众群体的“统治者”。随着在城市群体中产生了“统治者”,原先作为城市群体之公器的城市容器也在“统治者”的逻辑中成为以一人驭万人的“私器”。在此意义上,“城市”是一个集团实现对于另一个集团统治与剥夺的方式。芒福德总结道:“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释放与奴役,自由与强制。”[1](P570)
“城市”因为群体政治滋生的城市“统治者”而剥夺了城市个体之实现,因此,理想的城市应该是以人的个性实现为目的的城市形态。从以人的个性实现为目的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芒福德所谓的“理想城市”在具体城市形态上应体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是城市空间上的非中心性。城市空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产品,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在城市“统治者”专权的城市中,出于统治逻辑的需要,城市空间是高度中心性的;与此相反,在以城市个体为目的的理想城市中,每一个独立发展的个体在城市中都在创造着属于自身的空间。其次是城市生活世界中的狂欢时刻。在“统治者”的城市中,同样出于统治的需要,城市个体的内在世界遭到单一意识形态的驯化,而个体与个体之间又被城市统治者的铁律所限隔,因此造成了城市生活的单调乏味,而在以个体实现为目的的城市中,城市个体以极大地满足自身感官需要为指向,人与人之间因为共同的个性张扬而相互认同,颠覆权威,消解“统治者”,在城市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狂欢”时刻。再次是城市生产活动模式实现了个性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共生。在以个性实现为中心的城市中,经济活动的意义并不全在于经济生产自身,而在于一方面经济活动进入了城市个性自我构建的逻辑之中;另一方面,城市个性发展又为城市经济活动提供了真正的活力和源泉。
总之,芒福德所提出的“以个性实现为目的”的城市实际应是一个非中心、狂欢化、个性发展与经济发展良性共生的城市形态,只有在这样的城市中,个体的自我实现才是最终目的。那么,这样的城市形态如何能够实现?下面我们即以明清时期北京、天津城市形态的演变来观照此一转化演进的历程。
二、京杭大运河的冲击与明清京、津城市形态中的商业潜蕴
北京与天津,这两个北方的中心城市,在明清历史上与中国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城市一样,大体都可以划归芒福德所说的以城市“统治者”为中心的城市,在城市形态中过度发达的是政治与军事功能,城市发展的目的在于城市“统治”逻辑的实现而非城市个体自由个性的实现。
公元1153年,金主完颜亮完全仿照宋汴梁城(今河南开封)在今天北京城址的西南建造了金中都,从此之后,北京作为都城的命运便被写定。公元1272年,元代新建元大都,规划出了今天北京城的大体格局。公元1406年,朱棣在元代大都的基础上稍稍南移兴建北京城,历时14年而告成,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从江南的金陵(今南京)转移到北方,奠定了其后长久的政治格局。自元代开始,北京城凸显的是它的政治、军事功能,这从北京城历来被人们所称道的“城墙”意象以及整饬如棋盘一样的城市规划格局就看得很清楚了。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曾经在他专门研究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著作中对北京内城城墙做了令人难忘的描绘:“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2](P28)
至于天津,其军事功能的凸显与北京是一样的。早在宋、辽南北对峙时候,即以海河为界,天津正在海河沿岸建基。在金代,因为南北运河的开凿,天津一时风云际会成为九河下梢,在地理形势上成为京都门户,其军事防御位置骤然腾升。元代随着南北漕运的进一步完善,天津逐渐实现着从军事城市向经济港口城市的转变,但其军事功能仍然是最显著的。明代朱元璋定都北京之后,即在天津设三卫(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在一处而设置三卫,这在整个明代军事设置中也是少见的,更凸显了天津在中华封建帝国中的军事位置。顺治元年(1644年),清王朝在北京掌权,天津在新一代掌权者眼中不仅没有降格,反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连升两级,由“卫”升“州”,又由“州”升“府”,而这一切都是在强调天津这个城市“神京门户”的军事卫戍意义。
城市发展史表明:对于封建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构成真正冲击而实现城市个性解放的力量不可能来自于政治、军事本身,而只能是自由商贸活动。历史上的京、津两城,因为整体城市形态的政治、军事意味特别浓厚而决定了其自由贸易的契机只能是外来的冲击,而不太可能在其内部涌现。
在北京,从元代开始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为北京城的商业贸易注入了巨大活力。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记载,随着来自南方的漕船抵达北京,首先带动了积水潭附近的商业活力,形成了在北京城最富活力的商业圈。这个商业圈以积水潭北岸的斜市街市场(今北京海淀区鼓楼西大街)为中心,商业活力扩大到整个的钟鼓楼地区和东、西两城的东、西市各城门之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商圈的地理中心耸立着象征城市王权中心的钟鼓楼,而这一王权的城市象征在商业贸易的冲击下逐渐变得身份模糊,这从熊梦祥的描绘视角中可以约略窥知:“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齐政楼(鼓楼),都城之丽谯也……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明明是说钟鼓楼,但不自觉就转到了对钟鼓楼周围之商贸活力的叙述上,这说明当时商业贸易以其巨大活力逐渐剥蚀着人们心中对这个城市的王权认同。斜市街市场与西城的羊角市、东城枢密院角市,号称北京三大市,这三个大市以其巨大的商业活力冲击着元代棋盘式的城市政治格局。另外,还有齐化门外的东岳市场,也由京杭漕运所催生,香火隆盛,人烟辐辏,“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一时盛会也。”[3]
在天津,商业贸易的活力同样首先来自于运河。天津是南来漕粮转运北京的中转站,漕船到此卸载转运,加之天津处于九河下梢,南北商通往往趁着官方的漕运实现,诸种因素汇合起来,促使在天津不可撼动的城市军事功能格局中涌现巨大商机。天津的商业活力到达什么程度?元代张翥写道:“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通过清乾、嘉时代诗人崔旭的诗也可见一二:“畿南重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粮食仰关东。市声若沸虾鱼贱,人影如云巷陌通;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卫城东门外与北门外在地理位置上与运河航运相交,因此繁华异常。城内也发展起了十几处集贸市场,正如李东阳所描述的:“千家市远晨分集,两岸河平夜退潮。”可以看出,当时天津商业贸易的发达程度足以与江南号称“销金锅”的杭州比肩而毫不逊色。
自由商贸的冲击打破了城市军事、政治功能格局的限制,为城市个性的实现起到了破冰的作用,因此是“以个性实现为目的的城市”出现的第二个层次,与古典封建城市在一出现即具有的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构成了城市形态上的升华。
然而,商业活动的活力在本质上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物质层面的感性追求,在较浅的意义上体现着人性抒发,它虽然对城市个体之个性的自由实现具有破冰的意义,但本身又不是城市个性的真正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走向了真正个性实现的反面。即以历史上京、津两城而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政治、军事的城市功能逐渐为城市中崛起的商业贸易活动所剥蚀,体现出城市个体对于城市“统治者”的反抗和自我表达,但正因为商业活动所满足的是人们较浅层的感官需求,它在与城市“统治”逻辑构成张力的同时又很容易忘记自身个性发展的更高目的,而沦落为纯粹的感官享乐,甚至为新的城市“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新的城市统治方式。这就意味着,为了城市个性实现的最高目的,城市发展需要以自由商贸为基础实现更上一层的飞跃,在这一层飞跃中,艺术创造将取代自由商贸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逻辑。与自由商贸对于古典城市之政治、军事功能形态的第二层飞跃相比,这是城市发展向“以个性实现为目的”的城市形态转化演进的第三层飞跃,也是最高的升华。
三、京津曲艺的张力与明清京、津城市形态的个性转向
明清京、津城市文化中,将城市个体从第二层次的感性张扬带向第三层次个体真正解放的是京、津曲艺。京、津曲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艺术,与传统经典艺术对于自我现实使命的体认不同,它不是要以纯艺术的姿态从城市现实逻辑中拔升,当然也不是完全与城市现实沆瀣一气,而是以城市“职业”的状态存在于城市现实中,在实现其“职业”功能的同时又彰显其超越“职业”的升华意义,促生着城市从其自由商贸形态向自由个性形态转变。
一方面,京、津曲艺以“职业”的姿态隐身于城市的现实商业逻辑中。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京、津曲艺是以观众为中心的说唱艺术。曲艺包含演唱和表演的因素,但它与传统戏曲艺术不同。戏曲艺术是高台宣讲,真实的表演者隐身在表演面具之后,是所谓的“现身说法”;而曲艺是表演者以本来面目与观众相见,是所谓的“说法现身”。“说”之中强烈的个人倾向性以及“唱”与“作”中的本来面目相见,使曲艺艺术成为与观众贴得最近,同时也是观众参与性最强的艺术,这就是所谓的“以观众为中心”。
第二,京、津曲艺在城市语境中自我定位为一门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在京、津曲艺传统中,艺人们通常把曲艺看做是一门谋生的“职业”而非“艺术”。著名评书大家连阔如曾专门就天桥说书艺人上天桥“撂地”(指街头演出)发过议论:“今年夏天天桥的评书场儿要比往年多得很哪!有些说书的艺人还想不开,认为在天桥上地是寒碜,还不肯去上明地。其实,早年的评书演员都是在大街的路旁拉场子,露天讲演,在天桥上明地何足为辱?挣钱养家便算好手,何分彼此?我很希望说书的艺人迎合听主,往天桥上撂地。”[4](P271)这便是对京、津曲艺之“职业”本位的强调。曲艺的职业化造成了曲艺文本许多奇特的面貌,比如,评书中的“得胜头回”就是为了等待晚进场的观众,大量存在的“程式化”套路其实与师徒之间的方便传授有关,等等。
在表演形式上以观众为中心、自视为一门谋生的“职业”,京、津曲艺就这样藏身于城市社会诸种行业中,随着城市的商业逻辑而运行。因此,明清京、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商业贸易的活力一方面冲破了政治、军事之城市“统治”逻辑;另一方面也为曲艺这种“职业”的兴盛提供了土质丰沃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京、津曲艺又超越“职业”的限定,促进了城市的自由个性。京、津曲艺是一门“职业”,但它又与其他任何城市职业不同,通常城市职业是以满足人们的感官、物质目的来获得回报,曲艺艺术则是通过对城市个体深层精神需要的满足来获得回报,通过为城市个体的自由实现营造空间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京、津曲艺对于城市个体之个性实现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京、津曲艺与商业活动一道为城市个性的实现开辟了非中心性的城市空间格局。
明清时期,京、津两城的城市空间格局代表着中国古典城市的空间格局,是一种典型的权力集中的中心性空间格局。而空间之于城市的意义,正如西方学者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的生产》中所指出的:城市空间不仅仅是“被生产”的,本身也是“生产”性的。严整如棋盘的中心性城市空间格局是城市“统治者”对于城市个体实行监控和驯化的重要形式,城市个性的实现必须以对于此中心性城市空间格局的消解为前提。
城市中的商业活动的确极富消解古典城市中心性空间形态的潜在活力,但如果没有曲艺艺术在招致观众、增加商业活力、深化商业活动中个性自由内涵等方面予以配合的话,其对于古典城市中心性空间的消解是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的。连阔如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天津著名商业区“三不管”的衰落时说得很明白:“不料三不管儿发达得过猛了,十几年的功夫盖了多少万间房,把空场都盖没了,杂技场越弄越少。游逛的人们越来越不顺脚,亦日见稀少。有资产的人们虽然往那个地方投资,欲求获重利,却不研究此事,直到了衰落得不堪言状,亦无人整顿。”[4](P210)曲艺活动为大众所喜闻乐见,考察当时京、津两地曲艺演出的情形,在每一曲艺活动成功演出的“地点”都自发形成了一个城市“次中心”,人们围聚一起,在欣赏曲艺的同时交流感情、发表意见,于不经意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对于城市封建统治空间构成消解的城市另类空间,而这样的空间正是真正城市个体孕育形成的空间载体。
第二,京、津曲艺为城市个性的实现赋予了形式载体。
曲艺艺术进一步以其特有的艺术韵律和节奏赋予了城市个性之自由发展以表达形式。
曲艺是一种高度参与的艺术形式,在演出形式上本来面目相见、性情毕现,深深吸引着观众的参与冲动。曲艺在文本上不讲深度,内容是人们熟知的街头故事,主题是人们日常践行的大义伦常,而使这一切化腐朽为神奇产生极大吸引力的则是曲艺独特的唱腔韵律。曲艺的唱腔要求“一要清楚,二要单纯,三要质朴”,节奏简洁,周而复始,有一种神秘的原始力量,能将观众深深卷入其中。就是那些没有唱腔的曲艺,比如相声、评书、快板、莲花落等,也都有一种独特的节奏。曲艺正是凭借着这种简朴的节奏韵律,加之人人熟知的内容和极具召唤性的表演形式,使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参与曲艺的同时,也从人人隔绝的功利性世界中升华出来,参与到他人世界中去,实现人与人在城市世界中的共在,完成城市个体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在曲艺表演的催动下,城市个体突破了中心性的城市空间之限隔,共同“在场”,构成了古典城市中小型的城市狂欢。《江湖丛谈》中就多处记载了在曲艺表演现场城市民众积极参与的狂热,那真是如火如荼、如痴如醉,体现了城市个体从城市统治逻辑中解放的快乐。[4](P261)
曲艺所引发的城市个体狂欢使整个城市生活变成了一出喜剧。曲艺表演传统始终坚持让观众“笑”的表演效果,连阔如就这样总结道:“电影的片子还是笑片能引人入胜;戏台上还有丑角儿才能热闹。唱大鼓的亦有老倭瓜、架冬瓜的滑稽大板;单弦呢?亦有群信臣的滑稽单弦;说评书的能有叫座的魔力得双厚坪、品正三、刘继业、袁杰英、海文泉等,亦是以把人逗笑为拿手。”[4](P79)曲艺所引动起的观众的“笑”不仅仅是“为笑而笑”,其中还包含着从曲艺表演中所获得精神放松自由。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笑”是消解上层当权者之权威的最有力武器,在“笑”中曲艺艺术也实现了人们的相互“参与”、共同“在场”。
第三,京、津曲艺促生了城市个性发展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推动。
连阔如以天津“三不管”的衰落说明了曲艺艺术对于城市经济活动的推动作用,其实不仅是“三不管”,北京的东安市场何尝又不是?[4](P11)他将此规律推广开来说:“江湖中的艺人,无论练好了哪种艺术,都有百观不厌的长处。他们在哪里做艺,游逛的闲散人们就追到哪里游逛。不怕某处是个极冷静的地方,素日没有人到的,只要将江湖中生意人约了去,在那个冷静地方敲打锣鼓表演艺术,管保几天的工夫就能热闹起来。如若得罪了他们,或是由空块净盖房,盖来盖去将生意人挤了走啦,管保不多的日子,那个繁华热闹所在立刻就受影响,游人日稀,各种的买卖就没人照顾,日久就变成了个大大的垃圾堆。”[4](P20)
的确如此,因为在目的指向上的短视,城市经济活动无法在古典城市中获得真正发展,曲艺表演以其不可抵挡的艺术参与力量,吸引着人们以无目的的欣赏态度聚拢起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放松,满足了个体内在的深层需求——只有这样的深层满足才是真正使人不离不弃、追随始终的。曲艺吸引了忠实的观众,而这些“观众”正是城市经济活动最重要的“顾客”,这样曲艺就能化“无(目的)”为“有(目的)”,使城市个体的发展成为推动城市活动的重要力量。
在以王权、道德、宗法为城市“统治者”的古典城市形态中,曲艺艺术以城市个性自由的满足促生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许不是主流,但在当代完全以经济利润获取为“统治”逻辑的当代城市形态中,曲艺艺术的这一功能却有特别的启示意义,因为它开启了城市个性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而在当代城市现实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中心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