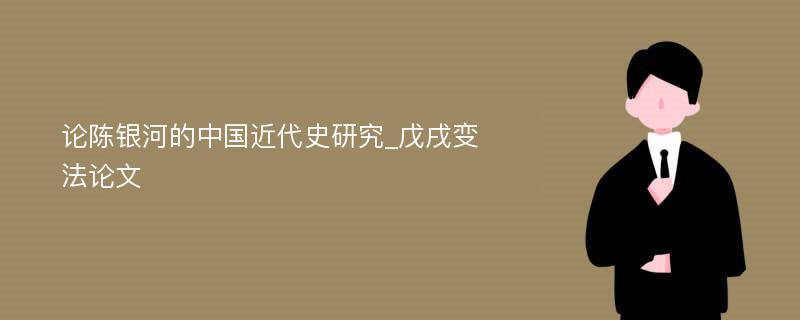
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寅恪先生虽然以研究中古史闻名于学术界,并坦承自己不敢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他对于中国近代史实际上也是有其独特见解的。(注:陈寅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其《寒柳堂记梦》中,此外,在其一些论文中也有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对此可参看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之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虽然该书在史料方面可能有某些不足,但基本看法与陈寅恪之《寒柳堂记梦》大体一致。)
一
陈寅恪对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他对慈禧太后的评价,认为晚清数十年间的多次事变与劫难,那拉氏实应承担主要责任,而关键在于其未处理好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此点之前半部容易得到认同,后半部似乎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清咸丰之季年,太平天国及其同盟军纵横于江淮区域。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文宗走避热河,实与元末庚申帝之情事相类。然以国内外错综复杂之因素,清室遂得苟延其将断之国祚者五十年。凡此五十年间政治中心,则在文宗孝钦显皇后那拉氏一人。……综观那拉氏一生之行事,约有数端:一,为把持政权,不以侄嗣穆宗,而以第承大统。后取本身之侄女强配德宗,酿成后来戊戌、庚子之事变。二,为重用出自湘军系统之淮军,以牵制湘军,遂启北洋军阀之一派,涂炭生灵者二十年。三,为违反祖制,信任阉宦,遂令晚清政治腐败更甚。四,为纵情娱乐,修筑园囿,移用海军经费,致有甲午之败。五,为分化汉人,复就汉人清、浊两派中,扬浊抑清,而以满人荣禄掌握兵权。后来摄政王载沣承其故智,变本加厉,终激起汉人排满复仇之观念。(注:石泉整理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
陈寅恪的这段论述,概括了他对清朝灭亡的基本观点,即认为清统治者对外没有处理好与列强的关系,导致列强步步进退;对内则没有处理好满汉关系、特别是上层官员中的满汉关系,导致种族之争。二者合起来看,仍然为忽视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就陈寅恪所指出的五点而言,除第四点外,都可归于种族与文化问题。本来,乾、嘉之后的汉族士大夫,已经认可了清朝这一异族(相对于汉族)统治的合法性,又在文字狱的恐怖下,转而搞纯粹的考据之学。少数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汉族文职官员,也是真心为王朝效力的。但到了光绪年间,慈禧等仍然视汉人为异己力量,不敢放心地重用,而搞什么分而治之(如对曾国番、李鸿章等),过于强调种族之分,忽略了此时满汉在文化上的认同感,反倒引起了满汉之间的冲突,无疑是自取灭亡。此外,笔者以为陈寅恪对慈禧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在一个专制政权下,个别统治者的决策会直接导致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折,强调此点并非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
第二,是其对于中日甲午之战中国何以战败原因的研究。首先,陈寅恪认为清廷统治者的腐败和昏庸愚昧是导致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这在前面所引一段话中说的很清楚,其承担主要责任者就是慈禧。(注:石泉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中指出:“三十年来,北京朝廷之最高领袖为慈禧太后,后之为人,才力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对于当时中国所处之变局,以及敌我强弱之悬殊,实无根本之如实体认,故对外于甲申中法、甲午中日皆尝一怒而言战。甲午一役,遂终于一发难收。”见该书第50页。)其次,陈寅恪以为当时清廷上层士大夫主要是清流与浊流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国家命运来搏个人之间恩怨及意气之争,这种派系之争在被利用后,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这又与文化和党派问题有关。陈寅恪指出:
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注:石泉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中指出:“三十年来,北京朝廷之最高领袖为慈禧太后,后之为人,才力足以控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对于当时中国所处之变局,以及敌我强弱之悬殊,实无根本之如实体认,故对外于甲申中法、甲午中日皆尝一怒而言战。甲午一役,遂终于一发难收。”见该书第50页。)
陈寅恪以为,对于李鸿章在甲午之战中应承担之责任,其实很简单,不在于他是战是和,而在于怎样做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当时中国军队徒有虚名,其战斗力实不堪一击,陈寅恪曾引吴渔川《庚子西狩丛谈》及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有关记载论述此事。(注:参看《寒柳堂记梦》及《寒柳堂记梦》(补)中有关部分。)然而李鸿章明知战则必败,却仅以慈禧之意为决定,又在翁常熟等逼迫下,强开战事,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所以陈氏父子才对李鸿章不满。黄秋岳对此评论说:“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注: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从陈寅恪父子的观点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地以主战或主和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大大落后西方列强的情况下,每次战争虽然正义都在中国一边,但每一次都会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求和表面上似乎是投降主义的做法而不得人心,但却可能换来中国的暂时喘息,延缓和避免民族灾难发生的进程。对国情和民情了解的人,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决不能意气用事,成为历史的罪人。在这方面,20世纪20年代列宁为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获得巩固而与德国签定的和约应该是很好的例证。
二
陈寅恪认为甲午之后,言变法维新实际上有两种观点,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派以郭嵩焘、陈宝箴为代表,二者在如何变法、变法的实际内容等方面均有分歧。倘若后者在当时能被采纳,也许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注: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对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是;“百日维新,表面如火如荼,实皆纸上文章。而当时比较开明通达、赞助新政之大臣,对于康之孔子改制学说,亦几一致不能同意。疆中之重心人物张之洞,且特著《劝学篇》,以矫维新人士过激之论,而京中则新旧僵持之局已成。维新诸健者,皆书生,更事少,愤太后之大权在握,挟制德宗,致不能有为,又惧太后一党或将先下手以不利于己,于是铤而走险,乃有联袁世凯谋发动政变,诛锄后党之举。终为袁所卖,而一败涂地。)当然,历史无法重演,如今我们更应思考的恐怕还是为什么康有为的观点被接受了,(不仅是光绪接受,慈禧在最初也并非不赞成康有为的变法)这与传统文化又有多少联系?请看陈寅恪的论述: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险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注:《寒柳堂集》,第148-149页。)
范肯堂在为陈宝箴撰写的墓志铭中,曾提及陈宝箴只喜康有为之才而不喜其学。康有为在挽陈宝箴的诗中也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之句,均可说明康与郭、陈等之观点确有分歧。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所依赖的理论依据,大致来自两个方面。在西学中主要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简单接受,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亦即进步)的而非倒退或一乱一治的循环,且全人类的发展进程和大趋势是一致的。各国历史的不同,只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最终会走到大同。这实质上已经是公羊三世进化说的来源。同时,由于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主要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遂误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解决哲学问题,这对于其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既然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则向西方学习是必然之举,晚学不如早学,学一点不如学彻底。但他们也注意到在中国不能立刻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所以还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途径。于是,通过《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撰写,康有为完成了对传统经学和道统的改造,而这种改变显然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气息。经过重新解释的孔子居然被说成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开创者,孔子遂成为康有为实行其变革的工具。这就为康有为扫清了变法的障碍,也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同情。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地学习西方,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上至皇帝,下至普通官员的支持,说明它确与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因素有关。
而郭嵩焘比起康有为来,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无疑要深刻得多,他认为:
西洋负强争胜,怀乐战之心,而用兵具有节度。其发谋常在数年数十年之前,而后乘衅以求逞犹不遽言兵也。挟其所争之势,曲折比附以为名,常使其气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挟,是以事先有预定之略,临变有必审之几。以彼之强,每一用兵,迟回审顾,久而后发。其阴谋广虑,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利导之,祸有所止,而所发明之奇巧转以为我利用厚生。……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为安,一战之胜而嘎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强方强者乎?彼固无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也!(注:转引自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比他的同时代人更能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已非昔比: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注:《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
因此,在彼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放弃闭关自守的态度,正确处理对外关系外,更应抓住时机,立即着手变革。但在变革进度方面,则应考虑到中国实际,只能渐变,不可求速成。(注:《郭嵩寿诗文集》有关论述。)为此郭嵩焘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略,即不仅要进行物质层面的变革,也要进行社会运行机制方面的改革。要大力兴办西学,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必须把了解中西方的不同国情作为救国之根本。他已意识到西方的发展得益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长期徘徊不前,统治者不了解下情,更不了解西方,这是最危险的。(注:可参阅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
与郭嵩焘相比,陈宝箴属于更务实、强调实干的一类人。作为巡抚,他有机会实践郭嵩焘屡屡提议却从未得以实行的许多变革措施,湖南在当时成为维新变法的热点地区,其兴新学、办报、开矿等措施,影响深远,尤其是出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对于陈宝箴,不仅曾国藩有很高评价,郭嵩焘亦然。他认为陈宝箴“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历之事,又见其渊然悱恻之发,求当于物而后已,其行之也,甚果以决。久之,而君所治事,群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则亦莫不顺而从之。所谓知仁勇三者,学素修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达。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作也,充乎其气而不慑也。”(注:《郭嵩焘诗文集》卷十四。)
1897年11月初,梁启超来到长沙。在梁启超赴湘之前,他与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应如何变革的讨论,可能对他们后来在时务学堂的教学指导思想以及在戊戌变法中的举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据史料记载: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同。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
当时时务学堂的授课方式,除讲学外就是令学生自学做读书札记,然后梁启超等教习为其写批语,其中颇有不少在当时被视为大逆不道之语。如提及废除跪拜之礼、开议院、改朔易服等,发聋振聩,影响广泛,再加上《湘学报》上不时刊登的言辞过激的文章,自然引起湖南保守势力的反对,其代表人物是王先谦、叶德辉等。(注:陈三立曾这样阐明其渐变主张:“窃惟国家兴度存亡之数,有其渐焉,非一朝夕之故也。有其几焉,谨而持之,审慎而操纵之,犹可转危为安,消祸萌而维国是也。”见《庸庵尚书奏议序》,《散原精舍文集》卷七。其思想除受郭嵩焘、张之洞等影响外,也受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之影响。)本来这些人与梁启超等私交甚好,梁氏初至长沙时,均与他有来往,他们也非人们所认为的是极端保守派,而是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理解的开明人士,事实上时务学堂之设立最初正是王先谦提议的。王先谦等与时务学堂师生的分歧在于他们对康有为之公羊托古改制学说不满,要对某些师生宣扬的反清、反帝制、开议院等过激主张不满,遂上书陈宝箴,斥责梁启超等多是散布谬论,误人子弟的乱臣贼子。陈宝箴据理驳斥,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从陈宝箴方面讲,他既要维护时务学堂,又并不完全赞成梁启超等人的过激之言,这也可看出他们与康梁等人的分歧。大体上陈氏父子与张之洞、郭嵩焘较为一致,主张渐进。就变革方式而言,他们反对托古改制,主张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变革。(注:《寒柳堂集》中《寒柳堂记梦》有关部分。)具体操作上,陈氏父子主张不可只将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而应劝引慈禧太后赞助改革,因大权仍在她的手中。否则帝后对立,母子冲突,矛盾激化后,大局将不可收拾。为此他们力主让张之洞进入权利中心,因慈禧太后对张一直有好感,推荐杨锐,即为此计划之先导。(注: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原载《万国公报》三五七卷,第77页。)
在此应当弄清一个问题,即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慈禧?她是否对变法一点也不赞同的顽固保守派呢?
三
中日甲午之战后,除极少数顽固守旧派外,事实上清廷朝野上下均已意识到中国的变革已刻不容缓,问题只在于如何去变,对此学术界已有共识。当时,在华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纷纷发表文章,试图影响中国的变革进程。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传教士认为,中国的变革,“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菲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即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也。”(注: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政治之本》,原载《万国公报》十三卷第24页。)坚持认为“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注:林乐知《大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记本末》,第六卷,第47页。)应当指出,这些建议自然有为他们本国利益着想的成分,却也的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于中国失败的原因,外国传教士普遍认为是“不当战而战”,欲速则不达。若因此能唤起朝野上下励精图治,从事变革,中国则大有希望,但万万不可因此而走急进之路;“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藉口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可惜,外国传教士的意见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陈宝箴父子似乎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以至数十年后,陈寅恪在谈到甲午之战时,其意见仍如当年传教士的观点,这是颇令人深思的。
其次,许多外国传教士并不以为慈禧是真正的顽固派,他们一面兴奋地表示支持,一面又不断提醒维新派不要操之过急:“特别要他的维新派朋友们记住,有必要把变法的影响施加在慈禧太后身上。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太后会像皇帝一样转变过来的。”(注:苏廉臣《李提摩太》,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平心而论,慈禧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却并非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顽固不化,只要不是推翻清朝的统治,只要不削弱她手中的权力,慈禧对于变法倒是支持的。事实上,甲午战后,慈禧也逐渐认识到了变法的重要性,对于康有为的思想她从整体上也是同意的。1895年5月,康有为的第三书送至光绪手中,光绪派人给慈禧看,慈禧“留览十日,二十六日乃发下。”(注: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22页。)可见慈禧是极为重视并表示同意才发下的,不然她完全可以留下不发。正因为此,光绪才将康之上书发至各省督抚,并据此颁发了具有变法内容的《学人才诏》等。此外慈禧对于变法的态度可从百日维新前夕看出,当时光绪面见慈禧,慈禧主动告诉光绪:“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戒第毋操之过蹙而已”。(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464、435页。)正是由于得到慈禧的支持,光绪才下决心立即实施变法。在变法期间,慈禧还向光绪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464、435页。)类似材料还有。总之,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富强且不会削弱清朝统治(也即不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利)的变革,都可以实行,但不能操之过急。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则一是因为康梁已有“围园杀禄”之谋在先,二是她对变法过程中日益激烈的方式感到不满,如光绪断然裁撤了京师一些闲散衙门,用意虽好,却使“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近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464、435页。)
事实上,对于帝、后之间的分岐以及他们对于变法的态度,即使在当时,无论是维新派还是保守派,都已有人看得很清楚。如王照评论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注: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第四册,第359页。)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同前引书,第一册,第481页。)上述二人,一为维新派,一为荣禄死党,然对慈禧的见解却惊人的相似,可见说慈禧与光绪之争主要为权利之争而非政见之争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令人遗憾的是,王照等虽曾把自己的建议告之于康有为,但康并未采纳,而是仍然“坚持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同前引书,第一册,第481页。)
今天看来,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的确想急于求成,这从他在短短百日内就发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谕旨这一点便可证明。其根源恐仍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失误有关,与光绪本人年轻气盛有关,更与康梁的实用主义倾向有关。就此而论,戊戌变法并非什么改良,而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其中甚至还有实实在在的刀光剑影:已有史料证明康梁等当时的确有“围园杀禄”的计划。他们希冀“挟天子以令诸侯”,尽快实施他们的变法纲领,其动机虽然良好却不免过于天真。且对康有为而言,也不乏借机博得盛名的个人动机,对此陈宝箴早有觉察,曾在给光绪的奏折中指出:“臣抚该员(康自为)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注:《湖南巡抚陈宝箴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31页,存北京国家档案局。)
我以为,研究戊戌变法,重点并不在于为何康有为的方式行不通,而在于为什么他的思想最后被光绪以及一些大臣接受了?因为他的托古改制其实是很幼稚的思路,陈寅恪曾讥讽为“支离怪诞,可谓‘神游太虚境’矣”(注:石泉整理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可惜,恰恰是这种思路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倾向和康有为对外来文化缺少基本理解的事实。仅仅看到中国需要变革,这只是第一步,而如何变革为重要。如果不能说康有为等人不了解国情,那么,他的急于求成只能让人理解为有迎合光绪之意愿和满足一己私利的成分,无怪乎陈氏一家对其有所不满了。
另一方面,戊戌变法之所以最后走上康梁所设计的激进道路,真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朝野上下均有大难临头之感,认为中国之亡在即,渐进之法已是远水难救近火,所以对康梁的主张,颇有无论怎样,先试试再说的想法。要么不做,要么快做,这就是当时包括光绪等人在内的思路。要么顽固排外,要么奴颜婢膝,慈禧对列强的态度也是如此。恰恰是中国方面的一次次内外政策的失误,使本来对瓜分中国不抱幻想的列强逐渐产生了中国已日趋衰亡、可以分而食之的想法。(注:英国驻华使节格纳在解任归国前对甲午战后的中国局势说过极为坦诚的意见,《翁同龢日记》对此有记载:“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乎?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若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有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吾英商贸易于中者,皆愿中国富强,无危险,故吾抒真心,说真说,不王爷肯信否?即信,所虑仍如耳边之风,一过即忘尔,此吾临别之言譬如遗折,言尽于此。”见翁日记第三十四册,第92-93页,1928年上海涵芬楼影印版。)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只有采取守势,以暂时的退让换取时间,争取变革的实施。郭嵩焘、张之洞和陈宝箴等人正是看到此点,才主张稳步缓行。事实上,即使到了庚子事变时期,西方列强限于种种原因,也并未有真正瓜分中国的计划,而是决定继续保有清朝的统治。自然,这出于它专门要更有效地控制中国的目的,但这本身已经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特殊性,对其采取强硬手段不如尊敬它和利用它,所以列强在最后也并未让光绪来取代慈禧。显而易见,在如何使中国避免出现混乱方面,它们认为慈禧比光绪更有经验。
对慈禧而言,在经历了如许事变后,她对清朝的前途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她执政的最后几年,所采取的变革措施,其大胆与彻底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例如,20世纪初清朝政府已经放宽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开始把公共事务交由公众讨论等。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人们的思想有了惊人的发展,在戊戌变法时被认为是过于激烈的康有为,此时已被认为是保守了。总之,“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注:《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5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言可能有些夸张,但在20世纪初,清朝的确表现出可能中兴的迹象,说是回光返照也好,垂死挣扎也好,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在一个日趋衰败的统治体系中进行适当的改革,即使不能促其再生,至少也可以延长它的生命。所以,今天再看陈氏三代人的思想,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远见卓识。
标签:戊戌变法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陈寅恪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历史论文; 光绪论文; 甲午年论文; 慈禧论文; 陈宝箴论文; 郭嵩焘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