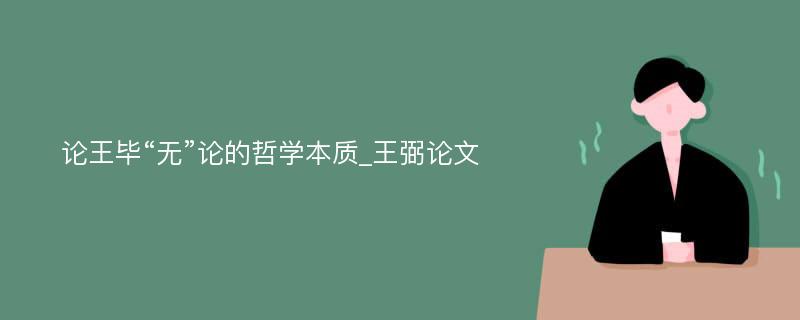
论王弼“无”本论的哲学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弼论文,实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要把握王弼“无”本论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王弼“无”本论与郭象“独化”论之间的本质联系,单靠从王弼和郭象的著作中寻章摘句地论述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这里首先必须从存在物的存在方式切入。
任何存在物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是绝对无疑的基本事实。那么,存在物为什么能存在呢?即它是通过什么方式才必然地如此这般地存在呢?值得追问。我们从这样一个逻辑追问开始:假如现在把世上一切的存在物都抽掉,只留下一个存在物,那么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物能否存在?否!因为它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它存在于哪里呢?只能存在于绝对虚无中。这样,它本身还能是有、在吗?所以,任何一个存在物要得以现实地存在的话,必然要与它之外的事物处在关联中,即一物和他物要同时并存着以构成一个相关联的、互相比较、参照的构架,即参照系构架。正是在这种参照系构架中,一物依赖于他物能存在着,并能使它自己与他物相区别而呈现出自身的特殊规定性。所以说,一物与他物各自自身处在二分并存中以构成一个参照系构架,这是存在物之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事实上,大千世界本身就是由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存在物的并存构成的,这就是个天然的参照系构架。
当一物和他物构成一个参照系构架后各自都能存在着,同时,一物和他物能够发生并必然要发生相参作用。相参的过程也就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物和他物均能并均要作用和影响对方,并同时接受对方的作用和影响,于是一物和他物在各自自身中均要打上他物的印痕和性质,就是说,此时一物和他物各自自身之中不但有原来的自身性、存在性、肯定性的规定和性质,且同时印上了非自身性、非存在性、否定性的规定和性质,即存在物自身内同时并存着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显然,存在物自身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的二分并存也构成了一个参照系构架,这可以叫做内参照系构架。相比较而言,以前那个由一物和他物各自自身处在二分并存中所构成的参照系构架可叫做外参照系构架。
很明显,外、内这两种参照系构架都是存在物的存在方式,缺一不可。这就表明,外、内这两种参照系构架之间是互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的。即:一方面,如果没有外参照系构架,一物和他物就不能二分并存着并发生相参过程。这样,一物和他物各自自身中就不会有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的二分并存,自然就没有内参照系构架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内参照系构架,当一物和他物存在着时各自自身中就仅有有、在这样一种存在性的规定性,因此,存在物自身中就没有接受他物之作用和影响的可能性,它自身就是个绝对的自己,根本不会与外物相关联,这哪里会有个外参照系构架出现呢?所以,外参照系构架和内参照系构架是相互依赖的。存在物的现实存在是同时处在外、内这两个参照系构架中的。
现在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外参照系构架是个空间构架,而内参照系构架是个时间构架。具体而言:外参照系构架是由一物和他物各自自身的二分并在所构成的,即表征的是一物和他物之二分并存着的状态。那么,一物和他物怎么才能二分并在着以构成外参照系构架呢?这必然在空间中才能实现。实际上,一物和他物之二分并存所构成的外参照系构架本身就构造出了空间。同理,内参照系构架是由存在物自身之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的二分并存所构成的,即表征的是存在物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二分并在的性质。那么,存在物如何才能把自身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同时保存下来呢?让这两种性质也像一物和他物在状态上那样同时并在下来吗?不行!因为,这样一来存在物就无法呈现出它的有、在的状态了。当存在物存在着时,与它的外在存在状态相一致,它这时只有个存在性、自身性存在着,而非自身性、非存在性只能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的一种未来发展趋势和可能性而出现,即孕育于存在性之中表征着存在性的发展趋向。所以说,存在物要把自身中的存在性和非存在性这两种性质同时保存住,它自身只能处在运动中,即处在由存在向非存在转化的过程中,而运动和过程只能在时间中呈现出来。可见,存在物自身中的自身性(存在性)和非自身性(非存在性)之二分并在所构成的内参照系构架本身就构造出了时间。因之,说存在物是在外参照系构架和内参照系构架中存在的,与说存在物是在空间构架和时间构架中存在的是等价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
既然存在物是以外参照系构架(空间构架)和内参照系构架(时间构架)为存在方式而现实地存在着,所以,人们既可能也应该从外、内两个角度上来认识和把握存在物的存在性质和本质。从外在的角度上看,存在物有着、在着,即具有有、在、存在的性质。把任何存在物都具有的这一存在性的规定性抽象出来,就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概念——“有”或“存在”,于是就有了“有”本论或存在论哲学。如果从内在的观点看,每个存在物中均有其自身性和非自身性,即存在性和非存在性或曰肯定性和否定性这样两种性质。但由于存在物的存在性(自身性、肯定性)是与其存在状态一致而不可分的,所以,真正能代表存在物的内在本质的是它的非存在性(非自身性、否定性),因为只有这个非存在性才预示着存在物的存在前景和结果,才使得存在物有了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和契机。如果把任何存在物所具有的这种非存在性的规定性加以抽象,就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另一个基本概念——“无”或“非存在”,也就有了“无”本论哲学。
可见,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有”本论和“无”本论这两种哲学理论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哲学理论体系而言,即作为本体论,“有”本论和“无”本论却有优劣之分。
就“有”本论言,这个“有”是空间构架这个外参照系构架的表征,这时的存在物的一物和他物各自处在二分并存中以构成参照,即此时的一物和他物之所以能够存在,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有、在的性质,完全是由于它之外的他物的存在,由于他物的有、在的性质。这就表明,这时一物之存在的根据或根并不在它自身中,而在它自身之外的他物身上,一物是个无根(据)的存在者。所以,“有”本体的存在并不充分,它是个无根的本体。
相比较,“无”本体的存在却是充分的。因为,“无”是时间构架这个内参照系构架的表征,这时的存在物在自身之内就有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样两种性质的二分并在以构成参照。存在物自身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是相反相成的矛盾关系,即相互包含和相互依赖着,以构成一个闭合系统。这是从静态的逻辑分析上讲的。如果从动态的存在状态上看,存在物为了把自身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相反的性质同时保存住,它自身必然要处在运动中,即处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这就构成了由自身性到非自身性再到新的自身性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闭合式圆圈运动。所以,在时间构架这个内参照系构架中,存在物的存在是有内在根据的,即是个有根(据)的存在者。可见,“无”本体是个有根的本体。
当有了“有”、“无”这两种范畴后,如何以它们为基石来构造理论体系呢?这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就“有”说,它是个抽象的理性概念,与具体的、个别的有截然二分,即“有”与有是各别的两个世界,这就决定了可以对“有”独立把握而不受有的羁绊;同时,这个“有”又是对有的抽象,可以说“有”存在于有之中,这又决定了“有”可以作为有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而来支配有。这样,从有可以析出“有”,而从“有”又可说明并支配、统治有,“有”与有在两个世界中独立运作着但又相互关联着。这,就是逻辑析理法。之所以在“有”这里能用这个方法,正是因为“有”与有这两极是二分并存的,即构成了一个外参照系的空间构架。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有”与有为什么能各自独立存在而构成两个世界(借用中国华严宗的语言说就叫“理”世界与事世界)?既然是两个世界为什么又能相关联?这里的关键环节和契机就在于有的状态和性质的同步不可分离性。前已指出,任何存在物都有有、在的性质即存在性,这个存在性只能是并必然是与存在物的存在状态相一致的,即它能外化出来而具体化。这样,当对存在物的存在性作概括、抽象以形成“有”(“存在”)概念时,就形成了“有”与有的两极二分;同时,又使得“有”与有相关联,即处在相参照中。进一步问:为什么有的存在性的性质与其状态相同步存在呢?正因为有是以空间构架这个外参照系构架为其根本存在方式的。所以,从有析出“有”和从“有”说明有均是在空间构架中进行的。“有”本论的方法论原则是逻辑分析法。
“无”怎么样呢?“无”本论也能用逻辑分析的辩名析理法吗?否!“无”表征的是存在物自身中的非自身性、非存在性、否定性的性质和规定,存在物的这一性质不同于其自身性、存在性、肯定性的性质,即它不能与存在物的存在状态同步存在,亦即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外化出来而具体化。我们也说过:存在物自身中的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两种性质是二分并存着的。但这是从逻辑上说的,是就存在物自身中理应有自身性和非自身性这样两种性质而言的。如果从存在物的实际存在状态上说,当存在物存在着时,它只能呈现出其有着、在着的存在性,即自己是自己的自身性,此时的非自身性、非存在性只是孕育在存在性、自身性之中并作为它的一种发展趋势、可能、未来前景的,如若自身性和非自身性在存在物身上同时显现出来,存在物也就不是自身了;而当存在物中的非自身性呈现于外时,即状态化了时,此时的存在物就由一物变为他物了,这时的这个非自身性也就成了自身性了。所以,存在物的非自身性永恒内在于其自身中不能状态化。这样,当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把存在物自身中的非自身性、否定性抽取、概括为“无”概念时,“无”不能像“有”那样能获得与之相截然二分开的具体的、状态存在上的无,即“无”没有抽象与具体的二分并存。至于说玻璃杯中的空虚部分,等等,那实际上只是有的不同形态(如玻璃杯的中空中装的是空气),并不是真无或不存在。因此,当有了“无”这个抽象概念后,它决不能独立化而像“有”那样存在;即使把它独立化,它也就转化为“有”而不是“无”了。这个“无”只能存在于、孕育于存在物的自身性、存在性之中作为存在物之存在状态的一种趋势、可能。故此,把握这个“无”或“无”本论决不能用辩名析理的逻辑定谓法,而只能用描述性的状摹法,就如同老子把“道”描述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窕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比喻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形容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那样。换言之,对“无”本体的把握不能用肯定法而只能用否定法,不能用语言叙说而只能用寓言、重言、巵言式的比喻,借用佛家的说法就是不能用“表诠”法而只能用“遮诠”法。可见,“无”是在时间构架这个内参照系构架中存在和运作的。“无”本论的方法论原则只能是描摹法。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王弼贵“无”论的哲学实质和意义。
王弼是在注释、发挥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时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的。他在《老子》第一章的注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他在《老子指略》一文中也开宗明义地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在王弼看来,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有是依赖于“无”而存在的,“无”是本和根,有只是现象,有恃“无”以生,“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返于无”(王弼:《老子注·第四十章》)。
王弼的确明确主张“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这一点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王弼的这个“无”究竟是什么?是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表征着存在物之非存在性、否定性的那个“无”吗?抑或是表征着存在物之存在性、肯定性的那个“有”呢?就是说,王弼的“无”究竟是真正的“无”呢还是“有”?如果是前者,即“无”是真“无”,那么这个“无”就只能体(会)而不能训(释)。怎么体?就是在有上体会“无”,即在用上体察体,因为这样的“无”本来就是体用如一的,是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为了把这样的本体之“无”告诉别人,所用的方法只能是描述和状摹,用比拟和形容,即庄子述道时所用的“寓言”、“巵言”、“重言”的方法,其目的不是定性地告诉你“无”是什么,而是启迪、引导你为自己造境,真正达到对“无”的体会、体悟。而如果是后者,即“无”是“有”,那么这个“无”就可以并必要作训(释),即作逻辑分析和定谓,亦即辩名析理,这就可以用一系列名词、概念来言说这个“无”,定性地告诉你“无”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王弼自己是如何对待他的这个“无”的呢?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有这样一段文字:“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若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看来,王弼已觉察到了真正的“无”的不可言说性,因为“说是一物即不中”。对这样的“无”只能意会、体悟,不可言传、叙说,如果王弼把自己对“无”的这一提法贯彻下去,那么,王弼对“无”必定要作状摹、描述,或用寓言,或用巵言,或用重言,或用“遮诠”,总之是采用比喻法来说“无”的,不能用语词来对“无”作分疏;这样的“无”也只能在有上显现出来,即通过有去体“无”,其结果就是人获得了人生境界或审美式体验,而不是一种策略(谋略)方法和原则。
那么,王弼是这样看待“无”的吗?他把自己关于“无”可体而不可训的认识贯彻到底了吗?在此,我们不便急于下结论,先从以下几方面作些论说。
1、概念上的辩名言理。王弼的“无”是在阐释老子的“道”时提出的。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王弼:《论语释疑》)又说:“言道以无影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王弼:《老子注·第一章》)“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王弼:《老子注·第三十二章》)他认为,老子的“道”是无形无名的,是“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的,不像具体的事物那样有形有名,有体有象,看得见,摸得着。既然这样,这个“道”就不是有而是无了。可见,王弼的“无”是对老子“道”的抽象性的一种定性称谓。在王弼这里,这个“无”和“道”并不是真正的那个“无”,而只能是“有”,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谓的“纯有”。同时,恰恰是这个没有任何内容规定的“有”(“纯有”)却可以概括、囊括一切的实在之有,“有”这个无任何内容的形式却可以套在任何内容上。正如王弼对“道”的解释:“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为音也则希声,为味也则无呈,故能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靡使不经也。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王弼:《老子指略》)从这段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王弼所说的“道”或“无”就是本体之“有”,即万有的抽象性,正因为它无形无名而高度抽象,才能适用于任何具体;可形可名的有始终受自身的形与名的限制而无法适用于别的有。可见,王弼的“无”并非真“无”而是“有”。
王弼是如何从阐释老子的“道”中把“道”定性为“无”(即“有”)的呢?显然,这只能用辩名析理的方法。王弼所主张和运用的也正是这一方法论原则。他明确指出:“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以论实也。”(王弼:《老子指略》)他认为,“辩名”与“言理”是一致的,辩证了名称也就讲出了道理。他就用这种辩名言理法对“道”、“玄”作了诠解:“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曰玄”。在王弼的《老子注》中,他用辩名言理的方法对老子的“道”、“无”、“德”、“玄”等等概念和意义作了解释和发挥,形成了他自己的“贵无”论思想。
2、体用上的本末二分。王弼把他的本体“无”和现象有的关系说成是体用关系。他认为“无”是天地万物之本,“本其所由,与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王弼:《老子注·第六章》)但是,“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必有之用极而无之功显”。(《周易·系辞上》,韩康伯注引王弼《大衍义》及其发挥)在王弼看来,“无”是体,有是用,“无之功”表现为“有之用”,把“有之用”发挥到了极致,“无之功”就能显现出来,现象世界尽管丰富多彩,都不过是以“无”为体,表现了“无”的功用。“故虽盛业大富而有万物,就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王弼:《老子注·第三十八章》)从体用关系上来说明本体“无”与现象有的关系并不错,认为本体“无”只有依靠于,即“因于”现象有才能呈现出来,本体“无”是显现在现象有中的,这也是对的。问题在于:本体“无”与现象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如一呢还是二分?如果是如一,那么“无”与有就是即“无”即有,即有即“无”,“无”中有有,有中有“无”,有“无”一源,显微无间。这样的“无”就只能在事物的“自足其性”(郭象语)中存在,即把事物的所以然之故(“无”)表现为其所当然之在(有)。这样,这个体用关系就只能用状摹和描述,而不可以明确地用体、用概念来述说了。而如果体、用二分,那么,“无”自然就是有的根,就是有的存在根据,是有的幕后支使者了。很明显,王弼所说的“无”与有之间的体用关系是二分的而不是如一的。他不但把体用概念对举来论述“无”与有的关系,而且他主张以“无”为体、为本来统摄有,这一点从他的“以无为君”(王弼:《老子注·第二十八章》)的政治哲学中可以明显看出:“从事于道者,以无为君”,“尊以自居,损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尽矣”。(王弼:《周易注·损卦》)王弼的这种政治主张与郭象所谓的“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凡得其性,用其自为者,虽复皂隶,犹不顾毁誉而自安其业”(郭象:《庄子注·齐物论》)的“自足其性”的政治策略主张明显有别。
王弼还用本末、动静、一多等关系来说明“无”体有用的体用关系。他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王弼:《老子指略》)他把老子哲学归结为“崇本息末”一句话,认为本与末对立二分,主张把本放在主导地位,要排除末(现象)对本(本体)的干扰、影响,以达到“言不远宗,事不失主”,不致迷失原则(本),脱离主宰。他还把这种本、末关系解释为母子关系:“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王弼:《老子注·第五十二章》)
王弼又认为,“无”是绝对的本体,它是不动不变的永恒存在;而现象有则是变动不居的。自然,他主张在这两者之间以不动的“无”为根本,这就叫“静为躁君”。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率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王弼:《老子注·第十六章》)又说:“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王弼:《周易注·复卦》)在此,他明显地把动(现象界)与静(本体界—“无”)二分开来并对立起来,认为静是本,是体,而动则是末,是用,主张“静为躁君”:“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止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王弼:《周易注·恒卦》)王弼既然认为“静非对动”,静、动二途,那么,“静”何以能产生和主宰“动”呢?岂不有谬!
王弼还从众与寡、多与一的关系上来论证“无”与有之间的二分关系。他指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二章》)“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王弼:《老子注·三十九章》)这个“一”就是“道”,也就是“无”,它是本体,所以它能统万有,并能派生出万有,是万有差别的出发点(“数之始”),并是万有的最后根据(“物之极”)。把这种“一”、多关系贯彻在社会政治观上,就是王弼“以寡治众”的政治策略(谋略):“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总之,王弼的“无”本论体现在体用关系上是两橛的。这就说明,王弼的“无”并不是真正的“无”,而是个真“有”。
3、认识论上的“得意忘象”。王弼的“无”本体的“有”本性实质在他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中有明显表现。王弼的认识论在其《周易略例·明象》中有集中论述: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
这里的“言”、“象”、“意”指的是《周易》的卦、爻辞,卦、爻象和一卦、一爻的含义,就哲学意义说它们分别指的是语言和概念、物象、义理。王弼在这里反复申述的无非是三点意思:其一,从功能、作用上说,言是用来表达、说明象的,象是用以表现、启示意的,所以,“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其二,从必要性上说,之所以要有言,是为了说明象的需要;之所以要立象,是为了表达意的需要。所以玩味言是把握象的途径、手段;而玩味象是把握意的途径、手段。这就叫“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其三,从最终目的来说,是为了明了、把握《易》之卦、爻象的寓意,言、象不过是用以把握意的工具和手段,这就像蹄是捕兔的器具而筌是网鱼的器具一样。这样,当然要“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了。否则,如果守住言、象不放而一味死抠,是最终无法把握住意的。
就王弼关于“言”、“象”、“意”之关系的这三个方面的意思看,他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以前我们往往说王弼的认识论是“言不尽意”的神秘主义认识论,这对王弼有失公正。这里并没有“言不尽意”的意思,相反,王弼明明说“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同时,他的认识论也丝毫不神秘,不就是通过语言、概念来理解卦象的含义并进而把握住卦象的实质意义吗?!有什么神秘的呢?!这些问题暂且不究。我要说的是这样两个意思:一、王弼认识论的路线和原则是什么?很清楚,是逻辑分析法或辩名析理法。他要析出的就是《易》之“意”,亦即一般的道或理,这大概就是他的“无”本体了。二、这个“意”是什么?是义理还是意境?如果是后者,即使采用逻辑析理法析出这个“意”,那么,真正把握这个“意”的方法决不能是析理法,即主客二分框架中的认识法,而只能是境界法,即审美式体验法,亦即庄子所主张的齐物我、齐是非的方法,也就是郭象所谓的“冥而忘迹”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言的确是无法尽意的。如果是前者,不仅可以用逻辑析理法析出这个“意”,而且可以用析理法把握这个“意”,即把“意”作为一个一般的、抽象的概念来把握。在这个意义上,言怎么能不尽意呢?!诚然,王弼说过“圣人体无”的话,但这种直觉体悟在他的“贵无”论玄学体系中并没有作为专门的方法,他所从事的主要是具体的分析法,这一点从他的《周易注》中可明显看出。所以,他所说的《易》之“意”是且只能是义理了。这就从认识论上证明,王弼的“无”实质上只是个“有”。
4、社会历史观上的“名教”出于“自然”。名教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这里的“名教”即指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自然”即指规律或“道”,亦即玄学家所追求的本体。王弼是如何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呢?
王弼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王弼:《老子注·第三十二章》)在王弼看来,包括政治教化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从“自然”(道)派生出来的,是“朴散”之后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他的“名教”出于“自然”说。他认为,统治者只要坚持自然无为的原则,“则可冕旒充目而不惧于欺,黈纩塞耳而无戚于慢”。(王弼:《老子注·第四十九章》)他甚至认为统治者在表面上要表现出某些愚,而不要明,“明,谓多见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王弼:《老子注·第六十五章》)
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不必多论证,在此值得一说的是:他把“名教”与“自然”截然二分开,并认为“自然”是“名教”的最高、最后根据。这与董仲舒所谓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如出一辙。从这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王弼的“无”实质上是个“有”,是个抽象的思想概念、范畴。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不难断定,王弼的“无”并不是表征着事物自身中的非自身性、否定性的那个真“无”,而是表征着事物之自身性、存在性、肯定性的真“有”。在他那里,这个“无”=“有”,不过他并不是在一般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个“有”的,而是在事物之所以然的规律的意义上来论述这个“有”的。但无论如何论述,他的“无”的“有”本论性质是不变的,正因为这样,从王弼的“贵无”论发展到裴頠的“崇有”论乃是自然的,裴頠只不过是在具体的有的层面上对王弼的抽象的“有”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诠解而已。真正使王弼的“贵无”论得以显露出真面目的倒是郭象的“独化”论,“独化”论与“无”本论才有着内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