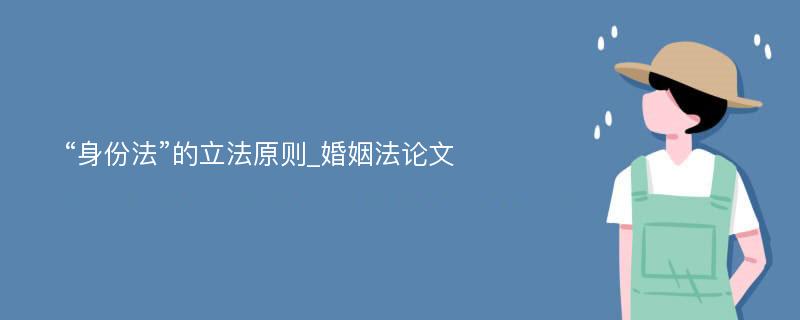
身份法之立法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1-0005-06
从广义上说,身份是指一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但身份法之身份系为亲属关系中的身份,而非一般的身份。此身份具有不可让与性。然何为身份法?学者的观点并非一致。争议的焦点在于身份法是否包括继承法。笔者认为,身份法是指规范身份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身份关系是与财产关系相对而言的,规范财产关系变动的法律为财产法,规范身份关系变动的法律则为身份法。身份关系的变动虽然也会涉及财产关系,但这仅是身份关系变动的相应或附带后果。因此,笔者认为,继承法中的继承权虽以特定身份关系为前提,但继承法毕竟不是以规范当事人间的身份关系为内容的。“现代法上之‘继承’,系属财产法之制度,而与往昔所存在之‘祭祀继承’或‘身份继承’制度为身份关系而与有财产色彩者,大有差别”。①继承法原则上应为财产法,而不属于身份法。这里所言的身份法主要是指婚姻法、收养法,或者说亲属法。关于身份法的基本原则,现行法上有明文规定。②对未来的身份法立法应采取哪些基本原则,学者的观点大同小异。如梁慧星教授主持制定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在亲属编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善良风俗、家庭生育计划;③王利明教授主持制定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在婚姻家庭编规定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原则为: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婚姻家庭制度。④笔者认为,身份法立法的原则主要应为自愿原则、平等和人格独立原则、保护弱者和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一、自由原则
身份法与财产法同为民法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身份法属于民法。民法的主要特征及规范意义在于私法自治,即个人得自主决定,自我负责地形成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⑤诚然,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言,亲属法方面的法律行为,由于对当事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而且它们通常还涉及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因此都需要具备某种形式。人身法方面的、旨在变更婚姻状况的法律行为,通常不得附有条件,而且只能由本人亲自从事,不得由代理人来执行。对于亲属法关系(婚姻、亲子关系)的内容,当事人不能自由约定和处分。除了法律规定的亲属法行为外,当事人不得从事其他亲属法方面的行为。这就是说,同物权法一样,在亲属法领域也适用“类型强制”原则。⑥这说明身份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必须看到,身份法毕竟属于私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私法自治原则也为其基本原则,类型强制原则不能否认私法自治原则,类型强制不能否认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因此,自由原则应为身份法的立法原则。身份法上的自由原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选择共同生活方式或者家庭模式的自由
自确立私有制以来,以婚姻这种身份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职能,传宗接代、维持血缘关系的纯净是婚姻的基本任务,因此,婚姻以生育为目的,婚姻只能是男女两性的自然结合,且婚姻成为家庭这一社会生活细胞的基础。而为保障实现生育目的,各国法上无不对婚姻规定了相应的条件。然而,在现代社会,尽管家庭仍然承担着人类再生产的职能,但是,一方面现代生育技术使生育可以与两性的自然性行为相分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家庭职能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生育或者说传宗接代已经不再成为许多人组成家庭的目的。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作为自然人社会共同生活的组织形式,是自然人追求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及于此基础上的共同的物质生活的结果。事实上,现实中除了传统的基于异性婚结成的一夫一妻为中心的家庭,还存在大量的单亲家庭以及非传统婚姻的同居关系。而选择何种形式的共同生活,应是人的自由。人们可以基于两性且以生育为目的结成婚姻,以求共同生活;也可以单身抚育子女,以过一种单亲的家庭生活;还可以基于两性结合但不求生育或者采取不生育的措施,只求共同生活在一起。另外,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有的人还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性趋向,即同性恋而非异性恋。有同性性趋向者追求的不是异性婚姻而是同性婚。如果立法上仅从生育的目的、异性结合上规定婚姻的条件,就会使这些人失去以婚姻形式结成共同生活体的权利。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现在有的国家已经承认同性婚家庭。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规定:“婚姻是男女两性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按法定程序以人身和财产事项为内容达成的合伙。两性人彼此之间或与全男人或全女人缔结的婚姻,允许之。同性人之间缔结的民事结合,在性质相宜的范围内,适用本编的一切规定。”⑦不可否认,在各种类型的共同生活体中,当事人之间都有一种与其人身不可分离的身份权益,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的稳定,这些身份关系都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未来的身份立法应当应对这种社会现实需求,承认传统婚姻关系外的同居关系,承认各种不同的家庭模式。
(二)身份行为的自由
身份行为是指以发生身份关系的得丧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有学者谓:所谓身份,是个人在亲属的身份共同生活关系秩序时,与之不可分离之属性又是其资格。故以此种身份之得丧为目的之行为,自为个人将要进入或脱离该身份共同生活关系秩序时之事实上行为。⑧但笔者认为,身份行为仍属法律行为,须以发生身份关系的得丧为目的,若无此目的,不能构成身份行为。身份关系的得丧,表现为建立还是脱离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秩序。因此,身份行为也是以当事人的意志自由为其基本生效要件的。无论是建立共同生活秩序(如结婚或同居⑨)还是脱离共同生活秩序(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都须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非基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志或者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不自由,当事人有权撤销该身份行为,而不使其发生建立或脱离共同生活关系秩序的法律效果。
身份关系也可基于单方行为与自然事实而发生。如继父或继母抚养未成年继子女即属因单方行为发生父母子女间的身份关系。(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也应属单方行为,但需经一定程序才可发生养父母子女关系。依现行规定,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应在社会福利机构抚养。收养这些儿童的,社会福利机构为送养人,这时收养身份关系仍是基于收养人与送养人间的双方行为发生。但笔者主张未来立法应承认对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的收养。)亲子关系是基于子女的出生而当然发生的,有身份关系的双方因一方的死亡而使该身份关系消灭,这都是基于自然事实发生的身份关系变动。单方行为须有行为人以发生身份关系为目的的自由意思,为其当然。即使在因出生这种自然事实发生身份关系中,父母一方发生父母子女关系的自由的意思表示也是起着关键性作用的。在传统的亲子关系中,血缘关系是认定亲子关系的唯一依据,因此,发生是否为亲子关系的争议时,DNA鉴定成为必要的技术手段。但是,在现代生育技术的情形下,通过人工生育技术生育的子女却不能以血缘关系为认定亲子关系的根据,而应以生育子女的当事人的意志为决定亲子关系的依据。于此情形下,DNA鉴定失去了在认定亲子关系中的作用。因为,DNA鉴定为有血缘关系的,并非有亲子关系;DNA鉴定没有血缘关系的,并非没有亲子关系。
身份之种类及内容等,皆不能依当事人之效果意思加以决定。⑩这是由亲属关系法定化决定的,但我们不能以此得出身份关系与当事人的意思无关的结论,更不能认为当事人在身份行为中的意志没有意义。诚然,对于法律没有承认的身份关系,当事人决定发生此种关系的意志不具有法律意义,不会导致该身份关系的成立。例如,在法律未承认同居关系的情形下,当事人双方即使有同居生活的合意和事实,也不能发生法律认可和保护的身份关系。但是,对于法律认可的身份法上的身份行为,当事人的意志对于身份关系的成立确有决定性意义。依《婚姻法》第8条规定,结婚登记是夫妻关系成立的法定要件,但笔者认为,婚姻关系的成立不是基于登记,而是基于当事人结婚的合意。结婚登记仅是对于男女双方婚姻行为的一种确认,而不能代替当事人自愿结婚的意思表示。法律之所以对于婚姻关系即夫妻关系的成立规定一定的形式要件,其目的在于以特定的形式公示婚姻关系。因此,即使取得结婚证,若并无当事人结婚的意思或合意,也不能认定当事人间确立夫妻关系。例如,甲以乙的名义与丙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领取了双方为乙与丙的结婚证,不能据此就认定乙丙间成立夫妻关系。因乙丙间并无结婚的意思,乙丙间的婚姻并不能成立,该婚姻关系只能在甲丙间成立。乙知情后当然有权请求登记机关注销该结婚登记(而不是撤销婚姻关系),登记机关应当注销该登记,而根据甲丙间的条件决定是否对甲丙间婚姻予以登记。也正因为结婚必须是双方完全自由的合意,因此,婚姻关系的成立须有当事人双方结成夫妻关系的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如果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当事人间的结婚这一身份行为应属于可撤销的行为。《婚姻法》第9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受胁迫的一方之所以得撤销婚姻,正是因为其并没有与对方结成婚姻关系的真实意思,该婚姻违反其自由意志。由于婚姻法仅规定胁迫的婚姻可以撤销,学者中对于受欺诈的婚姻可否撤销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说,不仅受胁迫的婚姻可以撤销,受欺诈的婚姻也可以撤销。也就是说,因受欺诈结婚的当事人也应有权请求撤销违反其自由意志的婚姻,因为该婚姻关系的成立并不是当事人自由的真实意思。
二、平等和人格独立原则
平等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不仅仅贯穿于财产法,当然也贯穿于身份法,因此,平等也应成为身份法的立法原则。
在古代社会,身份关系是一种服从关系,当事人各方并没有平等地位。罗马法中人格的产生或确认完全基于人的地位和身份。(11)在家庭中,无论是妻还是子女,并无独立人格。近代社会的私法以“人生而平等”为基本理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但在近代身份法上仍遗留着罗马法中家父权的痕迹。无论是在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中还是在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中,在身份法领域,当事人并无平等地位。我国古代身份法的身份关系也是以不平等和妻及子女的不独立人格为特征的。“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观念深植于身份关系中。如陈棋炎先生所言:吾国自古以来就有三从四德为妇女美德,且以夫妻一体、夫唱妇随为夫妻共同生活关系上之理想。故无论在哪一方面,妻应听从夫之指使,不敢有所违,换言之,妻之人格,于婚姻关系成立以后,为夫之人格所吸收,故妻在法律上并无人格可言,也就无从成为法律行为主体。此种夫妻同体主义,在近代法上渐由夫妻别体主义所取代,即夫妻在法律上各应有独立人格,又各应有法律行为能力。惟纵在近代法,亦不以人格独立为夫妻对抗之前提。(12)而现代社会,尤其是随着女权和人权运动的深入,各国普遍修改法律,赋予身份关系中男女以平等地位,使身份关系真正建立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没有人格上的独立也就谈不上平等;没有平等也就不会有人格独立。现代身份法不仅应以平等和人格独立为基础,而且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平等地位和人格独立为目标。
身份关系的确立,不仅发生当事人间的人身关系,也发生财产关系。但无论是在人身关系方面,还是在财产关系方面,当事人都不会也不能因身份关系的确立而失去其独立性与自主性。例如,就财产关系而言,婚前的个人财产不会仅因结婚而改变其个人所有的性质,只有结婚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才可成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然而,无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均可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而当事人得以自主约定的基础就在于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和独立的人格。因此,这一确定财产关系的规则在未来的身份立法中仍应坚持。
既然身份关系的当事人具有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每个人就都有行为自由,每个人都应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自由。在家庭成员间不尊重或侵害他人人格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家庭暴力。对何为家庭暴力,学者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以暴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体上、精神上或性方面的权利,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即是夫妻暴力,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暴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夫妻他方的人身权利包括身份上、精神上和性方面的权利,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行为。(13)笔者赞同将家庭暴力作广义与狭义上的区分。从字面意义上说,暴力行为是指一种作为。但笔者认为,对于家庭暴力的解释应不局限于字面意义。家庭暴力为家庭成员间一方侵害他方人身权利的不法行为,主要表现为作为,但也应当包括不作为。特别是在夫妻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冷落、轻视以至羞辱等情感上的虐待,以致对方身心受到伤害的现象更为常见。例如,夫妻一方实行网络恋,热衷于网络婚、过网络家庭生活,而对另一方予以冷落,严重损害他方的夫妻感情。这种冷暴力有时对他方伤害更严重。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国际社会和各国的立法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我国《婚姻法》第3条也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并于第43条规定了对发生家庭暴力时的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但笔者认为,现行身份立法禁止家庭暴力主要是从维护婚姻和家庭关系上考虑,而在保障人权、维护和保护身份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上考虑不足。因此,未来的身份立法应当从当事人地位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原则上设计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制度,应当将家庭暴力行为作为一种侵害人身权权益的侵权行为,实施家庭暴力者首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三、保护弱者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现代法上身份关系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由于天然条件的限制,有的人实际上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实现平等原则,使身份关系的当事人真正具有平等地位,法律必须对弱势的一方给予特别的保护。就整体而言,妇女、儿童、老人在人身关系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4条特别强调“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国家还专门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这种对老年人、妇女、儿童权益的特别保护在身份立法上应得到充分的体现。
老年人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老年人的赡养和扶养上。现行《婚姻法》对此有明确规定,第30条还特别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在我国养老模式中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基本养老模式。因此,尽力使老年人能有子女赡养,应是法律制度设计要考虑的。但是,现行收养法规定,被收养人只能是未成年人,而不许可收养成年人。(14)而现实中,有的老年人出于养老的需求,更希望收养成年人为其子女。老年人收养成年人为其子女并无害于社会。所以,从保护老年人权益上说,未来的身份法应当许可老年人收养成年人,以使双方形成父母子女关系,从而保障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妇女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夫妻关系上对女方的照顾。应当承认,现行法在夫妻关系的规定上体现了妇女权益保护原则。例如,《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第40条规定了离婚时一方的补偿义务,第42条规定了适当帮助。无论是补偿还是帮助,尽管也包括女方对男方的补偿和帮助,但主要是男方对女方的补偿与帮助。但婚姻法的上述规定太抽象,应当予以具体化,才能更好地保护妇女的权益。例如,就补偿而言,第40条规定:“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何为付出较多义务?实务中是难以量化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承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在家务劳动中的价值,与另一方从其他方面得到的财产价值等同。就适当帮助而言,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何为生活困难?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这一标准显然太低。笔者认为,离婚时的生活困难应当是与离婚前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而不应与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相比较。也就是说,如一方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的生活水平与离婚前的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尽管可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也应属于“生活困难”。
儿童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为在父母与未成年子女间关系上优先保护儿童利益。古代社会,在亲子关系上,子女是父之财产,并无独立人格可言。近代社会,虽承认子女具有独立的人格,但在亲子关系上,实行“父母本位”主义,优先考虑的是父母利益而非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现代法在亲子关系上则实行“子女本位”主义,优先考虑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作为亲子法的立法原则已是现代法的趋势,我国应当将其确立为身份法的立法原则。
身份法上贯彻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应当体现在涉及儿童利益的事项上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例如,在收养关系的成立和解除上,现行《收养法》第11条规定,“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第26条规定,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收养人与送养人双方可以协议解除关系,“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这两条规定将收养未成年人和解除未成年人的收养关系,仅限于被收养人为10周岁以上才应征得本人的同意,这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只要被收养人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就应当征得本人的同意。再如,在父母离婚时决定子女抚养上,现行《婚姻法》第36条规定:“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因双方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这一规定尽管规定了法院作出判决时应考虑子女的权益,但并未规定应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和优先考虑子女的利益。与此相关的,在父母离婚后对子女的探望事项决定上,也应尊重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这里的当事人显然仅指离婚的双方,而未包括未成年人子女。这种仅由离婚的父母协议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而未规定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的形式,不足以维护儿童最大利益。再如,在监护的设立上,也应征得未成年人的同意。
再次,在需要保护的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例如,收养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须双方自愿,且应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但如被收养人属于无相应认识能力的,收养就须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收养人与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收养的,即使因被收养人尚不具有相应的意思能力而不必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也须符合被收养人的最大利益。再如,夫妻双方有离婚的自由。依现行《婚姻法》第31条的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但夫妻的离婚自由不能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夫妻协议离婚的,只有对子女的安排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才可有效,而不能只是如同财产问题一样对子女问题已有适当处理即可。《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但在离婚时子女利益与女方利益并非是一致的,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并不能解决女方利益与儿童利益的冲突。法律应当规定于子女利益与女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须优先照顾未成年子女利益。
亲子关系因子女的出生而发生。父母有生育和不生育子女的自由,但生育子女的自由不能损害儿童最大利益。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制度主要是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在这一制度中也会发生不同利益间的冲突,因此,在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监护人的更换、撤销等制度的设计上也要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为原则。例如,针对现实中存在的对未成年子女实行魔鬼式训练、放任儿童失学等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现象,立法上应当规定监护的监管制度,以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3条仍沿袭《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依此规定,若造成他人损害的未成年人有财产即使其没有认识能力也须以自己的财产向受害人赔偿,而监护人却没有赔偿责任,这是不利于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可以说,这一规定与在监护人、未成年人、第三人利益上没有将儿童最大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不无关系。因此,对于在不同的利益冲突时如何优先保障儿童最大利益,是身份立法必须予以特别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继承法新论》,三民书局印行2001年版,第1页。
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第2条规定:“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③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332页。
④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⑤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⑥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⑦徐国栋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⑧参见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瑞明印刷厂印刷1980年版,第12—13页。
⑨当然,由于现行法上还未承认同居这种共同生活的结合关系,同居仅作为事实行为而不作为法律行为看待,法院也不受理解除同居关系的纠纷。但笔者主张未来立法上应承认同居关系。
⑩前引⑧,第125页。
(11)参见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12)前引⑧,第90—91页。
(13)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2010年版,第586页。
(14)这里涉及对《收养法》第7条规定的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可以不受“被收养人不满14周岁的限制”的理解。对此学者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理解为可收养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即成年人不能成为被收养人;另一种观点认为应理解为可以收养超过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可以收养成年人。有学者指出,在确有需要成立收养关系且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似不应以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为限。
标签:婚姻法论文; 法律论文; 亲子关系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婚姻与家庭论文; 婚姻论文; 父母关系论文; 民法论文; 家庭论文; 家庭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