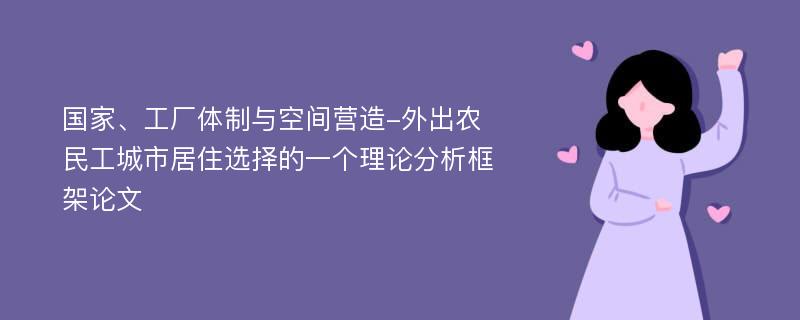
□ 社会学研究
国家、工厂体制与空间营造
——外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王 星
[摘 要] 作为流动人口,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涉及到三个层面,即居住区位选择、居住方式选择以及居住质量选择。在农民工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国家力量、工厂体制以及主体性因素相互作用。在居住区位上,地方政府空间营造能力越强,那么农民工的居住区位郊区化趋势越明显;农民工居住方式的选择与产业类型密切相关,低技能依赖型加工制造产业的农民工多选择集中居住,而服务业则倾向于分散居住;在居住质量上,存在着典型的“重生产、轻生活”的状况。在居住区位、居住方式以及居住质量三者中,居住质量是农民工唯一能够自主选择的,但却是他们选择过程中较少在乎的因素。在制定农民工住房政策时,关注其主体性、提升其可行能力远比简单改善其居住质量更为重要。
[关键词] 居住选择;居住区位;居住方式;居住质量;可行能力
一、问题的引出
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几乎都会面临贫困流动人口的住房短缺问题。在中国,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庞大,以及土地财政、制度隔离等结构因素,使其城市居住问题更加复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 894万人,其中需要在城市选择居住地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 610万人,约占总数的62%。这批外出农民工是城市新贫困群体的最大构成主体,在城市里处于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境地。[1]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出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问题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逐渐形成两种具体研究取向:要么关注居住生态,指出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住房体系之外并非只是因为经济贫困,而在于制度上的隔离与公民权的二元化;[2-4]要么从应用角度,关注其居住不平等现象,并借鉴西方“贫民窟”治理经验尝试进行本土化政策创设。[5-6]
这两个方向的研究涌现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不过在笔者看来,他们依然存在着缺憾:一是现有研究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城市人口与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隔离的现象,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因土地制度差异在中国城市中一般不会形成与南美洲和印度城市“贫民窟(slum)”(1) 无论是南美洲国家(如巴西),还是印度,城市化也导致大量贫困农民流入城市之中。由于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贫困农民多是出卖土地后举家搬到城市之中的。在城市住房短缺的背景下,这些贫困流动人口只能住在便宜简陋的房屋中,如此聚集就形成了“贫民窟(slum)”。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工实际上在农村老家一般都有宅基地,这些土地无法出售,因而流动农民工一般不会长期定居于城市,而多是以候鸟形式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同时也使城市中没有形成巴西和印度那样的贫民窟。不过,中国城市中存在着由于城市空间扩张而形成的“城中村”,在城中村的形成机制、内部结构以及空间安排上均与“贫民窟(slum)”有着本质差异。 类似的隔离居住格局;[7]二是多渗透着一种城市精英主义式情怀,将农民工视为一个整体并对其居住选择进行价值判断,忽略了这部分群体的主体性。其实,在居住偏好选择上,不但农民工群体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即便是外来流动人口集聚的“新移民社区”(2) 这种均质性更多地体现在地缘上,而在职业结构、居住偏好、居住结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互动关系上,不同新移民社区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内部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异质性。[8]219所以,有学者倡导应该回到行动者主体性中,关注行动者的自我选择机制[9]或农民工群体城市定居的意愿。[10]本文正是一种找回农民工主体性的尝试,具体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分析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上的行动特征;二是尝试从行为与结构互动的视角建构新理论框架,以解释形塑农民工居住选择行为的成因。
二、居住选择行动背后:经济成本抑或社会资本?
城市住房问题是农民工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现实阻碍之一,在住房资源获取上,候鸟式的农民工流动人口面临着“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的困境。[11]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逐渐将视野聚焦于城市农民工如何在城市里“落脚”之上,基本上形成了如下两个解释路径。
(一)经济成本驱动论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生态理论较为系统地讨论了经济成本对城市移民居住选择的影响,认为“房租梯度”导致了居住生态区位差异,不同位置会被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据,对于城市新移民来说,一般都会寻找最便宜的房子。[12]延续此解释逻辑,经济成本驱动论认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受制于“成本—收益”曲线,便宜性和便利性是其选择行为的原则。换言之,通勤成本与房租成本是影响农民工群体选择居住地的首要因素。[13]该理论认为,农民工居住是“权衡房价和职业需要”后的理性选择结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有研究发现,相较于低廉房租来说,薄弱管控才是流动人口选择居住地更多考虑的因素。[8]210还有学者指出,农民工居住选择与经济收入因素相关性不大,而是与其流动频率显著相关。[14]而且如果是单纯经济理性作用的话,那么为何在城市中会出现职业类型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等级差异较大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呢?如“浙江村”就是典型例证。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基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乡土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才是影响流动人口城市居住选择的关键变量。[15][16]22
(二)社会资本作用论
该理论认为,在农民工群体居住选择的过程中,基于乡土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比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首先在信息获取上,就业信息、房源信息乃至生产信息的共享需求推动了农民工群体选择老乡聚居。项飚在研究“浙江村”的过程中发现,浙江人是通过“链式流动”来到北京的;[16]51其次有助于建立社会信用,压缩居住选择中的交易成本,老房客能够成为后来求租老乡的信用“预审员”;[8]220最后更重要的是,同乡聚居能够增强农民工居住空间内部的身份认同和凝聚力,由此产生的“邻里效应”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社区的互助福利。在社会资本作用论看来,农民工流动到城市,“社会场所改变了,但并没有根本上改变乡土社会网络的边界”,[17]他们选择同乡聚居不但有利于减少其“搜寻”成本,而且能够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18]增加其福利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所谓居住区位,是一个带有空间社会学色彩的概念,指居住选择在空间上呈现出来的状态或特征,它虽然指涉地理空间上的分割,主要是根据功能所划分的物质空间,比如开发区、制造业区等;但更主要的是指社会空间上的区位分布,即指城市空间里“具有相同或相似社会经济属性、宗族种族乃至行为心理的社会群体所占有的空间”。[8]1空间社会学认为,农民工群体城市居住区位属于与主流社会空间分异的边缘空间,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居住空间带,以工业密集的近郊和外郊为主,比如上海外来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倒U字形,集中在近郊区以环状形态分布,北京的外来人口则主要分布在外郊工业密集区。[8]102
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其城市居住选择行为在结构上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即居住区位的选择,居住方式的选择,以及居住质量的选择。
三、农民工居住选择行动中的主体、工厂与国家
2.5 对农药残留问题的认识 农药的不科学使用容易造成农药残留量超限,危害人类健康。在此次调查研究中,83.4%的烟农认为烟草存在农药残留问题,对人体有危害,26.6%的烟农认为烟草经过了烘烤过程,后期还要经过燃烧,不存在农药残留。95.8%的烟农认为农药残留量逐年降低,也有4.2%的人认为时好时坏,主要根据当年病虫害发生情况而存在差异。
笔者以为,社会资本作用论是对经济成本论结构主义解释倾向的修正,如林南所言,社会资本是“行动者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的一种行动。[19]24这种带入群体主体性的解释路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对于乡土情结更为浓厚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更为适用。(3)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很多城市涌现的流动人口聚居的新移民社区——“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就是例证,社会资本的作用逻辑在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城市空间治理从最初的“清理隔离”逐渐向“同化疏导”转变,这种基于乡土关系形成的移民社区边界也逐渐模糊。(4) 如曾经是浙江人聚落的“浙江村”,现在已经成为北京的商圈——大红门,原初的居住隔离现象基本消解了。 而且,即便是在农民工群体聚居的移民社区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力也不尽相同。李志刚等人的研究指出,与“浙江村”不同,在“安徽村”内,“流动人口之间来源混杂,各操己业,来往很少,即便是来自同一乡村也不愿走得太近”,[8]219彼此间社会关系松散,多选择“散点状”独立居住。而且,现今大城市里的所谓新移民社区无论是在流动人口密度,还是在本地居民置换程度上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小聚居、大混居”的居住格局成为主要的居住形态。笔者看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生态的这些新变化实质上对过去的理论解释提出了挑战,无论是经济成本论,还是社会资本作用论在现今都面临着诸多的盲点,理论框架创新显得尤为必要了。
在空间社会学理论看来,居住区位不是行动者能够主观随意决定,而是受制于经济社会结构的。恰如Wilson所指出的,以“去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产业重构及产业转移导致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分化,带来了美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中产阶级居住“郊区化”,而边缘群体则受困于内城贫困区。经典的城市空间结构解析模型AMM(Alonso-Mills-Muth)模型[24-26]在分析消费者选择居住区位时指出,由于空间不匹配现象存在,那么地租区位差异导致的居住成本与通勤成本是影响消费者居住决策的关键因素。但是AMM模型中竞租曲线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化和竞争性住房市场前提之下的,而且该模型比较适用于消费者在“租房与买房”间进行选择均衡的情况,既没有考虑到居住区位选择背后的社会成本,也没有将国家干预因素纳入其中进行考量。
(1)动态定价,区分淡旺季。采用柔性定价,通过多元化的定价方式支持庐山民宿的价格弹性,淡旺季根据游客需求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有吸引力的价格。旺季游客数量巨大,多数游客的价格敏感度会降低,此时经营者可将民宿价格在消费者可接受的范围内调高,形成创收;庐山旅游淡季时,游客数量会大幅减少,此时山上民宿空房量大,供大于求,经营者应该相应的降低价格,通过保守的定价,以低价来刺激消费者对于民宿的需求。
所谓居住方式,是指外出农民工在城市中选择居住地的类型,与居住区位强调宏大空间规划不同,居住方式更强调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区空间。一般而言,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居住方式类型也就不同。国家统计局以住所类型对农民工居住方式进行了分类,分为“单位宿舍、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务工地自购房、租住房(与他人合租和独立租住)”等。[20]有学者从社区类型差异角度,分为居委会社区居住和村委会社区居住。也有根据群体规模分类的,如区分为群体性居住与独立或家庭式居住模式等。[21]上述居住方式多是基于收集数据便利角度进行归类的,缺乏属性上必要的理论抽象。本文将农民工群体居住方式分为集中居住和分散混合居住两种类型。集中居住主要是指大批外出农民工聚居在一起,“宿舍体制”是典型表现;而分散混合居住则是指与城市居民共同居住在一个社区空间中,可以是购买商品房居住,也可以是租住。
1.1 材料与仪器 克氏原螯虾,大连长兴水产市场;壳寡糖,大连中科格莱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隧道灌注式小龙虾冷冻机,江苏诺克诺菲智能机械有限公司;TMS-PRO质构仪,美国FTC(Food Technology Corporation);GC(7890B),美国安捷伦;GC/Q-TOF(/7200),美国安捷伦。
在农民工群体选择居住地而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居住区位、居住方式以及居住质量的选择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选择行为结构谱系。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居住区位、方式及质量三个层面的选择考量会有一个先后次序:区位选择是第一阶段,然后是方式与质量的选择。
所谓居住质量,是指居住地的住所条件以及与居住生活相关的配套环境状况。在城市,无论是保障性住房,还是商品住房,政府住建部门对其均有强制性质量标准,涉及到施工质量、用料质量、规划设计质量、环境质量等方面内容。一些空间社会学者采用社区分析和因子生态学分析方法,根据人口密度和分层、居住状况等指标计算出社会空间结构模式,[22]从而对社区的居住质量进行定量测算。还有些社会学者根据环境质量、医疗设施、物业服务等公共设施的可达性来衡量社区居住的质量。[23]一般而言,对于居住质量的测量大都采用多指标综合评分法,根据居住面积、住所适宜度、自然环境、配套设施、公共服务、邻里关系等,通过计算可以得出每个居住社区的质量等级。在本文中,笔者将农民工群体居住质量归类为硬件质量和软件质量两个部分,硬件主要是指居住配套设施、住房工程、规划设计、居住密度状况、社区环保等内容;软件质量主要是指物业服务状况、政府文化体育、卫生、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配套状况,以及邻里社会关系、社区治安状况等内容。当然,居住质量除了上述客观表征外,居住者的主观体验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比如居住满意度也是居住质量的体现。
(3)在“凵”型钢“一”型侧钻孔,孔距及孔大小与螺栓尺寸及间距相符;圆弧位置应将短边翼缘侧切开后将角钢按建筑物表面弧度预弯,在U型止水带上表面涂刷环氧结构胶黏结材料,其在未凝固状态将不锈钢压板黏接在止水带上,使橡胶止水带与不锈钢压板表面无缝对接,有效避免了止水带与不锈钢压板表面的渗漏通道。
(一)居住区位选择中的国家
在开始实际的Milk-run设计之前,必须对实施Milk-run的条件进行调整,以确定是否满足了允许在工厂内使用Milk-run生产系统的3个要求:布局、安全和物料。
所以,虽然居住区位的“空间分割”实质是源自于“社会分割”,[27]在中国城市空间分化过程中,这种机理同样适用——居住分层乃是社会结构分层的象征符号,[28-31]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与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不同,西方消费者居住区位空间分化更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是建立在“空间私有化”基础上的;而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其居住区位选择是在国家行政主导型城市化背景下进行的,地方政府通过“空间营造”方式规划了各类生产园区,从而在空间上也将农民工群体的居住区位划定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实质上是国家“再分配”力量决定了城市居住格局,是单位“体制分割”效应的延续。[32]当然,这种“体制分割”目前主要指涉的是单位属性间差异,但同样会投射到农民工居住区位的分布上,地方政府主导的保障房、公租房等项目排斥流动人口就是典型例证。所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营造历程不同,中国的郊区化主体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以边缘群体为主。在中国城市化空间营造过程中,地方政府能力越强,农民工的居住区位郊区化趋势越明显。
很多经验研究已经证明,农民工群体城市居住选择过程中,经济理性原则贯穿始终。但是经济理性的社会嵌入性同样也是不容否认的社会事实,农民工群体居住空间分布上的同乡化与同质化趋势正体现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力。面对这样的解释困境,笔者以为只有回到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细分居住选择行为的结构,方能调和经济成本论与社会资本论之间的矛盾,以更清楚地透析农民工群体落脚城市的过程。
(二)居住方式选择中的工厂体制
对于农民工而言,居住方式的选择是其落脚城市社会的重要步骤。在社会资本论者看来,虽然农民工群体选择集中居住乃是乡土社会“三缘关系”的城市延伸,但却易导致空间封闭,故社区混合居住有助于其“弱关系”式社会资本的培育,从而促进社会融入。不过,如上文所言,有研究已经证明,即便是在同乡农民工聚居的移民社区中,异质性也非常明显,同乡交往呈现出减少趋势,其居住方式选择上呈现出一种“散点状”分布。[8]219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我们大样本调查的证实,2013年8月份我们对全国8个城市2 000多位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发现,“邻近老乡亲友”基本上不是其选择居住方式所考虑的因素,考虑此因素的调查对象只占6.4%。(5) 数据来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调查于2013年8月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等城市同时展开,调查对象为“年龄16周岁以上,户口不在所调查城市,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且在本地居住或企业工作一个月以上的城市流动人口”。通过配额抽样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城市完成500个样本,其中80%为农民工。在经过奇异值剔除和缺失值处理后,获取有效数据样本3 801份,其中农民工样本为2 612份。 在农民工选择居住方式的过程中,传统乡土性社会资本功能弱化既与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网络信息获取便利性增强有关,也与新一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经验累积有关。不过,尽管经济成本或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居住选择行动之间均存在着相关性,但笔者以为,农民工职业类型是影响其居住方式的关键变量。有学者通过将农民工就业状态区分为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两种类型,以考察二者在居住选择上的差异。[1]可一直以来,非正规就业在农民工群体中都是常态,即便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后,非正规就业在农民工密集的行业依然普遍存在,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只有41.3%。但在非正规就业现象普遍存在的行业中,建筑行业与服务行业的农民工在居住方式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前者普遍是集中居住在工地工棚中,而后者居住选择则更为多元化。[20]
在本文中,笔者将职业类型区分为加工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两大类型,前者属于工业范畴,后者则是第三产业范畴。尽管这两类行业生产价值链条中有高端与低端之别,但就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职业身份而言,他们多从事的是处于生产价值链低端的低技能依赖职业。可以说,中国发展过程中选择基于“劳动力红利”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模式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农民工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态。换言之,形塑农民工居住方式背后力量是中国的“工厂体制”。[33]在布洛维看来,所谓“工厂体制”就是工厂生产劳动的组织机制,对“工人的理性专制”是其核心内容,它“建基于劳动力再生产与生产过程的统一”。[34]在“工厂体制”作用下,会形成与工厂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居住类型,比如美国的底特律,其居住格局基本上是围绕汽车产业而分布的。在中国,“工厂体制”对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取向:一是在居住区位上,出现大量的工人集中聚居的空间带。各大城市建设的蓝领公寓就是一种代表,工业革命时代遍布全英的 “工厂村”亦类似;[35]二是在居住方式上,表现为农民工被集中安置的工厂宿舍或工厂社区,“集中居住,私人空间集体化”是典型特征。在旧中国时代,工厂就为工人提供住房,当时叫工房,在性质上与现在的员工宿舍类似。其实,工作单位承担员工住房的责任是一种常见现象,但在中国“工厂体制”下,工厂提供给农民工劳动力的宿舍一般不是为了培养员工的忠诚,而更多是“为了确保在短期内获得单身的、廉价的、年轻的外来劳动力”,代表的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劳动与居住方式”,[35]属于一种建立在“工厂体制”基础上的劳工控制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任焰等人直接将此种劳动组织方式称呼为“宿舍劳动体制”,通过该体制,资本将农民工劳动力集中在一起,使其居住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合二为一,从而将农民工居住方式选择整合进资本运作的逻辑之中。[35]
我们的调查发现,当农民工群体面临“要工作和离住所较远”的两难困境时,绝大多数会改变现有居住方式而迁就工作。而且,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流动性会对其居住选择产生影响,但是只要转换的职业类型依然属于“工厂体制”下的大规模加工制造行业,那么其依然倾向于选择集中居住方式。而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比如家政服务、饭店服务、城市保洁等,由于用工方式和工作时间弹性化,因而资本无需也无兴趣为了控制和加班便利而将之集中安置,这种情况下,此类行业的农民工多会选择分散性混合居住方式。(6) 有学者根据住房资源供给方,将这两种居住方式定义为资本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 因而,农民工城市居住方式的选择与产业类型密切相关,低技能依赖型加工制造产业规模越大,那么农民工居住方式上集中化程度越高。
(三)居住质量选择中的农民工主体
至于居住质量,这是目前学界讨论农民工群体城市住房问题关注最多的内容。一般而言,目前的研究基本上立足于城市群体住房贫困的角度,认为农民工群体城市居住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居住权利上都处于被排斥和边缘化地位。[36-38]客观而言,农民工城市居住整体上质量低下,这不但体现在集中居住的工厂宿舍或工棚上,而且农民工分散居住的地方也多属于管理薄弱、租金便宜的城市底层社区。这些社区,一般是人员混杂,建筑密度大,居住面积狭小,绿化率低,公共卫生状况恶劣,住所内配套设施简陋且不齐全;而且在软件上,往往也是物业配套服务滞后,治安秩序混乱,社会管理服务不到位。可吊诡的是,尽管农民工群体的居住质量都比较低下,但他们对于其城市居住的满意度却比较高,选择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农民工比例在样本总数的61%左右。(7) 数据来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 而且,改善居住质量往往并不是农民工群体变换住所的首要动机,更多是因为工作变动而影响了其居住稳定性。所以,尽管农民工选择居住地时会考虑住所的软硬件质量,而且这或许是他们唯一能够依据自身经济支付能力而自我选择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却是他们在城市社会空间居住生活中最不在乎的。虽然目前有些研究也指出,在居住质量的要求上,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显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11]但是两代农民工针对居住质量的选择行动基本上均是以服务工作为基准的,上班“便利性”原则作用始终。遗憾的是,一直以来,中国农民工群体在居住质量上的这种主体性状况并没有得到学界以及政策制定者的足够关注和重视,而由此推演出来的以改善居住质量为主导取向的政策实践行动不但效果不显著,反而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2013年《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鉴》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制造居住隔离:住房政策是如何形塑低收入少数族裔家庭居住格局(Segregating Shelter:How Housing Policies Shape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s of Low-Income Minority Families)》的文章,论文系统评估了美国针对贫困家庭住房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该论文指出,为了提高贫困家庭的居住质量,美国住房政策以住房券方式补贴贫困者以鼓励其到市场上选择满足政府居住质量标准的住所。这种政策从理论上来看是可行的,也是市场至上主义者一直倡导的理想救助模式。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贫困者的主体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但没有改善贫困家庭居住状况,相反,由于对居所严格的质量审查机制,导致这些贫困家庭为了寻求满足条件的居住地而不得不总是搬家,从而使这些家庭根本没有时间去融入当地社区。换言之,尽管政府吸纳了市场化手段,可这种忽略贫困者居住选择主体性的政策安排带有强烈的父权主义色彩,不但未能起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反而制造了新的居住隔离。[39]对于中国农民工群体而言,情况同样如此,在城市里落脚的时候,居住稳定性或许比居住质量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而且,由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持久化特征,以及城市在居住资源配置上的政策排斥,导致他们在居住选择的过程中,意在改善居住质量的经济投入动机并不强烈,属于典型的“重生产、轻生活”状况。另外,虽然农民工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但在农民工群体内部,经济收入差距现象逐渐凸显,技能农民工的年收入不但比无技能农民工收入高出55%左右,甚至比普通白领收入高出30%—50%,[40]但是我们的调查发现,经济支付能力不同的农民工之间在居住质量上并无多大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仅仅体现在建筑类型上,而在居住配套设置以及满意度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四、无奈的结论:选择的可行能力在何处?
“可行能力”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在《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可行能力(capability)概念,[41]并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1999)》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此概念。所谓“可行能力”是指社会成员“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功能性活动组合)包括吃、穿、住、行、社会参与等”,可行能力意味着有选择,而有选择的可能才意味着自由。[42]据此,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指出,物质的匮乏并非是造成贫困与饥荒的根源,对社会成员可行能力的剥夺才是其中的罪魁祸首。因而,在阿马蒂亚·森看来,虽然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它绝不能成为目的,它只是“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自由的手段和方式,最终是为扩展个人实质自由服务的”,而且进步的社会发展应该是提升人民可行能力并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
在分析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尽管上个世纪7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推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浪潮,可是时至今日,在他们落脚城市的过程中,国家力量在城市空间营造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工厂体制中强势资本事实上已经规定了他们居住选择(尤其是居住区位和居住方式)上的可能性。这种对农民工可行能力的剥夺,使农民工即便已经在城市中经历了整整两代人,也无法使他们的居住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找回农民工的主体性,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中居住质量的改善虽然必要,但却不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这个颇为让人无奈的结果提醒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在营造空间以及制定住房政策时,改善城市贫困流动人口居住质量固然重要,可是去除制度上的社会排斥、培养流动人口的可行能力或许更加重要。从理论上而言,行动者选择主体性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讨论的一个核心命题,经典社会学理论一般纠缠于“结构决定行动还是行动建构结构”之间的争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将此争论悬置起来,通过解构理性的具体内容分析行动选择的情境性,进而解释不同内容的理性选择背后的成因。本文也正是这种理论视角的具体尝试,笔者通过对农民工居住理性选择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试图从理论上调和经济成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之间的解释冲突,从而进一步思考抽象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关系。当然本文只是做了一个理论解释框架建构,还有待具体实证数据进行证明。
2016年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的“2016年度美术学系毕业生作品展”,2017年参加文化部艺术发展中心举办的“春风润2017青年画家学术展”,2018年参加“阳春格物——艺术博士书画作品展”等展览。
参考文献:
[1] Zhilin Liu,Yujun Wang,Ran Tao.Social capital and migrant housing experiences in urban China: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J].Housing Studies,2013,28(8):343-365.
[2]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132.
[3] 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147-153.
[4] 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M].王春光,单丽卿,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0.
[5] 朱明芬.农民工家庭人口迁移模式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2):67-76.
[6] 杜凤姣,宁越敏.拉美地区的城市化、城市问题及治理经验[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S1):1-6.
[7] 联合国人居署.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M].于静,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4.
[8] 李志刚,顾朝林.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转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9] 毛小平.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J].社会,2014(2):118-139.
[10] 叶鹏飞.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社会,2011(2):153-169.
[11] 王星.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J].江海学刊,2013(1):101-108.
[12] James Spates and John Macionis.The sociology of citie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2:43.
[13]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EB/OL].(2011-03-11)[2019-05-26].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fxbg/201103/t20110310_16148.html.
[14] 林李月,朱宇.两栖状态下流动人口的居住状态及其制约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人口研究,2008(3):48-56.
[15] Zhang T W.Restructuring and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China in the 1990s[J].Urban Planning Review,2001(7):304-315.
[16]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上海:三联书店,2000.
[17]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42-52.
[18] 张文宏.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上)[J].江海学刊,2011(2):104-112.
[19] 林南.社会资本[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4.
[20] 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4-05-12)[2019-05-2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5/t20140512_551585.html.
[21] 侯慧丽,李春华.梯度城市化:不同社区类型下的流动人口居住模式和住房状况[J].人口研究,2013,37(2):83-92.
[22] Shevky E,Bell W.Social area analysis[M].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61-67.
[23] Smith N.The new urban frontier: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M].London:Routledge,1996:18.
[24] Alonso W.Location and land use[M].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114.
[25] Mills E S.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197-210.
[26] Muth R F.Cities and housing: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residential land us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29.
[27] 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C] //王志弘,译.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7-58.
[28] Bian Yanjie,Logan J R.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5):739-758.
[29] 李强,唐壮.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J].社会学研究,2002(6):13-25.
[30] 刘欣,中国城市的住房不平等 [J].复旦社会学论坛,2005(1):149-171.
[31] 甘满堂,王岩.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23-126.
[32] 方长春.体制分割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差异[J].社会,2014,34(3):92-116.
[33] Fulong Wu.China’s great transformation:Neoliberal- ization as establishing a market society[J].Geoforum,2008,39(3):1093-1096.
[34] 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M].Verso Books,1985:126-148.
[35] 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6(4):21-33.
[36] 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12-18.
[37] 任焰,梁宏.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珠三角”农民工居住状况分析[J].人口研究,2009,33(2):92-101.
[38] 郑思齐,廖俊平,任荣荣,等.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46(2):73-86.
[39] Stefanie Deluca,Philip M E Garboden,Peter Rosenblatt.Segregating shelter:How housing policies shape the residential locations of low-income minority families[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13,647:268-299.
[40] 李星.江西农民工收入较普通白领收入高30%—50% [EB/OL].(2014-04-11)[2019-05-26].http://news.jxntv.cn/2014/0411/5160736.shtml.
[41]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2-26.
[42]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2.
State ,Regime of Factory and Spatial Separ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Migrant Workers Housing Choice in Urban China
Wang Xing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
Abstract : Migrant workers’ housing choice include three different parts,namely the living location choice,the living type choice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choice.These three parts work in order of priority in the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 decision-making.For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the location choice refers to choose living areas where are the most convenient for users.Stronger is the ability to attract outside investment,the concent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ve in suburb is higher.Our data indicated that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who working in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tend to choose centralized living type,most of them live in the collective dormitories,what were supplied by the employers.Yet,who working in service industry usually live in the decentralized type,they tend to rent an apartment alone or with their relatives or friends in common communities.Although they would like to choose good quality housing as their income increase,but most of the rural-urban migrant workers did not care about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 Housing choice;Living location;Living type;Living conditions;Capability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9)05-0063-08
[收稿日期] 2019-07-24
[DOI] 10. 19669/ j. issn. 1009-5101. 2019. 05. 009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国家技能形成体制国际比较研究”(6318207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王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