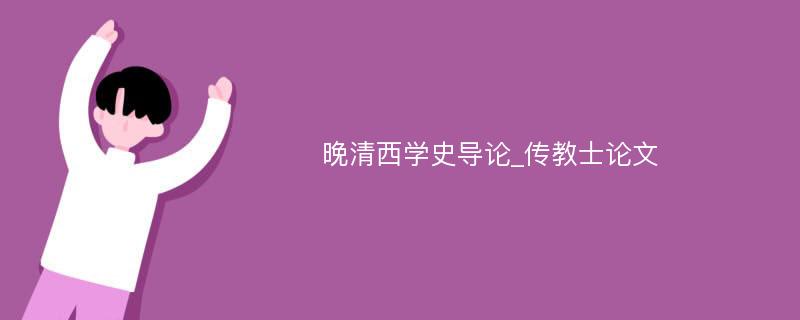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晚清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西学东渐,潮落潮涨,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到物竞天择,自由民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势如江涛翻卷,滚滚而来,影响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传播过程波谲云诡,社会反应百态千姿。本文概括地介绍了西学东渐历史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薄弱环节,对西学传播阶段的划分、影响西学传播的各种因素、不同时期西学传播的主题、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总体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研究概况与存在问题
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情况,1949年以前学术界已经作了不少的研究。
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台湾学者和外国学者的论著更多。如杜石然等人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982),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1984),钱存训的《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1954),郭廷以的《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和《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晚清译书与西学》(均载《大陆杂志》),等等。
然而,从总体上说,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料的挖掘,整理还有很大缺门。学者们研究这段历史,主要依据的目录书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及其增订版、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以及由此按图索骥所获得的各种西书。这三种目录书有两大缺陷,其一是对同治以前所出版的西书基本未收(只收录了墨海书馆等机构出版的少数几种)。这样,鸦片战争前后几十年中传教士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广州、宁波等地所出版的各种西书,便不大为人所知。其二是这些目录书收录西书的截止时间为1904年,此后的译书便被人们忽略。这样,斩头去尾,译书总数少了将近一半,自然难以得见西学传播之全貌。此外,对于各种译书机构的历史、重要西书的翻译过程、重要译员的译书背景,有待挖掘、整理的资料更多。比如,对于晚清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除了笔者几年前写了一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便无人作过深入研究。
二,西书内容有待进一步理清。许多西书,人们只闻其名,不知其实,其译自何书,内容如何,与原书有何区别,均不甚了了。例如,在19世纪末举国争诵、洛阳纸贵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其内容究竟如何,影响为什么那么广泛?并没有人仔细研究。传教士著作中,曾被送给清朝政府各个高级官员、影响极为广泛的《格物探原》和《自西徂东》,内容究竟如何?迄今无人研究。再如,被晚清学者称为介绍西方政治的最佳著作、许多思想家认真研读过的《佐治刍言》,其内容究竟如何?也没有人深入研究过。
三,对社会影响的研究相当薄弱。学者论及西学传播的社会影响,往往就是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的影响,对于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注意不够。例如,论及20世纪初西学的影响,论者每每以严译名著为例,其实,走进千家万户、莘莘学子朝夕诵读的各种新式教科书,其社会影响不知要比严译名著高出多少倍。再如,讨论西学社会影响,论者比较注意江南制造局、广学会等机构从西文直接译为中文的西书的影响,而忽略了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其实,无论从影响的广度还是深度来说,后者都远远超过前者。
四,对于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缺乏综合研究。对于传播西学的总体估计、传播阶段的划分、各个阶段的特点、译书方式的演变、传教士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在掌握比较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作细致的分析。
四个阶段
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成为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以后,传教士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开学校、办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这一阶段,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2种,比较重要的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了解世界情况的重要资料。英华书院、马礼逊学堂等学校创办,开始了传教士在华人中进行教育活动的历史,也培养了袁德辉等近代中国最早的译才。马礼逊等所出版的西书、报刊,所办的新式学校,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能与日后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相比,但这是一段历史的开端。近代西学东渐史上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诸如第一个中文印刷所,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教会学校,第一家中文杂志,第一部英汉字典,等等。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气势,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始了晚清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6个开放口岸,在西学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香港、广州,在割让或开埠以前,早有西人居住,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开埠以后,西人来此,又有新的发展。二是福州、厦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已通过在南洋闽籍华侨中的活动,学会方言,这两个城市开埠以后,传教士来此,没有语言障碍,西学传播活动比较容易进行。三是宁波、上海。这两个城市位于富庶的江浙地区,离中国中心地带比较近,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上述4城。在咸丰年间,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是上海、香港与宁波,出版西书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
从1843年至1860年,这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各城市所出西书总数、宗教书籍、科学书籍情况分别如下:香港60种,宗教37种,占61.7%;科学23种,占38.3%。广州42种,宗教29种,占69%;科学13种,占31%。福州42种,宗教26种,占61.9%;科学16种,占38.1%。厦门13种,全属宗教方面。宁波106种,宗教86种,占81%;科学20种,占19%。上海171种,宗教138种,占80.7%;科学33种,占19.3%。依出版科学书籍多少的顺序排序,依次为上海、香港、宁波、福州、广州、厦门。
这一阶段,西学东渐有几个特点:
1、通商口岸成为传播基地。此前,传教士在南洋一带活动,虽然西学书刊也能传到中国大陆,学校中也有不少华人,但毕竟水路迢迢,对中国影响有限。一口割让、五口通商以后,传教士以这些地方为基地,办学校,开医院,出书刊,进行各种西学传播活动。从此,新一轮的西学传播在大陆正式开始,半月形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率先接受西方影响的地区。
2、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科学著作。合信的《全体新论》等五种医学著作,是晚清第一批西医著作;蒙克利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著作;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力学著作;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
3、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主动了解吸收西学的趋向。林则徐、梁廷枬、魏源、徐继畬、李善兰等为其代表人物。尽管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国际常识、世界史地知识,但毕竟是一种新的动向。
4、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加译书工作。南洋时期,虽然也有中国人参与传教士的工作,如梁发协助米怜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那是以教徒的身份出现的,且限于宗教方面,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无所补益。1843年以后,在上海、广州,都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西书翻译工作,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为其著者。他们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参加工作,有些西书的译介,还是在他们主动提议下开展的,如《续〈几何原本〉》便是在李善兰的提议后着手翻译的。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开始了晚清中国历时数十年的西译中述的历史。管嗣复表示只译科学书、不译宗教书,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西方文化时的独立性和选择性。
第三阶段,1860-1900年。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天津条约》等条约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内容有:一、增开天津、南京、汉口等11个通商口岸,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二、传教自由,《中英天津条约》第八款规定:“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三、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中国政府应提供方便。四、开放长江。这样,加上先前割让的香港,开放的五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达17个。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到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其结果,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在清朝政府方面,以咸丰皇帝去世、祺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北京条约》的签订,成为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阶段的西学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传播机构多种多样。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按其属性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教会系统的,主要有广学会、美华书馆、益智书会、广州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二是清朝政府系统的,有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天津机器局、天津武备学堂;三是民办系统的,如商务印书馆、译书公会、时务报馆、农学报社。此外,有些教堂、学校、报馆、医院、海关、督抚衙门,也零零星星、断断续续地出版过一些西书。其中,最重要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
2、政府创办译书机构。此前,清朝个别官员,如林则徐,也曾在吸收西学方面作过努力,但那时临时应急措施,并无长久打算。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政府先设京师同文馆,再设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中国政府在被动开放的形势下作出的顺乎时代潮流的反应,是中国政府主动吸收西学的标志。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西书数量,在各种译书机构中,名列榜首,影响也最大,说明了官办译书机构在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主导作用。
3、翻译西书量多面广。40年中,共出各种西书555种①,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学、教育等,占总数22%;自然科学162种,含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光学、动植物学等,占总数29%;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占总数41%;其他45种,包括游记、杂著、议论等,占总数8%。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5倍多。至于质量方面,著名译作颇为不少,《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民约通义》都是影响广泛、轰传一时的译作。
4、上海成为译书中心。1860年以前,上海已有成为中国译书中心的迹象,与宁波、香港同为中国出版西书较多的地方。1860年以后,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系统,还是中国政府和民办系统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十之七八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部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77%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绝大多数最有影响的西书,都是上海出版的。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
5、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读者提问,从《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从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儿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生病不但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开后门进新式学校的事;光绪皇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0至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朝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方式亦因之一变。这一阶段西学传播特点主要有五: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的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万家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令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影响西学东渐因素分析
西学东渐的内容、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是影响西学东渐的首要因素。晚清中国,西学传播主体主要包括西书翻译人员、新式学校教习和部分报刊编辑,他们的西学素养、传播热情直接影响到传播质量。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一方面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没有传播,便无从接受,另一方面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制约的关系。传播主体翻译什么、介绍什么,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而是要看受传对象能够接受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有如剧院演戏,既要受演员表演水平、上演剧目制约,又要随观众的兴趣和需要而转移。晚清前三阶段所传西学,多属初等、中等程度,既与来华西人的文化素养有关,又为受传对象的接受基础所左右。傅兰雅、李提摩太等人的化学、物理等许多西学知识,都是因受传对象需要而在中国自学的,他们为此而耗资购买各种仪器。按理,他们身在中国,远离西方学术界,如凭个人兴趣爱好,则自修哲学、神学、法学,要比自修物理、化学更少依赖仪器设备,更为便当。但他们明白,后者比前者更为受传对象所需要,更受中国人欢迎。
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晚明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10年初见成效,取得一批士大夫支持,20年大见成效,进入北京城。晚清则不一样,即使以鸦片战争以后的情形而论,20年过去,到1860年前后,除了在几个通商口岸,西学传播、西教传播都没有太大的进展。照理,200多年过去,交通设施、通讯手段、印刷技术都较从前大为改进,文化传播应该取得更为可观的成效,但事实不然。考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在晚明时期,耶稣会士来华,虽然在整体上是属于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范畴,但从具体来说,中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主权国家,并不是耶稣会士所在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战败国,利玛窦等人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霸主心态,徐光启等人也没有受辱挨欺、卧薪尝胆的败国心态。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文化地位比较平等。晚清则不然,欧美传教士挟胜国之势,夸救世之口,兼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与作为受传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国家之间地位的不平等而构成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其二,晚明利玛窦等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时,采取的是以西顺中、以耶补儒、以儒证耶的策略,让士大夫们在不损害中国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晚清来华传教士则多以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这两点归结为一点,便是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问题。在晚明,两者心理距离较小,文化传播比较容易实现;在晚清,心理距离较大,文化传播的阻力也大。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一方面便利了传教士的活动,有助于西学传播,另一方面又拉大了传教士与中国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妨碍了西学传播。这是影响晚清西学传播效果的时代因素。
传播媒介是影响西学传播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印刷技术的进步,由木刻,而石印,而铅印;运输工具的发展,由帆船,而轮船,而火车;通讯手段的改进,由人工传递,而电报、电话,都使得传播速度不断加快,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晚清西学传播,同光之际之优于道咸之际,20世纪初之胜于19世纪末,不只是因为传播机构的扩大,传播人员的增多,而且因为传播手段的改进,传播媒介的发展。没有铅印,便很难想象每日成千上万张的报纸如何出版,很难想象《泰西新史揽要》那样动辄万册的书籍如何印出。没有海底电缆的铺设,没有电话的发明,也很难想象发生在地球那边的新闻如何瞬息传到这边。
译书方式是影响西学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在晚清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译中述是西书中译的基本模式,即由外国学者口译西书意思,由中国合作者润色加工,条理成文。诗无达诂,译无达译,从根本上说,任何翻译都有损益变异。中、西文化本属不同文化系统,长久隔阂,翻译更为不易,以仅通中文大意、难解个中奥蕴的西人口译,已经打了一个折扣,加上不通西文、难得西方文化真谛的中国学者的笔述,又打了一个折扣。这样三转两折,以中文印刷符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西方文化,已经加进了不少中国文化的成份。这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属于精神文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用“省”或“州”翻译美国的State,中国学者看到省、州字眼,总是以将其与中国的十三行省、省州府县等概念联系起来,但事实上,联邦制度下的State,与专制制度下的省、州决不是一回事,差别很大。最典型的例子是对西方民主国家总统President一词的翻译。因为在中文已有词汇中,是没有与总统对应词的,因而在口译时,西人只能从总统在国家的地位的角度,解释说这是国家元首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元首与皇帝是同义词,于是,中文笔述者理所当然地将President译为“皇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文西书和《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书刊中,随处可见美利坚国“选举皇帝”、“皇帝四年受代”等字眼。后来,林乐知发现以“皇帝”翻译总统,误解实在过分,特撰《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予以厘清。这种译书方式,在19世纪末已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到20世纪初,更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讽刺小说,就不止一次地以此类译书作为笑料。应该指出,这种方式是长久封闭而又被动开放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产物,也是一种过渡方式。所译之书,尽管可以批评的地方比比皆是,但有胜于无,它毕竟给闭塞的中国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其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五大主题
百年之中,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或为西人控制,或系华人主持,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综合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西学东渐是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的:
一、了解世界。鸦片战争,中西会面,三千年一大变局,西人面对的是闭塞的中国,国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让中国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是一批西人的愿望,也是中国洞烛机先之士的共识。前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郭实腊的《大英国统志》、《贸易通志》;中有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后有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傅兰雅译《公法总论》、《各国交涉公法论》,还有介绍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的各种新志、通史。这些著作,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介绍了国际交往的惯例通则,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
二、求强求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外国军队打到京师,逼签城下之盟。这对清朝政府来说,既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也是暴露积贫积弱的奇祸巨变。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因之而起。围绕着这一运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学技术,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主体部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输入此类西学的大本营。求强的译作有关于新式军队、先进兵器、西方兵法的系列书籍,《行军指要》、《水师操练》、《克虏伯炮说》、《制火药法》、《防海新论》等为其著者。求富的译作有探矿采煤、冶金制器、农工经济等方面,《宝藏兴焉》、《工程致富》、《探矿取金》、《西艺知新》、《农学初级》、《农务全书》等为其要者。与此同时,西方自然科学作为冶炼制造的基础知识,被广泛地介绍进来,举凡数、理、化、天、地、生,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有专门译作,而且一般都有普及读本与学术专著两个层次。分门别类的须知、入门、启蒙、图说、纲要、揭要、浅释,把自然科学界装点得色彩斑斓。
三、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瓜分之祸,迫在眉睫,摆在人们的面前,已经不是求强求富,而是救亡图存的问题。于是,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泰西新史揽要》风行一时;以亡国灭种作警告、以针砭时弊为特色的《中东战纪本末》传诵海内;以教育兴国作号召、以日本变法为借鉴的《文学兴国策》倍受欢迎。天演学说因之走红,立宪之议随之高扬,各种变政历史、亡国历史、维新传记纷纷出版,各种醒华、救华、兴华、振华的刍议、卑议、高议、新议、通议、危言、庸言竞争相提出。这一问题,自甲午迄辛亥,一直是中国志士仁人关心的重点之一,也是译书的重点之一。
四、民主革命。1900年以后,民主革命风潮涌起。民约论、自由论、自治论、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美国独立宣言》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弥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与反满宣传相呼应,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战纪、秘史、轶闻,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志士、杰士、义士、侠女的传记,译作纷呈。梁启超等改良派不赞成反满革命,但他们的许多翻译、宣传,仍属于广义的民主范畴。与民主思潮涌来的同时,被视为比民主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
五、科学启蒙。从狭义上说,有意识地介绍科学基础知识、以提高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为宗旨的活动为科学启蒙。从广义上说,晚清所输入的西方科学,绝大多数属于启蒙范畴,因为那时民众的科学素养,多很低浅,所传科学知识,从总体上说,多为基础知识。有意识地、比较系统地进行科学启蒙,自傅兰雅编辑《格致汇编》、中外合办格致书院开始,益智书会所编的大部分教材,也可归于此类。真正形成规模、影响深远的,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推行新的学制以后,涵盖各种学科、包括不同层次、遍布城市乡村、沿海内地的新式教科书。与此相呼应的,各种歌略、韵语、图说,也是科学启蒙的重要读物。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天文歌略》、《地理歌略》、《地球韵言》、《女学歌略》,虽然字不满千,纸仅数页,但其影响,往往超过同等内容的高头讲章。
百年历史,云谲波诡,时代主题,依次兴替。西学的形象,由夷学,而西学,而新学,而显学,而救时之灵丹妙药(邹容语),地位在不断上升,使命被不断加重,西学东渐的旋律,自然依时代主题的切换而改变。
传教士:宗教与科学
传教士在晚清西学东渐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角。但是,对于传教士在西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传播西学的目的,及其对待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不缺乏深入的讨论。传统的做法、说法有三:一是回避,在述及某些西学输入时,只提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译员的贡献与成就,闭口不提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传教士的努力。二是将宗教与科学分离,所谓传播科学是假,宣传宗教是真。三是认为传教士故意传播一些粗劣、过时的西学,隐匿西学中的精华部分。这些说法,在以前涉及传教士与西学问题的论著中,比比皆是。
有些问题,是无需论辩、不言自明的,如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中的作用、地位问题。既然当时译书形式是西译中述,肯定了中述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的作用与地位,毋庸置疑,同样应该肯定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的作用与地位。有些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传教士宣传西学的目的,有些则涉及到重要的文化理论问题,有必要加以研究和讨论。最核心的是,传教士对待科学的态度,亦即基督教与科学的问题。
说到基督教与科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宗教对科学的排斥,教廷对科学家的迫害,日心说遭排斥,伽利略受审判,布鲁诺被烧死,进化论遭攻击。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与科学,水火不容,互相对立。
其实,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一个显而易见的诘难是,如果两者关系确为水火,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在宗教统治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里,西方应该毫无科学可言,那么,近代科学何由而来?西方许多大科学家,开普勒、波义耳、牛顿为何同时也是虔诚的宗教徒?
对这个问题,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一种意见认为,基督教对科学不但不是完全、绝对排斥的,相反,还有一些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不同历史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古希腊科学留下了两种传统,即数学唯理主义自然观和机械主义自然观,前者以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自然界是按照数学原则构造起了的,因而可被人的理性从数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后者以阿基米德、托勒密等人为代表。中世纪基督教利用了作为统一意识形态的力量,将这两种观点灌输给整个社会。在中世纪的神学教育中,数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基督教为了使人们信服上帝,需要用自然秩序去论证上帝的伟大,认识自然秩序是认识上帝的必要途径。中世纪的神学家,都是通过自然界的和谐去论证上帝的存在。数学,则是研究自然的必备工具。宗教改革以后,新教伦理以如下三个原则促进了科学的发展:1、鼓励人们去赞颂上帝,颂扬上帝的伟大,是每个上帝臣民的职责。2、赞颂上帝的最好途径有二:一是研究和认识自然,因为上帝的智慧完全体现在它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中;二是为社会谋福利,最好的途径是运用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3、提倡以辛勤的劳作颂扬上帝,以过简朴的生活感谢上帝。②我以为这种解释是可以成立的。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段时间里,当科学的结论与宗教的教义相抵触时,宗教会排斥、压制科学。哥白尼的日心说与基督教信奉的地心说相抵触,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论与上帝造人说相违背,教会便对这些学说横加压制、排斥,伽利略受审判,进化论被冷落。但是,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广大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日心说终于被接受,伽利略毕竟被平反,就是明证。基督教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信仰系统,否则,在科学日益昌明的西方,基督教仍然是影响最广的第一大教,许多科学家同时也是信徒,甚至有些诺贝尔获得者最后又皈依上帝,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可以看出,第一,对于一般科学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生物、医学等传教士是乐于介绍、宣传的,没有必要隐瞒。第二,对于某些与基督教义相抵触的科学知识,传教士的处理方式与西方教会同步。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对日心说避而不谈,到了清代,蒋友仁等已不回避,且有准确的介绍。晚清来华传教士,宣传的都是日心说。对于达尔文的人猿同祖说,传教士一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也与西方教会的态度一致。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述及,傅兰雅在《格致汇编》中就曾提到。第三,所谓传教士对西方科学精华部分秘而不宣、只介绍低浅粗劣部分的说法,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的臆测之言。传教士中,科学素养不高者有之;所传西学中,低浅粗劣者亦不少见,但谓其故秘其宝、生怕以利器授人的说法并无根据。
对于宗教与科学,晚清来华传教士曾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
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象一对孪生子——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我会就是宗教和科学这两者的代表,用我们的出版物来向中国人宣扬,两者互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③对照他们在华传播西学的活动,我以为这个说法并无自诩过当之处。
当然,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对传播科学的态度、热情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说,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新教传教士所做工作较天主教传教士为多;新教传教士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世俗派所做工作较戴德生等基要派为多;19世纪后期所做工作较20世纪初期为多,但无论哪一派,哪一时期,都不存在完全排斥科学的情况。
注释:
①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截止1899年,共收西书567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减去1860年以前出版的12种,故总数为555种。
②参见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章。
③广学会年报,第十次,1897年。见《出版史料》,1991年第2期。
标签:传教士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清朝论文; 晚清论文; 李善兰论文; 马礼逊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