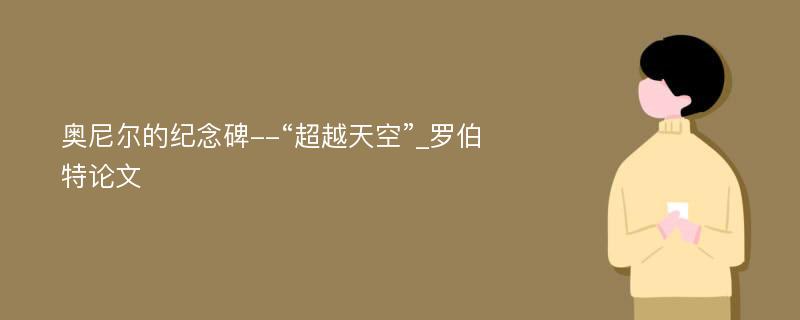
奥尼尔的一座丰碑——评话剧《天边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话论文,一座论文,丰碑论文,天边论文,奥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现代戏剧之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在1918年创作的话剧《天边外》,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使他第一次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奠定了他在美国戏剧史上第一流剧作家的地位。在创作这部剧作前,他主要是创作独幕剧,他虽已完成了四部大型话剧作品,但被人称为没有一部可供演出的。而《天边外》于1920年2月在摩洛斯剧院上演,使观众耳目为之一新,使那些只习惯于在瞬间看到奥尼尔洞察人生的观众,看到剧作家在多幕剧中如此善于充分发挥,写出令人信服的人物,为剧作家卓越的艺术才华而折服。
尤金·奥尼尔在《天边外》中表现的主题并不是剧作家创作上的初次出现,而是他早期戏剧创作中常出现的主题。《天边外》只不过是对以前表现过的主题加以综合:梦想使人能活得下去,梦想在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严峻的现实生活又给梦想蒙上种种阴影,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夫妻冲突、父子冲突,理想主义的诗人和实利主义的商人之间的对立的价值观,土地的魅力、大海的魅力。当然,剧作家给此剧命名为《天边外》又有意味深长的寓意:凡是人都必须去探求人生的终极意义,去寻求和发现在天边外的那种生命背后的神秘力量。当然,由于剧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使他并不能真正地认识美国社会的复杂,不能把握住人生的终极,而给人生蒙上一种神秘。
《天边外》这个戏的最初创作契机的产生是一件偶然而微不足道的小事。据说,有一天,尤金·奥尼尔坐在普罗文斯顿海滩上,有一个6岁的低能儿童对他“产生了一种深切的感情”,这个孩子走到剧作家跟前,向他喃喃地提出一连串的疑问:“海峡外边是什么?大海外边是什么?欧州外边是什么?”奥尼尔很简单地回答他:“天边。”那个孩子当然不满足剧作家的答案,他继续缠着问:“那么,天边外又是什么呢?”[1]
但《天边外》中的事和人物并非作家凭空臆想捏造,而是有现实生活根据的。《天边外》上演两个月后,获得很大的成功。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写道:
《天边外》的想法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来的。我在英国货船上当水手,往来于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船上有一位挪威水手跟我非常要好,他常常发牢骚说,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和错误,就是小时候离开他爸爸的小农庄逃到海上来,他在海上呆了二十年,没回一次家。他咒骂大海和海上生活,但却又夹杂着对海洋的温情厚意。他喜欢滔滔不绝大讲他如何离开农庄的那件蠢事。这大概就是生活吧。这个人常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我想,如果他带着那种感情,留在农庄上会怎么样呢?会出什么事呢?不过我马上就明白,他绝对不会留下。他装出一副想回农庄的样子,无非因为他觉得有趣。从那一点开始我就想出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更有文化、更文明一些,像我那位挪威同事一样,坐下来就喜欢大海的惊涛骇浪,只不过那种对海洋的向往在他心里却变成了模糊的、难以捉摸的漫游癖。他的意志力又不太坚强,为了一点带有诗意的渴望,比如说爱情吧,他就会抛却他的美梦,接受农庄的苦役……[2]
那个常发牢骚,认为从小离开爸爸农庄逃到海上来是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和错误的就成了《天边外》的安朱·梅约,而那个“更有文化、更文明些”,梦想大海,梦想到天边去闯荡的,带有诗人气质的青年,为了“男女之爱”而放弃自己对大海的梦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罗伯特·梅约。
而应指出的是罗伯特还揉进了剧作家奥尼尔身上的某些特征,如罗伯特身上的诗人气质,念过一年大学,体弱,身患肺病等,虽然他同父母和哥哥关系很亲密和谐,但他总感到天边外有什么魔力在召唤他。
我们从剧本中的戏剧情节中隐约可以发现与原型故事和人物有不少相似处和相同处。从这一点看,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天边外》的素材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天边外》中的事件是从剧作家自身生活经历和他接触的人物身上概括、提炼、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出来。所以,这是一出现实主义优秀剧作。
罗伯特和安朱虽是弟兄,同父母生,但他们的气质、文化、个性不同。安朱中学毕业就在父亲的农庄干活,他不仅成了父亲杰姆士的接班人,杰姆士还希望安朱和露斯结婚,以便把露斯家的农庄合并过来,扩大农庄规模,而且要使农庄成为州的优秀农庄。安朱也真爱土地,爱农庄,又有他心爱的姑娘,只是出于腼腆,未向青梅竹马的姑娘露斯表示爱,他也不知露斯是否爱自己,他们相处得很好,是好朋友,每每露斯和母亲到他家来做客,他都主动帮露斯推瘫痪的母亲坐的轮车。
而罗伯特,或许他身体从小不如哥哥安朱健壮,农庄的活儿,安朱和杰姆士都干了。所以,罗伯特从不干农活,他上了一年大学,杰姆士就不愿出钱让小儿子继续上大学。罗伯特休学在家,但他从小爱读书,整天埋在旧书里,他从书里开阔了眼界,使他想象力丰富,富于幻想,他从小就梦想到天边外去,而痛恨农场,他想到处跑,不在哪一个地方扎根;喜欢大海,向往大海,充满对天外边美好的憧憬。他梦想的是美。“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那叫我去的就是美,遥远而陌生的美,我在书本里读过的引人入胜的东方神秘和魅力,就是要到广大空间自由飞翔,欢欢喜喜漫游下去,追求那隐藏在天边以外的秘密。”
在生活中,每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梦想,都会做白日梦,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梦想、希望、理想。梦想和幻想、理想紧相连,可以说是兄弟。人从幼小到成熟,总会有天真浪漫稚真的想入非非,这就是人的幻想。但随着人成长、成熟,经历多了,经验丰富了,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形成他的理想,理想是根据主客观条件、时代、社会而制定出的接近实际的思想。理想要在实践中努力实现,而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沉溺在幻想中,停留在人的初级、幼稚阶段。而罗伯特却只处在幻想之中,从未看到幻想、理想与现实生活是存在着差异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距离,可以说现实生活是严峻的、残酷的,人与生活开不得玩笑。罗伯特是一个白日梦者,他不能适应现实生活,他不懂生活。
罗伯特和安朱迎接舅舅迪克·司各特、圣代号船长的到来,本来这是罗伯特实现梦想、理想的极好机会,他可以随着舅舅的船去到天边外,去实现周游世界,领略“东方的神秘和魅力”,“到广大空间自由飞翔,欢欢喜喜漫游下去,追求那隐藏在天边以外的秘密。”他正准备就绪要跟舅舅去航海,却在离开的当晚路遇姑娘露斯,而突然萌生对姑娘的爱情,向姑娘表示了爱,他意外发现姑娘露斯爱的不是哥哥安朱,而是他。
露斯坦露出自己的所爱,不知露斯是经过深思熟虑,还是一时冲动?但她的爱的表示是轻率,欠慎重的。露斯说出所爱,决定了罗伯特和安朱的一生的生活抉择,她给安朱和罗伯特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铸成两兄弟一生的悲剧,使安朱和罗伯特更改了生活的道路。痛恨土地的罗伯特决定留在农庄,不跟舅舅去过三年的海上生活,放弃自己的追求;安朱却因露斯爱上弟弟而不愿在尴尬处境中生活,决心离开喜爱的农庄,而随舅舅,代替罗伯特去当水手,去过周游世界的生活。
安朱的突然决定也使杰姆士顿生恼怒,他要让儿子娶露斯,把她家农庄扩大过来,使建成全州最好的农庄的美好计划在安朱身上实现,而如今,安朱为了一个女人却要离开他心爱的农庄,他一向认为了解大儿子,他是看着他长大的,熟知他的脾气,“你的脾气就是我的脾气。”在杰姆士·梅约眼里,安朱“从骨子里是个梅家人,他是天生的庄稼汉,而且还是一个好极的庄稼汉。他会像我所盼望的那样。”而如今,安朱的言行使杰姆士伤心、不满、愤懑,他的梦想眼看要扑灭。当然,杰姆士是不会甘心的。杰姆士与安朱之间的父子冲突,也可以说是土地与大海之间的冲突。当然这也是不可调和的。杰姆士虽然知道儿子为什么要离开父母、土地,但却挡不住儿子离家去航海。这就铸成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安朱离家随舅舅生活,杰姆士恨儿子,不愿再见他。一别父子再也未见面,直至杰姆士离开人间,也未谅解儿子安朱离家去航海的抉择。
应该说,安朱的抉择让全家都吃惊。人们明知安朱的抉择是不明智的,而是赌气出走,但却无法挽回。安朱和罗伯特是一对好兄弟,他们很和睦,即使俩人爱上一个姑娘,也未能破坏兄弟情谊,而仍知心,坦然交心,安朱明白无误地向罗伯特说出心里的话:“我告诉你,我非走不可,我呆在这里会发疯的。”“阿罗,你也爱她,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要记住,我到现在还是爱她的,要是我呆下去,我还会爱下去。”“要是我呆下去,我就会恨这个农庄,”“我不可能对工作再感到任何兴趣,因为看不到任何目标。”安朱他毕竟年轻。他离开农庄,当了一段海员,很快厌倦了海上生活,他离开大海,他穿梭于美国——智利之间做起粮食买卖,最后做起投机买卖,浪迹天涯。他不仅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商人,经过三年浪迹天涯,他人也变了。他的感情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据他自己说,他不仅不爱故土,他表示离家半年就不再爱露斯了,对自己的三年前的出走不后悔。
罗伯特为了露斯留在农庄,但不谙农活,他又不扎实地从头学农活,不会管理农庄,他的“旧病”未改,他仍爱他的书,干什么农活都不行。杰姆士自安朱出走后,他的美梦被扑灭,他眼瞅着罗伯特的所做所为,让他心灰意懒。安朱离家二年,他就含恨离开人世。父亲在世,罗伯特还有依靠,一旦父亲撒手而去,罗伯特一切都不顺心,他虽不偷懒,但一个不懂农业的人怎么能管好农庄呢?不仅在干农活、管理农庄上不行,在爱情上,他也很快失去了露斯的爱情,露斯的母亲也不断指责、抱怨罗伯特的无能。
露斯在与罗伯特结婚后,很快发现她爱的不是罗伯特,而是安朱,她很快就懊悔了。所以,当收到安朱来信,说要回来看看,露斯抑制很久的感情又复燃,她不让罗伯特和女儿玛丽在一起,她不再支持罗伯特看书,而是厌烦。她拿安朱与罗伯特比,她憎恶罗伯特:“阿安不像你,他喜欢农庄。”她毫不掩饰地对罗伯特说:“我不需要你了。阿安就要回来了。”罗伯特惊异地大喊大叫,露斯反抗地说:“我爱阿安。”“他也爱我!”“我知道他爱我。”
当他们听到安朱从路上发出“哎咳”的大声呼叫声,露斯情不自禁地欢呼:“阿安!阿安!”就冲过去开门。罗伯特见状命令她:“住手”,阻止她,他自己去接,外边传来的是:“哎咳,阿罗呀!”
安朱的回来并未使罗伯特振作起来,他独自跑到农庄的小山顶,他仍眺望天边,他的脸色苍白憔悴,表情极度沮丧,他不愿和安朱和露斯在一起。
安朱只想回农庄看看,看到农庄经营欠佳,父亲已不在。他虽不喜欢海上生活,但也不想留在农庄,这使露斯很失望,她的爱未得到回报。他对露斯很冷淡,他仍要去布宜诺艾利斯去经商,这时的安朱已不是三年前的安朱,他已成了实利主义者,所以他拿出一千元给罗伯特,但遭到自尊心很强的罗伯特的拒绝,他又匆匆离开农庄。
五年后,罗伯特经营的农庄濒临破产,罗伯特意识到他完全失败了,他事业上垮得一塌糊涂,他的女儿也病故了,他母亲也病故了,他在感情上也失去了露斯,他肺病也很重。但是他仍未完全丢掉梦,而且还在做另一个梦:他要带露斯进城,以写作为生,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梦。但他的身体彻底垮了,安朱请来城里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但也无济于事,他在临终前,要安朱照顾露斯,他自认最后得到解脱,他自由了。罗伯特的死意味着什么,给人留下深思,也许不同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
安朱由于失去露斯的爱而离开了心爱的土地,由爱土地转为恨土地,他在海上漂泊一段,也失去兴趣,转而经商,由种粮食的庄稼汉转为经营粮食买卖的投机商人,他在激烈的竞争中,发过财,几乎成了百万富翁,但他很快又失败了,失败并没使他丧失信心,他还要继续干,他无心经营快倒闭的农场。安朱变得对感情冷漠,不再爱原来曾爱过的女人,他也是一个失败者。
《天边外》中的人物可以说无一不是失败者。剧作家是个敢于正视现实生活的人,他用艺术家和诗人的目光和笔触解剖生活。作者笔下的人物虽是失败人物,但他们在曲折、失败中,不沮丧、不退缩、不屈服,勇敢地面对生活,所以,让观众(读者)看后,并没有颓唐,灰溜溜的感觉。剧作家写的是现实生活,他毫无粉饰生活之意。剧作家热爱生活,正视生活。
《天边外》问世,正处在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创作高产时期,而且是他的创作趋向成熟时期。《天边外》具有转型期的特点。剧作家由独幕剧转向多幕剧创作。从《天边外》剧本本身仍可窥其独幕剧的痕迹。如三幕戏,每幕分二场,每一幕都有一定独立性,三幕戏时间间隔长,幕与幕之间也没有用主要事件贯串,人物性格、感情跌宕大。从时间上看:三幕相隔八年有余,在剧中表现了三个季节:春、夏、秋。
另外,在表现方法上也有新特点,《天边外》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剧作,但也揉进象征主义手法,丰富了《天边外》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说,《天边外》是奥尼尔创作实验戏剧的开端。
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局限,他对美国现实生活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说,他看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活的不合理性,但他却难以看出人们可以左右自己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主人公的遭遇仿佛都是冥冥中由天安排的。人们盲目追求,拼命挣扎,无期等待,徒劳地同命运抗挣,但最终仍无法逃脱悲惨的结局。
《天边外》中的三个青年罗伯特、露斯、安朱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无论爱情、事业、生活都失败了。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希望、追求、憧憬,但他们把希望、憧憬寄托在“天边外”,可以说寄托在虚无飘渺中,所以无法获得成功。尤金·奥尼尔试图在剧中表现出人的命运不可知,人对未来的无法把握。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并不是哪个恶人造成的,而仅仅是露斯的一时冲动造成的,这一突兀的举动,露斯当时也很难解释,一旦她发觉错误时,为时已晚,这不仅毁了罗伯特和安朱兄弟,也毁了她自己的一生。作家把这一切归咎于不可捉摸的命运。
尤金·奥尼尔曾谈到:“《天边外》有三幕,每一幕有二场,一场室外,只见到地平线,暗示着人的欲望和梦想,另一场在室内,地平线不见了,暗示着人和他的梦想之间横着现实。用这一方法我试图造成一种节奏,一种渴求和失望的交替。”[3]
尤金·奥尼尔在创作《天边外》时,就设想做一个“有趣的技术实验”:三幕剧的每一幕分二场,一场内景,一场外景。目的在于“为了追求更大灵活性而作的形式方面的变革”,《天边外》现在的写法,我以为在艺术上收到了良好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室内布景设在同一地点,作者通过室内细节的变化,揭示出一个家庭的由盛而衰的变化。也间接寓意罗伯特的梦想在现实的单调的农庄生活中的毁灭。
我们从第一幕到第三幕屋内外表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梅家的剧变。原来那种日子过得富裕、和睦、兴旺的气氛不见了,因为这个家庭失去了能干、操劳、能持家的主人,而换了一个只会幻想,整日生活在书堆里,却不会经营管理农场的人,农庄从兴旺走向败落,家庭的败落也是必然的。
随着时间的变迁,农庄的败落,这个家庭的成员也发生巨大变化,梅约夫妇,罗伯特和露斯的女儿玛丽都因故去世,安朱离开农场。而露斯人不到三十岁,却变得“老得可怕。皱纹很深的苍白色的脸有一种麻木不仁的表情,好像对她这个人,一切都不存在了,她的热情能量已枯竭了。而罗伯特患病已奄奄一息。”
剧作家通过剧本提示,向观众揭示了梅家的衰败,罗伯特从理想到现实,到死去。
其二,剧作家通过每一幕分二场,一场外景,一场内景,不仅起到对比作用,而且产生了强烈的象征隐喻艺术效果。
广阔敞亮的外景,乡间大路,小山可眺望山外,海洋使人开阔视野;而内景农场会客室是狭窄,局促,四壁封闭。内外景在每一幕交替出现,给观众以迥然不同的视觉印象。外景的山外暗示了人们的愿望和梦想;小屋则是对梦想的禁闭。剧作家通过这种艺术处理,取得了渴望和失望的节奏与变化。
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运用室内外的对比,也揭示了罗伯特和安朱的思想矛盾变化。罗伯特爱大海、爱幻想,他本可以到广阔天地,到天边外去寻求理想,但因爱上一个女人留在农场,那小屋就象关他一辈子的牢笼。而安朱是热爱土地、爱农庄的,却因露斯爱上弟弟罗伯特,离开了农场,安朱去天边外闯荡,大显身手。他虽有失败,但继续在人生道路上挣扎、闯荡,不甘心失败。
其三,外景一些景物描写象征了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天边外》第一幕第一场,描写春天田野上,“黑土地里长着秋麦,绿油一片”,象征着安朱与土地的和谐,庄稼与土地的关系。
再如堤上那棵苹果树扎根在土壤,把它那多枝曲折的枝杈向天空伸展,但到第三幕,苹果树光秃秃没有树叶,“似乎是死的。”罗伯特用尽平生的力气,支起病弱的躯体,指向大海。罗伯特和苹果树一样,失去生命力,在死亡线上挣扎。
第二幕第二场,在小山顶上。小山顶一侧是海,天边外,一侧是农场。罗伯特和安朱对所处的环境并不满意。安朱经过三年海上生活,他诅咒大海,而罗伯特通过三年在农场的拼搏、挣扎,他则诅咒农场。并让露斯坦露自己的爱与恨,揭示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人只能面对现实,不能逃避现实。
而最后一场,可以说又回到第一幕第一场的乡下大路上。当然,时间变了,不仅是时间相隔八年多,季节也由春季变成秋季,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幕第一场是晚间,而第三幕第二场是清晨。使人们从荒芜的土地联想到玛丽的夭折,罗伯特重病奄奄一息,安朱投机买卖失败,整个气氛悲惨、绝望。而黑夜被黎明代替,旭日渐渐升起,蛇形栅栏的坍塌也许可看作是一个转折点。把罗伯特的幻想与现实生活隔绝的那堵墙,彻底毁掉。罗伯特在临终时,对生活有所醒悟:人生、生活就是苦难,通过受难,他得到拯救。罗伯特在临死前,给人的感觉不是凄凄惨惨,他发出了:“自由了——从农庄里解放出来——自由地去漫游——永远漫游下去!”的呼喊。罗伯特虽然是悲剧人物,但他给人预示:摆脱人世间的琐杂、平凡,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去了,他的梦想并没有泯灭,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罢了。安朱也是失败者,但他仍要去挣扎,去奋斗。他要重新去做粮食买卖,盼望发财后,重振农庄。即使露斯失去了女儿、丈夫,她也要生活下去。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的,有挫折、失败和胜利,有欢乐有痛苦,但人还要生存下去,去寻找“天边外”的世界。我们从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1918~1920年的笔记中获悉,剧作家曾有计划写《天边外续集》,继续把《天边外》剧终的场面写下去,写阿朱(安朱)的戏。
总之,《天边外》这部剧作在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众多剧作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剧作家第一部大获成功的多幕剧,它也是剧作家创作转折时期的优秀剧作,一座里程碑式的剧作。
注释:
[1]《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2]《奥尼尔剧作选·奥尼尔及其代表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
[3]参考巴雷特·克拉克《尤金·奥尼尔》罗伯特·麦克布来德公司,192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