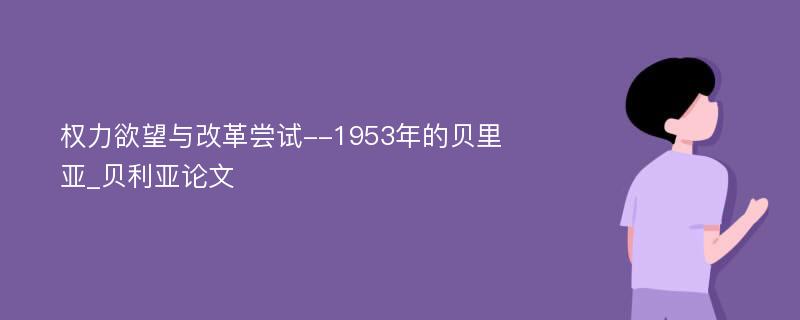
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欲望论文,贝利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1948年至1949年的“列宁格勒案”和1951年至1952年的“明格列尔案”,到1952年10月紧随苏共十九大宣布的最高领导层大变动和1953年1月的“医生阴谋案”,这一系列惊人的事件都突出地表明,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政治的病态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倾向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来缓解病态、避免灾难的潜在要求也随之滋长(注:斯大林去世前两三年,与多半以消极方式表现的民众不满情绪相应,苏联官方内部出现了比较积极、但甚为微弱的改革主张。它们在非常不利的国家政治环境中,采取了审慎地触动并试图曲折地修改斯大林模式的某些理论前提和基本政策的形态。其中之一,是隐约地针对斯大林据以推导并说明其治国模式绝对必要的“资本主义包围”论,提出欧亚众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已消除了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此外,同样被斯大林用来说明必须依靠国家集权体制高速发展军事—重工业的另一主要信条——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也遭到了怀疑甚至否定。一些蛛丝马迹显示,某些要人已在小心翼翼地提议改变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绝对优先地位,改变所有制形式的过于单一和经营管理权力的极端集中状态。不仅如此,有理由推测斯大林的基本对外政策——同美国及其北大西洋集团激烈对抗——也逐渐在高层内遭到怀疑,进而被认为是应当修改的。参见塔克《苏联政治心理——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之后的变化》Robert C.Tucker,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Stalinism andPost-Stalin Change,纽约1971年版,第94—96、 100页;列昂哈德著《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 , The
Kremlinsince Stalin,纽约1962年版,第37—39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斯大林去世提供了扭转恶化趋势的决定性机会,甚至历史必然性。有如著名的苏联学家罗伯特·C· 塔克所言,“斯大林主义政治秩序是一种个人体系。斯大林个人……是苏联政治的中心力量,整个苏联政治宇宙所环绕的太阳。因而,他的去世使莫斯科的内部政治形势一夜之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斯大林之死必然意味非斯大林化”。(注:塔克:《苏联政治心理》,第190页。 )在斯大林去世的短短几个月里,使苏联社会主义开始趋于逐渐解脱斯大林治国模式的种种事态,以堪称罕见的速度接连出现,其中包括:大致停止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予以不指名的批评;通过宣布局部大赦、公开平反“医生阴谋案”等举措应急性地缓解社会紧张;着手改革国家内部保安体制;推翻“明格列尔案”和在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替换俄罗斯裔最高领导人,以此着手修改苏联的民族政策;在苏联及其若干东欧盟国实行经济“新方针”,以改变国民经济发展的病态模式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尝试缓和同美国及其西方大国集团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停止反南斯拉夫运动并开始谋求苏南关系正常化。
苏联在紧随斯大林去世后发生的这些变化,既是苏联国家面对历史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性反应,又同最高领导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斯大林的极端专权及其晚年的病态政治心理,根本排除了某一名僚属单独继承绝对权力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他去世后,克里姆林宫内关于权力分配和派别力量对比的漫长斗争不可避免,而此类斗争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当时苏联政治的头号议程——改革斯大林治国模式的那些最直接、最严重的弊端来进行。改革所关乎的并非只是其内容问题,即在哪些方面和在多大程度上革除弊端,而且是其主持者问题,即由什么人或者什么派系主导改革,从而获得对于确立并巩固权力优势至关重要的政治主动和国内民望。关于改革内容的思想分歧和关于改革主持者问题的权力冲突相互交织,使得苏联政治在斯大林去世后大约两年里呈现出一波三折、扑朔迷离的复杂状况。这一时期的基本状况大致如下:对于一个已经占上风但优势并不牢靠的派别来说,最有助于它巩固权力优势的一个办法是带头改革斯大林模式,特别是抑制保安部门、废止滥捕滥杀、平反冤假错案和批评个人崇拜等。“在此,由于派系利益要求有一种快得令人不安的政策速度,就可能同整个政权潜在的保守倾向相冲突。然而,如果说将自己同非斯大林化政策联为一体符合暂占优势者的派别利益,那么根据这一事实本身,在当时反对这政策就符合对立一派的利益,直到其对手被搞下台为止,其间或许还同政权内部的极端保守分子结成联盟。”(注:塔克:《苏联政治心理》,第199页。)这里所说的暂占优势者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极端保守分子主要是莫洛托夫,而“对立一派”的领头者是赫鲁晓夫。
在30年代大清洗后苏联最高领导层复杂的纵横捭阖当中,贝利亚作为保安部门负责人,同起初掌管苏共中央人事组织部门的马林科夫逐渐结成了特殊关系。他们怂恿斯大林制造“列宁格勒案”,由此铲除沃兹涅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等影响日甚的最高层同僚,从而拥有了斯大林之下虽非牢靠、但仍属首屈一指的权势。在这两人中,贝利亚起着更关键的作用。在“列宁格勒案”以后的三年多里,马林科夫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和贝利亚的合作(注: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周围的人》(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而且,由于缺乏政治大才干和个性优柔寡断,他易于受贝利亚操纵。这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对苏联政治和政策的影响尤为重大。贝利亚的妻子后来回顾说,贝利亚“始终懂得一个格鲁吉亚人要在斯大林死后当领袖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亲近某个他能够利用的人——某个像马林科夫那样的人。”(注: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182页。)斯大林去世当夜, 核心圈子(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开会议决人事安排,贝利亚立即提议马林科夫出任当时权力最大的职务——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则随即提议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且主张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单一的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注:奈特:《贝利亚》,第181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467页。)。已有的优势加之政治上的主动,使得这些提议未经争议便得以通过,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尤其是后者)成了斯大林之后苏联第一轮掌舵者。
无论是出于如前所述的那些政治原因,还是出于个人情感,贝利亚都强烈地倾向于否定斯大林及其一系列政策。滥施镇压导致保安部门坐大,斯大林对贝利亚便难免由宠信变为猜疑甚而恐惧。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斯大林借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都掌握在贝利亚手里。斯大林明白,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斯大林所指定的随便哪一个人,那末贝利亚也能够根据他自己的选择或主动去消灭某一个人。斯大林害怕自己会成为贝利亚可能选择的第一个人。”(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88页。)事实上,斯大林搞“明格列尔案”的初衷, 就在于借此打击甚或除掉贝利亚,制造“医生阴谋案”一定程度上亦有此意(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49—450页;奈特:《贝利亚》,第171页。)。贝利亚对这些很清楚。斯大林弥留和去世之际他那几乎不加掩饰的得意和怨恨(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57—461、464—465页;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Svetlana Alliluyeva , Twenty Lettersto A Friend,第7—8页。),表明了他的内心。不过,对他来说, 变革主要不是为了泄愤和报复,而是出于政治利益,包括改变自己在苏联公众中的形象(注:贝利亚“深知国内多数居民对他的态度。对人民来说,他是斯大林的丑陋弄臣、刽子手。”参见鲍里斯·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继承人的斗争》,中译件由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研究员提供,在此谨表谢意。以下所引俄罗斯档案及其中译件均同于此,不再一一注明。)和加强自己的权力优势,同时为整个苏联政权的安全而缓解社会紧张和外部危险。贝利亚的大多数主席团同事都想摆脱斯大林那种极端高压和任意妄为的统治,实行某种开明化,但贝利亚将此推进得比他的同事们希望的更远(注:奈特:《贝利亚》,第184页。)。
二
斯大林去世后头几个月内苏联的政策变动和改革措施,大半源于贝利亚在马林科夫支持下采取的主动。他曾向米高扬谈了自己的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当把他们放掉,也不能随便把人送到劳改营去。内务部应当缩减,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保卫机关,而是对我们进行监视的机关。”(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3月9日,在斯大林葬礼上讲话时,他和马林科夫非同寻常地提到要保证每个苏联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人身权利(注:他们还强调苏联国家的多民族性质,示意发展消费品生产和缓解东西方紧张局势,并且很显著地降低了颂扬斯大林的调门。参见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50—53页;奈特:《贝利亚》,第182页;科恩:《重新思考苏联经验》,Stephen F.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纽约和牛津1985年版,第 103页。)。3月26日,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有关报告, 导致了第二天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局部大赦令,对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类囚犯予以释放或减刑,包括立即释放所有刑期5年以下者, 所有因为“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和军人犯罪”而被判处徒刑者,所有有10岁以下子女或怀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绝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余囚犯则刑期减半(被判“反革命罪”、严重贪污罪、抢劫罪和杀人罪者除外)。该命令还根据贝利亚的建议,宣布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宽容和从轻发落的原则进行修改(注:贝利亚关于必须实行大赦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26日, 载于俄罗斯《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 Documents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3,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发行,伦敦1956年版,第13—14页。)。由于这项举措,在全苏总共2 526 402 名犯人中,约100万人获得自由, 其中大多数无疑是无辜入狱和轻罪重判者,尽管仍有大量无辜者(包括斯大林时期无数政治冤案的所有尚存的直接受害者)依然身陷囹圄。在贯彻过程中,不少危险的重罪刑事犯也被一并释放,后来一些高度赞扬赫鲁晓夫的苏联著述则断定是贝利亚的阴谋,旨在借口应付由此而来的治安问题,将斯大林去世后他立即下令开进莫斯科等城市的内务部部队留驻下来,或者利用社会不稳提供的机会重施高压政治(注:R.麦德维杰夫和Z.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掌权岁月》Roy Medvedev and Zhores Medvedev , Khrushchev : TheYears in Power,纽约1975年版,第9页; 阿朱别依:《赫鲁晓夫执政十年》(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4—75页。)。第一种解释或许可信,但把它当做贝利亚搞局部大赦的首要甚或惟一动机,未免偏狭。
紧接着,贝利亚麾下的内务部于4月5日宣布,所谓以恐怖主义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的“医生阴谋案”纯属捏造,所有因此案被捕的人员予以平反,负责捏造的两名高级官员——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切夫和副部长留明已被逮捕(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5页。)。这一大冤案的平反系贝利亚所为,而且是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争取到公开发布平反公报。事实上,早在3月中旬他就下令复查此案, 并在当月释放了案犯(注: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复查一些特别重要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 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医生阴谋案”被推翻是30年代以后斯大林政治恐怖渐被否定的开端。苏联政府由此第一次公开承认和谴责了国家保安部门最高层存在着肆意践踏法制的严重状况,并且开始把消除这种状况的问题提上国家政治议程。《真理报》当时就“医生阴谋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政府公布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也史无前例地加上了这一内容(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17—18页;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5—66页。)。与“医生阴谋案”的平反大致同时,“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亦经贝利亚下令进行的复查而被推翻(注:贝利亚关于成立侦查小组复查一些特别重要案件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贝利亚关于复查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有罪判决案的命令,1953年3月18日。)。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注:奈特:《贝利亚》,第184页。),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规模极其庞大、权力几近无限的内务部将其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月间,就有近30 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北建设总局、古比雪夫水电站建设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注:贝利亚关于将苏联内务部所属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移交其他部给马林科夫的请示报告,1953年3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 年3月18日;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注:贝利亚关于将劳动改造营转交司法部管理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3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决定草案,1953年3月2 8日;奈特:《贝利亚》,第184页。)。有档案文件表明, 在其遭遇政治覆灭前10天,贝利亚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大清洗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贝利亚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特别会议权力向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1953年6月15日。)。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贝利亚还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注:贝利亚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的命令,1953年4月4日。该命令还陈述了保安部门以非法手段大搞逼供的情况:“国家安全部机构在侦查工作中有严重曲解苏联法律,滥捕无辜苏联公民,纵容假侦查材料,广泛采用各种拷问手段——残酷殴打被捕人员,昼夜不停地背拷双手,某些情况下竟持续数月,长期不许被捕人员睡眠,将被捕人员赤身关在寒冷的单人牢房等现象……这种极其残酷的‘审问方法’导致许多无辜被捕人员被侦查搞得体力不支,精神郁闷,其中某些人已丧失人的面目。制造伪证的侦查人员乘被捕人员处于这种状态,偷偷将事先炮制的关于反苏和间谍—恐怖活动的‘供词’塞给他们。”)。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30年代至40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
不论其个人报复心和政治野心如何,贝利亚还带头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并且进而倡议禁止现领导成员效法个人崇拜,包括在节日游行中展示或在企业、机关及团体建筑物悬挂他们的肖像(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奈特:《贝利亚》。)。他甚至搜集了揭露斯大林与捏造“医生阴谋案”相牵连的文件,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克里姆林宫的专门房间里阅读(注:奈特:《贝利亚》,第 185—186页。)。多半与他的促进相关,3月27日《真理报》以非常显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体领导是党的主要原则之一,要求苏共全体干部具有与此相应的“现代意识”。近20天后,该报再次载文强调党和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皆须领导成员集体解决,“个人作出的结论总是、或差不多总是偏狭的”。与此相应,斯大林葬礼过后其名字在苏联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少,以至于前几年里每天每页40次至60次提到斯大林的《真理报》,自1953年4月起难得再提其姓名。 此类变化很大程度上出自贝利亚的指示(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3—66页。)。到当年初夏,苏联头号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已开始启用“个人崇拜”这个政治术语来不指名地批评斯大林(注: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Roy Medvedev,Khrushchev,纽约州加登城1984年版,第64页。)。
在民族政策的修改方面,贝利亚是苏共中央推翻斯大林多半针对他搞起的格鲁吉亚“明格列尔案”的鼓动者,也是在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由当地民族出身的高层官员替换俄裔领导人的主持者。促使他这么做的不仅是对斯大林的泄愤心理,而且还有这么一种明确的认识,即在苏联非常广泛、非常严重的民族歧视或民族强制问题中包含着巨大危险。例如,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移植斯大林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居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医生阴谋案”宣布平反后仅5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 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把手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裔最高层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以便让当地民族对本加盟共和国的事务有较大影响(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67—68页;奈特:《贝利亚》,第188—190页。在替换俄裔领导干部方面,贝利亚先从他自己属下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机关做起。参见贝利亚关于白俄罗斯内务部机关民族干部成分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1953年6月8日。)。贝利亚还着手纠正斯大林在世时给某些非俄罗斯民族或其部分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强迫性集体迁徙,从供本文写作之用的档案材料来看,他深切地感觉到这种迁徙所包含的极端不公正及其引起的强烈不满(注:贝利亚关于成立复查强行将苏联公民从格鲁吉亚迁移案件委员会的命令,1953年3月13日; 贝利亚关于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4月11日第1007—430CC号决议,复查苏联前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从格鲁吉亚领土上强行迁移的公民案件程序的命令,1953年4月14 日;贝利亚关于苏联的德意志族人的状况的匿名信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附函,1953年5月27日。)。或许可以说, 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其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倒是正确的”(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
三
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内苏联外交方面的重要变化亦同贝利亚密切相关。60年代就有著作推测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特别倾向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近年解密的档案资料更加肯定对外政策变更的动力首先来自贝利亚。按照苏联30年代起就有的一种做法——由内务部系统而非外交部来进行某些重大外交行动,贝利亚谋求通过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谈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后来在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一份给南共联盟第三号领导人、南保安和情报部门首脑兰科维奇的一份便函,内容为贝利亚委托持函者告诉兰科维奇并转告铁托:贝利亚及其朋友们认为必须根本改善苏南关系;如果兰科维奇和铁托同意这一观点,便可为此指定全权代表,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秘密会晤。他期望的苏南接近远远超过他的大多数主席团同僚(特别是负责外交的莫洛托夫)当时的愿望,后者“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如同和其他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有勾结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关系”(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奈特:《贝利亚》,第186页。 关于莫洛托夫在重建苏南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参见时殷弘《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从斯大林去世到苏共二十大》,《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130—131 页。)。尽管如此,苏联的反南运动随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当南斯拉夫驻苏代办按照外交惯例,同一批外国外交官一起就斯大林去世向苏联副外长马立克表示悼念时,后者一反常态,主动同他握了手。“这的的确确是件大事”(注: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页。)。随后,在苏联官方颁发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宣传口号中,几年来惯常的反南口号不见了,苏联报纸也不再登载反南文章,尾随苏联反对本国政府的南斯拉夫在苏流亡者刊物则销声匿迹。5、6月间,苏联政府主动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换大使,恢复苏南决裂后即在事实上降格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年)》,第280页; 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 第 101 页;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1352页。)。总的来说, 这些促进苏南关系趋向基本正常的动作同贝利亚的意向密切相关,尽管其力度不及他希望的那样。
在个人权力欲和有关苏联国际处境的大局考虑的双重因素驱动下,贝利亚作了一项最具政治冒险性的政策变更尝试,那就是在东德推行“新方针”,甚至可能试探在德国中立化的条件下两德合并,亦即如同他后来被指控的那样“牺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非常清楚,对于随移植斯大林模式而来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现状,东德民众严重不满。根据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的通报,1951年1月至1953年4月,从东德逃到西德的人数共计45万,其中执政党及其外围青年组织的成员数以千计(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6月2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经数天会议产生了一个文件——《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措施》,主要精神为建议东德领导放弃“建设社会主义的强迫性政策”,它体现在停止实行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和消灭私有资本的政策、确保公民个人权利和改善法制、通过复查以纠正冤假错案等具体措施上。这个文件就是由贝利亚起草和签署的(注:奈特:《贝利亚》,第191 页。)。他起先提议的要旨是东德停止建设社会主义,用他当时的话说,苏联“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至于那里是不是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并无区别。”他还对主席团同僚们声称:如果德国统一起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对于苏联也足够了;统一的德国可以同美国在西欧的影响相抗衡。对此,莫洛托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强调放弃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想法将使其他东欧国家迷失方向,导致它们对美国屈膝投降(注: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参见《葛罗米柯回忆录》Andrei Gromyko,Memoirs,伦敦1989年版,第316页。)。按照多半出自东德高级官员的传说,贝利亚当时暗中筹划更换东德领导人,图谋通过与东德保安部门关系密切的统一社会党内“改革派”来扳倒倾向于守旧的一号人物乌布利希(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0—71页;奈特:《贝利亚》,第192页。)。 统一社会党中央于6月9日决定变更一系列政策,并以党中央和政府分别发表公报的方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注:《国际事务文件(1953 年)》,第154—159页。)。但是,这些措施同苏联建议的精神相比仍打了折扣,特别是未对怨艾甚深的工人作出经济上的抚慰,结果引发了当月的大骚乱。骚乱爆发后,苏联驻德代表据说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曾要求东德政府采取怀柔对策,未同意东德领导提出的立即出动驻德苏军加以镇压的请求(注:列昂哈德:《斯大林死后的克里姆林宫》,第71页。)。鉴于从1950年起,苏联一直保留有用德国统一和中立化来交换西德不重新武装的余地,加上东德先天不足使其长久的独立存在深刻的困难(注:乌拉姆:《扩张和共处——1917至1973年的苏联对外政策》Adam Ulam,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Soviet Foreign Policy,1917—1973,第2版,纽约1974年,第507—509页; 科弗里格:《墙与桥——美国与东欧》Bennett Kovrig,Of Walls and Bridges: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ern Europe,纽约和伦敦1991年版,第54—55页。),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在1953年7 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指责刚被逮捕的贝利亚试图创立一个统一、中立和“资产阶级的”德国似非信口雌黄,何况苏联当时确需寻求突破口,以便能通过同西方的谈判来实质性地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在欧洲的处境。无论如何,骚乱爆发后贝利亚关于东德问题的言行成了众矢之的,甚至马林科夫也不免将他视为祸端。在苏联最高领导成员中间,这位为人狠毒、权势炽盛的保安部门首领早就引起了强烈的忌恨和恐惧,他主持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尤其在一些加盟共和国更换不同民族成分的领导人方面)又导致了包括马林科夫在内的上层领导人的严重不满和猜疑(注: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476—477页;参见斯塔尔科夫《“卢比扬卡元帅”的一百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德问题使他彻底孤立起来,成为他迅速覆灭的一个关键因素。
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对贝利亚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美国学者阿米·奈特如此总结贝利亚的改革尝试:
虽然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贝利亚在斯大林死后采取了一种较为开明的路线,但只是近来,由于前面援引的那些文件公诸于世,他大胆主动的程度才完全大白于天下。他在提倡广泛的改革,如果它们取得成功,本来不仅会改变苏联制度的性质,还将为苏联集团的部分解体开辟道路。当然,贝利亚并不像他的同事们后来声称的那样想复辟资本主义。他也不想引进真正的民主。但他确实认识到急需背离严厉刻板的斯大林主义,急需依凭实际,从意识形态信条实行后撤,采用对公众有吸引力的政策。在这方面,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更讲求实际,更具前瞻眼光。赫鲁晓夫本人后来也采用了贝利亚的某些纲领,包括非斯大林化,这表明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理解苏联制度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实行某种改革。但是,贝利亚在推动改革方面似乎太性急了。而且,他未预料到突然的开明化会在东德造成的破坏稳定效应。东德危机给赫鲁晓夫提供了纠集力量来反对贝利亚的口实。(注:奈特:《贝利亚》,第193—194页。)只要充分考虑到贝利亚尝试改革的个人权势利益动机,并且对上述话语中的某些意识形态概念及价值取向作出批判性理解,便可以认为这番总结大抵是不错的。
标签:贝利亚论文; 斯大林论文; 内务部论文; 政治论文; 德国元帅论文; 苏联元帅论文; 赫鲁晓夫回忆录论文; 马林科夫论文; 主席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