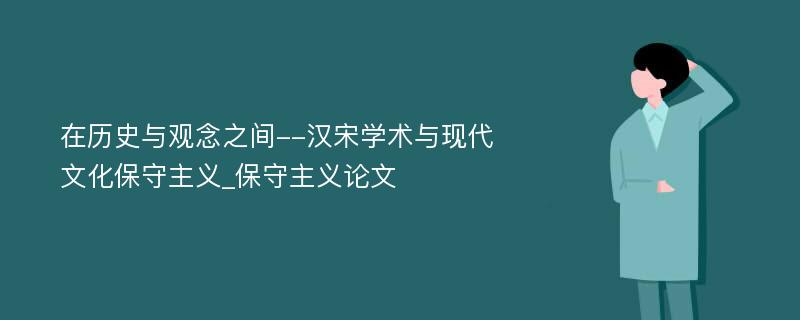
在历史与理念之间——汉宋学术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理念论文,学术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因外力作用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传统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前者属于传统——现代的矛盾,后者纠缠着本土——外来的问题。用中国学界熟悉的术语讲,一为古今之争,一为东西之争。从中国经验观察,两者是容易混同或可能转化的,但从起源与性质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传统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民族主义则既可以发生在前现代化的历史上,也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或区域之间。以经验为依据,从逻辑上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发展方向及社会功能,有非常内在的意义。
一、酒与瓶的说法
应付现代性冲击的不适感,任何民族文化自身都没有固有的经验可借鉴,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付异族文化的挑战,或者从文化上动员抗击异族入侵或统治的精神力量,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拥有丰富、且不乏成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当近现代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它很自然就被化简为某种反应模式,从而使这种保守主义带上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国文化消化外来文化最辉煌的成就,莫过于宋明新儒学对佛学的扬弃。这一点,常得到现代属保守主义文化阵营的大师,无论是哲学家(冯友兰)还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称道。佛教来自印度,是外来货。但继魏晋玄学之后,隋唐佛学鼎盛,不但在思想界有压倒儒学之势,甚至波及社会经济生活。儒释的差别或矛盾主要表现为:理论形态上,佛学有一个自觉精致而迷人的义理系统,而儒学以六经为主干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体系,理论较为粗疏。社会功能上,佛教以生活为苦,设立出家制度,要求解脱出世,这同提倡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造成冲突。站在儒学的立场上,这是不可接受而同时又是不易应付的。
接受这种挑战,举起卫道的旗帜,而又奠定了对佛学消解策略的人物是韩愈。他不是盲目排外,而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积极吸取佛学中于已有用的东西。例如,仿禅宗传灯系统建立儒家道统;受佛性论启发,通过表彰《孟子》、《大学》彰显儒家心性论等等。这也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韩愈的精神基本上为宋明儒学所继承、发扬。①陈寅恪曾议论说:
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而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又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受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者也。②
新儒学是成功的,其编织的体系基本成为宋元明清四朝意识形态的信条,雄踞庙堂达几个世纪。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胜利,它对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起很大的鼓舞作用。陈氏后来又引伸说:今日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的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③
阿寅恪承冯友兰的说法,把新儒家的经验,概括为“以新瓶而装旧酒”。然而,从保守主义的立论看,中国历史还提供另一类型的应付外来势力冲击的文化经验,它表现为清代汉学的兴起。无论梁启超还是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提及满清代明对明清之际华夏知识分子的刺激及促成学风转变的影响。从汉文化的观点看,满族是夷,清朝兴起是以夷变夏的惊变。其中,那些有使命感的汉族士人都在总结明朝覆灭的教训及寻求民族复兴的历史途径。他们也从文化上着手,顾炎武关于“保国”与“保天下”关系的议论最能说明问题: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食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④
亡国是政权易姓,亡天下是纲常失范。把“保天下”故在第一位,实质上是取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立场。顾氏谈的是魏晋,心目中的问题是明清。不仅玄学清谈,宋学也有清谈,尤其是心学一系。“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⑤他要求拨乱反正,转变学风,由虚学(心性之学)走向实学(经世之学)。其入手处,便是切实研读经史,由读经而晓夷夏之辨的大义,经治史则知历代兴亡之消息。此外,连带涉及边疆地理及漕运、钱粮、盐政之类经济问题的探究。沿顾氏及其同道之路,清学(无论做考据还是谈经世)复兴了汉学,为弘扬华夏民族文化作出其特有的贡献。尽管满洲贵族牢牢控制着政权,且清初通过文字狱对辨种性的异己行为进行镇压,但文化上最终被迫向汉族认同,把程朱理学接为正宗,暴力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征服。
宋学与(清代)汉学有其共同的目标,即寻护华夏文化复兴之道。但“道”在哪里,如何显现,双方理解的倾向却有歧异。宋学着重往圣之学,汉学关心先王治绩。宋学的道统不是靠师弟相传或典策传播来延续,而是“心传”,其所得之道便是通过“体贴”而来的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汉学以经典为中介,通过原典的考释解读去把握先王制礼作乐之精神及历代兴亡之故事,它关心的不是几个抽象的观念,而是“道”具体展开的历史。“六经皆史”可以看作汉学的纲领。
其实,这“道”的设定的区别,是与各自面对的历史情势不同,因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也不同相联系的。宋学把文化价值抽象化,让一套形而上的理念同佛学精致的义理相通约,从而化解佛学的优势,同时又把传统的制度风俗纳入新框架来说明,对固有的生活秩序作合理性辨护。用酒与瓶的说法,不变的制度风俗、生活秩序是老酒,新编织的义理系统则是新瓶,宋学所作的功夫就是为传统制作新瓶。汉学把传统精神具体化,它面对的不是异族精神文化的挑战,而是暴力的压迫,目的只是调动自家的精神资源,并促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从而维护自己的文化种姓。汉学对传统的着眼点是发掘而不是改造,它只沽老酒,不制新瓶。用哲学的术语表达,酒与瓶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内容的分离是哲学思考的产物,传统史学则不如是,它要让过程展示意义而不是将其抽象剥离,否则就是历史哲学,如公羊三世说之类。故从一个文化系统着眼,史学也不承担建立抽象理论、或曰制瓶的任务。
就完成各自的文化理想而言。宋学、汉学都是成功的。但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文化危机,面临的情形则复杂得多,不但有前两种形势的混合,又增添更严峻的条件。因此,固有的文化经验固然可以作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资源,但作为反应模式来借鉴,则会因面临新的难题而不得不加以变形。同时,在保守阵营内部,酿酒还是制瓶的策略选择,也是一个聚讼纷纭且令圈外人士感兴味的问题。
二、辨种姓与悼礼俗
二十世纪初,直接承清代学术传统而激发文化保守主义热情的重镇是章太炎。太炎在社会政治方面与康有为针锋相对,看来颇激进。然其表现激进的具体内容是排满。这排满其实正是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章氏自号太炎,又名绛,都有追慕顾炎武的意义。他说:
原此考证六经之学,始自明末儒先,深隐蒿莱,不求闻达,其所治乃与康熙诸臣绝异。若顾宁人者,甄明古韵,行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先德。吾辈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⑥
辛亥前夕,章太炎有两句著名的口号,叫“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姓”。这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人物事迹。这种国粹主义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但他不只是明末遗民意识的重复,而明确宣布有针对自甘暴弃的“欧化主义”的一面。⑦
太炎去世后,晚辈的史家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以作纪念,强调“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把其论史大义,归结为民族主义之史学,平民主义之史学及文化主义之史学三点。“然则太炎论史,三途同趣,曰归于民族文化是已。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⑧钱穆饮慕章氏,而他本人流传甚广的《国史大纲》,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史学的实践。该书引论评述近世史学之衰弱说:
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入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的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之未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无一能发展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于史学之不振矣。⑨
钱氏发愿填补这一空白。把修史同民族的存亡绝续联系起来,不仅是对史学史的一种认识,更是对自己直接置身于其中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国史大纲》撰写的年代,正是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与章太炎、钱穆通过治史渲染民族主义相比,王国维、陈寅恪则是突出传统主义一面的史家。王国维带着辫子自沉的形象及那“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只能看作一个传统主义者同现代世界的决绝行为及最后心声。王国维也曾研西学而有得,然终不抵其对传统的眷恋。他检讨西学的影响说:“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乃,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出于此。”王并强调“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⑩
王国维的治学道路是从哲学、经文学而走向史学。以治史为归宿,你可以说是其性格使然,更应说是与其世界观合辙。《殷周制度论》是其很有影响的史学文章,其结语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文化心态: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计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
对王国维之死,众说纷纭,但“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11)这是护同道也是述己志。他自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12)其中体西用思想,几乎终生不变。陈氏论史也对新旧嬗变极敏感,他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志,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13)
无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其所留恋的传统都非狭隘的由一家一姓治天下的君主制度,而是道德标准或社会风习,用社会学的术语,即与法理社会相对的礼俗世界的价值体系与生活秩序。(14)虽然陈寅恪提出“新瓶旧酒”的文化策略,其心目中的标本是宋学,但陈氏本人是史家,不但不必建构理论,也罕作宏观问题的历史预设,他是不制瓶而只沽酒的人物。
一般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领域容易与史学结缘,但治史未必就是保守主义的表现。关键在于立场。钱穆之所以在《国史大纲》中要求读者先“对本国已往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的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正是针对另一群持激进主义文化立场的史家而言的。首先是针对发起古史辩的疑古派。(15)与钱穆的温情、敬意相类似,陈寅恪在更早时候讲求对历史的欣赏与同情: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种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6)
史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必争的学术据点,但是,借治史来辨种姓,即表达民族意识,也许是古今皆然的方便法门,而靠治史来护礼俗,即实现传统主义的理想,则无论中外都可能成问题。换言之,即使如陈寅恪,用史家的眼光来总结宋儒的经验,他也不应不知道:如果隋唐真是圣道中落,是文化危机的话,那么它仍是传统社会内的危机,是纯粹的民族文化问题,而不是“现代性”冲击造成的危机。因以,其反应模式在其时即使成功,运用于二十世纪也很难奏效。事实上,陈氏在悼念王国维时,对传统在现代面临的文化危机,已有更透彻的说法,值得详引: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君无父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尤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疾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动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7)
这才是新危机的症结所在,理念的丧失只是表象,礼俗的瓦解才是其底蕴。按《共产党宣言》的表达是,现代化“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8)观念的维持或许可通过信心与学术来尝试,秩序的瓦解则无法用学问来修补。除非你学梁漱溟,带着一种唐·吉诃德精神,身体力行,搞乡村建设试验,作象征性的努力。尽管失败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史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不论你把正在消逝的礼俗描绘得如何动人,其意义客观上不是对它的挽留,而是一种深切的悼念。
三、理念的防线
文化保守主义还有另一条战线,力量来自一批热衷于制“瓶”的哲学家,其思想也来自有本,即宋学。与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样,这里也要从康有为说起。康氏的思想,最能体现转型期新旧纠缠、激进与保守杂揉的特色。在其“托古改制”、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中,破古文是激进,立今文(连带张扬宋学)则为保守。维新的措施实质是消解民族文化危机的方案,目标即所谓保国、保种、保教,手段则是援西入中,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这毋宁说是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只有当他要利用(被重新解释过的)传统为自己辩护,且在维新失败后仍突出保教的意义时,他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其保守思想混合有历史(今文)与理念(宋学)双重成份。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对他的攻击,重点正是抓住其历史形式(托古立教)的荒谬性。康氏的思想经验表明,传统只能提取抽象的义理而无法移用具体的原则,从历史提取政治方略不如从文化提取哲学精神更易立足。因此,宋学取代汉学成为另一批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取向。
新文化运动中,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出来向激进主义者“应答”的重要人士是梁漱溟。他的法宝是向传统吸取精神而非承袭经验。梁氏指责康有为“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而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19)不但康不行,一般旧派人物也不行。“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尤其是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独秀——引者)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而陈先生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20)
梁氏所谓“旧化的根本精神”,体现在他的一套文化哲学中。他用“意欲—生活—文化”的公式解释西方、中国及印度不同的精神生活,建立文化类型学说。认为意欲是生活的本质,而由于意欲的不可能满足,导致不同的生活态度,而不同态度的生活实践,便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西、中、印便分别代表着意欲向前、意欲持中及意欲向后三种文化路向。三者分别对解决人对自然、人对人及人对自身三种关系各有贡献。而从三种问题关联的逻辑发展看,大战后的世界,亟需解决的正是人与人的关系,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适逢其时。尽管它有自己的问题,必须向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学习,但到底应该批评地把原来的态度拿出来。经过一番抽象制作之后,激进主义者着力攻击,而一般保守主义者无力辩护的负面传统,便不是他的负担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21)因为其知行合一,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把中国文化之根分为“无形”与“有形”两种。无形之根是伦理精神,有形之根是乡村社会,两者是相适应的。当商业资本主义势力瓦解了乡村结构之后,梁漱溟要以他提取的传统精神来整合乡土社会,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传统文化危机。这是形上形下一体关切的文化战略,但传统在现代面临的危机,最开始且最根本的,恰好正是形下的那部份。梁氏的“知”到世纪末仍有反响,其“行”的痕迹则全淹没在历史的荒野之中。
梁漱溟在论及孔子精神时,曾以“仁”、“孔颜之乐”,“伦理精神”等作标榜,实际已触及宋明理学心性论的课题了,但他没有深入开掘,梁氏讲文化哲学,阵势仍然太大,难以逃避攻击。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熊十力则缩小阵脚,他讲的儒家精神,立足于形而上的层次上,主题是心性论。与宋明儒家相似之处,他也出入儒释,由释返儒。但他的目标不仅是重新消解佛学,而且是要抗击风头日劲的来自西学的功利主义思潮,即反物化。其代表作叫《新唯识论》,思路是用唯识论反唯物论,又用空宗反有宗,再用儒学反佛学。随说随扫,层层超越,最后去证会本心,明心见性,并衍化出体用不二、大用流行的命题。熊氏的主题从梁氏的社会文化凝缩到人生上来,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
理念上,熊十力比梁漱溟更有魅力。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基本上是接在熊十力一线上。在中国文化由经济到政治等经验层次级级崩坏且危及到道德领域的情势下,正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现代新儒家找到堪与西方文化抗争的最后防线,并试图以此为起点卷土重来。他们的形上学宣言是:
西方一般之形上学,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观宇宙之究极的实在,与一般的构造组织为目标的。而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这不是先固定的安置一心理行为或灵魂实体作对象,在外加以研究思索,亦是为了说明知识如何可能,而有此心性之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为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22)
从心性哲学的角度看,经济、政治都不是体、不是本,而是用或末。体不变,用则是可以更新的。由于新儒家从事的是哲学,与一般史学领域的保守主义者相比,能更灵活主动地构造理论体系,即能承担为传统之酒制新瓶的使命。他们应付现代性的挑战不是笼统宣扬传统的魅力或诅咒现代性的邪恶,而是把传统凝缩、提纯为一套抽象的价值理念构架,然后最大限度地吸收来自西学中的现代性因素,通过发展传统来保守传统。
陈寅恪是在评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提出“新瓶而装旧酒”的。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建立“新理学”的体系时,便声称是对旧理学“接着讲”,这是对陈氏号召的响应。由于历史情势的不同,新旧理学差别仍极大。宋儒是以固有的社会制度不变为根基,然后才改造抽象玄妙的佛学心性之理。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则不是始于学,而是始于力,是让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至政治秩序变形的巨大压力。“新理学”要保的不是整个具体的秩序,而首先是抽象的义理,它要把这种冲击的影响规范在其义理许可的范围之内。甚至要证明世俗生活的某种转变,也是义理发展的要求。因此,“新理学”还要讲“新事论”,要“别共殊,明层次”,主张通过产业革命,把生产家庭化转变为生产社会化。
港台新儒家多排斥冯友兰,然象牟宗三等人,与乃师熊十力不同之处,也在于企图从心性论的基础上延伸出社会政治哲学(及认识论),用传统的术语叫“内圣外王”、由内圣驾御外王。从回应现代性挑战来说,又叫“返本开新”。他们注解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如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出自传统文化内在自觉的要求,民主科学是其法,就不会引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当代科学民主不能相容的对立误解,也可以抛开西化移植的情感难堪。”(23)
现代新儒家与宋明新儒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站在义理的层次上,论证道德的本体论依据,并力主通过教化、修养来正人心、淳风俗、协和社会秩序,振兴民族精神。两者区别在于,现代新儒家放弃了儒学的传统意识形态功能,引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对科学理性主义作认真的反思,并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论证或表述自己的哲学信念。就此而言,现代新儒家同具有保守意识的史学家比,是显得较为激进的。余英时甚至断言:象熊十力的“反传统意识的激烈有时不在‘五四’主流派之下。”(24)如果要追问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主要内涵属什么,我们可以说,其民族主义一面强于传统主义的一面。不过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也与史家的辨种姓不同,他们是要传道统。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牟宗三、唐君毅对中外文化所作的“判教”功夫上。
总括而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方向,它们同汉、宋两种学术思想传统有渊源关系。在学术形态上,一表现为史学,一表现为哲学。史学以古为镜,考究、描述历代兴亡变迁之迹,显示民族文化精神凝聚、发展的实际历程,其方法是把信念还原于史实。哲学以明理为梏的,从历史过程中分离出价值观念系统,方法是从实际抽绎出理念。这具体与抽象之别,导致其思想功能也一样。史学的具体,使人们对往迹有体察入微的感受,对民族特性的揭示更细致,更易深入人心。而从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而言,传统经验中可借鉴的意义则不强,同时也无力提出整合新旧经验的理论方略,因而应变能力较弱。哲学的抽象,对以往的历史文化作理念上的概括,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易于把握,同时抛弃对许多具体陈迹的纠缠,历史的包袱不重,应变的能力自然就增强。然理念这东西,越空灵就越抽象,结果它所标示的传统内涵必定越稀薄,保守得到的价值就可能太少。
说现代新儒家是“新瓶旧酒”,可能还必须补充或限定。与保守派史家比,新儒家确系制新瓶,然却不是只盛老酒,而是新旧酒相兑的了。这是把理念当形式,把生活当内容,即前者为瓶后者为酒来看的说法。然理念也可以有形式与内容的分解,即可继续移用瓶与酒的区分。在这一层次上,依激进主义的立场来看,它的确就是新瓶旧酒,新的是它的表述方式,旧的则是其精神内涵。这就造成现代新儒家于思想史舞台上处在既可左右逢源也会两面受敌的局势中。不过,由于现代文化激进主义占主流,它也自然而然地被固定划分在保守主义阵营之中。
文化上,以激进主义为参照系,从反面界定保守主义可能省事,但观察会流于表面,本文从探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入手,对其作“历史”与“理念”两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意在把问题引向深入。这不是旧事物的标签,而是可以观察新现象的概念工具。正如工具可以在实践中改进一样,理念也应当在应用(尤其在批评)中修正。也许,这种以理解为宗旨的探讨,对于中国文化的有心人,无论是想有效的保守还是有效的激进者,都是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第2期,1954年5月。
② 转引自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至11页。
③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⑥ 章太炎:《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8页。
⑦ 参见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6页。
⑧ 钱穆:《馀杭章氏学别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页。
⑨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7页。
⑩ 王国维:《论政事疏》,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11)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
(12)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13) 陈寅恪:《元向诗笺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78页。
(14) 对礼俗世界的认识,可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15) 关于古史辩运动的思想史意义,参阅拙作《走向后经学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2期,1993年2月。
(1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页。
(17)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至5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至254页。
(19)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
(20)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1至532页。
(21) 参阅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页。
(23) 王邦雄:《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及其展开》,《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6页。
(24)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中国文化》第6期,第17页。
标签:保守主义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陈寅恪论文; 国史大纲论文; 国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佛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