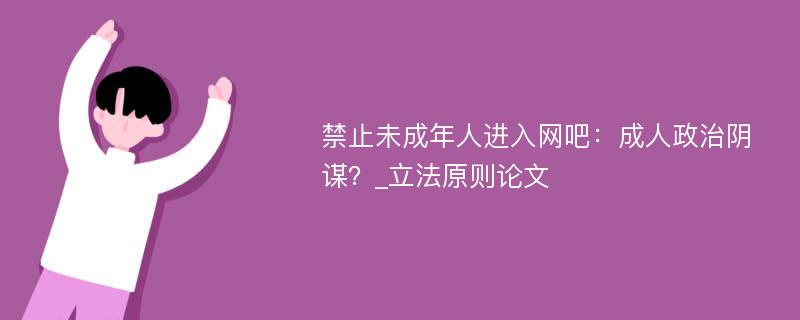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成人政治的一个密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成年人论文,成人论文,网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平等派成员菲·邦纳罗蒂曾经写过一部《为平等而密谋》,详尽描述了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及其理论。在法国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尽管平等派的这一系列“密谋”终究难逃失败的厄运,但其积极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今天,网络文明似已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文明上网、网络规范与网络法律问题的有关论述大有汗牛充栋之观,而铺天盖地的未成年人关涉网络引发的不良社会问题的报道则颇有成为媒体“永恒的主题”之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进行“限制”或“禁止”就成为在地位上占优势的成人政治社会对于网吧“痛定之后”“为未成年人着想”的必然规制手段。①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依法治国”与“立宪主义”已成为普遍共识的今天,这种规制在规制理由与规制手段两方面都存在违宪之虞,它背离了宪政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而于上述规制之外,则可映射出成人政治社会转嫁自身责任,并要求未成年人依前者设定方式成长的一种政治图谋。
一、有关管理规定及问题之所在
未成年人上网热是中国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曾几何时,计算机与网络是高新技术的代名词。然而,随着网络游戏、网络聊天以及网吧等服务的兴起,网吧也已从当初的“高新技术”龙椅上沦落为目前的与“歌舞游戏娱乐场所”平等列席的地位。②与此同时,跟网吧有关的负面报道也开始在媒体中流通开来,诸如“网络瘾”、“网络导致三好学生变成逃学威龙”、“模仿网络游戏的暴力行为”、“网络色情”、“学生通宵上网吧打游戏猝死”等等新闻充斥着我们的大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报道是出于媒体的刻意炒作,但是这些漫天飞舞的蛊惑之词的确不断加深着成人社会对于网吧的敌意。
基于这样一种地位状态的认识,对于未成年人的上网热,成人政治社会祭出强行管制的大旗,先后出台了多项涉及未成年人上网的法律规定。从此,各地有关的打击、禁止等管制行为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就规范的内容上看,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进行管制的全国性立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限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立法是2001年4月由信息产业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办法》)。该规章是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进行管制的开始,其主要的立法目的是“限年龄限时间”控制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因此,《办法》要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者“不得在本办法限定的时间外向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开放,不得允许无监护人陪伴的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其营业场所”(第10条第6项)。并且,“向未成年人开放的时间限于国家法定节假日每日8时至21时”(第13条)。
第二,“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标志性立法:(1)2002年9月由国务院公布实施的行政法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依《条例》的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不得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营业场所入口处的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第21条)。此外,考虑到网吧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非常不良的影响,《条例》还规定:“中学、小学校园周围200米范围内和居民住宅楼(院)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第9条)。(2)2006年12月修改通过的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基本肯定了上述规定的意义,并且首次将这些规定进一步规范化为法律: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肯定了网吧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非常不良的影响(第1条),因此“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是属于与“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一样的“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第36条);其次,由于“网吧”是“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因此,“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第36条);再次,为了彻底消除未成年人对上网之幻想及某些不良营业者违法之可能,该法律进一步规定了“中小学校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第36条);最后,与所有法律一样,该法律亦规定了若干违反时的法律责任。
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成人政治社会忧心如焚的未成年人上网问题,国家于此社会背景下出台“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禁令,这本无可非议。然而,诚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如果有谁对一个价值或义务判断作出主张,提出对正确性的要求,那么他就是在提出如下要求:其主张可以通过理性来证立。罗伯特·阿列克西在援引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时亦认同:“提出主张的人,不仅想表达其本人所相信的东西,而且还要超过此点宣称:其所讲的也是可以证立的,也就是说,主张的内容是真实的或正确的。这同样适用于规范性命题和非规范性命题。”③上述这些管制规定以及管制行为固然获得主流民意的支持,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因为一项法律或命令只有能够通过宪法的审查,才能获得宪法上的正当性。所谓的对法律的宪法审查通常是在国家权力干预到公民基本权利时由特定的宪法审查机关对法律进行的审查。
从立法技术上讲,要实现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制,从对象上看其手段可以有两种:规制网吧经营者或规制未成年人。由于直接规制未成年人必然要面对宪法上违宪的风险性,同时考虑到未成年人在法律上乃是属于无完全责任能力人以及实务操作上等原因,网吧监管制度直接规制的对象并非是不特定的未成年人而是网络服务经营者,直接限制的则是网吧经营者的经营自由(营业自由)。这种“经营自由”在德国法上乃是属于“职业自由”中的“职业执行自由”,在日本法中则是“执行职业的自由”,而在我国则可归结于宪法上劳动权的范畴。依宪法学通说,经营自由乃是属于经济自由的一种,而各国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一般采用较为宽松的宪法审查基准。因此,与“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范范式相比,直接规制网吧经营者“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就更容易通过宪法审查的门槛。
一般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从本质上来说反映的是一种公民对峙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对抗权。因此,基本权利受到干预,也是指国家的行为造成了基本权利的剥夺、限制或实现上的困难。传统的基本权利受到干预的概念内涵一般限于直接干预方面,在此严格限定下的基本权利所受到的“影响”尤其是“间接影响”并不认为是一种对基本权利干预的情形。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立宪主义在考虑到国家与人们的互动关系多样性的基础上,已经摒弃了上述古典理念,而把对基本权利干预的重心从“形式”或“手段”的考虑转移到对“结果”的判断上,只要国家权力的行使增加了人们基本权利实现的困难或致使人们基本权利无从实现者,无论该后果是国家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因法律行为或事实行为造成的,均可能构成对基本权利的干预。④无论如何,“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其实质目的就是要“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它必定会干预到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上述观点当无疑义,本文亦采取此立场。
从这种对抗权意义的角度出发,“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范范式无论是采取规制网吧经营者的方式还是采取规制未成年人的方式都将直面公民的两方面的权利:未成年人的宪法基本权利与网吧经营者的营业自由权。⑤换言之,《办法》、《条例》或者《未成年人保护法》要实现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管制,必将剥夺或限制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从宪政主义的立场上看,要剥夺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显然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一般来说,对于基本权利的剥夺或限制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否具有合宪的理由,亦即其积极介入的正当性基础何在;第二,手段是否必须。至于我国的“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是否具备这两个条件以及其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则有赖于下文进一步缕析之。
二、规制的理由及其宪法审查
尼尔·麦考密克曾经说过:“就出台法案、做出行动、提出主张和予以反驳这些活动来说,公众都需要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法律上的理由。”⑥对于“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这一规定而言,由于其客观上必然会干预到未成年人的上网自由,因此上述规定若要通过宪法的审查,其立法理由必须要满足宪法上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条件。
从未成年人上网自由的角度上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表面上似乎只关涉到未成年人的行为自由权,即宪法中人身自由权的展开形态。然而,倘若就网吧对于未成年人的重要性进行仔细分析的话,我们可发现网吧乃是未成年人娱乐休闲与思想交流之重要场所,同时,即使是网吧的反对者亦难以否认,网吧中网络的使用亦可以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倘若对于未成年人网吧活动行为进一步全面观察的话,实际上大致会涉及到与精神自由密切相关的诸如(网络)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网络)集会自由、(网络)结社自由、(网络)通讯自由等等一系列“高位阶的权利”。
除此之外,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里,网络已不仅仅只是硬件或知识的代名词,它同时还是未成年人个性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个性自由的一般范围,学说上乃承认主要包括了自我决定、自我维持和自我表现等不同展开形态的权利。未成年人要发展其自身的个性,其前提是他们要逐渐脱离成人的监护,凭借着自我的所感、所知、所想对周围事物作出自我决定。然而,这种决定能力的获得并不能凭借个体自我的才智与努力就可达成,它必须经过社会交往的长期过程才可能逐渐形成,这其中可能要经历种种蜕变与痛楚。对于绝大多数的未成年人来说,多数时间里他们是处于“学校—家庭”的封闭空间之中的,这极大地扼杀了未成年人交往发展的多样性空间。但是,网络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交往条件,无论他们上网是为了聊天、参与社团或合作进行游戏,都能藉由与其他人相互间的交流与协商而获得自我认知与自我决定的能力。时至今天,网络交往、网络道德以及网络人格等的出现几乎已根本颠覆了我们的传统生活,网络个性也由此而来。因此,未成年人希望通过网吧活动获得成为一个成熟个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为未成年人自我个性发展自由的展现方式之一,涉及个人作为主体的抽象品质,无疑属于宪法中个性自由或人格权的必然内容。
因此,网吧就关涉到宪法中极为重要且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一方面可构成精神自由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亦可构成德国宪法中未成年人个性自由(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精神自由是宪法保护的重心之所在,对它的干预一般要满足非常严格的宪法条件。在美日宪法中,包括表达自由在内的精神自由,在双重基准之下受到了非常严格的保障。⑦对此,日本学者认为:“双重基准系在美国判例上所形成,认为对于以表现自由为主的精神自由之规制,应依据严格的基准,严密检讨其合宪性,……亦即,关于规制精神自由的法律,主张合宪的一方,必须依据事实(此种支持法律合宪性的事实,称为立法事实),表示该规制系为实现非常重要的政府目的,无论如何不得不采的必要规制……”⑧日本芦部信喜教授更是指出,除了双重基准之外,对于精神自由中表达自由的规制还应该受到“禁止事前抑制”、“明确性理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基准及“限制性程度更小的其他可供选择之手段”等的限制。⑨就德国而言,战后德国宪法实践中也非常重视对精神自由的保障,亦形成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基准。在1958年吕特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对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国家而言,意见自由具有一种“绝对的”、“本质的”价值,并构成所有一般自由的基础,从而应该予以更严格的审查。⑩
个性自由是人格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人格权理论最为发达的德国,作为一个近代历史上市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传统上德国宪法均将人格权的保障置于价值上的核心地位。在德国宪法中,《基本法》以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为首位,规定了包括人格自由(个性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与自由。然而,宪法法院很少单独谈论个性自由而不提及人的尊严,亦即个性自由与人的尊严不可分离地构成人格权保障之核心部分。虽然个性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被法律所限制,但对它的审查一直都是较为慎重的。
因此,一般情形下,除非“为实现非常重要的国家目的”的情况下,国家方可对精神自由或者是人格权进行限制。(11)问题在于:我国“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理由是否满足了精神自由或个性自由的宪法限制基准呢?
对于我国“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立法目的与理由,从各方面人士有关讨论或者媒体的介绍中,大致可以整理出“促使未成年人回归学校”、“提供正常的休闲活动”以及“防止网吧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等理由。上述几个理由,从自由主义宪法的立足点来看,均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缺憾。唯有“防止未成年人身心受到危害”的共同关怀可以通过自由主义价值的审视,而其在宪法上的规范展开形式则是未成年人人身自由中身心不受伤害的权利范畴。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权内容及保护义务的要求,国家有积极介入的作为义务。这就要求国家截断危害源对于未成年人身心的不利影响,从而赋予了国家进行网吧管制的宪法正当性基础。而2006年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条首先就对“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理由作了类似上述的说明,即该法所采取的一切规制手段都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这一理由,“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第33条)。(12)
从未成年人利益的立场上看,一切对于未成年人上网的规制手段似乎总显得那么的“冠冕堂皇”:这是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而设计的完美制度。然而,姑且不论未成年人自己到底是如何想的,或许处于叛逆时期的青少年根本无法理喻和享受这些成人社会为其设计的“美好蓝图”,单从宪政的立场来看,“保护”与“伤害”之间的临界点到底何在恐怕本身就是个众说纷纭的话语。
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教授曾经指出:“现代政治并非‘原则政治’(politics by principle)。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利益政治’(politics by interest),不论是以明显具有歧视性的形式对待(奖励或惩罚)公民中的某类特定群体,或以某种精英论——基于预先假定某类人在有关对于我们所有人真正‘有益’的事情方面具有高人一筹的智慧,而将公民划分成该受奖赏和不该受奖赏之类。”(13)依其观点,对于人类的特定划分本身就是“利益政治”,是一个价值范畴。因此,“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制定者似乎忘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特殊人群或事物的专门保护一方面反映了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事实,从而可归入一种“利益政治”范畴;另一方面这种保护或许恰恰可构成哈耶克式的“自由的铁笼”,(14)从而激发进一步的“反保护行为”而导致新的伤害,而媒体曾大量报道过的“黑网吧失火案”及“北京的未成年人到河北去上网”等事例就可有力地佐证这种尴尬场面。于是,保护还是伤害,显然只是一个价值立场问题,立场不同,结论就有所差别。从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上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虽然直接限制的是经营者的经营自由,但是这种间接限制在现代宪法中亦可被认定为是一种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国家干预。依宪政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论这种干预的结果到底如何,其本身已经属于一个伤害的范畴。
上述说法可能会招致国家机关的异议,其论争的理由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制定这种规定本身属于国家机关权力的范畴,这也是公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第二,“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虽然对未成年人的网吧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与国家的直接干预有所不同,并且“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本身亦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从宪政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理由未必能够成立。从第一个理由来看,公权力的行使尽管有宪法上的根据,亦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但并非没有限度。倘若公权力的行使会造成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则此种权力的行使必须要接受合宪性的审查。对于第二个理由,有关规定虽然非直接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权利,且其制定的目的亦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然而合宪性与合理性在功能上毕竟不能等同,这种规制在事实上的确已经影响了未成年人基本权利的实现而可构成现代宪法上国家干预的情形。
饱受专制主义荼毒之苦的人们通常强调,对于限制或剥夺权利的行为或法律应该进行严格限制并要接受宪法审查,但是,并无多少人真正意识到,与限制或剥夺特定主体的基本权利相比,对于特定主体的“倾斜性保护”可能亦有“合宪”与“违宪”的讨论空间。早在1960年,肯尼迪总统在优惠少数种族的行政命令中曾首先提出过“纠偏行动”这一概念。此后,“纠偏行动”被普遍用于指:为了弥补与纠正法律歧视在历史上给妇女、有色人种或其它社会阶层造成的贻害,立法或行政机构在规定雇用、录取或交易过程中,决定给这些阶层带来特殊优惠。然而,“纠偏行动”在“平等保护”条款下的审查基准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以针对种族的“纠偏行动”项目为例,它们是否应该和有害歧视同样受制于严格审查?无论在法学界或法院内部,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受到广泛争议。(15)以此为启示,谁可断言我国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理由而规定“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这一“保护性”规定不存在与“纠偏行动”相似的宪法问题呢?
三、手段必要性的宪法分析
无论是《办法》还是《条例》,抑或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的一种规制手段,它必须接受手段必要性的宪法审查。宪法中对手段必要性的要求是指在所有能够达成目的(立法或行政目的)的手段中,必须选择对基本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
如前所述,精神自由的宪法审查一般采取严格的审查基准,对于手段必要性的要求亦不例外。在美日宪法中,这种要求一般是“不存在可不对自由加以限制的其他手段”。(16)而在德国的比例原则之下,对干涉及精神自由中诸如言论自由、通讯自由、结社自由等具有民主形成功能的基本权利案件以及涉及人格尊严案件,宪法法院将会使用与涉及生命、人身自由、婚姻家庭以及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需求领域一样的“强烈的审查基准”。而这种严格审查基准之下的手段必要性的要求则可援引宪法法院的一项判示予以说明:“别无其他相同有效而且对基本权未予限制或限制较少的手段”,(17)亦即立法者选择手段是必要的。
然而,“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却非解决未成年人网络问题的必要手段。从逻辑上讲,网吧或上网与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危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这里对于原因关联性的这种粗略测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哈特与奥诺尔合著的《法律中的因果关系》一书中就指出:“原因关联性和不可缺少的原因的观念并不是相同的,就后者对前者起着的指示作用来说,法律通常只与后者相联系。”(18)如果说进入网吧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损间有联系的话,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潜在的或然性因果关系。这种潜在的可能性一般并不足以构成宪法上限制的理由。汽车可能会造成车祸的出现,却从未有人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杜绝汽车的生产,以此为例来说明上述问题可能是再恰当不过了。从结果上看,显然未成年人迷恋网吧、网络色情与暴力游戏等问题不会因为“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而消失,而媒体亦曾报道过未成年人于家中迷恋网络的事例。再者,从宪法权利理论的角度来看,网络甚至还可导致一些新的网络人格的出现,亦能促成诸如“平等权”、“结社权”等传统权利的实现,即使是批评者亦无可否认“网络并非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一命题。易言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并不能获得诸如禁止未成年人吸烟、喝酒等法令同等的正当性。
从网吧危害的根源上看,媒体所谓的“网吧毒害”中诸如网络色情、暴力游戏等产生的终极原因应该归咎于政府管理不力之过而非未成年人或网吧经营者之错,至于未成年人不分昼夜上网则可归结于由成人强势地位为核心的监护人监护不力或不当的缘由之中。因此,透过现行法律法规的执行,以及各种行政管制手段的灵活运用,即足以导正网吧的营业环境,达成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不受伤害的目的。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制手段就显得有点多余。因此,倘若要对未成年人有关网络问题进行法律上预防或处理的话,其中关键并不在于对未成年人或者网吧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规制,而应在于确保政府对于网络内容的分级管理责任与未成年人监护人之监护义务的实现,纯粹的“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
退一步讲,倘若政府对于网络信息的管制没有充分履行其责任,或者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能以合理之道尽到其应有的抚养教育之监护义务,则纵使全中国没有了任何营业性网吧场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亦可能得不到保障,未成年人完全有可能寻找到其他上网的机会,亦有可能谋求到其他的“堕落”途径。(19)因此,“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手段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终极目的之间并无充分合理之关联,非“必要之手段”。易言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并非可满足双重基准下的“无论如何不得不”的标准。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美国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还是日本的《关于规制使用网络介绍异性业务诱引儿童等行为的法律》,其核心都在于强调政府对于网络信息内容进行技术性规制的责任,而非切换至诸如禁止进入网吧之类的或然性问题上。
最后,依德国宪法法院1991年的一项判决,(20)未成年人并无表明自己为未成年人的义务,否则即侵害到其人格权。从这个角度来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这一规定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就失去存在的技术基础。(21)
四、代结语:成人政治的一个密谋
笔者无意于哈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立场,然而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规定显然难以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理由下获得合宪性基础。再者,上述规定显非最佳的手段,的确存在违反宪法之虞。即使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理由下,国家亦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达成同样或更高的目的。申言之,“如果在目的达成的观点下,一个较强烈的侵害并不比另一个较温和的手段更有效时(可能只是相同有效或效果更差),立法者有义务选择较温和的手段。”(22)
从本质观之,“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禁止性规定实际上乃可映射出国家及作为成人的监护人意图将其自身责任转嫁于无完全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相对处于主流政治之外的网吧经营者身上,并实现迫使未成年人依自己设定方向成长的一种强制图谋,它体现了明显的成人政治价值取向。然而,从个性自由的人格主义观之,网络则可构成信息时代里人格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成长于21世纪的未成年人来说,一个满脑“教材之道”而不知“886”、“伊妹儿”等为何意或者根本不知网络为何物者,在今天反映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不足,而且会导致他与其他人间交流的困难乃至造成人格发展的不健全。网吧对于当下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的中国而言,可以说是许多经济条件受限家庭中未成年人接触网络的唯一条件,“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必将从根本上阻断他们通过网络健全人格的途径。因此,成长于“农耕时代”的家长们岂可要求处于“信息时代”中的未成年人按照“过时的”成长方式来发展,要求他们学习之余也只能牧牛或耕作,就不能进入网吧上网看信息、发帖、博客、看电影、QQ或玩游戏?
注释:
①甚至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营业性网吧(有关的报道可参见《重庆晚报》2006年12月26日)。不过,这一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在2006年12月29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为《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法律只规定网吧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第36条)。因此,可以认为,这一措辞与“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同义。
②2004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内不得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不得在可能干扰学校教学秩序的地方设立经营性娱乐场所。”(第九类第二十五项意见)而2006年修改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亦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与“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并列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第36条)。
③[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④参见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73页。
⑤在各国的宪法审查实践中,对于包括经营自由在内的经济自由的审查一般均采用相对宽松的审查基准,因此,倘若依此来分析“禁止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的违宪问题,论据并不充分,本文亦不再赘述。
⑥[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⑦当然,精神自由的保护亦非绝对。以言论自由为例,1917年《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之后,在1919年“抵制征兵第一案”中霍尔姆斯法官(J.Holmes)就曾阐明过“清楚与现存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基准。国家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但必须要证明言论可能产生的紧急危害且危害要达至相当严重程度,同时散布言论的被告具有故意违法的主观意图。换言之,为了促进重要公共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时,国家仍然可以调控言论的时间、地点或方式。尽管如此,国家调控必须保持“内容中性”(Content Neutral):即调控不得规定或限制言论所要表达的内容信息,从而在“清楚与现存危险”之下起着绝对保护的作用。
⑧[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正典、户松秀典:《宪法》(下册),周宗宪译,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67页。
⑨[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页。
⑩BverfGE7,198ff.
(11)同注⑧,第67页。
(12)在2001年的《办法》以及2002年的《条例》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办法》第1条就对其立法目的进行了说明:“在于为了加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促进互联网上网服务活动健康发展,保护上网用户的合法权益”。而2002年国务院公布实施的《条例》也秉承了这一立法意旨,在其第1条中也作了相似的解释:“为了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规范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维护公众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3)[美]詹姆斯.M·布坎南、罗杰·D·康格尔顿:《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张定淮、何志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15)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
(16)同注⑧,第67页。
(17)BverfGE30,292.
(18)H·L·A·哈特、托尼.奥诺尔:《法律中的因果关系》,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9)笔者曾骇闻山西方山县为了导正未成年人回归学业而全县关闭网吧,概不考虑成年与未成年的问题,意图从根本上消除网络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然而,此后有报道称“山西方山取缔网吧后迪厅台球厅成学生新去处”。参见搜狐网:http://learning.sohu.com/20061026/n246027497.shtml(2008年6月3日访问)。
(20)该判决表明:“禁治产人于订立租赁契约时有公开表明其系受禁治产宣告之义务时,即侵害到该禁治产人之人格权。”参见《关于“禁治产人一般人格权在租赁契约法上之保护/无公开表明之义务”之判决》,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三),(台湾地区)司法院1992年版,第247页。
(21)我国2006年修改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6条规定了:“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从宪法上看,这无疑是很值得拷问的。
(22)BverfGE33,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