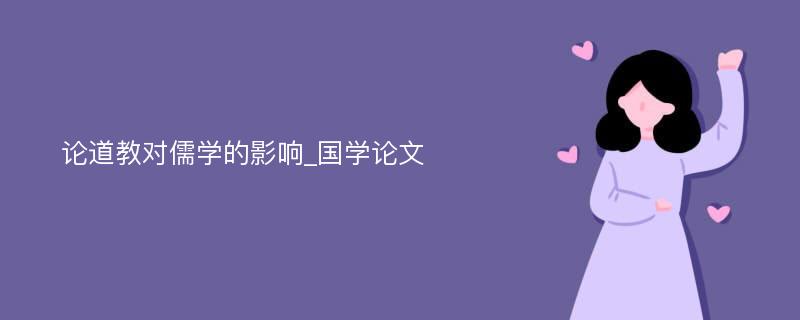
论道家对儒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3828—(1999)03—0053—06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学术文化大解放、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学说蜂起,学派林立,各种学说,各个学派在春秋战国所提供的历史大舞台上竞相表演,互相诘难,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由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对于这一时期的学术有人用“吹万不同”来加以描述,称这一时代为“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在这样一种学术情势下,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洁身自好”,丝毫不受其它学术和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在这种沸沸扬扬的学术论争中,各种学说、各个学派都从对方的理论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而充实、完善、发展自己,正是这种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最后才出现了“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学术一统的局面。因此,从中国哲学起源于先秦诸子来看,最初虽然呈现着一种多元横面并起的局势,但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域中所产生的多种思想,其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却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学术发展是多向磺面而又相互交错的,决不是单线纵向而彼此孤立的。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就体现了这种学术特点。
道家与儒家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对立性不仅表现在两个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和孔子那里,如老子崇尚人的自然性与自主性,抨击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却卫护礼,信守礼,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把礼作为社会的准则。老子主张“天”的自然性,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消除了传统天命观的神秘性和欺骗性,而孔子却不否认天的神性,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老子喜言天道,而孔子却“罕言天道”等等。而且信奉、学习两家学说的学人也彼此诎难,互相对立,“世之学老者则诎儒学,儒学亦诎老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认为这是“道不同”,所以才会“不相为谋”。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学派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学派,就必须有自己存在的依据,要有自己学说本身的特色,否则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无法立足了。从春秋战国的学术氛围来看,道家与儒家除了相互冲突之外,也还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得到说明。
第一,从孔、老的关系看道家对儒家的影响。关于孔、老关系,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其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老庄申韩列传》)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所说的那个时代的已经死了,连骨头也已经腐朽,流传于世的只有言论。君子生当其时就辅佐君王,从事社会活动,生不逢时就应该像断了根的蓬草随风飘荡,不要强为己难。我听说,善于做生意的人把珍贵的货物藏起来,装做什么也没有,盛德的君子外表上却像个傻瓜。你要去掉你现在这种旺盛的精力,去掉你过份的欲望,去掉你的进取之态,这些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所要告诫于你的,仅仅如此而已。这里形象地反映了一位饱经风霜,体验了世态炎凉的老者的心态,整个对话情形俨然一位慈善的老者在谆谆告诫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仅如此,司马迁还以传神之笔,记载了孔子对老子的印象: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同上)能飞的鸟,可以用箭来射;能游的鱼,可以用鱼钩来钩;能奔跑的野兽,可以用网来捕捉。至于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就无法抓住它了。而老子就正像龙一样。
对于这段文字中所记载的事实,唐代以前没有任何歧义,但从唐代韩愈起,就开始痛斥孔子师老之说。不过,韩愈的痛斥纯粹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而进行的义气之争,没有多少事实的根据,所以后人说韩愈是“卫道有心,论辩无据”(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自序)。韩愈开了这个头,宋儒就更加激进,开始怀疑老子其人的存在,如叶适就曾说:“孔子赞其为龙,则是为黄老学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也”,“教孔子者必非著书之老子,而为此书者,必非礼家所谓老聃,妄人讹而合之尔”。(《习学记言》)人都不存在,那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就更是子虚乌有的了。后来汪中、毕沅、崔述都怀疑老聃其人的真实性,近现代学者中的怀疑派以梁启超、钱穆、冯友兰最为典型。
对于怀疑派的种种言论,许多学者都作了详细的辩析,这里我们不再作赘述。我们认为,孔子问礼于老聃是确有其事,而不是向壁虚构,依据许多学者的观点,我们进一步申述其说。我们认为孔子问礼于老聃这一事实是真实的,主要理由是:
其一,,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能够据实直书,对于史料能够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加以剪裁和断定,因此其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其二,除《史记》外,在先秦的许多典籍中,如《庄子》、《礼记》、《吕氏春秋》都记载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史实。《庄子》属于道家学派的著作,在《庄子》一书中,称引孔子者达四十二处,称引老子者达十九处,而记述老子与孔子关系的达十一处(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4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而在记述孔、 老关系的文字中,老子总是以孔子前辈的姿态出现,如在《天地》篇中记述老子跟孔子谈论“至道”:“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是,则可谓圣人乎?’老聃曰:‘胥易技系,劳形状心者也。……丘!予告若,……有治在人,记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记之人,是之谓入于天”;《田子方》篇记述老子跟孔子谈论“天道”问题;“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披发而乾……孔子便而待之。老聃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另外在《知北游》篇中还有老子跟孔子谈论天地万物自发性问题的记载,在《天运》篇中有老子跟孔子谈论“三皇五帝治天下”、六经等问题的记载等等。《庄子》一书,尽管“寓言十九,重言十七”,然在寓言部分中,“除完全架空的人物以外,对历史人物相互关系的行辈,则从无紊乱”(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附录一《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台湾东海大学1963年版。转引自陈鼓应《老庄新探》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这也就充分说明,《庄子》书中所记载的此事,也是完全可信的。正如唐兰先生所说,《庄子》书所记孔子和老聃的谈话,“固然是因各崇其师的缘故,对于他们两人谈话的记载全都难信,但其事实总是真的,何以庄子不写成孔子见杨朱墨翟而单写见老聃,可见孔子的确见过老聃的。”(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古史辨》第四册)
《礼记》是一部传自儒家系统的著作,在其《曾子问》中,有四段材料涉及到了孔、老的关系,其中三段材料说“吾闻诸老聃曰”,如“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欤?’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有一段材料中还说到“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内容,都是孔子在一些特殊事变下,从老聃那里得到有关礼的启示。如果说《庄子》作为道家著作,本着为尊者讳,有“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辞”的倾向,然《曾子问》却是传自儒家的著作,与道家迥然有别,如果不是真有其事,儒家著作是不会记下此事的,况且“《礼记》编定于汉朝,儒、道两家的对立,已甚为明显。若《曾子问》中的四个故事,非传自先秦儒家之旧,则汉初儒家,又何肯将其杂入,以长他人的志气呢?”(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并断定“《曾子问》所述必然反映一些历史事实。”(张岱年:《老子哲学辨微》, 见《中国哲学发微》第332 页,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如果说《礼记·曾子问》所载属于儒家曲籍孤证的话,我们还可以从《韩诗外传》中得到佐证,《韩诗外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成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二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这段文字,尽管没有说明“仲尼学乎老聃”的具体内容,但我们从孔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来看,礼应该是孔子向老聃学习的内容之一。不仅如此,子夏还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功业著乎天下,名号传于后世,正是由于孔子向老聃请教的缘故,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老子对孔子的施教,孔子才能成为“圣人”。子夏是孔子弟子“七十二贤”之一,他的说法应该是十分可靠的。况且《韩诗外传》属于汉代儒家的作品,当时儒术独尊的叫喊已日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儒家自身的典籍仍然有“仲尼学乎老聃”的记载,可见此事不会有诬。另外这条记载,在刘向的《亲序》中也被采用,只是有关姓名与此稍异,如将“大坟”写作“大真”,“线图”写作“禄图”。这说明子夏、刘向等人都承认老聃为孔子老师。既然儒家典籍都毫不隐晦地承认此事,我们又何须为此多费笔墨,耗精费神呢?
其三,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告诫孔子的言论,与今本《道德经》和帛书《老子》相对照,思想完全吻合,如“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本《老子》中有“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四十一章),帛书本老子除“若”俱作“如”和其它字稍有不同外,其它都一样;十六章中还有“致虚极,守静笃。”又“去子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今本《老子》中“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帛书本除个别字句外,基本与此相同。从这些简单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记》所载是有根有据的,与老子思想没有任何冲突,双方若合符契。
孔、老的这种师生关系,说明了老子长于孔子,道家思想的产生要先于儒家,儒家从道家那里吸取了思想养料,这一点从《论语》中就可得到确证,更不用说宋明时期儒家学者借用道家的概念、范畴来建立理学的思想体系。正是儒、道学派的两位创始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才会出现儒、道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不清,道不白的现象,也才会导致一些儒家学者贬道扬儒,如韩愈、宋儒等,也才会出现在儒学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氛围中,道家学说始终绵绵若存,永不断绝。因为儒家学说需要不断地从道家学说中吸取养料来充实、丰富、发展自己,儒学的几次重大质变都吸收了道家的思想理论,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第二、从《论语》所载言论看道家对儒家的影响。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孔子曾以老子为师,向老子请教过许多问题,学到了许多知识,最后成了“圣人”。既然孔子师从于老子,那么其思想就多多少少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不会与老子思想毫无联系,这种思想联系我们在《论语》中可以得到佐证。
《论语》是人们所公认的研究孔子思想的最可靠的材料,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所辑录的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下面我们将《论语》所载的有关言论与老子思想加以简单比较,以便说明这一问题。
(一)《论语·卫灵公》有:“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政治思想,在《老子》一书中,有许多章都论述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如第十章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第六十四章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尽管“无为”二字不出自老子(《诗经·兔爰》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这大概是有关“无为”最早的文献记载),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老子区别于其它诸子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是毫无疑义的。孔子所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只不过是想用舜来对此加以证明。很显然,孔子在这一观点上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孔子的政治理想并非无为,何以忽然提出‘无为而治’来?如果认为是对老子学说的反响,不是容易理解吗?(张岱年:《老子哲学辨微》,《中国哲学史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以“大胆假设,精心求证”而整理国故的胡适先生也认为孔子“无为而治”的学说受到了老子的影响。(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古史辨》第9册,第419页。另外黄方刚先生也持此说,见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同上书第354页)
(二)《论语·阳货》记载:“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对老子“无为而治”的学说,孔子一方面是在为政的原则上加以推崇,另一方面又在个人原则上加以批评,这段话就正是孔子对老子无为学说的批评。孔子认为“无为而治”作为为政原则,运用在政治上是可以的,但是对个人来说却不宜无所作为而应有所作为,所以他奉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使惶惶如丧家之犬也不改初衷。
以上两段材料,一方面是说孔子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推崇,一方面是说孔子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批评,无论是推崇还是批评,应该说这都是老子思想对孔子思想影响的一种反映,从而也从侧面反映了道家对儒家的影响,及其儒、道之间的关系。
(三)《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这里所引的“报怨以德”,来源于《老子》六十三章,其文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有人将“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解释为:“‘大小者,大其小也,小而以为大也。‘多少’者,多其少也,少而以为多也。”(高亨:《老子正诂》,第132页,中国书店1988 年版)“德其怨也,怨而以为德也。”(张松如:《老子校读》第346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意谓谨小慎微。孔子却将此解释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用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拿恩惠来酬答恩惠。孔子在《里仁》、《公冶长》、《尧曰》等七篇中讲“无怨”、“不怨”、“远怨”、“匿怨”、“又何怨”、“又谁怨”达十二处之多,可见,孔子对“怨”何其重视。如果说老子采取的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而孔子采取的却是一种等值回报的态度,两相比较,双方宗旨,泾渭分明,针锋相对。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老子曾为孔子师,而《论语》又直接引用老子之言进行评论,尽管孔子与老子之旨相悖,但不可否认,正是老子的言论为孔子树立了靶子,才引发了孔子的这种议论。换句话说,孔子的这种灵感来源老子触媒的刺激,没有老子这一触媒,也就没有孔子的灵感,因而孔子受老子的影响是很显然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一样,“孔子于《宪问》答曰:‘何以报德?’此适与老子‘大小多少’句针锋相对”,因此,“孔子有老子学说在其心中也。”(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古史辨》第四册第354页)
(四)《论语·述而》载:“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这一段话中的“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很明显是有所指的,而且这段话也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老子》中的有关言论,“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白若辱”。孔子是从反到正(如“亡”与“有”,“虚”与“盈”,“约”与“泰”),老子是从正到反,(如“成”与“缺”,“巧”与“拙”,“直”与“屈”)尽管表达方式不一,但孔子是有所本的,而且孔子对这种人生态度是不赞成的,认为这样的人难于保持一定的操守。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在这里评述的正是老子。(李泰:《老庄研究》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孔子虽然对这种人生态度颇有微词,但在实际行动中又不自觉地加以践履,《泰伯》篇载:“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昔者吾友有从事于斯者矣”,尽管历代注家都认为这里的“吾友”是指颜回,然而又“安知不是孔子呢?”(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第58页。)
以上两条材料,是孔子对老子学说的评论,体现了孔子对老子学说的基本态度,同时,也反映了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五)《论语·宪问》载:“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意谓仁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仁。“仁”是孔子人学的一条主线,在伦理道德意义的层面上,它包括“爱人”、“克己复礼”、“恭”、“敬”、“惠”、“义”、“宽”、“信”(张岂之主编《中国儒学思想史》第29—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含义,孔子的“爱人”是一种有等差的爱,主要用来调整君臣、父子等的关系,因而包含有“慈”的含义。在《老子》六十七章中有“慈,故能勇。”将此与上段《论语》中的记载相对照,可以发现孔子所说的实际上是《老子》一语的扩大。因此,孔子这句话很可能是从《老子》那儿来的。(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
(六)《论语·泰伯》载:“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老子主张顺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理论,要求人道效法天道,像天道一样“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这构成了老子思想的一大特色,因此,《泰伯》篇所说“有天下而不与”的观点可能是从《老子》那儿来的。(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哲学研究》1988年第9期,又见《老庄新探》)
这两段材料是从思想来源上说明了孔子与老子的关系,反映了老子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七)《论语·公冶长》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述而》载孔子谓颜回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是主张积极入世的,这种无奈避世的思想恐怕与老子影响有关。将这些话与《史记》本传中所载老子告诫孔子之言“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互相对照,便会发现两者正相一致。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孟子的思想中,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论语》中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孔子曾受老子的影响,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从上面所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老子确实对孔子思想有着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影响,而且是整个两大学派、两种思想体系的互相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大学派本身的发展,这种影响越来越明显。
收稿日期1998—12—20
标签: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学派论文; 道家论文; 庄子论文; 论语论文; 礼记论文; 古史辨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