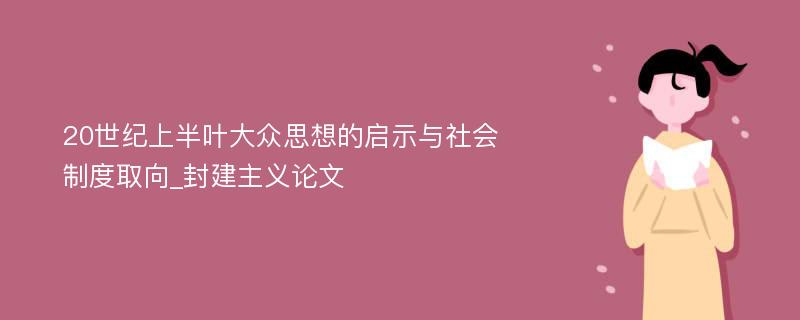
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与社会制度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取向论文,社会制度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功绩在于,它使大众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初步认清了实践于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传统观念及各种外来观念的面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从而带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道路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一个世纪的外族入侵,国内战争与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社会现实,使中国的大众思想接触了众多的观念形态。中国儒家观念、西方18世纪以来三个世纪里思想家们提出的各种观念以及马克思主义观念在大众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产生了激烈的撞击。在战争环境下,没有人能够不作选择而置身于是非之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社会现实面前,追求社会进步的人们首先从古老文化的陶醉中苏醒,向骄傲的过去告别,然后认同了西方文化的优越;在急速的社会革命洗礼中,又使执着于西方民主、自由、宪政理想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了构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终于走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与共产党人和农工大众一起确认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
然而也正是由于大众在苦难的年代里必须作出观念选择,使得各种思潮形成了如白驹过隙的奇特场面,人们往往来不及细细品味,就付诸社会实践或将其遗弃。思想论争伴随着“五四”爱国运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浪潮、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救亡运动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起,紧锣密鼓地开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因而思想的火花有如流萤,中国大众在没有彻底受到思想启蒙的情况下,匆匆走进了社会现代化、民主化历程。由此,引导大众思想启蒙的思想家们在这种特定社会环境里形成了三元二分法的思维模式,构建了两种重破轻立的新观念体系。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取向存在三元,即封建主义取向、资本主义取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而又将这三种取向区分为新与旧、民主与专制、进步与保守、唯物与唯心、文明与愚昧等两个对立的阵营。尤其是资本主义取向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向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对抗之中,导致了当时和以后一场接一场的思想政治运动与批判浪潮,极大地左右着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
一、思想的“典范形式”:大众思想启蒙的思想前提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实际上反映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思想史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20世纪上半叶思想史的演变也恰恰是当时历史演变的逻辑结果。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不是一种独立发展的社会形态,很难找到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典范形式”。相反,社会生活的多层次和多元化造就了各式各样的“典范形式”,以至发展为三种社会制度取向,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被裂变为众多阶层的大众的心灵中。因此,大众的社会制度取向也只能取决于几种主流观念的对垒状况以及被拟制为某种社会制度化身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状况。各种观念似乎都已现成地摆在大众面前,谁优谁劣,最后必须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大众在社会实践中选择观念的过程也就成了大众完成社会制度取向的过程。
中国的大众思想启蒙是在特定的民族危机的环境下催化,围绕着政治军事斗争展开,以封建主义、西方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的三元对垒为主要表现形式并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完成的。思想启蒙家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互相辩驳、论争这个问题上,而未能各自完成其观念的“典范形式”,让大众了解各种观念的范畴体系和实质内涵。因而,“文化快餐”式的新观念从一开始就体现出重破轻立的理论特点。也由此,西化还是复古(全盘西化还是本位文化)、西化还是苏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民主还是独裁(宪政还是一党专政)、科学还是迷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种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形成为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也成为大众社会制度取向的特征。
“五四”以前的思想启蒙形成为20世纪上半叶民主主义思想的“典范形式”。较早时期能够体现出思想启蒙特点的,是士大夫们自我启蒙的“洋务”与“维新”。士大夫阶层在西方强国炮舰进攻下终于发现中国的失败是技不如人,因而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指导了洋务运动;但他们在洋务实践中进一步发现,技不如人是由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落后,因而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猛喊,紧接着又试图把自由、平等、民权、宪政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这导致了维新运动的发生。他们相信,古老的帝国在习得了西方制器之术与民主、自由、宪政制度之后便能再生。然而,帝国统治者葬送了这一事业。但也正由于洋务、维新使一代新人的出现成为可能。在留学热、兴办新式学堂热与新式文化运动中,一整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他们较多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和政治观念,在社会制度取向上认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而打起了反清旗帜,葬送了帝制。以孙中山为旗帜的这一代人,他们改换了自身的观念;然而他们倡导的思想启蒙未能改换大众的观念——无论是“华老栓”还是“阿Q”(注:鲁迅作品《药》、 《阿Q正传》中的文学形象。), 都不可能懂得辛亥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因而到“五四”时代,出现了大众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将改变了知识分子而未改变大众的思想“典范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并因白话文的推广而变得现实可行。
而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后的广泛传播标志着一种与民主主义思潮抗衡的新的观念体系开始在中国诞生。这种新观念体系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介绍之后,即被用来指导社会实践,并加入到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行列。“五四”以来,无论是思想界的人生观论战、文化论战、宗教问题论战还是哲学论战,也无论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问题的争论,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中国的“典范形式”——新民主主义创造了条件。
因而儒家思想、民主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思想成为20世纪上半叶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前提。
二、“五四”大众思想启蒙: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达
以封建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命名的三种观念体系,在20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形成为三元,而它们又是被人们在二分法的思维模式中加以选择的,即封建主义排斥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排斥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排斥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并均以被排斥的两个异己作为同类加以批判。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末甚至还可得见。(注:如坚持社会主义,以唯心、剥削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共性加以批判;鼓吹全盘西化,以集权、独裁为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的共性加以抨击。)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大众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始,也是三元二分法思维模式的最初表达。
启蒙开始时的社会现实是,存在于中国的全是矛盾的社会现象。巡警与更夫、民国与清室、迫人尊孔与信仰自由、禁止重婚的法律与允许纳妾的习俗等等,那么不协调地整合着中国大众的生活与观点。就像李大钊指出的:“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注: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四卷五号。)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以何种观念来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关不住的闸门里汹涌的流水,闯进了中国人复杂的世界里;许多思想家以导师的身份站在思想启蒙的前沿,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思想论争。
当时影响最大的《新青年》杂志在《本志宣言》中宣称:“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注:《新青年》七卷一号。)它一面发出向旧观念宣战的号角,一面主张思想家创造新观念来指导新社会。
新与旧之分,是三元二分法思想模式的最初表达形式。
然而什么是新观念呢?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工读主义、互助论、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平民教育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抑或文字上的文学问题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从平民教育到“到民间去”、“到法国去”,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会自定出流的方向。”(注:瞿秋白《饿乡纪程》之四,《瞿秋白文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因而此时的新思想偏重于向大众(尤其是青年)传播,而欠研究与创造,更谈不上区分何种更合于中国的国情。也正因为这样,新思想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多元与分化的可能。实际上,对各种新思想的吸纳与容忍,也正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民主”精神所在。
随后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也作为一种新观念广泛传播到中国的思想界。从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启蒙运动导师,到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青年学子,都满怀激情地向中国大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现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展,并进而发展到探讨在中国组织共产党仿效俄国发动中国革命的具体办法。
同时,胡适派启蒙思想家提出,新思潮的意义在于“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注: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七卷一期。)。他们认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单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注: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存》一集二册。)因而他们认为此时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是好听的“空谈”,“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注: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存》一集二册。)是无用而危险的。
有的学者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说:“他们就看见马克思主义的一小点长处,他们就信仰马克思主义,甚而至于高谈马克思主义,哄骗一般无知识,最易受人愚的劳动者,以实行他们宣传的计划。然而能看到一点长处(不是好处),这还是好的,还是有一点人的灵性的人。最可怜而最可恨的那般无聊的青年,他们硬说马克思主义一无可訾,俄国实行了马克思主义,(其实,俄国哪里实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也得实行马克思主义才对。于是,他们就大吹大擂,为俄国捧场,好像戏园里流氓怪声呼好的一般模样。他们一面捧俄国,说俄国是乐土,是天堂;一面更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播其毒于中土。”(注:勉人《为谈主义者进一解》,钟离蒙、杨凤麟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年7月版, 第一集第二册第29页。)
当新潮思想家批评马克思主义时,守旧派也在痛斥这些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不顾是非利害,不计将来的效果,信口狂言,以全国天真烂漫之少年为其试验品,为其功利名誉之代价,是可忍孰不可忍!”(注: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汇编》第一集第一册第61页。)更有甚者,林琴南竟把所有新潮思想家的宣传当作“禽兽之言”,恨不得“骈二指按其脑”,“更以足贱”,使他们“怕死如猬,泥首水已”(注:林琴南《荆生》,《汇编》第一集第一册第35页。)而后快!
就这样,“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按其本身发展的逻辑蕴含着三种社会制度取向;在思维模式上,初步显露出三元二分法的特点。
然而,新思想未能在大众思想中占据绝对优势。固然,封建主义思想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中已遭到致命打击;但毕竟在农业中国存在着广阔的生长环境,难以一蹴而就;知识分子群体所向往的西方民主、自由、民权、宪政,在辛亥以来的社会实践中也显得那样苍白无力:“革命数十年,议论三十载:上不能破坏旧军事组织解除军阀的武装而使封建残局孳乳延长;下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而坐失了许多可以扩大兴奋的宣传运动之机会;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萦情于现成的势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帮助而不能自己,致使可以膨胀的革命潮常因而收缩。”(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汇编》第一集第二册第47页。)而一点一滴的改良、好人政府主义、废督裁兵、联省自治种种,也无法根除封建军阀势力生长的思想渊源,造就一个真正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华民国。因而各种新思想在经过了新旧思潮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无政府主义论战、社会主义论战、人生观论战以及东西文化论战等几场激烈的思想论争之后,再也激不起大众的热情;马克思主义宣传者队伍数量的弱小以及他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单薄,显然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在大众思想启蒙中征服大众。由新文化运动肇始的大众思想启蒙遂接近尾声。
三、新启蒙运动:根据地大众社会制度取向的定型和辐射
当毛泽东的红军队伍进行在乡村田园小径的时候,一天天扩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吞噬着新旧军事势力的地盘,在望不断的农家炊烟中延伸着走向新社会的具体道路。但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861~862页。)因此,在30年代,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共产党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
1936年下半年,陈伯达在《读书生活》四卷九期上发表《新哲学者的自我批评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最早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口号。随后,《现实月报》首先以“特辑”来响应和推动新启蒙运动,开始引起了普遍注意。1937年“五四”前后,张申府、吴承仕、程希孟、黄松龄、张郁光、田佩之、张友渔、吴觉先、谭培桢等名教授在北平发起了启蒙学会。张申府称:“五四所对付的问题,正是今日所应对付的问题。这个问题,经过十八年的岁月,非特未得解决,简直变本加厉。”“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不应该真只是启蒙而已,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有个真的深的认识。”(注:张申府《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汇编》第二集第六册第31页。)
陈伯达、艾思奇、胡绳、何干之等共产党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述新启蒙运动的意义、方法和内容。陈伯达说:“我们现在需要组织全民的抵抗,来挽救民族大破灭的危机。我们必须唤起全民族自我的觉醒。所以,我们这里需要自由,需要理性,需要光明需要热,需要新鲜的空气,需要奋斗,需要集体的力。我们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迷信,反对一切的愚昧政策。这就是我们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我们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注: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等,《汇编》第二集第一册第32、34页。)
然而,国统区的“新生活运动”与陶希圣等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以及中国文化问题论战中的“尊孔读经”的读书运动与复古思潮,与新启蒙运动的文化救亡恰成鲜明的对照。陶希圣认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反对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反对封建主义。一场大战,打个不休。但是,封建主义抹杀了现在。资本主义和一派社会主义抹杀了中国”。因此,“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注:陶希圣《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汇编》第二集第六册第74~75页。)与此相呼应,陈立夫也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讲坛上大谈“读书运动与民族复兴”。实际上,他们的宣传乃是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与“尊孔”、“读经”的继续,客观上又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王道复古”论一道,起着阻碍大众启蒙的作用。
更有甚者,北平师范大学物理系杨立奎通电全国,声讨组织启蒙学会的“文化教育界败类”张申府等“诋毁忠孝节义”、“蛊惑青年”,号召民众“全力铲除此灭伦丧德之枭獐”,(注:何干之《新启蒙运动的争战》,《汇编》第二集第六册第25页。)从新启蒙运动一开始就对它发起了进攻。
但是,文化界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党知识分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结成了文化同盟,继承“五四”时代精神,对中国大众作深入的再启蒙。在抗战的炮火中,新启蒙运动更明确地把握和推进了“五四”以来弘扬的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的方向。知识分子开始检讨过去的文化运动,开始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冲出来,喊出了“大众文化”的口号。抗日战争的客观环境使得文化生活深入到内地、接触到农村成为可能,因而新文化开始真正面对大众,走进大众,成为大众思想启蒙的精神力量。
在大众思想启蒙中,马克思主义者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政治环境,创作出了《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社会学大纲》、《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大众化哲学著作。他们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种不变的教条,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它,用实际斗争的经验去充实它,并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系统地普及于一般的群众,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伟大的群众化的革命理论”(注:梁平《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汇编》第二集第一册第57页。)。在大众思想启蒙中,根据地的农民、土兵和知识分子,以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规模和精神面貌投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洪流。也正因为这种启蒙,才使得农民大众最大程度地参加了中国革命,使大众的社会制度取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指向合二为一。在战争洪流中,根据地大众的社会制度取向进一步向广大的解放区农村大众辐射,成为中国农村大众不可逆转的社会制度取向。
毛泽东曾豪迈地宣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 2 版, 第1467页。)
这是对大众思想启蒙成果的总结,同时也反映了大众社会制度取向的期待。这种期待,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思想文化基础。
标签:封建主义论文; 法国启蒙运动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中苏论战论文; 新青年论文; 三元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