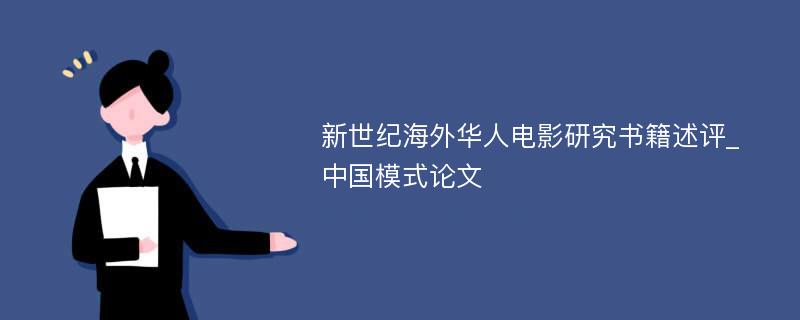
新世纪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电影论文,书评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期的“新世纪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栏目介绍近年出版的三部英文学术专著,按电影史的顺序排列,依次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过渡时期(裴开瑞)、新时期初到90年代末电影体制的改革及影响(朱影)、全球化时代华语地区的电影发行及盗版问题(王淑珍)。三部著作都强调电影文本研究以外的体制、工业及市场的重要性,也在理论概念和方法论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探索。这里我先做个点评,然后简单概括另一篇近年研究盗版的学术文章,作为电影工业研究的参照。
裴开瑞的著作虽然以“后社会主义”为题,但他有意不愿具体定义“后社会主义”,其原因是他对电影研究在方法论上新的理解。我已经另外撰文介绍海外学者对“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不同诠释,这里就不重复。裴开瑞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提醒大家,电影作为特殊的艺术形式,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双向”——我认为应该是“多向”——的话语关系。电影不仅仅单向、机械地“反映”现实,更通过其特殊的艺术方式,一方面反思历史、构造现实,另一方面想象、甚至“预测”未来。电影因此不仅仅表达某种政治“主张”(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①,因为即便说教模式的电影在表达主张(事先确定的显文本)的同时,也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表现了其他的意图(比如似是而非或相互矛盾的潜文本等)。裴开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1976—1981年定为中国电影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开端,虽然其他学者(比如德里克与张旭东)似乎更倾向将90年代的“后新时期”定为“后社会主义”的主导时期②。
从方法论角度看,朱影著作的贡献在于她强烈的工业研究意识。如果说裴开瑞重视的是电影的话语机构(即电影文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朱影强调的则是政治经济体系本身的转型及其对电影文化的显著影响,二者重点相当不同。换言之,裴开瑞关心的是电影如何超越现实、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而朱影则证明政治经济体系如何制约、进而改变艺术风格和制作法式。当然,二者都以中国电影本身为重点,从本土的立场出发提出电影研究的议题。朱影详细描述的改革过程国内同行们都亲身经历过,但她的“文化冷战”一说,她对“文化身份”的定义等,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90年代的“后新潮”(post-Wave)电影不一定都以商业市场为终极目的,因为近年一些依然“新潮”的独立电影针对的是海外的艺术市场(电影节等),而这一市场并没有完全纳入政府的机制改革的视野(这点因此与台湾电影不同)。应该注意,“市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多元性。
多元的市场在王淑珍的著作中表现得最突出:市场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更可以是本土的,问题是,这些市场在当今资本、资源(包括人才)高速流动的格局中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王淑珍的英文书名Framing Piracy中的“framing”一词多义:可以指“框架定位”,又可以指“栽赃陷害”。盗版是否“无辜”并不是王淑珍想要讨论的问题,但盗版是流动的,难以固定加框定位,所以英文用“framing”而不用“frame”,我们这里选用“追踪定位盗版”来表达一种持续的学术关注。王淑珍的研究框架来自社会科学,其“科学性”表现在资料的收集和分类,而不在于对盗版现象的纯理论解读,虽然她还是简要介绍了许多社会理论和传媒研究成果(如吉登斯[Giddens]等)。这里我提一个建议:如果将王淑珍书中的部分章节译成中文,应该有助于国内学界对海外媒体产业研究方法的了解。
最后举这三本书之外的一个理论解读盗版现象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考虑问题的不同角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论。彭丽君在2004年发表一篇题为《盗版/隐私:中国电影与集体性的绝望》的文章,旨在探讨全球与国家的冲突在盗版问题上的表现③。她认为国家和电影工业控制盗版的无能,说明国家已经成为自己开放政策的牺牲者:盗版一方面让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娱乐内容失去控制、在税收上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又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谴责中国无视知识产权、纵容盗版泛滥。她还认为,盗版并没有给消费者带来“民主”与“均等”,因为盗版的背后仍然是跨国资本在操纵,虽然这不再是好莱坞资本。彭丽君这里濒于“绝望”(despair,见其标题)的结论,与贾樟柯对VCD和DV的“民主”作用的呼吁截然相反④。如果说贾樟柯过高期待消费者(自然通过盗版)对世界影像资源索取一种民主性的享受权利,彭丽君则过低估计广大消费者的选择和接受能力,以为他们只喜欢好莱坞和香港的娱乐片,只认同电视连续剧中的达官显贵,而不曾或不懂得欣赏欧美的艺术片(这些“经典”同样流传于盗版市场)。彭丽君对“集体性”(collectivity)——尤其是“中国性”(Chineseness)——的质疑,既表现了文化研究界对资本与国家的批判意识,也透露了精英理论对消费大众的缺乏信任。这样,彭丽君对盗版的研究基本上只停留在理论阐释的层面,属于一家独言。
相比之下,王淑珍则实地追踪了盗版的流通途径,查寻资本的运转,访谈了影像产品的发行商和消费者,记录了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声音,为盗版现象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虽然她没有拘泥于某一套理论体系,但是她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参考数据和最新的理论观点,也为中国电影的工业研究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裴开瑞:《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后社会主义电影: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纽约:劳特里兹,2004),243页。(Chris Berry.Postsocialist Cinema in Post-Mao China: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Routledge,2004.)
本书主要研究中国电影如何从1949—1976年间的说教模式,过渡到1976—1981年色彩纷呈的局面。作者裴开瑞以“后社会主义电影”来指称1976年后出现的电影。裴开瑞详细而引人入胜地研究了这两个时段电影的主题、人物、观众、技巧、叙事,并分析了其结构特点,比如主观性闪回的使用。裴开瑞对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多贡献,其中之一是,他认为,不能说在某个时间点,或随着某部电影的出现,经典说教影片即变成后社会主义电影。他不认为这一变化是简单的二元回归。他相信,后社会主义电影的出现,应该说是一种渐进、过渡或变异,这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在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电影界发生了剧烈、全面或迅速的变化。
在此书“前言”部分,裴开瑞说,1976年后的中国电影,从电影这一角度构建了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文化,因此反映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变化。裴开瑞充分意识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电影的恢复与变革时期。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断说,这些变化“是在整个社会、文化领域发生的前所未有而持续的根本变化——即后社会主义——在电影上的最初体现。而且,这些变化之间彼此关联不大,说明后社会主义是一个分散的现象,逐渐在社会—文化领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零星出现”(4—5页)。裴开瑞点明,后社会主义电影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电影史话语,而非电影美学。后社会主义的电影话语,牵涉到重新协商(renegotiation)“民主集中制以及[电影]独立自主的程度”(10页)。这一关系也是双向的,因为电影话语在其社会和文化形成过程中,也影响了社会:最明显的就是当中国的电影话语被认为“超前或超出了政治话语界限的时候”(21页)。
此后各章内容如下。第2章在全书中篇幅最长,分析了1949—1979年电影的观众接受情况、作为社会体制的电影业,以及说教的叙述模式。本章分析的重要影片有《桥》、《永不消逝的电波》、《李双双》、《女篮五号》、《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第3章分析当后社会主义电影进入禁区,从负面刻画党内问题、揭露文化伤痕时,采取何种叙事结构。第4章集中考察电影叙事中英雄角色的衰落,分析了人物角色的变迁。第5章研究了关于爱情的叙事。第6章(最后一章)详细分析了受到批评的《苦恋》。在这些章节中,裴开瑞讨论到的1976年后的电影主要包括:《天云山传奇》、《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但愿人长久》、《螺旋》、《庐山恋》、《苦恋》。全书最后的“后记”,裴开瑞从学术写作、主体性、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电影等方面,为自己的研究定位。
就此书对电影本身的分析而言,裴开瑞会谨慎避开阐释方面的陷阱,比如说“电影主张了什么”。他清楚意识到,电影跟小说一样,不是用这种语言形式来传达,而更用形象来传达,所以永不能将其缩减为一个“主张”(statement)。裴开瑞对每部电影的分析,都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深入把握,以及他所说的“电影的具体性”。就本书而言,裴的方法是将电影置于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讨论(包括发行、放映、观众、报刊评论),以说明后社会主义电影与此前影片不同的潜力。因此,裴开瑞的研究方法就不只分析电影的风格、内容、人物/叙事再现,还考虑到电影的构图、建构等等。
在讨论每部电影前,裴开瑞都首先提供一个详尽的历史和理论框架。他把自己的分析建筑在对中西电影理论、政治历史的全面了解上。因此裴开瑞对每部电影的分析都详尽而清楚,文字读来流畅而富于启发性。因为采取了这种方式,裴开瑞显然成功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那就是“为一个更大问题做贡献,即勾勒出电影与各种现代性力量以及东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157页)。任何电影爱好者和学者,只要其“认为自己在以某种方式抵制着现代性的压迫性趋势和结构(无论其形式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57页)——对他们来说,这都将是一本好书。
总的来说,裴开瑞的一个目标就是达成一种恰当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在书中占有核心位置。在每个环节,裴开瑞都会解释自己的理论选择。这些内容特别引人入胜、富有效果。因而,从反面来说,裴开瑞对后社会主义电影的讨论,就似乎更像是本书的附庸,而非核心。这也许是因为本书是基于裴开瑞80年代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所做的博士论文,其内容后来已经在很多著作中澄清过了,比如:尼克·布朗(Nick Browne)等人主编的《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政治》(New Chinese Cinemas:Forms,Identities,Politics,1996);张旭东的《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中国新电影》(Chinese Modem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Cultural Fever,Avant- Garde Fiction,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1997);吕彤林(音译)的《在台湾与大陆中国的电影中面对现代性》(Confronting Modemity in the Cinema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2001),等等。
举例说,从此书第三章即可明显看出方法论所占的显要位置。此章题为“进入禁区,揭露伤痕”。这一章开篇以大量篇幅讨论历史细节,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人帮”被逮捕、邓小平的复出。这些信息提供了一个背景,以更好理解70年代后期决定电影的商业和政治体制的各种因素。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影人或者选择将自己的电影与文革区分开来,或者选择与文革接轨。除分析历史背景、政治局势外,裴开瑞还分析了《天云山传奇》等电影。这些电影表现出“尽管‘四人帮’1976年倒台,过去凭不正当手段爬上来的掌权者,仍阻挠着正义的实现”(97页)。这种分析方法让读者深入了解到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电影如何与历史时代及相关物质条件交织、纠缠。
因此,虽然此书的研究方法似乎比其分析结论更引人注目,总的来说,裴开瑞选择的方法论提升了全书的价值。可以认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后社会主义电影》的全面研究方法,会为未来的中国电影研究设定一个标准。此书凭其令人信服的理论、直截了当的风格、所剖析问题的重要性,为中国电影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韦杰生(James Wicks)、秦立彦
朱影:《改革时期的中国电影:一个聪明的系统》(美国:普拉杰,2003),230页(Ying Zhu:Chinese Cinema During the Era of Reform:The Ingenuity of the System.Westport,CT:Praeger,2003.)
随着研究“中国内地电影”这一文化现象的中西文著作大量问世,对近2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电影和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张元)的关注,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很多著作都集中于影人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所谓对立,常常把影人看成“反叛的电影作者”,抵制着国家掌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组学术著作则强调非西方的文化特色的价值,批评这些导演,说其显然在迎合海外趣味和海外资本。在这些我们熟知的领域,朱影的著作及时介入,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前提:引起轰动效果的中国内地电影,并非反映了颠覆性,也非“东方主义”的自我民俗化。有些政治和经济措施,旨在创造可行的中国文化产业,内地电影一直是这些措施的一个有机部分。朱影分析了“在后毛泽东时代,从说教到艺术到商业的过渡过程中,大陆电影的生成机制”(2页)。她把大陆电影的风格变化,看成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努力将社会现代化/市场化,同时,在与全球资本进行竞争的过程中,对“中国”的表现与身份的生产,维持垄断地位。
根本而言,这是一部国族别电影研究,但它不是把“国族”(nation)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描述范畴,而是力图澄清,1976年后的中国,在国家政策、文化讨论、电影生产制度等层面,如何不断重新发明“国族”的意义(这是一个复杂过程)。生产中国“艺术浪潮”电影的影人,虽然所拍的影片在国内不受欢迎,却是自愿参与了支持现代化这一“文化与意识形态现象”(65页)。他们的形式主义话语,与国家经济改革的语言有很多共通之处。虽然电影制片厂仍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力量相分离,但影人努力呈现一种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寓言,表达的是主流的思维模式,很吻合“非政治的艺术”的定义。朱影认为,80年代后期,由于缺乏票房成绩和国内资本(而不是因为反政府的情绪),很多新的电影作者到中国内地以外寻找制片人和投资人,形成了第五代导演在国际观众中的重要地位。
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电影业内已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再加上新兴起“与西方进行文化冷战”(95页)的思想和政治话语,这再一次吸纳了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等著名导演人才,使其投入到建构一个中国的、有群众基础的大众娱乐形式中来,以期抵抗好莱坞不断的文化入侵。大众传媒工具纵向整合,消费主义社会行为占上风。电影功能的这一变化,说明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朱影认为,人们“发现‘文化’是一个可积累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场所”(102页),结果出现了一种“后新潮”的新型电影风格, 其主要特点就是对市场力量的敏感。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片曾试图以民族斗争的名义,号召不断进行群众运动,以把中国群众团结起来。而90年代的娱乐电影,则把对国家、民族意向的再现,与休闲消费这一大众运动融合起来。朱影澄清了为何电影功能会出现这一差异(这一差异并非是绝对的)。她表明,在国家、产业、导演的共同推进下,电影朝以市场为基础的大众文化转变,这对中国内地电影的风格变化来说,仍能提供一些最有力的解释。
因此,本书为1976年后电影生产的重新分期,提供了大量证据,即按照电影生产的制度变化、政治经济结构变化来分期。此书强调中国国内产业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认为这是宏观的“生成机制”,使得大部分当代中国电影都明确属于商业娱乐形式。此书像王爱华(Aihwa Ong)(1999)的著作一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因为它从理论角度,把“民族文化”(或民族电影)作为本土当局的一种策略,以与跨国资本主义争夺人力和物质资源。该书的主要缺点,就是它常常认为,中国内地电影及文化的意义,即在于只是反映了现今大陆内部的制度性改革。朱影自己也曾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电影生产与现在进行比较。这样说来,有证据表明,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时间(包括殖民主义)依然存在,也丢削弱了朱影的理论立场。虽然如此,朝制度化的“再现模式”转变,这一说法仍然令人信服,为以后探索社会形式、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更正了人们对几个最著名中国导演的先入之见。
蒋迈(Matthew Johnson)、秦立彦
王淑珍:《追踪定位盗版:大中华格局里的全球化与电影发行》(美国:罗洛曼与里特菲尔,2003),215页(Shu-jen Wang:Framing Piracy:Globalization and Film Distribution in Greater China.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
王淑珍的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调查好莱坞影片在大中华地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发行的历史语境,以及中国内地、中国台湾相继加入WTO后的电影发行及其经济意义。第二部分提供7个个案分析,包括中国内地的电影发行与盗版,台湾地区的电影发行与盗版,香港地区的发行、盗版、平行进口情况。摘自第6章“中国内地的电影盗版”的这段话很能代表该书的风格:
虽然本书研究的是中国的电影盗版,但不能将问题孤立开来,只从中国内部看待。若不研究国内与跨国之间的多级别、多层次的流动,将是严重失误。盗版商品可以在全球如此高速、高效地流动,这说明了盗版者具备的网络能力。中国的盗版是在极为复杂的市场丛中运作的,各种网络在此交叉、互动。本节将研究并讨论中国国内、中国周围极为流动、灵活的盗版网络问题(84页)。
上面这段引文在很多方面都能代表全书的风格。一方面,王的一些说法显得过于简单——比如,不用说,外行人也明白,中国的复杂盗版问题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人人都知道盗版商品流动速度很快。因此,在这个有价值的题目上,王的文字流于表面。而另一方面,这段引文后的个案分析,则是深入、丰富、引人入胜的。全书均是如此。一些总结性话语——如“数字化消除了距离”(9页)——是尽人皆知的。但王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模式,来分析大中国地区的电影发行和全球化。尤其是王的很多个案研究,对学界的讨论来说,都是重要贡献。
王是这样寻找一个理论模式来研究电影发行。她不希望局限于预设的,或结果可以预期的框架,而是想采用一种能容纳变化的灵活方法。这方面研究必须考虑到“资本与知识产权产品的跨地区流动”,以及在“无规范、无规则的环境”中运作的盗版贸易的结构(16页)。对此而言,她的整合式方法虽然未必不可或缺,却是实用的。王提出的理论模式,能考虑到过程、关系、时空具体性,以及举凡出现的关节点。这一理论模式总的来说避开全局性以及历史/时代必然性的框架。在王的这一模式内,读者对全球电影发行和盗版整个过程内的某些具体关节点,会增进了解,而不是对电影发行和盗版这一多方面问题的全局有所把握。
可以说,王对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即在其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内容详尽,读来也趣味横生。写得最好、最引人入胜的个案研究是第7章:“台湾的电影发行”。在这一章中,王分析了台湾的电影史、电影产业、重要政策、独立发行商和主要电影发行商,以及美国与台湾的双边关系。王的分析方法是把大量资料梳理成清晰流畅的丰富内容。此章之后是对台湾Mata娱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Wolf Chen的访谈。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次访谈都为前面的讨论提供了有趣的补充和细节。总的来说,王在全书中始终把访谈和实地调查作为自己方法的一部分。 她访问的对象包括中国内地普通的VCD购买者以及电影业中的商人,以求聚焦电影发行过程中的具体环节。
虽然有这些优点,但此书还可作一些改进。就较小方面来说,此书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每一章都重复其理论框架,以及前面说过的不言自明的道理。此书这样撰写也许是为便于分成多部分出版。但这种格式令人难以一直读下去。不消说,反复陈说只是让讨论停在原地,而不是让读者对问题有更好的理解。再回到其理论模式。王写道:“多种方法的策略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单种方法能获取更多有效结果”(193页)。这可以解释王为什么访问了很多购买盗版VCD的上海市民,也可以解释她在“重新定位版权的语境”一节中,为什么采用图书馆/档案研究法,来阐明版权工业与全球贸易之间的明显联系。但最终读者不免会问:访谈方法,可否有助于版权工业的讨论;而档案研究法,可否澄清上海购买者的需求?简言之,选择使用每种具体方法时,或在某个问题上使用多种方法时,也许应进一步说明其理由。结果是,虽然此书也许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还要经过进一步测验,经受更严格的分析,读者才能完全接受。
王是否支持盗版?王是否更偏爱本土电影业,而不是好莱坞的进口商品?王是否支持2002年5月4日的台湾学生运动(该运动集体谴责台湾当局遵守美国和全球的版权法)?这些问题,王都没有回答。从书名可以看出,此书更关心的是为学术讨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而非阐释个人观点。王的框架是清楚的:盗版是一个复杂现象,植根于历史的物质因素中,并涉及很多方面的人士。而且,随着规则的变化,随着资本和盗版商品继续以惊人速度流动着,各方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
读过此书,令我们回想起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发行史,包括1948年的派拉蒙条例,以及版权在美国及海外地区的历史及其利润。我们也会了解VCD在亚洲的制造和传播。此外,读者会更明白,为什么好莱坞大片开始缩短发行“窗口”(windowing)的时间(即电影放映到录像产品的次序间隔),以减少盗版。关于外国市场对好莱坞电影收入的重要性,读者还可获得数据资料。因此,任何关注全球化和亚洲电影发行的人,都应注意这本书。因为它的研究(包括很多图表列举的经济和数据资料)是系统而深入的。总的来说,此书为这一重要问题成功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
韦杰生(James Wicks)、秦立彦
注释:
① “主张”一说,见Paul Pickowicz,“Popular Cinema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Mao China:Reflections on Official Pronouncements,Film,and the Film Audience,”in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and Paul Pickowicz,eds.,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Boulder:Westview,1989),39.
②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ed.,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
③ Laikwan Pang,“Piracy/Privacy:The Despair of Cinema and Collectivity in China,”Boundary 31.3(2004):101—124.
④ 贾樟柯.有了VCD和数码摄像机以后,《一个人的影像:DV完全手册》,张献民,张亚璇合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