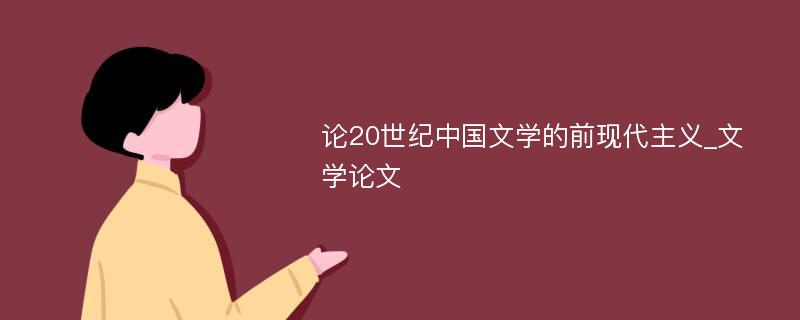
试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试论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分期,1840年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开端,而1919年五四运动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端。这种文学史分期是与中国历史的近现代分期相一致的。这种文学史分期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已经获得了现代性。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分期问题,而且也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性质的一种判断。对于这个问题,我与宋剑华先生曾经著文《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①]加以探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前文未及充分展开;尤其是袭用了传统的近代与现代概念,得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是近代文学的结论,而实质上这是一个前现代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展开,以期深化这场讨论。
首先,对现行的近代与现代划分本身作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西方没有近代和现代之分,在英文中近代与现代是一个词modern,它指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阶段,只是受苏联历史观的影响,翻译成中文时往往根据年代远近分别译作近代或现代。近代与现代之分始于苏联,后推广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方面按照西方历史分期,把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称作Новое Время(新时代),中文译作近代,同时又把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划出来,称作НовейщееВремя(最新时代),中文译作现代。苏联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因而НовейщееВремя即现代是比НовеоеВремя即近代(资本主义时代)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可见近代与现代划分是依据一种意识形态标准,而不是依据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尤其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因而并不适用于社会历史划分,更不适用于文学史划分。而且,这种历史分期并未获得世界公认,现在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采用这种历史分期。中国追随苏联,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近现代分界点,依然依据意识形态标准,即认为五四运动作为十月革命的反响,传播了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这种历史分期也应用于文学史,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被称作中国近代文学史,而五四运动以后被称作中国现代文学史。
现行的文学史分期,其不合理性是明显的。首先,出现了近代文学史太短的问题。从1840年到1919年,近代文学史仅有不足80年,作为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历史阶段,未免过于短暂了。欧洲近代文学史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长达四五百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欧洲近代文学史产生了众多文学大师、经典作品和思潮流派,因而完全可以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鼎足而立。而中国的近代文学史则形同虚设,很少文学实绩,没有出现足可称道的文学大师、经典作品,也没有产生重要的思潮流派,根本不能与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学相比肩,也难以与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并立,不能作为独立的文学史阶段而存在。总之,近代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划分不仅没有科学依据,也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是迎合苏联历史观的产物。
现行文学史分期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它预设了五四以后文学的现代性,掩盖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从而排除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问题。按照苏联历史分期的意识形态标准,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现代史,而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仍处于近代。对于文学史而言只有社会主义文学才具有现代性,而同时代其他文学则只能看作是腐朽没落文化,还没有资格进入“现代”(最新时代),这显然是荒谬的,不符合世界文学发展的实际。在苏联历史观影响下,中国文学史对五四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流派给以否定性评价,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遭到贬低和抹煞。同时,对于国外现代主义也予以排斥,国内当代文学中出现的现代主义倾向也被剥夺了合法性。因此,可以说苏联的历史观歪曲了中国文学史,也造成了中国文学长期封闭落后状态。
文学史分期的意识形态屏障使中国文学孤立于世界文学体系之外,与世界文学脱节,并且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这种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深深记取。现在,我们必须抛弃文学史分期的意识形态标准,科学地确定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扫清障碍。
现行的近代与现代分期虽然源于苏联的意识形态标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分期标准在实践中已经被悄悄地修正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分,因而又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一笔抹煞。实际上,现在国内史学界和整个理论界已经把现代概念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论断联系起来,认为20世纪或一次大战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近代)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现代),这种分期与以十月革命为界的分期大体相合,但其内容已经根本不同,它不是把意识形态(革命)而是把社会(主要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水平作为划分标准,从而现代史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且适用于整个世界。
如果依据这种修正了的近代与现代划分标准,现行中国文学史分期也不合理,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属于现代史,而只能属于近代史。中国社会在20世纪前半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通行的说法,科学的说法应当是半封建半官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落后,工业化还刚刚起步,资本主义只有初步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仍处于支配地位,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这一时期显然还处于前现代阶段,或者说是近代史。20世纪下半叶,也仍然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而且市场经济被取消,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还没有成熟、完善,现代化步伐也刚刚迈出,距离现代社会还有很长的路程。也就是说,按照近代与现代划分标准,中国还没有走出近代,进入现代。在这种社会发展阶段,文学也不可能是现代性质的,而只能是近代性质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只能是近代史而不是现代史。
如果具体地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此起彼伏的文学主潮都是近代文学思潮而非现代文学思潮。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学处于封闭状态,没有与世界文学相交流,它也一直停留于古典主义。只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打破封闭,与世界文学融汇交流,并引进外来文学思潮,打破古典主义。五四引进的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无异属于近代文学思潮,而非现代文学思潮。同时,对于当时勃兴的欧洲现代主义则采取了搁置一边,留待以后引进的态度。文学研究会在其宣言中指出:“写实主义文学,最近已见衰歇之象,就世界之立点而言,似乎已经不应多为介绍;然就国内文学界情形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以为进一层之预备。”[②]对现实主义之接受,对现代主义(即“非写实的文学”)之搁置,正是由于中国文学发展之前现代性所致。
五四文学革命被革命文学取代,文学思潮发生剧变,苏联文学思潮取代西方文学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取代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成为主潮。苏联文学思潮属于什么性质呢?虽然它仍源于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但已经向新古典主义蜕化。它对意识形态性的强调以及“典型化”规范的建立,表明其新古典主义性质。新古典主义是欧洲17世纪文学思潮,它尊崇理性,讲求规范,矫饰现实,以适应巩固王权的政治需要。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19世纪现实主义采取批判态度,指责其缺乏理想性,只有片面的批判性;只强调真实性,忽略了意识形态性。它实质上采用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化和规范化原则,矫饰现实,从而适应了计划经济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需要。解放前中国革命文学接受了苏联现实主义思潮,使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变体)带有理性化、规范化色彩,但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毕竟保留了现实主义精神,不能与新古典主义相提并论。建国以后,由于“左”的文学思想影响,文学走上了粉饰现实的道路,新古典主义色彩越来越浓,至1958年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更突出地以理想性(被理解为浪漫主义精神)来矫饰现实,遂使现实主义完全蜕化为新古典主义,直至“文革”中恶性发展为“三突出”等样板戏原则,现实主义精神丧失殆尽,演变为伪古典主义。可见,五四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文学主潮不仅没有走向现代,反而后退了。
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并恢复五四现实主义传统,从而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仍未摆脱近代性(前现代性)。80年代后期,产生了现代主义因素和流派,但并未成为主潮。这种倾向延续至90年代,现代主义因素有所发展,非理性倾向出现,但现实主义仍占主流,现代主义尚不成熟,未居主导地位,这表明,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并未走出近代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史尚未展开。
到此为止,我们仍然采用传统的近代与现代划分来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由于近代与现代划分并未被世界所公认,因此关于近代性的提法就成为问题,而这场讨论的前提应当加以审查。笔者以为,更好的作法是,不使用近代性概念,而以前现代性概念代替之,这样,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问题就转换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问题,从而避免了概念混乱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国外史学界把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称作现代,而现代概念的核心是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这两个问题正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只是它还没有被文学界所关注。关于现代化或现代性问题众说纷纭,未有定说,但大体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因而可以在一定意义上作出界说。所谓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它指工业革命以来的对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而工业化则成为现代化的基础,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结构、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的变革。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领域的概念,它指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理性精神,包括工具理性(科学)和人文精神(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在这种理性精神驱动下,人类文明才发生了反传统的变革,从而走出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两个概念从社会和文化两个层面阐释了现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学的现代性(这是判明现代文学的标志)是什么?社会进入现代史,并不意味着文学获得了现代性,进入了现代史。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不平衡、不同步,因而文学现代性的获得要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二是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二者性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按照传统的文学观,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那么,就会得出结论,社会现代化就会使文学获得现代性,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也成为文学现代性的内容。这样,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的文学,还是20世纪中国文学,都可以称作现代文学,因为它们都拥有了理性,从而也获得了现代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文学并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不是现实的某种再现,而是对现实的超越,它包含着对现实及现实观念(意识形态)的审美批判。因此,现代文学或文学的现代性不是对现代理性精神的肯定和表现,而是对理性的批判、否定。现代化和现代性固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异化,技术对人的统治,理性对自由的束缚,越来越难以忍受。如果说在现代化初期理性的负面影响还不明显,因而尚未成为文学批判的对象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化的完成,理性则成为人类自由的桎梏,而文学也把抗议理性的压迫作为自己的主题。这就是说,由于对理性(现代性)的抗议,文学才获得了现代性,才有了现代文学。
现代化初期,文学尚未反抗理性,反而呼唤理性,因而直至19世纪,文学并末获得现代性。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以理性反抗宗教非理性,以感性自然对抗宗教禁欲主义,人文主义成为文学的旗帜。新古典主义强化了理性规范,以理性抑制感性。启蒙文学以个体自由的理性精神为武器,反抗传统社会。这表明,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仍在呼吁现代化、现代性,而未开始批判现代化、现代性,因而也远没有获得现代性。浪漫主义文学开始反抗现代化和理性的桎梏,诉诸精神的自由,但它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走向非理性,它所追求的自由仍然是一种理性精神。现实主义更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现代化(工业化)带来的贫困、堕落,并企图以人道主义来加以疗救,这说明它仍然以理性为批判的武器,并没有放弃理性信念,并且还没有根本上否定现代化和现代性。
文学现代性的获得属于20世纪文学。此时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成熟,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向后工业社会转化。工业化带来的弊病突出显现,理性万能的神话也已破灭,人的非理性本质被发现(弗洛伊德)。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它以非理性精神对抗理性,抗议现代性,控诉现代化带来的异化。这就是说,现代主义开始,文学自觉地批判现代性(理性),从而获得了文学的现代性。因此,现代主义成为现代文学的代表,现代文学史也从此才真正开始。
反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并没有获得现代性。五四前曾经发生了由梁启超等人发动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三大革命旨在借助西方文学思想来更新、重振中国文学,但这种努力失败了,它没有扭转中国文学的颓势。于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引进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思想和19世纪文学思潮,取代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五四文学革命高举起科学、民主、个性解放的旗帜,这正是现代理性精神。五四文学革命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语)为样板,企图通过对国民性之改造,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都在这种理性精神照耀下,因而中国的浪漫主义缺少欧洲浪漫主义的神秘主义、颓废精神和反判性,中国的现实主义也较之欧洲现实主义更多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没有发展为自然主义。这就是说,五四文学还没有摆脱理性,还没有批判现代性,反而追求、肯定现代性,因而没有获得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如此,欧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中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则旨在反封建,呼唤资本主义现代化,这种时差更表明中国文学现代发展的滞后。
五四以后,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取代西方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成为主流,理性化倾向进一步加强,政治理性取代人文理性,阶级意识取代个性精神,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在政治理性桎梏下,中国文学更远离现代性。其间也有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因素、流派出现,但并未获得成熟、发展,更未成为主流。在主流文学和政治理性的强大威力下,在抗日战争形势下,现代主义逐渐消亡,其代表人物回归主流文学。综观这一段文学史,理性主义统治强固、长久,文学被拒之于现代发展的门外。
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政治理性的统治,又重新举起人道主义旗帜,反思历史、批判现实,闪耀着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出现了非理性思潮,王朔作品、贾平凹的《废都》和新写实小说,抛弃了理想主义,消解了理性信念,甚至对流行价值一概踏倒在地。这表明中国文学开始告别理性精神,对姗姗来迟的现代化也采取了批判立场。但是,这种非理性倾向并未成为主导倾向,理性精神仍居主导地位,现代文学的脚步声已经迫近,但还没有进门。
批判现代化、现代性,反抗理性是文学现代性的核心。同时,文学现代性还包括其他一些内容,它们也构成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任务,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因此现代文学才姗姗来迟。
第一,反传统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古代文学形成了稳固的古典传统,在欧洲文学中,古典传统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而消失,反而自文艺复兴得以恢复(因为欧洲有中世纪文学打断了古典传统),并延续至19世纪。其间在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中,古典传统得到强化。直到20世纪开始,现代主义出现,古典传统才被打破。现代主义不仅抛弃了理性精神,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完全反传统,意识流,非情节化,时空倒错,人物抽象化,荒诞风格……使文学面目全非。正是这种全面的反传统,才是文学现代性的生命力所在。
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引进欧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而不是现代主义)来反对中国古典主义传统。但是,浪漫主义尤其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并非根本对立,不仅理性精神一脉相承,而且叙述方式也相差不远,因此,五四文学反传统并未彻底,只是有限的修正。正是由于这种不彻底性,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才向传统回归。
五四文学的反传统倾向转为向传统回归,是借助苏联文学模式的确立而实现的。三十年代苏联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在左翼文学努力下在中国确立,它带有东方文化的烙印。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文学模式中国化,突出其意识形态化倾向,政治理性延续了传统文学的道德理性,新古典主义延续了古典主义传统,这种趋势直至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中国文学传统被片面地重建,因为它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而是极端地发展了其理性主义倾向。
新时期文学恢复五四传统,反对新传统文学模式(苏联文学模式的中国化),但仍然没有达到现代意义上的反传统。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反传统,现代主义虽然没有成为主潮,但它以彻底的反传统姿态打开了文学的现代之门。
第二,文学独立是现代文学的另一基本特征。古代社会人的精神需求被物质生存的迫切性抑制,因此文学作为精神生产并未独立,它更多地服务于社会现实要求,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强调其教化作用。现代社会物质生存迫切性缓解,人的精神需求得到解放,文学也摆脱意识形态桎梏,突出其非功利的审美本质。现代主义之前的欧洲文学还着重其现实功利性,而现代主义文学则直接诉诸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并且公开反叛意识形态。
五四文学革命举起了文学独立的旗帜,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创造社甚至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实际上,五四文学的独立性是有限的,它只是争取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独立,并没有拒绝所有意识形态,相反,它把文学归附于从西方引起的人文理性,并把文学当作启蒙救国的武器。“为艺术而艺术”也没有真正实行,它与欧洲唯美主义原则上不同,它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却有异曲同功之效,实际上反对文艺载封建之道,而又载上了科学、民主之道。
五四之后,文学又载上了政治之道,文学独立思想被批判、丢弃,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种倾向在抗战期间得到普遍化、强化。直至五六十年代,文学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性,终于在“文革”中沦为“全面专政”的工具,彻底丧失了审美本性。新时期文学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的信条,主张文学独立,但实际上与五四文学一样,文学仍然负载起启蒙使命,干预现实、宣传人道主义,并没有取得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独立。后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回到文学本体”的倾向,由现代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反叛,才真正开辟了文学独立的道路,但这种倾向刚刚出现,并未成为主导倾向。由此可见,20世纪文学尚未完成文学独立的任务。
第三,关注个体精神世界是现代文学的又一基本特征。古代文学关注社会问题,主题是善与恶的斗争。现代社会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问题初步解决,个体精神世界的困扰突出,因而现代文学转向关注个体精神生活,解除个体精神负担、为个体寻求生存意义成为文学基本任务。现代主义正是转变了文学的关注对象,完成了文学主题的转换。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是社会斗争,而不是个体精神自由。五四新文学争取个性从社会、家族压迫下的解放。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主题是阶级、民族的解放。三十年代前后也曾出现一些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的作家、作品,但并没有蔚为大观,后来也在抗日战争洪流中消隐、转向。解放以后文学的主题是歌颂光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文革”中文学的主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左”的思潮的批判。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出现了较多的关注个体精神世界的作品,但也仍然未成为主流。主流文学仍然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命运。这种情况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仍未完成向现代主题的转换。
第四,走向世界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另一基本特征。古代文学尚未打破民族界限,世界文学体系尚未形成。在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交往扩大,民族文学间的交流造成了文学思潮、文学思想、文学风格的吸取借鉴、融汇相通,从而形成了统一的世界文学体系。尽管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仍然存在,但封闭性已被打破,它们已经进入同一历史,同步发展。在欧美发达国家,文学已经成为超越民族界限的国际现象,现代文学是世界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在封闭条件下独立发展,只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才完全打开大门,引进欧洲文学,从而开始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开放并没有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而且并不持久。五四新文学虽然全面开放,但也限于引进19世纪文学思潮,对20世纪兴起的现代主义却搁置一旁,因而并未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没有形成共同的历史,也就是说,世界化的目标并未完全达到。五四以后,主流文学转向苏联,对西方文学采取批判态度,刚刚打开的大门又关上了一半,中国文学仍然未能赶上世界文学的步伐。这种趋势在五、六十年代进一步强化,直至“文革”对整个世界文学(包含苏联文学——被视作修正主义文学)关上大门。新时期文学重新向世界开放,但其目标是回到现实主义,而不是赶上现代文学的步伐。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开始关注国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这时才出现了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趋势。但是,要赶上现代文学步伐,还是下一个世纪的事。总之,20世纪中国文学尚未完成走向世界文学的任务。
确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性,是为了保证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我们这一个世纪已经基本上走完了前现代的路程,它崎岖坎坷、曲折迂回,也许还未达到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但却铺设了通向现代文学的道路,这是足可欣慰的。“后新时期文学”中现代性的发展,使我们坚信,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必然会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史。
注释:
① 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② 《小说月报改革宣言》,1924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