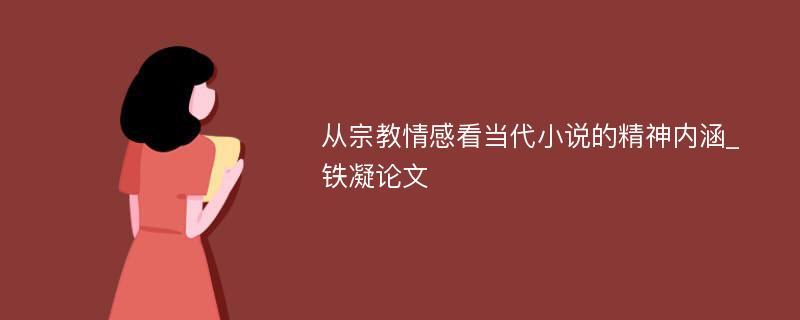
从宗教情怀看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情怀论文,内涵论文,当代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当在青烟缭绕的寺庙里看到人头攒动的景象,就想起了文学。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 否应该就是一座寺庙,读者在这座寺庙里同样也能获得某种心灵的慰藉?这使我思考起 长篇小说的宗教情怀问题。概括地说,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 程,却并没有把心灵慰藉作为一个显在的追求目标。20世纪80年代,小说基本上承担着 启蒙和拯救的社会职责,汇入到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大潮之中,其政治思想 的意义大于精神文化的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虽然小 说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拘禁,可是并没有因此而拓展精神层面,不过是顺应着市场化的潮 流,坠入了形而下的层面。回看这二十多年来的长篇小说,其精神内涵竟是如此的稀薄 和贫乏。由于精神内涵的稀薄和贫乏,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就不可能起到心灵慰藉的作 用。心灵慰藉是与宗教情怀有所关联的。逆向推理,宗教情怀的缺失是导致小说精神内 涵稀薄和贫乏的重要原因之一。
宗教对社会的观照虽然是虚幻的,但它还包含着观照人生的功能。“人生的本质问题 或核心问题乃在于对生命意义的追究,而这是一个关涉‘实体世界’的终极性问题。这 一问题乃是宗教关怀的真正领域。”(注:檀传宝:《试论对宗教信仰的社会观照与人 生观照》,引自《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宗教的人生观照所反映的正是人 类的终极需要,因而具有某种普遍性和永恒性特征。所谓宗教情怀,就是在这种终极需 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怀。宗教情怀其实是一种 很重要也很基本的文化基因,任何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都不会缺失宗教情怀这一基 本的文化基因,只不过在表现形态上各有差异而已。研究宗教史的休斯顿·史密斯认为 ,广义地说,可以把宗教界定为“环绕着一群人的终极关怀所编织成的一种生活方式” (注: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这显然是 对宗教的一种宽泛的定义。当一种生活方式关涉到终极关怀时,自然就充盈着宗教情怀 ;而这样的生活方式,就不仅仅是具备明确的物质形态的、仪式化了的宗教才能营造, 那些以强有力的思想信仰支撑的学说同样能够营造。
宗教情怀对于文学而言,它起到一种蒸发的作用,它使蕴藏在具体描写中的精神水分 化作水蒸气升腾起来,构成一种浓郁的精神氛围。我想,这就是宗教情怀所特有的超越 性。
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基本上还承担着思想启蒙的功能,体现着思想解放的时代特征, 小说的精神内涵是与激荡的社会思潮、与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 个时期听小说也渗透着一种宗教情怀,但这种宗教情怀是依附在革命信仰上面的,是一 种作了革命化处理的宗教情怀。进入90年代,可以说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欲望化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似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物质和数字来衡量,而精神价值变得可有可无,整个社会 的精神信仰极为迷茫。小说创作受其影响,作家们变得越来越实在,对具体事物的关注 超过了对精神的关注,小说的写实性得到空前的发展,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甚为流行。 物质化、欲望化、平面化是这类小说的突出特点,宗教情怀被阻隔在由物质与欲望围成 的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外。这一阶段的小说在个人化方面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个人经验的 充分表达给小说带来了丰富性,但受这一阶段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个人经验的表达多半 集中在情感或欲望的表达上,所缺少的仍然是对精神世界的体悟。总的说来,我们从这 一阶段的小说中感受到的,主要是世俗性、情欲性、物质性,我们很难从中感受到神圣 性、超越性以及空灵、飞升的境界,而后者又往往与宗教情怀相关。
凡成功的作品都是在精神内涵方面有所开掘。在解读小说的精神内涵时,我们能够感 觉到宗教情怀的脉动。在分析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时,也许可以把宗教情 怀的脉动视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因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作家是有意识 地立足于宗教文化,将宗教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这些小说固然也关涉到终极关怀和精 神追问,但它同时也把人们的思路拘束在具体宗教的教义上。我在这里要谈的还是那些 在普泛的宗教情怀的引发下对精神内涵的开掘。它的意义就在于,宗教情怀虽然起到引 发的作用,但并不是把人们的思路导入宗教的壳体内,它对人们的心灵慰藉更为纯净。 下面我想重点分析两部作品,一部是铁凝的《大浴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版) ,一部是范稳的《水乳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大浴女》:宗教情怀对俗世的超越
铁凝写于2000年的《大浴女》曾经引起人们的讨论,但人们的兴趣似乎只是由那个给 人太多诱惑和太多想象的题目所引起的。的确,“大浴女”这三个字具有充分的俗世性 ,人们由此很容易联想到色情、肉欲、暧昧、淫靡等场景,何况小说的基本情节也是非 常俗世的内容。然而,这部小说最富有精神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通过对俗世的进入,而 达到对俗世的超越。作者在对俗世的超越中表现出一种普泛的宗教情怀。铁凝曾说过, 这个小说的题目是受到塞尚的名画《大浴女》的启发。那么,铁凝从塞尚的画中读解到 的是什么呢?恰恰是超越俗世的宗教情怀。她在一本读画的书中谈到了她对塞尚的理解 。她说:“塞尚和尼采同时代,他们虽不认识,但尼采在《索罗埃斯特说教》中,形容 精神的三种变化——也可理解为三层境界,他解释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 ,最后狮又如何变成孩子时,说的简直就是塞尚。”而“能够变成孩子的狮必是达到了 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应和着宗教的和谐与超脱。所以铁凝以为塞尚的 《大浴女》“是在诗意地调和万物”,“是一幅世间万物的大谐和图”(注:铁凝:《 遥远的完美》,广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大浴女》可以说是一部忏悔小说。小说以尹小跳的自我反省为基本结构,讲述了一 个当代青年如何摆脱俗世烦恼与困惑,从而走向“内心深处的花园”的故事。尹小跳生 活的时代是一个物欲得到最充分的释放和纵容的时代。在和平与建设的理由下,物欲具 备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大浴女》充分描写出现实生活的物欲化特征,也表 现出物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俗世的眼光看,尹小跳是成功的,或者以伦理的眼光看 ,她也是完美的,但尹小跳始终处在一种自责的心理状态之中,显然这是一种试图超越 俗世的心理状态。尹小跳超越俗世的企图具体化为不断的内心忏悔,而一步一步走向更 纯净的精神境界。在尹小跳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清新的宗教情怀。这突 出表现在作者并不是以否定俗世的方式来达到超越俗世,恰恰相反,作者充分肯定了俗 世的意义。比方小说就是通过对俗世基本欲望的肯定来批判“文革”反人性的本质的。 “文革”时期,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对人的基本欲望持否定态度的,在那个政治惟上 的特殊年代,人的所有俗世需求都变成了大逆不道。但即使在政治高压下,也遏止不了 人的正常欲望的释放。苇河农场是“文革”期间发配知识分子的地方,山上有一间小屋 ,每到星期天对集体宿舍的夫妻开放,于是就在小屋前面出现了排队等候做爱的场景。 这是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这个黑色幽默继续延伸下去,作者就把最忌讳袒露个人俗世 欲望的知识分子们置于双重欲望的煎熬之下:星期天除了有山上小屋的诱惑之外,还有 苇河镇上的烧鸡,烧鸡解口腹之欲,这意味着星期天“食色”二欲都在召唤他们,要排 队做爱就没有时间去镇上买烧鸡了,二者不可兼得。尹小跳的母亲章妩就因为二者不可 兼得而生了大病。这样的情节耐人寻味。章妩的一生在不断地追求俗世的欲望,也许我 们可以把她视为一个大胆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但因此她也不得不承受俗世对她的惩罚 ,她在精神上获得一份自由的同时也获得一份折磨。她追求俗世的个人幸福并没有错, 问题是她缺乏一种自觉的宗教情怀,因而无法超越俗世,无法摆脱由此带来的精神痛苦 。在作者的笔下,尹小跳同样是一个对俗世生活充满情趣的人,这与她的母亲章妩相似 。还是中学生的尹小跳和她的两位好友悄悄地在家里尝试烹调、时装、化妆。当她们在 蜂窝煤炉上做成了烤小雪球时,激动得快要哭了,这时她们觉得所展示的“不再是小手 艺,而是大艺术”,她们屏气凝神地咀嚼自己的成果,就觉出了“生活是可以这样美” 。在那个否定俗世情趣的年代,尹小跳与她的母亲都在寻求着俗世的幸福,母女俩在这 一点上是共同的。问题是,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后,她们都面对着一个欲望化的时代,当 个人欲望的实现不再被禁止,反而变得冠冕堂皇时,母女俩的精神差异就显露出来。母 亲在反常年代追求个人的欲望,还有一种反抗精神的支撑,而到了欲望化的时代,她不 再需要为了欲望去反抗,卸下了精神支撑的武装,所以陷在俗世的精神痛苦中不能自拔 。尹小跳却有一种自我反省的勇气,这使她没有沉湎在俗世的情感之中,她始终有一种 不满足感,这种不满足感不是来自世俗的欲望,而是来自精神的召唤。
尹小跳的超越俗世的精神力量首先来自她的难以洗刷的罪孽感,这种罪孽感源于妹妹 尹小荃之死。妹妹尹小荃之死是尹小跳内心深处的一个郁结,伴随着她的精神成长。这 似乎印证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但铁凝不是一个基督徒,她也不是要借此宣谕《圣经》, 她设计这样一个贯穿尹小跳成长历程的细节,显然是要帮助自己的人物超越俗世。妹妹 尹小荃是母亲与唐医生偷情的产物,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她是恶的见证。尹小跳朦胧之 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本能地拒绝这个妹妹,她把对恶的憎恨转嫁到了尹小荃身上 。十二岁的尹小跳与七岁的尹小帆看到尹小荃朝着打开了井盖的污水井走去时,她们本 来可以及时制止,但她们只是互相拉住了手,似乎是心照不宣地,于是她们的妹妹就在 她们的眼前掉进了井里。从此,妹妹尹小荃之死就种在了尹小跳的心里,构成了类似于 原罪性质的因素,于是在她以后的生活中,当她获得俗世的成功,或当她遇到生活的困 惑,或当她面对精神的烦恼时,这个原初的罪孽感就会被激活,给她警示。铁凝在这部 小说里重点是通过尹小跳来写女性的自我反省的,而自我反省的起点就是童年时期目睹 妹妹之死的内心郁结。在我看来,铁凝设计的这个郁结比起原罪说具有更深刻的精神询 问,因为这个郁结不是一个先在的理念,它包含着血缘、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等社会性 的内容。也就是说,郁结在尹小跳内心的罪孽感,不是屈从于某种先知先觉的声音,而 是来自对社会的体验和总结。铁凝一再地暗示这一点,她写到无论是尹小帆,还是唐菲 、陈在,都有可能被视为导致尹小荃之死的参与者,这可以看作是一次社会的合谋。所 以从社会的层面,尹小跳完全可以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法性的理由。尹小跳也试图解脱 ,她曾想把这段经历从记忆中抹去,她还把这段经历看成是一种幻觉,然而随着她的成 长,她的罪孽感愈来愈明确,她就有了一种赎罪的意识和勇气,这种赎罪的意识和勇气 帮助她从俗世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尹小帆则是通过推卸责任的方式来解脱自己的。尹小 帆是与尹小跳共同面对尹小荃之死的,尹小帆就为自己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理由,所以 很轻松地就把自己解脱了,甚至她把自己想象成救人的英雄,只因为当时被身边的姐姐 拉住了才使得她未能当成英雄。尹小帆是一个没有精神负担的人,俗世的原则就是她的 最高原则,她不放过获取俗世幸福的丝毫机会,包括她夺取姐姐尹小跳的所爱,只要她 觉得这能满足她的俗世需要,她就去做,而且并不感到内疚。但我们从小说的描写中也 能看出来,追求俗世幸福的尹小帆想要得到的都得到了,她的幸福却只是停留在俗世的 层面,她的精神世界是空虚和无聊的,所以她从骨子里嫉妒姐姐尹小跳,这种嫉妒就在 于她在灵魂上的恐惧。
超越俗世是通过宽宥和理解的心态获取的。当一个人的宗教情怀十分充盈时,他就会 以一种宽宥的心态待人处世。铁凝在这部小说中写尹小跳的忏悔和反省,而这种忏悔和 反省就是通过对他人的宽宥和理解而实现的。她宽宥了玩弄她的爱情的电影明星方兢, 也宽宥了一直与她作对、与她争夺利益的尹小帆,也宽宥了失职的母亲和父亲。宽宥不 是屈从,宽宥首先必须建立在洞见之上。比如她对方兢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当她还认 识得不很清晰时,她会对方兢的失信和轻浮而痛苦,但当她认识到方兢不过是那种“在 时来运转的岁月里兜售和利用自己的苦难”的知识分子时,她释然了,她还会接受他的 邀请,去宾馆看望他,并祝愿他的生活能有美满结局,当然此时她也会严肃地拒绝他的 拥抱。尹小跳与母亲的关系也是小说的重头戏。铁凝通过这一重头戏,表现了她的“审 母”愿望,我们能从中感觉到作者对章妩的审视是相当冷峻的,也是无情的。她针对章 妩作出了这样的诘难:“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释放出母性的光辉,尽管世上的孩子 都渴望着被这光辉照耀。”但最终尹小跳还是宽宥了母亲,作者设计了一次解救母亲的 情节来表现尹小跳的宽宥。在商场里,章妩遭到无端的围攻。母亲的痛苦和无助,唤醒 了尹小跳“心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关怀和护卫的渴望”,她保护了母亲,搀扶着母亲回 家,这时候,她的感觉就是:“你的长辈就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具备这样的胸怀”。当 然,宽宥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理解之后的宽宥才是发自内心的宽宥。对本 人而言,这样的宽宥就会为自己收获一份精神的财富。《大浴女》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 :全书的主要部分描写了尹小跳的忏悔和反省的历程,这个历程使她一步步走向宽宥的 境界。小说的最后两个章节则是专门写尹小跳的解决,她一个又一个地解决了对他人的 宽宥。先有宽宥了方兢,接着宽宥了母亲;她是在得知尹小帆夺走了一直爱恋她的美国 朋友麦克后最终宽宥了尹小帆的,这场宽宥更为艰难。她本来十分激愤,但连她自己也 感到奇怪的是,她突然间就平和了下来,主动对尹小帆说我们讲和吧。我想这也许就类 似于宗教上所说的“顿悟”,这表明尹小跳经过这样的磨砺后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 。小说于是充满诗意地写道:“她拉着她自己的手往心房深处走,一路上到处是花和花 香,她终于走进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
铁凝是一位确定的无神论者,她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宗教情怀不是出于某种宗教信仰, 而是出于她内心对超世俗境界的感应,她的宗教情怀因此不会归结到宗教世界,而是归 结到人类自身。尹小跳最初郁结在内心的罪孽感就被铁凝作出了合乎人类理性的解释, 这就是小说结尾尹小跳与老省长俞大声讨论犹太人的用意。尹小跳认识到,在这个世界 上,生命最为重要,她知道,尹小荃摧毁了她“心中的庙宇圣殿”,但她为此摧毁了尹 小荃,却是更多的罪过,因为她摧毁的是一个生命。铁凝要告诉我们的是,人性比神性 更伟大。
《水乳大地》:宗教情怀对信仰的支撑
《水乳大地》是直接涉及宗教话题的作品,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澜沧江峡谷的滇 藏交界地区,这是藏文化、汉文化、东巴文化等民族文化交汇的地区,也是藏传佛教、 基督教、地方少数民族宗教以及巫术共同生存并相互影响的地区,这里有着神奇的自然 地理环境和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这里似乎是天然生长宗教大树的地方,它充满了神秘 和诡奇。小说带有丰富的宗教内容,但它与一些明确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还不一样,它 不是宣谕某种宗教教义的,也就是说,作者在这里的身份不是一个忠实的信徒,而是一 个学者,一个研究宗教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小说自然充盈着浓厚的宗教情怀, 这种宗教情怀既与小说所表现的宗教内容有关系,又不完全指向宗教本身,它仍然是植 根于作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是一种普泛的宗教情怀。
《水乳大地》算得上是一部学者小说。作者范稳一直在从事滇、藏地区的文化研究, 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到小说所写的卡瓦格博雪山和澜沧江峡谷做实地考察探险,他研究了 各种宗教的经典和历史资料,曾写过相关的学术性著作,但他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文学情 结,所以他还要试着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一部小说。显然,范稳感觉到有些东西在学术 著作中无法表达出来,这些无法在学术著作中表达的东西大概就与情感体验有关。对于 范稳来说,这种情感体验也包括着宗教情感的体验。他自述过他对这片地区的感受:“ 一些神奇、神秘甚至怪异的现象,在汉族地区可能是神奇的,没有多大说服力,但在滇 藏交界的地方,却完全是可能的。这里到处是神山、神佛、神灵,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中弥漫的就是这样一种气氛。对于民间中的一些信仰和宗教活动,如果我们轻率地将一 些神奇的东西都认定是迷信,是否过于残忍和武断了?”(注:引自《中国图书商报·书 评周刊》,2004年3月12日。)正是这里的神山、神佛、神灵,唤起了作者内心的宗教情 怀。
《水乳大地》写了滇藏地区一百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变迁,有人称其为一部史诗 性的作品,它包含的内容无疑很庞杂,但我更看重的是,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地区的变迁 表现出信仰的力量。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非常坚定地表达对信仰的敬意,这在当下 的文学创作中也许具有一种作用,因为这二十年间,在中国大地上,信仰经历了一场“ 滑铁卢”战役。极左政治曾把信仰变成一种禁锢人们灵魂的紧箍咒。随着对极左政治的 批判,人们开始质疑信仰本身的合法性,特别是人们在卸去紧箍咒之后感受到无所顾忌 的狂欢,人们似乎不愿意再受到信仰的约束。与信仰失落的社会现象相呼应,在我们的 文学作品中也难以觅见信仰的踪影。信仰失落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还有躲避崇高、英雄 隐退、道德沦丧,等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贬值的文化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的 文化背景下,《水乳大地》对信仰的召唤与讴歌,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关于信仰的重要性,我想,不需要在这篇文章里做理论上的阐释。在讨论小说的精神 内涵时,我宁肯把信仰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灵魂, 而信仰是灵魂的支柱,有了信仰我们的灵魂才会强壮起来。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时 代如果失落信仰的话,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精神危机,它将导致人们的灵魂衰竭。宗教 关乎信仰。《水乳大地》所描写的是一个多种宗教集合的地区,各种宗教因为教义的冲 突以及利益的冲突,相互间敌对、仇恨乃至杀戮,但同样因为宗教的信仰,人们有了生 存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的生命力才变得异常的顽强,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他们也能 奇迹般地延续着民族的命脉。就像上个世纪初纳西人的村庄和盐田被野贡土司强占了以 后,他们就在族长和万祥的带领下,在澜沧江边的六百尺悬崖上开出自己新的家园。问 题并不在人的这种求生的坚韧力,而在于作者聪明地借助地域文化的神奇性和神秘性, 渲染信仰的力量。野贡土司是崇尚武力的,他可以凭着强大的武力夺占纳西人的盐田, 但他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滂沱大雨带来澜沧江的洪水,洪水将江边所有的盐田荡涤一 空。令让迥活佛担忧的是,野贡土司一代比一代贪婪,连神灵都不屑敬畏,果然魔鬼就 毫不客气地用死亡的阴影席卷整条峡谷。作者在小心翼翼地触及各种宗教信仰的矛盾冲 突的历史时,似乎要给我们梳理出这样一条清晰的思路,这条峡谷里一百年间反反复复 的斗争,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导致的,而是藏在信仰背后的人的贪婪和利 欲,贪婪和利欲不仅造成了抢占盐田的流血,也造成了政治上的劫难。直到上个世纪80 年代,当和平与建设的时代之风也吹拂进这条峡谷时,从北京的神学院学成归来的安多 德神父才鼓起勇气说,魔鬼已经被打败了,胜利属于有信仰的人。
范稳在写作中始终把握住一点,他不是对宗教信仰的具体内涵感兴趣,而是要揭示宗 教信仰在人生观照上的巨大作用。在作者看来,关于来世现世、此岸彼岸,关于天堂地 狱,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信仰,有了信仰才会有生活的原则,才会有对生命 的关爱。他塑造了好些宗教人物,比如沙利士神父、让迥活佛、凯瑟琳修女,与其说他 们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还不如说他们是洞见人生哲理的智者,他们所做的工作也是拯救 人的灵魂。在60、70年代的政治劫难中,峡谷里的所有寺庙、教堂都被摧毁,让迥活佛 也成了牛鬼蛇神,他当不了活佛还可以去当藏医,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医术高明的扎西门 巴。可是当政治劫难过去后,他拿出行医多年的积蓄,买了木料、水泥和砖,要在噶丹 寺的废墟上重建寺庙,他说:“治病只能救人一世,而医治人的灵魂,却能救人生生世 世。还是让我们藏族人梦里的东西实在一点罢。”
范稳不仅写了宗教信仰,还写了革命信仰。革命信仰在科学理论烛照之下,应该对人 生的观照更为深邃,对生命的追问更为彻底。共产党员应该是由革命信仰武装起来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范稳着力塑造的 副专员木学文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当然,范稳主要的笔墨是写木学文如何正 确地执行了党的宗教政策,促进了这个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经济繁荣。但他显然把握住了 党的宗教政策的核心,这就是信仰自由,而以信仰自由为核心的政策,显然就是承认宗 教对人的信仰的支撑。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他在其苦难而传奇的经历中,深 深认识到信仰对一个人的生命是何等重要。所以当他从政治厄运中解放出来以后,首先 就想到请做门巴的让迥活佛回寺庙当活佛,因为他是把活佛当成医治人的心灵的人。他 对让迥活佛说:“藏族人的精神信仰是毁不了的。活佛,我们已经在拨乱反正了,医治 人的心灵,比医治人的病痛更重要。”也许,在今天的现实中,像木学文这样真正懂得 党的宗教政策精髓的共产党员并不是很多,说得更尖锐些,像木学文这样懂得信仰的意 义的共产党员也不是很多。在整部小说中,木学文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对信 仰的理解,一方面缘于马克思主义对他的教导,另一方面也缘于他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 。与此相应的还有关于红军的描写。尽管小说中的红军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作者紧紧 扣住信仰二字,年轻的政委对沙利士神父说:“我们不信仰上帝,但是我们信仰一个比 你们的耶稣更伟大的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这位政委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力量, 这种自信和力量无疑缘于已经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的信仰。绛边益西活佛对红军的评价 很有深意,他说有信仰的军队和有信仰的百姓之间是不会打仗的。
小说中最成功的人物应该是虔诚的传教士沙利士神父。作者把神父慈悲、宽阔的胸怀 ,宽容、豁达的心理,睿智、深邃的思想,表现得形象生动。沙利士这一形象的深刻意 义还在于,这位基督教神父的使命应该是在异域文化的土地上传播基督教教义,但异域 文化土地上的人民却成了他的教师,无论是藏族人,还是纳西人,他们有着各自的宗教 信仰,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信仰使人的灵魂更强壮。这一切使沙利士更加透彻地理解 了信仰的意义,于是他对藏传佛教发生了兴趣,对纳西族的东巴教也发生了兴趣。沙利 士在这片隐秘的峡谷生活了四十多年,这块充满文化色彩的土地改变了他。“他对上帝 的事业是否在西藏获得成功已再不在乎,当年来到峡谷之初一心要为上帝献身的狂热、 执著、理想,现在已经变成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冷静、隐忍、沉默……他已经是纳西 人的朋友,西方公认的纳西学者。谁知道再过上几十年,他会不会成为佛教徒的朋友, 成为一个藏学专家呢?”作者范稳通过沙利士表达了他对精神未来的憧憬,这将是一个 走向交融、走向合作的精神世界,而信仰的阳光将把这个精神世界照耀得无比灿烂。
结语:重建精神家园的呼唤
对于一名作家而言,深沉的宗教情怀并不意味着导向宗教本身,而更多的是意味着对 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怀有一种敬畏感、神圣感。正是从这一 意义上,宗教情怀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凝聚的作用。在现代化和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当代人借助后现代文化思潮,打倒了横亘在自由欲望面前的庞然大物。经 典、英雄、理想、使命以及上帝,等等,这些曾让人们敬畏和仰慕的内容,共同构成精 神的权威,令人们的精神俯首称臣。如今,这种权威逐渐瓦解,它似乎标志着一个权威 时代的结束。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一度越来越稀薄,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必然 反映。但对于文化进程而言,我们要摧毁的只是精神的权威,而不是精神本身。中国的 当代文化也许走到了这一步,在摧毁精神的权威之后,迫切需要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毫无疑问,文学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有着哲学、政治、社会机制、知识体系等不 可替代的特殊功能。所谓宗教情怀的问题,也就是针对重建精神家园而提出来的。作家 有意识地唤醒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就会以一种敬畏、神圣的心情和肃穆、虔诚的态度 去重新思考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问题,去追问自然和生命的本质,去谛听未来文明 传来的振幅。而这一切的努力,势必为长篇小说构成与过去迥然不同的丰富的精神内涵 。
最后,还应该谈及宗教情怀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是一种缺乏宗教意识的文化。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所说的宗教意识,应该是明确界 定为物质形态的宗教。单纯从物质形态的宗教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具有宗教氛围不 浓厚的特点,但物质形态的宗教是建立在精神形态的宗教情怀基础之上的,王治心先生 曾经很通俗地解释了宗教是感情的产物,而这种感情“是人类先天所固有的,就是从原 始以来蕴藏在人类心灵中的崇拜精神”(注: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 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宗教意识的说法,我们也能看到 另外一种观点,即把儒家学说界定为一种宗教,即儒教。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尽管“儒教是教非教”仍是一个存有分歧的学术问题,但至少有一点是无须 怀疑的,那就是中国传统文人及士大夫在学习和实践儒家学说时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怀 ,他们把普泛的宗教情怀移植到忧国忧民的胸怀和达济天下的志向之中。中国的知识分 子沿袭着这一传统,他们的宗教情怀往往是通过其强烈的社会承担精神表达出来的。所 以,有意识地强调宗教情怀,也是为了在小说创作中更好地开掘文化传统中的精神资源 。
标签:铁凝论文; 小说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宗教论文; 文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水乳大地论文; 大浴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