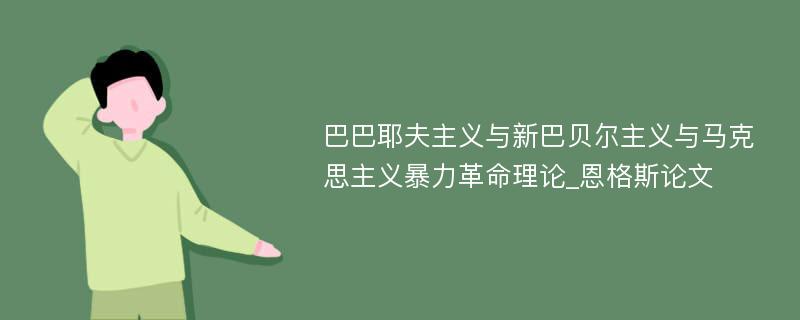
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学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暴力论文,巴贝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1998)06-0072-7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中,批判地汲取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材料,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革命变革。科学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而言,具有两大明显特征:一是批判性,即批判现实资本主义旧世界;二是建设性,即建设未来共产主义新世界。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与上述两大空想学说有着渊源关系。这两种学说,一是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即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二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本文着重就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形成的影响,作些粗浅的探讨。这种探讨或许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来源的深入研究。
一
18世纪末到19世纪30~40年代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与以前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已经有直接的共产主义的理论”[1]。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时,空想社会主义流派纷呈,良莠不齐,其中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影响较大,这一流派是“以巴贝夫为代表”[2]。他的学说代表了“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高成就”[3]。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兴盛不衰,对工人运动仍有较大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布朗基。他继承和发展了巴贝夫主义,所以有的学者称他的学说是新巴贝夫主义。
巴贝夫和布朗基生活在不同年代,但他们的学说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批判性。这种学说不同于当时的其它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它完全摆脱了文学游记的描绘和法律条文的虚拟,不仅批判和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张财产公有,而且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斗争精神和光荣传统,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民专政。不仅如此,巴贝夫和布朗基及其追随者还付诸革命行动,制定具体革命纲领和计划,建立严密组织,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1796年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和19世纪30年代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起义,就是工人阶级通过暴力斗争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巴贝夫和布朗基倡导的暴力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贝夫亲身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目睹了第三等级同国王和贵族的激烈斗争,并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但是,革命后不久,他发现这场革命远不是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革命后“人民流血流汗而生产出来的成果流入一小撮可恨的钱袋的库房里”。人民被穷困的生活弄得疲惫不堪,在国家中毫无地位。因此,他大胆地提出:“对于人民来说,革命并没有完成。”[4]他一再指出,必须进行一场“人民革命”,用暴力铲除私有制这个万恶的制度的根和暴政,建立起“不应有地位高人一等的人,也不应有地位低人一等的人”,的“新型社会制度”[5]。实际上已经有了革命专政的新思想火花。虽然他指的“人民”在阶级概念上还很模糊,但已包含有通过暴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思想。这种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一系列著述中。它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和穷苦群众反对压迫、渴望平等的愿望,代表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同时激发和坚定了他们反对剥削、争取解放的革命信念。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巴贝夫的著作是“在近代一切大革命里代表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6]。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文献具有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色彩,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批判地汲取巴贝夫主义的某些思想精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彻底研讨,将其暴力革命的思想转换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此,某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持相似的观点。例如,英国学者R·N·伯克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七种来源,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法国革命中涌现出的平等派共产主义传统。他指出: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学说,“正是对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冲突这一传统概念的更加精辟和系统的表述”[7]。前苏联学者维·彼·沃尔金也认为,在巴贝夫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他写道:“在革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巴贝夫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的先驱者。”[8]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文献和学说,了解巴贝夫主义并受其影响的话,那么布朗基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是直接的。
布朗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代人,但其革命生涯略早于后者,是后者的师辈。布朗基深受巴贝夫主义的影响,他早年参加的密谋团体就是以巴贝夫密谋思想为武器的烧炭党。他曾拜读过法国烧炭党创始人——巴贝夫的弟子邦纳罗蒂的著作《为平等而密谋》,并在1830年前后同邦纳罗蒂交往甚密。19世纪30年代,布朗基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传统,主张通过密谋暴动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人民专政,以实现人民的解放。他通过1831~1834年的里昂工人起义,敏锐地意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今后的斗争,基本上不再是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斗争,而是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因此,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建立起导致无产阶级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同巴贝夫一样,极力推崇暴力革命,指出:“武器和组织”是“消灭贫困的重要手段!”[9]“法国有了武装的劳动人民,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10]如果离开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先决条件,各种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方案就成为空洞的诺言。
布朗基在理论上不及巴贝夫系统,但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却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活动家,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享有很高威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11]。布朗基的思想以及他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有重要影响。共产主义者同盟又是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因此,布朗基的某些优秀思想必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产生影响。
19世纪40~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同布朗基主义者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曾一度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联合其它革命派别壮大革命力量,迎接新革命高潮的到来,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在这个文件中,他们的思想同布朗基主义是吻合的,即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赞同地下活动,信赖法国革命的首倡精神,武装无产阶级及解除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显然,在暴力革命认识方面,他们是一致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密谋和盲动的斗争策略,但在思想方面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布朗基关于进行政治革命和斗争的必要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布朗基主义看作当时欧洲最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流派,称它是“革命社会主义”,即“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12]。
任何伟大的学说都不是从真空中产生出来的,可以说,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尤其是他们的暴力革命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靥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3]同时,恩格斯也坦率地承认,布朗基等法国共产主义者“在我们发展的初期帮助了我们”[14]。
二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方面,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组织,通过邦纳罗蒂与19世纪30年代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联系起来,这一组织又通过德国流亡者所建立的“正义者同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联系在一起。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移居巴黎期间,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盟员以及法国的秘密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并为了解这些团体的活动,同工人阶级进行了广泛地接触。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科尔纽指出,这种接触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范畴,而是通过具体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接触,马克思才发现了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15],进而科学地揭示出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中的历史使命。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布斯巴姆在《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中指出:“19世纪30年代,从新巴贝夫主义,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政治传统中产生的共产主义,同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经验相融合,从而使共产主义运动变成了‘无产阶级’运动。”[16]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与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和影响分不开。当时,虽然流行着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但是它们对未来社会的虚幻设想和描绘,并没有对工人运动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还付诸革命实践,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引工人阶级进行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时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7]马克思通过对这一现实运动的考察,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是改造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而且也看到了“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18]。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期间,除了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外,还流行着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鼓吹的共产主义。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这种共产主义虽然在当时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
三
综上所述,批判性是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的重要特征,暴力革命是这一学说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彻底研讨,批评地汲取了暴力革命的思想,并将其升华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批判性特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表述自己的学说“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观点,并讨诸实践:“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1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将暴力革命思想奠定在科学的历史观之上,实现了暴力革命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他们在这本书中首次阐述了暴力革命的思想,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20]。1846年,恩格斯在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指出,无产阶级在消灭私有制,实现财产公有的斗争中“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21]。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明确表述: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2]。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通过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总结,研究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产生、发展和组成的规律,它的性质和主要统治手段,以及资产阶级总是首先动用自己的武装来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最后导致无产阶级的失败的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暴力革命的思想。
毋庸置疑,暴力革命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暴力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摧毁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和手段。正如列宁所说,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23]。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愿意“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24]。后来马克思认为,美国、英国和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25]。他们还根据巴黎公社失败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民主得到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增加的新情况,指出了运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增大了,国家增多了;但是,综观他们一生的全部思想,始终坚持暴力革命,直到恩格斯的晚年,他还把暴力革命看成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26]。
由此可见,巴贝夫主义和新巴贝夫主义所倡导的暴力革命思想,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先行思想,为后者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升华,是前者的进步转换。但是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于:空想共产主义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看不到无产阶级在改造旧世界中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们的暴力革命思想,虽然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遭受残酷的暴力统治的现实,反映了他们争取解放的愿望,但在实践上不是依靠全体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企图一样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这种含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暴力革命必然流于空想。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不同。这种学说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科学理论基石之上。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观点出发,揭示出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物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不同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同时,根据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必然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加重对工人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必然引起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工人贫穷的积累,最终形成革命形势。没有革命形势,暴力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必须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和途径,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从而也使暴力革命思想真正建立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基础之上。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学说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进步转换。1917年,俄国工人阶级运用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原则,推翻了沙皇封建专制统治,“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27]。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经济落后的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暴力革命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纷纷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成功,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在世界范围内显示出巨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标签: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