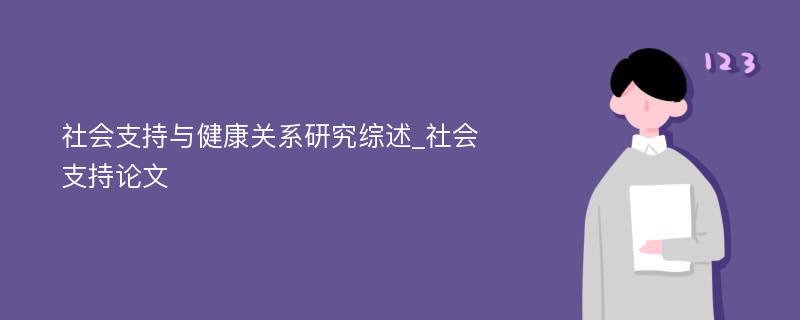
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关系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社会支持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进行了一些简要的回顾与总结。社会支持的作用模型主要有两种假说:缓冲器模型与主效果模型;社会支持概念的测量尽管多种多样的,但两种模型与两类测量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使用整体结构测量,结果会支持主效果模型,使用特殊功能测量,结果支持缓冲器模型;以往的研究都将社会支持作为一个环境变量,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人格因素在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社会支持,健康,缓冲器模型,主效果模型,人格因素,工作模型
对社会支持的研究兴趣是在探求生活压力对身心健康影响的背景下产生的(Homes & Rach,1967)。美国在60年代政治上动荡不安,人们承受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心身疾病发病率明显增高,自杀者频繁出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心理学界开始了生活压力与身心健康关系的探索。许多研究发现:相同的压力情境对不同的个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些较少发病的个体与受压力影响很大的个体相比,有着更多的社会关系。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压力情境下,那些受到来自伴侣,朋友或家庭成员较高心理或物理支持的人,比受到较少支持的人身心更为健康(Brodhead,et al,1983;Leavy,1983;Mithchell,et al.1982)。
早期的研究使人们对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深信不疑,但在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方面尚有争议。一部分心理学家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效果,无论个体是否面对压力情境,高的社会支持总伴随着良好的身心状况(社会支持的主效果模型)。而另一部分心理学家则认为:社会支持只是在人们面临高的生活压力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它使人们免受或较少地受压力事件的影响,保持和增进健康(缓冲器模型)。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结果莫衷一是。
迫于两种理论观点的激烈冲突,人们转而求助于方法学上的探讨。他们发现,社会支持概念测量方式的不同是导致两种不同结论的关键。利用整体结构性测量,其结果常支持主效果模型,而使用特殊功能性测量,其结果往往支持缓冲器模型。
与此同时,人们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社会支持一直被当作环境变量来考虑,无论结构性测量还是功能性测量其共同的假设是: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取决于环境的提供,与个体人格因素无关。但经验告诉人们:不同的个体吸引社会支持的数量、质量以及个人对社会支持的感受与评价都是不同的。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将人格因素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引入社会支持与健康的研究中,取得了新进展。
本文拟从社会支持的作用模型、社会支持的定义与测量及人格因素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过去的研究进行了一些回顾与总结,以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一点参考。
1 社会支持的作用模型
关于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有两种假设。
主效果模型(the main-effect model)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无论个体目前的社会支持水平如何,只要增加社会支持,必然导致个体健康状况的提高。这一论点在社会孤独者与高社会支持者身上都得到了证实(Berkman & Syme,1979;House,et al,1982);沃海特(G.H.Warheit,1979)将个体目前的婚姻状况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发现良好的婚姻状况与身心健康有明显的正相关。还有一些研究者将社会交往,社区参与及良好的亲属,朋友互动关系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其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主效果模型(Lin,et al,1979;Frydman,1981;Bell,et al,1982)。
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the buffering model)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Stress)条件下与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
作为缓冲器的社会支持常常是通过人的内部认知系统发挥作用的。科恩(S,Cohen,1984)认为,社会支持可能在压力事件与健康状况的关系链条的两个环节上发挥作用。首先,它可能作用于压力事件与主观评价的中间环节上。如果个体受到一定的社会支持,那么他将低估压力情境的伤害性,通过提高感知到的自我应付能力,减少对压力事件严重性的评价。其次,社会支持能够在压力的主观体验与疾病的获得之间起到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问题解决的策略,降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减轻压力体验的不良影响。
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既可能是一般性的,也可能是特异性的。一般性是指任何一种社会支持对任何一种压力事件都能起到缓冲作用(Kessler & Mcleod,1985);特异性是指某一特定的社会支持仅对某一特定的压力事件起到缓冲作用(Cohen & wills,1985)。比如,对于产后妇女,指导(guidance)与社会团体(Social integration)两项支持最能有效地防止其产生抑郁。因为这两种支持可以使她们得到更多关于抚养孩子的知识与信息,提高她们有效应付的能力,从而减少压力的不良影响。而对于老人而言,价值信念与抚养机会更能有效地防止他们产生不良的身心反应。这两项支持加强了他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照顾自己,预防各种身心疾病(Cutrona & Wills,1987)。
缓冲器模型的基本假设得到了许多研究结果的支持。布朗(G.W.Brown,1975)研究妇女亲密的社会关系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时发现,如果亲密关系的对象是她们的丈夫或男朋友,那么,这种社会关系能有效地防止消极事件带给她们的严重影响。佩克尔(E.S.Paykel,1980)发现产后妇女与丈夫之间做关于问题方面的沟通,也能防止作新母亲的压力给她们带来的影响。胡塞尼(B.A.Husaini,1982)研究结果表明,婚姻满意状况能很好地预测个体面临应激时的抑郁反应。还有许多研究者用亲密朋友关系,个体之间传达支持的行为作为社会支持的指标进行研究,结果也支持了缓冲器模型的假设(Henderson,1980;Pearlin,1981;Cutrona,1986)。
社会支持的两种模型将既往的研究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研究结论支持主效果模型,另一部分支持缓冲器模型。为了找到两类研究的根本分歧,有必要进行方法学上的回顾,尤其要从概念的定义与测量方式入手,在两类研究与两种模型之间找到某种联系。
2 社会支持的定义,测量方式与两种模型的关系
早期的研究对社会支持概念的操作定义千差万别,各有侧重。科恩(S,Cohen,1985)结合两种模型将社会支持的测量分为以下四类,即整体结构测量,特殊结构测量,整体功能测量,特殊功能测量。用整体结构测量,其结果支持主效果模型;用特殊功能测量,其结果支持缓冲器模型。下面将四类测量及有关研究的结论进行简要的介绍。
2.1 特殊结构测量
这种方法测量的是社会支持的单一维度,可能是数量上的,也可能是质量上的。常见的测量途径有:朋友的数量,来访的次数,亲属的数量等。
利用这些指标作为社会支持的信息,其研究结果不会支持任何一种假说(Eaton,1978,Husaini,1982;Monroe,1983;Thoits,1982;warheit,1979)。但如果测量的单一维度是个体的亲密关系,如婚姻状况,则有时会验证主效果模型或缓冲器模型。凯斯勒(R.C.Kessler,1982)研究发现,良好的婚姻状况对应激能够起缓冲作用,而沃海特(1979)发现,良好的婚姻状况对健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
2.2 整体结构测量
这种方法是对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情况进行测量。包括:邻里状况,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状况,与亲属的互动图式等。
使用整体结构测量,结果会支持主效果模型。斯凯伏尔(C.Schaefer,1982)利用这种方式对社会支持进行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联系对防止抑郁有明显的主效应。弗埃德曼(M.I.Frydman,1981)与凯斯勒(1982)的研究结果既有支持主效果模型的部分,也有支持缓冲器模型的部分,科恩认为,这是因为整体结构测量常含有功能测量的成分。
2.3 特殊功能测量
这种测量的方法是直接利用量表对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所提供的各种功能进行评定。这种测量能够验证缓冲器模型。最早使用此类量表是人际支持评价表(ISEL,Cohen & Hobeman,1983)。它主要测查个体感受到的评价支持(如,自信心,信息支持),实物(工具)支持及归属(社会友谊)支持等的情况。利用ISEL进行研究,结果能够验证缓冲器模型。
稍后出现的同类量表还有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Provision Scale,SPS)。这一量表共24个项目,包括6种功能的测量,即依恋、社会团体,抚养机会,价值信念,可靠同盟及指导。利用SPS进行的研究很多,如库多纳(1984)等,其研究结论都支持了缓冲器模型。
2.4 整体功能测量
这种测量方式是将各种特殊功能测量结合在一起,计算出一个总分作为支持指标。使用这种测量,其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但由于它是特殊功能测量的综合,因此也有些研究验证了缓冲器模型。
威尔科克斯(B.L.Wilcox,1981)利用整体功能测量评价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社会支持的可获性。他的量表隐含了三类支持功能:自尊心支持,工具性支持及信息支持。其研究结果证实了缓冲器模型。汉德森(S.Henderson,1981)制定了包含自信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以及社会友谊支持的支持量表,用此量表进行的研究表明,对于男性,社会支持具有缓冲器作用,而对于女性,则满足主效果模型。
通过上述分类与回顾,两种模型与两种类型的测量关系已基本明确了。使用整体结构测量,其研究结果支持主效果模型:使用特殊功能测量,其结果支持缓冲器模型、两种模型孰是孰非,还有赖于人们对于社会支持概念复杂性的深入认识,以及新的测量工具的出现。
3 人格因素的挑战
早期社会支持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社会支持本身对健康具有增益作用。因此,早期的许多研究都将注意力集中于社会支持作用的产生过程与机制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研究报告的逐渐增多,这种研究假设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怀疑。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之间有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另一些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之间没有任何相关,还有一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有一定的负向相关关系(Bunnk,1990)。
在深入探索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关系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人格因素的影响作用。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人格因素既可能是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的中介变量,也可能是引起身心健康的直接原因。这一部分将着重讨论人格因素在社会支持与心身健康关系中的地位。
人格因素影响社会支持的感知。有研究证明,个体的社会支持感与个体实际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之间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Dunkel-schetter & Bennett,1990;B.R.Sarason,Shearin,Pierce & I.G.Sarason,1987),并且,是前者而非后者更能有效预测个体的身心状况(Blazer,1982;Cohen & Syme,1985,Hobfoll,Nadler & Keiberman,1986;Sander & Barrera,1984;Wethington & Kessler,1986)。影响社会支持感的人格因素,除个体对社会支持问卷的反应风格外,更重要的是个体的社会认知变量。
大多数社会支持的测量都是通过问卷方式进行的,因此,各种反应风格,情绪状态等,很可能在社会支持分数与健康之间制造出某种虚假的相关。这些因素包括:墨认,精神状态等。例如:抑郁状态的个体更多地以消极的方式进行反应;神经症病人也倾向于报告较少的社会支持(Coyne,1978;Lewinsohn,1979)。
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在社会支持的感知中起着重要作用。工作模型(Working model)( Bowlby,1969,1973,1980)是目前社会认知研究中较受重视的一个概念。工作模型的含义与图式,原型,脚本很相近,是人格结构中稳定的一个方面。工作模型引导人们对于人际交往的感知,期望与互动,它是人们观察他人情感与行为的透镜,这种透镜的特性决定了人们注意的焦点与对信息的选择(Sarason,pierce,et al,1991)。研究表明,具有较高社会支持感的人的工作模型是:积极地估计别人的人际关系特性、社会应对能力与身心状况;认为自己是个具有独特价值,值得关注的个体,相信自己有较高的人际交往能力;而低社会支持感的个体的工作模型则与此相反,他们对他人的评估更消极,远离事实;而对于他们自己,则有人际无能,焦虑及社会拒斥感(Rosser,1986,Sarason,et al,1991)。工作模型很可能是早年亲子互动的结果,它的形成受到父母对儿童的看法及行为的影响,这种工作模型一旦形成,便成为个体人格结构中的一部分,影响今后对人际关系的感知(Sarason,pierce,Bannerman & Sarason,1983)。
人格因素影响社会交换感,社会交换感在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许多研究者都曾提到过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过程的重要作用(Autonucci & Jackson'1990;Bunnk & Hoorens,1992;Gofflieb,1985;Hobfoll,1985;Rook,1987)。例如,罗克(Rook,1987)指出,一个人一旦感知到自己给予的支持比接受的支持多,就会产生不公平感与反抗情绪,相反,如果一个人感知到自己给予别人的支持少于自己所接受的支持,就会产生欠疚感与羞耻感。社会支持的增效益果只有在这两种感觉达到平衡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一个人如果担心自己缺乏回报的能力,他便不会求助于人。
影响社会交换感的人格因素是“交换定向”(exchange orientation)与“公共定向”(Communal orientation)。交换定向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默斯坦(Murstein)及其同事提出来的(Milardo & Murstein,1979;Murstein,Cerreto & Mac Donald,1977)。这种人格特质指向直接的互惠。具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期待直接的,可以相比的回报。当他们为别人提供了利益,而别人未报答他时,或当他们得到了帮助却无法回报时,都会产生不愉快感,无法容忍这种不平衡。具有公共定向(Clark,et al,1987)人格特质的人则与此不同,这种人有一种根据需求得到别人帮助或给予别人恩惠的愿望。他们仅从需要出发,不强调互惠。研究表明,在提供与接受平衡的条件下,社会支持的增益作用对于两组个体来说都是相同的;而当提供与接受失衡时,社会支持只对公共定向的人起到增进身心健康的作用,对于交换定向的人来说,这种社会支持所带来的失衡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压力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Buunk Dooje,Jans & Hopstaken,1993)。
人格因素除上述中介作用外,也可能是引起身心健康的直接原因。某些人格变量可能既导致了个体较高的社会支持水平,也导致了其良好的身心状态。研究表明,低的神经质分数,较强的自信心及良好的应对技巧,很可能是同时导致高的社会支持与良好的身心状态的人格因素(Henderson,Duncan-Jones,Byrne & Scott,1983;Repetti,1987)。例如,一个具有良好应对技巧(Coping Skill)的人既可能很好地应付人际关系,吸引较多的社会支持,也可能有效地应付不良情绪状态及疾病的侵袭,保持身体健康。”健康的身体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同时出现在有能力的人身上”(Reis),用这种观点来看,也许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仅是通过人格因素表现为相关。
科恩(1985)在研究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时发现:高社会支持的个体较少地产生抑郁,但这些高社会支持者往往有较高的自我效能,如果利用统计技术,使自我效能保持不变,则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不再显示出显著的相关关系。可以说,自我效能不但导致了个体高的社会支持,同时也促成了个体良好的身心状态。它作为第三变量使没有明显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显示出高的相关。
将人格变量引入社会支持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中势在必行。人格因素作为第三变量的研究目前正方兴未艾,但人格变量是否是导致身心健康的直接原因,仍需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关于社会支持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尽管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但这一领域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尚待解决:第一,如何有效,准确地把握“社会支持”这一概念;第二,如何进一步探索人格因素在社会支持与健康关系中的作用。突破这两大问题,该领域的研究将会有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