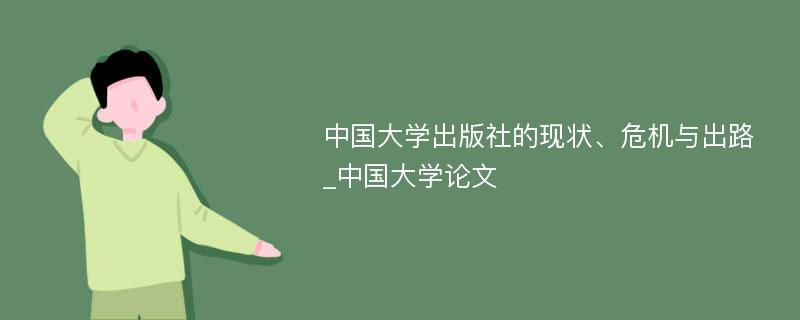
中国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危机和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出版社论文,中国论文,出路论文,现状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大学出版社的现状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一共98家。如果要算平均年龄,20岁还不到,但是它们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请看下面的统计数字(数据引自《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2001—2004》。2005年的数据尚未公布,但是大致情况与2004年的出入不大,据我所知,绝大部分数据都好于2004年)。
1.大学出版社的分类及比例
2004年全国有98家大学出版社,占全国572家出版社的17%。其中综合类大学社26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27%;理工类大学社42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43%;文科类大学社19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19%;师范类大学社11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11%。
2.大学出版社的地区分布
大学出版社的地区分布极不均匀。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社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37.7%。其中北京市25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25.5%,上海市12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12.2%;辽宁、江苏、陕西省各6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6.1%;湖北省5家,占全部大学社数量的5.1%;其他各省都在5家以下,其中河北、内蒙古、福建、广西、云南、甘肃、新疆仅为1家。
3.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与全国出版社图书定价总金额的比较
由于采集有关数据和将销售码洋统一折合为图书定价总金额比较困难,现将大学社销售码洋和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进行粗略比较。
(1)2003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为110.33亿元。
2004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为127.69亿元。
(2)2003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561.82亿元(《2004中国出版年鉴》第41页)。
2004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592.89亿元(《2005中国图书年鉴》第207页)。
(3)2003年大学社销售码洋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的19.64%。2004年大学社销售码洋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的21.54%,比2003年提高了约两个百分点。
4.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增长速度
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保持较快速度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更高于出版全行业增长速度。
大学出版社2001—2004年的销售码洋分别为73、90、110、127亿元,逐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3%、22%、15%,均高于“十五”期间GDP年均9.5%的增长速度,更高于“十五”期间全国出版行业3%~5%的增长速度。其中2004年全国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比2003年增长15%,比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6%的增长率高出9个百分点。
5.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根据销售码洋可以看出,大学社的发展两极分化严重,强者更强。
2004年,全部大学出版社平均销售码洋为1.3亿元,高于全国530多家出版社(不含30多家副社)的平均销售码洋1.12亿元,但大学出版社当中,2004年销售码洋超过大学社平均销售码洋(1.3亿元)的仅有12家,占全部大学社的12.2%。
2003年,销售码洋排前五位的大学出版社,其销售码洋占全部大学出版社销售码洋的比例为25.72%。2004年,这一比例为26.59%,比2003年的比例提高了几乎一个百分点。预计2005年这一比例还会有所提高,因为2005年销售码洋排前五位的大学出版社比2004年前五位的销售码洋增加了7亿元,增幅达21%,这个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全部大学社销售码洋的增长幅度。
在地区分布上,北京、上海两地的大学出版社以占全部大学出版社37%的数量,而占有55%以上的销售码洋。
通过对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状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以占全国出版社总数17%的份额,实现了占全国图书定价总金额21.54%的比例(如果将图书定价总金额折算成销售码洋,则比例会高得多)。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增长势头强劲,以2001年至2004年三年销售码洋增长的平均速度计,达到了20%,远远高于其他类出版社。
第三,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中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大社、强社,跻身于全国出版社综合实力前20名的排名中。
第四,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发展是不平衡的。外语类出版社、师范类出版社发展特别快;几所著名大学的出版社,如北大、清华、人大出版社发展也比较快;而一些学科比较偏、窄(如地质、林业等)的出版社和一些边远地区的出版社,发展比较困难。
二、中国大学出版社高速发展的原因
对于大学出版社快速发展的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做过很有价值的探讨。归纳起来,无非有以下几点:
一是资源优势。大学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优势。这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大学社都依托着一所大学,这是它的先天优势,只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就不愁没有好的选题。一些名牌大学出版社之所以发展得好,就得益于它所依托的那所大学的牌子,这就是品牌的优势。
二是人才优势。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物色到最优秀的人才。据统计,在全国出版社的人员结构中,大学社的整体学历层次最高。就我所知,全国出版社中,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发行科长就出在大学社。教授、博导出身的社长在大学出版社中也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学历越高本事就越大,出版事业的成功与否更不能与学历的高低划等号。但是,有一个整体上学历层次较高的团队,总是一种人才结构上的优势。事实也证明,中国大学出版社的成功与它的团队素质高,尤其是领导层素质高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区位优势。大学出版社处于中国教育的最前沿,“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是最早感知中国教育的春风、春雨和春潮的。中国的出版业离不开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出版业的繁荣是教育造就的。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由于与教育的天然联系,使它们有可能把教育的优势转化为出版的优势,把教育的资源转化为出版的资源,把教育的机会转化为出版的机会。这些年,师范类的大学社发展速度特别快,就足可印证这一观点。
但是,如果再仔细地分析一下,深入地思考一番,就可以发现,以上所谓的三个优势并不是大学社所独占的,它其实是一种公共资源,大学社可以用,其他社也同样可以用。要说大学社就是凭借这三点取得了超出一般出版社的发展业绩,是缺乏说服力的。人们还是要追问“为什么”,也就是说,大学社究竟有没有发展的“秘密”?
那么,什么是大学社发展的秘密呢?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大学社较早地直接面对市场、进入市场,并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改革和运作。中国的出版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对教育的依赖。中国的出版社有五百余家,发展得特别好的也就是各地的教育社和那些与教育有着各种联系的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出版市场,主要依赖所谓的“系统”,即计划体制和系统。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生比较晚,所以,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发现:教育出版的“系统市场”早已被瓜分一空,它们连残羹剩饭都吃不上。大学出版人领悟到,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在系统之外寻找生机,于是他们不得不走向市场。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出版市场继挂历热之后掀起的教辅热,主要就是由大学社(尤其是师大社)掀起的。取得了长足的市场经验以后,大学社又以市场的敏感和经验揳入系统,成功地拓展了系统的平台和领域,成为长袖善舞的经营者和竞争者。遗憾的是,就在大学社在残酷的市场中摸爬滚打的时候,那些体制内的出版社却还躺在计划经济的摇篮里吃着皇粮。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版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加大,于是就出现了较早适应市场的大学社“疯长”的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大学社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也是被市场培养出来的。
第二,中国的大学出版之所以可以“疯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它们享受了二十几年的免税待遇。国家为了支持教育产业的发展,多年来一直对校办产业实行免除所得税政策。大学出版社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产业有幸享受了这一政策。此外,根据国家有关支持文教科技事业的相关政策,国家对教材(指高等学校的教材)、科技类图书实行营业税先征后退的优惠。在大学出版社的图书结构中,这一类图书占据较大的份额,大学出版社自然成为这一政策的最大受惠者。
综合以上两点,我认为,中国大学出版社高速发展的秘密在于:第一是命好,所谓生逢其时;第二是争气,能够积极进取。
三、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危机
但是,大学出版社的命并不会永远好下去,它们的危机已经来临。
2003年,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进入WTO所做的承诺,国家取消了对校办产业的免税政策。大学出版社在进行了一系列苦苦的争取之后,终于走完它们得天独厚的路。从此以后,它们必须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
这一变革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因为中国的大学社,除了极个别学校如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的出版社外,都承担着向学校上缴利润以补贴学校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责任。据我所知,出版社向学校上缴利润少则20%、30%,最多的要上缴50%以上,如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等。
这对出版社来说是一件负担很重的事,因为它们还得上交33%的利税。这就是中国大学出版社面临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它们要双重纳税交费。
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局面还远远看不到尽头。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之下,中国的大学出版之路究竟如何走?如何把发展经济规模与提升学术品位完美地结合起来?是走纯商业出版之路,还是继续走学术出版之路?大学出版社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及产品与技术的转型?这些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出版人无法回避却又不知如何解决的问题。
此外,中国出版的集团化大趋势,也使中国的大学出版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大学社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生理缺陷”,决定了它不可能与其他的大学社重组而实行集团经营。除了几家已经发展得足够强大的大学社外,绝大多数大学社的实力还远不足以与那些大的出版集团抗衡。当下,中国的出版集团大多还处于整合期,它们的集团优势暂时还未显现出来。一旦这些集团渡过了磨合期,很多大学社就将面临严重的压力。面对集团化,大学社如何应对?这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四、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出路——改革
但是,对大学社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改制。
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以来,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地方出版社相继进行了改革试点并取得成果。但是大学社的改革却始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开始于2003年。但是大学社如何改,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没有定见,所以改革的试点并不涉及大学社。另一方面,大学社又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反对大学出版社的企业化改革。直到2006年,还有一家大学社趁工商登记的机会抢先以事业法人的身份登记,试图造成自己是公益性出版社的既成事实。
大学出版社反对体制改革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1.强调大学出版社为科研和教学服务的特殊性,不能视为单纯的企业。2.强调所谓的国际惯例,要求如牛津、剑桥一样享受免税的待遇(问题是,牛律、剑桥是不是如大家所说的免税还有着大大的疑问)。3.强调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学术出版不能市场化,如此等等。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其实,一些大学出版社反对改制的真正原因是希望脚踩两只船——既享受到企业的好处,又沾到事业单位的好处。如上文所分析,大学社的发展正是两头都占便宜的结果。它们不想丢掉既得的利益。所以,大学社没有改革的动力。
事情到2006年初发生了变化。2006年3月,中央又召开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会议,李长春、陈至立、刘云山纷纷发表讲话,重申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会议第一次明确指出,大学出版社属于改革的对象。紧接着,教育部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成了调研组深入各高校调研,确定了第一批试点的出版社。
与此同时,一些大社、名社(主要在北京地区)如北大、清华、北外、人大、北师大出版社表现出了极大的改革热情。人们看到,改革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既然要改,那还不如早改,早改还可以享受到试点单位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大学出版社的改制呢?我认为,出版社的改制,从所谓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变为企业,是出版社本质属性的回归,它使理顺出版社的经济关系、权属关系、人力资源关系成为可能,而这些关系是进入市场、驾驭市场、适应市场所必需的前提条件。事实上,随着教材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发展,中国出版业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外的“市场”会越来越萎缩,所以,改制是顺应潮流的。
再从现状来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其实一直是在按企业规律运作。那些发展得好的出版社正是企业化管理做得好的出版社。如果说,在2003年之前,大学社还沾到了事业单位的好处的话,那么免税优惠取消以后,大学社实际上已经得不到任何事业单位的好处(人员问题是个例外,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
而且,国家综合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将来国家在管理公益性单位时,严格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办法,那么,那些所谓的公益性出版社就会受到税收、出书范围、经营范围、薪酬分配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所以,我是改革派,我自始至终鼓吹改革、推动改革。
当然,改革是有风险的。
风险之一是如何控制改革的成本。改革必须付出成本,改革的成本究竟有多大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改革的成本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那么,这对企业将是致命的。所以,控制改革成本成了改革成败的关键。
风险之二是如何协调好各利益集团的关系。改革必定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又使那些利益受到侵害的少数人能够接受改革,这是一道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样的难题。但这又是一道我们必须解开的题目。
风险之三是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大学出版社这些年来的发展来之不易,但是改革却要求我们自己对自己动手术。怎样既搞好改革又不影响生产,这同样是一道难题。
风险之四来自我们的母体,也是我们的全额出资人——学校。学校能否开明地按照经济规律、出版规律办事,将直接影响改革的结果——成功抑或失败。
如果事业单位改革的结果是使那些死抱着“公益性”事业单位不放的人能够在事业与企业间两头得利,或者政策和法律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游刃有余,那么,我们将会看到大学出版社改革的全面复辟。
所以,中国的大学出版社风风雨雨二十几载,现在真是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我希望改制能给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让大学社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那么,假以时日,中国的“牛津”和“剑桥”就一定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