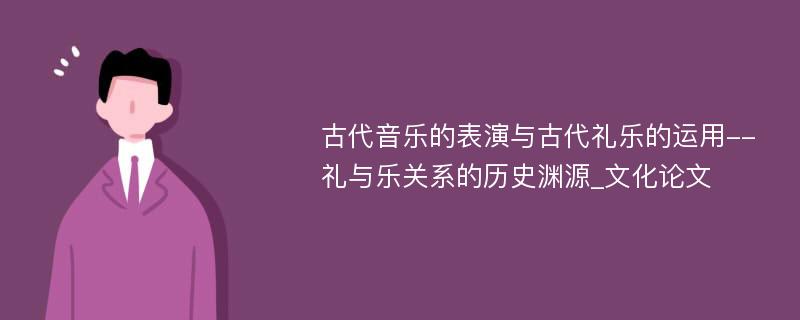
古乐的演奏与古礼的演习——礼乐关系的历史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乐论文,古乐论文,关系论文,历史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2—0173—04
《礼记·乐记》云:“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滞之音矣。”乐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的“音乐宇宙”世界。在这样一个天赐的音乐宇宙里,对应着的是礼的人伦世界。“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谐配,神人以和。在轰轰烈烈的原始宗教巫术礼仪气氛里,奏乐歌诗的声律,手舞足蹈的节奏使得天地相和,人神相会。礼与乐共同营造出宇宙之和谐、人间之秩序,礼乐关系深厚、长久的历史渊源奠定了礼乐文化形成的基础。
一、伐鼓救日与日神祭礼
日神崇拜是中国上古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太阳东升西落,周而复始,曾引起上古先民无限的想象和联想。它带给人类光明与温暖,促使动植物生命繁衍,人们崇拜它;烈日与酷热又带给人类痛苦与灾难,人们敬畏它。各种以太阳为祭祀对象的典礼经常举行,殷墟卜辞中就有许多“入日”、“出日”的祭日记载,早晨要举行迎日仪式,晚上要举行送日仪式。《尚书·尧典》所说“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应该就是指这种迎日、送日仪式。在各种祭日仪式中最重要的莫过于
日食发生时的“伐鼓救日”仪式。太阳的“丢失”实在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它或许是人类的行为得罪了日神,气愤的日神在向人类发出警示。怀着无限的忐忑和恐惧,祭祀日神的典礼应该是规模最大、气氛最严肃的一种仪式。在这样的典礼上,自然少不了乐的参与,最具神秘性和震撼力的鼓乐成为取悦于日神的最佳选择。
《尚书·夏书·胤征》云: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日食发生时,“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乐师瞽击鼓奏乐,主币之官啬夫驾车取币以礼天神,庶人也为救日奔忙不停。整个场面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忙碌。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秋天发了大洪水,击鼓用鼓乐、用牺牲祭祀土地神庙和城门神是不合于常礼的。凡是天灾,祭祀时只能用玉帛,不能用牺牲,不是日食、月食不能用鼓。可见,伐鼓奏乐只有在救日这样的隆重祭礼时才能使用。
《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礼也。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言充其阳也。
天子、诸侯、大夫、士在救日祭祀礼仪中的等级差别非常严格,“三鼓”、“五鼓”正是这种差别的具体体现。
《左传》昭公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馀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
日食发生,祝史请示所应该使用的祭品,昭子告诉他,日食发生时,天子不能进丰盛的菜肴,并到土地神庙里去击鼓。诸侯用祭品在土地神庙里祭祀,到朝廷上击鼓。“伐鼓救日”的祭祀礼仪从远古一直走到了商周时代。
二、笙竽交和与祈雨祭礼
《周礼·春官·司巫》云:“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雩”是上古时期求雨的祭礼。水是生命之源,在所有气候因素中,雨对人类的影响是最大的。殷商时期中国已进入农牧经济时代,人类靠天吃饭,雨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收成,从某种意义上说,雨水即生命之水。而降雨量的多少又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古人认为这一切权力都掌握在天神之手。每当久旱不雨之时,人类便只能祈求于天神,只能在神灵面前哀哀以求,于是,“吁嗟求雨之祭”在上古所有祭祀典礼中显得尤其重要。根据考古发现和有关文献记载,这种求雨祭祀活动不仅频繁地举行,而且场面宏大,“奏舞”、“奏乐”,载歌载舞,融歌舞表演、音乐表演、器乐表演于一体,是上古时期规模最大的乐舞盛会。《礼记·月令》对当时这种规模庞大的雩祭乐队作了详细的描述:“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古人认为,“阳气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兴云雨”,举行雩祭必须要用“盛乐”。只有组织规模宏大的乐队,用最高的规格才能谄谀雨神,因此,在将要举行大雩求雨祭礼时,需要准备好各种各样的乐器在雩祭时演奏,并配合各种各样的乐舞表演。
在安阳考古发现的殷契中,有不少关于求雨、卜雨和祭祀雨神的甲骨文,其中除了有一种是通过燃烧贡物献祭的方法以外,大部分还是通过“舞”或“奏舞”的形式来举行求雨祭礼的。“隶舞”就是在求雨时举行的一种大型歌舞演出活动。甲骨卜辞记载:“庚寅卜,辛卯隶舞雨;□,壬辰隶舞雨;庚寅卜,甲午隶舞雨”(甲,3069),隶舞在卜辞中又作“舞”“兹舞”。
兹舞,从舞。(乙,6859)
今日舞,(雨),今日舞,亡(雨)。(铁·120·3)
贞,我舞,雨。(乙,7171)[1](P132)
可见,在卜辞时代用奏乐跳舞的形式来祭祀雨神是普遍流行的一种祭神仪式。另外,我们还能从其他先秦文献中找到各种不同乐器用于祭祀雨神的例证。《诗经·小雅·甫田》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琴瑟击鼓的乐器合奏曾用于祭祀雨神。《吕氏春秋·古乐·仲夏纪·五日》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鼓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琴瑟之乐确为求雨祭礼的一种常用音乐。我们说求雨祭礼是原始人类规模宏大的歌舞盛会,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可以想见,在磬响钟鸣、竽笙交和的乐声中,一群女巫且歌且舞,场面热烈,盛况空前。①
三、歌舞祀神与图腾祭礼
原始音乐活动大多与图腾祭礼有关,因此,宗周以前的祭祀用乐几乎都是图腾祭祀音乐。《古今图书集成》第一卷《礼乐总部汇考》辑录了历代有关祭祀用乐的情况:
伏羲氏始制礼乐。按:《史记补·三皇本纪》太皥包羲氏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三十五弦之瑟。
神农氏行蜡祭之礼,作扶犁之乐。按:《史记补·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又作五弦之瑟。
黄帝作《咸池》之乐,定衮冕衣裳之制,备吉凶之礼。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
颛顼高阳氏定牲玉服度之制,作五基六茎之乐。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
帝喾高辛氏定升绛长幼及祭祀之礼,作《九招》之乐。按:《史记·五帝本纪》不载。
舜命伯夷淀三礼,夔典乐,又于巡狩正礼乐。
禹即位,定祭祀冕裳之制,建旗旐以别尊卑,作《大夏》之乐。按:《史记·夏本纪》不载。
汤即位,定朝会祭祀车服之仪,命伊尹作《大濩》之乐。按:《史记·殷本纪》不载。[2](P101—105)
黄帝部族之乐名为《云门》,也称《云门大卷》。黄帝部族以云为图腾,《云门》是他们的图腾乐舞。《左传·昭公十七年》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云名。”杜预注:“黄帝受命,有云端,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这一乐舞一直相沿到了周代,《周礼·大司乐》云:“舞《云门》以祀天神”,“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云门》被作为庄严、肃穆的祭祀天神用乐而得到广泛运用。以上文献把《咸池》也作为黄帝之乐,“黄帝作《咸池》之乐,定衮冕衣裳之制,备吉凶之礼。”《吕氏春秋·古乐》也有类似的记载,“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曰在癸,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咸池》之乐其实是炎帝部族之乐,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炎黄大战之后文化融合所至。
咸池,传说中是太阳初升沐浴的地方。《淮南子·天文训》曰:“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楚辞·离骚》王逸注:“咸池,日浴处也。”以《咸池》作为乐曲的名称,显然是与部族的太阳崇拜有关。而炎帝部族就是崇拜太阳的,太阳是他们的图腾。《左传》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庄子》记载孔子游学穷困潦倒时“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炎氏之风”。《咸池》为炎帝部落的图腾乐舞无疑。
“颛顼高阳氏定牲玉服度之制,作五基六茎之乐”,这与《汉书·礼乐志》的记载相同,《六茎》乃颛顼高阳氏之乐。但《吕氏春秋》说颛顼高阳氏之乐为《承云》,“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方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会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帝喾高辛氏定升绛长幼及祭祀之礼,作《九招》之乐。”帝喾高辛氏部族之乐名为《九招》。《吕氏春秋·古乐》云:“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垂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篪、鞀、椎,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汉书·礼乐志》载:“帝喾作《五英》。”从这些材料看,鸟类的羽舞可能是帝喾部族的图腾乐舞,这一时期打击乐器、管乐器已经出现。
帝尧部族之乐名为《大章》。《大章》是尧部族的图腾乐舞。《吕氏春秋·古乐》云:“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汉书·礼乐志》云:“尧作《大章》。”《大章》之乐,效山林溪谷之音,在鼓鼙、琴瑟的伴奏下,“百兽”起舞,规模之宏大,以前历代乐舞实难以比拟。
“舜命伯夷淀三礼,夔典乐,又于巡狩正礼乐”,舜部族之乐名为《箫韶》。《箫韶》是舜的图腾乐舞,以箫和磬为伴奏乐器。《尚书·虞书·益稷》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到西周时期,《韶》乐被加工改造成国乐,其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对吴国公子季札观乐时的那一段著名的描写,使我们在看到周乐盛况的同时,也能看到《韶》乐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禹即位,定祭祀冕裳之制,建旗旐以别尊卑,作《大夏》之乐”,夏禹部族之乐名为《大夏》。上则材料季札观乐时就有《大夏》之乐。“汤即位,定朝会祭祀车服之仪,命伊尹作《大濩》之乐”,商汤之乐名为《大濩》。这些古乐,集乐、史于一体,代代相传,成为周代制礼作乐的重要基础。
四、原始乐舞与生殖崇拜祭礼
生殖崇拜祭祀礼仪是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印度人将男根称为“林迦”(linga)、将女阴称为“由尼”(yoni),他们将立石制作成翘起的男根,直称“林迦”,或将石雕刻成“林迦”与“由尼”结合之状,实行生殖崇拜。希腊人在崇拜酒神时有举着生殖器游行的仪式[3](P324)。 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山洞岩画里有不少用于祭祀生殖女神的画像,这些岩画以夸张的形态,对女人的乳房、肚子、阴部进行强调。欧洲旧石器晚期,从比利牛斯山到顿河河谷出土的石质或象牙圆锥妇女像,一律具有高耸的甚至下垂的硕大乳房,凸出的腹部和臀部以及刻画形象的女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辽宁红山大型文化祭坛,无头孕妇陶像也突出地表现出生殖部位特征,夸张着人类旺盛的生命力。在宝鸡发现的晚期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造型逼真的男性生殖器官模型。而一些原始岩画中,也生动地描绘出两性交媾、性特征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着人类追求生命的迷狂精神[4] (P2)。直到今天,我国云南宁蒗永宁地区的摩梭人每年都还要举行祭祀生殖女神的“黑底干木”仪式。活动时摩梭人吹着笛子跳舞,他们称之为“麻达搓”,“麻达”就是笛子,“搓”是舞蹈,“麻达搓”即笛子舞,这种舞蹈也起源于原始生殖崇拜,麻达还有另一层含义是指男性生殖器。美洲的印第安人正好也将笛子视为男性生殖器。生殖崇拜表现出人类对生命的惊奇和对生命的礼赞,两性交媾的生命本能使原始人类第一次从自身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音乐的产生是抒情的需要,《礼记·乐记》说:“歌之言也,长言之也”,“情动于中,故行于声”,歌唱是语言的扩展与延伸。在没有任何束缚的原始部落里,两性交媾这种生命的游戏恰恰应该是音乐的一种身体的表达,它与音乐配合下的舞蹈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许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舞蹈。我们目前所发现的原始时期留下的古老岩画中,那些描写生殖崇拜祭祀场面的图像几乎全是载歌载舞的形象。虽然这样的生殖崇拜祭祀具体按什么样的程式进行我们现在已无从可考,但它与音乐、歌舞之间关系的存在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本师傅道彬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最早的钟鼓之乐一类的艺术活动正是伴随着生殖崇拜祭祀仪式进行的,他在《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从两方面作了分析,他说:“一是婚姻经常伴随着钟鼓之乐进行。《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所谓‘钟鼓乐之’,就是在鼓乐声中把她娶来。鼓乐是婚姻的代名词,那么在更古的时代,它当是庄严的性行为的必备形式。婚姻用鼓乐是对远古遗风的继承,所以后世还以琴瑟来比喻夫妻及夫妻的和睦关系。《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即是。另外,《诗·郑风·女曰鸡鸣》:‘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故琴瑟。’都是指夫妻间的和谐关系,这里面是不是凝聚着生殖崇拜形式的体验和回忆呢?二是古代还把巫师击鼓与求子的风俗联系起来。郑玄《诗谱》谓‘陈太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太姬无子便依据巫觋歌舞音乐来祈求生育,这里当有这样一个宗教心理背景,即远古社会总是在钟鼓音乐歌舞中,举行盛大的生命媾和活动,这样才影响到太姬的以钟鼓之乐乞求生子的行为。当然,无论是用钟鼓音乐象征夫妻关系也好,还是以音乐歌舞来祈求繁育也好,都是远古风俗在文明社会里的残响,在悠远往古它一定有更热烈的艺术、宗教和生殖崇拜融为一体的形式。”[4](P71)
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虽然我们现在还很难找到生殖祭祀礼仪与原始音乐歌舞之间直接联系的证据,但古乐器的遗存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上述结论提供了许多相关的佐证。我国古代原始乐器的命名有许多都是受到了生殖崇拜观念的影响,传说中和见于记载的许多古乐器如:鼓、笙、管、壎等,这些古老的乐器名称都与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内在联系。
鼓。《说文》曰:“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古曰鼓。”徐锴曰:“郭者,复冒之音。”鼓象物生长之状。古代祭社仪式也常常和鼓相联系,而祭社是典型的生殖崇拜礼仪,“社”用于祭祀母神,是最早的女性生殖崇拜的祭所。《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左传·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春秋繁露精华》:“大水鸣鼓而攻社。”日食、大水都是阴气过重所至,击鼓以调节阴阳,就必须在“社”这样一个祭祀母神的地方进行。
笙。《说文》曰:“笙十三簧,象凤之身也;笙,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谓之笙。”,显然,“笙”即“生”、“生命”、“生长”。“象凤之身”,凤是古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雌性神鸟,笙为凤就是说笙属阴性,应与女性生殖崇拜有关。《白虎通》曰:“匏曰笙。匏之为言施也。在十二月万物始施而牙。笙者,太匏之气,象万物之生,故曰笙。”《释名》曰:“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也。”笙这种乐器名称其最初的含义确实就是指生长和繁殖。最能证明笙与女性生殖崇拜关系的一条文献记载是《礼记·明堂》:“女娲之笙簧。”女娲是传说中的人类之母,她主宰人类的婚姻与生殖,创造了人类,笙与女娲的联系正好说明笙这种乐器名称的来历是女娲崇拜的体现,是生殖崇拜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5—11—10
注释:
① 《周礼·春官·司巫》云:“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暵,则舞雩。”其注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古人认为旱是阳气过剩,阴气不足,而女巫属阴性,故用女巫舞雩求雨,在“雩”祭中的舞蹈表演者几乎全是女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