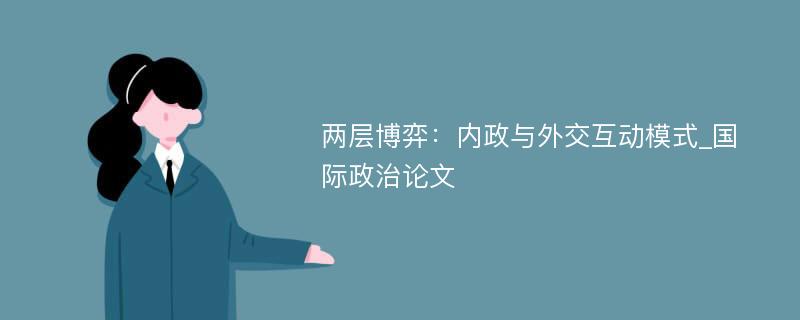
双层博弈理论: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内政论文,外交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2-0061-07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直被视为外交学的“公理”。其实,不仅内政制约外交,外交也会影响内政。那么,如何理解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众多关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互动的理论中,双层博弈是颇有特色的一种。自1988年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提出双层博弈模式后,又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拓展深化,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该模式,提高了它的理论化程度,增强了它的理论解释力。本文拟分析双层博弈理论的提出背景,概述其基本内容,追踪其发展进程,最后做出简要评析。
一、理论背景
双层博弈理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现实背景和学理背景。现实背景是,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各国之间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传统的国家主权受到挑战,外交和内政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就需要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现实背景: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断加深
罗伯特·普特南是在撰写《同舟共济:七大国首脑会议中的冲突与合作》时萌生双层博弈模式设想的,而这本著作的思想又与他在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期间的工作经历紧密相关[1]。他在研究世界七个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首脑会议的起源、发展过程中发现,七大国首脑会议机制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三个结构特征密切相关:经济相互依赖导致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日益紧密的联系;促进战后长期繁荣的美国霸权的衰退;国际关系的机制化,促使一些政治领导人发现这种趋向使决策变得更加复杂[2](P1)。国际贸易、投资的增长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产生了一系列国际、国内政治后果,导致国家主权与相互依赖的矛盾、困境。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使得各国共同利益增加,国家主权受到削弱,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国际合作增加,国际冲突减少。但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经济相互依赖一方面加深了各国的共同利害关系,促进了国际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国家主权观念依然存在,国家边界也未消失,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在执行,这使得协调各国政策比过去更困难。从国际政治角度看,协调各国政策困难的原因在于,不同国家目标、经济结构、信奉的经济理论、制度、政治气候不一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国家经济受制于国际因素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要为国家、次国家行为体负责。这就给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造成了困境[2](P2-3)。例如,一个美国议员的政治命运可能取决于布鲁塞尔或东京的决策、这时,他到底应该采取维护本国、本地区、自身利益的民族主义立场还是推进合作的国际主义的立场呢?由此,普特南萌发出双层博弈模式的设想。他认为,从政治角度看,国际经济协调可设想为双层博弈。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政治家则通过在那些集团中建立联盟来谋求权力。在国际层次,各国政府谋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压力的自由,同时使外部发展的不利结果最小化。政府也可能追求“国家”利益,如声望、安全,但它们与国内压力只是间接联系。这两层博弈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策是国内国际两股力量平行作用的结果。只要各国相互依赖,而且都是主权国家,那么政策制定者就不能忽视两个层次中的任何一层博弈[2](P4)。
2.学理背景:国际政治单一层次分析法的局限
为了科学研究的方便,国际政治学者把国际关系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进行研究,这就是层次分析法。它假定某一个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3](P246)。不同的学者对层次如何划分,重点研究哪个层次观点不一。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把国际体系结构、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为国家行为的解释原因,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国家层次的研究则是把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作为国家行为的解释原因,如民主和平论;个体层次的研究是把国家领导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作为国家行为的解释原因,如外交政策分析。层次分析法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单一层次分析法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于是,不少学者主张把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结合起来分析。普特南认为,从现有关于国内与国际事务关系的大部分文献看,要么是讨论不计其数的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要么是探讨国内与国际事务的“连锁”影响[4](P430)。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是第一个呼吁研究连锁政治(Linkage Politics)的学者,但是没有产生多少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第二个与此问题有关的流派是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h)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研究的地区一体化理论。该理论强调利益集团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哈斯提出的“外溢”(spillover)概念认识到了国内与国际发展的相互作用。但其核心变量是假定超国家机制的演进,而不是政策变革。受地区一体化理论影响,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提出的相互依赖理论,强调相互依赖与跨国主义,但忽视国内因素,而是只强调国际机制概念。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官僚政治模式,着重分析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由于利害的冲突对国家外交政策选择的影响,但忽视社会因素的作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倒置的第二意象”学派重点研究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把国内政治只是作为国际政治作用的“传送带”。因此,普特南强调,我们必须超越单一的国内因素对国际事件或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的研究,超越对这种影响的简单列举,创立一种能把国际、国内政治融合为一体,能够解释国际、国内政治相互联结的理论[4]。他创立的双层博弈模式,即决策者在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同时进行博弈,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就是对国际、国内二个层次分析法的综合。
二、理论框架
双层博弈理论要研究的问题是,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领导人如何进行外交决策?如何实现国际合作?他首先假定,中央决策者要同时协调国际国内事务,在外交政策选择中既面临战略机遇也面临战略挑战[4]。其次,他把外交谈判分为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对这两个层次的谈判,决策者都要同等认真对待,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因素,否则协议就得不到外国的接受和国内的批准,从而不能实现国际合作。比较而言,国内层次的博弈更为重要,因为决策者关于国际谈判的立场是由其对国内能否批准的考量决定的。外交谈判能否成功、国际合作能否实现,取决于各自的获胜集合是否存在交集。
具体地说,双层博弈理论的基本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双层博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模式
普特南认为,许多国际谈判的政治可以设想为双层博弈。在国家层次,国内集团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有利于己的政策,政治家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来谋求权力。在国际层次,政府谋求满足国内压力的自身能力的最大化,同时谋求国外发展负面结果的最小化。只要主权国家还存在,仍然相互依赖,中央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层博弈。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出现在两个棋盘上。在国际谈判桌的对面,坐着外国谈判对手,在领导人的旁边坐着外交官和其他国际顾问。在国内谈判桌周围,领导人的后面坐着执政党党员、国会议员,国内代理人的发言人,主要利益集团的代表,领导人的政治顾问。双层博弈的异常复杂性在于一个棋手在这一个棋盘上的行动是合理的(如提高能源价格、退让领土、限制汽车进口),在另一个棋盘对同一个棋手来说也许就是不明智的。在国际谈判桌上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的首席代表可以导致谈判失败。反之,未能满足国内谈判桌上的人的利益诉求的任何领导人都有下台的危险。有时,聪明的谈判代表在一个谈判桌上的一着棋会在另一个谈判桌上建立联盟,从而实现谈判目标。总之,普特南认为,双层博弈能比其他建立在单一国家行为体假定上的模式更好地抓住国际谈判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双层博弈理论把政治家作为主要的战略行为体,政治家的战略是其同时对国际国内两个棋盘面临的约束和机遇的双面算计。外交战略和战术同时受到其他国家接受程度和本国民众批准可能的制约。外交是一个战略互动的过程。在外交活动过程中,行为体需要同时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情况[1]。
2.双层博弈的关键:批准(Ratification)和获胜集合(Win-sets)的重要性
双层博弈理论假定,在国际谈判中,每方只由一个领导人或首席谈判手作为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政策偏好,只是谋求达成对他所代表的人有吸引力的协议。为方便分析,普特南把谈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层次Ⅰ,谈判代表之间讨价还价,达成暂时协议;层次Ⅱ,每个集团内部就是否批准协议分别进行讨论。把谈判过程按先后顺序分成两个阶段,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对研究是有益的。在现实中,预期结果非常重要。可能层次Ⅱ的预先商谈和争论就已经决定了层次Ⅰ的谈判立场。反之,层次Ⅱ批准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层次Ⅰ的谈判。实际上,由于预计到协议在层次Ⅱ会被否决,层次Ⅰ的实际谈判可能还未开始就流产了。由此可见,在理论上,层次I的协议最终需要在层次Ⅱ获得批准,这是两个层次的关键点。“批准”可能是层次Ⅱ正式的投票程序,例如,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批准条约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同意票。层次Ⅱ的行为体可以代表政府部门、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甚至是公众舆论。批准过程的唯一正式的约束是同一个协议需要双方批准,不重开层次Ⅰ谈判,层次Ⅰ达成的协议就不能在层次Ⅱ修改。换句话说,最后的批准就是同意或拒绝,对层次Ⅰ协议的任何修改都被视为拒绝,除非协议的其他各方同意修改。由此,普特南把“获胜集合”定义为当对层次Ⅰ协议进行支持或否决的表决时,在表决者中得到必需数量的支持者的集合。普特南认为,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因,层次Ⅱ获胜集合的大小对理解层次Ⅰ协议非常重要。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胜集合越大,层次Ⅰ协议越有可能达成。根据定义,任何成功的协议都应在协议各方获胜集合内。因此,只有各方获胜集合形成交集(overlap),达成协议才是可能的。获胜集合越大,越有可能产生交集。反之,获胜集合越小,谈判失败的危险越大。应把自愿违约(voluntary defection)与非自愿违约(involuntary defection)区别开来。自愿违约指在缺乏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的理性自我的违约。非自愿违约指由于协议未得到国内批准,代理人的违约行为。二是各方层次Ⅱ获胜集合的相对大小会影响国际谈判的共同所得的分配。一个谈判方的预期获胜集合越大,他更容易被其他谈判方“推着走”(pushed around)。反之,获胜集合小可能是谈判优势。
3.获胜集合的决定因素:层次Ⅱ偏好和联盟、层次Ⅱ制度、层次Ⅰ谈判代表的战略
获胜集合的大小与层次Ⅱ投票者间的权力分配、偏好和可能的联盟。普特南认为,任何可验证的国际谈判双层博弈理论必须植根于关于层次Ⅱ主要行为体的权力和偏好的国内政治理论。对层次Ⅱ政治细节的抽象,可以总结出决定获胜集合大小的原则。一是投票者达不成协议(no-agreement)的成本越低,获胜集合越小。达不成协议的成本对不同的投票者程度不一。对有些投票者来说成本低,而对另一些投票者来说则成本高,前者比后者更怀疑层次Ⅰ的协议。因此,有些投票者是一般性地反对或支持层次Ⅰ的协议,不关注协议的特定内容,而另一些投票者的决定则取决于协议的特定内容。获胜集合的大小取决于“孤立主义”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的相对强弱。小国、经济更开放的国家、对外依赖性强的国家支持国际合作的力量比自足性强的国家大。因为,在自足性强的国家,对大多数投票者来说,达不成协议的成本低,获胜集合小,谈判立场强硬,达成的国际协议少。二是在利益偏好一致(homogeneous)冲突和利益偏好不一致(heterogenerous)冲突两种情势下,谈判代表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在国内利益偏好一致(homogeneous)情势下,谈判代表在层次Ⅰ赢得越多,协议越容易在层次Ⅱ获得批准。谈判代表在层次Ⅱ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处理投票者的预期与谈判结果的落差。双方都不可能在己方投票者中找到对方投票者要求的同情者,或在对方投票者中找到己方投票者立场的支持者。在利益偏好不一致(heterogenerous)冲突情势下,谈判者面临的问题则复杂得多。例如,1919年,一些美国人反对凡尔赛条约,因为它对战败国太严厉,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对战败国太仁慈。所以,“越多越好”的原则不再适用。在有些情况下,层次Ⅰ的谈判手可能在对手国内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因此,可能出现跨国联盟,他们向各自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采取他们共同支持的政策。三是在不同集团和议题间的投票者参与率差异会影响获胜集合的大小。例如,国际金融问题比国际贸易问题的投票弃权率高。层次Ⅱ投票者的参与积极性会随着议题的政治化而发生变化。政治化、公开化程度越高,获胜集合越小。所以,职业外交官都强调保守秘密对于谈判成功至关重要。四是议题的单一或多重性会影响获胜集合的大小。在多重、复杂议题的谈判中,层次Ⅱ的各个利益集团在不同的议题上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偏好。一般地说,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具有最大利益的集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持最极端的立场。如果每个利益集团都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么什么协议也不能达成。因此,首席谈判代表必须在不同的议题、不同的集团之间进行平衡、协调。此外,还可采取议题联系(Issue Linkage)的办法以达成协议。普特南称之为协同联系(Synergistic Linkage)。例如,层次Ⅱ的大多数投票者反对某个政策,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作为回报,如果首席谈判代表能说服对手达成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国际协议,可能有些投票者就会改变原来的政策选择,批准协议。普特南预计,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协同联系将越来越多。
获胜集合的大小与层次Ⅱ的制度安排。批准程序会影响获胜集合的大小。例如,需要三分之二投票支持的制度的获胜集合比需要半数投票支持的简单多数制度的获胜集合小。普特南认为,民主国家如美国的获胜集合比专制国家小,谈判优势更大,但是非自愿违约的可能性也更高,国际合作更为困难。此外,其他制度也会影响获胜集合的大小。如执政党的严格纪律,能扩大获胜集合。反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松弛的政党纪律会减少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层次Ⅱ投票者中,中央决策者的自主权越大,获胜集合越大,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性越大。不过,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相对于国内压力的自主权越大,在国际谈判中的相对优势越小。例如,专制国家的谈判代表比民主国家的谈判代表让人相信达成不利协议的阻力和压力小。普特南指出,为了研究的简化,只限于两个层次。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制度安排规定需要数个层次的批准,这增加了获胜集合分析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例如美国和欧共体农业贸易谈判。根据《罗马条约》规定,欧共体国家的共同农业政策的修改需要代表成员国的部长理事会一致通过。然后,决定还需要在各国内部获得批准。在多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还需要在各个政党内部得到批准。同样,在美方,协议需要得到大多数农业组织的支持。在各个组织内部,需要各个利益集团、地区的支持。
获胜集合的大小与层次Ⅰ谈判代表的战略。每个层次Ⅰ的谈判代表都有兴趣最大化对方的获胜集合,但是涉及到他自身的获胜集合,他的动机则是复杂的。获胜集合越大,他越容易达成协议,但是他的相对谈判地位也越弱。假定某个谈判代表为批准某个协议希望扩大其获胜集合,他可以采用传统的额外支付(Side-Payments)和良好愿望(Good Will)战略。在博弈论和现实政治中,利用额外支付来吸引边缘支持者(Marginal Supporters)是个熟悉的战略。例如,为了说服立场不坚定的参议院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卡特政府提出了许多有利条件(如公共工程)。在双层博弈中,额外支付既可来自无关的国内,也可能是来自国际谈判。额外支付在双层博弈中的价值是在于促进协议批准的边际贡献,而不是对接受国的总体价值。它针对的是边缘投票者,而不是所有投票者。例如,在贸易谈判中,它针对的不是自由贸易主张者,也不是保护主义者,而是立场中间者。此外,首席谈判代表在国内地位高、声望好更容易使协议得到批准。每个层次Ⅰ的谈判代表都高度关注双方的受欢迎程度。因为,A方受欢迎能扩大其获胜集合,提高成功的可能和B方的谈判地位。所以,在正常情况下,谈判代表应该想方设法提高在各自投票者中的地位和声望。因为,高级谈判代表能提供更多的额外支付和良好愿望,所以,外国人都更愿意与政府首脑而不是低级官员谈判。
此外,普特南还探讨了信息不确定(Uncertainty)、谈判战术(Bargaining Tactics)、重构(Restructuring)和回应(Reverberation)及首要谈判者的作用(the Role of Chief Negotiator)对获胜集合大小、变化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三、双层博弈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普特南提出双层博弈理论后,引起了国际政治学界的关注,认为该理论为分析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联系、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框架和视角。此后有不少学者对它进行拓展、深化,从而在不同方面补充、发展、完善了该理论①。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
1.扩大研究范围,证明双层博弈理论的普适性。代表作是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哈罗德·雅各布森(Harold K.Jacobson)、罗伯特·普特南合编的《双面外交: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该书研究两个基本问题:(1)普特南的洞见和概括是否适用于包括非西方国家的谈判;(2)是否适用于经济问题外的其他谈判。此外,还拟探讨普特南的比喻或模式发展、提高、扩展的程度[1]。读过普特南的那篇论双层博弈理论的文章的人可能有种偏见,认为文中的例子主要是二战后工业发达民主国家间的经济合作谈判,这只是国际谈判中的一个特例,是以经济问题和正和博弈为优势的国内理论。为了证明双层博弈理论的普适性,该书作者在选择案例时注意了广泛性,包括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前、战后初、主要是近期外交,共11个案例,其中4个是关于安全和土地问题的,3个是关于南北关系的,4个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每个案例都利用双层博弈理论框架解释谈判结果的两个层面:(1)达成协议的成功或失败;(2)得失的分配。每一章都包括两个案例,一个成功,另一个失败。该书通过这11个案例的研究,对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式的理论含义在这几个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政治家利用守门人的角色获得的自主权;在发出信任威胁中的国内支持的作用;在国际谈判中不对称的国内政治信息的作用;政治家作为鹰派、鸽派、代理人的区别的重要性[1]。
2.对双层博弈理论概念化,提出可验证的假设。代表作是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的《利益、制度、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作者认为,普特南的双层博弈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分析框架,但是它缺乏可验证的假设,理论化程度不够。该书的目标
是对双层博弈理论概念化,提出可验证的假设。该书的核心议题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一个现实困惑是,为什么国家能互相合作?为什么国家不能互相合作?作者认为,国家间的合作受对他国的相对所得和欺骗行为的恐惧的影响要小于合作行为的国内分配的影响。合作协议在国内产生了赢利者和失利者,因此形成了支持者和反对者。这些集团间的内部斗争塑造了国际合作协议的可能性和性质。实现合作的国际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内政治,这种谈判也常常因为国内政治发起。合作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国内政治考虑的影响,因为合作是国内政治斗争另一种形式的延续。作者假定,国家不是单一行为体。国内政治不是严格的等级政治,而是在等级政治、中间状态、无政府状态间变动的连续体,其具体状态受三个因素决定:国内行为体(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利益集团)的偏好,规定权力如何在行为体中分配的政治制度,行为体间的信息分配。作者首先探讨了行为体的利益与政治制度间的关系。利益和制度的互动如何决定政策选择,社会和政治行为体在塑造政策中的相对重要性,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相对优点。其次探讨了政治制度在决定政策选择中的作用。行政部门决定议程,议会批准议程,利益集团直接影响政治行为体的偏好,扮演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但不能直接参与决策过程。最后探讨了信息分配的重要性。信息在行为体间分配的不完整性、不对称性、不确定性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降低效率,二是导致行政部门拥有信息的政治优势,立法部门没有这个优势[5]。
3.对合作后外交政策过程的长期性和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协议批准的影响进行研究。代表作是杰弗里·兰蒂施(Jeffrey S.Lantis)的《国内约束与国际协议的违约》。该书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即使国家领导人相信合作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时,仍然决定不遵守国际承诺?对国际组织承诺的违约有时让人吃惊,因为从结构条件预测应该合作(即有国际合作的巨大国际压力)。有时是非自愿的,因为领导人相信合作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作者认为,普特南在他那篇1988年发表的文章中对这种违约原因提供了最流行的解释,认为这是领导人在进行双层博弈时国际国内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但是,普特南及其理论支持者对合作后外交政策过程的长期性和国际协议批准所需时间的含义研究不够,对合作后过程和国内政治因素造成不坚持认可合作的国际承诺的计划的可能性研究不够。该书的目的是弥补普特南理论的不足,认为国际违约是承诺后政治阶段领导人将问题置于公众议程,外交决策受到国内约束的结果。承诺后阶段就是国内条件与行为体就国际协议联合起来的时期。它发生在国际组织环境中领导人承诺与他国合作之后,但是在最后作出分配政府资源认可诺言的外交决策之前。作者提出了以三个观点为基础的承诺后政治框架:(1)国际合作是连续过程的结果,不只是国内与国际条件同时作用的结果。领导人在国际组织框架内作出的与他国合作的初步承诺(不论问题领域)动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条件,划定了承诺后阶段的开始。(2)在承诺后阶段,领导人必须建立支持国际合作的共识。至少有五个国内政治条件可能影响领导人最初的国际合作的持久性:主要政党的一致,执政联盟的共识,外交决策效果的对称,选举表现和公众支持。(3)这些国内政治条件与执政精英的相近程度决定了对合作的外交决策的相当影响[6]。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双层博弈理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双层博弈是关于外交谈判的理论。学界对外交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是,没有谁能否认,外交的狭义解释就是通过谈判处理国际关系。既然谈判是外交的主要方法,那么从谈判角度来研究外交问题应是适当的。其次,双层博弈理论政治家视为外交谈判中的战略行为体。谈判立场是由政治家确定的,但是外交谈判要取得成功,达成协议,就要求政治家确定的谈判立场既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能为国内所批准。第三,双层博弈理论着重从国际与国内政治互动的角度来研究外交谈判。传统的外交谈判研究把国家看成是内部完全一致的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利益最大化为谈判目标。在双层博弈理论看来,在外交谈判中,谈判方不是内部完全一致的单一的理性行为体。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领导人对国内各种集团的利益诉求的折中。
双层博弈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创立的,是以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运用双层博弈理论研究非西方政治制度国家的外交决策时难免有局限性,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一定的修正和改进。正如有个美国学者指出的,“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方式差别很大。绝大多数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关注的都是美国的政治,如大众舆论的作用,行政机构和国会之间关系,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内部每年的预算之争的性质”。“这里就存在一种危险:当美国人把决策、冒险、官僚机构的预算之争、长期军备竞赛或严重危机中的互动行为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当作理性来考虑的时候,通过观察美国决策者的行为而得到的教训和经验就有可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到各种不同的决策环节中去,如莫斯科、北京、东京、新德里及曼谷”[7](P645-646)。因此,不能简单化地生搬硬套这个理论来研究非西方国家如中国的外交。
注释:
①See Jeffrey W.Knopf,"Beyond Two-Level Games:Domestic-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Negoti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Autumn 1993),pp.599-628; Keisuke Iida,"When and How Do Domestic Constraints Matter? Two-Level Games with Uncertainty,"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7,No.3.(Sep.,1993),pp.403-426;Peter F.Trumbore,"Public Opinion as a Domestic Constraint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Two-Level Games in the Anglo-Irish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3.(Sep.,1998),pp.545-565 ;Peter F.Trumbore ,Mark A.Boyer,"International Crisis Decisionmaking as a Two-Level Proces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37,No.6.(Nov.,2000),pp.679-697;Simon Hug,Thomas Kig,"In View of Ratification:Governmental Preferences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at the Amsterdam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Spring,2002),pp.447-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