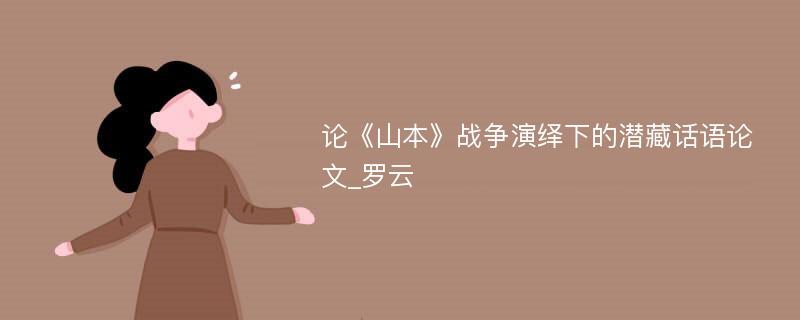
摘要:贾平凹新作《山本》以秦岭为书写背景,记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涡镇人民如何生存的传奇故事,而贾平凹却在如此宏大的时代风云下埋藏了他的潜藏话语。因此本文拂去战争书写的表象,进一步从中探究作者背后的意图。即从硝烟中的日常性、欲望中的尘土性以及死亡中的悲悯性阐释作者的潜藏话语,并深入作者内心,力求挖掘其精神指向。
关键词:日常性;尘土性;悲悯性
据贾平凹所说其原名是《秦岭志》,后来改成山本,并且作者创作的原初动力犹如《山本》里麻县长一样书写再版《山海经》的梦想,因此文本里描绘了大量的奇珍异兽和山川河流。同时也因为小说的背景置于军阀混战时期,其便以战争的形式书写,犹如小说的开头写到“涡镇之所以叫涡镇,是黑河从西北下来,白河从东北下来,两河在镇子南头外交汇了,那段褐色的岩岸下就有了一个涡潭”[1],因此黑与白的交汇形成了小说的中心涡镇。可是贾平凹却说“这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不是写战争的书”[2],由此看出作者虽书写了斗争,但在深层里潜藏了他的精神指向。
一、硝烟中的日常性
当他人询问贾平凹为什么涡镇人民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都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他这样回答道:“人生就是日子的堆集,所谓大事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写日常生活就看人是怎么活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3]因此虽然作者将自己的故事聚焦点置于一个入了冬不是刮风,就是不刮风的涡镇里,并且这个涡镇里的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但如果丢个东西下去,涡潭就动起来……能把什么都吸进去翻腾搅拌似的”[4],其隐喻涡镇将吸引各种力量基于不同目的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细读文本发现,战争时不时与涡镇人民的日常生活挂钩。开篇就写到井掌柜因为钱财遭到投身于革命却因缺乏革命活动经费的井宗丞绑架,而就因为被抢走了互济会的钱,不得不卖掉土地,在这期间井掌柜提着酒去找旧友闲聊,以及因雨大还在杨掌柜家里打牙祭,但是井掌柜最后却也因卖地而死。由此看来在涡镇平静生活的井掌柜也被间接地卷进战争当中,但是在作者的叙述下,战争所带来的紧张感相应地在这种日常生活性中磨损,反而增添了生活气息。
纵观小说的布局,作者主要聚焦在两条线上:一条是以井宗秀与陆菊人为代表的主线,其主要叙述涡镇所发生的故事;另一条是井宗丞他们所在的秦岭游击队,多表现军阀混战。由此汇集而成《山本》。在围绕井宗秀和陆菊人的这条线上,与涡镇相关的一切由此引出,同时正如贾平凹所说的,人如何活,人与人如何相处都在战争的硝烟中一一展现,像粮食短缺、生意问题、男女关系等等。在小说中,井宗秀与陆菊人之间的关系如迷一般存在。而两人之间的交集源于井宗秀阴差阳错得到了陆菊人神秘的“三分地”,由此开始了命运的转换,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争夺当中。因此,在以井为线索的权力争夺里,陆菊人则以金蟾的转世身份辅佐他,但两人身上时隐时现的情愫也牵动着读者。随着井宗秀权欲逐渐地膨胀,井与陆之间也产生嫌隙,小说中以修建戏楼为导火索,两人关系也因此恶化,所以以陆菊人和井宗秀为主的男女关系在争斗的背景下极致地展现出来。还有因战事,涡镇普通民众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也因之发生变化。涡镇因为多方势力的翻搅,所以在粮食上面经常出现短缺的情况,像小说中写到小贩们因为粮食问题,不得不将米泡一晚上而加重米的重量,从而获得高利润,这样的做法虽令人厌恶,但却也令人同情。战乱下的粮食紧张,通过涡镇百姓生活情境展现出来,这种硝烟下的日常性正是作者在建构中所达到的目的。
战争是残酷的,游离失所,饿殍满地,但在作者的叙述下,战争夹杂着生活的日常性,不仅将小说的旨趣置于人本身上,而且极大地展现战争背景下民众的生活场景。
二、欲望中的尘土性
“蜂有天毒,人也有天毒……人不知道削减啊!”[5]在小说的开篇,井掌柜死后,陈先生出场说的这句话也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做了个总概,每个人也因“天毒”将自己毁灭。
井宗秀因为父亲的死,回涡镇有板有眼地处置父亲突然弃世后的家事。这样一位初通人事的少年不仅安顿好六神无主的母亲,又设法将父亲很好的安葬,并且之后意外获得一份难能可贵的三分胭脂地,但也正是这份地将井宗秀的命运彻底改变了。在以保平安的初始目的下的井宗秀却也在权欲的膨胀下走向了自我的灭亡,这一点集中在井宗秀一意孤行地非要在涡镇建造戏楼这一细节上。在已经艰难建造好钟楼后,井宗秀又要建造戏楼,因此不断地横征暴敛,百姓的抵制与反抗在他眼里也不值一提,就这样他慢慢地走向了自己的另一面——权欲,由此权欲不断地吞噬着他。其实反过来从作者在塑造井宗秀的形象上看出,他原本的性格特征也预示他后来的结果。初始登场的井宗秀长得白净,而且在多方算计的情形下从画家手里学到绝活,由此便将井宗秀聪明,有眼色的形象树立起来。之后在对于麻县长要求他说出三种动物时,井宗秀给出“龙、狐、鳖”这个答案,龙意味着井认为自己能够飞黄腾达,狐则指他人认为他精明能干,然而这个“鳖”的形象是他的根本,善于隐忍。因此由此看出井宗秀只是在追逐权欲的途中暴露出本性,所以不论那三分地是否具有灵性,在开发出井宗秀的权欲之后,他是会不折手段的追求他一心企盼的权力。而与井宗秀相悖的人物是陈先生,他不仅以郎中的身份治疗着涡镇人身体上的疾患,而且以自己的智慧启发着芸芸众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陈先生一直以医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着涡镇所发生的一切,但时不时的发生充满哲理性的话语化解人生的种种苦难。而介于井宗秀无尽的欲望与陈先生视欲望为尘土之间的陆菊人身上不仅具有烟火气,而且以淳朴、善良的品质存在着。陆菊人来往于井宗秀与陈先生之间,一方面因与井宗秀微妙的情感而辅助他的权欲,另一方面受着陈先生的智慧启发而应对各种人生迷途。陆菊人在小说中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女性,一个人将自己婆家杨家打理得很妥善,同时在井宗秀身旁给与其激励与谏言,之后甚至接受井宗秀的委托管理茶行,果敢地改造旧的经营方式,使茶行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在面对井宗秀权欲不可遏制的时候,陆菊人站出来对其进行规劝,他们之间出现问题是在井宗秀起意要杀阮氏十七位族人时,面对陆菊人的谏言,井宗秀却不以为然地拒绝了。或许从这次,井宗秀与陆菊人产生了隔阂。所以当井宗秀死后,涡镇最终也在权欲下变成了一堆尘土,而将权欲视作尘土的陈先生与陆菊人也是涡镇仅存的生还者。
权欲推动小说的发展,但涡镇的人最终也葬于权欲之下。井宗秀追逐权欲,陈先生无视权欲,以及陆菊人在追逐与无视之间徘徊,最终意识到人生最终不过一堆尘土,再辉煌的人生,也是一堆尘土。
三、死亡中的悲悯性
战争伴随着死亡,而小说中死亡也夹杂着悲悯。小说中,陈先生把人喻为萝卜,指出生命只是一根萝卜被拔,别的萝卜挤到空缺的地上,继续生长着。《山本》里,死亡似乎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于生命的逝去没有任何的惋惜,可是在细读文本时,会发现死亡与悲悯是并向而行。死亡俨然成为小说的表层,潜层下悲悯无处不在。
在遍布死亡的《山本》中,打打杀杀的场景辗转在人类身上发生,甚至在作者的叙述下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死法,井掌柜掉入粪坑中溺死,安顿好军人的平民百姓也最终被无辜杀死,包括后面阮天保攻打涡镇时的惨死,等等都是将死亡叙述地淋漓尽致。可是就在死亡惨景的表象下,悲悯之情却也油然而生。小说的开头,在叙述陆菊人时,这似乎是一个通万物之灵性的女性,“(陆菊人)看纸坊沟两边的乱峰直起直立常插着刀弋,就觉得充满了杀气,听啄木鸟敲树的声音并不认为好听,而只感到树是在疼”[6]。被称为“大地之母”的陆菊人其实在开篇就体现出她对万物怜悯之情,直到后来嫁进杨家,恪尽职守地守护着家人,辅助开始仅还是希望涡镇平安的井宗秀,陆菊人这种类似地母宽厚的胸怀正是将死亡所带来的恐怖稀释,从而带来无限的悲悯之情。其次,宽展师傅和她的地藏王菩萨庙也是充满了悲悯感。“宽展师父是个尼姑,又是哑巴,总是微笑着,在手里揉搓一串野核桃,当杨钟和陆菊人在娘的牌位前上香祭酒,三磕六拜时,却从怀里掏出各个竹管来吹奏,顷刻间像是风过密林,空灵恬静,一种恍如隔世的忧郁笼罩在心上,弥漫在屋院。”[7]这是宽展师父的初次登场,她的出场将一切安逸、和谐展现出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尺八和地藏王菩萨庙,宽展师父每次吹奏尺八,都是在超度魂灵,超度涡镇的苦难。而地藏王菩萨在佛教文化当中属于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形象,他所企及地是度尽人间一切苦厄,普度众生。宽展师父以一种精神支柱的形式长存于涡镇,另一面陈先生与他的安仁堂则是从身体上给与他们安慰。就在作者这样的安排下,涡镇在战乱中的饿殍满地被安妥着。
生命是人存在的根本,作者在叙述中将死亡轻描淡写地叙述出来,但是在战争的潜层下埋藏了作者的悲悯之情,只是正如《三本》的结尾所说,涡镇成一堆尘土了,最终成“空”是生命的尾。
遍布争斗的《山本》,所有这些构成小说的骨架,而日常生活性、悲悯性都成为血液注入骨架当中,这样有血有肉的小说在品味骨架枯燥的同时给与了趣味性与生活性。同时小说也借鉴了许多明清小说的影子,宽展师父与陈先生形同《红楼梦》中“一道一僧”,小说中井宗秀、阮天保、井宗丞三方的力量类于《三国演义》中三足鼎立之景,甚至在许多杀人场景的叙述上类于《水浒传》中的血腥场面,它们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出属于秦岭的传奇故事。只是因作者在写作前将工作倾注于“收集秦岭二三十年的许许多多传奇”,而面对如此庞杂混乱的素材,作者为努力将之融合,从而造成篇幅过长,有些许冗杂之感,甚至在阅读过程易产生厌倦。其叙述方式犹如一位老者不紧不慢地讲着秦岭涡镇的传奇故事。或许作者要表达的太多,追求的太多,小说中有些故事与故事的关联性并不紧凑,譬如在井宗丞与井宗秀的两条武装线上,虽然开头井宗丞与井宗秀的亮相与涡镇紧密联系,可是在接下来的叙述上好像断了联系,而是成为了一个涡镇的传奇故事,一个秦岭游击队的故事。
因此,正如陈思和所说,“在《山本》中,‘一半’的艺术是表现永恒和完整,秦岭就是永恒和完整的象征……秦岭又是有生命的,它演化为大千世界,孕育了林林总总的生命现象……短暂而且破碎、偶然而且无常,此乃是‘另一半’的秦岭生命的故事”[8]。虽然秦岭人世风雨是短暂的,但是秦岭以其永恒长存于世间,甚至成为人类真正的归宿。
参考文献
[1]贾平凹.山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
[2]贾平凹.山本·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43页.
[3]杨辉,贾平凹.究天人之际:历史、自然和人——关于《山本》答杨辉问[J].杨子江评论,2018(3).
[4][5][6][7]贾平凹.山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17、2、5页.
[8]陈思和.试论贾平凹《山本》的民间性、传统性和现代性[J].小说评论,2018(4).
作者简介:罗云(1994.11-),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论文作者:罗云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0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12
标签:秦岭论文; 作者论文; 小说论文; 山本论文; 宽展论文; 战争论文; 尘土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0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