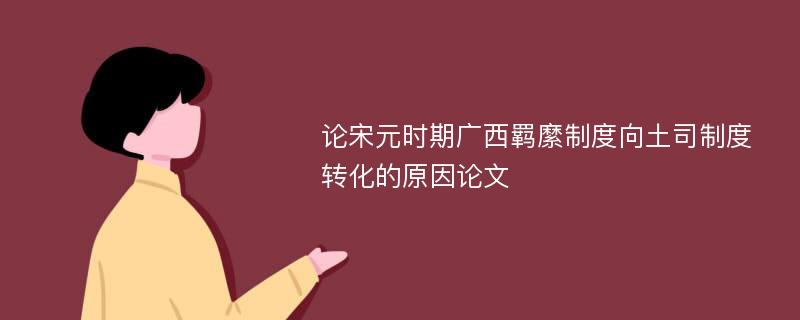
论宋元时期广西
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原因
黄金东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 100081)
摘 要: 宋元是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在广西实行的羁縻制度弊端不断显现,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朝廷统治广西思想的变化,羁縻制度下松散的统治方式与朝廷的统治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此,羁縻制度被土司制度所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基于当时广西地区的社会现实,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经济基础;制度变迁
唐宋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铁制农具在广西地区的普遍使用,加上大量移民的迁入,当地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至唐末宋初,广西东部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而西部地区也逐步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的转化。这一时期,中央朝廷在广西实行相对松散的羁縻统治方式,把广西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权力体系当中。应该说,羁縻制度在前期适应了广西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羁縻制度的各种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同时,边疆形势的变化,原来的统治方式与朝廷的统治思想冲突也越来越明显。此外,广西地区不断成长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也急需一种新的制度来确认,从而保障其继续向前发展。于是,羁縻制度被土司制度所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至元代,建立在羁縻制度基础之上,管理更严密,可以实现对当地社会更好控制的土司制度得以在广西确立。
宋元时期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它牵涉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是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经济上,封建领主制的形成,为广西土司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后在广西实行的土司制度,不仅以封建领主制为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对唐末宋初形成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种确认。除此外,以下几个方面也是其转化的重要原因。
一、羁縻统治政策弊端显现
唐宋时期在广西实行的羁縻制度,是一种在不改变当地社会和经济制度前提下,任用当地首领进行统治的方式。广西羁縻制度的萌芽阶段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岭南后,除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外,还在民族地区设有专门的“道”,立典客、典属国等官管理少数民族。汉代,除设“道”外,还设有“初郡”“边郡”。南北朝时期,则设置“左郡”“左县”或“俚郡”“僚郡”。这些机构大多通过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以其故俗治”的方式来管理,至多设置一些流官来进行监护,很难谈得上有效治理。正如汉代尚书令虞诩所指出的那样,“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1](P2833)可见,秦汉时期,广西对中央王朝来说,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意义,远离中央核心,处于边缘区域,不在重点拓展的疆域范围内。
唐代,中央政府空前强大,周边部族纷纷归附,各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在周边各民族的治理上,“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2](P1119)在内属蕃夷地区设置羁縻州县以法律的形式被确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王朝在广西等壮族先民地区总共设有羁縻州57,羁縻县48。[3](P429)宋代在广西进一步完善了羁縻州县的设置,并增加了洞的建置,政府的控制力得到增强。然而,唐宋时期的广西仍处在“化外”边缘,并不被重视。《桂海虞衡志》载:“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其法制尤疏,几似化外。”[4](P135)周去非著《岭外代答》亦曰:“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5](P3)因此,朝廷对于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采取“疏而治之”的政策,尽量采用不予干预的态度。[6](P13)朝廷对待广西的消极和轻视态度,使得整个广西地区的发展相对有限,左右江等西部地区奴隶制的消亡和封建化仍受到重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同时,当地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引起了各民族对宋朝统治的斗争。其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当属宋皇祐四年(1052)四月广源蛮首领侬智高领导的因朝廷屡次拒绝内附而被迫起兵的斗争。侬智高起事后,由于宋朝廷在广西采取松散的羁縻制度,致使守备薄弱,面对局势束手无策,官兵纷纷望风而逃,直至三四个月后才组织起队伍反抗。朝廷无力抵抗,使得侬智高“出入十有二州”,官兵“或死或不死,而无一人能守其州者”[7](P258),羁縻制度的弊端在侬智高起事面前暴露无遗。
方铁认为,羁縻制度在朝廷治理边疆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造成边疆蛮夷治策与邻邦应对政策的混同;以羁縻治策为亘古不变之策;羁縻治策的主要内容,主要源自经营北部边陲的经验,未必适合南部边疆复杂多元的社会形态;难以解决与经营边疆相伴的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边疆地区吏治问题突出,边疆官吏大多大权在握且缺少监督,贪渎腐败的情形相当普遍,无法解决大量称职边疆官吏问题;击败、胜出、瓦解蛮夷缺乏切实有效的策略,未能妥善解决“以夷治夷”的问题;对封建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在实践方面亦缺少有效措施。在边疆实行羁縻治策的大多数王朝多未能在边疆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封建教育,不利于华夏文明在边疆地区的传播。[8]
在讨论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各因素时,不能忽视当时广西社会的现实基础这个主体。实际上,所有发生的一切改变都围绕着广西社会主体进行,随着这个主体变动而变动。在所有的因素中,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才是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原因。
二、宋元统治者经营广西思想转变
宋承唐制,在广西边疆地区实行间接的羁縻统治制度。宋初,广西并不是朝廷经营的重点,甚至被视为化外之地。朝廷并不重视对广西的经营,整个广西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这种情况至南宋偏安江南后发生了变化,由于处在南宋的后方纵深地带,广西的地位得到提升,朝廷对广西的经营策略也发生了改变。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仅剩下半壁江山,财政及军需等用度均依赖南方,广南西路由于处在南宋后方纵深地带,政治地位较北宋得到提升,对国防具有重要作用,南宋政府对广西的经营策略变得积极起来。位于南宋版图西南部的广南西路,西接四川、北连荆湖、东邻广东,南与大理国、交趾毗邻。南宋政权南移后,广西的战略地位重要性凸现出来,成为内地的要津,《岭外代答》记载:
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令甲:邕、宜、钦、廉、融、琼州,吉阳、万安、昌化军,静江府,系沿边;柳、宾、贵、横、郁林、化、雷,系次边。总广西二十五州,而边州十七……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5](P3-4)
式中:△S为某一时段城市建成区扩展面积;St+1为监测时段末期建成区面积;St为监测时段初期城市建成区面积。
她们不再有活着的价值,因为她们到了使用的年限。就像汽车需要报废,充气娃娃也需要报废。戴菲儿的报废期限是十五年,但现在,她已经嫁给秦川整整十九年。秦川为她多申请了四年的生命,就像为一辆到了报废期的汽车多争取了三年的使用时间。秦川这样做,或许只因为节俭,或许还因为,他真的不忍将戴菲儿送进绞肉机般的报废机里。
由于较少歧视与偏见,元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边疆地区的经营。元代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扩张受到神的核准和保护,边界之外的所有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16](P405)因此,边疆地区与内地相比并无区别,“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4](P1346)不仅如此,元代统治者还把溪洞少数民族称为“吾民”,至元二十二年(1281),元世祖诏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安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杨赛因不花说:“自今以往,咸奠厥居,流移失所者,招谕复业,有司常加存恤,毋致烦扰,重困吾民。”[14](P1551)这表明,元代统治者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在蒙元统治者看来,边疆不仅是提供赋税物资的来源,也是进攻邻邦的基地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门户,因此应着力经营。在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不但刻意经营边疆地区的各行省,在不少方面还采取内地的方式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深入进行统治,普遍征收赋税,积极发展交通与开办学校,征调土军参加征伐战争等。对于西南边疆,蒙古人早就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当初大将木华黎引郭宝玉见太祖成吉思汗,太祖问以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14](P3521)因此,元朝虽然统治时间较短,但对西南边疆地区而言却是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7]
综上所述,广西在宋元时期统治者眼中逐步由“化外”变成“化内”,最终等同于内地。从宋初的的蔑视到南宋时期经营策略开始积极,及至元代的积极经营,广西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同时也越来越深入卷入王朝的权力体系。伴随着统治者经营广西思想的转变,广西的羁縻制度也得以逐步向土司制度转化。
在上述统治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积极经营广西。元初,置广南西路宣抚司,后改宣抚司为宣慰司。至元十五年(1278),改宣慰司为静江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七年(1290),成立了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至元三十年(1293)又在南丹州成立安抚司。元贞元年(1295)并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抚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正二十三年(1363),置广西行中书省。为了稳固在广西的统治,蒙元在广西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屯田;建立驿站,开通安南往来通道;开采矿藏,收取赋税;建立学校,鼓励广西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等措施。经过积极开拓,广西社会较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279年,蒙古人灭南宋,进而统一了整个中国。蒙古人入主中原,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其统治思想也经历了最初的沿用原有经验,对征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建立元朝后忽必烈接受儒士郝经“用夏变夷”建议,对统治制度进行调整;到仁宗时期则力主以儒术治国的过程。其中尤以第二个阶段的影响最大。后世对忽必烈行汉法极为赞赏:“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14](P377)但是元朝政策具有“二元性”,一方面接受并推行汉法,另一方面又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政策,同时在诸多方面保留了一些蒙古人后的旧俗。因此,由于蒙古族与汉族文化的差异以及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得汉法在元代推行的范围以及元代统治者接受的程度都是有限度的。这种“二元性”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方面,元朝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的民族歧视政策,另一方面,蒙古人本身又属于少数民族,较少有“华夷有别”和“内华夏、外夷狄”的正统观念,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与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土官制度。[15]
这段材料说明,宋代的广南西路,极西南方与极南方的边区地带上的州县,有“外控外邦,内制溪峒”的战略地位。《宋史·地理志》亦载:“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当牵牛婺女之分,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9](P2248)就周边环境来说,广南西路在广南东路之西,荆湖南北路之南,其西北边则是夔州路。就国内形势而言,广南西路为上述诸路的前方屏障。因此,如广南西路有失,则外力可从上述途径入侵,即可直达内地。《读史方舆纪要》载:“始安之峤,吾境内之险也。桂岭左右可飞越者不一处,栰岭峤之材,浮湘水而下,席捲衡、永,风趣长沙,湖南一倾,则湖北必动,动湖北则中原之声势通矣。”[12](P4788)黄宽重先生认为,南宋政权南移后,与当时西南地区大理、自杞、罗殿、特磨道等国及半独立的部落关系日益密切,而广南西路与西南各国及半独立的部落,境土相邻,关系最为密切。[11](P350)由此可见,随着形势的转变,南宋时期广西国防地位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转眼,孩子6个月大了,还有两个月就合同期满了。我该怎么办?失去孩子的惶恐让我寝食难安,终于,我鼓起勇气对陈清夫妇说:“作为孩子的母亲,我已经对两个孩子产生了感情。我也难以割舍掉他们。合同期满之后能不能让我抱走一个?”我一边恳求一边哭泣,还给他们跪下了。
宋朝对广西积极经营的策略使广西经济社会获得相对快速发展。广西地区在统治者眼中也由“化外”变成“化内”之地,这从宋高宗处理南丹莫公晟事件可以看出这一变化。南宋绍兴三年(1133),南丹州首领莫公晟围观州,焚宝积监,杀知监陈烈。面对此次叛乱,朝廷一改以往一味讨伐的做法,而是采取安抚息事的对策,“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检使、提举盗贼公事,给以南丹州刺史旧印,公晟未受命。二十四年,公晟始贡马,率诸蛮来归。”面对这一结果,宋高宗对辅臣说:“得南丹非为广地也,但徭人不叛,百姓安业,为可喜耳。”[9](P14201)可见,南宋时期统治者对广西地区并非简单以扩大版图而高兴,而是因为百姓安居乐业高兴,这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大改变,表明广西开始由“化外”转向“化内”,其本质则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广西的统治,这也是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用料:干葱头、大蒜子、粤式糖醋汁各100 g,李锦记豆瓣酱75 g,美极鲜味汁、白兰地酒、红葡萄酒、味精各50 g,老妈甜米酒200 g,色拉油 500 g(约耗50 g)。
随着广西地位的提升,统治者对广西的经营变得积极起来。绍兴初年,荆湖南路宣抚使李纲上疏高宗指出:“广南西路五十余州,旧号荒远,在今日实为要地。……兼两路皆有瑶人溪峒,乘势必须作过;广西与交趾相邻,恐亦有所窥伺,道里去朝廷最远,将来兵力难及。朝廷不可不深留意于此。”[13](P4995)因此,广西成为南宋朝廷经营的重点地区之一。从朝廷对广西盐政的经营就可见一斑。盐业作为广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时人曾称:“今日广右漕计,在盐而已。”[5](P179)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同时为了保证与西南少数政权及部落盐马贸易的正常进行,广西的盐政在整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上占有重要地位,“绍兴八年(1138),诏二广盐,通行客钞,专置提举一员于广州,尽领两路盐事。”[5](P183)经过苦心经营,广西盐政取得相当可观的收入,“一岁卖及八万箩,每箩一百斤,朝廷遂为岁额。每一箩钞钱五缗,岁得四十万缗,归于大农。内有八万四千四百缗付广西经略司买马,三万缗应副湖北靖州,十万缗以赡鄂州大军,余悉上供。”[5](P183)
三、特殊的社会基础是广西土司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侬智高起事后,迫使宋朝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检讨朝廷轻视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政策的失误。直史馆苏绅上言:“国家比以西北二边为意,而鲜复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诚不可不虑也。”[9](P9809)谏官余靖认为“皆由朝廷中外措置乖错,以起斯患”。[10](P3615)这促使宋朝统治者开始经营广西防务,加强对广西的控制。据《桂海虞衡志》记载,其主要措施有“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同时设置知寨、提举统摄各首领,减少各部之间的攻掠。[4](P135)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广西地区生产得到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但是整个北宋朝廷对周边民族经营的重心仍在西北,整个广西的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正如黄宽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北宋的首都在开封,政治与外交事务上仍以契丹和西夏为主,而相对的,西南边防及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就居次要地位。[11](P353)因此,整个北宋时期对中央王朝经营广西的成效不应高估,广西社会发展仍落后于其他地区,中央政权对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力仍相对有限。随着羁縻制度的弊端的不断显现,急需探寻一种新的统治方式。
其次,瘴气的存在影响了中央朝廷对古代广西的控制和经营,只能依赖当地土官进行统治。宋元时期,广西地区仍是瘴气遍布的地方,使得汉族官员不愿前往任职。为此,朝廷对前往的官员都是优渥有加。宋代规定,到邕州、宜州、钦州等地任知州,可准许报一子入官。《宋史》载:“广南转运、提点刑狱奏子孙或期亲合人官一人……邕、宜、钦极边烟瘴知州,听奏子孙一人。凡因战阵物故及殁于王事,许官其子孙。”[9](P3729-3730)元代,凡有资品的官员调到广西少数民族州、郡任职,给予提升一等或二等。《元史》载:“至元十九年省议,若腹里常调官员迁入两广、福建溪洞州郡者,于本等资历上,例升二等。”[14](P206)元朝甚至改变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14](P106)的规定,在广西地区改由汉人充任达鲁花赤,“左、右江口溪洞蛮獠,置四总管府,统州、县、洞百六十,而所调官畏惮瘴疠,多不敢赴,请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军官为民职,杂土人用之。”[14](P315)这就从国家官僚体系上肯定了“土人”即土官的政治地位。其他地区官员不愿前往,直接派驻军队则代价太大,也不太现实。早在隋朝时期,隋军进入宁氏世守的南平地区时就曾“阻瘴,不能进”[2](P6326)。宋庆历六年(1046)仁宗诏曰:“顷以东兵戍岭南,冒犯瘴疠,得还者十无五六。”[9](P4899)《宋史·张田传》亦说:“京师禁兵来戍,不习风土,往往病于瘴疠,田以兵法训峒丁而奏罢戍。”[9](P10706)可见,在当时直接派驻军队前往瘴气频发的广西,除了要考虑后勤补给等因素外,士兵水土不服,饱受瘴疠之苦,非战斗性减员时有发生,兵员的补充也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历代中央王朝只能依赖土官对广西进行控制和经营。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又需要克服羁縻制度存在无法有效控制当地社会,难于驾驭土官等问题。因此,有严格规定,可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土官,把当地社会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当中的土司制度成为一种选择。
首先,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广西重要的社会基础因素,也是广西社会现实存在的空间。总体上,广西的地理环境并不优越,山多平原少,岩溶广布,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一片海”之称。此外,各地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大多处在平地或山间平坝地带,有相当数量的冲积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力高,交通相对便利,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区则大多处在山区,石山所占比例较大,交通不便,耕地分散,土地贫瘠,水源缺乏,生产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社会发展相对缓慢。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了广西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并未达到质的飞跃,相比其他流官统治地区仍有较大落差,特别是红水河、左右江等地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对缓慢,社会大体还沿着旧的传统惯性发展。这是广西土司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宋代东部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西部地区也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经济,经济基础由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转变,但仍需一种政治制度来确认这种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比羁縻制度更严格、更规范,控制力更强的土司制度成为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制度选择。
如何确证人和自然、人和对象物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海德格尔沿袭“人栖居于世界”的整体存在论构思,进行物的哲学追问也即物的哲学规定性命题探究,遵循“真理—话语—物”的致思路径,据此构造出真理和话语反映物的本质,抑或物的本质归结于真理和话语并最终维系于人的尺度。恰如他在《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中的结论:“‘物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人是谁?’的问题。”[5]216海德格尔致力于从物的存在价值推导人的本质问题,不再遵循康德“人是目的”的先验性前提,初步作出了重建人与物之间整体存在关系以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尝试。
最后,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兵是土官与朝廷博弈的重要筹码,是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转化,且土司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手握土兵,使得土官成为朝廷极力争取和依靠的力量,是土司统治制度的重要保障。
宋代时期,广西土兵得到较快发展,有土丁、壮丁、洞丁、保丁等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獠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子、田丁,亦曰马前牌,总谓之洞丁。”[4](P134-135)宋嘉祐七年(1062),广南西路土丁“凡得三万九千八百人”。熙宁六年(1073),广南西路经略沈起言:“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大观二年(1108),诏:“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余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9](P4744-4748)由此可见,宋代时期,广西土兵数量众多,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为了加强控制,宋朝廷利用平定侬智高起事的时机,建立起了洞丁戍边制度,把洞丁纳入国家编制。治平二年(1065),“广南西路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洞知州、洞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以旗号。峒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病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9](P4746)此后,通过保甲等办法,宋朝进一步规范了洞丁戍边制度。随后,洞丁代替正军戍边的程度日趋提高。元丰六年(1084),“提点广西路刑狱彭次云言:‘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诏许彦先度之,彦先等言:‘若尽以代正兵,恐妨农。请计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轮二千赴邕州肄习武事。’从之。”[9](P4748)至南宋时期,官军在戍边上已不起作用,全赖土兵戍守。
元朝统治者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于兵力稀缺,因此在广西继续推行土兵制度。元代壮族土兵称土军和撞(僮)兵。元大德元年(1297)七月,“招收亡宋左右两江土军千人”。[14](P2546)至元二十九年(1292),左江总管黄坚言:“其管内黄胜许聚众二万,据忠州,乞调军万人,土兵三千人,命刘国杰讨之。”[14](P364)屯田制度是元代兴盛时期的基本国策之一,大德二年(1298)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以撞兵屯田,为广西土兵屯田之始。《元史》载:“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撞兵屯田:成宗大德二年,黄圣许叛,逃之交趾,遗弃水田五百四十五顷七亩。部民有吕瑛者,言募牧兰等处及融庆溪峒徭、撞民丁,于上浪、忠州诸处开屯耕种。十年,平大任峒贼黄德宁等,以其地所遗田土,续置藤州屯田。为户上浪屯一千二百八十二户,忠州屯六百一十四户,那扶屯一千九户,雷留屯一百八十七户,水口屯一千五百九十九户。续增藤州屯,二百八顷一十九亩。”[14](P2578-2579)总计屯田763顷26亩,屯户4690户以上,由此可见元代广西土兵之数量必不少。
朝廷虽以洞丁戍边,并把其纳入国家编制,但是洞丁的命运却掌握在土官手里。洞丁既是武装,也是农奴,人身依附于土官,土官对其有生杀大权。因此,土兵对土官可谓言听计从。宋代设置的提举,虽籍洞丁为兵卫,“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出其酋。”[5](P136)洞丁的命运掌握在当地首领手里,提举官也只有通过酋首,才能调用洞丁,“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强武可用。以为兵卫,谓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5](P134)这种情况造成了土官权势日益强大,朝廷对其也只有极力笼络。宋神宗深谙此道:“用峒丁之法,当先诱以实利,然后可以使人。甘言虚辞,岂能责其效命?”[9](P4747)南宋时期节制广南的李曾伯亦曰:“必尽得其首领之心,然后可赖其壮丁之力,此始用之以壮声势,则亦未可全恃之为吾用也。”[13](P5013)可见,土兵成为土官与朝廷博弈非常重要的砝码。
除了手握土兵武装,土官在当地社会的统治上更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广西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土官在本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当地传统文化受到外来冲击影响有限,土官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与土民存在着深厚的情感联系,在维持地方统治秩序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均能起到汉族官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央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和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出于巩固边防需要的考虑,任用土官实行间接统治方式成为一项成本相对低下的最优选择。明朝的闵珪在《论抚讲岑应疏》中说:“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各处蛮夷边境,地皆炎瘴,人皆顽梗,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仰惟高皇帝初定天下,特于前项夷方止设土官控制。[18]可见,拥有武装的土官在广西羁縻制度向土司制度的转化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朝廷的统治思想要求不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而在对地方的统治上土官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无可替代的优势,朝廷必须依赖土官;另一方面,土官也需要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于是,管理更严密的土司制度逐步取代松散的羁縻制度成为历史的选择。
当时沂南县共有人口28万人,据统计在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沂南人民一共出动了小推车10796辆,出动民工162849人次,几乎人人上战场。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张声震.壮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4](宋)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6]安国楼.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7.
[7](宋)王安石.桂州新城记[A].王安石集[C].李之亮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8]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J].中国边疆史研究,2011(2).
[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黄宽重.南宋时代邕州的横山寨[A].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史研究集(第十八辑)[C].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
[12](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六[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13](清)谢启昆修.广西通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4](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5]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03).
[16][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7]方铁,张维.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1).
[18](清)汪森辑.粤西文载·卷五[M].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氏梅雪堂刻本.
On Reasons for Transformation of Guangxi Jimi System to Tusi System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HUANG Jindong
(Library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ere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uangxi Jimi system into the Tusi system.In this process,the drawbacks of the Jimi system originally implemented in Guangxi were increasingly developed and the system was increasingly unsuitabl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With the change of the thought of the imperial court in ruling Guangxi,the loose rule mode in the Jimi system has a serious conflict with the ruling thought of the court.Therefore,the Jimi system being replaced by the Tusi system beca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The transformation was a complicated process,which was based on the social reality of Guangxi at that time,and wa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ation of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 and other factors.
Key words: Jimi system;Tusi system;economic base;institutional change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33(2019)04-0024-06
收稿日期: 2019-6-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桂学研究院·协同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黄金东(1981~),男,壮族,广西田东人,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历史文化与民族文献学。
【责任编辑:黄 玲】
标签:羁縻制度论文; 土司制度论文; 经济基础论文; 制度变迁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