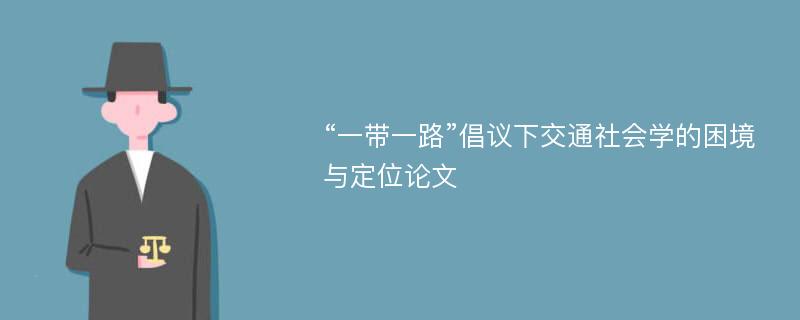
·交通问题研究 ·
“一带一路 ”倡议下交通社会学的困境与定位
王 斌
(西南交通大学,成都 611756)
摘 要 :交通社会学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交通与自然的关系、交通对认同的影响以及理论话语的更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交通社会学遭遇到一系列挑战。新时代的交通社会学必须重新定位,既要始终坚持生态性与社会性合一的学科视角,又需在研究中主动把握好“及物”与“及心”的关系,并积极建构具有中国品格的理论话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从单一的要素输出转向复合的全球治理。
关键词 :交通社会学; “一带一路”; 交通治理; 丝绸之路经济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交通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交通运输体系不断转型升级,现代交通模式持续完善,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1]。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走出去”的步伐加速,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深入实施,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日益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境合作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建成“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交通运输“走出去”,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范畴,更有助于中国实现在全球治理中所倡导的和平、繁荣、开放、创新与文明等愿景。如何促进交通技术层面的“道路相联”升华为交通治理意义上的“民心相通”,顺势成为了我国新时期交通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任务。
一、我国交通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广义的交通包括了运输和邮电两个方面,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前者。从运输角度来讲,交通社会学是通过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交通行为、交通现象和交通行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规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3]。这一学科并不将具体的交通要素(如车辆、道路、交通规则等)视为重点,而是试图分析交通建设及运行所引发的经济效应、政治过程、社会结构、文化后果及生态影响。事实上,从社会研究开始关注城市和技术的相互关系以来,学者们发现交通设施对人类行为、城乡环境和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4]。谷中原提出交通社会学研究应包括人类交通行为、人类交通文化、人类交通权利等九个方面的内容[5]。也有学者指出,交通社会学必须从“人与交通的关系”“交通与交通的关系”“交通中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重新诠释交通的本质和功能[6]。基于此,笔者认为当代交通社会学探讨的三个核心议题是:“交通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层面)、“交通对认同的影响”(心态层面)以及“交通社会学理论的更新”(话语层面)。
(一)厘清交通建设与生态环境间的社会关联
不同于道路生态学对水土环境、大气质量和噪音污染等问题的关注,交通社会学首先试图回答的是交通运输如何“社会性”地塑造自然。交通社会学认为大型的基建工程不仅能改变原生的自然环境,更会促进交通产业主要是汽车工业的增长,并可能引发过度开采与耗费资源的生态危机[7]。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对于我国边疆地区的生态影响尤为明显。比如,以往部分新建道路虽然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但过于迅疾的市场化却扭曲了原有的社区生计结构和人地关系,从而使得脆弱的边疆生态陷入持续恶化的境地[8]。
毋庸置疑,随着交通现代性的演进,生态环境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交通设施兴建和居民出行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从粗放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建立全民共享的集约型交通运输体系,这一跨越式的发展在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自然界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害。因而,我国交通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旨在通过形成社会倡议、干预社会文化和参与制定社会政策等路径,达到保护与修复环境的目的,实现生态文明和交通产业的和谐共生。
(二)分析交通工程对社会认同的影响机制
交通工程不仅是对地理空间的再造,而且会作用于人们对空间的认知。交通社会学就是要描述交通设施与城市空间的共变过程,并解释这一变迁对居民社会认同的影响机制。学界普遍认为改善交通状况能增进居民间的互动,推动形成正向的公民认同。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级政府却只关注到交通设施修建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作用,忽视了交通公共服务对于市民化的提升功能。由此,交通工程日益丧失人本主义的向度,造成“人的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困局。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一系列交通运输工程和技术装备正越来越频繁地走向全球。交通技术“走出去”在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产业升级的同时,必将给区域间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陆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复杂、生态系统多样、环保主题多元,极大程度地考验着我国交通技术向外输出的综合能力。然而,我国交通社会学对以上问题的关注却极不充分,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知识盲点和认知真空。
(三)更新交通社会学的理论话语与研究范式
20世纪以来,交通工具深刻地改变了时空结构,交通运输的国际化也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程度地拓展了交通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一方面,交通技术发展令全球化成为不可逆的现代性后果。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曾指出:距离并不总是用时间来度量的,随着交通系统对全球的联通,技术文明使得地球持续“收缩”,以至于“(时间上)不可跨越的鸿沟似乎(在空间上)可以跨越,整个地球皆可及”[10]。面向全球化的交通社会理论因而变得愈益重要。就我国现阶段的现实而言,如何处理国际交通枢纽建设与全球城市打造的关系,以及怎样协调交通技术“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等问题,成为了本土交通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关键命题。另一方面,交通运输的全球化也对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比如在2013年之前,围绕着“向陆”还是“向洋”的争论曾影响我国国际关系和交通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定位[11]。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才明确为我国各学科提出了“陆海复合型”的理论建设要求。不过,现阶段我国交通社会学理论的更新仍存在简单套用西方话语的倾向,本土化工作稍显不足。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交通运输“走出去”愈来愈多地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风险,交通社会学遭遇的困境更显严峻。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交通社会学的现实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解决治理困局的关键举措。其中联接沿线各国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和相应管道、通信设施等交通工程,正发挥着重要的纽带功能。随着亚欧大陆间交通路网的不断成型,促进新建道路有效契合当地生态环境,令沿线人民共享现代化福利,更成为一个愈发紧要的议题。从此角度上讲,我国要实现“一带一路”的建设愿景,需要得到交通社会学的理论支撑。但当前该学科的底子还十分薄弱,在回应“一带一路”重大现实问题时明显捉襟见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998年,翟桂芝从供销社下岗后,自己开始做生意,卖蔬菜、种子、农药和农膜。翟大姐做生意一向都是诚信经营,进货都进最好的,卖最好的,这样老百姓用着效果好,久而久之大家都很信任她。很多街坊邻居都跟她说:“翟大姐,我们就信你卖的东西,既然你都卖了种子、农药、农膜,你也卖卖化肥吧,省得我们还得去别处买。”
如若细加划分,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更立体地看待上述问题。从教师的角度而言,口语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何有效平衡同一个教学班级内语言能力不同的学生对教学的预期及要求,课堂的口语练习方式老套、内容陈旧,但同时教师们在改进方面又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训练,教师对自身语言能力的认知不令人满意。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学生对口语课堂活动的参与度较低,语言表现力也不够。从课堂的整体环境而言,没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教学环境,班级人数较多,有限的教学资源,教学时间不充足。
四十二岁那年,李白游到了京城,拜见了文坛高士贺知章。贺知章出于礼貌,随手翻阅着李白呈上的诗文。读到《蜀道难》时,老头登时被惊住,连呼“天纵奇才,下凡的谪仙!”。
进入11月,京津冀三地空气污染严重,污染物PM2.5浓度(微克/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均大幅反弹,雾霾反复出现。
(一)难以协调跨国交通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
我国交通社会学对以上现象进行了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该学科指出:由于我国交通空间欠缺人性化设计,城市公共领域的社会意义不断衰落,市民的实际需求和感受无法得到实际性的满足;因而,交通工程的兴建必须考虑到社会功能的发挥,以有效承担促进市民化、形成市民认同的责任[9]。当前,为落实“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交通社会学倡导通过加大交通公共服务建设,增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获得感。这对缓解社会分化、促进社会融合和推动市民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对西方交通社会学理论的掌握不深,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解释范围都存在认识不足的缺陷。比如,我国学者在分析交通设施的社会影响时,常不加批判地使用“时空压缩”和“时空延伸”等西方概念,选择性地忽视了中国的快速现代化与欧美发展历程之间的根本差异,致使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未被准确识别[16]。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交通建设同样如此,若不全面理解当地社会的现实情况,盲目使用西方概念,势必会产生误导和负面影响。二是我们缺少对本土已有交通社会学理论的梳理和反思,未对国内交通建设经验可否用于“一带一路”倡议作出有效评估。比如,当前我国的对外援助通常简单复制“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经验,但此做法在境外并非“百试百灵”。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警示,中国通过兴建交通设施带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在中蒙边境地区遭遇了“异化”危机;货运道路的修建非但没有加强两国边境人民的交往和互信,反倒演变成了一种制造社会距离和矛盾的技术[17]。故此,我国交通社会学在积极进行本土化理论建设和反思的同时,还必须思考理论解释的时空条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提供准确的智识资源。
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进而构建一个以共同现代化为基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新的全球治理愿景迫切需要得到中国话语的诠释,“有思路,才能有丝路”的论断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指引。这里提及的“思路”不仅是指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相关规划与战略配套,更是指隐藏在这些设计背后的本土理论资源和话语体系。笔者认为交通社会学在参与中国话语建构的过程中,须重点做好以下三点。
(二)无法提出多元文化背景下交通工程应如何凝聚共识的方法
交通设施的建设不单是对社会空间的改造,更是对公民社会认同和共同意识的模塑。但主体的社会认同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里逐步生成的,它极具传统的韧性。认同在短时间内并不会与交通对空间的变革完全一致,有时甚至会出现两者互为悖离的趋势。“一带一路”倡议牵扯到大量的跨国交通设施兴建,它涉及到的多元社会文化背景使得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公民所持认同更难达成一致。丹麦人类学者墨滕·尼尔森(Morten Nielsen)曾分析了跨国交通工程引致的认同分化现象。尼尔森基于中国交通企业驻莫桑比克建路工程的个案研究指出,相较于货币化的劳动报酬而言,本地工人更乐于接受能用于修建住房的泥石沙土等实物;由于中国交通企业没能及时洞悉这一传统需求,导致新修道路并不受当地人民的认同,这些“外来”的道路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他们的消极抵抗[14]。
实际上,我国交通社会学研究虽有对交通空间与认同关系的反思,但缺少对该问题的跨国调查和论证,无法为迫切需要“走出去”的中国交通企业提供有效的智识资源。而且缺失对交通与认同互动机制的评估,不同社会意义系统的交流所引发的纠纷和误解更是难以避免。于是我们常看到,中国在国外援建的大型工程常被他国媒体误认成一种变相的“经济殖民”和“文化侵略”。显然,单一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不能再营造出直接、深刻的“中国善意”了。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们不可再简单地将交通工程视为人与物的流动通道,相反,交通空间越来越成为了塑造集体情感、集体记忆和集体身份的重要载体。我们的研究必须顺应这一趋势,及时将重点转移到分析跨国交通工程的社会意义生产机制之中。现阶段交通社会学的薄弱环节正在于它忽视了交通建设背后所潜藏的“认同的力量”。
(三)缺乏理论创新导致学术话语权的日益丧失
杨传堂和李小鹏曾撰文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它既包括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又涵纳了制度、规则、标准衔接融通的“软件”建设[18]。这一论断为我国新时期的交通社会学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循此,为增强新时代的理论自信和话语能力,我国交通社会学应做好如下三点定位。
我国交通社会学特别缺少境外的相关调查,不能完全掌握沿线各国主要的生态议题和环保运动的情况,难以为我国“走出去”的交通工程提出相应的风险规避建议。例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里,由我国公司负责建设的交通工程必然会面临着来自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环保组织的监督。交通工程一旦触碰到当地的环保议题,就会引起所在地区的组织甚至是国际社会组织的强烈干预,从而带来工期和规模上的不确定性[12]。而对于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来说,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单会改变区域的自然环境,还将会冲击居民传统的生计结构。这极易催化混合了环保主题和民族情绪的社会运动,社会失范强度随之增大,“一带一路”的可预期前景也难免会受到制约。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交通社会学发展的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路”“带”“廊”“桥”等表述,以中国话语传递出了我国一贯坚守的平等、包容和“非极化”的外交原则[15]。作为全球化4.0版本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内涵和表达都旗帜鲜明地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和谐愿景,这无疑为我国新时期交通社会学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但目前中国交通社会学的理论发展并不乐观。一方面,助力“一带一路”走出去的理论资源大都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我国社会学尚未找准定位、积极发声,本应发挥重大支持功能的交通社会学更是处于哑然状态;另一方面,我国交通社会学除大量套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外,研究内容多在回应和验证国外理论,缺少构建和创新本土理论的尝试,无力回答“一带一路”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一)始终坚持生态性与社会性合一的学科视角
一方面,交通社会学要积极探索以交通设施更新促进民生事业发展的途径和规律。遏制交通运输的社会排斥功能,保证交通工程建成后的公共性。从学理层面提炼出增进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便利化的内在规律,在契合当地产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前提下,将“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工程真正打造成便民、惠民和利民的民生通道。另一方面,交通社会学还要激活社会组织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上的潜能,继续厘清社会组织参与交通治理的机制。随着“一带一路”中各条经济走廊的贯通,环境、人文和非传统安全等社会领域的交流会变得愈益重要,这也决定了社会组织在凝聚各国人民认同上的重要作用。从此角度上讲,当代交通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和供给都应主动面向交通类及相关社会组织的境外实践,通过社会组织带动交通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推动交通类及相关社会组织“走出去”,也是以公益服务的方式推介中国交通技术、展现中国交通文化、树立中国交通品牌,从而消解沿线国家及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顾虑和误解,最终达成交通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与彼此间的政治互信。
(二)正确把握好“及物”与“及心”的关系
在交通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中,所谓“及物”是指从宏观层面对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与交通政策所具社会影响的研究,而“及心”则是指对交通环境变化引发的社会互动变迁、行为策略调整与情感结构转型的分析。我们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一项“筑路”工程,更是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心”桥梁。助力“一带一路”从单一的“道路相联”到复合的“民心相通”,正构成了我国新时代交通社会学发展的新兴任务。说到底,这一任务就是要在跨文化和跨区域的条件下,通过改善交通条件来增强各国民众间的互动,以此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故此,无论是“及物”还是“及心”,“民”都是其不变的落脚点。坚持以“民”为主线,在“民生事业”和“民间组织”领域多下功夫,是当前交通社会学正确协调“物”与“心”关系的重点。
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当下,交通社会学需要以国际化的视野来处理交通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互为补足、互相促进。新时期的交通社会学必须在社会系统的整体框架之上,深入认识“一带一路”沿线交通设施建设中生态与社会的互动叠加效应,尽最大力量规避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一方面,从研究范式上讲,交通社会学要完成从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向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蜕变,切实建立环境正义的视野[19],以生态效益重新审思“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换言之,交通社会学必须将重点放在加强沿线生态环境的保护、维存生物多样性、共建共享绿色丝路之上,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打造各项重大的交通工程。同时,交通社会学还要积极回应和分析沿线各国公民群体高度差异化的环保诉求,避免环境问题被催化成社会矛盾乃至文化冲突。另一方面,从顶层设计上看,我国不同层次的科研基金需要设立扶持交通社会学的项目规划,在大力助推该学科从事境外调研和跨国比较分析的同时,要引导其揭示“一带一路”沿线生态特殊性及其对交通工程影响机制的内在规律。另外,交通社会学研究者及其团队应努力提升“走出去”的能力,探索“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对交通设施的具体需求,重点分析交通方式转变给当地自然环境和生计结构带来的影响,从而在有益于当地生态与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交通建设方案与升级路径。尤为重要的是,国内部分高校还应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结成合作联盟,通过交通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互补化交流,搭建国际研究机构在交通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对话平台,推动各国在环保机制、城市规划、民生发展等方面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三)积极建构具有中国品格的理论话语
就以上两种具体情况,我国交通社会学既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又无力帮助中国交通企业和相关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当地的生态治理。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一是在于交通社会学自身知识积累的薄弱,二是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区域尚未形成双边与多边的环境保护合作机制[13]。这种缺少共识的环境不仅令交通社会学很难有效获得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更使得其咨询成果无法发挥实际的应用价值。
岳西县是山洪灾害易发地区,洪灾发生概率较高,新中国成立以来共发生15次大的洪灾,其中21世纪就有5次。岳西县山洪灾害具有突发性、毁灭性、隐蔽性等特点,造成山洪灾害的主要因素有灾害性天气、特殊的地理环境、脆弱的水利设施等。
首先,要树立理论自信原则。虽然我国内地学者在1993年才首次提出建立交通社会学的设想,但通过社会学视角去解释交通现象的本土研究开展得较早。例如,杨庆堃在1949年就提到了交通事业与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关系[20]。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立具有中国品格的交通社会学必须追根求源,尤其是要回溯“丝绸之路”交通史和相关的本土经典文本,并对西方交通社会学理论进行建设性的批判理解,厚植实证基础,发展本土概念。
晌午,我到知青大院去还郝浮萍的自行车,她说,那个秃头刚走,他是来道歉的,还留下二十块钱,说是营养费。我说,既然伤得不重,就饶了他吧。郝浮萍面带难色,说,田青青已经去了公社,这事恐怕盖不住了。我知道秃头来道歉并赔钱,这肯定是赵世奎的点子。一旦这事捅到上边,必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其次,要在特色院校加强学科建设。交通社会学是一门专业交叉性极强的学科,它既需要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同时关涉到交通运输、物流、民族学和国际关系等专业知识。在一些交通特色鲜明、人文底蕴厚实的院校优先发展交通社会学,能够更加快速地搭建起学科平台、发布研究成果和树立权威话语。进而在积极回应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基础上,以更优的知识产出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最后,要促进智库合力的形成。当下,一大批以“一带一路”为研究对象的高校智库相继成立,为交通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现阶段的高校智库普遍存在着发展时间短、组建规模小、同质化程度高的缺陷,其知识产出缺乏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建构具有中国品格的交通社会学并非单个的智库“孤岛”可完成,只有通过组建关于交通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智库群”,加强智库间的交流合作,大力激发智库的整体合力,才能不断提升交通社会学的预判能力、解释能力和发声能力,最终建成具有自主话语权的交通社会学研究新高地。
良好的经典诵读活动,离不开科学的诵读指导,可以避免学生在整个诵读过程中出现不良习惯。诵读的总体要求是读音要准、停顿恰当、重音合理、感情气势、整体理解、篇篇诵读、认真思考、仔细记忆。此外,在整个诵读指导中,教师还要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于一些诵读基础差的学生,要重视经典诵读的“循序渐进”,不能“揠苗助长”,机械化地开展诵读活动。
四、结语:由“筑路”到“交心”
工业革命以来,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引发了运输动能和交通工具的巨变。这一方面带动了公民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便捷化和智能化;另一方面使得人与物的流动距离呈几何式增长,流动时间大幅度缩短,流动性持续提高,全球化“大交通时代”已然到来。从这个层面上看,交通事业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反过来又构成了现代性的动力。交通事业与现代性互构的关系为交通社会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与时代场景。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交通事业的发展不仅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更直接影响到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行。因此,交通社会学对缩减交通工程代价、增促交通事业进步有着十分关键的功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新一轮的全球化大交通浪潮得以开启。我国交通社会学的学科发展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和建设任务。基于此,新时期的中国交通社会学研究要在两个方面勤修内功:一是助力交通技术“走出去”,使其在“一带一路”沿途各国的互联互通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促使交通工程“走得稳”,令交通基础设施在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民众获得感的增强,以此引领他们对“一带一路”保持信任并愈加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21]总之,具有中国品格的交通社会学必须要把“筑路”升华为“交心”,这不单是实现“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一带一路”从要素输出转向实现全球治理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
[1] 胡鞍钢,童旭光,王亚华.当代中国交通发展:一场静悄悄的革命[J].湖南社会科学,2010(1):47.
[2]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N].人民日报,2017-05-15(3).
[3] 章辉美,谷中原.交通社会学:对一门新生应用社会学的构想[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6):48.
[4] YAGO G.The sociology of transporta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3,9(1):171-190.
[5] 谷中原.关于交通社会学发展的学术研究问题[J].求索,2006(8):102.
[6] 明海英.交通社会学:探寻制约交通发展的社会因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1-18(A2).
[7] 谢勒尔,厄里.城市与汽车[M]//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等.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8] 周永明.道路研究与路学[J].二十一世纪,2010(4):73.
[9] 何玉宏.汽车社会与城市交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98-208.
[10] 赫勒 A.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60.
[11] 吴征宇.向“陆”还是向“洋”[J].二十一世纪,2013(1):105-113.
[12] 徐飞.中国高铁“走出去”的十大挑战与战略对策[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14):74.
[13] 叶琪.“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境冲突与矛盾化解[J].现代经济探讨,2015(5):32.
[14] NIELSEN M.Roadside inventions: making time and money work at a road construction site in Mozambique[J].Mobilities,2012,7(4):555-569.
[15] 赵磊.“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M]//“一带一路”年度报告:从愿景到行动:2016.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
[16] 周永明.重建史迪威公路:全球化与西南中国的空间卡位战[J].二十一世纪,2012(4):66-76.
[17] PEDERSEN M A,BUNKENBORG M.Roads that separate:Sino-Mongolian relations in the inner Asian desert[J].Mobilities,2012,7(4):467-480.
[18] 杨传堂,李小鹏.“一带一路”建设,交通运输要先行[J].人民论坛,2017(18):6.
[19] CAIMS S, GREIG J,WACHS M.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transportation:a citizen’s handbook[M].Berkeley,CA: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Studies,2003:1.
[20] 杨庆堃.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J].岭南学报,1949(1):152-161.
[21]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6-01-22(3).
Dilemma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ociology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NG B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1756,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 of sociology of transportation includes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portation and ecology, the influence of transportation o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updating of the theor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ociology of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has confronted a series of challenges. Therefore, 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 grasp the initiative in th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 and “heart”, and actively construct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 thus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 :sociology of transportation; Belt and Road;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中图分类号 :C91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297(2019)02-0049-07
*收稿日期 :2018-05-23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社会组织‘走出去’能力建设研究”(2682017WBR14)
作者简介 :王斌(1987—),男,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讲师,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交通社会学。
(责任编辑 :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