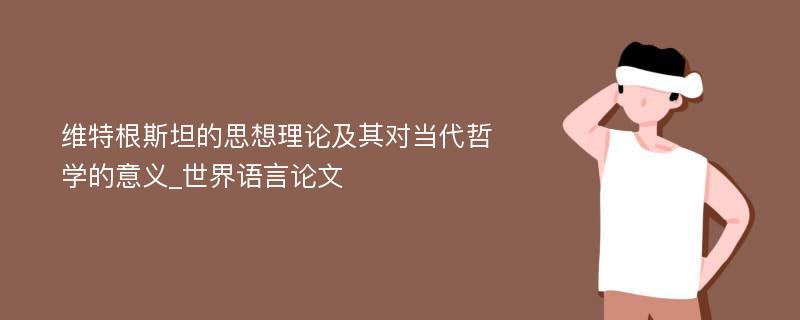
维特根斯坦论思想及其对当代哲学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其对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1-0001-08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1.001 思想(thought)①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推进。在当代哲学中,思想问题依然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学界讨论“思想”概念及其问题的基本框架 何谓思想(thought)?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贯穿于整部哲学史。在《泰阿泰德篇》里,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这样来回答“‘思想’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灵魂与它自身就所论及对象而做的交谈(A talk which the soul has with itself about the objects under its consideration)[1]。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中提出,语言不过是人内心中经验的一种符号。[2]因为人有不同种类的语言,如果如柏拉图所说思想就是在内心中说话,那么不同语言表达思想的方式就不同,人们之间就完全无法交流了。因此使得不同语言能够交流的可能性就在于人心中具有普遍的或者共同的内容,而这就是人的思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争论的焦点在于:思想内容的普遍性是如何被定义的,是由个别语言的约定所达到的一定范围内偶然的普遍性,还是由不受语言影响的心灵过程的一致而获得的必然的普遍性。 而在近代的哲学讨论中,笛卡尔区分思质(mind-stuff)和事质(body-stuff)的二元论思路为我们建立了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一思路发展到当代,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讨论中,关于思想的讨论也是重要的议题。以表征/计算理论或思想语言假说为出发点的图灵、乔姆斯基、福多、普特南等人的心灵主义(Mentalism)和语言哲学家赖尔、戴维森、达米特为代表的语言主义(Lingualism)始终持有不同的看法。[1]1前者更倾向于认为思想是人类内在的经由表征和计算建立起来的心理过程,是独立于语言的。而后者则倾向于认为人类的思想能力是由人类外在的智性行为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决定的,可以通过行为的倾向或解释来分析思想。 这两条思路的区分,按照霍克威(Christopher Hookway)的说法,是由于思想这个词汇的一般用法造成的: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思想。一种是通过观察,了解到思想和推理能力的范式例子(paradigmatic examples)的特征是在人类心中发生的事件或者过程。比如思想与推理与在有意识状态下的思想过程有着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与语言相互独立,思想是语言的伴随物。而另一种则是可以将思想看成一种行动(activity),它包含着一种解决问题的智慧,而内在的过程应当以它们在这一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定义。[1]即我们依据思想的成就,而非过程来定义思想。 虽然主流的思想研究者都赞同这一区分,并分别沿着两条道路发展出语言主义(行为主义)导向的解释理论和心灵主义导向的表征/计算理论。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文德勒[3]就认为,过于强调思想的过程与产物的区分是容易误导人的,因为思想的成就一般来说并不是思想,而是动作、行为、语言,如果我们求助于这些外显的事物来定义思想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引入了另外的概念,这样就错失了思想的本性,因此,思想的过程与产物不能做硬性区分。 维特根斯坦的想法既不同于语言主义,也不同于心灵主义,他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于这一区分的赞同。在前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他通过命题意义的逻辑图像论建立起来的思想学说,阐明了在本质或理想语言中思想作为世界与语言中介的表象载体的结构与语法特征,避免了上述论述中各种既定的理论设定所造成的偏见。后期维特根斯坦转向了中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他通过分析日常语言中与思想有关词汇的实际用法,来说明各种哲学理论是如何误用了日常语言而导致的诸种哲学困境,从而无法达到它们所设立的哲学目标。最终我们无法通过哲学理论的方式去获得对思想的理解,而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面对语词的实际用法,在用法中明晰思想的概念。 二、从“双重投影”到概念类型区分 大体来说,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正如其结构所显示的,如果说码段(1)和(2)主要讨论的主题是世界,那么(3)和(4)则是思想(或命题),(5)和(6)是语言,在理想语言或语言的本质结构中,三者之间处于同型同构的镜式反映之中,通过逻辑结构的共享性来彼此投射:思想是世界的投影,语言(命题)是思想的投影。维特根斯坦建立的是世界—思想—语言的三重结构。前期维特根斯坦用一段话来概述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现在清楚了,为什么我认为思想和语言是一样的。因为思想就是一种语言。因为一个思想当然也是,一个命题的逻辑图像,并因此它就是一种命题。”[4] 在码段(3)和(4)中,维特根斯坦从两个角度,即“事实的逻辑图像”(3)和“有意义的命题”(4)两个方面分别阐述了自己对思想的看法。先看第一个方面,在码段(3)中,维特根斯坦承接(1)和(2)中对于图像与世界关系的讨论,用“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来引入思想这个新概念。作为事实的命题记号若是想要表征同样作为事实的世界中的事实(事态),必须透过思想这一环节。然而,思想虽然是作为世界与语言之间的中介,但是它自身是不可直接表达的,因为命题才是唯一能够图示事实和表达思想的,“思想在命题中得到了一种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达”[4]32(3.1),即我们通过使用命题记号表达命题来表达思想。正确的命题形式表达思想,错误的或非本质的形式扰乱思想,在使用中显示出其错误,并需要得到澄清,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在逻辑上澄清思想(4.112)[4]48,将思想的真正形式通过命题表达出来,从而保证思想能够作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中介。 思想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像,它的可能性是因为“思想包含它所思想的情况的可能性,可以思想的东西也就是可能的东西”(3.02)[4]31。这里所涉及的是逻辑图像这个概念。而逻辑图像是用来图示世界的。这里的世界是逻辑空间中的世界,也就是对象及其结合的诸种可能性的世界。“逻辑空间”不是现实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思想的诸种情况是对象及其结合的可能情况,而不一定是其事实情况。而对于这种思想的可能性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思想非逻辑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必须非逻辑的思考。”(3.03)[4]31而同时:“在逻辑中没有纯粹是可能的事情。逻辑涉及每一种可能性,而一切可能性都是逻辑的事实。”(2.0121)[4]26由于逻辑形式是思想世界与对象及其结合的事实世界的共有形式,逻辑形式的一致性,保障了思想—世界的同型同构性。也就为思想作为世界的投影提供了依据。 另一个方面,维特根斯坦从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方面讨论了思想的另外一个面相。“被使用的、被思考的命题记号即是思想。”(3.5)“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4)[4]41。如果说第一方面讨论的着重点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的话,那么,第二方面讨论的是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对于世界或实在来说,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对于语言来说,思想是得到使用的命题记号,即有意义的命题,因此,“在命题中思想可以这样来表达,使得命题记号的要素与思维的对象相对应”(3.2)[4]33。这里的命题记号即我们用命题来表达思想的记号,联系到后文所讲的“命题的可能性建立在对象以记号为其代表物这一原理的基础上”(4.0312)[4]45。也就是说,通过建立命题记号与思想中的对象的代表关系,命题从而是思想的表达。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将代表基本思想的记号以特定的结合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个思想便为感官所能够知觉的方式作为命题而呈现给我们。同时也能够了解到,“一个命题就是一个处在对世界的投影关系中的命题记号”(3.12)[4]32。这样,命题与思想是两个建立起来的互相对应的系统。到这里,命题—思想—世界这种同型同构的投影关系逐渐显露。按照格劳克(Hans-Johann Glock)的说法,这里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对弗雷格将思想作为抽象实体的一个反动,思想是具有意义的未说出的命题,而命题并不是一个非物质的实体的名称,而是一个在应用中的句子(a-sentence-in-use),一个被放置到世界中的命题符号。[1]由于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以逻辑图像和有意义的命题两种面相来作为世界与语言的中介,因此,思想在语言中可以完全得到表达。 这样,就可以理解在上文中维特根斯坦提到的“语言与思想是一样的”的含义。思想作为世界的一幅逻辑图像,与同样作为实在的图像的命题有着同型同构的关系。因此用记号来代表思想对象构造命题,也在同样意义上意味着思想对象以记号组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思想就是一种语言。维特根斯坦在以上思路中显露出来的论证策略是避开对思想的直接言说,而是通过其与世界和语言的关系来阐明思想的位置。思想的表象能力,而非其心理特质,才是维特根斯坦真正关心的内容,因此,透过这种本质关系,我们知道作为心理内容的思想也只能是以其对世界的表象能力作为本质特征的一种表象语言。 然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足够意识到,他有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上文中的(3)和(4)是不兼容的。如果说“思想作为有意义的命题”这一点是较为清楚的话,“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这一点似乎是令人费解的。因为思想与语言之间具有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留意到的区别:思想不需要作为对象的命题记号,思想具有理解的直接性,不需要指示其“投射的方法”,命题或语言则需要思考其与实在的对应方式才能理解其意义。当我想到某事的时候,我并不对我意谓的和我在想的是什么而感到怀疑。而命题则不是这样。命题在不被使用的时候只是记号,似乎是思想赋予了命题以意义,思想建立起了命题记号与事实之间的描画关系。这一点在《哲学语法》时期得到了关注,维特根斯坦质疑说:“发生的不是这个符号不能被进一步解释,而是我并不解释,不解释的原因是我对当前的图像感到自然,当我解释的时候,我从思想的一个层次走向另一个。如果我‘从外面’看思想符号,我会意识到它可以被这样或那样解释;如果它是我的思想中的一步,那么它就是对我来说很自然的停靠处,并且它的进一步可解释性并不占据(或困扰)我。如同我拥有一个铁路时刻表,并且在不关心一个表格可以被以多种方式解释的事实的意义上使用它。”(PG 99)[5]思想是自然而然地被理解的,它不依赖于与事实对应的方式。 中期维特根斯坦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在《蓝皮书与褐皮书》时期,维特根斯坦解释这一点时说:“似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与语言活动相联系的心理过程,只有通过这个过程,语言才能发挥其作用。我指的是理解和意指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心理过程,我们的语言符号便似乎是僵死的;似乎可以认为,符号的唯一功能就是产生这样一些过程……如果有人问你名称与被命名者之间的关系时什么,你将倾向于回答说这些关系是心理的关系……这一活动似乎是在心灵这种神奇的媒介物中发生的。”[6]这样,思想依然不能只是一种语言,而是处于给予语言以意义的意向性关系之中,而思想的心理特质也并非一种非本质特征,心灵赋予语言符号以意义的模型依然延续并给我们造成哲学困扰。 中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着手进行解决。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从早期的逻辑分析和理想语言或本质语言建构的进向向中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和反本质主义思路转变,因此他的思想同时带有两种思路的痕迹,同时由于更彻底地对心理主义的拒斥,表现出意义的证实主义特征。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与语言属于不同类型的范畴,不能以语言来定义思想,但是思想与语言紧密相连,两者的关系处于一种操作活动与被操作者的关系之中,类型不同但不可分割。“思维本质上说是一种符号操作活动。当我们一边书写一边思考时,这种活动是通过手进行的;当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思考时,这种活动是通过嘴和咽喉进行的;当我们通过对符号或形象的想象来进行思考时,我不能向你指出任何一个进行思考的动作者。如果你那时说,在这种情况下是精神在思考,那我请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你是在使用一个比喻,在这里说精神是动作者,其意义不同于说在书写时手是动作者。”[6]10赖尔将这一思路继承,认为思想是具有副词性质(adverbial character)的动词[7],并不能独立于行动被单独的言说。比如,当我们匆忙的吃饭的时候,匆忙并不独立于“吃饭”这一行为,而是与这一行为一起表现出来。思想与语言或人类活动的关系,就像是歌词与声调、曲调、节拍等之间的关系一样,两者勾连在一起。思想不是一种独立的活动,它依附于语言建制、生活实践等人类活动,这些活动为思想提供内容,不是某种不可见的神秘的人类心理过程,而是可被度量和考察的人类活动的不可见部分。 为了摆脱心理过程对思想的纠缠,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这一策略,他说:“我可以给你如下这个按照经验办事的原则:如果你对思考、相信、知道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的本质不清楚,那就用思想等等的表达取代思想。这种取代的困难(同时也是这种取代的关键)在于,对相信、思考等等的表达只不过是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只有作为一个语言系统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演算之中的表达式,才有意义。”[6]55这里,维特根斯坦强调的是,思想并非是赋予无意义的符号以意义的活动,心理活动不能取代符号操作,而总是与后者处于逻辑联系中。 维特根斯坦对思想的想法从前期到中期的转变体现出他对自己思想的某种纠正,对早期逻辑图像论背后依然隐藏的“内在神话”残余的一种反思,但是这一想法依然带有简单化本质化的倾向,赖尔式的对思想的向性(disposition)行为主义解释可以看作是中期维特根斯坦想法的一个直接的延续。然而,在日常语言中,思想显然具有比这一定义更加多样和丰富的用法,而这些用法的阐明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工作。 三、后期维特根斯坦:破除神话 在一般想法中,思想往往被缠绕上一种神秘的光环。我们将思想看作是某种不同于物理世界的心灵世界的事物。可以透过感官感知到一个人的行为、动作、外貌等,但无法探知他的思想。广告语说:“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人们常常认为,人的身体可以被奴役,但是靠心灵世界却可以达至无限与永恒。在传统哲学中,思质的东西与事质的东西的对立一直是困扰哲学家们的问题。笛卡尔的二元论、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洛克的观念论、贝克莱的唯心主义、康德的先验图型论(transcendental schematism)学说,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角度。 但是,这些探讨思想问题的尝试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都从一开始就走错了道路。因为,他认为我们在这里将思想当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东西”,这是一种由“语法的欺幻产生出来的一种迷信。而这种迷信的狂热又反过来落向这些幻觉、这些问题”。这种幻觉让人以为是在讨论一种特殊的深刻的东西。是一种如同真理、语词、世界一般的“超级概念中的超级秩序”,然而,如果这些词真具有用处的话,它们和“桌子”“灯”“门”一样卑微。[8] 这种态度使得维特根斯坦对思想的研究转而走向对思想及其相关的语词或概念的用法的研究,以这种研究来破除传统以来对于思想研究的歧途。我们也许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思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应当是像传统的思路那样“像是在等待一个天文事件出现,到时候再匆匆作一番观察”,他问道,“难道你从不思想?难道你不会观察自己,看到这里发生的是什么?这该是挺简单的”[8]327。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思想’是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词,正如其他所有的心理学词汇那样。”思想并不是稀奇之物,我们思想的时候并不觉得思想很神奇,或者很神秘。而让思想显得神奇和神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错误的反思方式。我们对一个概念事实问它如何可能。比如,我们会问:我们怎么能思想那不存在的东西?这里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我们恰恰能够思想实情之所不是。[8]51 如果说在前期和中期维特根斯坦对思想的探讨中,他过于强调思想和语言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的话,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中,他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以及思想在不同情况下用法的差异。指出这种差别的目的就在于摧毁哲学建立起来的各种关于思想或思想与语言的意义神话。维特根斯坦说:“‘思想’,一个枝杈众多的概念。这个概念连系着很多生命表现。思想-现象散布的很广。”(Z 110)[9]“‘思想’是一个分支广泛的概念。这个概念把许多生活表现包含在它自身之中。所思考的各种现象相互之间相距遥远。”(RPP220)[10] 在《哲学研究》306—344节里,维特根斯坦集中讨论了一系列日常语言中有关思想的语言游戏。例如“边想边说”“边想边写”“闪电般的思想”“思想的摘要”“恍然大悟”“不讲话而思想”“怀疑自己在思想”“用语言思想”“思索着说和不假思索地说”“出声的想”“确信不疑”“表达式之前的思想”“思想的次序”“没有语言的思想”[8]122-128“动物的思想”、心算[8]132-135等话题。这些具体而微的讨论逐渐地撼动我们以为牢不可破的诸种思想神话。以下将简要地进行讨论。 维特根斯坦在讨论中首先隐含的对手是思想的伴随模型(accompanying model)[11],这是在思考有关思想的问题中最容易想到的。他引入一组容易令人误入歧途的比较,即将喊叫与疼痛的表达与句子和思想的表达混为一谈。仿佛句子的作用在于使人将注意力引向注意我们内部的某种伴随着话语说出的过程。但是当我们观察日常语言语法的时候,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内在过程这幅图画在日常语言中确实有位置,例如我们会边想边说或边想边写,在这里,思想与语言似乎并行。但是哲学家们却将这幅图画作为思想这一概念出现的唯一方式。而事实上,思想与语言并不总是并行或互相伴随的,例如,我们也谈及思想的迅速,例如恍然大悟,突然间把握到思想,或者说出却没有想到等。我们拥有关于思想起作用的各种图画,而不仅仅是某一种,而哲学家往往选择了某一种图画,并妄图用一幅图画来描画所有图画,他们的企图即使成功了,也往往失掉了各种图画根基于生活的不同意义。 即使是看似作为伴随模型典范的边想边说的例子中,思想与语言这种伴随关系也不是由某种固定的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特定的语言游戏或语法来决定的,因而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比如,当我在边想边算术的时候,我会想象大脑中在进行运算,而写下的就是运算的结果,但是,维特根斯坦举例,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说“这支笔够秃的,得了,就是它吧”。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先是想着说,然后是不假思索地说,最后是只是想这个思想而不关心语言。[8]125我们在这里要问的是,思想在这里是某种活动吗?那么,我们平时是如何定义一种活动的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写字,说话,打球,算术,等等,在这些活动的家族相似的序列中,是否能够找到思想这种活动的位置?这显然是很难,而哲学家往往轻易地这里下一个武断的结论,然后从这“完全不为人所注意的一步”[8]120出发,推论出哲学理论。这个例子和“打断的思想”[8]124的例子相似,某人在思考的过程中,去做了一次测量,那么,他的思想被打断了吗?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活动,那么该如何衡量它发生的持续时间,位置,施动者,以及该如何衡量它错误的可能性。这些都与思想作为一种独立活动的语法相关,而哲学家们往往急匆匆地略过这些差别,忽视了这些具体用法的重要性。 与思想是否是一种活动的问题相关的还有思想的载体的问题,这与本文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柏拉图的思路有关,思想是否是一种语言呢?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例子:“当我们用语言思想,语言表达式之外并不再有‘含义’向我浮现;而语言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8]125在日常语言中,经常有用各种各样东西作为思想载体的例子,例如用图像来思考,用语言来思考,用身体来思考等,但是这些表达式并不意味着图像和语言等在字面意义上变成了思想的载体,从而制造出某种内在空间的错觉,而是在于,上文中提到过的思想所具有的直接性,使得我们借助何种介质进行思考,都处于一种直接理解的状态,我们不再需要意义为这种思考方式提供保证。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处于为用语言来思考寻求意义支持的无穷后退的状态。 在通过不同语言游戏的差别的描述来阐述思想这一概念对于特定语言游戏语法的依赖性和由此导致的复杂性之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332节到343节较为正面表达了思想与语言之间的一般关系,维特根斯坦开始举了威廉·詹姆斯所谈到的一个例子:一个叫巴拉德的聋哑人在没有学会语言的时候,就能够思考上帝和世界的问题。例如问自己:“世界是怎么形成的?”维特根斯坦的疑问是:如果你没有学会一种语言,你肯定你自己在思考吗?而且,为什么你能够冒出这个问题来?这个问题似乎在平常的时候并不存在(因为缺乏恰当的语言环境)。也就是说,除非他学会了一种语言,否则他不可能说出这些内容。“我用来表达回忆的语词是我的回忆反应。”[8]128语言概念与思想概念之间经常是处于紧密的关联之中,一般情况下,只有谈及某种语言技术和建制的掌握,我们才能够谈及涉及思想的语言游戏。例如假如没有象棋,我们就没办法谈及下棋的意图;只有有了表达人内心状态的表达方式,我们才能有意义的谈及某人内心所想的东西;只有对于通常能够讲话的人,我们才能够说他可以在内心中与自己说话,等等。维特根斯坦说:“可以把不假思索而说和不是不假思索而说比作不假思索地演奏一段音乐和不是不假思索地演奏。”[8]128这里用音乐演奏的比喻来突出由于我们过于熟悉而觉察不到的语言使用的技术性,而这是在做哲学的时候容易忽视的,我们由于忽视表达式的使用的差别,而轻率地使用了如“无形的过程”“表达式之前的思想”“其实要说……”[8]126等容易引人误解的表达式,同时并没有重视这些表达式所使用的特殊语法,正是这些粗疏的使用使得我们走上了哲学疾患的歧途。 四、维特根斯坦论述的启示与意义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从早期到中后期对于思想概念处理的演变。从早期的逻辑图像说中阐明思想的本质特征,到中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分别从理想语言和日常语言两个方向对思想概念进行了探讨。后期维特根斯坦清除了早期遗留的心理主义杂质,通过描述思想概念的实际用法,阐明了思想概念的复杂性,而探讨思想概念的诸种哲学理论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而没能正确地解释思想这一概念。 在当代哲学中,关于思想问题的讨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分为两条进向。以副词理论和解释理论为代表的语言主义和以表征/计算理论和联结主义为代表的心灵主义,它们分别侧重思想的结果或产物的特质和思想的有意识到内在过程特质。 上文在讨论维特根斯坦中期论述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对于思想及心理过程与语言(行为)概念类型不同和对前者进行副词性解释的思路。赖尔在《心的概念》中发展出一套以倾向(propensity)或向性(disposition)来解释思想及思想与语言关系的理论。语言和行为是外显的可观察可评价的活动或过程,而思想则与语言和行为处于不同的概念类型之中,就如同赖尔所举的那个著名的例子,牛津大学与牛津大学的各种建筑物及其总和不是同一类型的概念,而维特根斯坦也曾经提出过,思想与行为的概念差别,类似于“火车车厢”“火车站”和“火车规章”之间的区别[6]84。在行为主义进向支持者看来,思想概念,是我们用于描述行为或语言的倾向性或向性概念,可以通过语法变形来体现这一点,即可以将向性词汇转换成副词形式用来修饰外显行为或语言的动词形式。 赖尔的想法体现了“语言转向”后语言哲学家们力图通过语言分析解决思想问题的意图。思想是无定形的,而语言使得思想得到明晰化,使得思想得到清楚的表达,因此他们设想用语言来定义思想。日常语言哲学家文德勒[3]280通过他对于英语心理动词的考察得到结论:言语的对象与思想的对象几乎普遍地同一。我们可以思想的事物,同样也能用语言换一种方式来说。例如希望、想要、打算,可以转化成语言中的起誓、允诺;责备、赞成、宽恕在语言中可以表达成赞扬、赞成和原谅,与语言相比,思想并未提出新的对象和表达方式。而一些二元论者被思想表达式的表面形式所俘获,设想与身心二元的世界观,是犯了范畴错误。 语言决定思想的进向在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界也在很长时间内占据着主导型的地位,心理学中,一般用外在主义的问题—解答模式来定义思想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从叶斯柏森的语言相对主义到萨皮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的语言牢笼论,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某种特定语言的习得,对于其思想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2]。 在当代,戴维森开创并由博姆德兹(Jose Luis Bermudez)和克拉克(Andy Clark)发展出的解释理论是语言主义的最新代表。戴维森认为,思想要求高阶思想(higher-order thought),思想要求一种对于思想的理解和解释能力,而这种高阶的能力需求语言。戴维森认为,“一生物如果不是另一生物的言语的解释者就不可能有思维”[13]。高阶的思想意味着区分表象主体与表象,而这就意味着语言能力的形成。动物如狗、猫不能够解释他们的思想,或缺乏语言表达的能力,因而我们就不能说它们有能力思想[11]。博姆德兹主要讨论了“无言的思想”(thinking without words)的可能性问题[13]636,按照丹尼特的说法,显然存在一个现象学事实(phenomenological fact),即无言的思想(wordless thought)。[1]我们可以只思想,而不说话,或者即使在我们说话时,内心中也可能有着很多和语言活动无关的内容。博姆德兹认为,思想的载体(vehicle)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表象事态,而心理过程形成的心灵模型不能在形成对事态的正确表象的意义上进入思想,即不能以句法模型(即命题形式)出现的心灵模型,不能够进入思想[13]637-640。 支持思想决定语言的心灵主义主要是由乔姆斯基对于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研究和图灵对于普遍的图灵机(a universal Turing machine)的设想所启发而形成的。既然语言能力是人一种普遍的先天本能,而计算机的表征/计算模型又为我们将思想类比于内部运算过程提供了启发。于是像福多(Jerry Fodor),平克(Steven Pinker),普特南(Hilary Putnam)等人就设想大脑就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计算机,人脑中存在思想的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就仿佛计算机由二进制形成的内码,有着比自然语言更复杂和丰富的语法与语义特征,而自然语言是思想语言的一种翻译,我们通过自然语言与别人交流,实际上是各自将自然语言与思想语言进行互译并传递的过程,类似于计算机由数据输入到中央处理器处理乃至输出的进程。在心理学研究中,代表性的学说是柏林-凯假说(Berlin-Kay hypothesis),与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语言决定思想的论调相反,研究表明,在例如颜色词等多个领域,人类的大多数语言有着高度的结构和类型一致性,这提示存在着某种先天的思想结构,为语言的一致性提供着可能性[12]86-87。 表征/计算理论设想的思想图景是由定义符号的形式特征而进行逻辑演算的逻辑系统,这种想法的理论来源在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设想的普遍理性设想。但是人类的思想是否全部或主要是逻辑的?在计算理论的设想之外,还有一派作为近代经验论的当代支持者们所提出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11]的想法,他们认为人脑中的由相似而引起的联想即观念联结是人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表征/计算理论都和联结主义共享着同一套理论设定,即相信某种心/脑中发生的内在过程、而不是外在的语言或行为产出,是思想的本质性内容。 以下将试图从维特根斯坦的角度对以上两种想法进行评论和回应。 第一,相对而言,行为主义或解释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为思想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标准,避免过度假设而引起的质疑。我们可以通过外显的行为和依据语言来为思想提供某种解释。而这种想法的弊端在于,他们对于内在过程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塑造了心灵模型或“意象”与外显行为或语言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实际上在实际思想与行动过程中这种两分是不存在的。当我们为思想的内心过程赋予意象和“内在性”的定义时,事实上也为外显行为和语言赋予了同样狭隘的定义和简单的图画。而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并没有这样人为规定的武断的定义。 我们的语言有更复杂的用法,行为主义错误地使用了我们的“倾向性”概念,因为日常所说的倾向性只是就外显行为所做出的一种推断,而为隐藏的思想内容保留了空间,行为主义却想要用倾向性概念涵盖一切。另外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曾经专门讨论过思想的目的问题,他问道“人为什么思想?思想有什么用?”[8]158(PI 466)他问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某种计算,而不是听凭偶然性来制造锅炉,因为计算过后制造出的锅炉也可能会发生爆炸,思想并不能总是能保证思想的产物达到人们的预期,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思想过后的产物,而非相信感觉,因为思想(深思熟虑)在这种类型的活动中是被要求的,而简单的动作和语言表达则试图训练我们到达不思想也能实现的水平,这种情况下思想不再是一个重心,而只是对动作来说具有辅助性的东西。在把手伸进点燃的火焰的例子中,我们可能具有给出理由的能力,但是我们倾向于不去思想这些,而直接躲开火焰。如果我们不参照某种具体的语言游戏中的使用,就无法给思想一种定义。此外,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一开始谈道:“一只狗相信它的主人就在门口。但它也能够相信它的主人后天回来吗?”[8]209戴维森否认动物有思想的原因是动物缺乏高阶思想乃至语言能力,但是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缺少一种使得动物具有思想的用法,缺乏一种游戏使得动物具有这种能力,这种重视语言游戏开放性和不确定的思路是比戴维森式的解释理论更具有可接受性的。 第二,表征/计算理论和思想语言假说产生的理论背景是解决传统的身心二元论与当代的物理主义之间的对立,哲学家们引入功能主义的思路,将物理感知的第一等级特性(first order property)与心灵状态的第二特性(second order property)之间的关系比作计算机式的物理识别(数据输入)—心理模块转化(数据处理)—结果输出(数据输出)过程,这样,就比较融贯地解决了内在与外在之间的矛盾,即把它们视为同一个物理实体的不同层次的展示[14]。它也继承了本文开始所谈到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普遍内容的想法,思想的内容是普遍的,虽然有多种多样的语言,但是在心理模块层次,它们都是一致的,差异只是我们在将它们作为数据输出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而已。 心灵主义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语义直觉,并非在日常意义上谈我们的思想,日常语言使用中的思想一般是不会以计算机模型作为参照的。然而维特根斯坦会认为,并非如此,因为表征/计算理论恰好是他所批评的将思想视为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意义神话,因为它提出了一种类似于神话般的对于思想这一日常概念的使用,但是我们几乎很少能够用到这种概念,而且极为缺少这种概念成立的周边环境。首先,我们无法确认这种内在的思想语言的客观标准,它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日常所说的“语言”是同一回事,因为我们毕竟只有参照日常语言才能谈及另一种符号系统是否是一种语言。维特根斯坦问:“我要对语言(词、句等等)有所说,我就必须说日常语言。这种语言是否对我们想说的东西有点太粗糙太笨重了?另外构造一种怎么样?——真奇怪,我们竟多多少少用得上我们现有的语言!”[8]57(PI 120)。若想要使得思想语言成为思想的语言,为其提供一种恰当的语言环境,思想语言假说支持者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不只是提出一种描述就可以了。第二,在上文中,维特根斯坦的确讨论过用语言思考这种情况,但是他所要强调的是,即使我们用语言思考,这也完全不同于计算机运行,因为计算机运行是内码与外码之间的互相转换,内码是完全不依赖于外码的,甚至不必然要求输出,完全处于黑箱的状态。但是人类的思想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如果没有语言的塑造,很难造成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计算机的模型并不要求一个语言所意向的外在世界,这让我们想到了塞尔所讲的“中文房间”,仅仅依靠计算与编码是不可能学会一种语言的,因为它缺少语言使用所要求的情境性和多样性。第三,语言是否会形成对思想的一种限制?或者造成一种类似于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中所提到的“语言牢笼”论的结果。就如同上文中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那样,不同的语言是否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而每个共同体中个体的思想内容,因为修习某种特定的语言而被这种语言所限定?对此,维特根斯坦的回应是:“假使我们看到一些生物在干活儿,它们的工作节奏、表情变化和我们相似,只不过他们不说话,那么我们也许会说,他们思想、考虑、做决定。那里有很多和寻常人类相应的东西。而这里无法断然决定,一定要有多准确的对应,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把‘思想’这个概念也应用到他们之上。”(Z102)[9]146共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而非某种特定的表达方式,才是思想的参照系。语言并非是一种外在于实在的对象,而是与实在,与诸种人类活动紧密相连的。我们用语言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猜谜语、算术、开玩笑、命令、传递信息等。我们通过已有的生活形式来作为参照系辨认陌生的语言及其生活形式,辨认思想内容,因此这一限制是不存在的。 综上,笔者讨论了前期、中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概念的演变,从前期的逻辑图像论到中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分析,阐明了思想作为日常概念的本质,而清除了哲学用法所带来的一些疑难。梳理了当代哲学中讨论这一问题的两条主要进向,并试图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角度对其进行评论,并得出了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误用日常语言、导致哲学谬误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对思想的讨论,阐明了这一问题研究所不可忽视的日常语言维度,对于当代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①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著作中,英文本中一般用的“think”“thinking”thought”,在中文中却又不同的翻译法,如:“想”“思考”“思想”“思维”,这里有可能产生疑问的是“思想”与“思维”两个词。在中文和德文的对照中,一般是“思维”对应“Denken”,而“思想”对应“Gedanke”,在陈嘉映版的《哲学研究》中,德文中的“Denken”与英文中的think相对应,一般被翻译成“想”或者“思考”或“思想”,而thought或“Gedanke”被翻译成“思想”。直接从德文译出的陈嘉映译本这里似乎避免出现“思维”这个词。李步楼版的《哲学研究》则区分两者。韩林合的译法同样对两者的不同加以分别,但是明显很多本应当译为“思想”的地方出现的是“思维”。高新民著的《现代西方哲学》里对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的翻译则都译为“思维”。 想、思考、思想、思维、在我们日常语言中大体意思相近,在使用中略微有差别,维特根斯坦本人并没有严格区分这类日常语言概念,时常混用。本文为求统一,论述部分将一致采用陈嘉映版本的译法,即采用英文词thought的一般中文翻译:思想,而其他引用部分则保持原译。标签:世界语言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逻辑符号论文; 维特根斯坦家族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符号计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