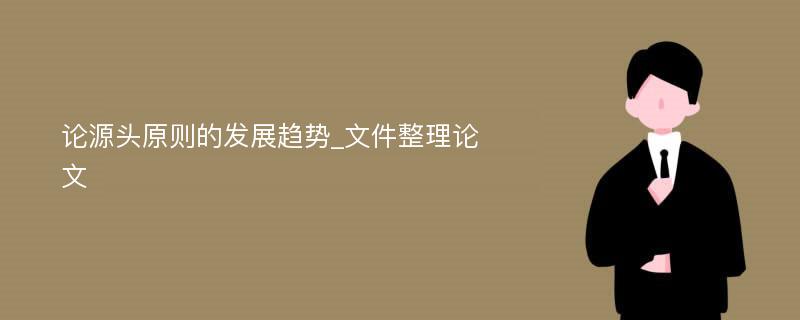
论来源原则的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则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源原则是档案学的特色理论之一,它从诞生至今走道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一百多年的实践检验中,来源原则几经沉浮,不断自我超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理论辨证回归的科学历程。综观整个来源原则的发展过程,根据各时期的不同特点,档案学理论界一般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来源阶段、双重来源阶段和新探索阶段。从来源观角度看,呈现出“一”而“二”,“二”而又“一”的有趣趋向。
一、传统来源原则——同一机关来源
1841年法国内政部部长杜卡特尔签署的《关于各省和各地区档案整理与分类的指令》的实施,标志了来源原则的正式诞生。后人对这一开山之举给予极高的评价和历史地位,因为它使“档案事业真正成为一项同图书馆事业相区别的独立事业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注:冯惠玲:《论档案整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而且“第一次开始接近文件运动规律,促进了近代档案学理论的诞生”(注:《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何嘉荪、傅荣校著,中国档案出版社)。这些结论无疑都是正确和客观的。但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当时的改革者并没有意识和预见到这一点。他们“不过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寻找一条便于查找档案的可行性措施而已”(注:《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韩玉梅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因此,在思路和逻辑上他们并不是十分清晰和严密的,他们所力求的不是理论上的有理有据,而是如何收拾前两任馆长卡缪和多努在档案整理上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因此,完全否定和抛弃事由原则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一方面我们可以把法国尊重全宗原则中残留的浓重的事由痕迹归结为是过去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把档案的功能单一化,仅仅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而为了历史研究的方便,就必须在来源原则的大框架下最大限度地按事由分类。所以说法国人提出的来源原则还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在尊重全宗的同时,却否定了档案形成过程中的原始联系。
推动来源原则进一步发展的是德国的登记室原则。它是在1881年柏林机密档案馆制订的分类条例中正式提出的。鉴于公文在国家机关的重要性,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发展的思想”逐渐渗透于档案整理原则中。加之德意志民族一向处世严谨、一丝不苟的品性,提出以档案来源确定性和原始次序不可更改性为主要内容的“登记室原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里,尊重全宗原则与历史发展的思想原则实现了伟大汇合。但登记室原则的弊病在于这种对原始次序的矫枉过正而扼杀了档案整理工作的生气和档案人员的创造性,档案工作者被无情地变成延长了的登记室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种思想都是由行政机关以法令、条令的形式发布的。这说明无论是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还是德国的登记室原则,他们的直接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理论研究。随着来源原则在欧洲的传播,荷兰学者首先开始了对来源原则的深入思考,第一次在理论上给来源原则提供了科学的论证。这就是1898年由缪勒、斐斯、福罗英三位学者合著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手册》的里程碑意义并不局限于书中独到的创见和更为具体的实施办法,而正如冯惠玲老师所言,它“使来源原则具备了一种普遍性的品格”,“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广为流传”,“并且促进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注:冯惠玲:《论档案整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传统来源原则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是以前苏联著名的“莫斯科公式”为代表的。与欧洲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前苏联的研究一度更加系统和全面,它对全宗和全宗内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一次明确地将全宗视为国家全部档案的基本分类单位。而且全宗内辨证唯物的文件分类法(即组织机构、年度、问题分类法)遵循了文件运动规律,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所有这些历史功绩都是不可抹杀的。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前苏联学者的“心口不一”。回顾法国第一次提出来源原则,它认为”全宗是来源于任何一个特定机关,如来源于一个行政当局、一个公司或一个家庭的历史上形成的档案体”(注:《档案文化论》,王英玮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而以莫斯科公式为基础建立的统一的全宗概念认为“在机关或个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地形成的档案材料的总和,称为机关或个人档案全宗”(注:《档案文化论》,王英玮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可见他们共同坚持了“统一”来源中的精髓——“机关来源”,因而形成了连他们自己的学者也承认的“在理论上抛弃了来源原则,而在实践中又恰恰坚持这一原则”(注:冯惠玲:《论档案整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的矛盾现象。谁又能说前苏联的全宗原则不是在来源原则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呢?
二、双重来源原则——机关来源与职能来源、历史联系与逻辑联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工作方式的巨大变化,档案种类和形成过程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新特征,传统的单一来源的来源原则几经成熟之后仍然受到了实践的挑战。实践的变化必然要求理论上的合理解释。秉承德意志民族血统的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首先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面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其著作《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中勇敢地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自由来源原则”,旨在“把来源和事由配成一种相当的比例关系,建立一种两者之间的综合体”(注:傅荣校:《布伦内克及其自由来源原则》,《档案与建设》1992年第4期)。这一理论的提出与布伦内克本人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有着实践和理论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实践上,他是一个真正的档案员,工作在档案整理第一线,在整理历史档案实践中,出于管理的实际需要,人为组织档案的方法得到肯定;在理论上,他有着十分深厚的哲学基础,因此他有能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审视荷兰人纯生物学角度的机械的“有机”思想,并从更为抽象的哲学角度重建这一思想,从而使档案整理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
然而布氏受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和档案管理实践水平的局限,他所引爆的“自由来源原则”难免有些晦涩和不明确,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后却没能明确指出前进的道路。实践期待着理论的继续深化。这就是五十年代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双重”来源原则。即,他认为当机关来源不能更好地解决某些特殊的档案整理问题时,那么以职能来源进行整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但遗憾的是他虽然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的来源原则在提供利用方面存在的局限,但仍然认为“它是确保档案完整的唯一方式”(注:《档案文化论》,王英玮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历史相当短的国家,因此没有太多的传统可以遵循和束缚,它的档案机构接收的文件往往较为凌乱。加之二战后美国行政机构的膨胀和“文件大爆炸”,人们在实践中“不得不容许各种不同地位和职权的组织机构文件在分级情况下形成组合”(注:《档案文化论》,王英玮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双重”原则中,始终贯彻着美国人历来信奉的“实用主义”思想,因此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是从文件本身而是从文件利用率着手,即当移交单位的文件整理状况不系统,降低了文件利用率时,他们认为就应该改变原来的整理状况。
可以说,到谢伦伯格的双重来源为止,来源原则所指导的档案整理实体基本上都是国家机关的公务文书,文书档案是理论和实践共同关注的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和交往的频繁,除文书档案外许多种类的专业专门档案相继出现。前苏联面对新问题再一次首当其冲,他们开出了“历史主义+逻辑主义”的药方,即认为“档案全宗是彼此具有历史联系和(或)逻辑联系的交由国家保管的文件综合体”(注:冯惠玲:《论档案整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载《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把各种类型的专业档案认为是逻辑主义的划分方法,通过扩大全宗范畴的方式从而在理论上对实践中已出现的现象以予了肯定。应该说前苏联此次对全宗定义的重大修正是及时的,是对实践的有力回应,是前进和发展的,但是它把全宗整体的本质联系之一概括为逻辑联系还是需要商榷的。
三、新探索阶段——同一社会活动过程与同一形成过程
70年代初前苏联的“双重联系”一经提出就受到了理论界的质疑,人们不禁要问“事由原则在被淘汰了100多年之后难道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注:《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何嘉荪、傅荣校著,中国档案出版社)?而且前苏联新全宗定义中的“逻辑联系”与“历史联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亦未说明,理论的现实意义究竟有多大呢?新的探索还在继续着。
70年代后期,我国著名档案学者何嘉荪和冯惠玲两位老师敏锐地抓住了档案工作中的全新现象,即专门性科技档案馆在各地的相继建立。为了在理论上对这一现象给以圆满的解释和指导未来的实践,他们提出了基于社会实践过程的“主客体全宗理论”。一时间这一理论引发了档案界的大讨论。与前苏联的“双重”联系相比,两理论的出发点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新出现的专业档案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立足点却是迥异的。之所以认为何、冯老师的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探索,是因为它致力于改变自布伦内克以来的双重来源在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实现“单”来源的辨证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回到原来的单一的机关来源上,而是回归到同一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它有偷换概念之嫌。但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开拓了档案学研究的新境界,同时它所作出的对电子文件时代全宗问题的超前性的思考预示了档案学和档案事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当电子文件这一全新的领域如所预料的那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新一轮的来源源则大讨论再次掀起。在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中,1996年第十三界国际档案大会有幸在中国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在总结各主要国家的档案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把传统的来源发展为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概念来源”,至今被档案界津津乐道。概念来源认为“来源不再仅仅表示全宗的单一形成者,而是一种更广义的、更抽象的、更广范围的联系”,“是以机构中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业务活动为重点的”(注:石珂:《原则与方法:信息时代来源原则定位的思考》,《山西档案》2002年第5期)。人们之所以对这一理论创新给以充分肯定是因为它从来源原则内涵的角度完成了它理论上的升华,是对档案本质及其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从此它跳出了档案整理领域,作为一种总则影响着整个文件生命周期和档案实践工作。
总而言之,来源原则从单一来源发展到双重来源,上世纪末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又回归到了单一来源,这一回归并不是从原点回到原点的简单机械运动,而是落到了一个更高阶梯上的辨证回归。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并不就意味着来源原则的发展就此可以划上圆满的句号,而恰恰相反的是,它应该是新征程的又一个起点。理论不可能一劳永逸,实践是它永远的鞭策。这也是来源原则保持生命活力的基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