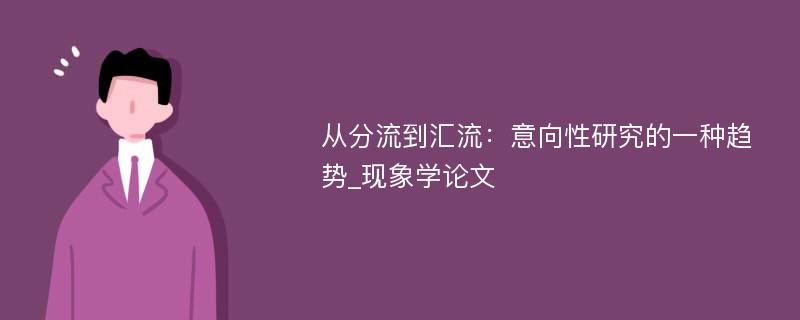
从分流到合流:意义-意向性研究的一种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向性论文,流到论文,走向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不仅意义、语义性、意向性、表征和心理内容等是不同学科的专门研究对象,而且,像意义这样的对象,同时还是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和解释学等不同学科的不同对象。这是因为,世界上不只语言这种现象有意义,其他许多存在都具有意义这一属性。格雷马斯说:“只要你对意义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意义无处不在,千姿百态。”①例如,如果我们不否认下述用法的合法性,那么我们不仅要承认意义的存在,而且还要肯定它的多样性:“认识的意义”、“知识的意义”、“真假的意义”、“情感的意义”、“经济的意义”、“劳动的意义”、“产品的意义”、“利润、地租、工资的意义”、“政治活动的意义”、“国家政党的意义”、“民主、法律的意义”、“进步的意义”、“天上的云彩的意义”、“古生物化石的意义”、“古松的意义”、“那块天然怪石的意义”等等。这么多的意义显然不是一门学科能统摄的。意向性也是如此,哲学自不待说,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行为科学、进化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都建立了自己的意向性理论。然而,随着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等向纵深的发展,与上述意义、意向性研究的“分流”同步的是,有关领域内出现了一种“合流”的走向,其表现有多方面,之一是,有关学科在对意义等作分门别类研究的同时,又从各自的视角把它们作为没有区别的统一的对象加以探讨,把“意义”、“内容”、“表征”、“关于性”和“意向性”等当作没有实质差别的概念加以理解。之二是,分析传统的意向性理论与现象学传统的意向性理论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最近又出现了靠拢乃至融合的趋势。之三是,在更高的层面对各种意义进行统一观照,以揭示最一般意义的“意义”和本质。
一、语言学、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概念——问题整合
意义研究合流的一个表现是,以前分属不同学科的不同问题,如意义问题、意向性问题、表征问题等,现在被看作同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意义问题以前主要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的课题,心理内容是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对象,表征是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中的对象,而意向性是哲学谈论较多的话题;在最近30年,它们几乎与意向性研究合而为一了,最明显的例证是,许多论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常用“或”把它们连在一起,作为同义词加以看待。问题的这种变化绝不是表面上的用语或概念上的变化,而是既意味着人们对研究对象内在本质及其关系的认识上的深化,又反映着有关学科的发展轨迹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更体现了学科内在关系的变化,例如在分化基础上的一体化和整体化倾向。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有关概念内涵的趋同乃至同一来说明有关学科的这种一体化走势。
合流性研究中用得最多的概念是“意向性”。在传统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一般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现象区别于其他非心理现象的一个独特的标志或特征,“关于性(aboutness)”或“关涉性(of-ness)”是语词的特征。新的倾向是,人们常用关于性等来说明意向性。海尔说:“心灵状态可能是‘投射性的’,如信念可以关于实际或可能的对象……这种关于性或对于性(for-ness),哲学家称之为‘意向性’,是心灵独有的。”②有的人甚至把它们当作同义词使用。最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学科常用“意义”说明意向性,或把意义当作意向性的一个代名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人们从哲学上追问“意义”的意义时,必然要触及言语符号何以有指称对象、表示事态的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根据、条件之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好就是意向性问题。另外,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之所以关注意义问题,是因为这些学科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其基础会受到威胁。因为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任务是要解释行为,而要如此,仅诉诸大脑状态似乎不行,还必须求助于人们所知道的东西。这便涉及了语义问题。还有人认为,传统哲学的意义问题仅靠哲学是不可能解决的,而认知科学在这方面则大有可为。③由于这些原因,意义问题便成了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问题,相应地,心灵哲学家也建立了自己的意义理论,它既可被称作意向性理论,也可被称作意义理论或语义学理论,如德雷斯基、米利肯和福多等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信息语义学”、“目的论语义学”和“因果性心理语义学”等。
与意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语义性”,它作为语义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语言符号这样的属性,即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在心灵哲学中,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它指的是心理符号的语义性,即强调心理符号尽管是形式化的东西,但它能把人与外在世界关联起来,能表示、指称外在事态,且有成真的条件。很显然,有语义性实际上就是有意向性。当然,有的人,如福多等人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语义性比意向性更根本。
在西方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中,谈论“心理内容”的很多,但多停留于抽象的层面,至多只把它设定为解释认识论、心理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一种必需的理论实在,尚未触及到其本体论、地形学、地貌学、结构学问题。随着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飞速发展,以及以心灵哲学在此背景下对心理地形学、结构学、运动学和动力学探讨的深化,心理内容越来越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其前沿课题主要有心理内容的本质、存在方式、自然化和因果作用等处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认知科学交叉地带的问题。按照新的理解,心理现象不外两大类,一是命题态度,二是包括躯体感觉、知觉、情感体验等在内的现象性经验。它们都有内容,前者有概念性、命题性内容,后者是非概念性内容。例如一信念“相信天要下雨”就是一命题态度。“天要下雨”是一命题或心理语句,亦即是相信这种态度的内容。如果它们就是内容,那么一系列哲学问题便接踵而至:描述信念内容所用的命题如“天要下雨”等在描述心灵时起什么作用?当我们求助于有关外部世界的命题来刻画心灵的特性时我们正在做什么?这些内容是实有的还是为解释人的需要而归属给人的?如果是实有的,它们以什么形式存在?它们为什么能够、又是如何表现外部世界的?等等,很显然,这些问题正好就是意向性问题的子问题。正是基于这种关系,人们一般把“意向性”、“意义”和“心理内容”等当作同义词使用。
“表征”以前一般多出现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之中,现在也有与意向性研究合流的迹象。所谓表征即是这样的一种代表,它代表着它之外的某东西,因此有本体论承诺,它能被计算或加工,还能被交流。从信息论的观点看,表征与信息密不可分,它代表着对象意味着它载荷着有关的信息。由于表征不仅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能主动地指向、关涉世界上的别的事物,因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哲学问题。例如表征是怎样起源的?表征为什么能够、又是由于什么而代表别的东西?头脑中被储存或加工的表征究竟是什么?表征是似语言的媒介物,还是图画式的东西,抑或是全息性的东西?除心灵之外,语词、记号、图标、人工符号系统等也能表征或关于别的事物。例如“禁止左转”的路标警示的是有关的车辆,而不是路标本身。因此,便有这样的问题:它们是怎么或由于什么而表征世界的?卡明斯鉴于表征问题涉及的方面太多,便对之作了概括和归类,认为它包括两大类问题:一是复数的表征(representations)问题。它们属于科学层面的问题,主要是试图从经验科学的层面探讨:怎样描述表征?它的物理实现是什么?在心理加工中有何作用?二是单数的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它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如表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相似、协变,还是功能作用、适应作用,表征关系究竟是心灵与柏拉图式的形式的原始的、非物理的关系,还是可还原为物理属性的关系?④很显然,这样表述的问题都是典型的意向性问题。当然,也有一些表征论者认为,弄清了表征问题,就可解释意向性问题。因为表征是科学概念,而意向性是常识概念。这一看法表达的是关于意向性的自然化的一种方案,即表征主义方案。
就有关领域的论者的看法而言,他们对“意义”、“内容”、“表征”、“关于性”和“意向性”等概念的关系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些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所隐含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应区别对待。这种观点可称作“分别论”。另一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可概括为“不加区分论”或“等同论”。它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若有区别,也只是表述的侧重点、角度上的区别。雅各布在《心灵能做什么》这本研究意向性的重要论著中说:“意向性就是让人的心灵状态即所谓的命题态度(如信念、愿望)关于或表征非心理的、心理的事物以及可能、实在和不可能的事态的东西。换言之,有意向性或表征,就是心灵的个别状态有语义属性。”⑤这就是说,有命题内容就是命题有意义,有意向性,有语义属性,即是关于或指向某存在或不存在的事态,或者说是对这些事态的表征。斯托纳克也认为,意向性问题就是关于表征本质的问题。众所周知,意向关系或表征关系似乎不同于自然界中的事物、事件之间存在的关系,如因果相互作用、时空关系、各种同一与差异的关系等。人可以画出、描绘、想到神或金山之类的东西,即使它们并不存在。⑥博格丹从进化论的角度说明了意向性与表征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表征中最高级的形式是元表征,而元表征是生物的意向性长期进化的结果。⑦吉勒特承认这些概念有微妙的差别,⑧但又强调:对意义的说明是与对概念的一般说明密不可分的。意义像表征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表现意向性,这是因为:(1)它们指向自身以外的对象和特征,而这些对象和特征又是在意义得以固定下来的实践中被分辨出来的。(2)它们使一系列运用于定向活动中的能力获得了结构。⑨
上述概念从细微的方面看确有区别,但只要我们进到其内核,就可看出它们没有实质区别。因为根据心理表征理论和关于心理的计算理论,以心理表征为加工媒介的心理状态就是命题态度,而命题态度是有机体与心理表征或心灵语言的心理语句的关系。因此有心理态度、有表征也就是有心理语句。而心理语句有句法和语义两种属性。句法属性是指心理语句像自然语言的句子一样也是由字词等符号按照一定的规则构造而成的,有其特定的物理关系和形式结构。语义属性是指心理语句也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它们总是关于某种存在或不存在的事态的。这是命题态度除因果性之外的又一根本特征,人们常称之为心理语义性,相应地把关于心理语义性的问题称为“意义”问题、把相应的理论称为心理语义学或关于心理语言的意义理论。从特定意义上说,心理语句“关于(about/of)”、意指、提及(refer to)什么,其实就是命题态度包含特定的内容,心理语句以特定的形式表达了这些内容,因此意向性问题也就是心理内容问题。还须注意的是,“心理内容”、“意义”、“心理语义性”、“心理表征”等范畴的出现绝不是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反映出心灵哲学在向心灵深掘过程中发现了传统意向性研究所未注意到的现象和问题。这些范畴在含义上有微妙的差异,在观照命题态度时的侧重点和切入点不同,但都窥探到了心理现象的某种更深层的奥秘和特点。
由于心灵哲学对意向性的整合性研究,汇合有关学科而成的统一的意向性问题或意义问题已成了一个有相对稳定的对象、包含许多深层次问题的研究领域。当代意向性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子问题:(1)意向性的主体。当代在物理主义、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心理内容理论所关心的意向性主体,主要是物质世界中最复杂的系统,特别是人的大脑。(2)心理内容的本体论地位,即意向性在物理主义世界观中有无位置的问题。(3)心理内容的本质、心理内容与所指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即心理内容是如何确定的?其个体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换言之,心理内容的个体化与意向心理状态持有者的内在生理物理因素、外在环境因素有何关系?(4)心理内容的因果性,即心理内容在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中有无因果作用?心对身体的作用是由心理表征的句法结构还是由语义属性(内容)承当的?
二、意向性研究中的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的融合走向
不可否认的是,意向性作为传统的哲学问题在进入现当代哲学视野之后,受哲学内部致思取向和思想方法的影响,又分化为两大传统或走向,一是英美的分析哲学走向,二是大陆的现象学传统。即使是今日出现了融合的走向,但分化仍是基本的事实。
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分析传统的意向性研究中的一些新的融合倾向。马巴赫认为,英美认知科学、心灵哲学在研究意向性时,忽视了现象学的视角,而这是不利的,因此他倡导来一场现象学转向。⑩他不否认心理表征对于说明意向性的作用,但认为,英美流行的据以解释意向性的心理表征理论,不管是认知科学中的,还是心灵哲学中的,都是错误的。其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在揭示心理表征的过程中,缺乏主观的、纯粹精神性的、亦即现象学的观点和视角。在他看来,要完成根据心理表征说明意向性的任务,必须真正实行“主观的”或“现象学的转向”。在马巴赫看来,英美的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的表征研究的问题是:在研究中,完全置意识于不顾,这就像研究物理学不研究物质和能量、研究生物学不研究生命一样荒唐。(11)
麦卡洛克像胡塞尔一样,从否定方面来说,公开站在自然主义的对立面,从肯定方面来说,他在意向性研究中明确贯彻现象学原则。但是经过对当今分析哲学意向性研究中盛行的外在主义思潮的了解和研究,他又发现,它有合理性,尽管与现象学有不合拍之处,但也不能轻易否弃。于是他把它们有机地揉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意向性理论。它由三个基本原则构成:(1)现象学的观点:有心灵就像有某种东西。(2)外在主义:心灵不在头脑之中。(3)认识论:关于心灵的知识不同于物理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从微观上说,这三方面分别构成了三种具体的理论,即内容理论,关于指向世界的理论和意向性理论。他的意向性理论的首要主张就是:现象学维度是其不可或缺的方面。他说:“对意向性的任何说明必须能涵盖这样的事实,即内容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方式出现在意识之中了,或者说内容有现象学维度。”(12)例如我在想到什么思想内容时,必然伴随有现象学知觉,在第三人称情况下也是如此,某人表现出他在想什么,或说出他在想什么,我能看到或听到他所意指的东西。这些都表明意向内容有现象学性质。根据这种观点,内容与现象学性质不可分割,因为思维就是有一些观念,而观念是觉知或意识的对象,因此是具有现象学性质的对象。例如想到猫,就是有关于猫的意象,就是关于猫,这也就是说,想到猫是一个有现象学性质的过程。因此要说明内容,说明意向性,形成关于它的理论,一定不能忽视现象学性质,必须尊重内容的现象学维度。
当然,麦卡洛克又强调:承认内容是现象学概念并不等于主张:要把内容还原为感觉,还原为心灵的纯粹的质的方面。他所说的外在主义是指这样的理论,它强调:心灵不在头脑之中,内容是由外在世界决定的。他深知:在说明意向性时坚持外在主义原则,不外是要做到:“根据思想者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真实的(即存在的、因果的和规范的)关系来说明作为真正心理特征看待的意向性”(13)。亦即,以外在主义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意向性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对立于二元论和唯心主义的整体论理论的,因为二元论,唯心主义承认有两个整体论世界,一是心灵王国,一是物理王国。而他所倡导的意向性理论由于坚持外在主义,因此尽管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的特征,但又主张:它只能根据外在世界的关联来予以理解。
在洛尔看来,关于心理内容的概念必须符合两个要求,一是不违背常识,即能说明行为是如何由意向内容产生的,二是要有内在决定的维度。根据这样的要求,心理内容应有水平和垂直两个方面,即既有从内在方面加以解释的概念作用,同时又有从外在方面可以说明的外在指称的意向性。也就是说,要形成关于心理内容的正确理解,必须把概念作用语义学和外在主义结合起来。(14)就意向性或内容的个体化问题而言,洛尔认为,英美之所以流行外在主义,主要原因是长期受分析传统的影响,而分析传统使关于心理内容的概念变得越来越贫乏,因为它“强调的是语言和指称”。“一当我们转向现象学……我们就会获得关于内在意向性的理解”。(15)由上所决定,在分析传统之下,人们忽视了对心理生活本身的探究兴趣和热情,往往简单地把它斥之为形而上学的虚伪对象而弃之不顾。反过来,如果转向现象学,关注对心理生活内在本质结构的研究,那么便必然走向内在主义。洛尔说:“关于心理生活的强烈的直觉就是把心理生活看作有意识、思想、情感和知觉的一种流动……这对我们建立关于心理的东西的构想来说至关重要。……这种流似乎有自己的、不依赖于外在环境而独自构成的生命。”(16)他还说:“我自己的心理流的意向特征——甚至思想的那些向外指向的特征——是独立于我在世界中的现实条件而构成的。”(17)这也就是说,在内容个体化问题上,受分析传统影响的外在主义仅注意静态的东西,外在世界中的现实条件,而不注意心理流,不注意现象学方面,因而必然会走入死胡同。因此在这里,不仅要有现象学的视角,而且最好是用它取代外在主义的那些分析方法。
皮科克是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中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在心理内容或意向性问题上,他发表了大量论著,有些观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经常的讨论,也启迪了许多后来人。在皮科克看来,心理内容领域尽管争论很多,但实质性的进步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内容的多种形式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其次是研究的方法、视角比较单一,尤其是缺乏与现象学的沟通。根据他的看法,有些内容如表征内容必须同时诉诸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具体科学的方法,才有可能得到澄清。
皮科克认为,至少有这样一些形式的内容,如信息内容、概念内容、经验内容和表征内容。它们彼此区别很大,例如从复杂程度上说,它们是不断加深的。信息内容是人的内部状态、身体部位、外界事物都可能携带的内容。例如地上留下的脚印有这样的信息内容:在过去的某一时刻,此地曾有人经过。概念内容又可看作判断内容,是人的意向状态所独有的内容,常通过命题的形式,由that-从句所表达。所谓经验内容实即现象学经验或感受性质(qualia)。当今的大多数论者都否认经验有内容或有意向性,皮科克则肯定经验也有自己特定的内容。他说:“一经验的内容应该与经验所引起的判断的内容区别开来。”(18)至于表征内容,他认为,它同时有两个特点。“第一,表征内容总是关于经验主体之外的世界的,因此本身可作真假评价。第二,这内容是内在于经验的某种东西——如果一种经验不是按内容描述的方式将世界再现于主体,那么这经验在现象学上就是不同类型的经验。”(19)由这些特点所决定,具有特定表征内容的经验之所以出现,总离不开过去经验和学习的作用。
在皮科克看来,要说明心理内容,就必须根据不同的内容形式选择不同的说明方式。例如对于信息内容和概念内容就可以用英美常见的自然化方法来分析、说明,而对于经验内容则只能用现象学方法来分析。因为根据外在对象、根据表述经验的概念或语词的分析都无法接近这种经验。而对于同时具有两种特点的表征内容则应同时运用自然化的分析方法和现象学的方法,因为每种方法在有它的优越性的同时又都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分析方法适合于把握表征内容的概念和信息方面,但对现象学特征于事无补,同时,现象学方法在把握表征内容的现象特征时必不可少,但在把握概念内容时不一定能比得上分析的方法。因为后者能基于作为意向结构之表现的语言结构的分析,较好地揭示意向结构及其本质。
吉勒特与麦克米兰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融合论,其宗旨就是把两种研究意向性的传统调和、结合起来,(20)例如要解决“意向性悖论”就必须这样。以我想到了方的圆为例。这里被想到的方的圆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确实想到了它,两者之间似乎有意向关系。而根据关系的要求,关系中的要件哪怕缺少一个,关系便不能存在。然而意向性居然被公认为是关系属性。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所谓的“意向性悖论”。(21)根据吉勒特等人的看法,要解决上述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塞尔和作为分析哲学家的埃文斯(G.Evans)的有关观点整合起来,然后作适当的改造和融合。
根据吉勒特等人的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肯定内在经验有两种意向相关项,一是意向对象,它把经验统一起来,同时让经验与对象关联起来,二是现实的对象。他的分析还表明:经验为什么具有统一性,以及经验中哪些因素可以作为经验统一体的组成部分,这都是由意向对象决定的。在胡塞尔看来,意向对象在意向指向现实对象时限定了现实世界的所指。如果我们在指称和超越个体心灵及其对指称的认知的意向活动之间能发现可靠的联系,那么就解决了意向性悖论。然而胡塞尔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虽然他拒绝怀疑主义,但他并没有把意向对象与世界关联起来,就像没有说明意识与对象之间的语义或意向关系一样。埃文斯的思想可弥补这一不足。他认为,关于特殊个体的思想后面肯定存在着比因果关系更为复杂的关系。对所想到的对象,思想者肯定是亲知的(acquaintance),而在这种对象和思想之间存在的关系则是一种“信息关联(information link)”,也就是说,某人之所以想到某对象,例如不存在的对象或古怪的对象,是因为他有有关的信息。信息组合不同,对象也不同。因此要进一步说明不同思想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如何形成的,还得具体说明“信息”。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有办法描述思想和对象的意向关系,更好说明思想为什么能是关于存在的和不存在的东西。根据他的观点,人是由时间、性别、地位等而个体化的。其他的事物则是由时空、形态特征等方面的信息而个体化的。就真实的思想对象而言,获得了我们所面对事物的特征方面的信息,借助我们的判断能力,就有对象出现在我们的思想中,就有关于事物怎样存在于世界中的理解。怪异的思想也不例外,我们之所以想到稀奇古怪的对象,是因为我们有与那对象的特定的信息联系。由于人所搜集、选择的信息有真有假,有可靠和不可靠之分,对信息的组合、分解、判断更有真实和胡编乱造之分,因此基于信息联系而形成的对象当然有真实和虚构之别。
三、寻求意义的统一理解
如前所述,意义的形式多种多样,范围极其广泛,如自然意义、符号意义、人生意义、道德意义、政治意义等等。既然如此,要想找到各种意义的共同本质,进而为其找到统一的理解,建立一种统一的理论,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也是这样,此前的意义研究一般只局限于某一领域的意义,充其量,进到了元理论的层面,以探讨某类意义的“意义”。到目前为止,意义理论关注的意义主要是语言及符号的意义。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严格限定的领域,其探索者自己都觉得晕头转向,因此很少有人敢奢望进到各种形式的意义的最高层面,探索所有意义的“意义”,直至建立关于意义的一般性理论。
然而,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人总是会出现的。上世纪末在意义研究中终于出现了这样的人:肖普和斯坦普等人。肖普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关于意义的统一理论(United Theory of Meaning)。围绕这一课题,他做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就是《有意义的实质——表示、表示力和意义》。他的意图很明确,他说:“现在的探讨并不完全局限于一个或另一个标准的领域,如心理分析的哲学、心灵哲学、语言哲学或认知科学的哲学研究等。确切地说,它试图表达关于‘有意义(meaningfulness)’的一种统一的观点,它涵盖了这样一些题目,如语言表达式和习惯符号的有意义,弗洛伊德关于各种心理现象和行为例示的有意义的观点,人做某事的意义,艺术作品的意义,甚至生产所具有的意义。”(22)
在肖普看来,现有的意义研究的处境十分尴尬,这表现在:尽管出了那么多的成果,尽管那么多的成果都旨在说明意义的本质和条件,揭示意义的奥秘,但“意义”的意义直到今天仍是最不清楚的一种现象。这种状况无异于“盲人摸象”。“意义”就是要认识的大象,研究意义的各方面的专家不过是来摸象的盲人。他们对意义的认识只涉及意义的某一局部或方面。而不幸的是,他们都把自己对意义的认识看作对一般意义现象的认识。
肖普倡导建立统一的意义理论。在他看来,意义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突破,没有实现认识上的质的飞跃,而只有意义理论、学说的数量上的增加,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都是从自己所熟悉的学科出发,进而抓住意义的某一方面、某一种形式进行研究,然后武断地把自己所认识到的“意义”的意义看作是关于一般意义的认识,把自己的意义理论宣称为一般的乃至哲学的意义理论。在肖普看来,现有的意义理论严格说来都算不上名副其实的意义理论,充其量,它们只是关于某一种意义如语言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的理论。
肖普还考察了关于意义的表征论、意向论和内容论(即把意义问题与内容问题等同看待的观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根据内容说明意义,充其量只能说明什么使一种心理状态不同于另一种心理状态,例如同是愿望,“想喝水”与“想喝饮料”的区别何在。在他们看来,x关于y,就是x表征了y。肖普认为,只有心理符号的意义问题与心理内容有关系,至多只有这种意义能与心理内容等同,而其他许多形式的意义,如格赖斯所说的自然意义显然与心理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由于肖普的目的是建立关于意义的统一的、一般的理论,因此他不太关心内容理论。
基于同样的理由,肖普也反对当今流行的做法,即把意义问题与意向性、关于性、表征性连在一起,甚至把它们等量齐观。他强调:意义与意向性、关于性、表征是不同的东西,在存在的层次、显现的方式上有很大差别,因此是不能混同的。例如,某句子关于什么,与说某句子有何意义、意指什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仔细推敲,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另外,某物在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意义与它在某时某地对某人的特殊意义也是不同的。亦即,一项目有什么意义与一项目实际表现出的意义是不同的。再则,意向性与心灵密不可分,但意义则不一定,例如树的年轮表示的是树的年龄,即使与心灵没有关系,它也有这个意义。(23)
在肖普看来,现有的意义理论有两大问题,其一,只关心某种形式、某一局部的意义;其二,忽视了意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有意义(meaningfulness)”。这两个问题就是他试图建立的关于意义的统一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确立了他的意义理论的主要任务、内容和基本特征,而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则构成了他的意义理论的切入点、基本思路和方法。
意义和有意义两者有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它们都不能独立存在,都依赖于一定的载体,甚至可同时存在于同一个载体中,因此可以说它们是由一定载体表现出来的属性。但两者又不能混同,前者是这载体所具体显示出来的意义,如一物冒烟的意义就是那里有火。因此可以说,意义是意义载体(如符号)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意义。而有意义则不同,它与具体意义无关,它比意义更抽象、更重要、更根本。另外,这两者的成立条件是不一样的。一事物有什么意义是由有关的具体因素决定的,而一事物具有“有意义”这一属性则是由更一般的条件决定的,是由更一般的因素构成的。最后“有意义”存在的范围比意义要广泛得多,也就是说,有些事物有“有意义”的属性,但不一定有“意义”。因为“有意义”即是某物自身充满意义,包含意义,即使没有有情识的东西在它后面,没有这存在感知和识别它,它也照样会由其载体所载荷,并表现出来。“有意义”尽管很抽象,但它们肯定是存在的,肯定有自己的本体论地位。不仅如此,“有意义”还具有普遍的存在性。他说:“‘有意义’和表征渗透到了与人有关的一切事实之中。”(24)但可惜的是,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学者只看到了很小范围内的意义,相应地也只注意与它们有关的意义载体,以为只有它们才能表现出意义,不仅如此,更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有人注意到“有意义”这一方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所建立的、关于“有意义”的统一观点(unified view of meaningfulness),除了要研究各种意义之外,还要探讨极其广泛的“有意义”现象,如语言表达式的有意义,常见符号的有意义,弗洛伊德关于各种心理现象和行为事例的有意义,人所做的事情的有意义,艺术品的有意义,甚至生命所具有的意义。由此可见,他的所谓的统一的意义理论,不仅是要对一切形式的意义作统一观照,而且要对一切“有意义”现象作出探讨进而对两者作出统一的说明。
他对两者的“统一”说明表现何在呢?很简单,那就是把意义统一于“有意义”,根据后者对前者作出说明。在他看来,要解释关于意义的根本问题,出路在于分析“有意义”。他说:“一般地说明有意义对于解决关于意义的各种各样的特殊难题具有重要价值。”(25)众所周知,意义问题有许多难题,如意义是宽还是窄,再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中涉及的意义问题,生命的意义问题等。
“有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怎样才能解决“有意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既简单,又复杂。所谓简单,就是他认为,可根据关于“表示”的理论来说明有意义。因为要说明各种形式的意义,必须知道更一般的“有意义”。而说明有意义,不外乎说明有意义是如何可能的,根源于什么,由什么所决定,亦即为它的成立提供充分条件。因此有意义的问题实即如何说明其构成、如何揭示其充分条件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弄清有意义事物的一个更根本的属性,即表示(representing)。因为一事物有意义,实即它能表示它之外的某事物,或具有表示的力量和性质。所谓复杂,主要是因为“表示”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另外,根据“表示”来说明各种形式的意义也是一相当繁难的工作。
什么是表示?表示是不是人们常说的表征?如不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属性?在内容理论中,人们一般把“x表示(represent)y”与“x是y的表征”同一起来。肖普认为,它们是不能等同的。因为即使天花板上有光的点表示的是火星儿,但是如果说它是火星儿的表征或代表就不妥了,因此表征只是表示的一个属或一种形式。(26)
当某物表示了某事,但又不是某事的表征时,这个特定的某物就存在于表示某事的状态之中,该状态的出现或存在就是名词“表征”的一通常含义。在肖普看来,“表征”实际上是“提供了表征”,例如温度计上的水银柱的高度提供了关于温度的表征,即高度代表的是温度。但是,水银柱的高度本身不是一个个体或一个子目,也不是作为表征本身的子目的一个方面。可见,提供一个表征就是存在于一种表征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允许一子目表示某物,例如水银柱的高度就是一种表征状态,因为它有某种表示温度的幅度。基于上述讨论,肖普重点分析了表示,而未强调构成表征的具体项目。
在他看来,要理解表示(representing),必须把它与能表示的事物(representing object)放在一起来理解。他认为,它们是一对很重要的概念。后者指有意义的载体,而前者是它的一种属性或作用,即能表示的事物所具有的能表示某种意义的属性。由于有这种属性,该载体才会在特定的环境下,当相应条件得到满足时,向外界显现出具体的意义。
问题在于:一能表示的事物为什么具有表示的能力?这能力是如何可能的呢?如前所述,所谓“表示”指的是事物具有能表示别的什么东西的属性,如x表示y。对此可从因果关系和认识关系两方面作出分析。换言之,一物的表示属性是由因果关系和认识关系两种因素共同决定的,是两类因素的结合。因此,这种对表示的分析既是充分条件分析,又是构成要素分析。这也就是说,y之所以被x表示,一方面是由于x所具有的特定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又是由于有我们对它的认识关系。由于有后一种关系,因此“表示从特定的方面来说与心灵有一定的关系”(27)。这也就是说,x之所以表示y,离不开人的存在及认识,只有当它们与人发生了关系时,才有它们的表示和被表示的关系。而人之所以有这种作用,又是因为人有心灵。总之,表示关系的存在“离不开某时有心灵存在”。(28)当然,这并不是说,表示关系依赖于心灵而存在,在心灵之内而存在,而只是说,只有当人的认识关系发生了,表示关系才有可能出现,因此认识关系只是表示关系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肖普看来,一状态要能表示另外的东西,还离不开特定的因果关系。他说:“x要表示y,x和y之间必须有某种因果关系存在。”(29)这也就是说,一符号、一图像要表示某事物,它必须有某种表示力,它内部有表示他物的因果力,而要有这x及其因果力,又必须有某种因果关系或因果历史,是它们授予x以能表示他物的因果力。例如“桌子”一词之所以能表示实际存在的桌子,是因为此前曾经有这样的过程,它赋予“桌子”以这样的表示力。人的血压升高之所以能表示体内有某种疾病,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因果联系。总之,表示关系之成立离不开“因果力和正常的因果链”的存在。(30)肖普认为,根据对表示的分析,可以建立一种统一的意义理论,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相对于语境C来说]x的意义就是h(或者说x指示的东西就是h),当且仅当
(1)x的内容-答案是h,且
(2)有h。
内容-答案是对“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有这个问题,是意义产生的一个条件。例如只有当有可能问:一棵树的年龄是“什么”时,树的年轮才会有表示的意义。
有了关于表示的一般理论,那么“就有可能解决关于意义的各种课题”。这正是肖普的基本思路。他说:“我们对表示现象的分析,目的就在于分析意义。”(31)例如常见符号的意义、自然现象的意义、弗洛伊德所说的梦和精神病症状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都可根据表示理论得到说明。不管是什么意义,都可看作一种有表示力的事物或状态所表示的东西。就言语的非自然意义来说,一事物x有非自然意义y,无疑就是x表示了y。同样,“x表示y也可成为x有自然意义的例示。因此自然意义和语言意义便以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了”(32)。梦和精神病症状的意义也不例外。他说:“这一关于意义的方案有助于我们理解:当x是有意识的梦境、精神病症状或动作倒错时,精神分析为什么把意义赋予x。”(33)在这里,我们可以把 Sx当作发生的事态,它们包含了x的内容细节,把Sy当作产生这种事态的原因,它们引起了一系列联系。由于有这种因果联系,当y是x的一种意义时,它便意味着x之所以发生,部分原因是:y并非完全是有意识的,或完全表现出来了,另外,它也意味着,y是x所服从的一些意图或目的的结合,是x在某些心理状态系列中所处的位置。生命的意义也可这样来理解。生命有无意义取决于生命有没有这样的表示力和因果链,如果有,生命就有意义,反之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之所以比另一个人的生活更有意义,也是由各自表示力的因果链决定的。(34)再拿宗教信徒来说,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表示的是神的作用。例如如果他们如此这样去做,那么他们就会受到如此这般的奖赏或惩罚,这是神的意旨的表现,因此生命的意义就是:某人因为其努力而受到神的奖赏。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可能会认为生命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能采取有价值的行为,取得有价值的成功,因为生命表示的是遵循那些价值准则的奋斗。(35)
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意义问题中,最难的问题莫过于“意义”的意义问题。肖普说:“关于‘有意义’的本质所获得的结论将帮助我们回答‘意义’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36)根据他对“表示”的分析,“有意义就是有这样的事项,它表示了某事,或者说有意义就是以某种方式相关于能表示某事的事项,既然如此,那事项出现在与它表示的东西有因果联系的情境中的方式就表明了关于后者的有关命题。因此意义是我们世界的形而上的和认识上的特征的混血儿”(37)。
寻求意义的统一理解,是科学发展的整合趋势在意义研究中的反映,因而有其必然性。既然如此,肖普对意义统一理论的建构就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的理论也不是一花独放。早在他之前,格赖斯就作出了自己的尝试。例如他试图找到各种意义后面的统一性。为此,他把视角指向一切意义,并把它们分为非自然的意义(语词的意义)和自然的意义(如树的年轮的意义)两种,认为,根据某种对结果概念的解释,如果x意指h,那么它作为h这一事实就是x的结果。也就是说h的发生,即与“that h”这一表述形式一致的事态的发生,无需是x的发生的一个因果性的结果,它只是x意指h的一个证明性的结果。例如一个人的呻吟声意味着他处在疼痛之中,这种声音并未引起疼痛,而只是对那个人处在疼痛之中这一结果提供了证据。当然在别的情况下,这里的结果可能是因果性的。无论结果如何,“x意指h”总有其可分辨的结果。后来的斯坦普在寻求对意义的统一理解时,也注意到了“表示”,认为表示实质上就是一种指示(indication)。例如一对象只要在某时处在特定的放射性状态就会指示它下一阶段会释放什么粒子。斯托尔纳克认为,有表示能力的事物指示的是:情况就是这样,如温度计指示:温度是80°F。在他看来,所谓“指示”实即能指示的事物与所表示的东西之间的一种关系,其发展的高级形式就是意向关系。(38)
注释:
①A.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页。
②J.Heil,Philosophy of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521.
③参见Z.W.Pylyshyn et al(eds.),Meaning and Cognitive Structure,“Preface”,New Jersey: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6,p.vii。
④参见R.Cummins,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1989,pp.1-10。
⑤P.Jacob,What Minds Can D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
⑥参见M.Tye,“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ality”,in P.French et al (eds.),Philosophical Naturalism,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4,p.124。
⑦参见R.Bogdan,Minding Mind,Cambridge,MA:MIT Press,2000,pp.95-96。
⑧参见G.Gillett,Representation:Meaning and Though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101。
⑨参见同上书,第135页。
⑩参见E.Marbarch,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sciousnes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3,p.19。
(11)同上书,第4页。
(12)G.McCuloch,The Life of Mind,Oxford:Routledge,2003,p.10.
(13)G.McCuloch,The Life of Mind,Oxford:Routledge,2003,p.11.
(14)参见B.Loar,“Phenomenal Intentionality as Basis of Mental Content”,in M.Hahn and B.Ramberg(eds.),Reflections and Replies,Cambridge,MA:MIT Press,2003,p.234。
(15)同上书,第230页。
(16)同上书,第230页。
(17)同上书,第230页。
(18)C.Peacocke,Sense and Cont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p.5-6.
(19)同上书,第9页。
(20)参见同上书,第9页。
(21)参见同上书,第72页。
(22)R.K.Shope,The Nature of Meaningfulness:Representation,Power,and Meaning,Oxford: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Inc.,1999,p.xi.
(23)参见R.K.Shope,The Nature of Meaningfulness:Representation,Power,and Meaning,p.8。
(24)同上书,第3页。
(25)R.K.Shope,The Nature of Meaningfulness:Representation,Power,and Meaning,pp.4-5.
(26)参见同上书,第18页。
(27)R.K.Shope,The Nature of Meaningfulness:Representation,Power,and Meaning,p.7.
(28)同上书,第7页。
(29)同上书,第25页。
(30)参见同上书,第63页。
(31)同上书,第139页。
(32)同上书,第158页。
(33)同上书,第177页。
(34)参见R.K.Shope,The Nature of Meaningfulness:Representation,Power,and Meaning,p.185.
(35)参见同上书,第182-183页。
(36)同上书,第187页。
(37)同上书,第205页。
(38)参见同上书,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