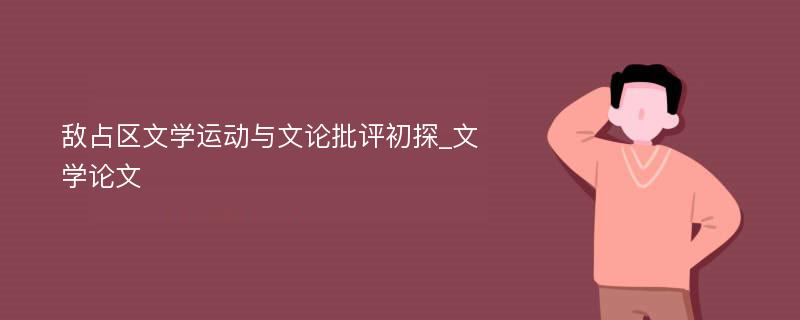
沦陷区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初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沦陷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1053(2000)01—0081—07
沦陷区是指中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段时间先后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范围,最大时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五大地区以及台湾,其地域之广阔达大半个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南京、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都在这一区域内。相应地,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则是指这一地域内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以及台湾等几个地域板块,也可以从时间的角度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但由于论题的需要,这里,我主要从宏观的角度、比较的角度把沦陷区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个总体来进行研究,地域上相对应的国统区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解放区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性质上相对应的抗战文学及其文学理论批评将始终是我们论述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参照系或坐标。上海“孤岛”文学及理论不在此研究范围内,但仍然是我们研究问题的重要背景。
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中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特别是沦陷区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至今几乎还是空白,未见有专著出版和论文发表。其实,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地域上和国统区、解放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是三足鼎立的,在成就上它虽然与后两大地域不可同日而语,但它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客观存在却是不能否定的。据有人统计,不包括台湾在内,沦陷区“沦陷时期出版的作品集在600 种以上,文学刊物(包括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杂志)在150种以上, 有影响的作家有百余人”。[1]这个期刊数肯定是保守的。又据有人统计, “华东沦陷区的文艺和以文艺为主的期刊”仅查到的就有304个, 这里所谓“华东”是一个区域概念,包括上海“孤岛”和台湾,其中“孤岛”的期刊有一百多种,“为整个上海沦陷期间文艺杂志的半数”,“‘孤岛’之外上海沦陷时期以文艺为主的杂志也有百余种。”[2] 而华北沦陷时期以文艺为主的期刊有177种,其中文艺期刊82种。[3]再加上东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的文艺和以文艺为主的期刊,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众多的文艺和以文艺为主的期刊,充分说明了沦陷区的文学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研究和评价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有意耸人听闻地夸大它,象美国有学者“认为1937年至1945年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是产生在沦陷区的作品”,[4]这是错误的。 但完全漠视它,甚至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有意地贬低它,也是不正确、不公正、不客观的。研究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既要看到它的绝对历史维度上的不足,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沦陷区的成就和影响都绝对性地不大,但同时也要看到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要看到它相对性的成就。抗战期间,除了象周作人这样的极少数名作家还滞留在沦陷区以外,当时比较有名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撤退到了后方,留在沦陷区的大多是一些“文学青年”和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可以说,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是在文化“大逃亡”之后的文化荒地上重建起来的,最后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应该说相当的不易。同时,我们还应该特别考虑到沦陷区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国人民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下,其生存环境是异常严峻的,文化在铁蹄下苦苦挣扎,其情形可以想见是何等的艰难。文学和文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它处处受到压抑和限制,不可能产生鲁迅那样的民族魂似的大师级作家和理论家,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有人所说,沦陷区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5]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两大标准来评论和研究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对于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民族标准应该是第一标准,在异族的军事、政治、经济的高压统治下,文学仍然保持民族的血脉,仍然保持民族的文学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具有民族的特色,无论是用长远的历史尺度还是用短期的政治功效尺度来衡量,都是值得肯定的。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置生命于度外,勇敢地和侵略者进行抗争,这固然是英雄,值得钦佩和敬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心理上的不屈服,以保持民族特色作反抗,这却是普遍的方式,也是比较现实的方式,这同样是值得肯定的。在沦陷这种特定的背景下,逃避也是一种反抗。政治的标准绝对是需要的,对于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敌人,卖国求荣的汉奸文学和文学理论,无论它多么有艺术性和理论的深度,都是不可能令国人原谅的,这是全世界的共同标准。但对于沦陷区和后方,显然不能用同一个政治标准。对于后方来说,抗日是一般的标准,而对于沦陷区来说,就是高标准了,所以,同样是抗日,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与文学理论比后方的抗日文学和文学理论更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
1937年至1945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在文学和文学理论上,抗战显然是非常显著的特点,也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但这时的文学显然不只是抗战。不论是在解放区、国统区还是沦陷区,都存在着“与抗战无关”或者与抗战没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抗战期间,三大地域的最高文学成就恰恰都不是抗战文学,解放区的最高文学成就是工农兵文学;国统区的最高文学成就是讽刺文学、暴露文学的“七月派”文学;沦陷区的最高文学成就是乡土文学、讽刺文学、洋场文学。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作家主要有赵树理、艾青、张天翼、沙汀、艾芜、路翎、张爱玲、钱钟书等,这些人显然都不是因为抗战文学(狭义)而成名的。具体对于沦陷区文学,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既有抗战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有非抗战文学和文学理论。
大致来说,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和特点:
一、旗帜鲜明的抗战文学在沦陷区是存在的,比如程造之的长篇小说《地下》,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水浒》,但这毕竟不是沦陷区普遍的文学现象。同样是抗日文学,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不同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抗日文学,它不是直接的,不表现在激烈的言辞上,没有明显的愤激的情绪,而是曲折的、深沉的、内在的抗争。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在沦陷区文学中)“同敌伪统治直接对抗的逆鳞之作并不多见,而大多数采取曲折的抗争方式。……较多的作品致力于‘心理的抵抗’的开掘或描写种种蕴含着民族复苏生机的传统民风,其中潜行着某种民族正气。……‘隐忍’、‘深藏’也成为相当多作品的特色,表面似乎对现实统治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实际上深藏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反抗,对现实的愤愤不平。”[6] 比如广泛盛行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上的“乡土文学”,就是通过对祖国风俗民情的真实描写,通过对民族性、国民性的发掘和高扬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文学,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忧虑,从而具有抵抗的性质。
在沦陷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文学抵抗”的就更少。在日本帝国主义文化高压统治之下,整个沦陷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表现得非常惨淡和萧条,因为比起创作来,理论更缺乏含蓄和隐讳的特点,所以直接提出文学的抗日就更具有生存的困难、更冒险、更缺乏可能性。因此,和文学上的曲折抗日一样,沦陷区的抗日文学理论也表现出一种深藏和内在的特点,它主要通过提倡民族性、现实性、国民性来抵抗异族统治和异族的文化渗透与侵略。倡导“乡土文学”,强调坚持五四新文学传统和保持传统民族文学的血脉,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等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特征的表现。
二、汉奸文学及其理论则是沦陷区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一个独特现象。什么是汉奸文学?毛泽东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汉奸文艺。”[7]这其实还比较笼统, 不能算作是对汉奸文学的定义,比如周作人,他作为汉奸是确凿无疑的,但他在当汉奸时写的文学是否就是汉奸文学,显然还是有争议的。我认为,所谓汉奸文学,是指中国人写的,配合异族的政治、文化侵略的,出卖民族利益的文学,比如1934年东北出版的剧本《王道光》、1943 年1月在北京出版的配合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征文集《短篇小说展览会杰作集》、1942年3月武汉出版的剧本《三个方向》、 1943年7月广东出版的《和平剧集第一集》、1944年4月蒙古自治邦政府弘报局出版的《适用剧本第三集》(内收《感谢皇军》、《八路军的丑恶》等剧)等是典型的汉奸文学。在沦陷区,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策划、操纵、强制推行、压迫、引诱下,汉奸文学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成为一种思潮或运动,这是客观存在,虽然我们今天极不情愿承认这一事实。在沦陷区,上有汪伪政府,下有汉奸团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汉奸机制,有汉奸思想,有汉奸运动。在文学上,有汉奸文人、汉奸文艺杂志、汉奸文学团体、汉奸文学理论,还有所谓“年会”、“纪念会”、“座谈会”、“有奖征文”等,汉奸文学及其理论可以说有声有色,是一种带有普遍性运动或思潮。
汉奸文学在理论上主要是所谓“和平文学”和“大东亚文学”。“和平文学”在理论上主张用文学来宣传和平思想,使文学“透过了和平、反共、建国的理论”,“替和平运动,定更良好的根基”。[8] “大东亚文学”理论是“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政治理论的派生物,它主张整个大东亚文学为一个整体,而日本则是这个东亚一体的霸主,宣传只有以“先进”的日本为领袖,才能“复兴中国”,“建设东亚”。在内容上要求文学为“大东亚战争”服务,宣传所谓“共存共荣”的思想,美化日本侵略行径,反共,煽动中国人仇视英美。由伪新民会主办的《新民报》宣称其刊物和宗旨是:“欲于唇口笔墨之微力,促成今日东亚之伟大的建设事业,扫荡现在残余之共党,排斥世界两大恶魔: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9] 周作人说:“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没有第二条,这与新中国之复兴走的是同一条路。……文学是文化的一部门,文化的进路不能与政治分歧,那么文学也是如此。”[10]周作人的文章写得很恍惚,但意思还是看得出来的。把文学和法西斯政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是“大东亚文学”理论的最本质特征。上面所提到的剧本《王道光》可以说是体现这种汉奸文学理论的“典范”作品,它写一个叫田元良的农民,因为躲债上山当了土匪,几年后他下山看妻儿,发现他的家乡在日本人的“王道”治理下变得非常美好,人人快乐幸福,简直就是天国,他非常感动与感激,于是下定决心做良民。
汉奸文学理论以“和平”为幌子,泯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识,而又以“复兴”“繁荣”为诱导,号召中国人民进行“大东亚战争”,完全是颠倒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是强盗逻辑。但它当时却迷惑了很多人,包括很多文学青年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以,研究沦陷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汉奸文学运动与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能忽视的。
三、乡土文学及其理论是沦陷区在特定环境下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沦陷区的乡土文学最早开始于台湾,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东北和华北盛行,形成一股潮流,代表作家有赖和、钟理和、疑迟、山丁、秋萤、黄军、范紫、关永吉、马骊等。中国现代文学的“乡土小说”是由鲁迅首开风气的,它在二十年代形成为一种文学潮流。但二十年代的中国乡土小说主要是一种艺术上的探索和题材上的开掘,而沦陷区的乡土文学则不同,它除了艺术和题材的意义以外,还有一层明显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政治色彩。赖和的乡土文学其目的就与日本的“皇民文学”分庭抗争。东北沦陷区,山丁和秋萤在1937年系统地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要写出“我们一大部分人的现实生活,我们的乡土”,[11]要“暴露乡土现实”,写“平凡的市镇和平凡的乡下”,[12]“能使我们嗅到强烈的土巴味”,[13]其意在于抗衡日人的“移植文学”理论。乡土文学理论还提倡“描写真实”。联系沦陷区的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日伪提倡粉饰现实阿谀“太平”的特殊文学背景,我们可以看到,山丁等人提出“乡土文学”理论,具有明显的民族对抗意识,它以“暴露现实”对抗“粉饰现实”,以浓郁的乡土色彩高扬民族意识。
乡土文学理论的反抗性在华北沦陷区关永吉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关永吉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独自的国土(地理环境),独自的语言、习俗、历史,和独自的社会制度。由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条件限制着的作家,他在这国土、语言、习俗、历史和社会制度中间生活发展,其生活发展的具象,自然有一种特征。把握了这特征的作品,就可以说是‘乡土文学’。”[14]之所以提倡乡土文学,关永吉说:“我们要把今日地方的文坛活动归复于主流,而且使之健康发展,所以在题材上提出‘乡土文学’,求其扩展视野,抓取现实。此处之所谓‘乡土’,并非单纯的农村之谓,乃是说的‘我乡我土’。”[15]这里,意思比较明确,“乡土文学”既是从文学上的复兴的考虑,但同时也是从政治上的抵抗的考虑,关永吉后来说得更清楚:“我们提出‘乡土文学’的要求,其动机和企图,是认为‘乡土文学’是克服今日文坛堕落倾向的唯一武器,才拿这武器来引导今日的新文学运动,复归于历史的主流。……我们所需要的‘乡土文学’,是要正确的认识现实,把握现实,而且在形式和内容上,要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和具备民族底的与国民底的性格。”[16]国民性、民族性、现实性,这几乎就是乡土文学的代名词。林榕说:乡土文学“最重要的是国民性和民族性两点。国民性是由一个国家传统的风俗习惯而来,民族性是由种族历史的进展而获得”。[17]从这些论述来看,沦陷区的乡土文学理论不仅仅只是继承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人乡土文学理论的传统,同时还在内容上有所丰富、深化和发展,这是沦陷区的文学理论的重要成就之一。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沦陷区的乡土文学理论表明的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政治、文化处境的反抗意识,隐含着民族主义立场,具有抵抗性质。
四、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是沦陷区文学理论很重要的内容。在沦陷区,除了汉奸文学是虚假的伪浪漫主义以外,其它文学都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的特征,“乡土文学”是这样,抗日文学是这样,都市文学是这样,就是同现实政治比较“疏离”的“纯情”文学、洋场文学、通俗文学等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比如钱钟书对知识分子心理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张爱玲对中产阶级生活和心理的细致的刻画和描写,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封建性生活的反映,予且对爱情婚姻生活的解剖,苏青对“现代”家庭日常生活特别是家庭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反映与剖析,等等,都显然属于现实主义的。就是一向沉溺于才子佳人、打斗豪侠等虚幻世界的言情、武打文学,在沦陷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也失去了往昔的那种悠闲和轻松,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现实主义特征。比如一向以商业趣味迎合读者、逃避现实的“鸳鸯派”这时也开始面对现实,“鸳鸯派”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周瘦鹃1943年重新创办《紫罗兰》通俗文学月刊,在创刊号的《写在〈紫罗兰〉前头》一文中声言该刊的原则是“趣味与意义兼顾”。[18]在第8 期则进一步声明:“这些年来,兵连祸结,天天老是在生活线下挣扎着,哪里有这闲情逸致侈谈恋爱呢?”因而强调“态度严肃,并且一些没有肉麻的意味”。[19]事实上也是,比起从前,这时的《紫罗兰》其大多数作品明显地比较贴近生活,比较注意把审美趣味和特定的时代文化内涵和心理特征结合起来。
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之一,也是五四文学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在理论上,经过茅盾等人的建树,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抗战之前就已经非常成熟,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高峰。所以,在理论上,沦陷区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也很难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它主要是如何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并把它贯彻到创作中去的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在沦陷区,现实主义具有双重意义:既有文学理论上的进步的意义,也有政治上的抵抗的意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一切进步文学的共同点,只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就必然勇于面对现实从而反映和表现现实,具体于沦陷区,只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就必然要反映日本侵略军的统治暴行,就必然要反映沦陷区人民在铁蹄下挣扎的残酷与困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胜利”。(注: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页461—463。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有偏见,但他严格地遵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是第一方面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在沦陷区提倡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又有一种对日伪反动文学理论的抵抗的意味。关沫南说:“新的文学之创造的美学基础,是站在社会现实的生活上,积极地发掘我们的现实,以忠实的美学观点,来忠实的观看人生,忠实的描写生活。”[20]“真的文章”要由“真的生活者”来写。[21]又说:“只一味地写‘感谢情调’的赞歌”的“国策文学”是“最卑劣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上所最唾弃的”。[22]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其政治色彩也是很明显的。
五、洋场文学、都市文学、幽默和讽刺文学等同时代、现实比较“疏离”的文学是沦陷区最有特色、也是最有成就的文学。我们之所以认为,在同一时期,沦陷区文学可以和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鼎足而立,其最大的理由就是有这些文学作为根据。钱钟书、张爱玲、师陀、苏青、张秀亚、杨绛、李健吾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他们以其作品而名垂中国现代文学史,缺少了这些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不全面的,也是缺少一些色彩的。
总的来说,这类作品在艺术上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唯美主义、趣味性、富于诗意与哲理,面对现实但却避开敏感的政治问题,而多写爱情、婚姻、家庭,主要在人情、人性、人的心理等方面进行深层的挖掘与表现。比如华北沦陷后第一个纯文艺刊物《朔风》明确表示“不谈政治时事”,除“向中上阶级供给一些精神的粮食”外,“毫无其他作用”。[23]与《朔风》约略同时的文艺性刊物《沙漠画报》也公开申明:“惟以趣味为主且请勿伤大雅,含政治色彩者,希勿见惠。”[24]当时华北沦陷区影响最大的刊物《中国文艺》则标榜“坦白性和纯洁性”,明确宣称不刊载“含有某种宣传作用的东西”。[25]华东沦陷区的文学的这种特点更明显,苏青说:“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齐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26]具体地,张爱玲、苏青主要追求日常生活的情趣,爵青、袁犀主要是表现人生的哲理,关注人的生存、人的心理结构、人的本能等问题,杨绛的喜剧则在轻松幽默的背后深刻地表现出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等等。
我认为,沦陷区文学的这种特点,既是作家在艺术上的自由的选择,同时也是作家们在现实政治环境的重压下的不得已的一种自我保护之计。比如华北沦陷区的文学在散文上特别活跃,这除了一些艺术的原因以外,其实,也有一些特殊环境逼迫的意味,有人说:“散文随笔的范围较广,所写的内容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包。同时,以个人生活为主,不至于牵涉到另外的事情;写的是自己生活中的琐事,用不着担心意外的麻烦。”[27]所谓“意外的麻烦”,其意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避世倾向、唯美主义、世俗化、个性化、追求纯艺术,沦陷区文学在艺术上意想不到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无法在思想上、在重大社会事件上有所作为时,他们便躲进“象牙之塔”,主要在艺术技巧上,在人情世态上,在日常生活上,在一些中性的题材上有所突破、开拓、发掘和贡献,因此,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都具有某种恒久性,这正是他们在艺术上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沦陷区的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子,这是被迫和无奈,但却正好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和中国现代政治紧密地连在一起,沦陷区的文学被迫与政治疏离,而在爱情、婚姻等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等这些所谓“永恒”的题材和主题上进行开掘,正好填补了五四新文学的一些空白。时过境迁,当民族仇恨的切身感受被疏远、这些作品的写作背景被淡化之后,重读这些作品,其艺术技巧上的娴熟、精巧、完美,真是让人感到震惊。当时,这些作品是人们茶余饭后的很好的消遣,今天,它们仍然是人们茶余饭后的很好的消遣。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地在这个领域有新的“发现”,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其实,与其说是“重新发现”,还不如说是被“遮敝”了。
收稿日期:1999—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