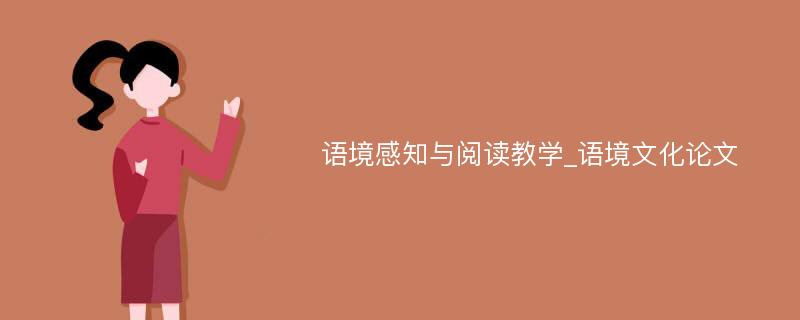
语境体察与阅读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阅读教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阅读教学,特别是现代文的阅读教学,成了语文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总学时中,阅读教学占的比重最大,然而,教学效果总不能尽如人意。学生对文中基本语义的正确理解尚且不能完全做到,更谈不上对一些美文有所鉴赏与品评了。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语文教师的忧虑。怎么办?我们以为,在阅读教学中注重语境的分析和体察,是提高学生阅读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那么,怎样体认各种语境形式,让学生较多地接触在语境中变化多端的活的语言,以提高阅读教学的效果?我们以为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着手。
1.调动语境的背景知识,体味语词的深层含义。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来,学生在进入阅读时,主本心理上已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这种图式,有人称为阅读的“前结构”。“前结构”由“前有”、“前识”和“前设”三方面构成,“前有”指预先有的文化习惯,“前识”是预先有的知识系统,“前设”即预先作的假设。这三者结合成为理解活动赖以发生的前提条件。课本中各类文章的语境酿造,常常是“在言语的经验之内留连”,(柏克语)语词的语义“不是通过它们固有的价值,而是通过它们相对的位置”(索绪尔语)而起作用的,所以,许多文章的语境都呈现为“经验语境”,包括生活经验的积累,文化视野的扩展,知识网络的构建,等等。这些内容正包含在阅读的“前结构”中。如果缺乏主体上的这种理解的心理图式,对文中的许多隐含内容或深层语义就无法理解。因此,扩展学生对语境背景的有关知识,充实阅读“前结构”的固有模式,才可能迅速提高他们对语词深层含义的解读能力。比如,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的开头说: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开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这段文字最后用了“标致”一词,作为语篇的终结。在词典里,“标致”的语义是确定的,它形容相貌、姿态美丽(多用于女子),是褒义词。如果学生的阅读“前结构”中缺乏相关的知识,这个词的语境义无法体认,更不能领会作家运用所表达的特殊感情了。在理解上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用褒义词赞扬清国留学生的丑恶姿态与灵魂,明显地违背话语中心,系语词误用:二是以男为女,用词不当。如果我们适当扩展一些有关背景知识,就会领悟其深层意蕴。清朝的男人是蓄辫子的,而这些“速成班”的学生因刚到日本,视辫子为国粹,(事实上鲁迅等一批留日学生早就剪掉了辫子)故意招摇,让人望而生厌。而“标致”一词正是在这种“言语的经验之内流连”,故而它就失去了词典意义而呈现出了语境义。在这里,“标致”具有了“令人作呕”的意思。细细体味,就会觉得这个词不仅用得恰当得体,而且更加突现了清国留学生的丑陋、愚昧,表达得幽默、深切,入木三分;作家的悲愤之状也跃然纸上了。
经验语意属于大语境,它很注重表达的具体场合和社会环境。语义的表达也常常因场合、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如果缺乏对它们的了解,有些语境表达就很不容易被理解,这往往构成阅读教学中的难点。正如波兰语义学家沙夫所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随着它所在的那个论域而不同的。……换句话说,被表达物的内容只有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够被理解。”(《语义学·引论》)这里,沙夫显然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语言交际,它的言语义都必须依赖于所在的论域。论域,就是文中隐含的文化积淀和社会时代背景,只有让学生清晰地了解它们,阅读中的难点才会迎刃而解。比如,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有一句:“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句话,长期以来成为这篇精美散文阅读的难解之谜。为什么月色朦胧、荷香四溢的幽静空翠之夜会令作家突然“惦着江南”?文中用“到底”一词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时常困扰着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只要弄清文章的有关背景,也就是这句话所在的“论域”,就能体味出它所释放出来的许多美趣。如所周知,这篇散文是抒写作者心境的一个名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作家在起首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中点出全文之旨。接着,作家宕开笔墨,用小路的“静”,荷塘景色“静”,月色空朦的“静”,引出苛塘四周蝉声和蛙鸣的“闹”。以此引发,联想到江南采莲的旧俗,梁元帝的《采莲赋》和《西洲曲》关于采莲的热闹、嬉戏的情景。这个“闹”,才是作家刻意经营的重心,“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中的“到底”一语正是点睛之笔,它含蓄地提示了“心里颇不宁静”的原因。为什么?因为江南时期的朱自清,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曾经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战斗过,呼唤过;然而,大革命失败以后,严酷的斗争现实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以致于“心里颇不宁静”。从表面上看,作品处处扣住一个“静”字,从各个侧面,用各种手法描写、渲染荷塘的“静”;实质上,作家所着力表现的却是“闹”,突出作家心中的喧哗与骚动。这一点,只有从语境的背景知识中才能领悟到,否则,以“静”为脉,那就不但对“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无法理解,而且就连“心里颇不宁静”以及采莲热闹场面的语境酿造也会认为是冗赘之笔了。2.寻绎语境的语篇联系,品赏文意的弦外之音。
一些语用学家指出,语境的酿造是以语篇为基础的,一定的言语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语篇之中,语篇的含义依赖于语境,而语境的生存空间却是语篇;它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语篇,通常指一系列连续的话段或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语篇的重要特征就是衔接和连贯,衔接体现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上,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的使用,都可以表现结构上的粘着性,它是语篇的有形网络;连贯性指的是语义的关联,连贯存在于语篇的底层,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它是语篇的无形网络。有许多语境的酿造,就是靠语篇的这种无形网络来完成的,因而造成阅读上的因难,成为教学中的难点。它,只有靠寻找语境的辣篇联系来解决。比如《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写贾母询及黛玉念书的情节时,这样写:
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只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姐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的是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
可是到宝玉问到黛玉读书的情况时,作家又这样写:
宝玉便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
上面两段话中,问的内容大致相同,而黛玉的答语却迥然各异,这是为什么?是作家一时疏忽,前言不搭后语,还是黛玉性格轻浮,前后判若两人?学生在阅读中,一时很难弄清。其实,只要我们从语篇的连贯网络中去找答案,就会觉得这两段在特定语境中的答案妙不可言。这篇文字是写黛玉初次出场,作家意在表现她细心多虑的性格特征和自尊自重的情感姿质。作家在本篇开端就有一段叙述:
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过,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去。
这段话正是黛玉答语构成不同语境的语篇网络。作家也是运用这些语境的细微变异,充分展示人物“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情状和心态,曲曲传出黛玉“惟恐被人耻笑”的细心多虑和自尊自贵的情感指征的。其实,黛玉回答贾母的话语已经很简短,也很拘谨,的确没有“轻易多说一句话”。然而,当她听到贾母的话后,也许自悔失言(女子无才便是德),很敏捷地觉察出这样的答语不够得体。所以,当宝玉再次问到读书的情况时,她作了较大的改变。这样一来,两段答语构成了语境的逆向撞击,显得格外耐人寻味。作家的艺术匠心和语言造诣确乎达到了极致。
的确,作为一个表示整体意义的语篇,语境的直向性总受到语法或逻辑的制约,这为我们在阅读中准确理解文意或品赏话语的弦外之音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这种方法,在品味隐语境所表达的情感信息时尤为重要。一般说来,隐语境对于情感的传达在语篇上没有明显的语义连贯标志,在语言的选择上,言语义更加偏向语言义的变异或再造,形成一种“意指错位”的表现效果。因此,可以这样说,隐语境乃是有意制造语符的表层义与内含义的矛盾状态,在语义的反差中透露一种情感经验或逻辑暗示。这样,阅读中容易造成不可名状的困惑状态。比如,孙犁在《荷花淀》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听说他产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孙犁笔下所展现的是几个深明大义而又挚爱自己丈夫的青年妇女的心境情态。其中,特别是那位声称“有什么看头啊”的年轻女人正用一种“反差语”揭示了她急于想再看看丈夫的情状心态。可是,作家在文中用的是语词的语言义,说的是女人们“不想见到自己的丈夫”,这种“反差语”从何而来?这就必须寻绎语境在语篇中的逻辑暗示,那就是作家在开头设置的大前提:“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语篇在这句话的语境暗示中,话语的言语义出现了对语言义的偏离、错位,“反差语”的弦外之音悠然而现,一个时时想见到丈夫而又羞于启齿的青年妇女的情貌神态毕现于纸上。语境体察的结果会使我们真正领略到暗含于字里行间的充满了艺术张力的情感信息。
